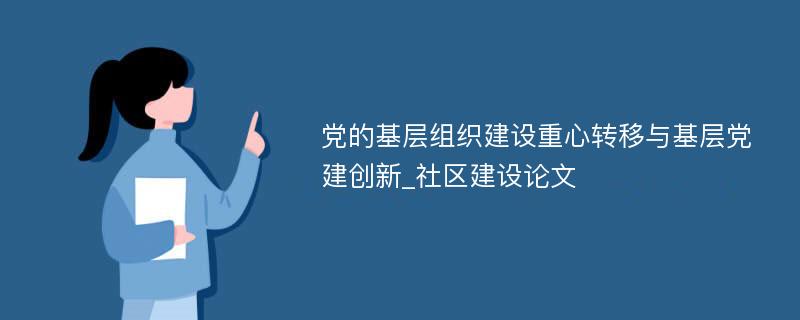
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心转移与基层党建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重心论文,基层论文,党的基层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6)01-0016-04
基层组织建设的状况关系党的战斗力,党如何根据单位制式微、城市社区① 兴起的新情况,实现基层组织建设重心从单位党建向社区党建的战略性转移,并实现对基层党建的创新,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区的兴起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心转移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又取决于其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契合程度。自“三湾改编”始,党在人民军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组织建设原则。由于党的组织结构与人民军队的组织结构相契合,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在执政后逐渐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在各基层组织建立了党支部。在城市,便是把支部建在了单位和街道,并以单位党建作为基层组织建设重心,街道党建处于从属地位。这一设计是与计划经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相契合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资源并通过单位来分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附属于某一固定单位,只有少数不能为单位所覆盖的社会成员由街道负责。由此,整个城市社会结构由单位社会和地方(街道)社会两部分组成,单位无疑成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对社会进行整合。党又在单位中建立了自身组织系统,整个社会实际形成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的单位制社会结构。由此,党获得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动员能力。单位党建控制了绝大多数政治资源,也成为党从社会汲取政治资源的主要途径,街道党建只是在剩余空间起拾遗补缺的作用。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给社会带来了全方位冲击。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大大减弱,个人也不必必须附属于某一固定单位,社会成员获得了越来越广的个人权利空间,社区蓬勃发展起来。毫无疑问,社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与西方在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还带有更多“行政化”色彩,以至于有人称它不过是政府的“翻牌”。但所有人都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它将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成为社会个体生活、主张权利的最主要空间。党要继续保持对社会的强大领导能力,永葆执政地位的永固,就必须富有前瞻性地意识到未来党进行社会整合的主要方式将不再是通过单位而是社区,党摄取政治资源,争取群众支持的主要基地也不再是单位而是社区。由此决定了党要有效整合社会并为长期执政赢得雄厚的社会基础,党的建设就必须实现战略性转移,即将自身生长和活动的主要空间从单位移向社区,以社区为主要空间,组织党员、发展党员、动员社会和整合社会[1] 11。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要求党在继续加强单位党建的同时,逐渐将基层党建的重心向社区党建转移。加强社区党建决非权宜之计。社区党建所承载的不仅是党的自我完善,更重要的是在新型社会结构中,党如何永葆执政合法性,拥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这一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任务:第一,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其同社会结构间保持内在契合,保证党的基层组织的生命力、战斗力。第二,在社区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吸纳新党员,有助于扩大党的队伍,夯实党的基层组织。第三,有利于永葆执政合法性。执政合法性中最根本的是“人民同意”。党在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具有了强大的执政合法性,又在领导建设和改革的事业中增进了执政合法性。但是由历史形成的合法性重要却不是唯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形成的绩效合法性边际效应又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递减趋势。党在加强社区党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社区这一载体整合社会,更好的发挥政党的利益综合、利益表达功能,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第四,社区是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会矛盾的聚集区,在社区开展党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党察觉社会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略,矛盾的化解又有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第五,进行社区党建,使党员干部直接面向群众,接受群众教育、监督,并能不断吸纳社会精英,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
二、社区党建与社区发展的互动双赢
顺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党必须将基层组织建设重心由单位向社区转移,社区将逐渐成为党的基层组织活动的最重要空间,成为党进行政治整合和政治动员、凝聚群众、巩固执政社会基础的新的也是最具战略性的阵地依托。因而,社区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社区自身的发展,还意味着扎根于社区的党自身建设空间的扩展。反过来,社区发展也离不开党的作用。社区将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发展了的社区又有利于党组织的壮大,壮大了的党又能更好地领导社区发展。因而,社区党建和社区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互动双赢。作为身兼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党的自身现代化重任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实现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双赢为目标,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然而,理论界有关社区发展的理论设计中,党常常成为一个不该缺席的“缺席者”。有人认为社区在本质上是自治的,政府、政党在其中发挥作用会危及其自治性。有的人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的社区自治模式,却避而不谈党的作用。实际上,在社区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党的作用无时无处不在。我们也很难想像中国可以在党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论社区自治,单纯依靠社区自治的力量推动社区发展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中国城市社区就是在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整合的客观需要,及在为满足社会上述需要而由党和政府所大力提倡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中发展起来的,这与西方社区主要是自发形成有很大不同。而那种单纯强调政府作用,不讲党的作用的观点既不符合社区发展的历史,也在实际中行不通。在注意到中国社会自治功能不足,不得不需要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党是社区建设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方面,政府就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保证社区发展正确方向和持续动力的必备条件。从长远看,为避免因过多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而使社区自治重蹈居委会一度过度“行政化”的覆辙,政府在社区的作用将越来越小,会有计划的退缩。在政府力量逐渐相对退缩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依靠日益壮大起来的社会自治力量推动社区发展,同时,国家也有必要通过加强党对社区的参与和领导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依靠政党的力量推动社区发展比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更有优势,更符合其自治的本质。
政府是一种外在于社区的力量,它对社区建设的推动,凭借的是行政力量,这往往会抑止社区自治因素的发展。政党不仅具有政治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2] 158。建在社区的党组织,通过推动社区发展为党聚拢政治资源、进行政治整合,并不会产生社区自治的异己力量。因为社区党组织是内在于社区的,其党员都是社区居民。政党组织对社区建设的介入,同时意味着社区内党员居民的政治参与。党员的社区建设参与能力的提高,就是社区居民社区建设参与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党组织对居民区党员的动员,并不依赖物质力量或行政权力,而是党组织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资源。实际上,党员个人对社区自治的参与,往往会起到榜样、示范效应。一个党员居民可带动其家庭乃至左邻右舍对社区自治的参与,从而逐渐扩大政治参与面[3] 65-66,使政党借以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动员。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有效承担起这一职责的政党组织惟有中国共产党。
相对于其它国家的政党或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具有在尊重社区自治规律基础上,推动社区建设的诸多优势:第一,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没有任何私利。这决定了她能超越社区内各种带有私利性的异质化要求,协调各种矛盾,保证社区稳定、有序发展。第二,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②,比起单纯具有执政功能的一般执政党,不仅因掌握执政权力而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对社区发展予以推动,更能以领导党的身份,通过发挥内在于社区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社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社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第三,党具有高度的源于人民选择的执政合法性,这是党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政治优势。第四,党的群众工作优势与社会动员的要求相契合[2] 162。通过行政力量的动员,往往使居民参与具有被动性色彩,而以说服教育等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使居民主动、自愿参加社区建设较行政的动员方式更具优势。群众工作恰是党的优良传统,拥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发挥党的这一优良传统,用社区党组织、党员耐心细致的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能有效引导居民群众主动、自愿参加到社区建设中来。第五,党具有庞大的组织体系,拥有近7000万名党员,遍布城乡社区。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将其投入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无疑将发挥难以估量的效用。
三、社区党建对城市基层党建的创新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心由单位向社区转移,要求我们必须对城市基层党建方式与时俱进地予以创新,以永葆党的战斗力。
第一,观念创新,树立融入社会、发育社会的观念。在传统党建中,党和政府包办了社会,尽管一度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但长此下去,却导致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悖论,即国家管辖范围非常宽泛,但国家实际渗透社会的能力软弱。同时,社会肌体发育不全,社会组织功能萎缩,反过来又成为国家强化对社会控制的理由,进一步扼制社会发育,形成恶性循环。要充分认识到,党组织只有在尊重社会运行规律基础之上发育社会,才能融入社会、领导社会。发育社会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培育独立的市场主体,依法支持居民自治。党要首先自觉定位于社会发育的积极参与者、服务社会的政治力量,通过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方向保证功能、党员的榜样示范效应、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等方面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
第二,党的功能重新定位,由高度行政化的功能定位转向高度政党化的功能定位[1]。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原理,政党是联结民众与国家政权的纽带。在政治过程中,政党实际上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沟通社会与国家政权的桥梁;另一方面,它是社会控制国家政权之手的延伸。政党基层组织担负着反映民意、服务社会、凝聚民心、动员社会的职责。中国共产党同一切政党一样,都必须遵循执政规律,负起政党的职责。作为在社区的基层党组织,要摈弃传统基层组织包办一切社会事物的行政化定位,实现“党要回党”,时刻关心、代表、综合社区居民利益,将居民要求及时注入政治体系之中,从而在赢得民众的信赖基础上,真正成为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的政治核心。
第三,领导方式的创新。1.依法执政。在传统单位党建中,虽有依法执政的要求,但单位的主体性不明显。而在社区党建中,社区居民、各种新生组织主体性很强。一旦社区党建的某些做法损及其主体性,会激发其法律回应。2.社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平等性,在社区自治过程中,不能再重复传统单位党建中党发号施令那一套,而必须发扬民主。3.社区的自治性,要求党从以强调纪律使单位成员服从党组织,转到社区党建的坚持被领导者自愿、服从基础上来[4]。4.传统党建,经常抽象强调党的政治性。社区党建中,党的政治性要融于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之中,党组织尤其要重视在社会公益性活动中发挥作用,借以赢得民众对党的认可。
第四,活动范围的扩展,从“剩余空间”到社区全部空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党建控制了绝大多数政治资源,街道党建只是在剩余空间内活动。社区党建与街道党建有历史承接性,但并非同一事物。社区党建活动的范围不再是“剩余空间”,而是覆盖整个社区方方面面的“区域性”党建工作。它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总支为基础,以社区所有党员为主体,调动驻社区所有单位党组织的积极性,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发展。这就需要向社区党建注入大量党建资源,改变条强块弱的党建格局,使社区党建与单位党建都获得巨大发展。
第五,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传统的基层党组织按照生产和地区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有党员三人以上即可建立党支部。该方式的前提条件是:组织的政治化色彩所决定的高度稳定性;组成人员由生存和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对组织的高度依附性[5]。在市场经济下,传统单位组织日益专业化,其政治化色彩淡化。新生社会组织往往不带有政治色彩,兼并、破产使其生存状态多不稳定。大量社会成员脱离了原单位组织变为社会人,许多党员游离于单位之外,大量农村党员涌进城市,成为“口袋党员”,出现了党员找不到党组织和党组织找不到党员的现象。在社区中涌现的众多新社会组织,多是党的工作的空白点。种种情况表明,必须探索新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实践中出现了“属地化”党建模式的探索,即“以地域为载体,以社区为依托,设立党的基层组织,统一管理社区内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党员的现代党组织设置方式和党员队伍管理模式。”[6] 在社区各类新生组织中的“建党”工作中,各地因地制宜,创造出不少新鲜方式。如凡有党员三人以上的设支部,三人以下的,可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原则,建立联合党组织。没有党员的,建立党建工作联络员制度,积极发展党员,等。如何在党章范围内,结合新的实际,积极有效的建立社区党组织,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深入探讨。
注释:
①社区可以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种,二者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应,城市社区党建与农村社区党建也各有特点。本文所讲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均指城市社区和城市社区党建。
②执政和领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广义上的领导包括执政,这里所讲的领导是狭义上的领导,不包括执政党的通过党的代表控制国家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执政。
标签:社区建设论文; 党的基层组织论文; 社区自治论文; 政治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居民自治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时政论文; 党组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