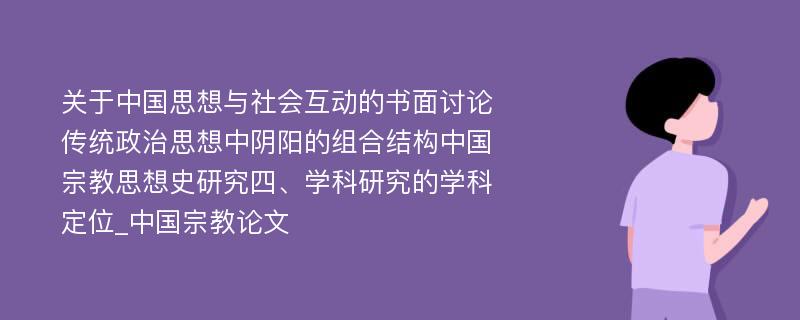
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笔谈——1.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2.关于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3.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4.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5.“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想论文,组合论文,笔谈论文,互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KO,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5—0033—20
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
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混沌”,吕思勉先生在《文史通义评》中曾有论述。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文中指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其缺陷之一就是“混沌思维”。所谓“混沌”,就是思想概念、范畴的界定与运用,没有严密的区分。对这种现象中外学者都有过论述。
说混沌,其实也不是混沌一片,细分还是有其理路的,至少在政治思想中是如此。其理路就是阴阳组合结构。多年以前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其学理上是很难找出理论元点的,各种理论命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以往我们有时称之为‘混沌性’,有时称之为‘阴阳结构’,有时称之为‘主辅组合命题’等。”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说“混沌”还只是表征,尚待更深入分析。于是提出了“阴阳结构”,“阴阳组合命题”或“主辅组合命题”。
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我们的先哲几乎都不从一个理论元点来推导自己的理论,而是在“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思维和阐明道理。这里不妨先开列一些具体的阴阳组合命题,诸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民本与君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等级与均平;纳谏(听众)与独断;思想一统与人各有志;教化与愚民;王遵礼法与王制礼法;民为衣食父母与皇恩浩荡、仰上而生……我开列了这一大串,为了说明这种组合命题的普遍性。这里用了“阴阳组合结构”,而不用对立统一,是有用意的。在上述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 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因此阴阳组合结构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两者不是等同的。我上边罗列的各个命题,都是阴阳组合关系,主辅不能错位。比如在君本与民本这对阴阳组合命题中,君本与民本互相依存,谈到君本一定要说民本;同样,谈到民本也离不开君本,但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下边就两个组合命题稍作说明,以示其概。
先说“道高于君与君主体道”的组合。“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是理性(也包含程度不同的神性)的最高抽象,又是整个思想文化的命脉。
“王”是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同时又代表着以专制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以及与这种秩序相对应的观念体系。
道与王是什么关系?就我拜读过的论著,特别是新儒家,十分强调儒家的道与王是二分的,常常把“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作为理论元点来进行推理,认定道是社会的独立的理性系统,由儒生操握,对王起着规范、牵制和制约作用。就一隅而论,足以成理;然全面考察,则多偏颇。在我看来,道与王的关系是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的有机组合关系,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分合相辅,以合为主。这不限于儒家,而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干。
“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只是组合命题一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这就是“君主体道”、“王、道同体”、“道出于王”。
先秦诸子把圣人、君子视为道之原,同时又认为先王、圣王也是道之原。在这一点上先秦诸子没有分歧,可以说是共识。这一理论为王与道一体化,以及道源于王铺平了道路。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把自己视为与道同体、自己生道的君主。秦始皇宣布自己是“体道行德”,实现了王、道一体化。“体道”这个词最早见于《庄子·知北游》。其后荀子说:“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韩非进一步提出“体道”是君主有国、保身之本。秦始皇的“体道”便是由此而来。秦始皇不仅体道,又是圣王,他颁布的制度、命令是“圣制”、“圣意”、“圣志”,永垂万世。先秦诸子创造的巍巍高尚的“道”一下子变成了秦始皇的囊中之物。秦朝虽然很快垮台了,秦始皇的思想却流传给后世。其后,贾谊提出“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他还有人所熟悉的“王道通三”之说。道、王道、王混为一体,道由王出。于是李觏竟说出这样的话:“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尽管可以把道捧上天,但一遇到“圣旨”,它就得乖乖让路。在漫长的年代里,帝王既要搞朕即国家,又要搞朕即道。
宋、明理学家高扬道统的大旗,道统俨然独立于王之外。然而恰恰在把道统说得神乎其神的同时,却又把这个神圣的道敬献给帝王,这一点在谥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应道”、“法道”、“继道”、“合道”、“同道”、“循道”、“备道”、“建道”、“行道”、“章道”、“弘道”、“体道”、“崇道”、“立道”、“凝道”、“明道”、“达道”、“履道”、“隆道”、“契道”、“阐道”、“守道”等词。汉语词汇实在太丰富了,在这里,都说明一个问题:帝王是道的体现者。
王对道的占有,或者说道依附于王,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几乎所有的思想家,甚至包括一些具有异端性质的人,都没有从“王道”等大框框中走出来。只要还崇拜“王道”等,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被王制和王的观念所锢,而且所说的道也是为王服务的。
其实,王对道的占有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更应注意道本身的王权主义精神。在思想史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们在阐发、高扬“道”的观念过程中,一直向“道”注入王权主义精神。进而言之,道的主旨是王权主义。这一点被我们的许多学者,特别是被新儒学所忽视。只要稍稍留意观察,这一事实应该说是昭然的。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无所不在,千姿百态,但影响最大、最具有普遍性的,要属有关宇宙结构、本体、规律方面的含义了。 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中给予王以特殊的定位。《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交而生万物,而君臣尊卑之位便是宇宙结构和秩序的一环。被形而上学化的伦理纲常的首位就是君主关系。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朱熹说:“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又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儒家所论的伦理纲常无疑比具体的君主更有普遍意义,甚至经常高举纲常的大旗批判某些君主,有时还走到“革命”的地步。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君主制度的否定,恰恰相反,而是从更高的层次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用形而上学论证了君主制度是永恒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的纲常对王的规范和批判意义,同时也不宜忽视这种规范和批判的归结点是对王权制度的肯定。张扬儒学的朋友对此实在有点漠视,或视而不见,真不知其可也!
道、王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是有机组合关系,同时也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从这种范式中走出来。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比具体内容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
再说“民本与君本”的组合。“民本”与“君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两大基点。历代思想家、清醒的帝王和政治家都把“君为民主”与“民惟国本”两大命题相提并论,并在理论上形成稳定的“阴阳组合”结构。
“君为民主”把君奉为政治的最高主宰,这是讲君权的绝对性;“民为国本”承认民之向背对政治兴败具有最终决定作用,这是讲君权的相对性。依照逻辑推理,这两者是不能共容的。如果把“民为国本”视为最高的理论元点,就应否定“君为民主”的思路,进而赋予民众政治权利,以民主方式选举国家元首并设计必要的政治程序以制衡其权力。可惜,中国古代一切民本论者都没能从君为民主、治权在君、君为政本的思路中走出来,从而跃入民主主义范畴。这就注定了“民为国本”命题是“君为民主”命题的附庸,重民的主体是君主,民众只是政治的客体,民是君主施治、教化的对象,其中并没有“民治”的思想。这种“民本论”所导出的仅仅是统治者的得民之道、保民之道、治民之道。民本的最终归宿是实现君本。
“民惟邦本”与“君为政本”,“民贵君轻”与“君尊民卑”,“君以民为本”与“民以君为主”,从平面上看是相对的。如果置入“阴阳结构”中,而两者各得其位,中国古代政治思维巧妙地将二者圆融在同一理论体系之中。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结构注定了民本论同时具有尊君、罪君双重功能。在这个结构中,罪君不是要改革君主制度,而是乞求清明的君主降临人世。
“阴阳组合结构”无疑是我们的概括,但其内容则是古代政治思维的普遍事实,这种结构性的思维应该说是极其高明的,它反映了事务的对立与统一的一个基本面。也可以说是“中庸”、“执两用中”思想的具体化。这种“结构”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路线对把握事务非常有用,也非常聪慧,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曾用“边际平衡”来分析和说明孔子的“中庸”思想,应该说“阴阳组合结构”把“边际平衡”更具体地揭示出来了。就思想来说,这种结构的容量很大,说东有东,说西有西,既可以把君主之尊和伟大捧得比天高,但又可以进谏批评,乃至对桀纣之君进行革命。由于有极大的容量,以至于人们无法从这种结构中跳出来,至少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直到西方新政治思想传入以前,先哲们没有人能突破这种阴阳组合结构。最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虽有过超乎前人的试跳,但终归没有跳过去。
在政治实践上,这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政治理念具有广泛的和切实的应用性。以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为例,一方面它是那样的稳固,不管有多少波澜起伏,多少次改朝换代,这种体制横竖岿然不动;另一方面,它有相当宽的自我调整空间和适应性。我想这些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政治思维的阴阳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调整。
这种思维定式影响至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广泛流行, 依然笼罩着许多人的思维。如果我们不从这种阴阳组合结构中走出来,我们就不可能登上历史的新台阶。
关于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
孙昌武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开展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紧迫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这里所谓“中国宗教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宗教史,也不同于某一中国具体宗教如佛教、道教的思想史,是指历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宗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延伸开来,还应包括历代不同社会阶层认识、对待、处理宗教现象、宗教事务的历史,无神论与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等等。宗教思想乃是整个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巨大的影响,往往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例如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往往是在一定的宗教观念指引下发动起来的;某一朝代统治者的宗教思想决定他们对待宗教的方针、策略,对于历史发展会造成重大影响,等等。一定历史时期的宗教思想又和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史学思想、民族思想等等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至于具体到宗教史研究,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宗教思想指引、规范着人们的宗教活动,制约着宗教的发展。这样,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西方神学家孔汉思(HansKǖng)指出:
今天的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继承普兰克、爱因斯坦和海森堡传统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都在强调分析和综合互补,理性知识和直觉智能互补,科研和伦理互补,也就是科学和宗教互补。(秦嘉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第233页,三联书店,1997年)
这是从维护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肯定宗教在当代的意义的。他说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就是宗教活动仍是当前人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并没有因为知识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而削弱其意义和作用。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类正普遍地被各种新的难题所困扰: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失衡,国家间、民族间以至宗教间相互对抗,社会伦理观和价值观普遍偏失与空洞化,财富积累和集中造成严重社会不公,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着焦灼不安和欲求不满,如此等等,都为宗教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需要与空间。这样,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情怀等等,又为现代人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与巨大作用的精神内容。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活动、宗教信仰呈现活跃形势的重要原因。面对这样的情况,研究历史上中国人的宗教思想,总结其发展规律,明确其经验教训,又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
中国自先民时期即和人类其它文明一样形成宗教思维、宗教信仰,从事活跃的宗教活动。夏鼐指出:
在宗教信仰方面,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当时埋葬死者还随葬着生活用具和饮料食物,以便他们死后仍可享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且(祖)的发现,表明当时有生殖崇拜的习俗……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占卜术,我们在各地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术更为盛行,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字。周代占卜术衰落,但仍有少数占卜的甲骨出土。 战国时代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上的怪兽,是楚人“信巫鬼”的表现。(《敦煌考古漫记》,第14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但是在人类宗教史上,中国宗教的形成、发展又走过特殊的道路,有其独特的形态,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例如就宗教的形成说,按照宗教学的一般定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即所谓“历史宗教”、“教团宗教”或“传播性宗教”形成较迟。外来佛教输入大约在两汉之际,原始教派道教形成是东汉末年。按这种看法,在这之前中华文明有明确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处在宗教“真空”状态。当然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宗教还有不同看法。比如对于殷商以来国家主持的祭祀活动,有的学者就认为是国家宗教的特有形态。但无论看法如何,上古时期中国宗教不同于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形态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思想史上一般把殷、周之际看作是“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士林二》)的转折时期,侯外庐等人所著《中国思想通史》说到周人“政治宗教化”:
由于周人的政治宗教化,在思想意识上便产生了‘礼’。‘礼’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礼器之文为铭文,《书》谓之诰辞,《诗》谓之颂辞,其中所含的意识都表现出政治、道德、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78页)
而钱穆则从另一个角度说:
孔子根据礼意,把古代贵族礼直推演到平民社会上来,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趋向人生伦理化的最后一步骤……因此我们若说中国古代文化进展,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73—74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无论如何做出分析和判断,中国古代宗教观念、宗教思想的内容和形态具有特殊性是可以肯定的。而在佛教输入、道教形成的时期,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强大的专制政治体系,形成具有丰富、优秀的人文理念和理性精神的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此后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重要一点是在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之下,宗教神权必须隶属于世俗政权,宗教活动必然受到世俗政权的支配或限制。又人类文化学总结出一个规律:政治的权威与宗教信仰的绝对性正成反比例。在中国强大的中央专制体制下,宗教信仰心相对地薄弱,而且在多种信仰间游移,不可能确立唯一神的绝对信仰。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多种宗教共存并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宗教势力相对薄弱,对于其发挥社会作用的影响不单纯是负面的。正因为宗教被严格管束在社会体制之内,反而使它们有可能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成为十分活跃的社会力量。这种种状况,造成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宗教观念、宗教思想的复杂性。
在整个人类宗教思想的发展中,中国的宗教思想又具有突出的优长和独特的价值。殷商是中国宗教的草创时期,也是宗教思想的形成时期。胡适曾指出:
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和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
殷商时期宗教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神权信仰奠定在祖先崇拜基础之上,而祖先崇拜的根基在对于先人即“人”的信仰,而不是对于超越的“神”的信仰。“周因于殷礼。”关于周代制度和思想的变革,王国维指出:
……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此非无征之说也,以经证之。《礼经》言治之迹者,但言天子诸侯卿大夫事;而《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 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复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其言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理念,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且其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固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士大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卜由此者,谓之非彝。(《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
这是说周初“制度典礼”转变的核心因素是宗教性的“天命”观念的衰落,相对应的则是人文观念的勃兴。在周初文献里,可以发现当时统治者经常表现对于“天”的权威和“天命”的绝对作用的怀疑,如《康诰》所谓“天畏棐忱”,“惟命不于常”;《君奭》所谓“天不可信”,等等,都鲜明地道出了对于上天的神圣性和绝对性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人”的作用的肯定和重视。如《酒诰》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在春秋时代政治家的诸多言论里,如“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等等,说这些话的,大体是当时居于时代思想前列的政治家,他们在观念里都把“民”放在比“神”更重要的位置上(虽然具体论定“神”的意义和作用不一)。这样,周人所开启的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途径,也就奠定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和理性传统。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全部发展要从先秦寻求源头,那么探讨历史上宗教思想的发展、演变会发现,浓厚的人文色彩、清醒的理性精神一直也是中国宗教思想传统的主要特色之一。从这样的角度讲,中国在人类宗教思想史上更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做出了特殊贡献。
当然,中国宗教发展形态的特殊和复杂,也给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数不尽的难题。首先作为前提的,什么是“宗教思想”,宗教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内容如何,就是亟待明确的问题。又比如前面提到的如何定义宗教,如何定义中国宗教:殷周时期的“敬天法祖”的国家祭祀活动是不是宗教,后来“儒教”是否算宗教,还有极其复杂的民间宗教思想,更是解析十分困难而内容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是对于认真的研究者来说,有待研究课题的艰难正是其魅力之所在。问题越是复杂,问题的意义越是重大,就越是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宗教思想史正是这样的课题。
中国宗教思想史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由于我国宗教学术研究基础薄弱,对于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不能期望急速可以呈功。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资料搜集和分析方面,都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努力,我国的宗教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相信对于开展中国宗教思想史这样的综合课题的研究已经准备了一定条件。现在需要的是有人发愿从事这一工作,并能够持久地做出努力。
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
陈启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
1.小引 最近国内新兴的“科研平台”、“创新基地”的一项任务, 是推动跨学科超领域的科研工作。这是先师钱穆生平治学的旨愿,也是我自己数十年来治学的途径。关于这方面的学理,我发表过一些文章,如:《漫谈历史研究:汉学、史学、社会科学》(《思与言》,第5卷第2期,1967年);《历史与文化、思想与哲学——人文学理论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卷第3期,1994年。修改本:《现代中西文化与文化理论之互动趋向》,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竹企思想文化丛书总序》(1997年,又见武汉大学《人文论丛,1998卷》);《文化传统与现代认知》(《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关于思想文化史研究》(《开放时代》,2003年6月);《钱穆师与中西文化比较》(《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史学集刊》,第4期, 2005年)。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隐》:“案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因应这传统,下文简述一些有关思想与社会的“跨学科与超领域研究”的史学事证。
2.中国传统学术的“跨学科、超领域”本质 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宗师李约瑟(Joseph Need- ham)在《时间与东方人》中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史学)是万学之母(后)”(Time and Eastern Man,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65,P.9)。历史内涵包括“人”的“过去”的一切。其实历史阐述的不止是“过去”,更包括了“现在”、“当下”。“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者强调过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现在”、“当下”。但从严格的时间观念来说,“现在”反而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有瞬息间的存在),当我们想到或说出“现在”时,这“现在”即已成为“过去”了。因此,“历史”关注的不只是“人过去的一切”,而是“人的一切、与人有关的一切”。这包括了人的思想、社会、经济生活、文艺创作的一切。
钱穆师在《湖上闲思录》首篇《人文与自然》中说:
宇宙之大……是够可惊人的……人类在整个宇宙间……譬如在大黑深夜,无边的旷野里有着一点微光……如萤火虫般……奔向前程……
人类的心智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黑暗中寻光明,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这些……累积着的文化遗产,我们称之曰:“人文”……这是真实的……但……也只是萤尾梢头的一点微光……但就人而论,也只有这样。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文史》国际计划委员会总裁杜蒙(George-Henri Dumont,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project,UNESCO)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页:《人文史》资料汇编《工程/计划简介》(UNESCO:Collection of History of Humanity,Description of the Project,updated 03—01—01)中写道:
我们研究历史……是要把所有的过去,从一无所有的虚空挽救回来;没有历史,所有的过去都消失于虚空;没有历史,便没有过去……历史以外,没有任何存在。在一页网页中,对钱师五十年前的述意,重述了四遍。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广义的“史学”在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是极明确的。从传说所云在上古没有文字时代,人们便“结绳以记事”(《周易正义·系辞下》,及《老子》第八十章);殷商卜辞对人的行事年月日时间的关注;中国过去数千年史料(包括近年的考古发现)之丰富和史书体裁之多元多样而整饰,在人类文化传统中居首位是无疑义的(Chi-yun Chen,“Immanental Human-beings in Transcendent Time-Epis- temological Basis of Pristine Chines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in Chun-Chieh Huang & John B.Henderson eds.,Notions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6;高专诚节译《中国古代历史意识中的人和时》(《开放时代》,2002年3月)。
经、史、子、集四部群书,“史部”固然是专门史学,“经学”亦有“六经皆史也,皆先皇之典籍也”之说(章学诚《文史通义》首章);“子部”论说也大都从人本立场,以先王、先圣、先哲、先贤的遗训行事为基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诸子……皆……六经之支与流裔”)。至于“集部”,在现代学术分类,属于“文学”,但由于传统文学的本源离不开“经、史、子”,换句话说,传统中国人的关注对象、思维方式和著述的形式都依归或趋向于广义的“历史”,因此“集部”文章内涵亦赋有此史学特色。
历史文化的内涵多元、多方、多层面,学术思想的关注自然应该是多元、多方、多层面的。庄子主张无限包容,无穷与有限两立,绝对与相对兼存,大与小相通,人籁地籁天籁尽知。《荀子》:“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天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非相》);“故能宽容……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非相》)。《管子·宙合》篇说:“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案不可不多……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韩非子》:“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万物所异理而道尽。稽万物故不得不化。”(《解老》)《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自述治学,意在“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东汉末年,荀悦在《申鉴》中也说:“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非博无以通矣。博其方。”(《时事二》)
中国学术偏离这大传统,肇始于近千年来“宋学”和“汉学”的对立。“宋学”和“汉学”的对立对传统中国学者并未造成过大的困扰,因为在过去中华思想文化是一整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学者虽有“汉”、“宋”之分,但识者大都知道这是门户之见,各有所偏。近百年来,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势下,中国文教学术全面接受了西方分科分系的近代教育和学术系统。这些分科西学,如何与中华学术传统衔接,便成为困扰的问题。过去“汉”、“宋”、“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之分虽严,但只是门户之分,其研究讨论之客体对象,仍是中华文化整体。现代学术把这种宗派门户分别定位为“哲学”和“历史”两种不同的学科;哲学系不必理会历史,而历史系不必理会哲学。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目前国内号称“哲学史”的大都只是“思想史”)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两种客体。当然,略有通识的人都会知道,历史和思想过去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绝不会是互不相干的(“哲学史”、“思想史”都是“史”之一体)。这种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千头万绪,不容易弄清楚。惟其如此,这问题更值 得我们去研究探讨。
3.近代西方学术“跨学科、超领域”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分科学术虽然来自西方,现代西方学术界却是深知这种分科学术的毛病,因而大力倡导“跨学科、超领域”的科研(inter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近年世界各国高教体系都在推动“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上面说过,历史文化本体就是跨学科的。以当代学术体系而言,人文方面有“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社会科学方面有“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自然科学方面,“博物学”原名即为“自然史”(naturalhistory),其它如地质学有“地质演化史”,生物学有“物种进化史”,天文有“天体演变史”及“天文学史”等等,都是广义的史学领域。西方新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更是以“历史情境”来从事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体、文本、语境都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其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即筹备撰写一《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这是聚集世界主要国家史学界精英,历时二十多年始完成的巨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于1962年在所撰《前言》中宣称:
本书题称《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严格地说,是叙述无数世代人们个别地与集体地(社会)意识(思想)建构的人类人性人文。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以意识(思想)塑成自己的人性人文——文明社会:含社会,经济,科技等。(UNESCO:History of Mankind,vol.1,pp.xii-xiii)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新编一套《人文史》,1980年开始筹办,1994年出版第一卷, 1999年出版第五卷,第六、七卷尚待出版。在《前言》(1994年)中,此书筹划委员会的前任执行长(Charles Moraze,专业哲学家)感叹说道:当前人类的知识注重专门分析的倾向大大地妨碍了大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综合整体观察(p.x);历史研究的分歧专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研究互不相干,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学史的研究各成独立山头,妨碍了人们对自己明智的历史理解(p.xii)。
1964年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中,有一关于“汉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论战。参加讨论的论文发表于《亚洲学报》第23卷第4期(JAS.23:4,August 1964)。其中,第三篇论文《中国研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s)由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讲。他评论过去传统汉学过于注重考证方法,甚至于为考证而考证;而且汉学家只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与其它方面的学术汇通。他主张用整体的人文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这样才能对一般人文及社会科学有所贡献。最后他希望欧美人文社会科学家多多注重中国研究。
第五篇论文《汉学的统整性》(The Case for 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由牟复礼(Frederic Mote)主讲。他认为“汉学”“中国研究”不应各自为政,亦不应分别依附于各种社会科学。他主张应该有一整体性的全盘计划来彻底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第六篇论文为讨论会主席慕斐(Rhoads Murphey)的综合报告。他指出与会诸人意见的分歧性和统整性,认为“史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环,不管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所受的训练或所采用的方法和态度是什么(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他必须在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文化史学者(comparative cultural historian)。
第七篇论文为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的综合批评。他本着人文学者的立场,对于过分强调社会科学方法一点加以批评。他的结论是:
无论一个人所受的是哪一种学科方法的训练,他本人的文化修养越广博深厚,则越能在那种方法上发挥他一切的智能。无论这些智能是不是由那种特殊学科训练上得来的,它(指由文化修养而得来的智能)都可以使一个人的说话有份量,有价值。反之,由一个修养浅薄、目光短狭的人,机械地应用一种孤立的学科方法,常常会产生浅陋的, 甚至荒谬的结果。(陈启云《汉学、史学、社会科学》,第12—13页;《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第45—47页)。
这正是钱穆师和我生平治学的志业。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
张荣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现代学术分野中,哲学与史学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学科,各有自己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另一方面,哲学与史学往往又交织在一起,讨论共同的课题,相互启发,有时也发生激烈的学术争辩。一些哲学家研究现实问题,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借用历史资源为自己的论证作支撑;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问题,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由于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个交叉地带,双方立场不同,于是往往发生学术对立。这当中,中国思想史研究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
中国思想史学科,到底应该归属于历史学还是哲学,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从理论上说似乎不是问题,但实际上问题不少。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情形:都在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身处历史学科的研究者指责身处哲学学科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历史事实”,身处哲学学科的研究者认为身处历史学科的研究者的研究“远离现实,缺乏意义”。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国思想史学科的不成熟有关。
顾名思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现象,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都属于中国思想史的范畴。随着学科的分化和研究的深入,不同分支的思想史不断地被划分到相关学科中,如政治思想史归入政治学科,经济思想史归入经济学科,军事思想史归入军事学科。于是我们看到了现今的情形,思想史的研究者有的身处历史学科,有的身处文学学科,有的身处哲学学科等等。不管哪一个分支的思想史,最终都属于思想史。这印证了先贤的一句名言:史学乃万学之母。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非物质、非制度层面,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无论研究的是哪一分支的思想史,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都应该以历史研究的目标为彀的。
历史是逝去的存在。历史的研究者无法直接面对过去,无法直接观察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无法直接面对自己试图研究的对象。研究者若要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不得不依赖于特定的中介物——历史资料。正因如此,前辈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史料研究,史学就是史料学。用史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已是历史学界从兰克到傅斯年以至今日学人的老生常谈。实际上,逝去的历史无法成为历史学家直接研究的对象,事实上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资料。广义上的历史资料不但包括文字资料——历史档案、历史著作等,还包括非文字资料——实物、录音录像等。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以文字资料为主,并泛称之为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事件的碎片。就像考古学家用发掘出的陶器碎片复原陶器一样,无论发掘出多少陶器碎片,考古学家也无法承诺一定能复原出土碎片的全部陶器,更不用说复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全部陶器了。殷墟卜辞的发现造成了对商朝历史一次颠覆性的改写,竹简文献的不断出土也使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被不断刷新。这里我们看到,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在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真实的历史 是不变的,而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却在不断更新。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一般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任务是揭示文献资料所反映的特定人物、特定事件和特定时期的思想现象,以及不同思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大体规律。也就是说,研究者的工作任务是分析文献资料中的思想事件,透过文献资料中的思想事件投射历史中的思想事件。这是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是当下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者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思想家。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学与中国哲学、历史学家与思想家的分野。中国思想史上有“今文经学”。众所周知,今文经学虽也引经据典,但今文经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是经典本身,而是现实。无论是董仲舒、康有为,还是现代新儒家,都是这样。康有为把孔子说成是伟大的改革者和议会制度的提倡者,现代新儒家把孔子塑造成现代圣人。这是时代赋予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任务,而不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任务。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各有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不应混淆在一起,更不应彼此在学术上作无谓的厮杀混战。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不包含对历史资料中的思想现象作道德的、意义的评判。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现象璀璨绚丽,异彩纷呈。商周时代的宗教思想,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汉代的经学思想,唐代的佛学思想,宋明的道学思想等等,各具特色,自有道理。在这里,历史学家应该向生物学家学习。对于生物学家来说,无论是一株病毒还是一朵鲜花,都是客观存在,与个人的好恶无关。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商代的神权思想,还是孔子的人文思想,都是历史实在,研究者没必要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其作价值的定性。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全面选择被研究的文献资料,甄别文献资料的真伪,判定文献资料的性质,然后对文献资料作全面的归纳分析,最后形成有前提条件的结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历史文献资料,从事一项课题的研究首先应该明确被研究的史料。这就像士兵在训练场上打靶,靶子不明确,难免无的放矢。史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史料与研究结论之间应当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史料是验证结论正确与否的唯一依据。研究者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必须内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史料中,而不是存在于史料之外。正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是“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带史”。对象资料不是研究者的奴隶,不应该听命于研究者,相反它是与研究者并存的、独立的存在。诚然,文献资料离不开人的理解和解释,但解释工作不应该随心所欲,不应该是公羊学或今文学的,相反,应该是训诂学的,对文献资料的解释应该具有学术的稳定性。
应该全面地搜集史料。为了使研究成果客观可信,研究者应该尽量全面地搜集史料。受主体利益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往往在无意当中忽略掉自己不需要的资料,有时甚至故意隐瞒不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史料。海登·怀特批评说,“我们关于历史结构和过程的解释,与其说受我们所加入的内容的支配,不如说受我们所漏掉的内容的支配”。此言虽显过激,但确实指出了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弊端。承诺全面搜集史料是专业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职业操守,虽然这一承诺在常人看来显得荒唐或不可思议。“让史料说话”不是让部分史料说话,而是让自己掌握的全部史料说话。历史学家有权利在学术上保持缄默,也有权利揭示事件真相,但不应该随心所欲地选取和抛弃历史文献资料——否则就是伪历史学家。这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来说同样适用。
史料的考据和辨伪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是“小学”,也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兰克就强调应该辨别伪档案和伪史料,中国学者(清代的考据派和近代的疑古派)也在史料的辨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任何一项研究如果忽略了史料的真伪,就潜在着结论的科学性风险。不仅应该注 意史料的真伪,还应该注意史料的性质。任何史料都是特定的人制作的, 都有特定的视角和立场,因而都有主体性。没有主体性的、完全超然的史料不存在。在自然事件中,人处于主体地位,自然现象处于客体地位,史料的主体性可以被忽略。但在社会事件中,特别是在冲突性的社会事件中,矛盾冲突的双方互为主客,都会提供相应的史料,而这些史料可能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就像诉讼案件中控辩双方各自都会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一样。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冲突性的社会事件都应该留下冲突双方各自的“证据”。但在实践上,我们有时仅看到一方面的证据和史料,并且往往不自觉地被那些一面之词所迷惑。在中国的“正史”中,末代帝王大多被描述得不甚完美甚至充满罪恶,宫廷政变中的失败者也往往被说成是无能之辈甚至是残暴无道者。这不应该被看成是偶然现象,在这背后隐藏着史料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所能看到的作为“证据”的文献史料往往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失败者的“证据”可能已被胜利者销毁。这是权力意志的结果。谨慎地评估文献史料的性质,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客观研究的起点。
中国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归纳,其次才是演绎。通过对史料的归纳和分析,研究者可以对个案事件得出基本的认识和结论;通过对若干个案的研究,可以形成有前提条件的假说或理论。个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初级成果,理论是历史研究的高级成果。理论的意义在于从已知推测未知,使人们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更高的抽象的层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方法,是演绎方法在史学领域中的运用。但是,如果忽略甚至放弃了归纳的方法,一味地采用演绎的方法,将某种历史理论神圣化,这样的历史研究就失去了真正的功能和意义,或者说它发挥的不是历史学的功能。简言之,在归纳与演绎方法的关系上,归纳是本,演绎是末。
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推导出的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文献资料研究的成果,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被研究的史料可以是一条,也可以是许多条,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料都是有限的,因而只能得出有限的结论。任何“资料证明”都是有限的证明,任何“事实证明”都是有限的事实的证明,不存在绝对真理。这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客观主义和理性精神。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恒久性,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应该努力消除自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研究工作的干扰。对于身处特定环境中的研究者来说,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道德观念。社会化使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然而,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就不能不受到质疑。受特定意识形态支配的人们往往习惯于给不同的思想学说作价值、意义判断,其实这种判断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来说不仅不必要,而且是有害的。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既没有必要对历史上的某种学说加以褒奖,也没有必要对某种学说加以贬斥。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还应该消除个人信仰对研究工作的干扰。兰克曾经自信地说,他写的《教皇史》应该能够被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信徒认可和接受。但是,他却无法承诺能被伊斯兰教徒所接受。这是宗教信仰对历史研究工作的干扰。同样,无神论也会造成对历史研究的干扰。很多现代人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愚昧的行为,应该被否定。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有的研究者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大加挞伐,有的研究者对孔子的鬼神观讳莫如深。历史学家声称“让材料说话”,但在遇到此类资料的时候,恰恰是不让材料说话,而一定要自己站出来说话。在有些学者看来,如果让带有宗教色彩的资料说话,研究者难免有唯心主义的嫌疑,甚至有被人认为宣传迷信的风险。克罗齐讥讽说这标志着“语文文献性历史的破产”——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史料说话”原则的破产。其实,第一,文献史料所说的话不等于研究者所说的话;第二,只有揭示文献史料的真实内容,才能进一步发现不同文献资料反映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揭示历史的脉络。
只要研究者明确了自己研究的对象资料,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方法, 就可以摆脱研究工作与个人信念之间的纠葛。兰克为此曾作过尝试和努力,但仍不够彻底,问题出在学界没有建立公认的完善的研究程序和规则。海登·怀特说历史学仍处于前科学阶段,值得历史学家反思和探索。
“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
王中江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19世纪以降,从“内外关系”的变化以及理解和处理这种变化的方式中,演生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而用来解释近代中国转变的“帝国主义”模式,一直是作为“外部世界”的力量来运用的,它忽视甚至掩盖了清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帝国体系”,这一体系是以“宗主国对藩邦”为基本构架和以“怀柔对朝贡”为机能的世界体系和秩序,清帝国位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并作为上方之国扮演着“天下共主”的角色。因此,外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晚清帝国之间从一开始所展开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两种帝国主义”都试图垄断国际权力而进行的争夺。
在鸦片作为导火线引起的中英战争之前,晚清帝国一再坚持,它奉行的国际准则是“天朝定制”之下的“一视同仁”,限制在广州的对外关系和贸易制度,已经是帝国对外关系和秩序的最好安 排,任何想改变这种关系和制度的要求不仅违背了它的“一视同仁”的国际准则,而且更背于天朝的定制(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晚清帝国拒绝英国的一些要求,就是基于满足英国的要求就会破坏“一视同仁”的普遍性准则。严格来说,晚清帝国宗藩世界体系的有效范围,基本上限于东亚属国。但出于与晚清帝国贸易需求的西方国家,开始时一般都接受了广州的贸易制度,乃至默认把它们作为宗藩体系之下的远方的朝贡国。即使英国坚持它不是朝贡国,但中国官员还是在马嗄尔尼运送礼品到达北京的车辆上都插上了象征着朝贡礼车的旗帜。不管在什么意义上,晚清帝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制度和国际交往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因此,英国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贸易制度和国际关系。但晚清帝国坚持认为,广州开放的贸易是对好利的西方人所施予的“恩惠”,接受它的贸易制度和所要求的交往方式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晚清帝国常常以贸易封锁和闭关的方式来迫使西方国家就范。
晚清帝国的常情常理是,它丰富的物产能够满足它所需要的一切,西方国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求助于它的国家的。帝国有权利对贸易作出各种限制,也有权利随时中止贸易关系。在现在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断绝关系是自己的权利,对当时的晚清帝国来说这更是自然的。当然,对于要求开辟世界市场甚至是殖民主义者来说,一个国家是没有权利闭关锁国的,它有义务开放自己的市场以通商互利。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体系在接受和默认晚清帝国的贸易制度和交往方式的同时,一直与晚清帝国之间存在着摩擦甚至是冲突。从两种帝国主义的特性来说,晚清帝国禁止鸦片贸易只是中英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它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新帝国体系与晚清老帝国体系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和国际交往观,更深层的原因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冲突。一个是以工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近代军队,是由新兴的民族国家和以欧洲国际法来维持的国际关系,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制度;而另一个则仍然是未经分化的以农业为中心自给自足的国家,是传统延伸下来的中心对边缘的宗藩国际关系。但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无疑是非法的(这是连英国人也承认的),而且是不人道的,因此,晚清帝国禁止鸦片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林则徐当时就从有限的国际法知识中寻找到了合法性的根据。但一旦诉之于战争,英帝国与晚清帝国的关系如何,最终就由军事上的强弱来决定了。
鸦片战争是一条分界线,自此晚清帝国就丧失了根据自己的世界秩序观来维持宗藩世界体系的“主导性”(或“主动性”)。按照欧洲的国际法(林则徐从中寻找根据实际上是承认它的有效性,后来它成为中国面对的一个复杂问题),如果说之前晚清帝国把一些片面的“不平等”性制度施诸给西方帝国,那么之后就是西方帝国变本加厉地不断把“不平等”的条约强加给晚清帝国。《南京条约》是大量不平等条约出现的开始而不是条约的结束,虽然在这个条约中彼此都宣示永久友好,晚清帝国更喜欢把这个条约称之为“万年和约”,希望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外部帝国(特别是与英帝国)的冲突。但事实上,由于老帝国一味地守护既成的秩序而不能适应新的世界大势果敢有效地应对巨大的挑战,由于外部新帝国列强本身的冒险性、进攻性和征服性,结果晚清帝国中心对边缘的传统宗藩世界秩序,就在内外两个方向上开始动摇甚至是瓦解,一是作为帝国内部的国家主权的“分割”,最突出地表现就是一般所说的“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其他诸如传教活动、海关和贸易、军事等许多内部事务也不能完全“自决”,失去了控制权,演变到最后以至于到了整个帝国将被“瓜分”的局面;一是作为帝国外围的它的属国或藩邦如琉球、越南、缅甸和朝鲜等,一一都脱离开其所依附的旧的世界体系,而被列强强行编入到它们的新世界体系的版图之中。
从世界史来看待晚清帝国的近代转变发人深思。欧洲近代以君主制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从罗马统一世界帝国分离出来和摆脱封建制的过程,欧洲新的世界秩序和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君主国家的彼此主权独立而又相互承认的国际法基础之上。相对于此,晚清帝国本来就是 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制”国家,它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却是一个丧失“大一统”秩序和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是西方近代新生的民族国家通过军事和“条约制度”进行控制而晚清帝国进行反控制的过程。
处在帝国旧世界秩序急速变迁过程之中的晚清开明士大夫,反思帝国发生巨变的性质,积极引导和重构帝国新的世界秩序和主权体系。他们认识到不能再简单地用“华夷之防”和“华夷之辨”来解释和说明晚清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为西方帝国本身也拥有自己的文明体系,这一认识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扩大而加深。从指称西方和西方的事物为“夷”和“夷物”变为“泰西”和“西学”是直观性的例证。这一过程也许比人们期望的要长,不过如果想到这一传统模式的悠久性,再考虑到西方列强对晚清的军事征服和利益掠夺,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晚清帝国的官方文书一直坚持用歧视性的“夷”字称呼西方国家,并发明了一种方法,在西人的中文译名上都加上“口”字偏旁,这看上去就像是一串密码,失去了中文语义所能引起的任何美感。“夷”的称谓在官方文书中禁止使用,是列强作为条约中的一项内容提出的。《筹办夷务始末》的编者,继续坚持使用“夷(务)”字,而不是当时已开始使用的“洋(务)”。在文化和人们的心理意识上,其消退的过程当然更为缓慢。不过开明的士大夫和文化精英相信,“华夷之辨”已经不能客观地反映出中西文明的实际情况了,它不是文明对野蛮的关系,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伴随“文野”固定界限的变化而出现的另一个变化,是“中心”对“边缘”固定界限的变化,即原来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两种彼此相连的变化,既为接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正当性的根据,而且客观上也要求晚清帝国把自己作为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中与其他国家平等的一员。实际上的复杂性在于,晚清帝国的统治者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世界秩序观,至少在一些形式上,它拒绝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关系,如晚清帝国一直拒绝西方国家往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认为这是天朝最根本性的秩序;而列强则一直在向晚清帝国要求这方面的“国际平等”。与此同时,列强通过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已严重破坏了晚清的内外秩序。对于开明的晚清士大夫来说,内外秩序的重建,要求晚清帝国转变意识以适应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万国公法”的引入和转化构成了晚清帝国重建内外秩序的一个重要尺度和框架。它首先是作为一部国际法著作被引入的,而且是由总理衙门恭亲王奕奏请批准而由同文馆教官丁韪良主持翻译的,可它远远超出了一部书的意义,其国际视野的“世界秩序观”,折射出新的“中国意识”。《万国公法》是近代中国认识、接受和转化国际法的转折点,为晚清提供了国际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和行为规范。但这一过程同时又是把“万国公法”合理化和正当化的过程,因为“华夷之辨”把它视之为“夷物”。“万国”和“公法”这两个译名本身就意味深长。超出原来地域范围的“众多国家”观念有助于一个国家意识到它的“界限”,用“公”来指称国家间的法律容易把它普遍化和客观化。事实上,这正是晚清开明人士把国际法合理化的一个方式。他们首先是相信“公法”的可借鉴性和有效性,进而相信它是普遍公正的,相信它是国际关系中的“公理”。在“公理”与“公法”结合到一起时,万国公法的普遍公正就成了它的广泛有效性的前提。
在为“万国公法”寻找合理性的方法上,晚清人士也诉诸于传统。在他们看来,“万国公法”就是或者类似于古代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家的公法。这基于他们的这样一种判断,即春秋战国的国际格局及局势与近代欧洲国家是高度近似的。一般把这视之为近代中国“西学中源说”的一个表现,或者把它作为一种“附会论”,而没有注意到它也有正当的一面。因为一是理解和解释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它已有的“先见”;二是不能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法与近代欧洲的国际法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合理化和正当化之下的“万国公法”,反过来就成为判断国际关系的根据和准则。如上所说,作为约束中外国际关系的晚清“条约”,它是晚清帝国与其他国家间共同签订的规范彼此 交往的法律,它应该被当事国双方互相遵守, 但这些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极不对称的,它的一些条款恰恰违背了万国公法,严重损害了了晚清帝国的国家主权。
正是万国公法使人们认识到了中外“条约制度”的严重问题,人们纷纷运用“万国公法”暴露条约的“问题性”,并从万国公法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据和途径,甚至于重建世界秩序和大同的可能性。但是,面对西方列强在华的强权行为和不平等条约,也出现了怀疑万国公法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处理国家间关系单靠国际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强权。有人甚至根本上就否认国际法的合理性,相信国际社会完全是由强权决定的世界,强权即是正义和公理。这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在国际社会中的运用。这种运用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旨在以国际竞争的残酷性来激发国民的精神和活力,以自己的强权参与到国际社会的角逐之中。但它的困境在于,如果把强权完全合理化,那么列强对待中国的一切强权行为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实际上处在贫弱状态的中国,如果被列强征服了,那也只能说是活该,虽然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并不相信处在守势和劣势的中国真的会被淘汰。
以“三亡”(“亡国”、“亡种”和“亡教”)表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一直是与追求“三保”(“保国”、“保种”和“保教”)和富强大国的目标不可分的。但是,必然清醒的是,完全相信国际社会是一个优胜劣败和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同时也就失去了批判强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既然国际社会和关系本来就是由力量决定的,自然就没有根据说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和不正当的。殖民主义者从来就是把其殖民行为看成是天然正当的,他们以他们的征服力来证明其民族、种族的优越性和高贵性。从整体上说,晚清帝国人士相信“万国公法”的正义性和“公理性”,坚持建立以“国际正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但同时又对万国公法保持着“限度性”意识,把物质“力量”作为建立合理世界秩序的辅助性手段,表现出把公理与强权、德与力、理与势等统一起来的倾向。
(本刊编者注:原刊这组笔谈文章共7篇,根据篇幅和内容需要,本刊节选其中5篇)
注释:
① 1948年6月1日上海《申报》副刊《学津》第26期;收在《湖上闲思录》,1948年成稿于苏州,1960年香港初版,本文据台北市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中国思想史小丛书》2001年版。
标签: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宗教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国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