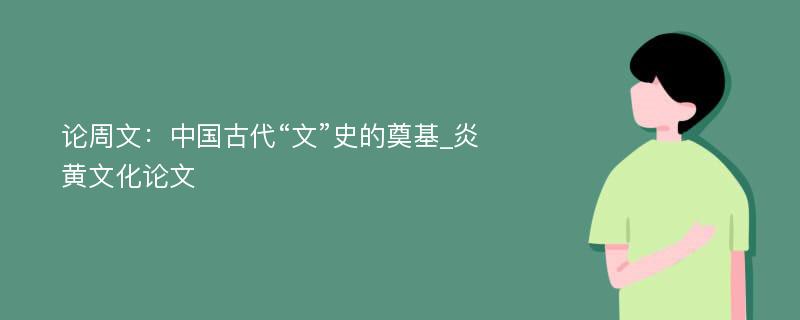
论“周文”——中国古代“文”的历史之奠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历史论文,周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2)05-0066-08
所谓“周文”有多层含义。一是指周代贵族统治者“德治”、“文治”的治国方略,二是指周人的文章,三是指周代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董仲舒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①
这段文字出于《春秋繁露·十指》,董仲舒在这篇文章里谈论“六科十指”,是公羊学家专门讨论《春秋》所蕴含的治国平天下之方略的。这是在讲治国,讲政治教化,所以这里的“周文”主要是指西周的“文治”或“德治”的治国理念。章学诚说: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②
这段话出于《文史通义·诗教上》,是专门讨论战国诸子的文章对后世之影响的。所以这里的“周文”显然是指文章而言。在章学诚看来,“周文”——周代的文章典籍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衰微了,但却孕育出了战国诸子百家之文,并从而成为后世之文的源头。牟宗三先生尝言:
这套周文在周朝时粲然完备,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做“周文疲弊”。诸子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③
在这篇讲演中,牟宗三先生是在讨论诸子百家之发生缘由问题,他所说的“周文”是指整个周代典章制度与礼乐文化而言。
“文”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文”之传统。这一传统滥觞于夏商而奠基于西周。假如没有西周贵族阶层的戛戛独造,很难想象中国古代会形成这样一个恢弘壮丽的“文”之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文”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变化着。在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贵族社会中,“文”实质上就是贵族制度与贵族文化的总名,同时也是使贵族成为贵族的文化符号系统。孔子说:“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论语·述而》)这里的“文”就是指贵族社会的礼乐文化与典章制度而言④。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价值秩序中,“文”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这里的“文”没有任何负面含义。到了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际,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文”在诸子百家的不同语境中,就具有了不同的含义。或褒或贬,判若云泥。而到了秦汉之后,随着士大夫阶层身份的变化,“文”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衍生出诸多新的义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文学史”。我们有的是“文”的历史,这是一种“大文学史”或者“广义文学史”;同样,我们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我们有的是对“文”的解读以及“诗文评”传统。通过对这个“文”的历史的考察,我们庶几可以窥见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精神演变的历程,从而从一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新的理解。
一、贵族话语系统中的“文”
在先秦典籍中,“文”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就字源学的演变看,这个词最初含义很可能如《易传》所说,是“物相杂,故曰文”。或《说文》所谓“错画也。象交文。”抑或如《周礼》郑注所说:“画绘之事,青与赤谓之文”。总之是不同事物或线条或颜色的交错杂陈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然而即使是早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文”的含义也已经很复杂了,让我们看看《尚书·周书》、《诗经》、《周易》等典籍中那些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文献的情况即可明了。
《周书》: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康诰》)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洛诰》)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洛诰》)
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由“文”字组成的复合词出现最多的大约莫过于“文王”以及代指文王和武王的“文武”了。对“文王”、“武王”称谓,自司马迁始,古人大都以为是谥号,今人或以为不是谥号而是自称或者是其生前臣下对他们的尊称。对我们来说,这里的“文”、“武”是否为谥号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文”在这里的含义是什么。谥号也罢,自称或尊称也罢,“文”是一个赞美的词是无疑的。那么它是何义呢?我们看周代文献,还有一个与“文组合而成的词多次出现,那就是“文人”,如:
“父义和,汝克昭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周书·文侯之命》)
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经·大雅·江汉》)
“文人”,古人注疏指为“前文德之人”(孔传)或“先祖诸有德美见记者”(郑笺),也就是说,这个“文”是“文德”或“美德”之意。与此相类,则“文王”之文,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就是说,“文王”就是有美德的或者品德高尚的王,文王的“文”与武王的“武”相对,也具有通过文治而得人心的意味。
对于《洛诰》中的“咸秩无文”之“文”,孔传曰“礼文”,孔疏曰“文法”⑤。这意味着,早在西周时期,“文”已经具有了典章制度方面的含义,与春秋之末孔子所谓“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之“文”同义⑥。
《诗经》: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周颂·烈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周颂·思文》)
此处之“烈文”,据前人注释,是光明而有文章的意思⑦;“思文”是思念先祖有文德之人的意思⑧。盖“文德”、“文章”相通,都是指在道德品质方面有过人之处,能够令人信服,与“武”,即武功相辅相成。
我们再来看《周易》: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小畜·象传》)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同人·彖传》)
对“君子以懿文德”孔疏云:“喻君子之人但修美文德,待时而发。”⑨对“文明以健”,王注云:“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⑩
从以上诸例证可以看出,“文”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概念,指涉美好品德、典章制度以及通过文治而得人心等义项,可以说与周人崇尚的“德”这一价值范畴意义相近(11)。或者可以说,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形式以及美好的道德品质均可概言之曰“文”。究其缘由,盖在殷商之前,周人原本是偏居于西北一隅之地的地方部落,自后稷以降,历代先祖勤勤恳恳劳作耕耘,渐渐兴盛起来。最终姬昌、姬发父子趁着商纣凶顽残暴,激起天下诸侯不满之际,暗中联络,一举推翻殷商统治。这就意味着,周人不是根基深厚的贵族,其统治也没有自明的合法性依据,一切都靠自己去建设。于是执政的周公在平定内乱、天下初定之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封土地,建诸侯”与“制礼作乐”。前者是最根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建设,后者是与政治经济体制直接相配套的文化制度建设。“封建”的结果是建立起严密的贵族等级制政治形式;“制礼作乐”的结果是建立起整套的礼仪制度与意识形态,这也就是“文”的系统。获得了政权的西周统治者,通过“封建”而获得合法的经济与政治特权,进而又通过“礼乐制度”而获得合法的精神文化乃至审美层面的特权。正是后者通过贵族教育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大作用深入到贵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贵族打造成一个与一般社会大众迥然不同的、有特殊教养的社会阶层。《礼记·经解》载: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这段话是关于贵族教育效果的描述。《诗》、《书》、《礼》、《乐》、《易》、《春秋》各有各的教育目的,总之是使贵族成为有教养的人,从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周礼》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基本技能,在贵族教育中属于“小学”部分的内容,至于“大学”,则旨在教育贵族做人与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其教育内容均属于“文”之范畴。因此,在贵族时代,“文”就是贵族阶级日常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教养、价值观念之总名,其功能是确证并巩固既有的贵族等级制,使之获得合法性。对于贵族来说“文”的重要作用是使其获得身份上的正当性与神圣性。《左传》载卫大夫北宫文子论“威仪”云: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襄公三十一年》)
这里所谓“威仪”正是指周代贵族按照不同身份而拥有的形式上和价值观上的神圣性,这种“威仪”使贵族成其为贵族,而这正是“周文”之主要功能。周人精心创造出来的那套繁缛的礼仪形式绝非为了耳目感官的享受,它们无不具有这样一种政治功能。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周文”的这一功能已丧失殆尽,故而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家都已经无法理解这套形式的价值,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予以否定了。《国语》载周襄王对晋正卿范武子说的一段话:
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礼烝而已。饫以显物,宴以合好,故岁饫不倦,时宴不淫,月会、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德建。古之善礼者,将焉用全烝?(《周语中》)
这里所说的“服物”、“采饰”、“文章”、“周旋”、“容貌”、“威仪”、“五味”、“五色”、“五声”、“五义”等等,都是礼仪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即“文”之系统,它们自身原无意义可言,但它们都具有“昭德”的功能,因此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当然,在今天看来,所谓“德”从根本上说,并非美好的品德,高尚的行为之谓,乃是对严格的贵族等级制的认同与恪守,是自觉地依照贵族等级规范来立身行事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看,“小邦周”从“大国商”手中仅靠牧野一役就夺取了天下,在惊喜之余,也十分诧异,因此对于“殷鉴”是极为重视的。通过总结经验,周人意识到商人在“德化”方面大有欠缺,主要是靠杀伐控制天下诸侯。而“小邦周”之有天下,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德化”——天下诸侯受文王感化而弃商从周,即使是牧野之战也主要是靠殷商军队的“倒戈”才获得胜利。故而他们就把文教德化视若生命(12)。如此看来,周人之重“文”,与后世赵宋之重“文”颇有相近的政治考量,并非出于个别执政者的性格与偏好。《国语》载: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周语上》)
这里“德”与“文”相通,是指崇尚德化文教,而不推崇武力,这是周人自周公以降历代的主张,因而重“德”与重“文”紧密相关。劳思光尝论及周人重“德”的原因及与重“文”之关联,其云:
……天命归于有德,而是否能敬德,则是人可自作主宰者。于是,人对于天命,并非处于完全被动承受之地位;反之,人通过“德”,即可决定天命之归向矣。
此种强调人之自觉努力之思想,乃周文化之第一特色。就历史之发生因素言,则使此种思想产生之契机,乃上所述之艰危形势。亦即《召诰》所谓“惟王受命,无疆惟体,亦无疆惟恤”是也。然不论发生因素为何,此思想发生后,即循其特性而展开影响。日后周文化之其他特色,可说皆由此基本方向生出。
首先可指出者是:由强调人之主宰地位,必生出改造自然世界及生活之要求。此种要求在周人即表现为建立礼制,创生一种文化意义之生活秩序,以规范自然生活之努力。周人之“德”观念,倘若逆溯而上,则可通往一道德哲学。但周初建国时,此种智慧尚未成熟,其表现只是顺推而下。即由“德”观念衍生出礼治秩序之建立。
周初之封土建君,已使各地区之政权,脱离原始自然状态,再以立长立嫡之继承法确定政权传递之轨道,初步之政治秩序即已建立。另一面再制定种种仪文,使生活中处处有一规范。于是所谓郁郁乎周文之局面,即由此大定。(13)
这些论述,把周人重德尚文的缘由以及“德”与“文”之间的密切关联很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德”与“文”的对立面是武力杀伐与严刑峻法。对于打天下、获权力而言,武力杀伐常常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控制天下、维持社会秩序而言,严刑峻法常常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古代帝王的统治是根本无法离开征伐与刑罚的。但是,自汉朝以降,历代君主又大都标榜“德治”“文治”,极为重视道德教化,这就是继承了周人的政治策略,可以理解为“周文”之延续。因此,所谓“周文”,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伦理道德为手段来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当然,在此根本目的基础上,“周文”还建构起一套非常复杂的文化符号系统,使得严酷的政治控制和等级秩序被温情脉脉的说教、典雅肃穆的礼仪、精致华美的装饰所包裹,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统治方式,而中国早期的文学艺术都是现在这样一种“道德—政治—审美”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周代贵族建立起了“文”的系统,将政治、伦理、道德、宗教、艺术熔于一炉。后世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就是在这个大的系统中发展演变并渐渐获得相对独立性的。由于这样的渊源,对中国古代诗文的理解就不能离开这一“文”的语境,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或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周文疲弊”及其结果
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他把“文”的命运交付于天,可见其内心的不自信。作为“周文”的自觉拥护者,孔子面对“礼崩乐坏”、“周文疲弊”的局面可谓痛心疾首。他试图通过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克己复礼”,使已然失去光彩的周文重新灿烂起来。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即使是贵族,对于周文也已经不那么虔诚恭敬了。对于诸侯贵族而言,“文”的价值渐渐不及“武”和“法”的功用那么切实有效了。当然,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春秋前期,由于文化惯习的作用,“文”作为一个价值范畴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齐桓公)即位数年……岳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缧,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故又大施忠焉。……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矣。是故大国惭愧,小国附协。唯能用管夷吾、宁喜、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国语·齐语》)
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行文道”或“文事”意味着在国家政治策略和治国方略上重视文化教育、道德修养方面,通过灿烂的文明与高尚的道德感召其他诸侯国,使之宾服,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相对而言,“武”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是老子所说“不得已而用之”的“不祥之器”。从这里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隐武事,行文道”、“文事胜”乃是春秋前期诸侯霸主最高的政治理想了。这说明,对于秉承了西周文化的春秋前期的贵族阶层来说,“文”依然是一个富于魅力的价值范畴。一般说来,在此时,“文”虽然已经不像西周那样是每位贵族必须遵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但依然是一种受到尊重的贵族教养。《左传》载一则秦伯宴请流落于外的晋公子重耳的故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僖公二十三年》)
赵衰是晋国大夫,从公子重耳出奔,周游列国,以“文”著称,在诸侯面前多次为重耳博得尊重。僖公二十七年楚国率诸侯围宋,晋国拟出兵救宋,求帅。赵衰曰:
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
可知赵衰确实是位精通诗书礼乐的贵族。也正因为这样,他在晋文公面前极受重用,从而奠定了赵氏一族在晋国的特殊地位。这说明在春秋前期,“文”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惯习或者教养而受到尊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还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与功能。又: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左传·成公九年》)
楚囚的言谈表现出一种修养,一种令人尊敬的品德,范文子因为楚囚的这种“仁、信、忠、敏”的道德修养而劝晋侯释放了他,可见“文”——贵族教养在当时人们心中还是具有很重要的位置。像晋国的赵衰、范文子、鲁国的叔孙穆子以及宋襄公等代表着那些不仅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而且自觉恪守贵族精神的一批人。只不过越是后来,这样的人就越少了。请看下面的例子: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庆封是齐国大夫,曾经执政,出身古老的贵族家族,然而却对赋诗这样最基本礼仪都茫然不知了。到了春秋后期,像庆封这样的贵族比比皆是,他们是徒有贵族之名位而无其文化教养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周文”无论曾经是多么灿烂,多么令人赞叹,它的衰落都是必然的,并非少数缺乏教养的当权者破坏的结果。一切都源于王纲解纽,诸侯各自为政,从而导致激烈竞争。因为事实上,“文”只有在天下秩序良好、政令统一的太平时代才会发挥积极作用,而在春秋战国这样诸侯竞争的政治格局之下,“文”的建设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那些恪守“周文”的人反而会在竞争中吃亏,而武力往往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请看下面的例子: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对于不了解贵族文化或者心中缺乏道德感的人来说,宋襄公的行为是可笑的、愚蠢的,然而他所恪守、导致他失败的原则,却体现着真正的贵族精神,是西周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周文”的表现。子鱼代表的则是春秋时期形成的功利主义精神,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择手段。这显然与重荣誉胜于生命的贵族精神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襄公的失败代表着贵族精神的失败,代表着“文”的失败。
“周文疲弊”或曰“文”的失败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文”原本是形式系统与价值观念系统的完美融合,现在分为两橛了。孔子痛心疾首地哀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礼乐原本是贵族等级制及贵族精神之表征,有着极为明显的象征意义,然而到了春秋之末,这一礼乐文化系统就只剩下外在形式了。而与意义系统想脱离的形式系统也就只剩下耳目感官的娱乐功能了。这与当初周公“制礼作乐”时的初衷以及“礼乐”在长期的贵族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政治功能是大相径庭了。其次,“周文疲弊”还表现在“文”的秩序与原来所依托的社会等级秩序的错位上。在西周时期,“文”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证既定的贵族等级制,使身份差异形式化、固定化,因此“文”自身的内在秩序与贵族身份的等级秩序是完全对应的,二者相辅相成。到了春秋后期,这种对应关系被打破了,“文”也就失去了其意识形态功能,变为纯粹的形式。类似于“八佾舞于庭”这样的事件在春秋后期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这表明“文”已经失去昔日的庄严与神圣,沦为掌权者们娱乐的工具了。在天下分崩离析,诸侯各自为政的历史语境中,以武力为依托的权力才是确证人们身份最可靠的因素。韩非尝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争于气力”的“当今”正是指战乱不已的春秋战国时代。
在春秋之末,作为贵族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相交织的“文”的体系遭到破坏,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按照哲学阐释学的观点,一种文化遗存、一种“历史流传物”一旦形成,就会融进传统之中,成为传统的组成部分,从而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阐释过程中不断生发新的意义,历久而弥新。西周贵族阶层所创造的“文”之系统同样是如此。在诸子时代,“文”作为一种话语资源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这样来理解,春秋时期的“周文疲弊”恰恰是中国古代“文”之历史进入新阶段之标志。
三、“周文”作为“古之道术”
从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丰富,到了西周后期已经形成一套极为繁复、极为华丽的礼乐仪式与文化符号系统。这可以从《诗经》的某些篇什、《史记》、《周书》、《逸周书》、《左传》、《国语》等史籍的相关记载以及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上看出来。然而平王东迁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出现了所谓“王纲解纽”——一体化的贵族等级制度破坏了,诸侯各自为政、互相争夺的局面开始了。与此相应,那种统一的、完备的、一体化的价值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礼仪形式等文化符号系统也遭到破坏。这就是前面论及的“周文疲弊”现象。然而,“周文”的解体并没有导致文化的停滞与衰落,相反倒是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大繁荣局面的形成,这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周文”的盛与衰,也就不会有诸子百家的繁荣。
诸子百家的勃然而兴在学术史上堪称奇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之论指出了这一奇迹并非中国所独有,却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对此一现象,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各种不同说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下》所论,其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看这段文字,我们可以觉察到,在其作者心目中原本有一个完整、统一、完美无缺的“道术”存在,只是因为天下大乱才导致了这一“道术”的破坏。诸子百家不过是出于各自的目的从“道术”中撷取了一鳞半爪而已,是“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学”。那么这个完整的“道术”即“内圣外王之道”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真的存在过?我们有理由认为,根据《庄子·天下》的逻辑,这个“道术”正是西周贵族建构的“文”之系统,即“周文”。其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细究此段文义,古之人所具有的那种完备的“道术”,其功能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究其实质,无非是虔诚地祭祀天地日月山川之神祗以及祖先神明,规范统治阶层内部的秩序、和睦其关系,并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这恰恰是西周贵族“制礼作乐”的初衷,而且实际上也正是“周文”的基本功能。如前所述,“周文”所标示的礼乐文化或曰“文”之系统集礼仪形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话语表征、意义系统于一体,它无所不在,构成贵族社会的整个外在形态与内在价值准则。因此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文化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它的影响依然是无处不在的。在诸侯国的政治制度中,在史传记载中,在《诗》、《书》、《礼》、《乐》等文本中都保留着它的印记。即使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也随处都有其痕迹,班班可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诸子百家之学都是以这个“文”的系统为其最主要的话语资源的。因此,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论并非毫无道理。他的错误在于把王官学与诸子学之间的关联理解得过于僵死了。“王官之学”对于诸子之学来说是作为先在的整体性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而存在的,不能把某一官守与某家之学一一对应起来,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只能说,“周文”是诸子百家之母体。
然而诸子百家虽然无不受惠于西周贵族阶层创造的以“文”为标志的符号体系与观念体系,但是具体言之,则不同学派对它们的选择或者态度是迥然不同的。换言之,如果把“周文”的系统比作一片巨大的废墟,那么在这座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诸子百家之学却是异彩纷呈的——诸子们以不同方式选择和利用了这片废墟上的建筑材料。可以这样来表述:诸子百家都是面向着“周文”的废墟有所言说的,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大厦,从而使天下从无序恢复到有序状态。诸子百家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们对这片废墟的选择和利用各不相同。具体说到诸子学说与“周文”之关联,或者说“周文”究竟如何影响到儒、墨、名、法、道诸家之思想,则须另外撰文讨论了。
注释:
①董仲舒:《春秋繁露·十指》,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版,第145页。
②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③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三讲“中国哲学之重点以及先秦诸子之起源问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8页。
④朱熹注云:“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见《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8页。
⑤《尚书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408页。
⑥章太炎先生尝言:“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文学总略》,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⑦⑧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90、1309页。
⑨⑩《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86页。
(11)侯外庐先生在论及文王之“文”时认为:“……‘文’字与敬字、昭字、穆字是相连的,周金与《周书》‘前文人’的术语,也做前德人解,即所谓‘允文’之义,与德字相同。”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90页。
(12)柳诒徵尝言:“三教改易,至周而尚文。盖文王、周公皆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其心盖深知武备国防不可废。而开国之初,提倡尚武主义,则强藩列辟,日日称戈,其祸将不可止。不得已而为折中之法,务以文化戢天下人之野心,其旨深矣!”见柳诒徽:《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119—120页。
(1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周文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国语论文; 国学论文; 洛诰论文; 礼乐论文; 文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