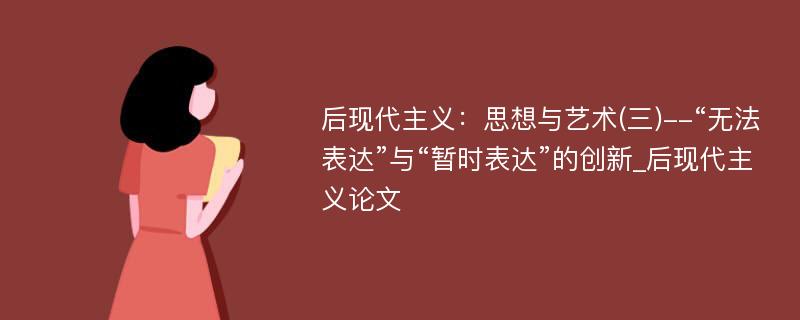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思想与艺术(3)——在“不可表达”与“姑且表达”之间创新不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思想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美的不确定性及其悖论
美,对人来说,既是最令人向往,又是神奇莫测。只有人,才感受到美的奇妙性和诱惑性,同时又体验到它潜在的烦恼性,预感到它将人引导到充满欢乐和痛苦的矛盾之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人人似乎都可以感受到美的存在,但每当需要人指出和表达美的时候,人们却无所适从,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美的基本性质。因此,美往往为人们所追求,而当它出现的时候,人们又茫然地陷入复杂的矛盾心态。
自从人从动物转向文明生活的时候起,甚至当人还没有完全真正脱离动物的状态的时候,美就已经开始紧紧跟随人的生存,特别是在人的生命中和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时时扮演着非常奇妙的角色,使人既不沉醉于五花八门的物质世界,也不深陷于虚幻而又充满吸引力的精神世界,而是随审美力的发展,努力超越现实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赋予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自身引向永远可更新和可期待的新世界。
美随着人的出现而呈现,给予人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之外,提供了一种将两个世界和人的生活提升到新的境界的可能性。但这样一来,从美介入人的生活世界的那一刻开始,美就给予人以矛盾和悖论的感受,在不知不觉和难以抵御的情况下,既向人提供意想不到的“礼物”,又把人陷入一种情感上的“圈套”。显然,美始终伴随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试图将两者在人的生活中复杂地交错起来,并引导人们以新的形式进行一种超越,既改变人本身,又创造新的生活世界,甚至启示人们从现有的实际环境出发,尽可能向新的可能世界转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美成为了人摆脱现有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创新动力,也给人提供走向不存在的美好世界的途径。
在人类文化史和哲学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智者和哲学家们,不断地探索美的性质,也试图概括和总结出关于美的各种观念和理论,但美始终未能改变它作为神秘不可测的力量而存在于人的生活中的事实,同样美也始终没有改变其引发人们思索和向往的对象的神奇性。
不管美的性质复杂到什么程度,也不管美是否因人们的探索而逐渐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美毕竟继续隐含于人的本性内部,同时又作为环绕于人的生活而呈现为盘旋在人的生活氛围中的力量,显示出美不同于由观念和概念所构成的知识真理体系,同样也异于约束人的言行的道德伦理,呈现出它独特的不可取代性,也表现出它对人的不可抗拒的干预和渗透性。
值得肯定的是,在哲学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已经深刻地洞察到美不同于知识和道德的独特性质。从柏拉图到康德,从黑格尔到德里达和福柯,都在这一条思路上,进行过各种可能的探索。在当代的思想家中,试图跳出传统思维模式而探索美的神奇性,福柯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先是严厉批判被称为“权力论述系统”的知识真理体系的虚伪性,接着坚决拒绝被称为“监视和宰制人的言行的规范”的伦理道德的残酷性,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杰出思想家所累积的实践智慧中,总结出超越真理和道德约束,造就一个没有固定的主体性的审美自身,为现代人提供了走向审美世界、并在审美世界的微妙神奇结构中,不断实现无拘无束的创新生活。福柯的思路为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艺术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使他们彻底跳出传统对美的探索思路,在各种尽可能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在直接的生活实践中,在前所未有的品尝冒险的可能超越中,置真理和道德于生活之外,向神秘的审美世界深化,寻求人们在以往的时代中所没有经历过和没有感受过的新生活。
以往思想家深受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和近现代自然科学思维模式的限制,往往回避美的矛盾和悖论性质,试图给美这样或那样的明确定义,从而歪曲了美的真正性质及其与人的生活的复杂关系。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宁愿从悖论本身出发探索美的悖论性,因为他们已经品尝够了生活本身的悖论性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美的独特观点,就在于抓住美本身的不确定性及其悖论性,并将这种悖论当成寻求美的动力和创新的力量。利欧塔在他的《非人》一书中,高度评价康德对美的不确定性的分析。他说:康德对审美观和审美愉悦的分析,给予自由以同样重要的重视。在纯审美愉悦、联想和自由式关注中的形式,都是尽可能独立于任何经验论和认识论的考虑。现象的美是与其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渐进性成正比的。康德用两个隐喻来说明现象美“一是炉膛中摇曳不定的火苗的不确定性,二是小溪水流淌过后不规则的痕迹”。
在后现代艺术作品中,美的不确定性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它的不可把握性和不可表达性。在这方面,原籍法国的美国后现代画家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和祖籍波兰的美国另一位后现代画家纽曼(Barnett Newman,1905-1970)都明确地表示:艺术作品中的美,只是生命本身的呈现,而且还只是“生命的此时此刻的呈现”,如此而已。美的不确定性,其源初的真正奥秘,就在于此!换句话说,美的不确定性,源自生命随时随地的不确定性。而且,美当然也和生命一样,因其不确定性而难以把握,难以表达。
利欧塔在分析杜尚和纽曼的作品时,始终紧紧抓住其中的美的瞬间性、不确定性及其生命的不确定性的源初基础。正如利欧塔所说:“他(纽曼)的许多绘画的主题,都倾向于表达‘悖论性的源初开端’的理念。作为动词的‘开端’,就像黑暗中的一道闪电,或者,像荒野上的一条无名之道,它离析、分割和构成一种不断地产生‘区分的区分’的延异,使人可以通过它去品味,哪怕这种延异竟如此细腻,以致揭开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感性世界”。利欧塔接着指出:“源初的开端是一种二律背反(悖论)。它作为源初延异,在世界历史初始中发生。它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它造成的。它是‘无历史’(un-historic)。这种悖论是令人惊异、而又导致创新的悖论,或者,它就是一种机遇性的悖论”。
机遇又是什么?它是不可预料的“临到”。这是一种随时无法判断的“降临到此”或“此时到达此处”的瞬时,是最令人惊异,且又顿时使人受到预料不到的启示,灵感和思路突然蜂拥而来、喷发外溢,谁也阻挡不住,同时又激荡起波涛汹涌的激情,难以自已。此时此刻,是如此闪烁奇妙,以致难以判断其来临以及其消失:一切都在瞬时间。它的呈现的一刹那,却也占据了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位置”,使它无法被否认,确确实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作痕迹。只是它只给人造成“有”的感受,却没有可把握的“在那儿”。它以其“有”的呈现,唤起过、并将继续在记忆中唤起美的感受性,使人回味无穷,启示无限。正因为这样,杜尚的主题是瞬间的不可把握性,他曾经试图以“流星雨”来说明这种不可把握性;而纽曼的《装饰1号》之后所作的一系列作品,都只是为了呈现生命所是的那一时刻罢了。正如利欧塔所指出的:“绘画呈现了存在;这个存在现在在这里自我呈现”。
所以,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说:“纽曼作品的主题总的来讲是艺术创作本身,是创世的那一瞬间的象征”。因此,纽曼自己也说:“创造的主题是混沌”。
既然美就是一刹那间的“当下呈现”,它就像一切新世界的最初开端那样,不可思议。人们总是认为世界一旦诞生,就不再重生;殊不知在艺术家看来,世界不但可以不断再生,而且还“应该”重生,并“应该”通过艺术家自身的生命的不断重生而导致世界一再地重演其源初的开端。艺术的生命力,不在于柏拉图所说的那种“不变的永恒美”,而在于它天生地和随时地包含着生命开端的瞬时美。艺术以其创造性,将世界和生命的同一种的“随时重生”闪电般地呈现出来,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奇迹和机遇。但是,利欧塔指出:“这闪电‘随时’在那儿,却从不在那儿”。世界因此而“不停地开始着”。
美,在世界的各种不可预料的偶然性“事件”中,一再地返回到它的源初的开端。但“美”的“现在”究竟在哪里?当人们要去把握它的时候,它已经不再那儿。此时此刻只在此时此刻;当此时此刻到来时,它已经不是此时此刻,因为它在顿时呈现时又顿时消失。作为世界源初开端的美,是独一无二的“有”,它不需要“在”。美的珍贵性就在于它的瞬时的“有”以及它之“不屑于在”。利欧塔说过:“理念是不可表现的,人们无法援用例子、事件甚至象征之类来显示它。宇宙是不可表现的,人性、历史的终结、瞬间、空间和善等概莫能外。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它是普遍的绝对。倘若表现它们,就会把他们相对化,把它们置于表现过程的情景和条件下。所以,绝对是表现不出来的”。
所以,真正的美是不可表达、不可表现的,因为它是在偶然的情景下,由某个活生生的人,以他当时当地的特殊情感、品味、欲望和想象力,同他所遭遇的某个具体事物相交感而突发出来的一次性复杂心态;在它之中,隐含着一系列难以确定的中介性因素和主客观力量,以当时当地的氛围而凝聚成一定的密码而交织形成、并即刻升华为崇高的个人情感,因此与人早先隐含于其内心的理念相结合和相碰撞。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真正的美都是唯一的、绝对的、一次性的。
生命本身的悖论,使真正的创作永远在生与死、愉悦与痛苦、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中挣扎。迦达默在他的具有“诠释学转向”伟大意义的奠基性著作《真理与方法》中也说:在人类的生活中,到处存在着“不可表达的”“不可表现性”。迦达默列举了“共同感”和“机敏”(即古希腊人所说的“实践智慧”)等,说明不可表达性的普遍性。同样地,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例如古代的赫拉克里特、文艺复兴时代的维柯、德国启蒙时代的哈曼等人,他们都反对把理性绝对化,强调人类生活的高度复杂性及其不可表达性和不可通约性。
但是,人们可以以一定的智慧和某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存在的某种绝对,这就是所谓“负表现”,康德也说过这是一种“抽象的”表现。1912年以来,抽象派绘画的潮流所应对的,正是这种“用可见的形式而间接又明白无误地暗示出不可见性的要求”。美的悖论及其不确定性和不可表达性,促使后现代主义艺术家采取一种特殊的创作态度:在创作中使创作美进行自我否定,让作品只是采取瞬时爆发的呈现形式,不计较它的完整性,使之永远留待在“可持续再生”的可能性中,从而也使他们自身“在‘不可表达’与‘姑且表达’”之间,不断游荡,创新不止。
2、不可表达性原则与不确定性原则
正如我在第一讲中所说:法国现代派的最早代表人物波德莱,在他的《1845沙龙》中提出了现代派创作的三大基本原则:过渡性、逃脱性、偶然性。这三条原则试图表达高度自由的创作活动所必备的性质:不稳定性、变动性、非系统性、反形式性、流动性、点滴性、瞬时性、模糊性、混乱性、非一致性、任意性、即席性及不完整性等。
被称为波德莱的“文学兄弟”的同时代的美国现代作家爱伦波,在大西洋的彼岸,也不约而同地在其创作中,贯彻了上述原则。他认为,诗歌的原则是如此严谨而单纯,它无非就是“超凡的美对于人的启示”,并始终都只能在心灵的崇高化的激荡中被寻觅到。因此,真正的创作,只能在零散的、偶然的和过渡性的绵延、含混而又无秩序的散播式时空中进行,它必须以常人所做不到的手法和技巧,避免复制和重演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
显然,波德莱等现代派作家所强调的,是艺术家特有的那种接近神秘的敏感性以及置之于绝对优先地位的决心,以便保证艺术有可能超越表面的现象,优先捕捉创作者本人发自内心的独一无二的审美冲动感。他们认为,创作的珍贵性,正是在于它的瞬间性、流动性、激发性、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由现代派所创立的上述创作原则,后来就成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的创作策略的出发点。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不确定性原则始终伴随着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创作活动,在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中展现出来。差不多与波德莱同一时代,评论家多列就已经在他的1847年的沙龙中宣称:“如果绘画的目的是向他人传递艺术家在自然面前的印象的话,那么,柯洛的作品就符合艺术的要求”。正因为这样,柯洛常常被认为是具有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双重身份的印象主义的先驱。柯洛在其绘画中所表现的“印象”,正是为了突出艺术家主观感受、想象、情绪波动以及其他各种内心世界的模糊而变动不定的变化因素的现代派美学的特征,因而也隐含了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受波德莱启发而产生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明确地与贯彻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确性原则相对抗,强调艺术创作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莫列亚斯为此指出:“客观只向艺术提供一个极端简明的起点,而象征主义将以主观变形来构成它的作品”。
以毕沙罗、德嘉、希斯利、塞尚、莫内、柏斯·莫里索、勒诺瓦及居岳敏等为代表的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以他们的神奇的笔触,力图描绘那些昙花一现的流变以及景色的变幻不定性昙,艺术家以巧夺天工的技艺细腻表现的光线变异,则加强了色彩和轮廓的模糊性,使之在艺术作品中显现类似梦幻、细雨蒙蒙又像迷雾,既含糊不清,随时可以消失和重现,又隐约地随处飘荡,直至深邃无边的神奇世界;它是无法通过理性来捕捉,更不能用公式来概括。现代派所贯彻的这项原则,正是后现代派所赞赏、并要始终坚持的。反过来说,后现代派对于现代派所不满的,也正是它们未能把这一原则实施到底,致使现代派在实际创作中,在追求艺术形式美的传统框架内,断送了它们原有的变幻莫测的创作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具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双重性格的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和阿多尔诺,也先后以极大的注意力,珍视不确定性原则的创造性价值。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不确定性”,原本来自现代性,只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把它发挥到极点,以致反过来由此显示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
3、不确定性原则的反传统原则
“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它既然是无法确定和不可确定,就不能作为一个原则或逻辑概念确定下来,更无从讨论其内涵和意涵。同后现代主义的其他说法一样,它只是创作实践的一种实施和表达的策略。但是,它和后现代主义所隐含的基本特征一样,实际上更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悖论,其目的在于凸现传统文化深陷危机绝境的无可救药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同传统之间的不可共存性、不可翻译性和不可化约性。这种反传统的意向,早在二十世纪初就由杜尚在其作品《下楼梯的裸女》中显示出来;同一年,基亚果莫·巴拉也创作《奔驰中的汽车》,试图以动态的瞬时性,取代传统的静态绘画形式,打碎和超越欧几里德所确定的三维度传统空间框架。此后,后现代主义艺术沿着反传统的路线,无止尽地实施不确定性策略,试图从传统的单调乏味的逻辑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以便使艺术创作有利于表现各种带有神秘编码的偶然性,呈现更丰富的极端复杂的世界,特别是表现创作者在其创作过程中的极度自由的复杂心态。
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曾经采用油脂作为原料创造了《油脂椅子》的雕塑作品。油脂,在他那里,成为一种“可能性”的象征。他要让艺术本身变成为表达未来可能性的时空架构及其极度可变性。波伊斯明确地说:“如果我们不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核心、并在那里把它加以改造,现在的艺术也就不再可能成为艺术”;“在我看来,艺术是唯一的进化力量;达也就是说,只有从人的创造性出发,才能使环境得到改变”。他认为,艺术不应该停留在传统的描摹、模仿、审美想象的范围内,而是应该变成“可能的世界”的实验室,而且也应该成为各种超越极限的探险创造游戏的场域。
所以,约瑟夫·波伊斯的油脂之“在场”出现,意味着未来一切可能性的变化潜能;它是这种潜能的储存库,也是朝向各种可能的变化的神秘密码的集中缩影。这样一来,绘画就像一切创作活动那样,是一种“永远无法界定的自我延异”。艺术在这种创作的每一个刹那,也就超越出传统艺术的界限而成为非艺术本身。同样地,由美国后现代音乐家庄·凯兹所创立的“机遇音乐”,继承了荀贝克的“无调性”音乐的创造精神,成为了后现代音乐的一个典范。
庄·凯兹创造了一系列著名的“不确定乐曲”。他在一九五二年谱写出一首题名为《四分三十三秒》(4′33″)的钢琴曲。这部作品在演奏时,是一位身穿礼服的钢琴手走上台,安静地坐在钢琴前四分三十三秒,然后又一声不响地走下台。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正常”的乐声发出。庄·凯兹的《四分三十三秒》这部作品的创作和演奏,是后现代音乐以其自身的自我表演去实现对传统音乐的批判的典型范例。首先,它批判了传统的“音乐”概念本身。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的音乐对声音的探索,基本上建立在对“有规则”振动的“乐音”和不规则振动的“噪音”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所谓音乐,就是依据有规则、有规律振动及其调和的原理,以乐音的高低、强弱、音色的“节奏”、“旋律”及“和声”合理配合而成的一种艺术。因此,传统音乐把“节奏”、“旋律”及“和声”当成三大基本因素。
庄·凯兹的《四分三十三秒》这部作品却没有出现任何乐音,更谈不上其“节奏”、“旋律”及“和声”。庄·凯兹的《四分三十三秒》这部作品所展现的,是一种非乐音的寂静及其时空结构。听众以期待的心情所盼望听到的“音乐”,不像传统音乐演奏那样出现。但正是在这种沉默期待过程中所经历的特定时空结构,以及表演者和听众在其中共时地分别偶发出来的“惊异”心情,通过众目睽睽和焦急期待的复杂心态的立体式交感,通过在各个不同听众与台上演奏者之间紧张而奇妙的互动关系网的持续,使《四分三十三秒》这部作品的演奏,从原来似乎毫无内容的一片空虚,顿时自然地演变成台上台下各个不同心灵的无形神秘交感曲,不但时时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多元化的可能的创造内容,而且,也时时可能引爆出导向一切维度的创作方向和趋势。也就是说,时时隐含着向新的创作转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时时孕育着最多样化的创作动力和能量,时时可能爆发出由不同心灵的激烈震撼所产生的奇特交响乐曲。因此,沉默的时空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含苞待放的最美音乐花朵,是构成音乐创作的最丰富潜能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发源地。
由于《四分三十三秒》所开辟的“寂静”时空,提供了一个自由想象的世界,使得作者、演奏者和听者三方,感受到在这个新的世界中“一切可能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于是,这里提供的“寂静”时空,成为了最大音乐创作和欣赏的时机总汇。同时,《四分三十三秒》的演奏,也成为了艺术家和鉴赏者通过艺术再次直接地面对世界和生活的一个珍贵时机。正如庄·凯兹所期望的,在《四分三十三秒》的寂静中,艺术家和欣赏者开始聚精会神地注意到周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无目的和偶发的声音,不管是其中迸发出来的某种咳嗽声、天花板被风吹产生的嘎嘎声,还是哪位不耐烦的听众移动脚步的声音,甚至是某位听众自己的耳鸣声,这一切都深深地感染着那身临其境的人们,使他们再一次亲身经历了真正的世界本身;不过,这是在一次预想不到的“音乐”演奏中亲身经历的真正的世界。正如凯兹所说,他的作品无非是要人们“去认识我们现实的生活”,而且只是在艺术活动的本身范围内猛然发现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罢了!
总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必须让画家依据他本人在遭遇的情景中所形成的突发情感的驱使下,选择他的特殊表现形式,去表现和展示那些“不可表现性”。正如利欧塔所说“让人们看到存在着某种可以被构想、但不能被看到、也不能使它可见的东西;这就是现代绘画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