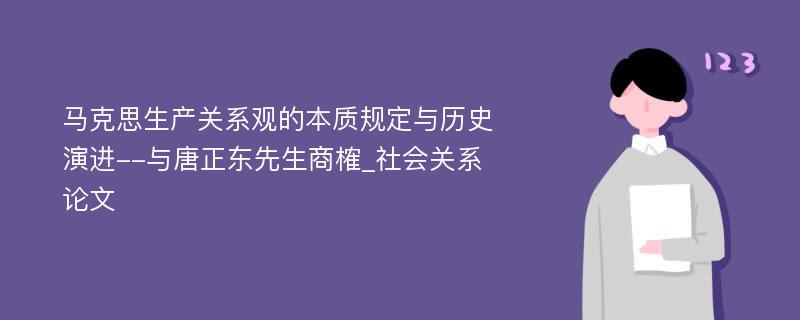
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嬗变——与唐正东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生产关系论文,本质论文,概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断加强并深化对生产关系概念的研究和认识,是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唐正东先生在《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的《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以下简称唐文)一文,堪称这方面最新、也最具颠覆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唐文的一个总的判断——马克思在1857年前后才完成了对生产关系概念的科学认识,此前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尽管有时候用的是生产关系概念,但他头脑中想的却只是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内涵”。——笔者不敢苟同,故作此文就教于唐正东先生,并希望以此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生产关系概念 就生产关系概念的本质规定而言,传统教科书提供了较早一点的解释:生产关系就是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唐文的解释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等内容。”可以说,唐文并没有给出像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或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的社会形式,或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这样的本质规定。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世界来看,把生产关系解读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空穴来风。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马克思,2004年b,第994页)但马克思这段话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这里的社会生活,指的是物质生活,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生活;相应的,这里的生产,指的也是物质生产,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生产。因为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物质资料或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特别是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包括同样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或技术关系。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分析表明,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关系不仅同权力关系有质的区别,而且决不能把像分工与协作这样的技术关系或劳动关系也纳入生产关系的概念之中。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同上,第922页)他还说:“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5-456页)很明显,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并且,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与劳动者相异化、相反对的权力。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就意味着生产了一种异己的权力。这种异己的权力决定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马克思,2004年a,第743页) 当然,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不是悬在空中的,这种关系只有借助于物,才能得以建构并表现出来。而体现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又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考察。其中,人与劳动条件之间的关系,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对此,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可以说,资本(以及资本作为自身的对立物而包括进来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对土地拥有排他的所有权,总之,就是存在着论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已经说明过的全部关系。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看作与生产关系相对立而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那种东西。人们谈到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马克思,2004年b,第995页)这就表明:不同的所有权,以劳动条件或生产条件在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配为前提。如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资本家和土地贵族的手中。在此意义上,不同的个人之于劳动条件的分配关系,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所有权的确立,因而是内在地包含了所有权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意义上的分配关系叫做“分配关系Ⅰ”,与此相对的,就是“分配关系Ⅱ”,即不同的个人对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劳动产品的各种不同的索取权。在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分配关系Ⅰ”构成一定生产关系,即一定当事人(如资本家)与直接生产者(如工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前者所执行的基于这种对立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没有“分配关系Ⅰ”,也就谈不上物质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和生产关系。至于如何看待“分配关系Ⅱ”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论述道:“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同上,第998页)这里,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劳动条件或生产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这种权力决定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而决定用于消费的劳动产品在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即“分配关系Ⅱ”。在此,马克思讲得也很清楚,“分配关系Ⅱ”是特定生产关系的表现。 由此可见,无论是所有制关系还是分配关系,都不过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和实现。在它们两者之间,则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不能一概而论。把分配和生产对立起来,进而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看成是构成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来看是缺乏根据的。这种划分法,与其说属于马克思,不如说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马克思讲得非常明确:“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但是,“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29页)这几个项目就是分配、交换和消费。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分为三篇,分别是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参见萨伊,第58、318、436页);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分为五编,其中第一编、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是生产、分配和交换(参见约翰·穆勒,第35、225、489页);首次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项目整合在一块的,当推约翰·穆勒的父亲、李嘉图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穆勒所著《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参见詹姆斯·穆勒,第5、16、50、121页)这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之所以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就四个项目之间的关系作出说明,只是因为它们构成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讨论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和背景。马克思的说明也只是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全面阐释这四个项目之间的所谓辩证关系,他甚至认为把这些项目板块化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资本论》所采用的基本构架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作为它们的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而不是像詹姆斯·穆勒那样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构架展开。这种结构安排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是一致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年a,第8页) 就生产关系概念的演化轨迹而言,一般的解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基本形成。只不过,生产关系概念尚未完全确定下来,他们常常把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联系起来表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有时直接使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有时也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并列使用。这说明,生产关系的概念还处于从交往、交往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形式等概念的“脱胎”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中进行选择。(参见黄楠森等,第448页)与此不同,在《哲学的贫困》这一文本中,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完全是以一种独有的科学术语来阐述他的崭新的历史哲学。生产关系这一重要范畴在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也得到了更准确、更科学的规定,它已作为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而被确定下来了,而且进一步精确化了。在这里,交往形式已被生产关系所代替,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作了明确的界定。(同上,第535-536、538页) 我们看到,在对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的理解上,唐文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是,在对这一概念的演化进程的把握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唐文看来:“马克思真正从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换方式的社会性质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概念之内涵的时间,应该在1857年前后”。代表性文本就是《导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具体来说,在《导言》中,“马克思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生产、分配、交换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详细和科学的说明”。这些说明以一种“崭新的学术观点”决定了马克思“从此之后一定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从交换关系或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了”。《手稿》就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从以下两个层面对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与交换关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解读”:其一,“生产关系是交换关系的发展形态”,前者因而是不同并超越于后者的。这也表明,马克思“已经从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质即生产关系的层面,去理解交换关系的性质了”,“交换关系不再是一种笼统的或者说自为存在的关系,而是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解读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时引进了生产力发展的线索”,把特定的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正是这种内含着生产力发展线索的生产关系,才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 关于《导言》中马克思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项目所作的分析,我们已经作了说明,唐文将之作为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达于科学的标志,其实并不科学。至于如何看待唐文所讲的,《手稿》才第一次确立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才第一次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这需要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的文本上来。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概念 唐文认同这样的事实:马克思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首次运用生产关系概念的。但在唐文看来,马克思此时对生产关系概念“其实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这表现在:第一,“他只是从笼统的一般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的”。第二,“马克思尽管在哲学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构建上已经达成了,但在对生产关系内涵之解读这一具体问题上,尚存在着一些遗憾”。这些遗憾如生产关系概念“与交换关系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尚未被明确地辨析”。第三,这使得马克思无法把握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发展的特征”。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不仅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交换关系等内容也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那么,是什么原因妨碍了马克思对生产关系概念的准确把握呢?唐文认为,“这跟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理解水平是直接相关的”。具体言之,第一,“此时的他还无法对手工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之间的区别作出准确的把握。对马克思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金钱关系或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之不同而已,而没有更多的实质上的不同”。第二,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本质其实还没有完全地把握住。这就使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大工业”。正因为此,“他选择了与斯密相同的视角,从分工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从交换关系、交往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发展。”第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生产方式便只是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方式,而所谓的生产关系便只是这些独立的商品持有者之间的交换或交往关系。” 从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论述来看,唐文提出的三条原因并不成立。在《形态》中,马克思从生产工具出发,把资本统治有别于地产统治的主要特点概括为:生产工具是由文明创造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各个人受劳动产品(而不是自然)的支配;彼此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个人通过交换(而不是通过家庭、部落、土地等)结合在一起;以人与人(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为主;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所有者依靠物即货币(而不是共同体)实现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工业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分工(而不是个人之间尚未分工)基础上的工业(而不是小工业)等。单从这一段论述来看,似乎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统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未能达到大工业的高度。但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非仅限于此,紧接着他就对资本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进一步分析,并把资本的统治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即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阶段,以生产和交往的分离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4-107、107-113、113-115页) 由此可见,第一,马克思不仅明确区分了(而非唐文所说的无法区分)手工业资本主义与大工业资本主义,而且明确区分了资本统治的三个不同时期。可以说,这种区分成为《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分工协作和机器大工业的最早的雏形。第二,马克思不仅从更为广泛的(而非唐文所说的仅仅从分工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他把生产工具从自然形态向文明形态的转变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把技术发明看作是重要的生产力等(同上,第107页),而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也已经深入到所有制和占有制(而非唐文所说的仅仅在交换关系、交往关系)的层面,例如,他谈到了所有制关系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第三,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显然是一种雇佣劳动(而非唐文所说的独立的商品持有者或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体所有)意义上的私有制,即是一种大私有制(而非唐文所说的小私有制)。固然,这两种私有制都以市场关系、商品货币关系、金钱关系为基础,但是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简单劳动关系,另一个则是雇佣劳动关系。其实,即便是马克思区分资本统治与地产统治的论述,也绝难说就是停留于交换关系或货币关系的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很明显,马克思的论述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远不是市场关系所能涵盖得了的。例如,马克思讲的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形式问题,就显然触及所有制和占有制这一最重要的生产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地产统治和资本统治的论述,加上他关于消灭了分工和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的论述,构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讲的三种社会形态,前者因而是后者的最早的雏形。 既然唐文提出的三条原因并不成立,其基本论点自然也就难以成立了。我们来看马克思的其他论述。马克思指出:“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90页)作为生产关系的体现和实现,从所有制和财产状况中产生的权力关系,意味着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在此,马克思把财产即所有制关系与社会权力联系在一起。当然,生产关系意义上的权力关系又不同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讲:“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同上,第133页)马克思还讲:“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同上,第68页)其意思是:在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存在着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因为,现实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与分工的发展相适应,分工发展的阶段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但是,这些关系不是悬在空中的,而是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离开了同这些物的关系,就不存在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在此,如果说所有制关系所指的,就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既表现为个人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即劳动条件的关系,也表现为个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由此形成“所有制关系Ⅰ”。如果说所有制关系所指的,只是个人与劳动条件或生产条件的关系,由此形成“所有制关系Ⅱ”,那么,个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不正是前述“分配关系Ⅱ”吗?至于“分配关系Ⅰ”,马克思的下列论述可援为佐证:“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同上,第127页)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些不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阐释的生产关系概念吗? 由上可见,第一,《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概念决不是一种笼统的一般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已经把生产关系提升到权力关系的高度,并且把它同劳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联系起来。第二,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辨析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之间的区别不假,但若由此以为,他把生产关系降格到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层面,进而把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混为一谈,就有诠释不当之嫌了。因为马克思不仅把生产与交往、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生产条件与交往条件相对置,更是明确地把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相对置。(参见同上,第122、129、126、122页)第三,以为马克思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特征,也是偏颇的。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同上,第68页)与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相适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前,先后出现了部落[Stamm]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69、70页),也即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关系。怎么能说马克思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特征呢?怎么能说只是在《手稿》中才出现生产力发展的线索呢?又怎么能说《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概念是不科学的呢?完全可以说,《形态》中的生产关系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唐文大大地低估了生产关系概念在《形态》中达到的水准。 毋庸讳言,《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概念有其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既不是单纯的表达方式或语言形式的问题,否则,就是过分地拔高了这一文本;更不是唐文所说的那种内涵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绝然不分的缺憾,否则,就决不可能有《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问世。在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方面,生产关系概念在《形态》中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但仍然有待明确、统一和完善。例如,马克思讲:“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同上,第71页)这里,马克思谈到了所有制,但是尚未明确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虽然已经使用了生产资料的概念(参见同上,第106页);马克思把所有制的结构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但是尚未明确区分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技术关系,虽然已经使用了与财产状况相关的社会权力的概念(同上,第90页);马克思把资本和所有制形式联系起来,但是尚未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和封建行会生产,虽然已经使用了不同于行会帮工和师傅的工人和雇主的概念。(同上,第110页)这些缺陷之所以存在,当然与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水平有关,但决不是唐文所讲的那种手工业资本主义与大工业资本主义绝然不分的水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形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阐释,而不是对任何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具体解剖。 三、《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概念 唐文对《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的看法是:在这一文本中,“生产关系概念不再是一个遮遮掩掩的概念,而是被作为核心概念提了出来”,并在“很多地方”得到使用。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此时“已经完全把握住了生产关系概念的准确内涵”。因为“马克思其实只是从分工关系、货币关系等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的,也就是说,就总体而言,他未超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从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内涵的思想水平”。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关系仍然是那种并不错、但“太笼统”的“生产过程所置立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因此他“在这一文本的有些地方依然把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概念混用在一起”。个中原因仍然在于没能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区别开来。这表现在:马克思还没有发现,“随着手工业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转变,原本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会演变成资本对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或者说演变成资本自身的增值过程”。由于没能“深入到这一层次”,马克思仍然只是“满足于对交换关系的关注”,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还表现在:由于马克思把“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作为“假定的理论前提”,他实际上“是以简单商品流通的社会为现实参照系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不可能把握住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最核心内容。在他的脑海中,只可能出现任何的生产过程都无法脱离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的交换、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等内容。” 唐文还认为,《贫困》的核心任务在于“批判蒲鲁东把分工、货币等当作固定的、永恒不变的范畴来看待的形而上学观点”,并“对这些生产关系范畴的历史产生过程进行客观的研究”。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缺陷,马克思“尽管已经开始了这种研究,但还远远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种研究”。从《贫困》的文本来看,唐文的理解与马克思的论述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第一,唐文对马克思下面这段话的解读是错误的:“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140页)在唐文看来,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仍然局限于从分工关系、货币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其实正好相反,马克思是站在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分工和货币等经济范畴的。他明确指出:“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同上,第119页)这种社会关系也不像唐文所说的那样笼统,它就是生产关系:“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像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同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范畴,必然要反映和体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第二,唐文对“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的所谓“假定的理论前提”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假定前提不属于马克思,而是属于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布雷和完全沿袭了布雷思路的蒲鲁东。他们二人都认为,消除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唯一出路,就是整个社会仅仅是由以工资形式领得自己的产品的直接劳动者所组成,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费用或蒲鲁东所说的构成价值决定,在市场上相等的价值总是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马克思认为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因而在交换经济存在的前提下,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参见同上,第99、114、116页) 第三,就《贫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而言,决非如唐文所说的,仅仅局限于简单商品流通的社会,而没能达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高度。就拿唐文所讲的马克思脑海中出现的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的交换来说,它固然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并且遵循着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但决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范围内的交换,更不是任何的生产过程都无法脱离的交换。因为这种交换在本质上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话说,就是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它反映和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包括大工业)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正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参见同上,第135页)怎么能说马克思没有达到机器大工业的高度,没有深入到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层次,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呢? 第四,就《贫困》对蒲鲁东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而言,唐文大大低估了这种批判的力度和深度,因为它大大低估了马克思对分工、货币等经济现象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水准。以分工为例,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在分工和机器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不仅阐述了分工的历史性:“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现代工厂里我们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同上,第170页);而且像《资本论》及其手稿一样,把社会内部的分工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分工区分开来:“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同上,第165页)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货币等经济范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决定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又决定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马克思讲:“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同上,第155页)可见,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性的研究决不是一个开始了这种研究所能表达得了的。 唐文还认为,由于马克思在《贫困》中引入了比《形态》“更为强烈的阶级对抗的理论线索”,所以,“他此时在从交换关系的角度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时,已经不再停留在简单的交换关系的层面,而是进入到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的理论层面,尤其是作为积累劳动的资本与直接劳动的不平等交换关系的层面”。进而,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在经济学上接受了旨在研究“全部产品”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法则问题”的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所以,很自然地就把上述“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推进到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关系的理论层面”。因此,当马克思“在思考生产关系概念时,其解读视域已经深入到了分配关系的层面”。 即便如此,在唐文看来,由于“依然从物的维度上把资本理解为积累劳动,而不是从关系的维度上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甚至是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此时所具有的分配关系的理论层面与其原来具有的交换关系的理论层面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后,由于《贫困》重点阐述的“是经济学范畴在整个私有制社会中的形成过程,而不是这些范畴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变化过程”,所以,马克思就不可能“意识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分配根源于其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其交换的社会性质”,因此,也就不可能“从分配关系的理论层面中生发出新的理论质点”。 唐文的这些观点同《贫困》的文本也存在不小的距离。第一,唐文对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的交换的诠释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讲:“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唐文先是认为,马克思把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的关系看成是任何的生产过程都无法脱离的商品与商品之间平等的交换关系,并由此断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局限于简单商品流通的社会;随后却又把它解读为资本与直接劳动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并由此断言马克思从简单的交换关系层面进入到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层面。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来看,唐文面临着一种二律背反:承认马克思看到了交换的不平等,就得同时承认已经深入到生产关系层面;否定了后者,同时就否定了前者。因为无论是简单商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无论是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大工业资本主义,在市场交换的意义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都不违背等价交换规律。要认识到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不平等交换,要说明这种不平等,就决不能停留在市场交换关系的层面,而是必须深入到生产领域和生产关系的层面。 第二,即使撇开上述矛盾不谈,唐文对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理解也有悖于马克思的论述。就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而言,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马克思,2004年a,第669页)商品交换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过程。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同处一个层面,怎么能把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说成是一种思想内容上的深入或推进呢?客观地说,唐文在这一点上也有前后矛盾之嫌:先是认为是一种推进,随后又认为两个层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在《贫困》中指出:“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由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是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决定生产关系。可见,事实并非唐文所说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第一次确立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 第三,就对资本本质的认识而言,唐文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仍然理解为一种物即积累劳动,而不是生产关系。其实正好相反,在《贫困》中,马克思反对在物的维度理解任何一个经济范畴。他说:“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同上,第163页)物不是经济范畴,因为“范畴只是它(指生产关系——引者注)在理论上的表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同上,第140、143页)这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论述是一致的。如在谈到劳动的价值时,马克思讲:“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像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马克思,2004年a,第616页)即使像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这样的非科学概念,在本质上也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和体现,何况是资本概念呢?在《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权力即资本”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6页),并把它具体化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同上,第180页)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参见同上,第180、184、190、189、192页)可以说,《贫困》对资本范畴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它在生产关系的高度和角度理解和认识一切经济范畴,生产关系从而升华为一种方法论原则,由此确立了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就《贫困》阐述的重点和主旨而言,经济范畴的历史运动,肯定如唐文所言是一个重点。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因为是经济关系的运动决定经济范畴的运动。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不仅批判了蒲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形而上学观点,而且批判了被他扭曲了的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在思想认识上,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高度的,是蒲鲁东而不是马克思;看不到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及其现实基础的,也是蒲鲁东而不是马克思。特别是,蒲鲁东的观点会给正在勃兴的工人运动造成不良影响,所以,马克思阐述经济范畴的本质及其历史性,阐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特质,最终目的在于为现实的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引导。在《贫困》中,马克思多次提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上,第139、154、156页),怎么能说他对经济范畴的阐述没能达到资本主义的高度呢?至于唐文所讲的新的理论质点,难道说在生产关系的高度上理解和把握经济范畴的本质及其历史性,从而首次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合,不就是这样的理论质点吗?实际上,即便是蒲鲁东,即便其观点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也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其理论仅仅局限于简单商品生产的水平。 当然,虽说《贫困》比《形态》讨论的经济问题更为广泛,站得层面更高,但由其论战的特点决定,它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讨论尚待具体化、精确化;由剩余价值理论的缺席决定,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阐释尚待具体化、精确化。因此,《贫困》不可能达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水准。但是,唐文显然大大低估了《贫困》的理论水平,一如它大大低估了《形态》的理论水平。标签:社会关系论文; 唐正东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产品概念论文; 哲学的贫困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资本论论文; 所有制论文; 经济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