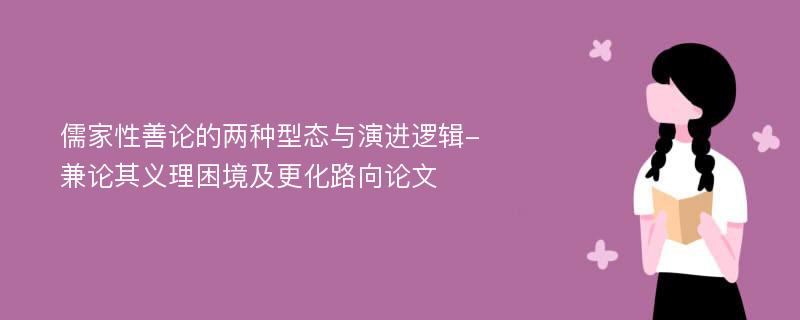
儒家性善论的两种型态与演进逻辑
——兼论其义理困境及更化路向
邹晓东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 要: 儒学史上存在两种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回归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历史地检讨这两种性善论的学理得失,可以有效地促成儒学义理的更新转化。作为最原始的性善论形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始于《中庸》对无所不在的“真知”问题的着重揭示与专门回应,这是一种融贯一致且以“率性”意识为中心的性善论。其短板在于:无法有效容纳传统德目与施教权威,其服膺者在“自作主宰”精神的鼓荡下,往往难以组成和谐有序之社会。“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试图以传统德目规定“善性本体”,这固然容纳了社会智识传统与政教权威,但却因为推崇、仰仗既定的教义与外在的治教,而架空或放逐了内在善性即时指引的活泼功能,故实质性地落入“重教— 外铄— 性恶”的荀学思路。论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性善论。在“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基础上,自觉引入或充分强调“率性的处境”与“共识的更新”这两个维度:将“传统教义”“施教权威”以及“他人异见”统统归入“率性的处境”范畴,并力求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在新处境下的率性体认”,不断就公共事务达成“新的共识”—— 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机制,应是传统儒家性善论更化升级的新路向。
关键词: 真知问题;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率性的处境;共识更新
流行观点认为,性善论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界定性体,将儒家对传统伦常的持守提升到了本体论层次。这种观点确实可以获得经典文本的支持,如《孟子·公孙丑上》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在此基础上,朱熹《大学章句序》理所当然地提出了“仁义礼智之性”的提法。就此而言,将儒家伦常“塞进”善性本体,进而再以善性本体之名义捍卫之,这似乎就是儒家性善论的基本使命① 例如,作为这种流行观点在国际中国哲学研究舞台上的代表,余纪元教授在其比较研究代表作《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这样评论“性善论”在孟子那里的兴起:“孟子在捍卫孔子之‘道’时清晰地提出了这一理论。孟子发展其‘性善论’理论的主要动力,在于应对各种对立哲学流派对孔子‘道’论的严重挑战”(第101页);“这些缺陷由孟子填上。他的策略似乎是这样的:墨子和杨朱提出的严重挑战在于他们声称天道在他们那边,而孔子之‘道’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如果孟子能证明人的真正本性是一些不同于追逐、保存利益之物,那么墨子和杨朱的立场就都失去了根基。如果孟子能进一步证明我们人类的真正本性是最终导向孔子之德性的事物,那么他就成功地论证了孔子的观点才与天道相符。据此,孟子为了击败墨子和杨朱,由此论述真正的人性,并表明孔子的价值是人性固有的,而发展了另一套‘性’论”(第103页)。 。但儒学中还有另一种性善论传统:虽然认定性善,却不界定善性本体的具体内容。《中庸》开篇在提出“天命之谓性”命题(而在就敬天情感中认定此性为善)之后,丝毫没有留恋性本体的界定问题,而是紧接着抛出了“率性之谓道”命题,并通过“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等提法,大谈特谈“率性”体验① 由于本体论思维的流行,学界往往不注意《中庸》首章未对“性体(本体)”进行具体界定的文本事实。相反,在本体论思维中,读者们倒是倾向于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视为《中庸》对“性体(本体)”内容的一种界定。对此,我的反驳是:首先,“喜怒哀乐之未发”是一种人为可控的主观心态,而非没有任何意识活动的原始的寂静状态,否则读者将无法把这句话转化为功夫实践,因为任何“转化”都伴随着人为的、知情一体的意识活动。其次,下文“致中和”的“致”字,明显指称特定的人为努力,也就是说“中”(包括“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而非天生固有的本体。实际上,金景芳先生早就指出:“朱熹给《中庸》作注,说‘其未发’是性,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对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本’是根本,形容重要。‘天下之大本’就是天下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什么事都能做到中,那是最好的,所以是‘天下之大本’。”在金先生看来,“中”非“天命之性”,而是需要人为努力才“能做到”的。说见氏著:《论〈中庸〉的“中”与“和”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 。在不界定性本体的情况下,直接谈论率性,这是《中庸》作者理论思维“幼稚”所致吗?若是,则极力推崇孟子“良知”概念的王阳明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明知孟子“四端之心”及朱子“仁义礼智之性”等学说的情况下,王阳明却转而旗帜鲜明地倡导“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轻飘飘的一句“受了禅学影响”,真足以解释王阳明的这种转向?我们则认为,《中庸》不界定“天命之性”本体,与王阳明力倡“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二者委实相映成趣地反映了儒家性善论的另一种思维,即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②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倪培民教授的《从功夫论的角度解读〈中庸〉——评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英译》(《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这篇文章,以及陈明教授提出的“即用见体”这个概念(参考陈明:《即用见体再说》,陈明主编:《原道》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天心:《文化的政治:陈明的即用见体与公民宗教说——大陆新儒学试析之二》,《博览群书》2007年第12期)。倪教授认为,《中庸》以及《孟子》里的所有核心概念,均旨在推荐相应功法,而非构建形而上学或表达实体宇宙观。陈教授的“即用见体”提法颇具启发性,但他本人更措意于用此提法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建构张目,并未由此发展出专门的《中庸》解释。 。
就现象而言,儒学中确实存在两种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针对这两种性善论,本篇重点关注:一、从发生学角度看,哪种性善论更原始?二、驱使它出场的问题意识又是什么?三、逻辑地看,哪种性善论更融贯?四、儒家究竟在什么意义上需要一种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五、在二者的分歧与竞争之中,蕴含着何种未竟的问题?六、有无可行的解决渠道?从“天命之性”到“四端之心”,从“仁义礼智之性”等提法再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通过考察儒家性善论的不同形态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上发生的动因和演进逻辑,本篇将和读者诸君一道思考上述问题。
人才培养注重与实际相结合,避免轻实践、重理论的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在校期间,以学期为阶段对学生的实践、管理、个人能力进行分段式培养,避免突击式、短期外出游玩式的实践考察活动。每个单独的学期进行实践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课程体系的设置由浅入深,使学生的专业能力在每一个学期结束后都有明显提升。建立系统的实习计划和渐进式能力培养课程体系,课程设置要符合学校的地理位置特征,避免千校一面、开设课程重叠化,突出区域特征,形成特色鲜明的培养模式。加大选修课力度,丰富多样、层次明晰的选课设置对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一、“真知”问题与“率性”意识的发生
《论语》中的人性论,以《阳货》篇中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最引人注目。单看前半句,此“相近”之性,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还可以是“善恶混”“无善恶”或“可引为善,亦可引为恶”“有善有恶”“中[品]即相近者”等③ 参考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四册,第1177-1184页。其中,受宋明儒学“性善论”意识熏染,顾炎武、李光地等主张:“相近,近于善也”或“‘性善’,即相近之说也”。由于宋明儒学(推崇孟学,强调性善)传统的强大,这种解释颇有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宋明儒学的代表性人物朱熹和程子则认为:“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参见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5-176页。 。半句“性相近”留下了近乎真空的发挥空间,就此而言,孔子并不太重视“性”论。《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感叹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推崇性善论并以其为正统义理首要组成部分的宋明儒学而言,“夫子(孔子)罕言性”是不合常理不可想象的,诸如“圣门教不躐等”之类的解释遂逐风而起④ 朱子一方面承认“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另一方面则追随程子“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认为“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参见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79页。关于本章历代解释,还可参考甘祥满:《〈论语〉“性与天道”章疏证》,《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3期。 。但按诸《论语》全书,“性”字仅两见(两处文本以上皆已征引),实在算不上突出的议题。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圣门教不躐等”的教学次第,而“性”论被设置为高阶教学内容,这至少也意味着“性”论并非孔门为学修德必先明了的基础议题;换言之,绕过“性”论,学者也还是可以为学修德。综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毋宁意在引导听者将注意力集中到“习”上① 戴震在一定程度上持这种解读:“孔子但言性相近,意在于警人慎习,非因论性而发,故不必直断以善与?曰然。”转引自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四册,第1179、1181页。 :“性”既是天生的,又是众所相近的,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原始而普遍的现象而已,真正的生存问题出在“习相远”的“习”上。“习”既是后天的、人为的,也是五花八门差异极大的,特别地,在未经学习和修养的情况下它往往是恶的。
那么,什么是“好的习”,又如何获得“好的习”呢?前一个问题可以从“恒”,也即“稳定的品格”角度来思考。《论语·子罕》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偶然的好行为尚构不成“好的习”,严格意义上的“好的习”必须能够经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论语·子路》有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所处理的往往都是超常规事项,“卜筮以决疑”即意味着当事人已经走到了知识或经验的尽头——而即便在这种非常规的情况下(即不得不求助于巫医② 笔者当然注意到了“无恒之人,即巫医贱业亦不可为”这种解释,然而根据上下文,笔者更倾向于“巫医不能治无常之人”(“作,立也”)。参考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三册,第932-934页。 ),孔子仍然主张坚持上述南人谚语所传递出来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遵守常规德目”之精神。“好的习”归根结底即“稳定地践行常规德目的品格”,那么,如何养成这种“稳定的品格”呢?
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认为,《论语》以“学而”开篇,实际上是有深意的。王博教授指出,较之“思”,“学”的外向性更加突出[1]。换言之,“学”需要有外在教材或学习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学”往往被解释为“效”(效法、仿效)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学而”之“学”曰:“学之为言效也。”持心学立场的毛奇龄则认为,强调外在的学习对象(师法、榜样、文本)等于架空了学者原本饱满的自主性,故而批评朱熹“训实作虚”。毛说见氏著《四书改错》,转引自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一册,第3页。毛奇龄的解释实际上是将《论语》往更加纯粹的心学思路上归化,背后则有“正典一体,承载一以贯之的道统真理(解释者所认定的‘最佳义理’)”这种非历史的解释学预设作为推手。 。对于孔子来说,周“礼”或周“文”,是基本的研习教材;通过研读文本(包括某些口头叙述)而还原或体贴出来的周公乃至尧、舜等形象,则是“好的习”或“应然之品格”的卓越代表。对于孔子的学生来说,作为文本的“礼”或“文”同样也是他们的学习教材,而学养深厚、品行粲然可观的孔子则是现场指导他们进行学习的教师。在不断回答弟子“问仁”、“问礼之本”、问“为政”等问题的同时,孔子也不时就学生的某些理解、言行、品格进行点评,如《论语·先进》所记“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等。孔子通过言语指出“过”与“不及”等问题,意味着这些问题可以在“理解”(认识到问题之所在)的基础上加以改正——这既是“知识-理解”问题的具体提出,同时也是对具体的“知识-理解”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直接依赖于孔子的卓越学识、个人修养与洞察力。这是权威教师在场的“学”,也即直接受惠于教师指导的“好的习”的养成机制。作为一部由弟子及再传弟子集体编撰(不同的弟子圈进而汇成孔门集体)而成的语录体作品,孔子的言论显然构成了《论语》中判别是非对错的权威。
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众望所归的权威教师不复出现,对于孔子语录的理解(乃至取舍)也出现了分歧。倘若孔子在世,或可通过现场指导指示正路化解分歧;而孔子一旦离世,何为“真孔子”(如何理解孔子语录)都成了问题④ 《韩非子·显学》触及到了此一问题,其曰:“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又曰:“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进言之,在缺乏有效的现场指导的情况下,准确理解孔子思想由以脱胎而来的“礼”与“文”(一系列古代文献),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知识-理解”问题?
作为另类孔子语录,《中庸》的语录体部分,旨在向读者呈现另一种孔子精神。《中庸》作者有意识地将孔子论述“中庸”及“过”与“不及”的语录进行了逻辑性较强的精心选编① 《中庸》中的孔子语录绝大多数可以在《论语》中找到相似或相关者(参考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上)》郭沂撰第三章第一节《〈中庸〉其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2-287页),但必须注意的是,与《论语》比较,《中庸》对孔子语录的遴选与编连是为叙述、探讨编者所特别关注的问题与方案服务的。 ,一方面将包括知者、愚者、贤者、不肖者在内的一切生存者皆置于非“过之”即“不及”的普遍出错境地,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普遍的“过”与“不及”归结为“鲜能知味”,即当事人的“知识—理解”出了问题。
《中庸》这种广义上的知识论溯因,同《论语》在“有恒之德行”意义上强调“品格”,形成了鲜明对照。要之,在《论语》式“好的习-稳定的品行”视野下,最不容宽恕的是“恶习”,就是“知而不行”意义上的“无恒”。按前面的分析,在有权威教师(孔子)在场的情况下,“知(知识-理解)”从根本上被认为不成问题——学生可随时向老师请教,老师也可随时因材施教予以指点,只要“教—学”双方能够持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品行,学生的“知识-理解”问题将自然而然得以解决,只是一个程度如何、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中庸》却反其道而行,它所选编的孔子语录中有这样两句,其一:“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其二:“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第二句中的前半句意味着人所自称的“予知”实际上是错误的“知”,否则当事人就会知道避开罟擭陷阱了;后半句意味着所谓“知而不行”(能“择”不能“守”)实际上是“不知”——若真切地知道所择为善,必会心悦诚服践行之。实际上,第一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已经点明不“知味”才是一切行为偏差的总根源② 对于这种“知行一体”的思想,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生存分析,谢文郁教授短文《真理情结:从柏拉图到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4日,第6版)对此作了清晰的梳理:“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人皆求善’命题时,遇到一个问题:从经验观察出发,似乎既有求善者,也有求恶者。如果人皆求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苏格拉底采取了一种排除法的论证。他说,在现实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人求善(A),有人求恶(B)。有人善恶不分而以恶为善,在善的名义下求恶(B1),有人明知为恶而求恶(B2)。进一步,有人明知为恶但因为有利而求恶(B2-1),有人明知为恶且无利而求恶(B2-2)。就广延来看,这里的A+B1+B2-1+B2-2等于全部人。显然,A是求善者;B1在自我意识上也是求善者(虽然善恶不分);对于B2-1,如果把‘利’理解为暂时利益,尽管目光短浅,但当事人认为他是在追求善;B2-2是空项,无法找到个例,人不会选择从各个角度看都是恶的事物。由此看来,在现实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在追求善。至于那些被认为是追求‘恶’的现象,原因在于人们的善恶观念出了问题。” 。这样,通过有计划地选编孔子语录,《中庸》突出地表现出了直面“真知”问题的勇气。
较之《论语》,《中庸》这是在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论语》中,孔子是师尊,是学生获取真知的源泉。在《中庸》中,孔子仍然享有无与伦比的权威,但这位权威却旨在向学生挑明“真知”问题,并要求学生直面此“真知”问题。对此,可以做下述分析与追问:作为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知识-理解”或“真知”问题既然也普遍发生在孔子的学生身上,而且这一问题既然是几乎无可挑剔的优秀教师孔子本人在感慨中加以指出的,那么,解决此问题的最终希望就不在教师(包括作为历代教师之遗教的各种文献)身上,而只能落在每一个学生自己身上,否则,为什么要感慨并责备学生,而非责备教师或教师自责呢?相应地,“知识—理解”或“真知”问题就进一步转化为:学生本人凭什么能够肩负起解决“真知”问题的重任?
(26)长刺带叶苔 Pallavicinia subciliata(Austin)Steph.李粉霞等(2011)
健全畜产品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对畜产品生产实施全程监控。从源头上抓实养殖业投入品监管。重点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使用兽药、饲料及“瘦肉精”等添加剂的行为,有序推进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退出,严格处方药物监管,逐步规范规模养殖场用药休药期制度的执行,保证养殖源头安全。做到不加工、不食用、不销售、不转运、不丢弃,对病死畜禽尸体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病死畜禽及病害猪流入市场。
二、“如何率性”与“四端之心”
设定了生而固有且绝对可靠的“真知”源泉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如何切实利用此内在资源处理“真知”问题?《中庸》开篇第二句“率性之谓道”,即是在言说对此内在资源的利用问题。“率性之谓道”,在“真知”问题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体察内在固有之“性”的发见或指引,由此获得的“应然”方向感(作为一种“知识—理解”),即当事人在处境中所当行的正“道”。就此而言,“天命之性”是人“生而固有且绝对可靠的内在向导”,“率性”即“体察此内在向导的指引”,“道”即是“对性之发见或指引的体察(由此而来的应然方向感)”② 参考拙作:《〈大学〉“明德”并非〈中庸〉之“性”——基于思想史趋势的考察》第一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该文修订版见拙著:《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第二章)。 。相关术语大致可作以上梳理,但落实为生存意识,究竟何为“性之发见或指引”,又如何“体察性之发见或指引”?换言之,何为“率性”,又如何“率性”?
在2016年中国诠释学大连年会上,台湾大学哲学系李贤中教授曾针对笔者重释《中庸》首章的会议论文如此评论道(大意):尽管你主张性本体是不可界定的,一旦界定就会堕入“以教蔽性”的误区,但这种“不界定”不也正类似于国画中的“留白”,实际上还是在发挥着某种界定作用吗?顺着李教授的上述评论,我们还可以对“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提出更多“知识—理解”上的追问与探讨:
取干燥的具塞试管3支,分别编号为1、2、3,在3支试管中均加入5 mL乙醛、0.1 g乙醛脱氢酶和1.5 g余甘果果肉,分放在30℃、37℃和40℃下放置10 h,然后测定乙醛含量。每组实验均做3组平行实验。
《中庸》首章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和“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来言说作为“率性”的“慎其独”。“率性”意义上的“慎其独”不再纠缠于“独处”还是“有人关注(监督)”这样的问题,而是更关心当事人能否直面并体察作为内在固有资源或向导的“性”的发见或指引。这样,“慎其独”的“独”字,在《中庸》语境下便不再指称“独处”,而是指当事人自身固有之“性”——除了当事人自己,其他人根本无法直面并体察当事人内在之“性”在具体处境中的发见或指引,故而,这只能是一种“独知”① 朱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这个提法,用来翻译“慎其独”。这个提法既可以理解为“因为是独处,无他人或监督者在场,故人不知而己独知”,也可以理解为“性之发见是个人内在之事,故而只能是己独知之”。前一种理解适用于《大学》,后一种理解适用于《中庸》,可见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准确的翻译。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提法既可以做《大学》式解读,也可以做《中庸》式解读,严格来讲它并不是一种解释——至少不是一种准确的解释(我们因而称之为“翻译”)。朱子的论述参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7、18页。 。特别地,作为能动的向导,“性”在处境中的发见或指引是活泼而常新的,当事人不应沉溺在既往的“率性”体察中。任何既有的“率性”体察,都是一种现成的“知识—理解”,本质上都是“可睹”“可闻”的对象。“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则要求当事人不断从“既有体察(现成的‘知识—理解’)”中摆脱出来,在随时变迁的处境中不断地重新体察“性”之发见或指引。换个角度看,只有从“既有的体察”中摆脱出来,进入一种“无所睹”“无所闻”的“中立”心态② 所谓“‘中立’心态”是对“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的功夫论解读,此不同于传统的或流行的本体论解读,可参考拙作:《〈中庸〉首章:本体论误区与生存论新解》,《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 ,当事人才能腾出注意力重新体察下一时刻的“性”之发见或指引。“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和“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所形容的,正是这种“摆脱出来—腾出注意力”的“不断重新体察”。但是,“出错”的风险仍然存在。一方面,人有记忆的能力(包括对几乎遗忘的东西进行回忆),而且我们似乎也不能指望“性”在相似处境下做出迥异的发见或指引。那么,如何区分“对既往体察的记忆(回忆)”与“对‘性’之发见或指引的实时体察”呢?另一方面,“执念(沉溺于既有的体察或‘知识—理解’)”也未必是一成不变。例如,爱财之心在特定处境下是合理的(出于实时的“性”之发见或指引),但沉溺并执着于特定的爱财样式则会被称为守财奴,而守财奴本人在深深感受到这一外号的讽刺效果之后也可能转而变得奢侈,但奢侈之心仍然是以爱财之心为本位的——在很大程度上,上述转变只是同一种“执念(知识—理解)”的不同表现,因而算不得是在“重新体察‘性’之发见或指引”。鉴于诸如上述风险或误区,“何为率性,如何率性”的问题,遂必须被重新摆上桌面。
《中庸》后半篇用“诚”来言说“率性”,有诸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的提法。然而,仅从“诚”“诚之”“曲能有诚”“至诚”等多样化的提法中,读者约略可以窥知:这里实际上还存在着“何为真正的诚,如何做到真正的诚”的问题。这实质上也是将“真知”问题反加给了“率性”,而遇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平心而论,《中庸》只是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但并未给出有力的解决方案——“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一旦提出,则“率性”自身就成了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无法充当“上手”状态的“真知起点”。为此,在临近结尾之际,《中庸》试图将“什么是真正的诚(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诚(真正的率性)”问题推给出神入化的“至诚—至圣”者;然而,这种美好的想象要想成为落地生根的现实方案,其路程之遥,远远超出了《中庸》作者的所料。
以上无休止的学理辩难,还是从“思想学说不断发展”的“开放”角度而言的。本文第三节马上就要考察的“仁义礼智之性”等概念与“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以一种“独断(偏执)”的方式继承了上述《孟子》“性善—四端之心”说的学理瓶颈。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性善—四端之心”说只是《孟子》性善论的一个方面,《孟子》中其实同时还蕴藏着“善性本体不可界定”的意识,其中,最具感染力的就是其藉“揠苗助长”寓言表达出来的“勿助长”意识。《孟子·公孙丑上》所批评的“助长”,实质上就是“以现成的‘知识—理解’取代对于‘性之发见’的即时体察”,“勿助长”的提法则意味着孟子对于现成的“知识—理解”与即时的“性之发见”之间的分野还是有相当深刻的体会的。故尽管《孟子》的“四端之心”启发了儒学史上的“仁义礼智之性”等概念,但就思维方式而言不可谓《孟子》只有“界定本体的性善论”。
无论如何,生而固有且绝对可靠的“天命之性(善性)”,如果只发见为上述“四端之心”,或者只通过上述“四端之心”发布内在指引,则“率性”就会是一桩相对简单的事情。凡是内心直接涌现出来的带有“恻隐”、“羞恶”、“辞让”或“恭敬”、“是非”四种标志的“知识—理解”,便可判定为“性”之发见或指引(也即适切处境的“真知”),并坚定地予以顺从执行;凡是无此四种标志的“知识—理解”,则可以忽略不计,且绝不将其落实为行动。除此之外,无需再为其他事情操心。而正因自认为找打了简便易行的“率性”门径,《孟子·尽心上》开篇才会豪迈地宣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养”字,朱熹解释为“顺而不害”(而非意味着“性由不完善成长为完善”)[3](P349),而从根本上规避了“性不完善—有待养成”的歧路(有待完善的“性”不值得“率/循”),可谓不以辞害意,得孟子“四端之心—尽心—知性—知天”之“性善论”思路的精髓。
不过,《孟子》即“四端之心”言“性善”,固然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率性”门径,同时也强化了儒家主流德目的权威地位(“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但在学理上也留下了聚讼难解的公案。例如:凭什么说“性”只有“四端”?孟子之后,“信”的地位不断提升,“仁义礼信智”或“仁义礼智信”合而为“五常”——“信”难道不应该在孟子式“性善”论中有相应的一“端”吗?《大学》强调“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荀子》亦推崇“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静”为什么就不能成为重要的一“端”(乃至据此将老、释吸纳为儒学的分支)? 《大学》、《中庸》、《孟子》皆推崇的“诚”字,如此重要的范畴,为何未被列为一“端”?退一步讲,如果本着思想学说“不断发展”的意识,将上述“信”心、“静”心、“诚”心统统补充为“性”之“端”,那么这些“心”或“端”之间又应该有着怎样的秩序?在具体操作之际,应该首先关注看起来更抽象(或遍在)的“静”、“诚”,还是首先关注看起来更具体的“仁义礼智信”?以此反观,还可以追问:《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之间,究竟是相互平等呢,还是其中一者统摄其他三者?更严重的是,这种“发展”“补充”有无尽头?如果没有尽头,则无论尽“四端”之心还是尽“五端”“六端”“七端”……之心,岂不都是一种“偏执”,根本无法通达“知其性—知天”的圆满境界?
而面对“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这一具体操作问题,孟子的“性善—四端之心”便显出了它的优越性。唐君毅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将孟子定位为“即心言性”,所谓“乃就心之直接感应,以指证此心之性之善”,“此心之性为善,又兼可由心之自好自悦其善以证之”[2](P13),此所谓“心”即“人之仁义礼智之心”[2](P16),《孟子·公孙丑上》称之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也。”《告子上》又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以“四端之心”言“性善”,最大之便利就是使“率性”有了切实可行的门径。上述《孟子》引文所提倡的“能”与“思”,无非就是留意“四端之心”在吾人内部之发动,顺从遵行这四种特征明显的“心态”驱动。
三、“仁义礼智之性”与“界定本体的性善论”
上节指出,《孟子》的“性善—四端之心”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率性”的具体门径提出来的。这是对《中庸》后半篇所触及到的“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的一种回应。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亲切有味的体验式现象指点,《孟子》即“四端之心”言“性善”的做法,大大增强了“性善”的可信度。顺此,自然会出现这样一种理论冲动,即从“性体(善性本体)”中寻找作为“用”的“四端之心”的根源。“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由此步入思想史舞台。
如何界定作为本体的“性”,特别地,如何才能在“性本体”中找到“四端之心”的对应物(作为根源)呢?按“天命之谓性”,论者如能在“天生人生物”的机制方面有所建树,那么他就可以凭着自己对这种机制的了解,谈论“天”所赋予人、物之“性”的具体内涵。这是一种“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一体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在汉代非常流行① 汉初流行所谓“黄老”之学。我们知道,《老子》既将“道”视为宇宙的本源(“始”+“母”),又认为万物既生之后仍然以“道”为本体(“贵食母”),宇宙论、生成论与本体论在此显然是不分家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一体,乃是跨学派的交叠共识。著名的儒术提倡者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三中,提出了掷地有声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5页)。“道出于天,天中有道,道本于天”正是一种“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合一的思维。张岱年先生曾使用“本根论”作为其《中国哲学大纲》第一部分宇宙论之第一篇的标题,这显然正是基于传统中国哲学“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往往不分家的考虑。可参考氏著:《中国哲学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7-40页。 ,《礼记正义》注疏正是在此种框架下解释《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孔颖达疏与郑玄注一脉相承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什么样的天以什么样的方式命生什么样的性”问题上。其中,郑注曰:
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
孔疏进一步解释曰:
这几年来,眼睁睁看着房价攀升,易非不是没动过买房的心,只是,她觉得自己的钱似乎应该有更大的用途,她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向南开家影楼,或者成为一笔小小的原始资本,她甚至比向南更渴望功成名就,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要替爸爸活着,要为爸爸扬眉吐气。可这一次,敏之姐的话,真的在她心里留下涟漪了。
“天命之谓性”者,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但人感自然而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之谓性”。
(1)砾类土单层土体。主要分布在该地区南部的陡坡和坡脚堆积区。陡边坡和坡脚主要由厚度较大的单层砾石层组成,填砂,结构密度略高,粒径较好,骨架颗粒连续接触,地层相对均匀,工程地质条件良好。依据区域经验值,承载力特征值可达300 kPa以上。
……云“《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不云“命”者,郑以通解性命为一,故不复言命。但性情之义,说者不通,亦略言之。贺玚云:“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案《左传》云‘天有六气,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类,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独禀秀气,故《礼运》云‘人者,五行之秀气’。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义、礼、知、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则性之与情,似金与镮印。镮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镮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则性者静,情者动。故《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故《诗序》云‘情动于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为五常,得其清气,备者为圣人;得其浊气,简者为愚人。降圣以下,愚人以上,所禀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为九等。孔子云:‘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论语》云:‘性相近,习相远也。’亦据中人七等也。”[4](P1988-1999)
有学者曾反复强调,汉儒将阴阳五行的宇宙论纳入儒学体系,是儒学体量的一次巨大拓展② 参考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见《中国思想史论》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39-180页。劳思光先生有类似的观察,但观点比较消极,认为“汉儒卑陋,只讲一种‘宇宙中心之哲学’”,“由战国至秦汉之儒者所建立之形上观念,对后世之影响,乃有时超过孔孟之说”,“而其结果,则使后人误解孔孟,并误解儒学之基本立场”(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8页)。遗憾的是,劳先生未能充分深思自己是否也受到了上述宇宙论—形上学传统的“误导”,例如,劳先生认为宋明儒学“内在化过程”的第一步是走向“形上学与宇宙论之混合阶段”(这是一种可喜的复返,但远未臻儒学基本立场之境),“此阶段之理论,即与《易传》及《中庸》接近”(同上,第88页),这个看法与本篇对《中庸》的定位(“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的典型文本)大相径庭,似对本篇构成挑战。但细审之下,劳先生对《中庸》的理解深受朱熹与宋儒乃至汉唐旧注影响,例如其从“心性”“体用”角度理解《中庸》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段(同上,第49页),可谓并无新意。对此一段的非体用论解读,可参考拙作:《〈中庸〉首章:本体论误区与生存论新解》,《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 。上引《礼记正义》之郑注,即是在以“木金火水土”五行配“仁义礼信智”五常,孔疏则试图补充“刚柔”或“好恶”以配“阴阳”(刚、好配阳,柔、恶配阴)。解释者进而推论:天在以阴阳五行命生人的同时,必然赋予人“刚柔(或好恶)五常之性”。其中,“好恶”可以理解为“喜好和厌恶”,这样,郑注便可最大限度地与性善论兼容。而如果再同时悬搁或剔除孔疏中“贤愚吉凶”之“愚”“凶”因素,则《礼记正义》至此所给出的尚算是一种性善论。这种性善论对于人性中善的因素的阐释,构成了更宏大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阴阳五行”以及由之而有的“刚柔或好恶五常”即人的善性本体(暂不考虑贺玚的“情”“性”之辨)。相应地,“性善论”的基础,就由《孟子》的“四端之心”主观体验,转移到了更具旁观色彩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上,善性本体由此似乎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客观界定。
5.1.3 Sustainable mixed agriculture production system in Peacock River valley.
但是,只解释“性善”现象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是不完整的,人身上那些“不善”的现象(如荀子以“性恶”或“情性”名义指出的“欲—求—争—乱—穷”)也需要在“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框架下得到解释,而一旦将这些“不善”的因素纳入“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系统之中,《中庸》《孟子》所揭橥的“性善论”立场就会受到污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孔颖达所援引的贺玚的论述中,圣人之性纯善、愚人之性纯恶、中人七等之性可逐物而移——贺玚特别强调,《论语》中的“性相近”之性,即“中人七等”之性。换言之,不可移易的上智(善)、下愚(恶)之性,与绝大多数人没有直接关系,而绝大多数人所属的“中人七等”之性实即“善恶混”之性。走到了这一步,《礼记正义》的“性善论”立场几乎已经全盘沦陷;尽管这些说法是借贺玚之口说出来的,但从思想发展角度看,却是“性善论”被纳入“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框架之后的自然结果。实际上,除了总体上肯定“唯人独禀秀气”之外,上述“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只能从运气好坏的角度主张“所禀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为九等”(禀上智清气的圣人运气最好),而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进一步推论人性中善的因素要比恶的因素更原始或更实在,因为一旦强调不善的因素缺乏原始性或实在性,就等于放弃了对这些因素进行“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解释的努力。如此,则“性善论”演变为“性善恶混论”,在“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框架下就成为势不可挡之事了。
更重要的是,一旦将“性善论”置于“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框架下,以特定的宇宙生成论机制解释善性本体的生成与内涵,则原本作为“真知起点”的善性,就会立马降格为“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的研判对象① 王阳明曾提出“说性”与“见性”的区分,郭美华教授在此基础上指出:“所‘说’之性,作为概念之所指,往往因为理智抽象而悬设为脱离切实践行的先天之物,所以在大程看来,它就不是真的人之性了”;“从‘说性’角度对于性的理解,往往有颠倒:现实本来是理解人性(甚至生成人性)的基础,但理智往往扭曲地从自身抽象出一个先天本性或实体,作为理解现实的基础”。参见郭美华:《致良知与性善——阳明〈传习录〉对孟子道德哲学的深化》,《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在这种谈论方式中,既定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才是实际上的“知识起点”。这种试图从既定的知识系统出发的思路,本质上正是荀学的“性恶—外铄”思路。唐宋之际,性善论开始在儒学中复兴,到二程时代,性善论已经在儒学中确立起正统地位,讲性恶的荀子遭到贬斥,如《二程集》云:“荀、杨性已不识,更说甚道?”[5](P255)又云:“荀子极偏駮,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5](P262)这样一来,朱熹的《学庸章句》明面上必然要拒斥《礼记正义》孔疏所征引的贺玚式“性善恶混”立场,但仍把性善论镶嵌在“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系统中的朱熹,要摆脱“性善恶混”乃至实质上的“性恶—外铄”思路却并不容易。
我们知道,《大学》通篇只有一处“性”字,且完全处于“陪衬”地位,其与朱子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不可同日而语。朱熹则创造性地将《大学》开篇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明德”,等同于《中庸》意义上的“天命之性”。例如,在《大学章句序》第二句话中,朱熹即胸有成竹地宣称:“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3](P1)“仁义礼智之性”实际上是将《孟子》的“四端之心”现象进一步本体化的结果,即以“仁义礼智之性”作为“恻隐”、“羞恶”、“辞让”(或“恭敬”)、“是非”这“四端之心”的本根,是为《礼记正义》注疏的基本思路。《中庸章句》在解释“天命之谓性”句时,尤为明显地继承了《礼记正义》注疏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思路: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礼记正义》以“阴阳五行(木金火水土)”配“刚柔(或好恶)五常(仁义礼信智)”的做法,在《中庸章句》中被稍稍改造为以“阴阳五行”配“健顺五常”。与《礼记正义》孔疏中偶尔出现的“贤愚吉凶”之“愚”“凶”字眼(贬义词)相比,出自《易传》的“健”“顺”则是基本德目,较之“好”“恶”甚至“刚”“柔”更具褒义色彩。显然,《中庸章句》尽量避免使用贬义或褒义色彩不足的词语形容性本体,就此而言,它的性善论立场要比《礼记正义》(尤其是孔疏或孔疏所引之贺玚)更自觉。
但尽管如此,一旦上了“在‘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框架下界定性本体”这条船,朱熹亦不得不在此框架下进一步解析人性或生存中的不善因素。人性或生存中存在着不善的因素,这正是修身的必要性所在,而朱子用力最深的《大学》则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章句》在解释开篇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时,遂安排善性和不善的因素同时共居于人之中: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有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3](P3)
作为“天命之性”的“明德”,在此被具体解释为“所得乎天”“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的“不昧”之“虚灵”。若仅依据这些字眼,则可说朱熹对“天命之性—明德”的理解,非常接近于《孟子·尽心上》所谓“良能”“良知”。但与《孟子》满足于指点切实可行的“率性”途径,而无意构建完备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系统不同,朱子正是站在建构这样一个理论架构的全局性高度,对人性或生存中善与不善的因素之共存进行说明。故此,在高调提出《大学》“明德”相当于《孟子》“良能”“良知”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之性”(联系《大学章句序》)之后,朱子旋即提出了“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有时而昏”的构想。也就是说,人性或生存中的不善因素(有其“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根源),对于善性的功能发挥形成了干扰。尽管在强烈的性善论立场驱动下,朱子进而强调“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有息者”,但从性本体的功能发挥(或当事人是否能体验到性之发见或指引)的角度看,它毕竟是“有时而昏”了。因此,这可以说是一种打了折扣的性善论① 向世陵教授曾指出,在朱熹那里“‘性之本体’与‘性’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与气相隔离的”,后者则是“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的人性”。见氏著:《“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当然,“复其初”之后,“气质”将不再对“性本体”的功能构成拘蔽,但在“复其初”之前,考虑到“气质”对“性本体”功能的拘蔽,在“能发见—被感知”的意义上,“性善”显然是打了折扣的。向教授所揭示出来的朱熹“二性”“二善”说,实际上正是朱子“性善论”思维不够彻底的表现。 。
鉴于这种现实功能发挥上的“有时而昏”,修身者在成功“复其初”之前,每时每刻都“率性”而行是不可能的(尚未“复其初”的修身者,时常感受不到“性”之发见或指引)。若从时间维度分析朱子在此提倡的“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条功夫,基本情况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当事人在某些时刻有幸感受或体察到了“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也即“性之发见”);其次,因为本体在现实功能发挥上“有时而昏”,当事人对“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性之发见)”的感受或体察因而是不连续的,也即为若干昏暗的时段所隔断。“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主要就是在昏暗时段用功,此时,当事人必须动用自己身上的“率性(体察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之外的其他能力,借以推演(“因”)自己对于过往“体察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率性)”的记忆,以此扫除“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所导致的性本体在现实功能发挥上的“有时而昏”。当这种“拘—蔽—昏”被完全扫除净尽之后,当事人便进入了“复其初”的成功境界。
现在的问题是:在“本体之明/性之发见”不提供即时指引的情况下,当事人究竟凭什么、又如何正确地去“因(推演)”那业已沦为记忆(而与当下处境脱节)的“其所发”呢?必须强调,朱子所谓人为努力的“因(推演)”,并不需要以“本体之明(性本体)在修身者生存意识中的即时发见”作为实时指引。无论如何,在昏暗时段,过往的“对于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性之发见)的体察”只是记忆中的推演(“因”)对象,对于“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性之发见)”的新的体察(足以指导包括“因”在内的当下生存活动)尚未出现。而按照“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这一愿景,“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性之发见)”的新的体察是否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取决于“因(推演)”的功夫做得怎么样。这样,“本体之明的具体发见(性之发见)”便从总体上丧失了指引“因其所发而遂明之”的作用,而反过来沦为“因其所发而遂明之”功夫所帮助的对象。换言之,只有充分借助“因”的功夫,“本体之明(善性本体)”才能在修身者的生存意识中更好地发见。
站在“知识—理解”角度看,上述“因”的功夫,在《大学章句》中又被进一步落实为“格物致知(即物而穷其理)”,“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亦被相应地改写为“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3](P7)。王阳明后来特别批评说,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物”为“外物”,“格物致知”因而带有突出的求知于“性”外的取向(实质上就是不相信“性善”)。对此,朱学服膺者们的辩护空间是极小的,他们固然可以说“已知之理”是来自“善性本体的具体发见”,但朱学功夫的重头不在于体察这种“发见”(“率性”),而是主要在于“率性”之外的“因……而益穷之”。特别地,从“已知之理(既往的‘率性’记忆)”通往“豁然贯通”的“至极”之“理”的路径,并非是由作为内在向导的“性”即时指引的,而是需要当事人凭借来路不明的“因”的能力自行开拓。既往的“率性”记忆,即便在这种“因”的功夫中派上了用场,它也不是作为“即时的指引”出场,而是不折不扣地沦为了“因”的客体(对象)。我们知道,《荀子》所谓的“善假于物也”主要是指“学习礼义”,传统“礼义”是“学习”所指向的外在对象——朱子所谓的“已知之理”尽管当初是来自“对善性本体具体发见的体察”,然而一旦时过境迁成为“因”的对象,在本质上便与外在的“传统礼义”没有二致了。这样,在功夫论层面,“界定本体的性善论”最终可谓彻底倒向了“性恶论”① 李泽厚先生及其所引用的蔡元培的观察值得注意,其说曰:“朱熹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进行‘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格物致知’,以外在的、先验的天理(实际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礼’,即外在社会规范)来主宰、控管、约束、规范人的一切自然情欲,以此日积月累地不断磨打、锻炼从而培育人的意志以及观念和情感,有如蔡元培所简明指出‘其为说也,矫恶过于乐善,方外过于直内’(《中国伦理学史》),由外而内,由伦理规范而道德行为,而这,不正是荀学么?”又曰:“与此相关,韩国数百年前关于‘四端’‘七情’的各派激烈争辩,细致深入,已超中国。其中一说认为‘四端’(仁义礼智)乃理性抽象,‘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自然情欲,主张以‘四端’控‘七情’来解孟子。其实这正是朱学。程朱将‘四端’说成有关形上、太极的天理,把‘孝为仁之本’(《论语》)变作‘仁为孝之本’,从而尽管高谈‘性善’‘四端’,实际有如上说,已转入荀学。”(李泽厚:《举孟旗行荀学——为〈伦理学纲要〉一辩》,《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
从《孟子》的“四端之心”现象指点,到“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框架下的“健顺五常之性”、“仁义礼智之性”等性本体界定,本节考察的这段漫长的性善论演变史,最终(在实践,也即功夫论层面,落实为生存意识)完全背叛了性善论立场,而近乎自相矛盾。以上,我们反复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思维;但严格来讲,仅仅“界定本体”这一条就足以导致上述逆转了。本篇下一节将借助于王阳明当年的挣扎与转变,进一步暴露“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的逻辑误区,并重点展示一种“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及其优势。
四、“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意识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
本文第二节通过追溯儒家性善论的起源指出,“知识—理解”或“真知”问题是促使《中庸》高举“天命之性”概念的根本动因。我们分析指出,“知识—理解”归根结底是当事人自己的知识—理解,书本(教材)与教师即便水平再高,也无法向学生直接灌输知识—理解,更无法代替当事人亲自理解。“天命之性”因而受到极大地重视,被视为当事人读懂书本(教材)或理解教师传授,乃至主动探索适切具体处境之真知的生而固有的内在向导。除了通过“天命之谓性”诉诸时人的“敬天”情感,并在这种积极的宗教情感中认定“天命之性”绝对可靠(纯善)之外,《中庸》并未对此善性本体做内涵上的具体界定。经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就可大致理解其中的原委了。显然,关于性本体内涵的具体界定,本身是一种“知识—理解”,而且必须是“真知”。就算《中庸》作者拥有这些真知,并通过写作表述这些真知,但只要读者的“真知起点”尚未确立,读者也还是无法正确理解《中庸》作者欲借《中庸》文本传达的关于善性本体具体内涵的真知。可见,“真知起点”或“知识—理解的恰当途径”,在“真知”问题语境下,要比本体论界定更具优先性。“真知起点”或“知识—理解的恰当途径”问题一旦解决,则具体的“真知”或“正确的知识—理解”完全可以在当事人需要之际即时获取。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6](卷26,P1067-1068)
而若站在《中庸》“性善论”角度看,在“率性”之外“读书讲明道义”根本是不可能之事。本文第一节已经指出,正因为意识到了外在书本和教师无法代替学生亲自理解,《中庸》才不得不设定并高举生而固有且绝对可靠的真知向导——“天命之性”,并鼓励读者切实利用这种人人固有的内在向导。但到了朱熹这里,这个次序却被颠倒过来:须先获取真知,并利用真知界定善性本体,然后再按照具体的内涵界定推论何为率性,最后才将作为推论结果的“率性”付诸实施。上述“颠倒”的关键在于:其一,对于“性(真知向导)”的直接可利用性缺乏信心,不相信“率性”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上手的;其二,想当然地相信“读书—教学”活动足以促成真知,对学生本人的“认知—理解”能力在“读书—教学”中的关键作用估计不足。早年王阳明在服膺朱派“格物致知”与读书方法时,便因上述“对于‘性(真知向导)’的直接可利用性缺乏信心”,而始终觉得读书所得与真切的体知隔着一层。特别地,他曾一度格竹无功反而致疾,后再度耐住性子勉强遵循朱熹的读书法而“思得渐渍渐浃”,然深彻的自我怀疑(不相信“率性”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上手的)终使他觉得“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②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6、1348-1350页。 。王阳明的上述亲身经历表明,放弃了直接从“天命之性”出发的“率性”意识,就等于放弃了择取真知的判断力,而只能枉然地看着自己心中念出念没,渴望真知却又无力把捉。
据《年谱一》记载,王阳明32岁时开始对“爱亲本性”这种提法流露出真情实感,此颇类似于《孟子》即“四端之心”言“性善”。这种趋向进一步发展,到37岁时,王阳明于龙场夜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5](卷33,P1351-1355)。“求理于事物”正是王阳明对自己早年所力求服膺的朱学路线的本质概括。在龙场悟道之际,王阳明明确将其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性善论路线对立起来,并把这种“求理于事物”的认知路线判定为“误也”。从这时起,王阳明开始正式面临一项沉甸甸的解经任务:将如日中天的《大学》文本,从朱派解读中“抢救”出来,也即,本着单纯的生存论(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性善论思路重新解释《大学》。为此,王阳明彻底撇弃了《大学》中外向的“教—学”因素,并照单全收了朱熹引《中庸》《孟子》入《大学》、以“天命之性”“四端之性”释《大学》“明德”、以“《大学》孔子传经曾子作传,《中庸》作者子思则为曾子之徒”暗示“学庸一体”的学术遗产,甚至有板有眼儿地补充说“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但在进一步的具体解释上,王阳明的《大学问》则明显放弃了“本体论”之“界定本体”的“旁观者”视角,而代之以类似《孟子》的体验式指点(我们因而称之为“生存论”视角)。其曰: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6](卷26,P1066)
那么,究竟如何避免既有之“知识—理解”成为即时体察“性之发见”的障碍呢?当《孟子》即“四端之心”以言“性善”时,尽管同时保持着我们所谓的“善性本体不可界定”的意识,但总地来说不还是导致了以“仁义礼智”等德目规定“善性本体”的思潮吗?龙场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又有什么招数来切实避免这一后果呢?招数应该是王阳明对“知”进行二分:一种是即时“发见/感应”之知,又称为“良知”;另一种是时过境迁之后“发见/感应”在记忆中的留影。在“发见/感应”之际,“良知”之“知”是不容拟议、绝对可靠的“真知”,而在变化了的处境中,记忆中的“良知发见/感应”留影,作为一种现成的“知”则不宜继续充当生存指南。但记忆中既然存在着此等“知识—理解”,则它们当然可以成为拟议、揣摩的对象。王阳明所批评的“私意小智”,无非就是依据不合时宜的旧知留影,推论测度已然变化了的事态与处境。正确的做法是:面对变化了的事态与处境,当事人宜将“旧知留影(也即自己既有的知识—理解)”视为新处境的一部分(如作为知识背景),并在此新处境下重新体察“即时的性(至善)之发见/感应”。这样,当事人的“知识—理解”就会与时俱进,而非顽固地执着于既定的旧知留影。“即时的性(至善)之发见/感应”除了是一种“知识—理解”外,同时还附带着一种“新鲜感”,即“这是刚刚生成的”。而这种“新鲜感”,似乎正是王阳明用来辨别“即时发见/感应”与“旧知留影”的唯一标志。深入分析“王门四句教”① 王门四句教存在不同版本,根据学界通例,尤其是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24页)、杨海文(《阳明“四句教”出处辑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的考证,本文所论将以《传习录下》、《年谱三》所记王阳明自己的表述为准。 ,可进一步印证这一点。
这里,王阳明表面上借用了朱熹的“虚灵不昧(本体之明)—有时而昏(气质所拘,人欲所蔽蔽)”的双重架构,但更重要的是,王阳明以一种体验式指引代替了朱熹的旁观式描画界定。历史地看,这是由汉唐式“本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向《孟子》式“体验—指引”言说模式的回转。例如,上述引文以体验式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代替了“虚灵不昧”、“其本体之明未尝有息者”等的旁观式界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中的“以……为……”二字,要求读者必须亲自尝试相应的体验,才算切身理解了该提法的意涵。相形之下,朱熹使用的“人欲所蔽”提法则是一旁观式刻画,给人的印象是“性本体上静态地覆盖了一层人欲”。王阳明则将其改写为“动于欲,蔽于私”、“分隔隘陋矣”,也即对“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思想境界的打破。这样,“善性”(内在资源)与生存中的“不善”(问题所在)因素,便双双获得了亲切有味的体验式赋义。
《大学问》的“至善”论继续贯彻了这种将问题与出路落实到生存体验上去的原则:
冰烟囱是南极另一个有趣的火星类比奇观。在南极罗斯岛的埃里伯斯峰,许多的冰烟囱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吐着热气。冰烟囱是由活火山散发的热气在冰雪覆盖的地表上作用形成的。冰烟囱的外层是寒冷干燥的空气,而内部却是温暖湿润的环境;冰层还有效阻挡了紫外线,使烟囱内的环境更温和更宜居。虽然目前在火星表面还没有直接观察到冰烟囱,但类似这样温暖湿润的被埋藏的通道,却被认为是可能存在的。
反过来看,先以宏大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框架或简单地以“刚柔五常”、“健顺五常”“仁义礼智”等概念界定“善性本体”,再从被界定过的“善性本体”之内涵推论应然之道(“率性之谓道”),这种先后次序本身就意味着:在“率性”之外还有其他有效的“真知(正确的知识—理解)”获取渠道。换言之,上述理论构建者(及其心目中的读者)如果不是在学会“率性”之前已然有能力获取“真知(正确的知识—理解)”,他(他们)又怎么可能正确地界定或理解“善性本体”?在朱熹那里,这种“率性”之外的其他“真知获取渠道”,说穿了,最主要的就是“读书讲明道义”① 可参考陈荣捷:《朱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3、77页。 。也就是说,“读书”+“教—学”在朱熹这里反而是“认识性本体”进而学会“率性”的前提。就此而言,除了“性善”这块招牌,朱学几乎与推崇“传统礼义”加“君师治教”的荀学外铄思维没有任何区别。而“性善”这块招牌,严格来讲根本也是不必要的:界定者用来界定性本体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或“刚柔五常/健顺五常/仁义礼智”等基要概念,已然是近乎全备的真知(不全备便不足以界定性本体)——如此这般的“真知”已然在手,“性善”还是“性不善”还有什么重要的呢?在此“真知”在手的基础上,当事人只需集中精力在行动上贯彻这些现成的“真知”就可以了!
在谈及“明德(天命之性)”的功能时,朱熹用“虚灵不昧”之“虚”指称“尚未知但能知”的态势。这种“虚”,与《荀子·解蔽》的“虚一而静”有相通之处:“以具众理”仅止于潜在地保障“虚一而静”之心“能知”,但所具的“众理”并不跑到前台直接指示“真知”。经此朱熹式旁观界定之后,生存者具体该凭借怎样的主观心态,如何利用所“具”的“众理”,则依然停留在晦暗之中。对荀子和朱熹来说,认知的关键在于进入“虚”的姿态。但“虚”,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怀疑或否定,而在深彻的自我怀疑或否定中,生存者根本无法择取“知识—理解”。在上述引文中,王阳明的“至善”论则从“发见”的角度谈论“灵昭不昧”。作为本体的“明德(天命之性)”,不再满足于消极地或潜在地为“能知”背书,而是随时随地冲在前台,不断发布处境化的“是非”“轻重”“厚薄”指示。王阳明又将这种“发见”称为“感应”。
为了能够心无旁骛地体认这种“发见”或“感应”,王阳明特别强调:除了体认直接的“发见/感应”外,任何多余的“拟议增损”“揣摸测度”即便初衷再好,也无非都是在以“私欲”遮蔽那正在“发见/感应”的“明德(天命之性)”。这些“拟议增损”、“揣摸测度”归根结底只能算“私意小智”。联系王阳明早年的为学经历,朱熹所谓的“因其所发而遂明之/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功夫,正可谓是这种“私意小智”的典型。按照朱熹上述功夫论的基本精神,只要当事人尚未“豁然贯通”而彻底明了“众物之表里精粗”,则“(善性本体)所发”便只有充当作为被探究(“因”)对象的“已知之理”的份儿(参考本文第三节),“率性”在性善论中所应具有的“真知起点”地位,就此被一种研究“率性”记忆的“因”的功夫所取代。换言之,当事人因为忙于这种“因”的功夫,遂不再关注作为“真知起点”的“至善(性)之发见”。正因为如此,王阳明将诸如朱子“因其所发而遂明之/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之类的功夫贬称为“私意小智”。
4.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危房是指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鉴定属于整栋危房(D级)或局部危险(C级)的房屋。属整栋危房(D级)的应拆除重建,属局部危险(C级)的应修缮加固。危房改造应执行“三最两就”原则,即“三最”,优先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的住房安全问题;“两就”,采取就地、就近重建翻建的改造方式。
王门四句教第一句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命题是王阳明吸纳释老“空”“无”思想的结② 可参考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247-252页;杨海文:《阳明“四句教”出处辑考》。杨文最后一节指出,站在“尊孔孟、辟佛老”的立场上,既可以指责阳明四句教为异端,也可以对其正统地位进行辩护。就此而言,正统或异端的标签对于理解阳明四句教意义不大,因此相关研究宜超越正统、异端之争,转而挖掘四句教“抽象作者”的精神旨趣。本节后面的论述,可看作是朝此方向的努力。 。但无论如何,这种吸纳并未取消四句教的性善论底色,毋宁说,在“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将性善论者的生存意识引向“权威的教义名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堕入“性恶论”藩篱之后,大张旗鼓地强调“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实乃“性善—率性”意识重新自觉并自我纯化的内在要求。释老“空”“无”风气的激荡,可谓只是一种外在契机。
王门四句教第二句是“有善有恶是意之动”。如果认为“善意”“恶意”同时起源于“心之体”,那么,“无善无恶”的“心之体”实际上就是“善恶混”的了。我们需要暂时悬搁对第二句的解释,先展示一下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的“性善论(良知论)”底色。真正的“知善知恶”之“知”当然必须是“真知”,这种真知是心灵中《孟子》式的“良知良能”功能的展现,而心灵中之所以存在这种良善功能乃是因为“性善”。就此而言,必须承认“心之体”是“纯善”的。由此,再回到第二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从“纯善的心之体”发见出“善意”以及“知善知恶(真知)”的“良知”,这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心之体”既然“纯善”,人的心灵中又怎么会出现“恶意”?
我们需要郑重地引入“时间”这个维度,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个问题。作为一种主观体验,“无善无恶”即“无感无知”。相应地,“知善知恶”之“真知”,从现象上看,就是从“无(无感无知)”中冒出来的。这样,“良知”的每一次发动,或者“知善知恶”之“真知”的每一次出现,便会同时附带着“从无到有”的“新鲜感”。至于“意之动”中的“恶意”,由于不能将其视为“心之体”的直接发见(有悖于“性善”路线),故而只能将其存在视为“记忆中的旧知留影”。要之,这些“旧知”当初也是作为“新鲜的良知”或“新鲜的善意”而出现的,但在时过境迁之后,它们不再是“适切当下处境的真知”,试图继续以它们指导当下生存的“意”因而就成为“恶意”① 《大学问》谓“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据此“意之所发”字样,似可认为“恶意”、“善意”皆以类似的机制直接出于“意之本体”。然而,对于将“心”“知”“意”“物”概念相互打通的王阳明来说,“意之本体”也即“心之本体”,反之亦然。认为“善意”“恶意”以类似的机制直接出于“意之本体/心之本体”,即等于认为“意之本体/心之本体”乃善恶混或无道德属性。如此一来,知善知恶的“良知”将成为无本之木,王阳明肯定不会接受这种结论。《大学问》中明确说,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鉴于此,似宜强调:“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之“发”字,并无交代“善意”“恶意”具体来源之意,而只是在陈述“有善有恶意之动”即“有善意也有恶意”这一现象。关于“恶意”“善意”各自不同的发生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在正文中以善意来自良知或善意即良知,而恶意则是时过境迁的善意留影,来解释“恶意”之“发”或“动”,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王阳明著述的限度,但作为对王阳明核心思路的一种推演当有其价值。 。
王门四句教第四句是“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并非是说经过相应的功夫修炼之后,“意”的“记忆”或“旧知留影”部分可以被彻底清除。毋宁说,“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从一开始就承认“善意(即时新知)”与“恶意(旧知记忆)”在“意”中始终并存。“恶”无非就是执着于“旧知”,试图继续以其指导生存。但当事人只要能够不断体认“鲜活的新知”,则“旧知留影”就会被不断被“即时新知”的涌入所刷新。这样,“为善去恶”既是不断以“即时新知”取代“旧知记忆”作为行动准则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知体认”不断刷新“旧知记忆”的过程② 学界一般认为,王阳明及其后学以“无善无恶”界定至善之“心体”,即“心体”或“善性本体”是超越有对待之善恶者。将“无善无恶”说成是一种“超善恶”的概念界定,势必将读者引向以“空寂”为最高境界的佛老思路上去。这显然不是龙场悟道之后作为儒者的王阳明的取向。陈来先生慧眼独具地认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主旨在于“无滞(纯粹的无执着性)”(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230—240页),而“‘四句教’之精义,唯阳明弟子何庭仁揭之甚明:‘师称无善无恶者,指心之应感无迹,过而不留,天然至善之体也。心之应感谓之意,有善有恶,物而不化,着于有矣,故曰意之动。’(《明儒学案》卷十九)”何庭仁以“应感无迹,过而不留”解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此与我们从“即时发见/即时感应”与“即时性/新鲜感”的角度解释“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在思路上完全相通。至于其将“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之“善意”“恶意”均理解为“物而不化,着于有矣”,则恐怕不妥:一方面,这意味着“心之感应(意)”必然固着,而固着之“意”有善有恶——如此一来,“无善无恶”的“心之体”实质上就是“兼善兼恶”,此与王阳明的性善论立场(“一体之仁”、“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相违;另一方面,在“知善知恶是良知”之外另立“兼善兼恶”之“意”,进而以“良知”作为“善意—恶意”的分辨者,恰恰是将“意”与“知”析为两节(而王阳明曾反复强调“身、心、意、知、物是一件”,可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03页),不免重蹈王阳明早年所经历的“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困境。实际上,“善意”正是“即时发见/即时感应”意义上的“知善知恶是良知”,而“恶意”则是时过境迁之后的“旧知留影”。“恶意”在其“发见/感应”之初本是“善意”,只是因为时过境迁不再适切变化了的处境而沦为“恶”。总之,“记忆(留影)”与“时变”才是“恶意”的根源,“无善无恶”或“至善”的“心之体”中不存在生发“恶意”的基因。陈来先生的结论值得重视:“它所讨论的是一个与社会道德伦理不同面向(di mention)的问题,指心本来具有纯粹的无执着性,指心的这种对任何东西都不执着的本然状态是人实现理想的自在境界的内在根据。”(第240页) 。
从试图服膺朱学到与朱学彻底决裂,在此转向过程中,王阳明的“性善论”思维先后经历了“爱亲本性”“良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几个阶段。王阳明的上述转变始终深受“真知”问题意识驱动。作为后来转向的预示,王阳明在32岁时感兴趣的“爱亲本性”,非常类似于《孟子》的“四端之心”,重在即生存意识中的“善端”提示“善性”的实在性。龙场悟道之后的“良知”说,则重在强调善性本体在现实处境下“知善知恶”的功能,而非以“仁义礼智”或“孝(爱亲)慈”等德目界定“良知”本体。晚年的王门四句教进一步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冠于“知善知恶是良知”之前,此可视为其“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的最终完成。而这,在笔者看来,也正是《中庸》性善论思维的精髓所在。
五、“率性的处境”与“真知”问题的政治哲学出路
以上,我们完成了从“天命之性”到“四端之心”再到诸如“仁义礼智之性”再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一儒家性善论的哲学史梳理。总地来说,“四端之心”的提出是儒家性善论的一个转折点,启发并开启了界定本体的性善论范式。“天命之性(善性)”一旦沦为被研判、被界定的对象,则用来研判、界定善性本体的知识系统(如“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系统)便会架空“率性”意识,而成为实际上的“知识—理解”来源。由于既定之知识系统取得了善性本体的界定者地位,这种名义上的“性善论(界定本体的性善论)”所引导的生存意识实际上更接近荀学的“外铄”思路。性善论因而名存实亡。就此而言,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实乃自相矛盾。
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命题,并非是要制造一种类似《老子》“混沌之‘无’”的“心体”或“本体”概念,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断绝人们“界定性本体”的企图。只有放弃凭借既有“知识—理解”界定各种本体的冲动,当事人才能悬搁自己既有的“知识—理解”,专心聆听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天命之性”的实时指引。这种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因能始终高举“率性”意识,故而是融贯一致彻头彻尾的性善论。
4.在多元理解有误时诱导。《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这种“多元”的理解,有时就出现对文本价值取向的曲解或误解。这时候,教师要进行诱导。
由此反观,《中庸》首章满足于在敬天情感中认定“天命之性”绝对可靠(纯善),然后在未界定“性体”的情况下,即将注意力转向“率性”——这种原始的理论形态反而是性善论之正途。经过了整整一圈的思想史运动之后,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为代表的王阳明学说,则可视为对性善论原始形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的强势回归。
不过,逻辑上融贯一致是一回事,是否有效解决了性善论由以被推向儒学前台的“真知”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者坚信——而非界定——每个人都天生固有绝对可靠的内在真知向导(“天命之性”),倡导直接通过体察此内在向导的指引(“率性”)获取适切处境的真知并落实为行动(“修道”)。但是,《中庸》作者自己在后半篇中亦隐约触及到:“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本身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的“真知”问题。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在实践中同样也会遭遇此类问题。在“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中,“真知”就是当事人真切体会到的“应然感”。但面对一桩公共事务,作为“率性者”(“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意义上的“率性者”),涉事诸方心中往往会涌现出不尽相同乃至相互冲突的“应然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当事人真切的‘应然感’就是‘真知’”吗?在“性善—率性”之名义下,涉事诸方若因为见解不同而打得不可开交,那么,“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又将从何立威?
别的不说,仅就解读“格物致知”这桩学术公案(是学术界的一桩公共事务)而言,清初刘宗周指出“格物之说,古今聚讼者有七十二家”[7](P71)。除朱熹的补传和王阳明的新解之外,这“七十二家格物之说”中也不乏王门后学的争鸣之论。对此,可以简单归咎为这些王门后学“不知道到什么是真正的率性,不知道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以及在面对“格物致知”的解释问题时,不自觉地运用“私意小智”“拟议增损”而未能体察到“真正的性之发见”的指引吗?换言之,如果王门后学们“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率性,真能够做到真正的率性”,他们关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就必定不会出现分歧吗?如果回答是,那么这意味着,“率性”并非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上手的“真知起点”,要想“率性”,就必须先在“知识—理解”上解决“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此即将“真知”问题反加诸“率性”。而由此观之,在《中庸》率先提出了“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之后,《孟子》的“性善—四端之心”说、《礼记正义》与朱熹的“刚柔(健顺)五常之性”“仁义礼智之性”等善性本体界定纷纷登上性善论舞台,其根本动因实际上就是旨在回答“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但结局并不美好,以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回答“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结果只能在自相矛盾地在功夫论(或生存意识)层面堕入“性恶—外铄”的路子上。
按照上述分析,如果学生本人无力负起解决“真知”问题的责任,则“真知”问题就会是不可解决的,严肃的生活因而就成为既不可望也不可求的。这不是《中庸》作者的选项。相反,《中庸》作者从孔子“道不远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反求诸已”等教诲中,获得了另一种鼓舞:“自”或“己”里面有着充足可用的“真知”资源。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庸》开篇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将《论语》中偶尔且分散出现的“天”“天命”“命”“性”“天道”,整合为“天命之谓性”命题,并将其推崇为孔门或儒学的第一原理了。简言之,“天命之性”即“自”或“己”中绝对可靠的“真知”源泉。这种“绝对可靠的‘真知’源泉(性)”不是概念界定的对象① 牟宗三先生一方面指出,单就“天命之谓性”一语本身,“尚看不出此天所命而定然如此之‘性’究竟是何层面之性”,另一方面则根据“率性之谓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等语,断定《中庸》之性“可能是根据孟子言性善而来”,认为《中庸》以“性体与道体通而为一”与《易传》以“元亨利贞”言“乾道实体”为“同一思理模式”,是“道德意识之充其极”的“圆满之发展”。由前一方面可见牟先生已注意到了《中庸》之“性”不是概念界定的对象,不过,牟先生真正措意而长篇大论的却是后一个方面,即《中庸》《易传》将“道体(天道)”与“性体”打通为一,赋予“性体-道体”以“元亨利贞四德”“仁体”等内涵。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是在“道德本心”及其“能起道德创造”之意义上援引“元亨利贞”“仁”等提法的,如此,作为“道德本心”的“心体-性体”就成为一“即活动即存有”的主体,其具体内涵则只能通过其在具体处境中的“发见(活动)”自行彰显(不断彰显)。就此而言,牟先生是将《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一体归入了本篇所谓的“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之列。尤值得指出的是,牟先生所着力表彰的胡五峰、刘蕺山基于“於穆不已”体验而谈论的“性体”,虽曰“客观”,但完全不同于伊川、朱子在“仁义礼智”之“理”意义上所界定的“性”。参考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28-38、39-44页。尽管牟宗三先生的洞见与本篇有相合之处,但牟先生以宋明心学为本“一以贯之”的《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叙事,未免太过理想化,遮蔽了历史地形成的文本之间(乃至同一文本内部)的思想分歧及与此相伴的思想史(哲学史)逻辑。站在方法论角度,可对上述叙事提出如下两点批评:其一,追随宋明道统论余绪,先入为主地认定儒学正典(《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一以贯之,极力淡化这些文本之间的思想分歧;其二,《心体与性体》作为一部评述宋明儒学的厚重作品,其对《论语》《孟子》《中庸》《易传》的文本解读直接脱胎于宋明儒学思路(当然是经过了牟先生取舍提炼)。相关批评可参考拙作:《〈大学〉、〈中庸〉研究: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该文修订版见拙著:《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上述两点决定了牟先生关于《中庸》的相关论述实为其宋明儒学相关评述之附庸,缺乏相对独立的学术史研究品格。此外,牟先生所谓“客观地讲性体”的提法亦值得商榷,无论如何,五峰、蕺山的“於穆不已”体验,是他们谈论“性体”的意识基础。 ,而是通过“天命”术语所承载的正面宗教情感,自我鼓舞并感染读者去义无反顾地先行认定的(因而必须作为《中庸》开篇首句)。
与大肠埃希菌相比,肺炎克雷伯菌产ESBLs的比例要低的多,但ICU菌株对3种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率均大于10%,远远高于张秀芳等[14]的研究(亚胺培南耐药率为0.5%)。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随着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病原菌对其耐药率呈逐年上升趋势;②国内各个省份的流行病学情况有着较大区别;③医院感控部门对多重耐药菌的防治意识和防治工作有差别[14-15]。CRE机制复杂,如何治疗CRE菌株导致的感染也是当下研究的热点之一[16-17]。
《中庸》首章稍后以“慎其独”来解释“率性”,但反过来看,这何尝又不是在本着“率性”意识重新定义“慎其独”?顺着《论语》强调后天之“习—恒—品格”的思路,也有一种“慎其独”,即“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或“在独处中谨慎不苟”。这也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慎独”概念,包括《辞海》、《辞源》、《现代汉语大词典》、《古代汉语词典》在内的大小辞书往往无不采取上述解释③ 例如,《现代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编纂:《现代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三卷,第1645页。又如,《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91页。 。这种意义上的“慎独”,其核心旨趣在于:在独处时尚能谨慎不苟,在有人关注(监督)的场合下自然更是端庄。这种“慎独”旨在堵住“意志薄弱—无恒”者的最后借口,以成就最持之以恒的践行既定德目的“习—品格”。《大学》“所谓诚其意者”章正是在这个思路上谈论“慎独”的。但站在“知识—理解”问题角度看,这种被当事人坚定不移地设定为自己的行事为人原则的既定德目,是否果真为适切处境的“真知”呢?无论如何,当事人只能在特定的“知识—理解”中设定并坚持相关德目,而如果这些“德目—知识—理解”存在这样那样的偏差,那么,决绝的“谨慎不苟”必然也会将其中的错误因素坚持到底。显然,在这种以“意志”持守而非以“智力”问题为本的“慎独”论中,存在着严重的知识论盲点。《中庸》本着“真知”问题语境下的“率性”意识重新定义“慎独”,恰恰是要对治《论语》以及《大学》的上述盲点或软肋。
首先,我们可以追问:在“敬天”情感中所认定的“性善”或“善性”,是否可以直接转化为“直面”并“体察”的对象?如果可以,则“敬天”情感就足以充当“真正的率性”的体验性标志,也即:凡伴随着“敬天”情感而出现的“真切的应然感”,就是适切当事人此时此刻处境的“真知”。但问题在于,在“敬天”情感中所认定的“善性”并无具体指向(《中庸》所谓“不睹”“不闻”),因而也就无法出示“率性”所应直面的实体;与此同时,“敬天”情感可以和多种“观念—倾向”相结合,那种以特定“知识—理解”系统为真理的人在坚持其既定“知识—理解”(而非体察“鲜活的性之发见”)时,同样也可以有“敬天”情感相伴,《大学》所谓的“顾諟天之明命”,一种平实的解读便是将其理解为权威的“传统德目”① 当然,拔高的解读便是将“天之明命”理解为“天命之性”,如朱子所谓“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参考[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
或者,也许还存在这样的希望:诸如“戒慎”“恐惧”“慎其独”“王门四句教”等功夫论言辞,是否足以帮助当事人准确地锁定“性之发见”?对此,只要想想《大学》“慎其独”实际上迥异于《中庸》“慎其独”(前者更近于荀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言辞要想成为界定“真正的率性”的有效指标,必须先在“知识—理解”上解决自己的界定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无法在作为“真知起点”的“率性”之外,处理“知识—理解”或“真知”问题。
可见,在“性善论”框架下,“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根本就是令人绝望的问题。对“真正的率性”提出的任何界定P,马上又会招致新的真知追问(“什么是真正的P”),最终在“什么是真正的……”陷入无限后退。就此而言,“真知”问题不能再反加诸“率性”,换言之,性善论(当然,只能是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必须自觉悬搁“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并勇敢地将“率性”等同于“体察真切的应然感”。
2.2.2 对苏丹草全磷的影响 不同接种剂对苏丹草全磷含量均有影响,全磷含量由高至低的处理依次为F5>F6>MR>F1>F4>F3>CK>P>F2。各接种剂处理(除P、F2外)较CK全磷含量可提高6.7%~26.7%,F2最低为0.26%,F5含量最高,为0.38%,F5与CK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余处理均与CK差异不显著(图2-B)。
这样做看似如释重负了,但接下来却必须面对“不同的率性者围绕同一桩公共事务率性者出现分歧乃至激烈的冲突”的问题——“真切的应然感”常常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界定本体的性善—率性论”最终只能导向一种类似“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共处模式吗?如此的话,在涉事诸方分歧深刻、冲突严峻的情况下,这种“性善—率性”论必定难以为继。特别地,在需要采取统一行动的公共事务上,“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式的“各自跟着各自的感觉走”的交往模式,注定只能被弃若敝屣。鉴于此,我们需要在公共生活领域为“不界定本体的性善—率性论”,增设一条“谋求共识”的补充原则。这样,涉事诸方之间分歧的暴露、冲突的进展,可以不断被设定为新一轮“率性”的处境因子——涉事诸方本着“谋求共识”的意识,不断在更新了的“处境”意识下重新“率性”,直到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共识。如此,涉事诸方自然而然会因问题获得了成功的解决,而强化其对于“不界定本体的性善—率性—谋求共识”意识下的交往模式的信心——“性善”信念与“率性”意识在其中矣② 更多相关讨论,可参考拙作:《〈大学〉“教—学”论与〈中庸〉“教—化”论——儒家政治的“真知”困境与可能出路》第四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当然,问题未必如此简单:分歧与冲突一旦超出涉事各方理性所能承受的范围,则“不界定本体的性善—率性—谋求共识”意识与交往模式完全有可能走向破裂——这样,“性善”信念、“率性”意识势必将与“谋求共识”的善意俱焚。
六、小结
最后,我们逐一回答引言最后一段提出的六个问题,作为本篇之结论:
(一)从发生学角度看,哪种性善论更原始?
“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要比“界定本体的性善论”更原始,儒家性善论的原始文本就是《中庸》(按照本篇的叙述逻辑,《中庸》当成书于《孟子》之前① 目前,难有可靠的朴学证据证明《中庸》、《孟子》的成书先后顺序,相关论说归根结底皆取决于论者所采取的文本解释方案与心目中的思想史(哲学史)逻辑。学界曾一度根据“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等字样,断定《中庸》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后来,郭沫若转而强调:“任何古书,除刊铸于青铜器者外,没有不曾经过窜易与润色的东西。但假如仅因枝节的后添或移接,而否定根干的不古,那却未免太早计了。”参见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1982版编校再版),1996年,第130页。李学勤先生亦有类似考量,可参考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它所提供的正是一种“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
(1)情报信息机构科技在服务于创新领域的工作过程中,其知识服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2013年前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在2009年和2013年达到高位,之后其文献发表数量开始呈下降趋势,表明近几年情报信息机构在知识服务领域的研究活跃性降低。
(二)驱使这种性善论出场的问题意识又是什么?
《中庸》作者藉孔子语录,从普遍性的非“过之”即“不及”现象中,体会到“真知”问题是一切生存问题的总根源。《中庸》作者同时通过孔子语录意识到,“知识—理解”归根结底只能是“当事人亲自理解”,特别地,书本和教师无法直接向当事人灌输理解。正是这种普遍地落在一切学者头上的“真知”问题,迫使《中庸》作者不得不义无反顾地认定“人人生而固有绝对可靠的内在的真知向导”,此即“天命之性”。在“绝对可靠”的意义上,此“性”是纯善的。
(三)逻辑地看,哪种性善论更融贯?
“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不得不奉既定的知识系统,尤其是特定的“宇宙论—生成论—本体论”系统为圭臬,在功夫论层面势必滑向“依赖既定知识系统外铄”的性恶论思维。“界定本体的性善论”故而在总体上自相矛盾。退一步说,即便存在一整套现成的“界定本体的性善论”,但由于功夫论上的“性恶”取向,这种性善论者亦将缺乏作为“真知起点”的“率性”意识,从而无法正确理解“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对善性本体的具体界定,无法从中获取指导自己生存的“应然真知”。而“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则全然围绕“如何维持‘率性’意识的‘真知起点’地位”展开,因而是一种彻头彻尾融贯一致的性善论。
(四)儒家究竟在什么意义上需要一种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
处于上手状态的“真知起点”,对于处理“真知”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优先性。没有“真知起点”,就无法获取“真知”,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考虑到“界定本体的性善论”无法维持“率性”意识的“真知起点”地位,儒学因而需要“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协助(实质上是鼓励)生存者树立或发动“率性”意识。除非“性恶—外铄(教)”论找到了向受教者(学生)直接灌输“真知”的有效途径,否则,在“树立真知起点”的意义上,儒学将永远离不开“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
(五)在两种性善论的分歧与竞争之中,蕴含着何种未竟的问题?
“界定本体的性善论”的提出,实质上是想把“真知”问题,反过来加诸“率性”或“真知起点”本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冲动呢?这是因为:在现实生存中,对于同一桩公共事务,不同的率性者常常会在见解与行动上出现分歧——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率性”,乃至对于“性善”的怀疑,就会应运而生。然而,在“真知起点”(作为一种上手状态的生存意识)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界定性本体而规定何为真正的率性,或在否定“性善”的同时诉诸“教—学”授受“应然之知”,这两种做法(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严格来讲(就其作为“真知”问题的处理方案而言)都是无效的,必须另觅无解决之道。
(六)有无可行的解决渠道?
我们有如下简单设想:将见解与行动上的分歧,作为涉事诸方新一轮“率性”的新处境,涉事诸方通过新一轮(几轮)的“率性”不断谋求新共识,只要能够通过这种一轮接一轮的“率性”不断化解分歧,当事人的“性善”信念与“率性”意识就会被不断巩固并挑旺。这种方案是否可行,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韧性,即:在分歧严重乃至极端冲突情况下,涉事诸方是否仍然愿意本着“率性”意识谋求共识?一旦“在‘率性’意识中谋求‘新共识’”的意识断裂,涉事诸方即便最终平安度过了分歧与冲突,亦不会再将功劳归给“性善—率性”。
参考文献:
[1]王博.论《劝学篇》在《荀子》及儒家中的意义[J].哲学研究,2008,(5).
[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戴琏章,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M].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
Two Types of the Conf ucian Theories Concer ning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Logic of Their Evolution——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al Dile mma and the Ap proach of Upgr ade
ZOU Xiao-do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 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 ’nan 250100,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ether or not defining the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 itself,there appeared in the histor y of Conf ucianis mt wo types of t heor y on the topic.By retur ning back to the basic problem of existence,observing the t wo statuses of the theories historically,and discovering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 traditional Conf ucianis m w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and may creatively find its way of f urther develop ment.As the original stat us of t 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 t heor y,Zhongyong does not define the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 itself but just make use of the active and continuous guiding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which constitutes a coherent thinking f ocus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observing t he instant guiding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However,the disadvantage of this thinking is that sinceit cannot effectively include the traditional items of the virtue or the authority of exter nal gover ning-teaching the autono mous agents f ull of the spirit of self-centralis m may be ver y difficult to constitute a har monious society.There also exists another type of the theory that does define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 itself fr o m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items really highlights the exter nal authority,in which circu mstance,however,the active and continuous guiding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is replaced by the deduction of the given teaching of authority.Logically speaking,this latter type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 ure theory is a self-contradiction.In or der to deal wit h such a cr ucial issue,it is necessar y to introduce both t he concept of the circu mstances of obeying one’s Nature and t he mechanis m of renewing the social member’s co mmon views.
Key wor ds: proble m of knowing the tr uth;defining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not defining the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 man nature;circu mstances of observing the instant guiding of one’s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renewing of the co mmon views around the public affairs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2019)01-05-019
收稿日期: 2017-08-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性论通史”(15ZDB004)
作者简介: 邹晓东,男,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暨《文史哲》编辑部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春梅
标签:真知问题论文; 不界定本体的性善论论文; 界定本体的性善论论文; 率性的处境论文; 共识更新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