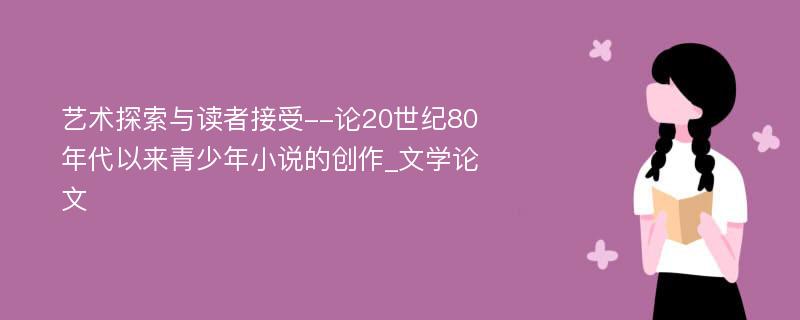
艺术探索与读者接受——80年代以来少年小说创作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读者论文,少年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艺术探索和接受疑难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正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学过程的转换期。一方面,世界上最庞大的少年儿童读者群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精神饥荒期;人们在茫然四顾、痛心疾首之余,不免生出一缕伴着浓浓惆怅的怀旧感——50年代被称为当代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它仍然向20年后的文坛放射着它光荣的余辉。另一方面,被传统熏陶和调教出来的人们也已经隐约意识到,一个正在到来的文学时代期待的是新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传统文学观念的许多方面,首先是它所负载的价值观念,将被一一重新检测,其中相当一部分将发生根本的动摇和瓦解。
例如,继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引起整个社会广泛的震动和公众普遍的焦虑感之后,王安忆的少年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相隔一年多以后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另一场轩然大波。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小说的人物个性和品质上。这一事件虽然不是起因于一个单纯的艺术争议,但它的出现仍然是富有挑战性和象征意味的:它从价值观念的层面上开始向传统儿童文学的艺术规范发难,并且多少意味着一个新的儿童文学艺术里程的即将到来。
因此,至少在70年代末,后来少年小说的一些新的艺术动向和艺术品质已经初露端倪了。这些艺术动向和品质的逐渐酝酿和展现,最终汇聚成了一个令我今天一旦回想起来便会怦然心动的文学时代。
这个文学时代的真正到来是在80年代。对于80年代的儿童文学来说,太阳确实每天都是新的。新的观念、新的作者,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一个个题材禁区、观念禁区的突破,一个个新的文学手法、技巧的尝试和运用,儿童文学跟整个当代文学界一样,被“创新”这根魔棒指挥得团团打转。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小说一直扮演着最为活跃的文体角色(以“热闹派”、“抒情派”为代表的童话创作也有十分活跃的艺术表现,本文对此暂不涉及)。以程玮、曹文轩、班马、梅子涵、张之路、董宏猷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作家(他们的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创作了《白色的塔》、《古堡》、《鱼幻》、《蓝鸟》、《空箱子》、《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等一大批少年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以其对传统少年小说艺术规范的强烈的反叛意图和倾向,以其对少年小说新的艺术表现可能的大胆探寻和求索,而被人们称为“探索性”作品。例如,在班马的小说《鱼幻》中,对一种“江南”味道的传达,以及感觉描写中表现的象征和暗示,意象的变幻不定所带来的神秘感等等,都给人以强烈的新奇感。董宏猷的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则追求文体上的“魔方效应”,那一百个不同年龄孩子的梦幻仿佛构成魔方的那许多小小的色块,可以随心所欲地拧出各种不同的图案,而这些不同色块的组合也有其内在的规律,那是一种“最美丽的杂乱无章”,一种“潜在的秩序”。这些作品所提供的文学内涵和文学形态,是过去少年小说中难以见到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它们以自己的出现,丰富、发展了少年小说的审美形态,甚至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提高了儿童文学的美学品位。
然而,少年小说艺术现象的这种丰富和发展又必然是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进行的:它试图以一种新的文体构成方式来更新人们对生活和经验乃至对文学本身的感觉。当习惯了传统文学形态的读者突然面对着这么一些陌生的作品的时候,种种困惑、怀疑、诘难甚至拒绝的出现便是十分自然的了。而所有这些表示,最终又汇聚成一个共同的疑难:少年读者能接受这些作品吗——因而,这些作品能算是儿童文学(少年小说)吗?有关《鱼幻》的种种讨论,十分典型地向我们传达了少年小说艺术实践中的这种接受疑难。
《鱼幻》缺乏传统少年小说所具有的那种审美上的明晰性。对于习惯于用一两句话拎出作品主题思想的读者来说,它所传达的“江南味道的意境”可能反而容易被轻易地忽视掉。作者班马曾经表示说:“写《鱼幻》的动机,便是想让小读者得到一点江南味道的意境,也就是在心中增添那么一点中国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对他们已成为陌生的了,而‘陌生’,却正是我所要表现的”(《关于〈鱼幻〉的通信》,见《儿童文学选刊》1987年第4期)。 陌生的文化背景加上陌生的传达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传统的视读经验感到加倍的陌生了。
当然,那些有着良好文学素养的大读者还是喜欢《鱼幻》的,他们担心的是少年读者能否接受这篇作品。于是,“接受”,成了当代少儿文学发展进程中最令人困惑也最使人感兴趣的理论话题。在许多作品的讨论中,最强有力的诘难都是从“接受”的角度提出的。比如我们不时听到这样的说法:少年读者无法理解和欣赏如此高深莫测的作品。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接受疑难呢?
二、寻求新的视野融合
对当代少年读者实际接受能力的隔膜和缺乏了解,是现今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疏忽。由于这一疏忽,在考察和探讨儿童文学的最新发展时,人们面对新的艺术现象,手中却操着既定的评判尺度,这一尺度是以对少年儿童接受能力的固定的、单一化的理解为依据而刻定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尺度可靠吗?
很显然,当人们用一种固定单一的尺度去衡量测度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时,人们显然没有认识到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对少儿读者文学接受行为的塑造和潜在的制约作用。与成人比较起来,少年儿童的接受行为常常表现出对于特定审美传统和文化背景较为疏离的状况,但是,少年儿童审美心理的发展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是从生命的自然行为走向审美的文化实现的过程,因此,当我们看到少年儿童审美接受过程中童年生命的自然冲动的一面时,还应意识到特定社会文化现实对这种自然行为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充分认识当代少年儿童接受心理和行为的某些深刻的变化。
从生理层面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普遍出现了性发育早熟的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欧洲女孩子月经初潮从19世纪中叶的16—17岁,在20世纪中叶提前到12—13岁。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80年代初期的调查表明,中国大城市女孩初潮平均年龄12.8岁,80%的城市男孩15—16岁出现遗精。这种性成熟期的提前必然会对当代青少年的心理行为模式和文化消费需求产生相应的影响。“从整个世界来看,青年期到来越发提前、持续越来越长。数年前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现在则影响到高中,甚至更小的学生”(彼得·伯杰等著《人生各阶段分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 页)。未来学家托夫勒曾提出了“未来冲击”(future shock)一词,用以说明由于社会结构和组织的高速变化,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及消费者产品的锐变,使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发生超负荷负担并产生惊异、紧张的现象。托夫勒借助这个术语解释当代西方社会的某些奇特情况,如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再像孩子样。在这样一个时代,少年儿童的文学接受行为也必然会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和变化性。对20世纪的少年儿童读者来说,他们的文学趣味和能力与以往时代的同龄人相比,都大大地发展变化了。德国作家柏吉尔很早就谈到了20世纪少年儿童接受趣味的变化——古代传奇性的作品已很难激发儿童的喜爱之情,很难使他们迷恋了。“20世纪的孩子,已经养成一种强烈的现实意识,和一种对日常生活密切接触的技术产品的爱好……他宁愿玩机械的火车,而不愿玩我们少年时代所喜欢的滑稽木偶;他对于那些穿插着近代技术伟迹与紧张冒险的故事,比之《狼与小红帽》的童话更感兴趣。”这种接受趣味和行为的变化无疑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塑造的结果。
同样,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艺术文化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这一代少年儿童的接受趣味和能力。因此,人们完全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当代少年儿童读者的文学接受趣味和能力的那些超出成年人想象的变异和发展。从笔者在各地学校实地调查的结果看,当代少儿读者的阅读内容中,中外文学名著和通俗小说占了主要位置,而当代少儿文学作品却很少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因此是否可以说,传统艺术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少儿文学包括少年小说作品与少儿读者阅读视野的脱钩?由此看来,少儿文学创作必须寻求与少年儿童读者的新的对话可能和对话方式,借用接受美学的说法,也就是要寻求少儿文学文本结构与少儿读者期待视野的新的融合。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上,我们看到了当代少年小说作家寻求与当代少儿读者建立新的艺术对话和审美联系的文学探索和努力。
三、探索性作品所表达的接受观念
80年代以来少年小说作家以他们的探索性作品表达了他们对当代少儿读者和少儿文学接受问题的独特观念和认识。
首先,探索性作品的出现表明,一些作家调整了对于当代少儿读者文学阅读需要和接受能力的认识。他们不满足于充当一个传统文学对话关系的继承人,而尝试与新一代少年读者签订一份新的文学契约。他们认为,传统的少年小说艺术规范已无法满足当代少年读者的接受需求,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文学语境中进行新的艺术探索。这种探索所带来的文学形态的变化,当然并不预示着传统少年小说艺术形态将完全失去其存在价值,相反,它带来的是少年小说审美形态和对话姿态的丰富。
其次,探索性少年小说不是从一般少年读者已有的审美感受力出发,而是更着眼于如何拓宽少年读者的审美感受阈,因此在表现出作家对少年读者接受能力的新的理解的同时,又体现了一种审美上的启蒙意图和超前意识。曾经写过《蓝鸟》、《双人茶座》、《我们没有表》等作品、近年来着意于寻求新的少年小说叙述形式的梅子涵在一次会议上与笔者谈到,他的意图之一即在于训练少年读者的接受能力,“你不会读,作品教你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性作品不是放弃与当代少儿读者的艺术对话,而正是为了加强和扩大这种对话。
第三,探索性作品的创作者意识到,少儿读者并不是没有内部差异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包含着各种差异的读者群。由于这种内部差异,少年读者的文学接受能力和趣味也呈现出种种分化趋势。探索性作品的创作者们即试图以较高层次的那一部分少年读者作为自己的接受者,并在这种文学接受关系中来确定自己的生存价值。
毋庸讳言,对于当今大多数少年读者来说,探索性作品强烈的“陌生感”使得作家的努力在他们那里的收效究竟如何尚需打一个问号。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已有的探索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少年小说实验性文本,其开拓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起初以“先锋”身份出现的实验性少年小说艺术形态逐渐成为新的艺术常态。比如张之路,他的相当一些少年小说作品往往不拘泥于传统的写实手法的限制,而大胆地借鉴了某些童话式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大框架怪诞而细节真实”或“大框架真实而细节怪诞离奇”的“怪诞小说”。在语言层面上,张之路的叙述口气是适度收敛而又“侃味儿”十足的,表现出较高品味的语言智慧和幽默才能。当这种怪诞小说在少年小说领域出现时,它们新奇的表现手法和诱人的叙事效果是令人惊叹的,但它们很快获得了读者的接受和喜爱。同样,梅子涵的小说最初出现在少儿文学刊物上时,少年读者曾为其独特的文体和语感而感到陌生和困惑。但是,当他的近作《林东的故事》入选《儿童文学选刊》时,人们几乎已经感到习以为常。耐人寻味的是,《林东的故事》进入《儿童文学选刊》是因为读者的喜爱和推荐。
四、90年代概观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少年小说创作的美学起点、文学语境、成长环境等已完全不同。进入90年代,整个儿童文学界平静了许多,少年小说也不像80年代那样总是会不时给人们带来一些新的感受和阅读刺激。不过,90年代的少年小说创作虽然未能再现80年代的艺术探索景观(事实上,简单的再现已不可能),但这并不等于说少年小说创作又回到了80年代的起点,而且,90年代一些执著于少年小说创作的作家、编辑们仍以自己的方式做着新的文学努力。只是,这种努力变得更为内在了。有的作家说自己仍像80年代一样写作,江苏《少年文艺》在1995年开始了“新体验小说”的倡导和试验。这些是否可以证明:探寻和创造新的艺术可能的信念,在今天的少年小说创作中依然没有缺席?
内容上看,近年少年小说创作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许多作品表达了进入90年代后作家们对当代少年精神个性和品质的新的艺术发现和诗意把握。比如,同样是表现青春期少年的心理萌动、渴望或烦恼、迷茫,80年代的少年小说作家们常常忙着做出种种价值分析和判断,而90年代的作家们似乎并不急于摆出这种姿态。他们更关注的是当代少年心灵在日常生活流动中的独特生存和展示方式。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想见米男》,梅子涵的《曹迪民先生的故事》、《女儿的故事》、《林东的故事》,班马的长篇小说《六年级大逃亡》等。我以为,这些作品对当代生活和少年人生的揭示,有着一种更质朴、更幽默、也更耐人寻味的力量。
从叙事形式和技巧方面看,90年代的作家变得更自觉、更自由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对形式更新和创造的迷恋,一直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十多年来的少年小说创作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具有强烈的形式创造意识的作家,有了一批或成功或幼稚或失败的形式探索与创新之作。不久前,我读到了上海《少年文艺》刊登的梅子涵的近作《曹迪民先生的故事》,它再次给了我的阅读经验以相当强烈的冲击。梅子涵无疑是近十几年来少年小说界最具有形式感和先锋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显示了强烈的个性表达欲望和形式更新倾向。可以说,《曹迪民先生的故事》又将这种表达欲望和形式倾向推向了新的极致。它的叙事方式似乎毫不经意,用传统的技术主义观点来看,它的随意和任性更是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不过,我自己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充满了愉悦,因为我不知道梅子涵将告诉我一些有关曹迪民先生的什么故事,不知道他将用何种“腔调”来叙述曹迪民先生的故事。整个阅读过程因此充满了意外和悠然会心之处——这使我感到相当的满意。事实上,一个叫梅子涵的作家和一个正上五年级的叫曹迪民的先生之间的交往,不就是那么随意、天真和有趣吗?而在看似随意的叙述形式中,隐伏或昭示的是并不随意的精神价值和心灵形式。因此,作品在似不经意的叙述形式中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技术美学观念的文本形式。
由此可见,90年代少年小说创作仍然保持着应有的艺术创造姿态。只是,读者已经变了。面对90年代少年小说相对丰富多彩的文学现实,今天的少年读者已经开始习惯于镇定的接受各式各样的少年小说作品了。
因此,由少年小说作家的艺术探索而引起的少年读者“接受”方面的疑难,在90年代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但是,90年代少年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相对成熟和自信,却并未在少年读者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从现象上看,90年代少年文学作品的发行量除了个别作品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等外,一直未能“攀高”。不久前揭晓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获奖的19部各类作品,大多数的发行量均只有数千册到一万册左右。这就是说,当代少年读者对当代少儿文学作品的实际上的“接受”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例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之下,商业话语权以不容置辩的强势姿态挤压着儿童文学的纯艺术话语权;又如,各种迅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兴文艺消费类型的出现,也蚕食着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再如,“应试教育”重负下的当代少年儿童读者群不得不被迫与儿童文学保持着某种距离。问题看来十分严峻,而且,如何使当代少年儿童读者重新亲近儿童文学(少年小说),这显然不是一个纯艺术范围内的问题。
看来,处于世纪之交的少年小说创作,将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来思考自身的艺术创造和读者接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