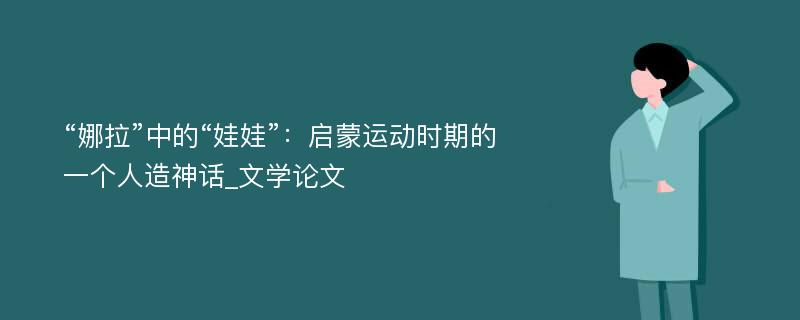
“玩偶”被“娜拉”:一个启蒙时代的人造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玩偶论文,神话论文,娜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到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我们首先会想到挪威作家易卜生。众所周知,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一个“易卜生专号”,使中国人知道了西方有个女性名叫“娜拉”,她敢于反抗性别歧视并勇敢地离家出走,最终摆脱了受制于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于是一时间,“女性解放”之声不绝于耳,“娜拉”不仅成为了中国女性的效法对象,同时更为处境尴尬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一针令人兴奋的强心剂①。因为将妇女问题升华为社会问题,无疑会增强国人对于思想启蒙的关注热情;而《玩偶之家》绝对中国化的意义阐释,又直接导致了“五四”时期“所有价值观念的变革”②。所以茅盾才会颇有感慨地回忆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等新运动的象征。那个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上,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③
毋庸置疑,易卜生以其《玩偶之家》拯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中国“娜拉”所负载起的那些苦难意识,也被悄然转换成了民族振兴的时代符号。但“娜拉”一词原本是出自于男性之口,它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普遍意义而非性别意义。比如,胡适早在倡导“易卜生主义”时,就已经开诚布公地声明在先:“我们的宗旨……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④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社会改革”一词的巧妙使用——什么是“社会”?说穿了无非就是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所以“社会变革”的真正实质,就是新的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要颠覆旧的男性主体的利益集团,“性别”只不过是一种用来遮掩的幌子罢了。“五四”女作家庐隐最早看出了一些门道,她曾直言不讳地抨击道,男性言说“娜拉”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想改变女性群体的“玩偶”地位,而是在“利用妇女解放‘冠冕堂皇’名目,施行阴险狡诈伎俩”而已。因为庐隐并不相信男人的良心发现,所以她才会向社会大声呼吁说:“妇女解放问题,一定要妇女本身解决。”⑤其实何止是庐隐一人,中国现代女作家如沉樱、石评梅、凌淑华、罗洪、萧红、梅娘、施济美、张爱玲、苏青等人,也都对“娜拉”主义持顽强抵触的排斥态度,她们以一篇篇充满着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学作品,向读者述说着一个个新女性被“娜拉”而实为“玩偶”的悲惨命运。
一、“玩偶”的失语——谁在言说与为谁言说
谈到中国新女性的真实处境,我们仍然需要从思想启蒙说起。
众所周知,受西方人文思潮的深刻影响,早在晚清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女性解放”的响亮口号,就已经是铺天盖地呼声四起。根据现有史料的线索来看,上海《申报》于1876年3月,曾发起过一场“兴办女学”的社会大讨论;其中署名为“棣华书屋”的长文《论女学》,便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了1878年,《申报》又组织文章,对女子参与社交问题再次展开热烈讨论;而1897年春天,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更是在中国妇女界兴起了一场“天足运动”。从此以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感召之下,国内“女性解放”的强劲势头,则更是此起彼伏锐不可当。
然而,“女性解放”究竟是“谁在言说”?当然是那些男性启蒙精英了。紧接着便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男性启蒙者究竟是在“为谁言说”?关于这一问题那可就大有深意了。晚清时期倡导“女性解放”运动之不遗余力者,当首推岭南思想革命家梁启超。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文里,提出来一个绝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⑥梁启超这种“救国”需始于“救国人母”的鸿篇高论,几乎受到了当时社会大多数知识精英的全力追捧。比如“竹庄”就在《女子世界》上撰文响应说:“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所由来也。”故他认为无“国母”便无“国民”,只有“国母”解放了,“国民”才能够得以解放⑦。而“亚特”也撰文阐明立场,他强调“国母”为“因”而“国民”为“果”,若“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⑧
综观晚清时期男性知识精英的启蒙言说,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言说者注意到了中国妇女没有人权地位的历史事实,并且也意识到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此在一个女性缺少掌握自我命运话语权的封建体制内,由他们出面去替那些不幸女性诉说苦难和代言解放,无疑是一种有识之士悲天怜人的正义之举,我们应该对其正面意义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充分肯定。二是言说者畅言解放“国民之母”的真实意图,却并非是在于“母”而是在于“民”,梁启超等人其实是想要通过“母”与“民”之间关系的逻辑转换,去突现他们“新一国之民”的梦寐以求的人文理想,这又与西方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根本宗旨完全不同。如此一来,由“男性”在“言说”到为“男性”而“言说”,便构成了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全部内容;而那些作为男性“玩偶”的中国女性,则始终是处在高度失语的状态之下。虽然晚清也出了一个女中豪杰秋瑾,并对女界发出过除去奴隶根性的热切呼唤,但是秋瑾本人则在《勉女权》一诗中明确地表示过,女性解放必须同“反清排满”的社会革命结为一体,只有在“恢复江山劳素手”中“独立占头筹”,才能够“一洗从前羞耻垢”获取属于自身性别的“真自由”!秋瑾将女性解放捆绑于社会解放,这说明她也并不了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同时更是流露出女性渴望被男性拯救的殷切期待,对此无论学界怎样去辩解都是令人沮丧的徒劳之举。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女性解放”最热闹的一个时代,各种打着西方旗号的理论主张轮番上阵,营造了一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繁荣场景。比如从《易卜生主义》中人们引申出了“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从《娜拉走后怎样》中人们又引申出了“独立女性”与“职业女性”。其它诸如“贞操”与“节烈”、“离婚”与“试婚”等一系列问题,也都成为了当时启蒙精英常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甚至更有人借“女性解放”之口号,去大肆宣扬“一妇多夫主义”,认为“一个女子可以恋爱几个男子”,只要“不妨碍社会上其他的人便得了”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解放”浪潮,实际上仍没有逃脱男性“言说”且为“男性”言说的历史窠臼,“言说”主体还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男性启蒙精英,“女性解放”只不过是开启“社会解放”的一种铺垫。笔者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具有历史依据的,比如胡适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表面上对中国新女性有所期待,但实际上女性问题却并不是他要谈的核心问题:
如今所讲美国妇女特别精神,只在她们的自立心,只在她们那种“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这种观念是文明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我们中国的姊妹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足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超于贤妻良母人生观”来补足我们的“贤妻良母”观念,定可以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⑩
仔细阅读这番女性解放的思想高论,有一细微变化之处不应被忽视:胡适从女子“自立”过渡到男女“自立”,笔锋一转便使命题概念发生了质变——“性别”解放已经不再是他想要言说的中心思想,而“人”的“自立”才是他突出强调的“意义”重心。尽管“女子”与“男女”只是一字之差,可其位置却被放在了“男人”之后。这种偷梁换柱式的语言表述,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里也出现过,比如他在对女子“节烈”进行了一通讨伐之后,却将他对于未来社会解放的全部希望,都转向了“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最终使“人类都受到正当的幸福”(11),“性别”意识更是被升华到了“人类”意识的启蒙高度——“女性解放”的自身意义,无疑遭到了遮蔽与消解。伴随着“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按理说她们应该就性别解放问题去进行独立的思考,然而不幸的是长期受封建礼教的思想束缚,她们已经难以彻底摆脱对于男性社会思维的心理盲从,即使偶尔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叛逆之声,也会很快地被气场强大的男权话语所淹没掉。检视一下“五四”新女性最经典的解放主张,无非就是表示要求去做一个“独立的人”;至于究竟怎么样才能够争取到这种“做人”的资格,向警予则颇有代表性地说出了她们的共同心声:“只有整个民族、整个劳苦大众都获得了解放,中国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2)这无疑是秋瑾女性解放观的再次重现。做一个“独立的人”与做一个“独立的女人”,虽然字面意义相似但本质意义却完全不同——做一个“独立的人”是对男权社会解放话语的积极响应,而做一个“独立的女人”则是对男权社会的直接挑战。新女性并没有超越男权话语形成性别解放的理论主张,无论她们如何去挣扎,都难逃男性“玩偶”的悲剧命运。
由男权话语所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不仅在思想文化层面造成了一种全民响应的社会声势,同时更是在文学创作领域建构起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原则。稍微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践,我们便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高度雷同的叙事模式:中国女性深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她们从来就过着任男性肆意蹂躏的奴隶生活;中国女性中封建礼教的毒害之深令人发指,她们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解放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性都发自内心地渴望婚恋自由,却又苦于守旧势力的过于强大而无所适从,所以她们必然要寻找一个思想启蒙的男性导师,进而通过他们的指引最终走向性别解放的光明坦途。
我们不妨以《节妇》(彭家煌)、《模特儿》(许钦文)、《获虎之夜》(田汉)和《伤逝》(鲁迅)这四部作品为范本,来做一番生动而形象的艺术分析。《节妇》讲述阿银十八岁便成了七十岁“候补道大人”的续弦填房,可仅仅过了两年“候补道大人”便驾鹤归西;阿银在家人眼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为了生存她只能够去委身于长子柏年;然而没过多久其长孙振黄也对年轻的“祖母”产生了好感,他又瞒着父亲将“阿银接到自己的寓所里住了半个月”。作者让阿银成为“候补道大人”一家三代男性的共同“玩物”,无非是想通过这一荒唐故事去说明两个问题——孔孟之徒的虚伪本质与中国女性的非人生活。《模特儿》描写某少妇为夫守寡七年,村中大户均赞其美丽贤惠有意续娶,但她却恪守礼教执意守节概不应允;无论其公婆是如何地刁钻刻薄,她都不离不弃始终侍奉于左右,即使生计艰难也无怨无悔从一而终。《模特儿》的创作主题意在告诉读者,中国女性受传统旧俗的毒害极深,她们早已麻木到了难以自救的可怕地步。难道中国女性就没有她们自己的思想追求了吗?回答当然是有的!《获虎之夜》里的富家女魏莲姑,就敢于同表兄黄大傻眉目传情私订终身;遗憾的是这种缺乏现代感的爱情故事,终难抵挡住家长专制力量的外部干预——古老的故事必定会产生古老的结局,至多不过为中国文学史再增添一部悲剧作品而已。于是,《伤逝》便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引导性意义:整篇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涓生一个人在“言说”,他对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种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是使子君茅塞顿开幡然醒悟,终于向全社会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反抗呐喊!涓生启蒙子君的叙事模式,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不仅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对其进行了全盘仿效,就连巴金《家》中觉民与琴表妹的情节编排也留有鲜明的借鉴痕迹。毫无疑问,男性“解放”了女人,实际上就是解放了自己,否则子君也不会成为涓生逃避孤独与寂寞的宣泄工具,素裳也不会堕入施洵白所设下的温柔陷阱。对于男性言说的“女性解放”,笔者个人的看法其实很简单,无论男人怎样去言说解放女人,其骨子里所想到的还是男人。换言之,男性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绝不是去追求什么男女平等,他们只不过是在借助这一话题,去实现自身想要达到的某种目的!
男性精英关于“女性解放”的启蒙言说,曾受到过庐隐等人的强烈质疑,也遭到过丁玲等人的激烈反抗,这本应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是由于男性在中国现代社会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新女性自身弱势难以抗衡的尴尬局面,这就迫使她们不得不去承认一个客观事实,新女性只能是作为“被拯救者”而存在。所以,杨沫干脆便以一部《青春之歌》,自觉地终结了“五四”以来的性别之争,因为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锡、江华)和一个女人(林道静)的故事结构,已经十分明确地阐释了她对“女性解放”的基本立场——女人思想的“成长”过程,根本就离不开男人的扶持与提携!
二、“娜拉”的叹息——谁被蒙骗与被谁蒙骗
西方现代女权主义者曾抱怨说:“女性心理学至今为止都仅仅从男性的观点角度进行考虑……女性心理学至今实际上代表了欲望的沉淀和男人的失望。”(13)毫无疑问,这种抱怨带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那就是她们对于男性主观言说女性的强烈不满。在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中,新女性虽然始终都是处于一种主体“失语”的沉寂状态,既没有提出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但却并不表明她们一直都在被动地相信性别解放的男性言说。比如五四女作家庐隐,便在小说《海滨故人》里,以一声“知识误我”的悲凉呐喊,向男权话语发起了诘难。
科学地诠释“知识误我”的真实含义,首先牵扯到一个什么是“知识”的关键命题,然后才能够去准确地回答它究竟是怎样“误我”的。自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开始,“婚姻自主”与“恋爱自由”等因素,就被当作是现代西方的人文“知识”,成为了“个性解放”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至于西方文艺复兴是否是以“女性解放”为滥觞,我们在这里姑且可以暂时不论;但发生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明显表现为一场全民“恋爱”的时代热潮。这里有一个十分微妙的逻辑关系,值得我们研究者去高度重视:将“婚恋自由”作为启蒙话语,就必然绕不开“女性解放”;因为女人若是不“自由”,男人就不可能去“恋爱”。所以聪明的男性启蒙者便以西方人文精神为借口,干脆就把“女性解放”运动,直接定性为是一场“恋爱”运动。用茅盾的话来说,“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14)茅盾此番言说,精辟概括了启蒙“知识”的基本内涵;而新女性热衷于为情“出走”,又以实际行动对其提供了佐证。
我们不妨举两个当时轰动上海的具体案例:一是黄慧如与陆根荣主仆“私奔”案——大户千金黄慧如与家中车夫陆根荣,两厢情愿偷食禁果并且在外同居,被黄家发现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结果是闹得满城风雨世人皆知(15)。二是孙小妹与王书义为情“私奔”案——孙小妹不满父母包办婚姻,与青年男子王书义私订终身,于是父母状告王书义诱拐其女,而孙小妹本人却勇敢地站出来请求社会“维持其自由恋爱之婚姻”(16),其他如蒋碧薇与徐悲鸿、杨之华与瞿秋白、陆小曼与徐志摩、王映霞与郁达夫等浪漫故事,也都曾是“五四”时代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误我”。由男性启蒙精英所积极倡导的“婚恋自由”,到底为新女性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福音?如果说真是一场性别“解放”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那么也就根本不会产生什么“知识误我”的女性哀鸣;但是“被娜拉”而实为“玩偶”的现实写照,则理所当然地会促使女性去发泄“知识误我”的满腹牢骚。只要我们翻翻当时社会的报刊杂志,有关因“自由恋爱”所造成的女性悲剧,几乎是俯拾皆是。比如1923年新女性梅淑娟不顾父母反对,与某男青年“自由恋爱”并且同居,没想到该男青年的热情劲没有持续多久,便将梅淑娟抛弃而另娶他人,结果使她不堪此精神打击抑郁而亡(17)。又如1924年黄女士受新思潮影响,与已婚男子王某发生了“自由恋爱”;王某在骗取了黄女士的财色之后又移情别恋,最终使她人生绝望跳楼自尽(18)。再如1928年的马振华与汪世昌事件,两人以“婚恋自由”为借口仅仅同居了三个月,汪姓男子就以马振华已不是处女为借口离她而去,逼得该女子只能是以投水而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苏雪林也曾以“五四”见证者的身份,向人们讲述了这种畸形“自由恋爱”的真实场景,她说那时大学里“男学生都想交结一个女朋友,哪怕那个男生家中已有妻儿,也非结交一个女朋友不可”(20)。男性如此疯狂地去猎取女性,这不能不引起新女性的反感和反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庐隐所说的“知识误我”,其“知识”就是指“恋爱”,而“误我”则是指“自由”!再深究一下此语的潜台词,我们发现还有一层讽刺之意: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固然是把女性当作“玩偶”,而“自由恋爱”游戏同样是把女性当作“玩偶”;古代男权社会是用宗法制度去压迫女性,而现代男权社会则是用花言巧语去欺骗女性。所以从庐隐开始,“不再相信男人”的启蒙言说几乎成了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共同心声;因为她们曾“听将令”跟随着男性离家出走,到头来却落得个遍体鳞伤狼狈而归,萧红一部《呼兰河传》便是新女性自我忏悔的代表之作!(21)
“知识误我”的文学表现,则是男性欲望的整体转移。因为男人写女人无法超越性别障碍,所以用男性视角去透视女性心理,进而以“臆想”的女人去代表真实的女人,也就成了中国现代男作家的创作法宝。男性欲望直接投影于女性身上,使得他们笔下的女性叙事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共性特点:首先,他们认为凡是女人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性欲”要求,只不过是这种欲望长期以来一直都受到传统观念的人为压制;由于她们不能也不可能去向社会伸张自己的合理要求,故替她们言说“性”之渴望也就变成了“女性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叶灵凤的小说《昙花庵的春风》,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文本——故事讲述十七岁的小尼姑月谛,独自一人下山去化缘,遇到一对男女在野地里偷欢,于是回来后立刻浮想联翩情不能禁:月谛躺在床上,双手抚摸着胸部,“只觉面部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她“发了狂似的抱着被在床上反复乱滚”,浑身像“小爬虫在骚动着想钻出”般难受,她“只觉得自己无力制止自己不这样做”,因为手淫所产生的肉体快感已使她飘飘欲仙了。叶灵凤这段少女思春的生动描写,无非是在表达他所理解的女人本质——女人原本就是一个丧失了自由的欲望动物,是外界因素制约了她们的生命本能;只有彻底解除历史所赋予她们的精神枷锁,让其放纵欲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其次,男性作家主观地认为“爱”是女人生存的全部意义,并肆无忌惮地去描写女人为“爱”而狂的痴迷状态;他们完全不顾女性“被爱”而“不是爱”的客观事实(22);最终却因作者自己的性别错位而漏洞百出。顾瓍的短篇小说《失踪》,就向读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刘渡航不仅是个热情似火的新女性,同时更是个驾驭男性情感的“恋爱”高手;她对自己所特别中意的那个“他”,始终都处于一种自我表演的主导地位:一句“喂!乖!这么爱人,像什么呢?像……你好好凑过来,让我吃它一下。乖!”立刻凸显出她那泼辣直率的大胆个性。而“哭着跪爬在他怀里”,呜咽着用“直瞪着水汪汪的两支眼睛”,向他诉说“我真心爱你”的孤独与寂寞时,又是那般媚态万千的令“他”神魂颠倒。小说《失踪》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五四”新女性的开放性格,她们似乎才是“爱情”游戏的最大赢家,而男性却是凄楚可怜的被动客体!再者,男性作家让女性成为“自由恋爱”的实际主体,并将一切爱情悲剧都视为女性欲望所惹的祸;表面观之他们是在歌颂新女性的“敢做敢为”,其实质却是在堂而皇之地替男性开脱罪责。比如杨振声的短篇小说《一封信》,便较早运用了这种偷梁换柱的叙事模式——“他从不在女子跟前献殷勤”的君子之态,使少女“我”魂不守舍地迷恋于“他”;“我”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去倾诉相思之苦,可“他”却冷若冰霜始终不回;“我”被“他”那冷漠态度刺激得几乎发疯了,“夜间每为恶梦所扰”且身体也支撑不住了,于是想要以死去解脱这相思之苦,并表示即使是遭到家人和社会的谴责也“虽死不恨”!杨振声让一个纯情少女一人在那里“爱”得发狂,而男主角却躲在幕后千呼万唤也不出来,这种男性借女性去宣泄自身欲望的拙劣伎俩,虽然逃避了社会责任却难掩其“偷窥”女性的肮脏心理。鲁迅在评价梅兰芳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23)而男人以小说去“扮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情况呢?
“必须‘摆脱男性思维模式’,真实的描绘女性的心理”(24),这是西方现代女权主义者,对女性文学所提出的一个要求。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虽然还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思想水准,但却依然以她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被娜拉”的强烈不满。新女性并不是没有生理欲望,但是她们更注重于对情感的追求,像凌淑华的《绣枕》、石评梅的《祷告》、萧红的《小城三月》、含草的《重逢》等作品,都是女作家倾情讲述其渴望“情爱”而非“性爱”的经典作品。“情”与“性”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眼中意义截然不同,“情”是爱的主体因素而“性”则是爱的附加因素;无“情”而“性”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属性,它绝不能成为人类美好爱情的牢固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女作家对于“女性解放”的启蒙话语,有着超乎男性想象的理性认识,她们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娜拉”神话,更不相信男性会为“女性解放”而去两肋插刀;她们看穿了男性为“欲望”而“女人”的真实意图,深切地感受了“被娜拉”所遭受到的人格侮辱,于是她们以新女性的现身说法,去揭穿那些男性启蒙精英的墨写谎言。
沉樱的小说《喜筵之后》,写的是新女性茜华新婚燕尔,便发现曾经狂爱自己的丈夫“现在对自己是连普通的夫妇的感情都没有”,因为他“近来正向别的女性追求”。伤感之余她只能在痛苦中去回忆往事。邢禾丽的小说《出走》,则是写“少女时代活泼爱动”的焕英,“婚后被‘成年’的锁链,箍得紧紧地再也不能放纵地嬉笑自如了”。当她把人生希望全都寄托在丈夫身上时,却突然从丈夫激情褪尽的冷漠表情里,读到了他要出轨“变心的前奏”信息。凌淑华在其小说《花之寺》中,写诗人幽泉一方面对爱妻燕倩卿卿我我,另一方面却又在外面寻找容易猎取的女性对象,幽泉最终落入到燕倩为他设计的一个圈套,受到了妻子劈头盖脸的一通批驳:“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边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意思了?”萧红的小说《小城三月》同样是借女主人公“翠姨”之口,传达出了作者对“负心”男性的“怨恨”心理:“翠姨听说了很多故事。关于男学生结婚的事情,就是我们本县里,已经有几件事情不幸的了。有的结了婚,从此就不回家了;有的娶来了姨太太,把太太放在另一间屋子里住着,而且自己却永久地住在书房里。”
为什么提倡“恋爱自由”的男性精英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现代版的花花公子了呢?女作家所给出的一致答案,多少会令男性感到汗颜——“男人是严凉的人类”(萧红《生死场》);女性解放可“常常叫女子方面吃亏”(凌淑华《女儿身世太凄凉》);“自由恋爱的招牌底下,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被践踏着”(石评梅《弃妇》);所以她们一再告诫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女子,千万“别上那些书本子的鬼当”(施济美《十二金钗》),更不要去相信男人“我爱你”的一派谎言(沉樱《爱情的开始》),所谓“自由恋爱”无非就是“用男人的钱陪男人睡觉”(关露《姨太太日记》)——因为在“恋爱死亡之后”(石评梅《恶梦中的扮演》),她们发现“男人大多数是靠不住的”(汪丽玲《婚事》)。笔者个人认为新女性自我检讨最为深刻的,还应属海派女作家苏青自我的一番调侃:“我发现自己被欺——不是被欺于对方,而是自己的希望过奢,骗了自己。”(《结婚十年》)此话真可谓一语中的,新女性不仅被男性“蒙骗”,更被自己盲目的期望值所“欺骗”;如果她们对于男权文化保持足够的思想警惕性,也就不会到头来闹得个哀鸿一片的悲惨结局。故笔者认为,苏青身上那种具有批判理性的自省意识,才代表着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光明前程。
三、“梦魇”的轮回——谁人哭泣与为谁哭泣
在“婚恋自由”的启蒙时代,为什么被牺牲的总是女性?这曾经是民国女学者陈学昭向社会发出过的强烈质疑(25)。而女作家梅娘的回答则更为绝妙:“捕蟹的人在船上张着灯,蟹自己便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蟹》)梅娘的比喻生动而形象,女人永远渴望光明,却又始终堕入黑暗;因为男人用诱骗之“灯”把她们引入到悲剧之“网”,进而造成了女人“梦魇”的命运轮回。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去解开一个谜底:“五四”时代男性启蒙者以“娜拉”为榜样,去鼓励新女性离家出走寻求解放;但从一开始人们就对于这一理论定位表现出了中国人所特有的聪明智慧——西方“娜拉”从“夫家”走向“社会”,是想要获得一个做“独立人”的存在价值;而中国女性从“父家”走向“夫家”,却是想要获得一个做幸福女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即使是如此微薄的一己愿望,她们也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故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发誓说:“今后不再流眼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萧红《沙粒·十一》)
“五四”启蒙运动以后,中国新女性的命运究竟是如何?她们真实的社会地位究竟又是怎样?这是部分中国现代女性问题研究者目前不愿去深入探讨的一个命题。笔者个人认为,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就因为她们是女人,这是由性别所决定的一种身份。女人在男人眼中,永远都是他们本能欲望的发泄对象;如果想要男人放弃这种本能欲望,那么无疑是与虎谋皮痴心妄想。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曾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后来就一反常态地讥讽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恋爱’这纯东西,男女问题不过是生理上自然的要求,有何神圣可言,偶尔游戏,消遣则可,为此妨碍立身建业,实是糊涂。”(26)陈独秀的话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婚恋自由”纯属生理要求,只能是一种男女间的“偶尔游戏”;二是“女性解放”不仅不关启蒙大局,并且还会“妨碍”男人的“立身建业”!就连陈独秀都持如此之看法,那么其他人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
男性启蒙者以“游戏”之姿态去倡导“女性解放”运动,除了为自己解决“生理要求”去制造借口,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思考什么女性问题。所以,“五四”时期“婚恋自由”的口号提出,不仅没有消除封建社会的思想毒瘤,相反还遮蔽性地延续了一些传统文化的陈腐恶习——比如新女性由“妾”变成“姨太太”,便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玩笑!众所周知,早在1913年,“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就明确规定,要“厉行一夫一妻制”,“置纳婢妾者不得为本会会员”(27),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政要都曾纷纷表态给予支持。“五四”思想启蒙时期,反对“纳妾”的社会呼声更是深入人心。有人做过统计,“五四”时期男女知识青年,其反对“纳妾”者极为普遍,人数也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28)。但是恰恰从此开始,打着反对封建婚姻的幌子,已婚男子争先“纳妾”,他们不仅理直气壮而且还毫无愧色。王邗华等人在《民国名人罗曼史》一书中,就曾讲过著名画家张大千的一个故事:某报纸载文说张大千有8个夫人,张听说后哈哈大笑连忙解释道:“要打对折!要打对折!”即使是打个对折,不还有4个之多吗?难怪当时就有人斥责说:“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无怪一干乡愚,要效而尤之,放辟邪侈,无所不为了。”(29)将新女性的社会身份定位为“妾”,这是民国时期法律工作者所提出的一种见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司法界人士就曾对“五四”以后嫁与已婚男子的那些女性,做出过态度明确的身份释义:“凡不依婚礼聘娶,不以法律手续,而与有妻的男子结婚的即为妾”(30);或“有妻而更与他之女子同居,而此与之同居之女子,谓之妾”(31)。不过,笔者个人更认同这样一种比较温和的辩证说法:“已有配偶之男子,隐瞒其配偶,或确知其配偶可不为刑法上之告诉,而与另一女子筑金屋以同居,在此情形下,虽不称为娶妾,而女方实处于妾的地位。”(32)如果我们按照此种解释去重新审视“婚恋自由”的社会现象,那么历来被人们所称道的爱情传奇,也只不过是些“金屋藏娇”的老套故事,不仅不值得去赞扬相反还应给予否定!像许广平、于立群、陆小曼、王映霞等新女性,她们牺牲自我去成就名人的伟业,这种不以“妾”之身份为耻的开放观念,完全是对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强烈反讽!因为任何一个新女性的婚姻幸福,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旧女性的婚姻痛苦,无论学界出于何种目的去加以辩解,“喜新厌旧”都是一种不道德的社会行为!
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相濡以沫的浪漫爱情,便是一个值得我们去重新斟酌的典型范例。鲁迅逝世三个月后,上海文化界同仁拟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大家都认为书中应有一份“鲁迅年谱”。当时决定民元以前由周作人来撰写,南京和北平部分则由许寿裳来撰写,上海部分当然是由许广平本人来撰写。许寿裳打算按历史事实去撰写鲁迅的婚姻状况。为了不得罪许广平本人,他事先写信给许打招呼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谅察。”他还说关于许的地位问题,“裳拟依照事实,直书为‘以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谅解。”故年谱这样写道: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结合,成为伴侣”。尽管许广平看了非常不舒服,但却一再表示“我决不会那么小气量”,她还干脆将年谱中的该项条目,径直地改写为“与许广平同居”(33)。笔者总觉得许广平这是在和男性赌气,因为新女性牺牲了自己成就了别人,可到头来连一个正式名分都没有,难怪她们对自己的付出会倍感不平。无独有偶,郁达夫也曾与王映霞爱得死去活来,可当王映霞移情别恋离家出走以后,郁达夫便一气之下找来笔墨,在她留下的白色纱衫上写下了这样12个大字:“下堂妾王氏改嫁之前遗留品”!这“下堂妾”虽然只是郁达夫的一时气话,却多少反映出了男性社会的真实心态,以及新女性沦落为“妾”的可悲现实。
中国女性作家对于新女性的“妾”之地位,自然是深信不疑且充满着怨恨之气;但是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里,她们也只能是对此发发“哀”而“怨”的牢骚而已。比如凌淑华的小说《转变》,就向读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徐宛珍在我记忆中真是个了不得的女子”,她曾是个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烈女子,也是个学习成绩门门优秀的好学生,她人格独立思想前卫凡事都走在前面,在作者眼里无疑就是一个新女性的完美偶像。可是当“我”多年以后再见到她时,她却穿戴华丽派头十足“俨然是一个主妇”,依偎在一个比她母亲还大两岁的男人怀里,做起了享受富贵荣华生活的“三姨太太”。对于“我”的诧异之情,宛珍十分坦然地告诉“我”——她经历过男性社会的求职歧视,经历过神圣爱情的谎言欺骗;她说与其去追求一个由男人编织的美丽神话,还不如嫁给一个有钱的已婚男人去做姨太太。她甚至还充满苦涩地自嘲说,“我从前常常骂女人是寄生虫,堕落种”,“现在若有人给我一千块钱叫我再骂一句,我都不忍心骂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宛珍的思想大变?用她自己本人的话来讲,男人永远也不会理解“女子在社会上是怎样的受罪”!
如果说凌淑华的《转变》,是通过徐宛珍的人格“堕落”去揭示新女性在现实压迫下的“务实”心理;那么梅娘的小说《鱼》,则是通过主人公“芬”的不幸遭遇,形象地表现了新女性“堕落”的真正原因:在那个充满着诗意的大学校园里,“芬”遇到了她的追求者林省民;他以十二分的真诚表白,重复地对“芬”说:“我爱你!”于是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并有了他们自己的爱情结晶。可是林省民却欺骗了“我”,他在家里早已有了妻子。此时“我”有了儿子辞了工作,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所以“我”只能“接受了林家的意见,归到林家去,安安分分地做林省民的二姨太太,好好地养着林家的承继人”。梅娘通过“芬”的悲剧故事,透露了这样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新女性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得到现代社会的人格尊重,她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遭遇与旧女性相比并无什么本质差异;相反,受现代思想启蒙影响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希望的破灭则更将加重她们精神上的痛苦。这一点梅娘与庐隐的思想认识应该说是完全相同并无分歧的。二是男性太了解女性对于婚姻的务实想法,因此他们往往以物资利益为前提,去诱惑已婚女性对自己的绝对臣服,一旦遭遇反抗便又以剥夺物资生活权利为借口,去对她们进行精神方面的巨大施压。而女性追于生计就不得不消解自我去苟且偷生,故新女性同样难以逃脱旧女性的悲剧命运。这无疑是梅娘本人内心世界的巨大悲哀。
徐宛珍成了“姨太太”,“芬”也成了“姨太太”,现代新女性的整体沉沦,究竟应是谁之过错呢?回答当然是男性社会。因为男性用他们的精神狂欢,造就了“女性解放”的社会假象;他们得到了女人也得到了荣誉,而女人则牺牲了肉体也失去了灵魂!所以女人只能去暗自哭泣,为了自己的幼稚而哭泣;因为她们从来就被男人视为是“玩偶”,“娜拉”只不过是一个由男性编织出来的美丽神话!
①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这样写道:“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鲁迅此言其实说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初期所冷遇的尴尬局面。
②[挪]丹尼尔·哈康逊、伊丽莎白·埃德:《易卜生在挪威和中国》,《易卜生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29页。
③沈雁冰:《谈谈〈玩偶之家〉》,《文学周报》第176期,1925年。
④胡适:《答T·F·C〈论译戏剧〉》,《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
⑤庐隐:《“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钱虹编:《庐隐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⑥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0页。
⑦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
⑧亚特:《论铸造国民母》,《女子世界》第7期,1907年。
⑨毛伊若:《读“新恋爱道”后》,《新女友》第3卷第12号,1928年。
⑩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
(11)鲁迅:《我之节烈观》,《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
(12)转引自2010年3月6日《文汇报》刊载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们》一文。
(13)[美]卡伦·霍妮:《女性心理学》,许科、王怀勇译,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14)茅盾:《解放与恋爱》,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29日副刊《妇女评论》。
(15)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8页。
(16)黄亚中:《恋爱的悲剧》,《妇女杂志》第9卷第12号,1923年。
(17)刘维坤:《黄女士的自述》,《妇女杂志》第10卷第2号,1924年。
(18)《关于马汪事件》,《新女性》第3卷第4号,1928年。
(19)《自由女控父母阻止真爱情》,《申报》1927年9月21日。
(20)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第45页。
(21)可参见拙文《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对此问题的论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
(22)[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23)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第187页。
(24)[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第142页。
(25)陈学昭:《时代妇女》,上海:女子书店,1932年,第4页。
(26)沈寂等编:《陈独秀:人生哲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27)《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暂行草章》,《北京档案》1986年第2期。
(28)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第320页。
(29)音奇:《我所希望于男子》,《妇女杂志》第10卷第10号,1924年。
(30)关瑞梧:《妾制研究》,《社会学界》第6卷,1932年。
(31)胡长清:《中国民法亲属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页。
(32)陈文浩:《同居关系之法律观》,《法律评论》总第762-763期合刊,1948年。
(33)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第3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