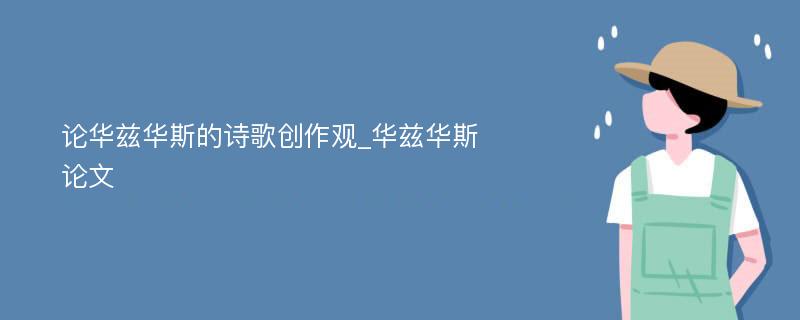
论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兹华斯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华兹华斯处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交,是英国文论史上的一位过渡性人物。他的创作观与传统诗歌理论既是相异的又是相属的。他虽然攻击古典主义,但是并非一切推倒重来;他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摹仿论,然后把其对象局限为乡村,赋予它特定的社会意义;他继承了18世纪的情感说,然后将其与理性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创作论;他反对僵死的“诗意辞藻”,倡导使用日常语言进行诗歌创作;他扩展了前人的实用说,提出了以友爱为核心的文学社会功能观。
【关键词】 华兹华斯 浪漫主义 诗歌创作观 自然 理性 情感 语言
威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再版前言》(以下简称《前言》)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的美学宣言,英国近代诗歌理论的开端。在《前言》中,华兹华斯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诗歌创作观,除此之外,他的诗歌创作观还散见于与友人的通讯往来、谈话记录以及部分诗作之中。本文首先论述华兹华斯的基本文学概念,然后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他的诗歌创作观。
一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789)首版中说,该集子中的诗歌具实验性质,其目的是为了探索用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日常交际所用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可行性。在1800年的《前言》中,他称集子中的作品为优秀诗歌的典范。《前言》的核心问题是诗歌应该表现什么样的题材和主题,创作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语言。
新古典主义的诗歌理论对诗歌和戏剧进行等级划分,认为史诗和悲剧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喜剧、讽剌诗、田园诗,短小的抒情诗居于最低的地位。而且,诗歌(包括戏剧)使用的语言必须遵循所谓的“相称得体原则”(decorum),即, 题材(特别是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一定要按照其在诗歌等级中的高低贵贱,以“恰如其分”的词令、韵律、形式和音调来表达。针对这种情况,华兹华斯在《前言》中首先谈到了题材问题。华兹华斯认为,诗人在创作时应该:
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景物,尽量自始至终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景物上加上某种想象的色彩,使日常的东西以不平常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心灵面前;而且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事件和景物中真实地而非虚浮地探索我们的天性的根本规律;主要是关于我们在心情振奋的时候如何把各个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样就使这些事件和景物显得富有趣味。〔1〕
这里的“日常生活”不包括都市生活,而是“微贱的田园生活”。在华兹华斯看来,城市文明是一个没有活力的精神世界。正如他在《伦敦》一诗中所说,那里“象一潭死水”,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人们没有自由,没有权力;“古老英国内蕴的快乐”荡然无存,道德败坏,人欲横流。而且,城市生活使人们心灵的“分辨能力迟钝起来,使人们的头脑不能自如运用,蜕化到野蛮人的麻木状态”(第161页)。显然, 他的这些论述具有深刻的预见性:工业文明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面对初露端倪的现代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诗歌已经受到了“人的总体异化”的全面威胁。当然,华兹华斯并未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从本质上“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对立”。〔2〕但是他察觉到了其弊端之一:大众传播媒体和大众文化可能损害人们的辨别能力,使人蜕化变质,陷入麻木状态。
与此相对的是“田园生活”。在那里,人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因此能让我们更确切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美的永久形式合为一体的”;关键的一点还在于那里的人们“使用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那样的“语言产生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比诗人常常用来代替它的辞藻更能持久,更具有哲学意味”(第159页)。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华兹华斯的“乡村情结”。其一,对自然的崇拜和当时流行的泛神论有密切联系。在华兹华斯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眼里,自然被看作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回到自然实际上要突出人与自然之间在感情上的共鸣,使景物拟人化,使其成为精神上的某种象征。其二,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象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一样,华兹华斯面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恐惧心理。在他眼里,城市代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的种种负面因素,代表了新古典主义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原则。那些东西严重地压抑了人的灵性,使人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痛苦和忧郁。而人们又无法回到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之前的中古时期,于是,还未受到城市化冲击的乡村便成了他心目中的伊甸园。其三,坎坷的个人生活的影响。华兹华斯童年时期家境困顿,其母亲去世后,他被送进霍克斯黑德的寄宿学校,那里乡间的湖光山水熏陶了他热爱自然的情感。另外,他在法国之行中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和情绪变化,也寄希望于大自然来恢复心境的平静。以上诸多原因促使他在1795年迁居乡村,实现了接近大自然,探讨人生的夙愿。
在华兹华斯看来,热爱大自然就是热爱人类自身。我们知道,华兹华斯是英国文学史上成功地表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诗人。在他的眼里,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源泉,而且还提供了人类发展和壮大的原则。人与自然是相互适应的,人的心灵天生就是自然中最美好、最有趣的东西。华兹华斯的大多数诗作都推崇一种和谐之美——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尤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共存。据说,在第一次旅居法国期间,有一件事情给华兹华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见一个饥肠辘辘的法国小女孩一边放牛,一边编织衣物。这时一位法国共和军军官对他说“我们反对的就这是这个。”第一次法国之行使他确立了“自然中最可贵的是人”的思想。〔3〕在《丁登寺旁》、 《序曲》等著名诗作中都可看到这一点。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不同的是,华兹华斯对包括作为个人的人性和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性持有独到的见解。对他来说,提倡回归自然就是要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关系。在他的诗歌里,乡村与其说是一个具体场所,不如说是一种文本意义的符号。它隐喻了一种和谐的群体,是抵抗与其相异的种种偏重理性力量的堡垒,与他心目中的“自然”同一的。
二
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该采用日常生活中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
首先,这是由题材所决定的。要表现微贱的田园生活,诗人就必须使用那里的“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第159页)。他认为, “朴素的语言”(rustic speech)有力、真切、自然,“富有哲学意味”, 是语言中的精华。这样,华兹华斯实际上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信条,即,诗歌的语言必须有它专用的辞藻和修饰手法,以便使其高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华兹华斯反对的是狭义的“诗意辞藻”(poetic diction),即“相称得体原则”指导下的陈规陋习。它包括:新古典主义常用的某些修饰手法(如拟人、迂回说法、拉丁词汇等)、句法结构(如倒装、对仗等)和罗列式的搭配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华兹华斯本人所用“朴素语言”(rustic speech)这一概念前后并非完全一致。他在1802年的《〈抒情歌谣集〉再版补遗》、1815年的《〈抒情歌谣集〉再版前言》和《补充说明》以及与友人的通信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在第一篇《再版前言》中,“朴素语言”指的是他当时所居住的湖畔乡村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之相对的是伦敦方言,他是从社会阶层来区分的。在1807年给友人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为什么要用“朴素语言”来写作,并且认为,伟大的诗作往往最初不被人们所接受,伟大的诗人应该培养读者的欣赏能力。“每一位伟大的、有创造性的诗人……都得培养读者对自己作品的鉴赏情趣,都得向他们传授如何解读他们作品的方法。”〔4〕在那里“朴素语言”指的是那些认同他的诗作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之相对的是持不同意见的读者群所使用的语言。
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观还有一层更为重大的理论意义。我们知道,在18世纪末,英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怎样对待蓬勃兴起的自然科学。不少人相信泛科学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实验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衡量,只有可以量度的东西才是客观的,只有客观的才是真实的。面对这种挑战,新古典主义作家们似乎显得软弱无力,陷入了概念论(conceptualism)的泥潭, 把诗歌变成了经过语言修饰的概念性陈述,使之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经得起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与之相反,华兹华斯采用让诗歌无限自我扩张的办法来为诗歌辩解。他认为,诗人和自然科学家一样,也是对自然进行探索。前者观照的是“普遍的自然”,而后者研究的是“自然的特定部分”。诗是“一切知识的精髓”,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象人的心灵一样永存不朽。”接着,他的话锋一转:
任何对诗歌抱有我所要表达的崇高概念的人,都不会采用空幻的、非本质的修饰品(transitory and accidental ornaments)来损害他所描绘的东西的神圣性和真实性,都不会用人为的技巧来博得读者的赞美;显然,只有自认为题材卑下的诗人才不得不依靠那些修饰品。(第167页)
华兹华斯认为微贱的田园生活是诗歌创作最高尚的题材,普通人使用的语言是最富于表现力的诗歌语言。既然如此,所谓的“诗用辞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被抛弃的对象了。我们知道,文学这种文化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异性:作为一种艺术,它有别于其它艺术;作为语言,它有别于其它话语;作为与现实环境相关的活动,它有别于其它实践活动。“科学话语”和“哲学话语”都是以表达抽象概念为主的;华兹华斯在这里以它们为对立面,为“文学话语”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还应指出的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界定诗歌在那时是颇有创见性的。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观点相似,华兹华斯的见解最终导致这样一个结论:科学是事实性陈述,诗歌是情感性表达。现在看来,那种观点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是,后来的“客观说”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加以开拓发展,绕过作家的心理活动这个他们不感兴趣的问题,从语言使用的方式上来说明文学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区别的。这样,诗歌所包含的就不仅仅是浪漫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的情感了。
其次,华兹华斯认为这是诗歌创作本身的要求。诗人“只要能够选择恰当的题材,在适当的时候自然就会有热情;而由热情产生的语言,只要选择得正确和恰当,也必然高贵而且丰富多彩”。当然,华兹华斯并不是鼓吹对语言进行自然主义的复制。诗人还得“从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里进行选择。”对华兹华斯来说,选择的过程是颇费功夫的。他告诉侄子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人在诗歌的语言风格方面用了大量功夫,不逊于同时代任何一位诗人。本人对诗歌的热爱不逊于任何人,因此我是怀着崇敬、充满激情、兢兢业业进行创作的。就语言风格而言,本人主要致力于使用纯正易懂的英语进行诗歌创作。〔5〕
这里的“纯正”(pure)和前面所说的“朴素”(rustic)表示同样的意义,指的是“语言中的精华”。这也说明为什么读者在欣赏华兹华斯的诗歌时,常常为其语言的优美和流畅所陶醉。在华兹华斯的佳作中,他对语言的把握真的做到了“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几乎进入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为什么需要选择呢?我们知道,华兹华斯关于诗歌语言的观点基于他对诗歌的全新定义:“诗是强烈感情的自发流露,它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第168页)。 这里的“自发流露”出现在创作过程之中,而创作过程自身却受到诗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技巧的影响。华兹华斯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诗人接触的语言“在生动性和真实性上比不过实际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实际生活中的人真实地体会情感,而诗人只是在自己的内心创造或自以为创造了那些情感的影子。”因此,在对那些情感进行描述和模仿时,诗人从总体上讲处于一种“服从”地位,免不了带有“机械性”。华兹华斯接着解释说:
诗人希望使自己的情感接近对象的情感,进而让自己暂时进入一种幻想状态,甚至让自己的情感与他们的混为一体,与他们的产生认同;只是考虑到描述那些情感的特定目的是为了使人感到愉快,他才对他们的语言稍加改动……通过选择,除去情感中令人痛苦和不快的东西;他觉得不必去粉饰或拔高自然。他越是努力实行这个原则,他就会越发相信,在他的幻想或想象中出现的文字是根本不能与出自现实和真理的语言相比的。(第165页)显然,华兹华斯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语言在表达情感和情绪时的局限性。新古典主义倡导使用精确的语言,其用意在于说明诗歌的意象和修辞缺乏准确性;华兹华斯在此承认创作过程中语言对诗人的局限,但是希望通过选择语言来尽可能完整地表达情感。他相信,建立在兴趣和情感基础之上的这种选择可以形成一种最初想象不到的特点,并且使诗歌完全避免日常生活的庸俗和鄙陋。
三
除了题材和语言外,诗歌创作还涉及其它一些因素。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一种艺术。作为艺术创作者,诗人首先需要问答的问题是:诗歌创作中的审美本质是什么?
华兹华斯认为,情感是诗人的“靠山和支柱”,贯穿于整个诗歌创作过程之中。诗人的“热情产生语言”(第165页), “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为什么如此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尤其是1660年至1750年那一阶段)崇尚理性、崇尚科学的风气使人们普遍对情感产生怀疑,把情感同清教主义以及其它形式的极端主义相联系。华兹华斯的可贵之处是把情感同语言联系起来,从创作的角度阐明情感的重要性,以反拨偏重理性、抑制情感的新古典主义诗风。严格地说来,他既不属于感性派也不属于理性派,前者将美与艺术的本质归结为感性快感,后者将美与艺术的本质归结为先天理性。在华兹华斯那里,诗歌创作是一种审美愉快,它既涉及对象的形象又涉及主体的愉快,因而是客体与主体、感性与理性、真与善之间的过渡和桥梁。华兹华斯认为,直接给人愉快是诗歌创作的要旨,“诗人在创作时只有一个限制,那就是必须直接给人愉快。”这是因为“只有愉快激发起来的东西才引起我们的同情……没有任何知识(即任何一般原理)是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思考而得出来的;知识从愉快之中而来,并且只有凭借愉快才存在于我们心中”(第166页)。 出现在创作中的这种愉快是主体因不受对象的感性存在和理性概念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所引起的一种情感愉悦,其基础是主观上的各种心理功能的协调一致。
第二个问题是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华兹华斯谈到了对自然美的欣赏情趣,认为“对自然景物的任何合理而实在的愉悦都取决于两个基础——上帝和人。”他在信中结尾处说:
简言之,如果让我就对自然美的欣赏情趣这一题目撰写文章……我要说的一切将会从人的心中开始,在人的心中结束;在神圣的大自然的引导之下,人们赋予观察到的(自然)景物以价值,并且指出它们包含了哪些宝贵的东西。〔6〕
华兹华斯的这段话的核心问题是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审美特点,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他所说的“合理而实在的愉悦”指的就是审美观念:它包含了无限的理性内容,因而是“合理的”;它同时又是一个具体的现象,所以是“实在的”。一般地说来,理性观念需要借助于概念来表达,但审美观念却不经过概念,仅借助于一表象将无比丰富的理性观念直接显现出来。换言之,艺术美是无限的理性内容与有限的感性形象的自由统一,具有寓无限于有限的特征。再则,华兹华斯实际上说明,自然美是客观存在的,而艺术美是诗人创造的,自然美是艺术美的基础。这就是说,自然美只是事物本身美,而艺术美则是对事物所作的形象描绘;诗人通过审美(创作)过程变自然美为艺术美。
第三问题是理性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上面的引文告诉我们,华兹华斯对理性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人们赋予观察到的(自然)景物以价值,并且指出它们包含了哪些宝贵的东西。”换言之,诗歌的形象描绘中已经包含了诗人的理性观念;诗人对景物作了某些程度的理性改造,诗歌作为艺术美必然包含理性。华兹华斯在一次通信中谈到了诗歌创作中理性与愉悦的关系。他说,“本人总是十分满意地看到,自己所提供的愉悦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7〕在《前言》中, 他也强调“诗歌所追求的不是个别的或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和具有操作性的真理”(第165页)。 这和约翰生关于诗歌应该表现“真理的稳固性”有异曲同工之妙。〔8〕当然,对华兹华斯来说, 理性总是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是诗人的支柱”。创作过程中的认知是特殊的,它不凭借概念而只是凭借形象。这就使其带有直观的无意识的性质,是一种形象的感染、情绪的启迪。诗歌创作过程中的认识本质上不是概念所表达的认识,其逻辑不是外在的逻辑,而是一种形象所唤起的认识和内在的情感逻辑。虽然作品中含有理性,含有概念,但是显露在读者面前的只是同生活面目一样的形象,即自然之中的形象。艺术魅力是理性与形象、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由此可见,华兹华斯实际上并未抛弃理性,而是将其同情感、头脑和心灵重新加以综合。
最后一个问题是任何诗歌创作观都无法回避的,即对诗人的想象力的认识。在《前言》中,华兹华斯虽然提到诗歌应该使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景具有“想象力的色彩”,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阐述其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在同其侄子克里托弗·华兹华斯的一次谈话中,华兹华斯说:
想象力是主观的,它所处理的不是现实中的事物,而是那些事物在诗人心灵的形象……想象力是智力的透镜(intellectual lens), 诗人通过它来审视自己观察到的事物,其时那些事物的形状和色彩都产生了变化;想象力是一位有创造力的舞台造型师,剧中人物通过他着上新装或做出新的造型;想象力是一种化学功能,不同性质和种类元素的通过它混合(are blended together)成和谐而相似的整体。〔9〕
这里的想象力有三层意思:1)作为智力的透镜, 它是人的心智对现实世界的纯粹主观性把握,即心智进行回忆以及对形象进行组合的功能;2)作为灵感,它不受人的意识(甚至人的心灵)控制;3)以上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兼有它们的某些特征,并且需要它们进行合作,共同起作用。华兹华斯对想象力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显然不及柯勒律治,后者用想象力这一概念来代替具有约翰生色彩的“理智”。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里的论述近一步强调了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诗歌创作真正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同一部著作的第22章中充分肯定了华兹华斯的创作才能,声称华兹华斯对想象力的运用是近代作家里最接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一人。
四
在《前言》中,华兹华斯是这样描述诗歌创作过程的:
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在这种情感中沉思,直到一种反应使原来的平静逐渐消失;然后,一种与先前类似的情感便逐渐产生出来,并且存在于诗人的内心里。成功的创作一般都是这样开始,并且以类似的方式继续下去的。(第168页)
按照先后次序,这里有几种不同的情感:首先是诗人面对自然景物时的情感,其次是“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再次是作为沉思对象的情感,接着是与沉思开始之前“类似的情感”,最后才是诗,即“强烈的感情”。在华兹华斯看来,诗歌创作如同一种情感的化学变化;在这个过程之中,诗人“总是带着愉快”回忆和沉思,而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是情感。
对华兹华斯来说,诗歌不是当场的即兴之作,它所表达的强烈情感是经过冷却和深化以后才入诗的。他认为回忆和联想在创作活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离开了这个环节,诗歌就会变成对情感所作的自然主义记录。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创作的要旨是“我们在心情振奋的时候如何把各个观念联系起来”(第159页)。 而且,由于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回忆和联想的常常是大自然中的美好景物,他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净化。
华兹华斯关于创作中心理活动的观点受到了大卫·哈特立(David Hartley)的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在1749年问世的《对人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Man)一书中, 哈特立提出了“身心功能一致”说。他继承和发展了洛克在《人类理解》中阐述的联想概念,试图说明最复杂的心理过程(表象、记忆、推理)可被分解成基本感觉印象的集合或系列,而所有的心理活动最终可以用单一的联想律来解释。哈特立认为,五官感觉是心理活动的基础。它们与快乐和痛苦的概念相联系,形成某种结构;那种结构经过适当的培养,可以转化为道德规范,使人区分善恶。华兹华斯根据这种观点来解释早年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例如,《序曲》中有一个片段就表现了孩提时期大自然的影响是怎样在他的身上产生作用的。〔10〕
在华兹华斯看来,婴孩刚刚记事的时期是一个“时间之点”(spot of time),这类时间之点使人得到大自然的陶冶和教育;而且,时间之点具有更新能力,使人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纯洁,达到更高的境界。自然给予世间万物以生命,给人以情感;观照自然界中美好的事物可以“净化人的情感和思想”,使人领悟到“自己内心里的崇高和伟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式的“情感净化”发生在观众身上,那么华兹华斯式的诗歌创作可被视为诗人情感的自我净化过程,一个将积蓄在内心的情感幻化为艺术作品的过程。对华兹华斯来说,这个过程中充满愉快的。他在著名的《丁登寺旁》中写到:
These beauteous forms,
Through a long absence,have not been to me
As is a landscape to a blind man's eye:
But oft,in lonely rooms,and 'mid the din
Of towns and cities,I have owed to them,
In hours of weariness,sensations sweet,
Felt in the blood,and felt in the heart;
And passing even into my purer mind,
With tranquil restoration:- -feelings too
Of unremembered pleasure:such,perhaps,
As have no slight or trivial influence
On that best portion of a good man's life
His little,nameless,unremembered,acts
Of kindness and of love.Nor less,I trust,
To them I may have owed another gift,
Of aspect more sublime;that blessed mood,
In which the burthen of mystery,
In which the the heavy and weary weight,
Of all this unintelligible world,
Is lightened:- -that serene and blessed mood,
In which the affections gently lead us on,- -
Until,the breath of this corporeal frame
And even the motion of our human blood
Almost suspended,we are laid asleep
In body,and become a living soul:
While with an eye made quiet by the power
Of harmony ,and the deep power of joy,
We see into the life of things.〔11〕
柯勒律治擅长这种五音步抑扬格无韵诗,并将其称为对话体诗歌(conversation poem)。 这种诗体以与人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诗人对某一事物或者主题的思考,其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向内转”的倾向,诗人的观照重点不在山情野趣,而是自己的内心世界。
促成这一转换的原因之一是康德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康德采用使客观统一于主观的方法来克服对主体和客体的划分。按照他的观点,心灵活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从我们以时空形式进行思维和观察这一点来讲,时空是主观的;从任何人都无法取掉时空眼镜这一点来讲,时空又是客观的。诚然,世界上的事物是独立于人们的客观存在,但是人们却不能直接地认识它们。人们利用时空形式和各种理解的范畴,按照各自的心理特质,从感觉中建构客观世界。
对华兹华斯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来说,康德的这一观点有两个重要提示:第一,主观至少可以帮助构成自然;其二,文学作品无疑是作家心灵的创造物。如果主观建构客观世界,那么,心灵的创造力就自然而然地优于对客观世界的摹仿或再现力。重要的不是如何摹仿自然,而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感受。于是,诗歌创作活动就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摹仿现实就是表现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样一来,诗歌就变成了“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丁灯寺旁》形象地再现了他创作诗歌的过程。在这个片断里,诗人“沉思”的对象是崇高;但是,这种崇高不是自然界的具体事物,而是沁入内心的一种情感。从感受到回味的过程就是从现实世界进入诗的境界的过程。这时的形象所依据的是大自然所提供的素材,其外在形式保持事物在大自然中的本来面目,看上去似乎同自然的事物一样地无目的,无理性。但是,在实质上它们却是经过理性改造的东西,渗透着理性内容,因而具有某种超越自然的魅力。由于这种心灵妙悟是一种内心的经历,所以诗人无法将其完全具体化;加之这种内心经历具有原始意味,其本质上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概念,所以诗人也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它。
仔细分析这首诗的英语全文我们不难看出,华兹华斯没有采用18世纪流行的英雄双韵体,没有采用传统的行、句合一法,而是让语句跨行排列。例如,引文中的第一句跨了14行,第二句长达15行。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诗人不断探索的过程,这种跨行行文给人一种动感,画出了诗人心灵运动的轨迹。显然,华兹华斯在这里主要关心的不是诗体的形式,而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怎样表达当时的思绪。尽管诗句的结构颇为复杂,但仍旧好象没有把诗人的感受“说清楚”。这是因为诗人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感受,那是“从血里心里感到”的。在诗歌创作的认知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是融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很难有主次之分。这时,外界对诗人心灵的抗拒已经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结果是诗人“领悟到万物的生命”。在此,语言本身就是克服外界对心灵进行抗拒的一种手段;要完全表达自己的感受,诗人就得使语言变得完美无缺。显然,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尽可能简单明了的语言。
五
华兹华斯的主张与传统诗歌理论既是相异的又是相属的。现有的研究往往强调他的文学主张对英国新古典主义进行反拨的一面,忽视了与其互相交织和渗透,对其进行发展和张扬的一面。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之一是传统的文学史对这一时期的划分的影响。一般认为,英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时期始于1660的光荣革命,包括复辟时期(1660—1700)、奥古斯都时期(1700—1750)和约翰生时期(1750—1798),止于《抒情歌谣集》发表的1798年。其实,对文学史各个阶段的划分往往是粗略的,带有很大的人为性。处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交那样的文化氛围,华兹华斯的思想必然带有上一个时代的某些特征。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与传统诗歌理论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18世纪下半叶反理性主义文学思潮的继承和发展。纵观英国文学史我们发现,1700—1750这一阶段是新古典主义的鼎盛时期。那时,法国作家布瓦洛在《诗艺》集中论述的古典主义的原则已经得以实现,各种文学作品的体裁分类已经确立,文学语言基本定型。在文学创作方面,薄柏的作品集中地体现了古典主义的诗风;艾迪森的古典悲剧、西柏和斯蒂尔等人的喜剧代表了新古典主义在戏剧方面的最高成就;斯威夫特、菲尔丁和笛福的创作标志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巅峰。
随之而来的约翰生时期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新古典主义由盛而衰,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当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生仍旧极力实践古典主义,在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辞典编撰等方面均有建树。但是,发展较早的德国浪漫主义已经传到了英国,要求个性解放,强调创作自由,反对传统束缚的浪漫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逐渐增强。英国作家的兴趣开始转向自然,转向乡村生活,转向其它具有原始美的东西。例如,这一阶段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彭斯充分体现了其过渡特点。彭斯继承和发扬民间传统,既拥有幻想,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擅长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不平凡的东西。他以民歌为本,用苏格兰方言创作,其纯朴的农村题材和清新的风格表达了崭新的自由平等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诗扎《致拉布雷克书》中针对当时新古典主义诗歌注重文雅、讲究节制的风气,提出了诗的灵感来自大自然、诗的价值在于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的浪漫主义观点。尽管其他一些作家(如爱德华·扬格)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从题材和诗歌语言两个方面上考虑,彭斯的创作思想堪称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的先导。
第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著名哲学家洛克早在《论人的理解力》中就提出了“物质世界是感觉的源泉,环境创造人”的观点。在18世纪初,贝克莱提出“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我论命题,进一步强调了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后来,修谟把经验主义推向了极端,提出了“不可知论”,将人类认识的主观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且,修谟认为情感是原始的事实或存在,本身圆满自足,因此,它们就不可能被断定为真的或伪的,违反理性或符合于理性的。这样一来,修谟实际上否定了自从古希借以来人们所信奉的哲学思想,指责了用理性指导情感、压抑情感的谬误。
在这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作家关注的重心从客观世界转向了自己的主观感觉。由于物质世界存在与否,客观标准存在与否不再居于中心地位,重要的便是作家自我对外在世界的感觉如何了。因此,文学创作有意识地向内转,作家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其次,创作思想从理性的道德说教转向张扬个体特性、崇尚情感真实的唯情主义。既然情感是自然生命的表现,内心体验真实可靠,原始的情感能够表现世界的真谛,那么,作家就应该倡导归返自然,倡导表现人的心灵感受和情感。再次,创作题材从现在转向过去,从城市转向乡村。如果人们只能通过感性经验来认识世界,而每个人的经验又是十分有限的,那么感知以外的东西是无法认识的。面对杂乱的现实世界,作家陷入茫然,于是只有通过怀古,通过歌颂尚未失去天真与稚朴的田园生活来抒发自己无尽的感慨和哀伤。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反理性主义诗歌和小说充分反应了这种倾向,前者如汤姆逊的《四季》、后者如歌尔斯密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传记》以及理查孙的书信体小说等等。
第三,华兹华斯的一些基本文学概念仍旧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谈到,例如,他的“诗歌所追求的不是个别的或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和具有操作性的真理”的观点,他的“永恒的自然,世间万物变化的伟大灵魂”的观点。除此之外,华兹华斯还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人文思想,重申了其主要的价值观(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各种生命表现形式的崇敬,崇尚表现生命力量的快乐原则等等),而且还涉及了启蒙运动中广泛讨论过其它的问题(如,理智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人类的共同属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等)。
注释:
〔1〕William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with Pastoral and Other Poems"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6),p.159.以下括号内的页码如无特殊说明也指同一文集。
〔2〕《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第106页。
〔3〕James Stephen et al.ed.,English Romantic Poets( New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35),P.2.
〔4〕参见《致博蒙特男爵夫人》,同上,第117至118页。
〔5〕参见《与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的谈话片断》, 同上, 第139页。
〔6〕参见《致乔治·博蒙特男爵》,同上,第124页。
〔7〕参见《致伯纳德·巴顿》,同上,第119页。
〔8〕约翰生:《〈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见《西方文论选》(上卷),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527页。
〔9〕参见《与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的谈话片断》,同注3, 第140页。
〔10〕William Wordsworth,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 & COMMPANY,1986).pp.238—239.
〔11〕William Wordsworth,"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6).pp.151—152.
〔12〕参见《致约翰·威尔逊》,同注3,第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