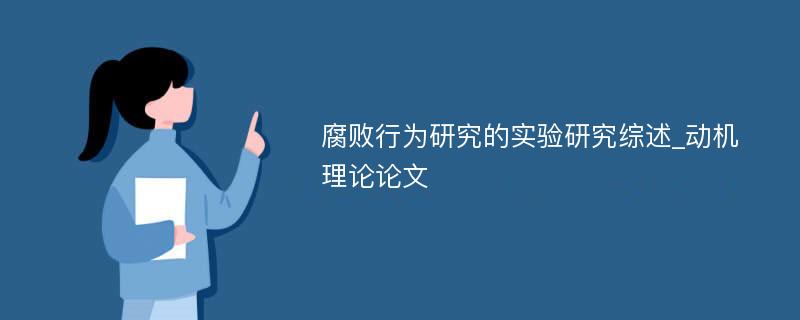
腐败行为研究的实验进路:一个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对腐败表现出持续的研究兴趣(见如Rose-Ackerman,2006)。腐败,在经济学中最常被定义为利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官员作为理性自利的行动者,拥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利益诉求,且其利益常常与公共利益相违背(Serra,2009)。 经济学家关注腐败是因为腐败会对效率和公平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虽然有研究认为腐败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商业发展(Kaufmann & Wei,1999;González et al.,2002),但更多的经验证据表明,它对私人投资和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以及公共支出配置等都有很强的负面影响(Mauro,1995;Bardhan,1997;Gupta et al.,2002;Reinikka & Svensson,2004;吴一平和芮萌,2010;刘勇政和冯海波,2011),也因此被看成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World Bank,2008)。为求识别出可以抑制腐败的机制策略,诸多学者致力于从理论上和经验上探究腐败形成的原因和决定因素。 理论上,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常常依托委托—代理模型,假定理性的行动者会在比较预期收益和成本后做出决策(Becker & Stigler,1974;Bardhan,1997)。沿着这一思路,后续研究试图寻找影响作为代理人的官员的机会成本的激励机制来抑制腐败(Becker,1968;Becker & Stigler,1974;Klitgaard,1991)。在此基础上,制度经济学者强调了利用腐败交易的不稳定性来进行反腐机制的设计,提出引入竞争和告密、提高透明度、增加公民参与等制度安排的重要性(Shleifer & Vishny,1993;Rose-Ackerman,1999;Kaufmann et al.,2002)。国内学者也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如盛宇明(2000)和郑利平(2001)。 经验上,由于腐败行为的非法性和隐蔽性,学者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依赖于调查获得的主观数据(如国际透明度指数)和已经发生的客观数据(如腐败犯罪率)来识别腐败的决定因素,检验常见的反腐机制的效果。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法律健全度和宗教信仰传统、英美法传统和民主历史长短、分权程度、新闻自由度都会影响到腐败程度(Ades & Di Tella,1999;Laffont & Guessan,1999;La Porta et al.,1999;Treisman,2000;Fisman & Gatti,2002;Brunetti & Weder,2003),而高薪养廉与监督制裁都是有效的(Van Rijckeghem & Weder,2001;Rauch & Evans,2000)。沿着类似路径,国内一些学者也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规模和教育水平对我国不同区域腐败水平的影响(刘文革等,2003;孙刚等,2005;周黎安、陶婧,2009)。 总体上,虽然有关腐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过去的20年间迅速增加,并且也识别出许多会显著影响到腐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变量(Triesman,2000的综述),然而,这种研究的进路存在着诸多明显的缺陷。一方面,传统的理论研究一直建立在“似真”(弗里德曼,2007)的行为假设基础上,缺乏扎实的“基于实践”的微观实证基础(西蒙,2009),使其在解释预测和实践启发上的功能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典型的一个问题是,仅以经济人模型来解释腐败是否足够?这种思路是否忽视了腐败背后可能存在的其他深层次动机,如负罪感?而如果类似负罪感的情感动机确实存在并可以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建基于自利模型而导出的机制设计可能就会出现另一种意义上的激励不兼容,比如,导致惩罚威慑的过度(布坎南,2009)。再比如,设定的发现概率就是个体将感知到的发现概率吗?个体对于被发现的概率上升的反应与其对惩罚严厉程度上升的反应是否一致?而来自行为经济学关于启发式决策的大量证据已经挑战了这些传统的假设(Kahneman & Tversky,1982)。因此,对于腐败,我们还需要有更精致的动机或者认知层面的研究,考虑不同激励系统的交互作用。 另一方面,因为主要依赖于跨国数据和主观感知数据,已有的经验研究首先均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衡量误差问题。比如,在使用跨文化调查获得的主观数据研究腐败时,潜在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不同文化中的行为主体对于腐败的定义是一致的。然而,已有的关于公平感的跨文化研究(Henrich et al.,2001;Ottone et al.,2008)或者送礼是不是一种腐败(Lambsdorff & Frank,2010)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与此同时,已有研究的结论常常不一致(Rose-Ackerman,2004)。这可能或者是因为在研究中应用了不同的条件组、解释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及遗漏变量问题(Serra,2006),或者是因为某些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水平等是内生的,从而导致最终的检验都只能是对混合了环境、制度、经济人行为理论假设而进行的检验(罗卫东、范良聪,2010)。最后,由于已有研究大都基于跨国宏观层面数据完成,关注的是文化、宗教等变量,因此其对于国内层面上针对个体而完成的反腐机制设计到底有多少借鉴意义也是不清楚的。 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这些缺陷将影响到这些研究应用时的有效性。正是有鉴于此,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受控实验来研究腐败行为。由于可控可重复,实验方法可以通过模仿腐败决策发生的环境,使得研究者直接在个体水平上观察腐败行为,从而为研究者带来有针对性的、纯粹的、可分的数据,帮助研究者识别微观层次上有关“信念、预期和计算的过程”(西蒙,2009),更有效地检验理论成立或者失败的条件,发现腐败行为的“真实”规则。事实上,借助于受控的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已有研究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从第一个腐败实验研究出现至今不过十多年,但是实验室实验已经在腐败的影响因素识别、腐败决策的动机分析和反腐机制的比较检验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关于腐败行为的理解。 正是鉴于腐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当前我国关于反腐工作的迫切性,本文尝试对以往有关腐败的实验研究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为实验研究在该领域中发挥作用铺路。本文的思路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引介经典的腐败实验框架;第三部分介绍已有研究识别出的影响腐败微观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第四部分深入动机层次,在区分腐败行为决策的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基础上,探讨不同反腐机制作用的机理原因;最后展望实验手段可能在未来腐败研究中的作用方向。 二、典型的实验框架 Frank & Schulze(2000)完成了第一个介于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之间的腐败实验。他们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个体决策环境:实验在电影院中进行,被试是电影俱乐部的会员。在电影开始前,学生们被告知,俱乐部有一笔钱掉进了排水管道,需要雇用管道服务公司将钱取出。作为会员,他们需要代表俱乐部在十个向俱乐部报价的管道公司中选择一个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些公司的报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服务费,另一部分是这家公司给决策者的回扣。电影结束后,组织者将随机抽取一个公司获得合同,幸运的决策者将获得相应的报酬。在该框架中,被试需要在个体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最大化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捕获了腐败的本质特征——将公共权力用于私人目的。这以后,研究腐败的文章日趋增加,学者们也发展出了一些比较经典并被后续学者沿用的实验框架。 (一)贿赂实验 实验经济学家关注最多的腐败类型是贿赂。Abbink et al.(2002)设计了一个基于信任博弈的序贯博弈框架,用于描述贿赂的情境。该博弈有两个参与人,先行动的参与人代表潜在的行贿者,后行动的参与人代表公共官员。第一阶段,先行动者决定是否向后行动者转移禀赋以及转移多少禀赋,以求引致一个有利于他的决策;如果他选择不转移,则博弈结束;如果选择转移,则无论后行动者是否接受,他都要付出一笔“转移费”,这个费用代表了行贿者与官员建立互惠关系的一个初始成本。第二阶段,后行动者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先行动者转移的禀赋,如果他选择拒绝,则博弈结束;如果选择接受,则后行动者将获得一笔报酬,这笔报酬的额度是先行动者转移的禀赋的3倍。①而后,后行动者需要在一个稍微有利于自己的选项X和另一个大大有利于先行动者的选项Y中做出一个选择。 这是第一个研究贿赂行为的实验框架。此后直到Barr & Serra(2009)提出新的实验框架之前,大部分贿赂实验都是基于这个框架完成的。这个框架很好地捕获了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互惠关系,但是却忽视了腐败行为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即腐败往往会带来负的外部性。为了捕获这种负的外部性,Abbink et al.(2002)在另一组实验中引入了一个第三方,以模拟社会公众。当第二行动者选择Y选项时,这些第三方将遭受一笔货币损失。他们是以同一场实验中的其他被试来模拟这种第三方的存在,而后续的学者,如Barr & Serra(2009)则直接引入了一个被动的、不做任何决策的被试来实现这种模拟。 Barr & Serra(2009)的实验框架建立在最后通牒博弈的基础上。在他们的实验中,每组实验包括5个厂商、5个官员以及5个公民。被试拥有一份初始禀赋。实验决策过程如下:厂商和官员两两配对,厂商先决定是否向官员行贿,以获得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行贿是有成本的;而后,官员选择是否接受贿赂,如果接受贿赂,则行贿的厂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决策,但是官员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且,每次贿赂行为产生都将给5个公民带来一定的损失。最近有关贿赂的研究中,包括Cameron et al.(2009)、Barr & Serra(2010)以及Drugov et al.(2011)都沿用该设计。 前述实验设计很直观地捕获了贿赂这种腐败行为的一些根本特征,但却未能捕获官员索贿这种类型的腐败。于是,为研究索贿,Serra(2012)对Abbink et al.(2002)的贿赂博弈框架做了一些改进,增加了一个官员可以要求贿赂的阶段,而后再进入潜在行贿者决定是否行贿的第二阶段。最后,如果当事人满足官员的要求,则有利于当事人的决定将自动实施。 (二)贪污实验 贪污虽然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类型,但却少有实验关注。第一个研究贪污行为的实验框架是由Azfar & Nelson(2007)提出的。他们的实验框架很复杂,是一个涉及多名参与者与角色的多阶段博弈。每一轮开始时将进行角色分配,8名被试中的3名将被随机选出作为官员候选人,其他5名需要通过投票在这3名中选出1名作为官员。而后,另2名候选人中的1名将被执行官任命或者由投票者选出,成为检察官,负责监督官员。最后,剩下的1名候选人与其他5名参与者一起,扮演公民的角色。在角色分配完成之后,官员将获得一份工资,然后他需要通过掷骰子的方式决定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选民之间分配。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和其他一些无价值的东西混在一起,他可以自由选择给自己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一行动就构成了实验中的贪污。检察官的任务是随机翻检官员留下的东西,不过最多只能检查4次。被翻检出的东西将当场披露,有价值的将被没收。检察官的前两次翻检不需要成本,但是后两次翻检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实验者用该框架检验了工资、透明度、选举等制度因素对贪污行为的影响。后来,Barr et al.(2009)沿用了该框架,用于研究贪污的治理机制。 在另一项研究中,Abbink & Ellman(2004)引入了一个简单的分配场景:每一组实验共有5个参与者:1个中介,4个村民。2个村民富裕,禀赋为50;2个村民贫穷,没有初始禀赋;中介是最富的村民,禀赋100。另外,中介还将获得额外的100禀赋,用于分配给贫穷的村民,但具体如何分配由中介决定。村民可以抱怨,不过抱怨有成本。如果抱怨出现,中介就会被调查并可能受到惩罚。 总体上看,相比贿赂,贪污的实验框架更为复杂。而且,已有的对贪污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分配环节,而未能如贿赂的实验框架一般纳入对生产环节的考虑。而事实上,如前所述,大量经验研究证明,腐败行为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负外部性就在于,它不仅会把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而且将挤出正常的或者说有效率的生产活动。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有关贪污的实验研究仍然还有值得改进之处。 (三)田野实验 因为其高度抽象和人工性,研究者们对实验室实验外部有效性的质疑从未停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一些研究者开始把实验室搬到田野,通过改变被试群体、实验任务、商品对象、信息结构、彩注报酬、环境规则等实验要素(Harrison & List,2004),以求增强实验的真实性。这其中,最受田野实验学者关注的是自然田野实验。这种实验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即使实验的被试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参加实验。如此,威胁到实验室实验内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霍桑效应就得到了控制,因为此时被试可能就不会像在被观察时那般纠结于道德与财富的冲突(Levitt & List,2007)。就腐败研究而言,由于非货币的考虑(如伦常)也可能是腐败决策的重要诱因,因此引入这种自然田野实验显然非常有必要。不过由于田野实验常常因情景而异,不存在统一的实验框架,因此我们这里仅简单介绍两个有意思的田野实验研究。② Armantier & Boly(2011)设计了一个阅卷的场景用于研究贿赂——在阅卷过程中引入一个受贿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通过招募兼职改卷学生的名义招募的被试,因此被试并不知道他们参加的是一场实验。在实验中,被募来的学生需要给20份试卷打分。每位被试面对的第11份卷子中都夹着一笔钱和一条信息:“请给我打高分”。研究者通过变换不同的实验参数以观察行贿的数量、改卷者的工资以及监督和制裁水平对腐败行为的影响。 在另一个实验中,Peisakhin & Pinto(2010)走进了印度的贫民窟,将这个贫民窟的人群分为三个对照组和一个控制组,通过比较贫困居民获得一份粮食资助所需要等待的时间和贿赂、透明度等控制变量的关系,研究了透明度对于抑制腐败的作用。这里,研究者操控的变量是不同的申请辅助手段。控制组没有任何辅助手段,按标准流程进行。第一对照组的被试在提出申请之后立即提交一份信息公开申请。第二对照组的被试在申请时将出示一份来自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证明信。第三对照组的被试则通过一个中间人向地方官员行贿。 相比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以更真实的情景引出了被试更真实的行为反应。虽然田野实验的控制性可能不如实验室实验,但是它在外部有效性上更有优势。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自然田野实验的方法,它在寻求外部有效性的过程中力求保证研究的内部有效性,可以说是研究者理想的环境。当然,这两种实验方法彼此形成了互补,都是研究者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 三、腐败的影响因子研究 腐败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社会人口统计特征、腐败的组织机制、社群地理文化属性都可能影响到个体的腐败决策。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从个体到组织进而进入宏观环境层面,讨论腐败的影响因子。 (一)个体属性与腐败的关系 1.专业背景 学经济学的人比其他专业的人更腐败吗?Frank & Schulze(2000)的实验发现,经济学的学生要显著比其他学生更为腐败,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是源于自选择效应,而非经济学的学习经历所造成,因为那些学习时间更长的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行为与刚开始学习的学生并没有显著不同。在后续的研究中,Schulze & Frank(2003)进一步发现,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确实表现得比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加腐败,但是这种差异在存在被发现的风险时消失了。 有证据表明,女性要比男性更为关系导向,拥有更高的伦理行为标准,更关注公共利益(Dollar et al.,2001)。如果这些成立,那么对于政治生活而言将有重要的含义。但是,男性真的会比女性更腐败吗?Schulze & Frank(2003)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结果显示,在不存在被发现的风险时,女性的腐败表现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当存在风险时,女性确实表现得比男性更不腐败。不过,基于在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完成的跨文化研究,Alatas et al.(2008)的实验结果发现,只有澳大利亚的男性和女性在接受贿赂上存在显著差别。此外,Armantier & Boly(2011)也没有在他们的田野实验中发现性别差异。 有鉴于这种不一致的矛盾,Rivas(2008)运用Abbink et al.(2002)的贿赂框架,专门探讨了性别对腐败的影响。借助以2×2设计,作者在实验中研究了男性作为企业角色而女性作为官员、女性作为企业角色而男性作为官员角色、只有男性角色以及只有女性角色四种不同设定下腐败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对于行贿的频率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女性的行贿数量显著小于男性;如果行贿者是女性,女性官员更倾向于拒绝贿赂;在接受贿赂后的互惠决策中,女性官员选择互惠决策的频率也显著小于男性官员。因此,Rivas认为男性确实比女性更加腐败,在容易发生腐败的部门启用更多女性官员也许可以减少腐败的水平。 3.工作背景 Alatas et al.(2009)的实验还检验了工作背景是否会对腐败行为产生影响。他们比较了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被试和公务员被试的实验结果之后发现,学生被试不管是扮演企业身份还是官员身份都比公务员被试更倾向于腐败。 (二)组织与腐败的关系 腐败的组织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家的注意(如Hasker & Okten,2008)。然而,由于组织性腐败的隐蔽性极强,要对其展开经验研究尤为困难。于是,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使用实验手段模拟组织腐败的关键特征,比如对中介可能在腐败交易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Drugov et al.,2011)。Drugov et al.认为,中介的存在会通过降低搜寻和协商等信息成本润滑腐败关系;同时,中介还可以降低被发现和受惩罚以及违约的风险,因为中介能够与受贿者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而这对于行贿者而言是不可能的。实验结果显示,中介的出现确实会显著地增加腐败水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发现,虽然腐败的这种增加部分源于不确定性的剔除,但是中介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中介的出现还将导致私人个体和官员腐败时道德和心理成本的下降,从而导致腐败水平的增加。这种机理也得到了雷震(2013)研究的进一步证实。他通过比较集体组和个体组的决策发现,集体组的腐败率要显著高于个体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集体决策更理性,同时降低了决策者的心理成本。 (三)文化与腐败的关系 文化的重要性在已有的跨国经验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如Treisman,2000)。不过如前所述,这种研究并不能干净地剔除潜在因素的影响,因此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在实验研究之中取得突破,典型的如Cameron et al.(2009)、Barr & Serra(2010)等。 Cameron et al.(2009)在四个国家中检验了文化对个体腐败决策的影响。他们发现,与澳大利亚相比较,所处环境更腐败的印度人参与腐败的倾向更高,惩罚腐败的频率更低;与此相反,尽管印度尼西亚人面临的腐败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他们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更低;而尽管腐败程度很低,但是新加坡的被试非常倾向于参与腐败,并且不倾向于惩罚腐败。另外,他们还通过不同的实验设计检验了贿赂行为的觉察成本对于腐败的影响,并且发现这种影响也因文化而异。 不过由于Cameron et al.的研究仅仅是对被试的更换,我们无法确定其结果的差异就是源自文化。在腐败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更值得一提的是Barr & Serra(2010)完成的研究,依托牛津大学中来自腐败程度非常不同的40个国家的学生被试,作者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进行了两次贿赂博弈实验。2005年的实验结果显示,本科生在实验中的行为可以由学生母国的腐败水平(以腐败指数来表示)所预测:来自腐败指数越高地区的学生,在实验中参与腐败行为的倾向越高。这表明,参与者腐败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他们在自己成长的国家中内化了的有关腐败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两年后以不同的样本重复完成的实验结果很稳健。这说明,腐败行为确实与文化背景相关,并且也从侧面证明,实验室中生成的环境可以用于捕获行为主体的腐败倾向。 四、腐败的动机及治理机制研究 上述研究识别出了一些腐败的影响因子,但是它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因子为什么会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深入到个体行为动机层面,介绍已有的关于腐败行为决策的动力机制研究。 (一)外部动机与治理机制 传统有关腐败经济学的研究强调的是作为代理人的官员腐败的机会成本,进而据此通过赏罚实现对腐败的控制(Becker,1968;Becker & Stigler,1974)。这种思路背后所体现的是典型的经济学逻辑,即把官员看成一个理性的个体,认为其决策会受到成本收益的影响。基于这种考虑,一些相应的提高腐败成本的机制也就应运而生,如高薪养廉、监督惩罚、举报等。于是,也就有一些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室中检验了这种外部动机以及相应的机制设计的作用。 首先,研究发现,高薪养廉的效果并不明确。理论上,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就意味着其被辞退的机会成本的上升,因此会对公务员形成一种威慑;一些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Treisman,2000;Van Rijckeghem & Weder,2001;吴一平,2008)。然而,来自实验室的结果并不确定。虽然Schulze & Frank(2003)、Azfar & Nelson(2007)均发现,报酬更高的官员确实腐败更少,但是Abbink(2002)、Barr et al.(2009)以及Armantier & Boly(2011)的研究却显示,工资水平高低对于被试的腐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这种不一致之所以出现,可能是因为高工资还将通过其他渠道影响腐败决策,比如已有研究表明,物质激励的引入可能会挤出被试保持廉洁的内部动机(Frey,1997;Bowles,2008);而有研究表明,高工资发挥作用的路径不仅在于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而且在于引出官员的互惠之心(Armantier & Boly,2011)。另外,这种不一致出现还可能是因为实验对该机制的检验不够彻底,即因为实验中并没有罢免威胁,因此未能很好地引入潜在的机会成本;换句话说,这种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许取决于是否存在可信的罢免威胁。 其次,研究发现,监督惩罚机制的反腐效果很好且很稳健。实验中的监督惩罚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外生的惩罚,即事前外生给定发现概率和惩罚程度,如Abbink et al.(2002),Schulze & Frank(2003)等。这些实验发现,这样的惩罚机制既能有效降低腐败的平均水平,也能有效减少被试选择腐败的频率。二是内生的惩罚,Berninghaus et al.(2012)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官员被抓的概率取决于腐败的人数,越多人腐败,被抓的可能性越低,因此其中存在着诚实或者腐败的多重均衡。结果发现,官员的信念成为影响腐败决策的重要因素。尽管腐败的人数越多越安全,但对其他人行为信念的模糊性可以显著减少腐败。这就为通过公共宣传或者树典型影响官员信念等反腐政策提供了一些支持。三是通过操控监督机制实现,如引入监督者,进而考虑监督者的激励机制设计。监督者面临的激励是多重的:一方面,监督是有成本的,因此少监督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另一方面,因为监督者常常拥有很好的物质报酬,因此他也有激励尽职尽责,以求保住饭碗。Azfar & Nelson(2007)与Barr et al.(2009)通过在实验中引入不同的监督者遴选程序发现,监督可以很好地抑制腐败,但是如果有两个以上监督者存在,就可能引出搭便车行为,降低该机制的效果;同时,监督者如何遴选也很重要,保证监督者的独立选拔尤其重要(Azfar & Nelson,200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举报(告密)机制的效果。Schikora(2011b)融合了行贿和索贿的双重框架,实施了一个实验。在他的实验中,腐败既可以由企业行贿开始,也可以由官员索贿开始。结果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和官员双方都有举报权时,腐败行为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显著增加了。作者的解释发人深省,他认为,双方的举报权稳定了腐败者的互惠动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Serra(2012)完成的一项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她比较了纯外生惩罚和结合了举报的惩罚机制的反腐效果。在控制组中,索贿官员有4%的可能性受到惩罚;在对照组中,这种外生的惩罚机制需要有当事人的举报才能得以启动,不过启动之后,官员面临的惩罚可能性仍然是4%。作者解释,控制组模拟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策略;而对照组模拟的是一种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腐机制。基于标准理性模型的预测是,第二种机制的效果可能会弱于第一种,因为此时惩罚的概率有可能变小。然而,实验结果出人意料,官员的贿赂需求在第二种情形下显著变少。作者猜测,这可能是因为此时官员感知到两条路径的威胁,从而错误地在心理上认为惩罚威胁更大了;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举报权利的引入诱发了官员的羞愧感。 (二)内部动机与治理机制 有意思的是,从上述有关外部动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学者在遇到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的实验结果之后,往往会转而向替代性假设求助,尤其是指向人类行为的其他激励系统:内部动机。实际上,大量证据证明,选择遵从还是不遵从正式规则或者规范的个体不仅会依据他们所面对的外部激励,更会依据他们自己的内部动机理性化其行动(Kreps,1997)。忽略诸如内疚厌恶(Battigalli & Dufwenberg,2007)、不公平厌恶(Fehr & Schmidt,1999)、社会尊重(Bénabou & Tirole,2006)等内部动机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能正是导致传统经济学预测失灵的重要原因。而如果非货币激励确实会影响腐败,那么仅仅依赖货币激励的反腐败干预的效果就可能因为挤出这种内部动机而弱化,因此在腐败问题的讨论上,不能忽视内部动机的作用。正是有鉴于此,很多实验经济学家开始在博弈框架中纳入心理和内化的社会规范因素,③在实验室中检验腐败行为的内部动机以及基于此而做出的反腐机制设计的作用。 实验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操控腐败行为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大小来检验内疚厌恶这种内部动机的作用。其背后的直觉是清晰的,腐败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可能会引出腐败者的负罪感和内疚感,于是,为了不让他人失望,个体可能会减少自己的腐败需求。实验中,不同学者引入负外部性的方式不尽相同:Abbink et al.(2002)通过减少同实验场中所有其他被试的收益来实现;Azfar & Nelson(2007)、Barr & Serra(2009)以及Cameron et al.(2009)通过减少一组被动的博弈参与者的收益实现;Lambsdorff & Frank(2010)则通过撤销部分实验者承诺向慈善组织的捐赠实现。结果,Abbink et al.(2002)发现,引入负外部性既没能减少腐败的数量,也没能降低腐败的频率。他们总结说,这些结果挑战了以宣传运动来增强官员对腐败行为负效应的感知的有效性。不过与他们不同,Barr & Serra(2009)的实验结果显示,在负外部性相对较高时,不管是企业的行贿倾向还是官员的受贿频率都相对较低。 其次,如前所述,基于主观调查的腐败研究依赖于一个不大现实的假设,即不同文化中行为主体对于什么是腐败有着一致的定义。比如,由于传统上对礼制的遵循,送礼与行贿在国人眼中就从来没有得到过清楚的区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腐败一个漂亮的“挡箭牌”,消除腐败可能隐藏的风险和心理负效用。那么,这种被文化传统塑形的定义框架是否真的会影响到个体的腐败决策呢?④Abbink & Hennig-Schmidt(2006)第一次通过一组对比实验研究了框架效应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参照组中的实验介绍全部使用中性词语,对照组中的实验介绍则使用与腐败有关的暗示性语言。不过,实验结果与他们的预期不同,框架化并没有减少腐败水平,两组之间不管是企业行贿的数额还是官员接受贿赂的频率都没有显著差异。与他们一样,Barr & Serra(2009)也没有发现框架效应会起作用。 不过在一个更近的实验中,Lambsdorff & Frank(2010)更直接地检验了用词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发现把腐败称为礼物是有影响的。实验中,商人可以选择将自己送出的贿赂称为是“贿赂”或者“礼物”,而官员可以选择进行互惠、举报行贿行为或者接受贿赂但不采取任何行动;商人还将获得惩罚官员的机会。实验结果显示,将自己的贿赂称为“贿赂”的商人,在看到官员接受贿赂但不采取任何行动后给出的惩罚显著大于将贿赂称为“礼物”的商人。作者认为,将贿赂称为“贿赂”的商人是在发送一种期望得到官员的互惠的信号,而“礼物”称呼的这种信号发送强度要弱很多。这意味着,直接挑明的腐败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腐败者的互惠关系。 最后,有关公平考虑⑤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在腐败研究中。Abbink(2005)在实验中检验了不公平厌恶对腐败行为的影响。他让控制组中被腐败伤害的个体工资总是低于官员,让对照组中被腐败伤害的个体保持更高收入,即使他们受到负外部性的最大伤害。如果公平考虑是存在的,那么高工资情形中的腐败就会更多。然而,实验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不过,近来由Van Veldhuizen(2011)完成的研究发现了相反的证据。作者同样是采用的Abbink et al.(2002)的贿赂框架,只是在他的实验中,官员的报酬会因博弈而异,因而行贿者与官员之间的相对支付是变化着的,相对支付的差距更为凸显,感知到的公平或者不公平也拥有更强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高工资的官员所做的腐败决定要比低工资官员所做的腐败决定低上三分之一。这一结果对于高薪养廉机制的具体设计可能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所谓“高薪”也许不应该是绝对工资最高,而是在于工资的相对差距。 (三)其他反腐败的制度安排 在理论界之外,实践界也提出了一些反腐败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岗位轮换机制和引入两个官员“四只眼睛”(Four-Eyes-Principle)的制衡机制。同样,借助实验室实验在比较机制上的强大功能,也有实验经济学家在实验室中对这两种机制的效果进行了检验。 岗位轮换是很多国家用于预防腐败关系建构的一种常规手段。这种设计背后的逻辑在于,给定腐败是建立在行贿受贿方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的,因此可以预期,潜在的行贿者和公共官员之间的长期关系将有利于腐败的滋生,因为这意味着未来潜在合作次数进而预期收益的提升。也因此,岗位轮换机制的引入将可以通过影响官员和行贿者的信念而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当官员无法预期是否还有未来,他们就可能更不为贿赂所影响;相应的,行贿者也可能因预期官员的合作行为会变少,而降低对官员的互惠信任度。那么,这种机制是否可以如实践者所设想的那般抑制腐败呢?Abbink(2004)在一个实验中引入了一个随机再配对的实验情形,把其与Abbink et al.(2002)进行对比,检验了这种机制的效果。结果表明,岗位轮换确实可以显著地减少贿赂以及因为贿赂而导致无效决策出现的频率,其有效性甚至超过惩罚、高薪养廉等机制。 “四只眼睛”机制已成为世界银行力推的反腐利器。通过引入两个官员,这种机制会通过两种效应影响到腐败决策:首先是分成效应。给定贿赂的多人分享将降低腐败的经济吸引力,从而减少腐败;其次是集体行动效应。集体行动效应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方面,集体行动将引出搭便车问题和协调难题,从而减少腐败的可能性;但是同时,小群体集体行动也很容易形成稳定的串谋,使腐败走向组织化和网络化。于是,我们同样需要问的是,这种机制在经验上的表现到底如何?Schikora(2011a)在一个实验中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分成效应确实存在,但是这种效应的效果将为集体行动效应所抵消。最终的腐败水平是上升了。 综上,已有的对反腐机制的实验检验表明,监督惩罚和岗位轮换机制的作用比较稳健,而其他机制的效果均不是非常稳健。而且,即使对于监督惩罚而言,不同机制设计的效果也非常不一样。这些结果还表明,我们还需要对每一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微观行为基础和机理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因为,任何一条机制都可能存在多条作用机理,或者通过影响内部动机,或者通过影响外部动机。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结合了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组合机制设计显示出值得期待的效果。⑥当然,需要小心的是,上述结果往往只是基于一个或者两个研究而得出,其稳健性以及可能适用的范围仍需进一步研究。而且,实验室之中的机制设计很多都经过抽象和简化,具体的实施可能还将面临着实施成本的问题。比如,虽然岗位轮换机制有着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一天一个岗位必然极大地提升行政部门的运行成本,降低其运作效率。因此,综合审慎的评估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必要步骤。 五、评述与展望 实验经济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分支之一。目前,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使用实验来解释经济现象和行为(Roth,1995)。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连续授予实验经济学家更是进一步确认了这种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之中的合法性。事实上,作为自然科学长期以来所依赖的主要手段,受控实验在许多地方展示出了其他技术手段所没有的优势,比如在有效数据生成、行为假设检验、行为规则发现乃至制度比较分析等方面。这一点在腐败问题研究之中尤为明显。因为腐败的隐蔽性,自然生成的数据很难获得,行为动机更难把握。也正因此,通过实验的手段研究腐败问题的文章在国际知名期刊中日益增多。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理解。我们认为,未来的腐败研究可以继续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细致的考虑。 首先,从已有研究的结果看,同一因素或者机制在不同实验中的结果不尽相同,说明目前已有的实验框架可能还未能很好地控制或者捕捉到腐败行为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动机。⑦与此同时,目前大部分的框架都针对贿赂这一腐败形式,而对于贪污、渎职等其他类型的腐败行为关注较少;对于腐败所带来的分配方面的负效应关注较多,而对于腐败所带来的生产方面的负效应的研究较少。因此,为了增强实验研究对于现实中腐败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实验框架的进一步优化设计将是未来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个过程中,应用自然田野实验的思路捕获真实可控的实验机会也许是未来值得给予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 其次,有效的机制设计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实证研究基础上,尤其是对行为动机的识别。目前已有的研究虽然已经证实,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都在个体的腐败决策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基于此识别出了一些能有效抑制腐败水平的治理机制,但是已有研究很少着眼于动机与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机制与动机之间的挤入挤出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然而,如前所述,这一点可能正是有些机制效果不稳健,而有些机制效果很好的原因所在。因此,借助实验的手段,逐渐剥离出腐败行为背后隐藏的各种动机,特别是内部动机,有可能会为人们理解腐败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腐机制的设计带来新的启示。 再次,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中介完成的,或者是部门内部合谋的组织性腐败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腐败的组织问题,意识到腐败并非单个人的事件,但是相关研究仍然很少,亟待加强。 最后,就我国而言,截至目前,相关研究还十分少见。考虑到已有研究所证实的文化因素在腐败决策之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本土样本,结合实验室实验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内腐败行为者的行为模式,进而与西方样本进行比较,无疑具有很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这不仅可以增添有关腐败行为决策的知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更有效和符合国情的反腐机制,增进社会福利。 ①该比例可以看成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货币边际效用的差异。 ②其他还可参见Bertrand et al.(2007)以及Olken(2007)。 ③有关信念和心理博弈的理论发展和应用,可以参见姜树广和韦倩(2013)的文献综述。 ④Dufwenberg et al.(2011)认为框架可以通过影响信念来影响选择和行动。 ⑤Fehr & Schmidt(1999)、Bolton & Ockenfels(2000)认为个体不仅在乎自己的绝对物质收益,还在乎其收益与其他人收益的相对大小。此外,Rabin(1993)、Dufwenberg & Kirchsteiger(2004)都提出,基于意图的公平偏好也会影响到个体决策。 ⑥这一结果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和直觉的。比如,新加坡反腐的成功可能就是源于多种机制的组合使用。 ⑦比如在Abbink et al.(2002)的贿赂博弈框架中,即使剔除掉互惠动机的影响,官员选择腐败仍然可能是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因为官员接受贿赂带来的社会总收益将超过拒绝贿赂时的社会总收益。标签:动机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