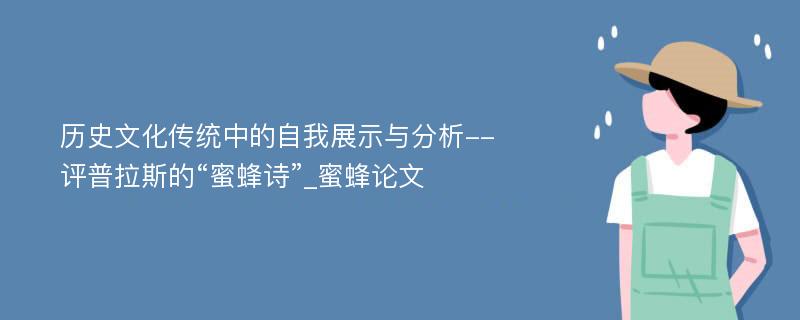
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展示和剖析自我——评普拉斯的“蜜蜂组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蜜蜂论文,历史文化论文,传统论文,自我论文,普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08)03-0053-05
美国自白派诗歌(Confessional Poetry)发端于1950年代末期,盛行于1960年代。自白派诗人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试图建立针对自我的分析学”[1](P64),他们打破了艾略特的已经僵化了的“非个性化”模式,以一种独特的艺术方式,即通过暴露自我和分析自我来揭示那一代人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以达到宣泄受压抑的情感的目的,使烦乱的内心获得一种暂时的宁静。这很能引起生活于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的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自白派诗人并不是直白地抒写自我,而是很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意识。他们的诗歌引用了很多神话、寓言、历史事件、文学名篇,与历史文化形成互文关系,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可以说自白派诗人是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展现和剖析自我,他们的诗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使得人们对自白派诗歌的兴趣越来越浓。
一
普拉斯从小就很有文学天赋,勤奋好学,且有远大抱负,她想成为一个“想当上帝的女孩”和“女人中有名望的女人”[2](P149~150)。她进大学前就已经发表了不少诗作。就读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期间,她发表的作品多次获奖。195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奖学金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与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1930-1998)相识,两人志趣相投,很快结婚。婚后,他们曾一度返回美国住在波斯顿,专事写作,休斯的第一部诗集获得一项诗歌奖,这实现了普拉斯向他许诺的要帮助他成功的诺言。1959年普拉斯参加了自白派诗歌主将罗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开办的诗歌写作班,深受影响,并结识了后来也成了自白派诗歌的一员大将的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是年底夫妻返回伦敦,随后住在郊区,继续勤奋耕耘,偶尔也骑马、养蜂,以增添生活的乐趣。所有这些经历,都先后成了普拉斯创作诗歌和小说的题材。1962年,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巨像及其他诗歌》(The Colossuss and Other Poems)。
由于普拉斯本人的个人嫉妒、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性别角色认识的差异,以及普拉斯家族遗传给她的抑郁症的复发,她和特德·休斯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休斯另有情人,普拉斯带着孩子孤独、恼怒地生活在伦敦郊区的一所旧房屋里,手头十分拮据。第一个小孩才两岁半,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她内心的苦恼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作为诗人和小说家,她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写作,因深受罗威尔暴露自我的主张的影响,她的内心世界就通过她的作品呈现了出来。1962年10月她主动提出与休斯离婚。离婚后的她获得了自由,才思泉涌,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写下了奠定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25首诗歌,其中有《拉撒路夫人》、《阿丽尔》、《爸爸》、《高烧103度》以及五首“蜜蜂组诗”:《蜂会》(The Bee Meeting)、《蜂箱的到来》(The Arrival of the Bee Box)、《蛰》(Stings)、《蜂群》(The Swarm)和《越冬》(Wintering)。她对离婚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这从她写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我是作家,我是有天赋的作家,我正在写一生中最好的诗歌,它们会让我出名的。”[3]她从郊外搬进伦敦城里的一间寓所,雇了钟点工帮忙料理一些家务,努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的自传体小说《钟罐》(Bell Jar)也于1963年1月出版,新诗集手稿也编排好了。可惜的是,那年天大寒,是伦敦150年一遇的最冷的冬天,再加上她的抑郁症和失眠,她没有像她在“蜜蜂组诗”的最后那首诗《越冬》的最后一句诗行里所说的那样,要度过寒冷的冬天,期盼“品味春天”①,就于1963年2月11日在家中用煤气自杀身亡。
“蜜蜂组诗”收录在她死后由她前夫休斯稍作整理后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诗集《阿丽尔》(Ariel,1965)中。其实这个诗集在诗人自杀前就已经由她本人编排好了,“蜜蜂组诗”被诗人放在诗集的末尾作为压卷之作[4](P297),其寓意十分明显,就是要熬过“属于女人的冬天”(《越冬》),进入来年,迎接春天。但在1965年出版于英国和一年之后出版于美国的这个诗集,并没有按照普拉斯的编排顺序。当时休斯并不十分了解普拉斯,甚至是歪曲了普拉斯的本意,他把她的描写自杀的几首诗放在诗集的最后,用以表明诗人的自杀和她的这些诗有关。
普拉斯确实对自杀很着迷,自杀之前已经有过几次自杀念头。她也写过几首流露出自杀情绪的诗,如《拉撒路夫人》就说“自杀是一种艺术”,《罂黍花》也表达了对死亡的着迷。难怪《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把她看成是“自我毁灭的、充满激情的天才”[5](P76),还把她与嗜酒如命、英年早逝的艾伦·坡并列在一起。但这些是否就说明了诗人对生活一点信心都没有呢?尽管生活中有许多烦恼和挫折,尽管她那么年轻就主动选择了生命的终结,她其实一直徜徉在艺术的殿堂,对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常被研究者忽略的“蜜蜂组诗”中窥见一斑。诗人在这组诗里,对自己的处境,自己与外界环境、家庭、艺术等的关系做了较完整的剖析,阐发了她的历史文化意识以及要冷静地对待寒冷漫长的冬季和渴望下一个春天到来的愿望。
二
《蜂会》写的是诗人跟着一群村民去山林捕捉蜂后的经历,揭示出诗人在群体中的处境和感受。一开始,诗人就将自己置于脆弱和分离的地位,与村民格格不入。到桥上来迎接她的那些村民,戴着手套、帽子和面纱,而诗人却穿着没有衣袖的夏裙,脖子也裸露在外:“我没有保护”,而“他们都带着手套和头巾”。村民们要诗人随他们到树林里去,把那些未交配过的雌蜂搬走,目的在于保护蜂后。可蜂后并不领情,“她很聪明”,飞向天空去了。诗人在这里认同的还不是飞走的蜂后,而是那个空巢,即那个幸存下来的“山林中的白色盒子”。为何那个盒子令诗人“感到如此寒冷”?原来诗人是在感叹自己的空巢。她写此诗的时候刚刚离婚,她把丈夫赶出了家门,她却不愿意走,也不能走。一方面是因为她有两个待哺的小孩,另一方面则因为她是美国人,远离家乡。“我不能跑开,我生根了。”“我若不能永远跑开,我就不能跑开”。此外,她也十分倔强,不肯向困难低头,“我是巫师的女儿,决不退缩”。
她和村民们一起进入树林去会蜜蜂,但她那身打扮肯定会遭到蜜蜂的攻击,于是一位村民将她严严实实地裹起来。由于她天生脆弱胆小,未能融入到当地村民的生活中去,被裹起来后,又要近距离靠近蜜蜂,内心的恐惧反而增加了。她幻想自己变成“马蹄筋丝”以保护自己。“现在我是马蹄筋丝,蜜蜂不会注意到/他们不会闻到我的畏惧,我的畏惧,我的畏惧。”“如果我站着不动,他们会认为我是/马芹菜。”诗人把自己想象成达夫妮,变成植物,逃避侵扰。众所周知,在希腊神话中,达夫妮(Daphne)是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她为了逃避天神阿波罗的性骚扰,变成了一棵桂树,以保护自己[6](P429)。在《蜂箱的到来》中,达夫妮神话再次出现:“我想它们是否会忘记我/要是我将锁打开,站到后面/变成一棵树。”通过这几行诗,诗人刻画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她与居住地村民的关系以及她努力保护弱小的自己的心态。
她即使变成了植物将自己掩藏起来,内心的恐惧也没有减少。她敏感的大脑却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周围的植物都活动起来了。山林中的蚕豆花在“扇动它们的手”,这些蚕豆花犹如“黑色的眼珠”,令人心生恐惧,其叶子像“穿孔的心脏”,在滴血;山楂在“扼杀自己的孩子”。诗人在这两段对充满恶意的植物的描写中,用了“scarlet flowers”(红花)和“hawthorn”(山楂),这隐含了对19世纪美国作家、《红字》(Scarlet Letter,1850)的作者霍桑(Nathaniel Hawthorn,1804-1864)的观点的引用和认同。霍桑在很多作品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恶,罪恶是人类的天性[7](P322)。他的短篇小说《年轻的好小伙布朗》(The Young Goodman Brown)写布朗走进森林,发现所有树木皆发出邪恶的熊熊火焰,当地教区不同身份的人都在参加那个好似“魔鬼晚会”的聚会,连他的新婚妻子也在其中。这个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从幼稚走向了成熟,获得了一种对人生的顿悟。普拉斯在这里表达了她从单纯走向认识到人性中隐藏着罪恶的心路历程。这种心路历程,在根据骑马经历而写成的《阿丽尔》中,读者也能窥见:诗人天没亮就骑马出发,看见天空渐渐明朗,她感到自己好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从愚昧走向了文明,变被动为主动,像一支箭射向太阳,同时又像一滴露珠,将被太阳融化,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在她看来,成熟带给自己的是恐惧和毁灭。
这首诗是蜜蜂组诗的第一首,时间是夏天。蜜蜂组诗开始于夏天,终于冬天,展望春天。组诗的最后一行,也应该说是诗人自己编排的《阿丽尔》诗集的最后一行,是结束在“春天”这个词上。这样的时间安排恰好与19世纪主张追求精神充实的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1854)十分类似。《瓦尔登湖》的描写始于夏天,是以“春天”篇结束全书的[8](P325)。我们完全可以猜想,普拉斯接受了梭罗的时间周期观,也有可能接受了梭罗对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未来满怀信心的乐观精神。
夏天意味着最强盛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最出成果的生命期。诗人在这一年,生了第二个孩子,第一本诗集正在印刷,也找到了第一部小说的出版商。可是她却把自己的丈夫拱手让给另一位女人。她开始思索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包括跟邻居,跟其他女人,跟自己的关系,重新评价自己,改变自己。诗人这年刚好三十岁,正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她在这第一首蜜蜂组诗里,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诗人做了回答,如一开始:“这些到桥上来迎接我的人们是谁?/他们是村民。”第四小节:那些卷须往茎上拉的是血块吗?/不,不,那是某天可以吃的红花。”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当然也没有必要找出答案。如第三小节:“哪一位是教区牧师,是那个穿黑衣的男子吗?/哪一位是接生婆,是那个穿蓝色外套的人吗?”这首诗以问句开始,以问句结束,全诗共有十一个问句。这充分说明诗人在进行反思,在剖析自我。然而过多的反思却令她疲惫不堪。
在《蜂会》中,“白色的盒子”(即蜂巢)犹如棺材,令人心生悲哀,她因处处设防而显得很被动。但到了组诗的第二首《蜂箱的到来》中,那个“干净的木盒子”(即蜂箱)则是她主动订购的、她将拥有并为之负责任的东西。盒子上了锁,她想打开盒子,但是又怕在里面骚动的蜜蜂会跑出来蜇她,将她毁灭。内心的矛盾冲突通过“盒子”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剖析。这个盒子意象多次出现在她的诗歌里。在纪念她父亲的早期诗歌《养蜂人的女儿》(The Beekeeper's Daughter)中,养蜂人的女儿就曾经跪下来往蜂箱里看:“我把眼睛放在洞口,遇见一只眼睛/又圆又绿,像一滴忧伤的眼泪。”蜂箱中那个蜂后的忧伤的眼睛引起了这个女孩的共鸣。但在《蜂箱的到来》里,蜜蜂不是闷闷不乐,而是狂怒。实际上,与其说是诗人听到它们狂怒的声音,不如说是诗人听到了自己压抑太久而发展到了狂怒的声音。黑压压一群蜜蜂在黑黑的蜂箱里爬行,愤怒地想外逃,这使她联想到非洲黑奴,好像他们在船舱里拥挤在一起,被运往海外,很值得同情。接着诗人又把蜜蜂比喻成罗马的一群分不清是非的愚民。诗人自己不是恺撒,既听不懂它们的话,也不能主宰它们。这个比喻使读者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朱利阿斯·恺撒》中的一个场景:在罗马广场,一群愚民在布鲁特斯和安东尼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演讲中,时而觉得恺撒有野心,时而又觉得恺撒没有野心,完全分不清是与非[9](P468~469)。蜂箱是诗人自己订购来的,她是蜂箱的主人,有权利处置蜜蜂。诗人说“它们会死。我无需给它们任何东西吃。”值得庆幸的是,诗人不想对蜜蜂实施完全的控制,“我想它们一定很饿”这句诗行已经暗示了诗人不会拒绝给蜜蜂食物的,她会让它们获得自由的。她不知道自己释放蜜蜂后,蜜蜂会怎样对待她,于是她又想变成一棵树以保护自己。仅变成树枝树叶还不够,她还要穿上太空服,戴着葬礼面纱,以便蜜蜂完全看不出她来。诗人同情蜜蜂,又害怕蜜蜂。矛盾的心态通过几个比喻跃然纸上。
这首诗里,蜜蜂已幻化为感情受到压抑的诗人自己。她害怕自己的记忆和愤怒战胜她。狂怒的蜜蜂所发出的“难以理解的音节”,其实就是诗人自己内心深处愤怒的声音,这种愤怒的声音不能表达出来,是最令她“心生恐惧的东西”。诗人有强烈的冲动要释放蜜蜂,这隐含她有强烈的冲动要暴露自我。但把自我暴露于有偏见的社会,有可能遭受世人的讥笑乃至攻击,所以她想在释放蜜蜂的同时,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蜜蜂的困扰。这时被放出来有可能蜇人的蜜蜂又被幻化成有可能对她造成伤害的社会。这首诗表面写的是养蜂人打开蜂箱,在深层面上看来,可看作西方妇女想释放自己的受压抑的情感和自白诗人暴露自我的矛盾心态。在形式上,其余四首蜜蜂诗都是整齐的每小节五行,惟有这首与众不同,最后一句“盒子只是暂时的”成为独立的一节,这表明诗人有意识地打破形式,要将蜜蜂释放出来,也就是要让自己受压抑的内心世界最终爆发出来。
组诗的第三首《蜂群》体现了诗人的历史意识。她在1962年10月回答采访记者时说:“我发现自己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现在读的历史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目前我对拿破仑很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有历史意识。”[10](P170)这首诗被普拉斯置于蜜蜂组诗的中间。在诗人亲手编排好的手稿中,其他四首都是用打字机打好的,惟独这首是手抄的,很明显是后来才被放进去的,而且这首诗看起来也好像与蜜蜂主题有些背离,似乎不能归入蜜蜂组诗当中。不过,诗人将其归入组诗,自有她个人的道理。这首诗是因蜜蜂而展开的一组联想。
《蜂群》一开始,说有人在街上“嘭,嘭”放枪,原来树上有一群蜜蜂,开枪者是一位很务实的生意人,他开枪射击蜜蜂群的理由是“它们会杀了我的”。他的话是虚拟语气的完成时态,意思是说他已经把蜜蜂干掉了,他要是不先下手,蜜蜂就可能先蜇他了。不过,诗人却觉得,制造流血事件的原因,恐怕是“嫉妒”吧。蜂群被驱赶得四处逃窜,这使诗人联想到拿破仑和他的军队,于是《蜂群》的中心人物就成了拿破仑,蜜蜂就被比喻成了拿破仑的军队。“刀枪出鞘是对付你,/在滑铁卢,滑铁卢的拿破仑”。“最后一块胜利的勋章。/蜂群被打进向上翘的草帽,/厄尔巴,厄尔巴,海上的一个大疱。”拿破仑的军队最后一次在滑铁卢同反法联军作战,结果大败,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群龙无首的将领们,像虫子一样爬进入坟墓般的神龛,只在历史上找到他们应有的位置。而那些蜜蜂们却走进象牙宫殿的新坟墓,为新的帝王效力。蜜蜂的四处逃窜,还让诗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他们密密麻麻挤在车站,这车站就像蜂箱,被来来去去的火车拉往集中营。
一群蜜蜂,让普拉斯联想到拿破仑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集中营,还有在《蜂箱的到来》中提到的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黑奴、罗马帝国时期的没有主见的愚民等,诗人的历史意识可谓深矣。普拉斯曾经说过,诗人“应该能够用见多识广的知识头脑来控制和操纵哪怕是最令人心生恐惧的经历”[11](P2736)。T·S·艾略特曾经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人在创作时应该有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要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能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12](P2)普拉斯等自白派诗人虽然不主张“非个性化”,其实他们还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置于历史的长河。普拉斯的历史、文学知识非常丰富,她把创作放在神话、寓言、文学史和战争史这个巨大的背景中,将自己的才能与文化历史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真正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
组诗第四首《蛰》中,诗人看见那些忙碌的工蜂,觉得自己在几年的婚姻生活中,就跟那些工蜂一样操持家务。她根本不想成为工蜂一样的人,倒希望成为蜂后。这表达了诗人作为家庭主妇的自我和作为诗人自我的矛盾心态。诗人看见的只有雌工蜂,它们是“长翅膀的,普普通通的女人/酿蜜的工蜂。”这些雌蜂只知道来回奔忙,它们的消息就是盛开的樱花和三叶草。普拉斯写这组诗时,刚解脱婚姻,她曾经有过的痛苦的婚姻生活就不可避免地隐含在诗行之中。她说:“我不是工蜂,/虽然几年来我吃灰尘/用我浓密的头发擦干碗盘。”诗人在这里用了西方妇孺皆知的“灰姑娘”故事,表达她作为英国诗人休斯的妻子的苦恼。她为了帮助丈夫成名,揽下一切家务,做丈夫的秘书,但是她作为诗人的梦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到头来丈夫却有了外遇,她感到自己的付出实在不值,为此十分恼怒,甚至大动肝火。“吃灰尘”还隐喻《圣经》中对蛇的惩罚。夏娃被变成蛇的撒旦引诱吃禁果,上帝从此惩罚蛇吃泥土。另外,耶酥的追随者Mary Masdalene用她的眼泪为他洗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他的脚,为他服务。而生活于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现代社会的普拉斯,不甘心做灰姑娘和追随者、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角色,也不愿意像夏娃那样忍辱受罚。她渴望自己的独立,渴望自己能有所作为。
在这首诗中,普拉斯还叙述了工蜂对人的袭击。蜜蜂蜇人之后,必死无疑,但它们毫不后悔,反而觉得“死了也值”。而诗人却不愿意这样,她拒绝死亡,当然也就不去攻击。她说:“而我,一只蜂后,要拯救自我。”她特别关心蜂后的命运,想象着蜂后离开了那个坟墓一样的蜂箱,可能飞向天空去了,像一颗红色的疤痕,又像一颗红色的彗星。疤痕比喻正在康复的伤口,彗星则是好运的象征。显然,普拉斯在这里把自己认同于那只已经飞走的蜂后,觉得自己也从不幸的坟墓般的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飞向了天空,受伤的心灵已经结痂,不久将痊愈。自己也会很快交上好运,未来的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组诗的最后一首《越冬》写诗人在孤寂中的反思。冬天到了,蜜蜂不再忙碌,开始过冬。诗人养蜂所获得的六罐蜂蜜,被放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中间,旁边是“发臭的果酱”、“光亮的空瓶”和“某某先生的荷兰酒”。这隐含她在六年的婚姻生活中,成功的收获伴随着许多对青春岁月的浪费。对蜜蜂而言,现在是“坚持下去的时节”,“寒冷逼近”了,就“聚成一团,/黑色的心智对抗着白色的一切”。天气稍微暖和一点时,蜜蜂就将死者的尸体搬出蜂巢。但诗人发现并感叹到,这些蜜蜂全是雌的(The bees are all women,或者说忙碌的人都是妇女),她们永远是高贵的淑女,而那些男人却“愚钝、笨拙、结巴、粗俗”,怪不得他们在冬季都死掉了。这道出了普拉斯对背叛感情的前夫休斯的满腔憎恨,也赞美了辛勤劳动并独自苦熬于冬季的女人。普拉斯在最后两节对自己的状况做了一番描述:冬天只属于女人。一位女人仍然在婴儿的摇篮边编织,身体因冷而卷束成一团,脑子变得麻木,不再去想太多的问题,只希望火炉不会完全熄灭,能进入到第二年,品尝圣诞节的玫瑰,然后高飞,去品尝春天。
三
普拉斯的父亲阿托·普拉斯(Otto Plath)是哈佛大学的德语教授和生物学家,曾经写过一本《蜜蜂与它们的生活方式》(Of Bumblebees and Their Ways,1934),详细记述了蜂群的生活,如引诱蜜蜂入蜂箱、蜜蜂如何蜇人、怎样越冬等。尽管其父在她八岁时就因病去世,父亲对她的影响却非常大。她很小就对昆虫感兴趣,八岁多时就发表过描写小昆虫的散文。她父亲是德国人,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成人的普拉斯对父亲的感情爱恨参半,这种情感在她的诗歌《爸爸》中有强烈的表述。普拉斯养蜂和写蜜蜂组诗,也可以说是对早逝的父亲的纪念。
美国19世纪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有不少诗歌描写了可爱的蜜蜂,如《蜜蜂对我毫不畏惧》、《我从蜜蜂家偷来的》、《花,不必责备蜜蜂》、《如果蓝铃花为爱慕她的蜜蜂》、《有一种花,蜜蜂爱》、《名声是一只蜜蜂》,蜜蜂成为了狄金森诗歌的一个主题。狄金森在《我每天都在说》中还表达了想当皇后的愿望:“我每天都在说/如果明天,我当上女王——/我一定这样做——/所以我略微,梳妆”。诗人要做好当女王的准备,换上新的衣袍,像个女王的样子,免得那些被招进宫来的“乡下佬”惊诧“我”土里土气的装束打扮[13](P107~108)。普拉斯有很多的诗歌形式和主题,都能找到狄金森的影子,可见她受狄金森的影响之深,她也曾经公开承认:“与艾米莉·狄金森的任何相似都完全是有意为之”[2](P151)。普拉斯在“蜜蜂组诗”中把狄金森诗歌中两个不相干的蜜蜂主题和皇后主题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更新奇的意象,展现了她既有普通蜜蜂的品质、也像或梦想成为一位皇后的自我形象。
通过以上细读分析,我们不难这样说,自白诗人普拉斯一方面以养蜂的经历艺术性地揭示和剖析自我,渴望走出困境,憧憬美好的明天。她在创作“暴露自我”的自白诗歌时,并非直白地抒发胸臆,而是脑海里充满了历史和文化意识,通过引用神话、寓言、历史事件、文学名篇等来展现和剖析自我。“蜜蜂组诗”既暴露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又与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一个互文的体系,显示了诗人极高的艺术才华。
注释:
①“蜜蜂组诗”原文下载于www.amcricanpoems.com/plath.,文中该组诗的引文皆为笔者所译。这里引用的普拉斯的其他诗歌皆为笔者所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