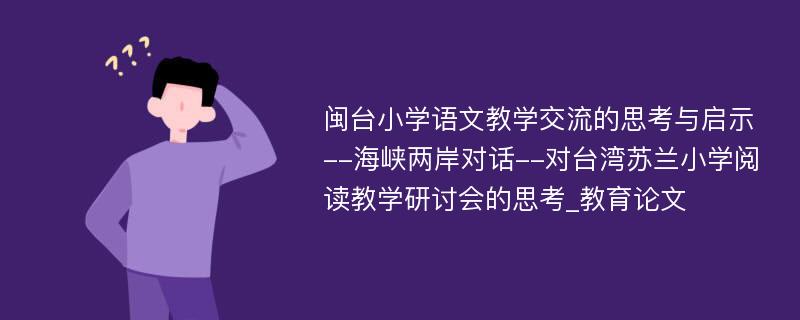
闽台两地小学语文教学交流的思考与启示——跨越海峡的对话——台湾苏兰老师小学阅读教学研讨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两地论文,海峡论文,启示论文,阅读教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策划、组稿/《福建基础教育研究》编辑部
2009年7月,由台湾小学语文教学协会会长赵镜中博士率领的台湾小学教师代表团,来福州进行闽台小学语文教学研讨交流,笔者听了台湾知名小学语文教师苏兰老师执教的两节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课。苏老师执教的教材,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课程实验教材,所教的是小学六年级语文教科书中一首现代诗歌《生活是多么宽广》。
仔细品味苏老师的这两节课,笔者既受到很大启发,也引发一些思考,愿提出来与更多参与本次研讨活动的朋友讨论。
研讨课后第二天,赵镜中博士在报告伊始直言,这样的“公开课”,尤其是“借”其他教师任教的学生上课,实在是迫不得已,在台湾是没有的。台湾教师关注课堂教学的真实状况,认为这是研究教学的起码要求。
想到大陆屡见不鲜的“公开课”“借班上课”“借班教学比武”,不能不令人深思:教学(包括语文教学)究竟是师生真实的互动,还是教师公开表演?教育的真谛在于促进人的发展,教学中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原则,但是,因材施教恐怕是最为根本的一个原则。如果教师不熟悉自己的教育对象,教师凭什么展开自己的教学?如果教学只是一方“主导”,另一方“配合”,“教学”还存在什么“教育”的意义?现代教育学奠基人赫尔巴特曾说,“我得立刻承认,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样。”也就是说,“教育”必然蕴含于“教学”之中,而真正的“教学”必然具有“教育”的意蕴。“借班上课”等做法,其致命弱点在于把教师“高超”的知识传授技能,“了无痕迹”的控制课堂秩序的技能,流畅的表演技能当做“教学”,而把“学生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在新课程理念下追求的“促进学生主动发展”丢到了一边。说得刻薄一些,这样的所谓“公开教学”,也许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教育”了。《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重要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方智范教授认为,“语文之‘本’,我们认为首先要树立一个观念,也就是人本。对于语文课程来说,首要的是人,即学生。”
从上述分析可知,台湾同仁的观点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在借班上课的“无奈”之下,苏兰老师的一个“小动作”,不但新颖别致,而且未必不透露出她的教育观念。这两堂课上,苏老师给每一位学生佩戴一枚印有学生姓名的胸卡,上课伊始,她花费六七分钟,认识每一位学生,让学生简单地介绍自己。在每一位学生介绍完之后,苏老师都不厌其烦地问候一句“某某(某某,即某同学的“名”)同学,你好!”这种小小的设计,不仅为后来教学中师生互动,教师直呼其名提供方便,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教师没有仅仅把学生当作自己“公开教学”的配角,而是自己合作的伙伴。这其中蕴含的教育理念,可能就是在苏老师看来,这节研讨课不仅是师生之间要完成“公开教学”这样一件“事”,更同时是在培育眼前这三十几位“人”。
小小的安排,在笔者看来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现代诗人何其芳的《生活是多么宽广》是这两节课教学的内容,但是,在苏老师的课上,这首诗似乎只是一个由头、一个起点,两节课教学由诗歌展开,但很快就进入学生联想、仿写和各自独特的体验表达。每位学生口头表达自己“仿写”的作品,成为两节课的主轴。这与我们常见的教师一言堂,或者教师“提问”、学生“填空”的问答模式,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但恰恰是这一不同,透露出苏老师要把学生推到前台,把“教”的精彩,努力推向教“学”达到的实效,从中体现出其符合当代世界教学改革的基本趋势。事实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谈论“以学生的发展为主”,但是,如果长期把学生置于“受众”位置,学生的主体性必然受到压制,不论是教师独占课堂的一言堂,还是教师早就安排了“脚本”,导演学生的表演,学生总被教师紧紧地控制着,学生的个性在这种控制中被钳制,学生的创造力在这种控制中泯灭。苏老师的教学让我们看到了海峡对岸的同仁与我们不一样的努力,看出他们开辟出的不一样的小学语文教学境界。
当然,教学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师问题,教师背后的课程文化、学校制度,乃至更为宽广的社会环境无不影响、甚至制约着教师课堂教学行为。但是,教师并非没有自己的创造空间,新课程也并非没有为课堂教学提供必要的庇护,教师的“欲为”毕竟是教师“能为”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教师没有这样的觉醒、意愿,当然就谈不上创造出这种“境界”的可能。这是苏老师的给笔者的第二个启发。
第三个启示也许更不同寻常。经过一段时间教师学生围绕文本活动之后,还有十来位学生没能或没敢及时表达自己的体验。苏老师请这些同学站起来。也许是怕两岸教师交流存在着一些障碍,教学进行中,苏老师中断了教学,直接对着台下五六百名听课教师表白起来。她说,“这些到现在还没有表达意见的孩子,就是最需要我帮助的孩子。我一定要帮他们走过这一关,一个也不能放过。”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这一理念,自新课程实施以来已经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是,挂在口头的未必就挂在心上。的确,在课堂教学中把“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这样较真地付诸实施,在我们的课堂似乎并不多见。苏老师作为台湾“特殊优良教师”“语文卓越教师”,的确并非徒有虚名,也的确给我们深刻的警示。愿我们能从中读出教育的真正意义和不同凡响的教育者的“大爱”。
把引发与保护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作为教学重要的考量,这是苏老师这两节课给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的确,大陆语文教学由于受到过度的考试压力制约、现行教育管理制度及教师素质等影响,教科书始终在教学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允地说,语文教学重视教科书的作用并不是什么过错,反而是语文教学的题中之意。但是,我们语文教学在统考制度规范下,尤其是在“教什么考什么”的现行考试试卷下,“用教材教”替代“教教材”的梦想始终还停留在一个悠悠忽忽的难以把握的梦境中,落不到实处。但苏老师却如天马行空,教学中,由何其芳奔向梅兰芳,甚至带出孟小冬;从诗歌到戏剧、到电影;从现代、从时尚,到历史、到前后赤壁。仿佛就是转轮盘,变魔方。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兴致盎然,流连忘返。如何在新课程实施中真正落实“用教材教”,苏老师的课未必不能给我们一些新思路、新启示。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真能把苏老师这两节课真正当作研讨课,对苏老师执教的这两节课,的确也有我们的思考。
首先是苏老师提供的教学设计方案,方案中“教学目标”的设计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对象。一般而言,教学目标就是对教学结果的预期,它应该比较具体,这样既利于指导教学活动,又利于检查教学活动的效果。可是苏老师提供的这两节课的“教学目标”却是“深度阅读——倾听、观察、思考、感悟、表达、应用”。但是,从专业的角度看,苏老师列出的这几项,只是学生学习行为方式,并不是学生通过教学之后要达到的行为、情感、态度变化的程度,用这些表述作为课堂教学目标用语,似乎未必合适,教学中也无法把握。
思考之二。苏老师的这两节课,固然没有受到“教教材”的约束,但又似乎把教材赶到一个过于冷清的角落。这是否就是后来赵镜中博士所说的“教课文”与“教阅读”的区别。我们没有机会与苏老师本人讨论,也没有与赵博士直接交流。但是,听过赵镜中博士的报告,我们却认为“教课文”与“教阅读”不但在学理上不能形成相对立的两面,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也不应该被处理成势不两立的两面。事实上,大陆新课程实施以来,停用教学大纲,采用课程标准,就是要改变“指定”中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既往方式,力求在课程内容(包括教科书中的课文)选择上赋予地方、学校与教师更大的自主权。说白了,也就是要废除“为教课文而教课文”的局面。但是,在新课程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之下,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各学段目标规范之下,起码在大陆现实师资水平和教育管理的基本结构之下,台湾同仁的做法虽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视角,但毕竟不是我们可以简单搬用的模式。
两岸同仁的交流,不论在教育教学理念,还是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彼此的差异正提供了彼此转换视角思考自己“习以为常的观念、行为”的机会,也为我们取得可能的进步提供了机会,但这些都需要我们真诚的“研讨”,而非只是热热闹闹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