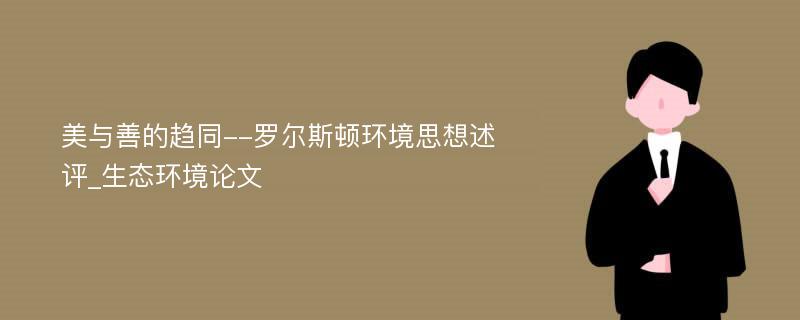
美与善的汇通——罗尔斯顿环境思想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通论文,思想论文,环境论文,罗尔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国际上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思想已被国人所知。但是,在对罗尔斯顿有关著作的研究上,国人往往因为过于关注他的伦理思想而忽略了他的美学情结——《哲学走向荒野》以对环境的体验与欣赏结束全文,《环境伦理学》以诗意地栖息于地球结尾,在《从美到责任:自然的美学与环境伦理学》一文中,他甚至提出了美学走向荒野的观念。国人研究中的这种忽略导致了目前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种偏颇,那就是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很少关涉环境美学问题,或者说环境伦理学研究者们在探讨环境问题时极少将环境美与环境善结合起来。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认为,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罗尔斯顿的环境美学思想与其环境伦理学思想也紧密相连,环境美学甚至可以成为环境伦理思想的基础。忽略罗尔斯顿的审美情怀不仅使我们不能全面地把握其思想,而且也会导致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盲点。
无论是环境美学观,还是环境伦理思想,罗尔斯顿均将其立足于自然价值论,其环境伦理观和环境美学思想,也均以整体和谐为旨归。稳定、和谐、健康不仅是“环境善”的评判标准,而且也是构成“环境美”的前提条件。“环境美”与“环境善”的动因不是主体的一种赋予,而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创化能力。在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中,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美与善的相通性。我们甚至可以说,罗尔斯顿的环境思想是对美、善相亲关系的再一次说明。
一、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自然价值论
罗尔斯顿认为,美与善的相通性首先表现在它们拥有共同的哲学基础:自然价值论。
在传统价值观看来,价值就是指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人是价值的主体,是评价价值性质的唯一尺度,离开人这个特定的利益主体,是无所谓价值的。正如有人指出,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相对于人的意义而言的。立足于此类价值观念,许多理论家否认自然价值一说,即使勉强承认自然价值的概念,也仅仅是在工具性意义上说的。如佩里认为自然事物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它能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价值是“欲望的函数”。詹姆斯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没有意义色彩,没有价值特征。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只不过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寂静的沙漠没有价值,直到某些跋涉者发现了它的孤寂和可怕;大瀑布,直到某些爱好者发现了它的伟大,或者它被利用来满足人的需要时,才具有价值。自然界的事物,直到人们发现了它们的用途时才有价值,而且,它们的价值,根据人对它们需要的程度,可以提高到相应的高度。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了价值。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建立在对上述价值观的反拨上的。在罗尔斯顿看来,将人视为价值唯一尺度的做法过于武断,是属于主观主义的价值论。这种价值论由于完全否认了价值评价与价值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自然物的价值理解成了完全由人的兴趣和欲望来随心所欲捏塑的泥团,使对自然价值的认定完全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之中。
罗尔斯顿认为,人类可以体验自然所承载的各种价值,但价值却不是主观的一种臆想。价值就是自然物身上所具有的那些创造性属性,是进化的生态系统内在具有的属性。也就是说,主体与客体的结合导致了价值的诞生,自然价值是存在于自然中的那些价值的反映。价值的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评价的内容却是客观的。罗尔斯顿把自然价值分为13种:支撑生命的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娱乐价值、基因多样性的价值、自然史和文化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性格培养价值、治疗价值、辨证的价值、自然界稳定和开放的价值、尊重生命的价值、科学和宗教的价值。这些价值大致分为两类: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工具价值是指自然界对人的价值;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及其存在物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前者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价值,后者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自然价值。面对自然,我们既不能仅从人的角度来评价,也不能仅从自然的角度来评价。因为有些自然价值的发现离不开人,而有些自然价值的存在是非人类中心、非人类来源的。
立足于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充满生机的进化和生态运动,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并非不好意义上的“荒野”,也不是堕落的,更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她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自然的价值(善)可以表现为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即表现出工具性的价值,但另一方面自然也有其自身的目的,即自身的善。每一种有机体都有属于其物种的善,它把自己当做一个好的物种来加以维护。一个有机体所追求的那种属于它自己的“善”,并不是以人的利益为唯一标尺的。花绽放、鸟飞翔、狼逐兔,自然善存在于自然中,我们不能因为狼或荨麻草都力图维护它们自己的“善”,就说它们是恶的。
立足于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认为,审美价值也不是主观的偏好。自然中的美是关联性的,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人类点燃了美之火,正如他们点燃了道德之火一样。“没有我们,森林甚至不是绿色,更不用说美了。”“人类到来时,美被点燃了。在被评价的和有价值的森林、盆地湖、山脉、美洲杉或沙丘鹤中并不自动地存在美,美伴随着主体的出现而产生。”[1] 另一方面高山悬崖周围飘浮的薄雾、漫天飞舞的雪花、细小别致的水晶确实能增添登山者的审美体验。如果它们消失了,登山者的审美体验就会减弱,可见,自然的审美价值不可能离开具有审美属性的事物而存在。没有鲜花,对花的审美体验就成了无源之水。虽然对花的欣赏建构了花的审美价值,但是鲜花的审美价值仍然是客观地附丽在绽放于草丛中的鲜花身上的。
罗尔斯顿对自然美的把握类似于杜夫海纳对艺术美的理解。一方面,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是审美地被知觉的客体,亦即作为审美物被知觉的客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审美对象一直就存在在那里,只等待我前去感知、欣赏。它像物那样顽强地呈现出来。它为了我存在在那里,但又像不存在在那里。审美对象不规定我去做任何事情,但要我去感知,即把我自己向感性开放。因为审美对象首先就是感性的不可抗拒的出色的呈现。废墟之所以仍是审美对象,是因为废墟的石头仍是石头,即使磨损变旧,它也表现出石头的本质。因此,审美对象就是辉煌地呈现的感性。我们除了去感知以外,没有其他办法[2](P114—116)。
在对自然善与自然美的把握中,罗尔斯顿立足于自然价值论,一方面将自然善、自然美与主体相联,另一方面又将对自然善、自然美的把握与自然本身联系起来。通过把价值从人们的主观体验延伸到自然的客观生命中,达到美、善把握上的对主观论和客观论的超越。
二、善与美的前提:健康的生态环境
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不仅关注自然的价值、自然善的问题,而且也重视自然的审美价值、自然美的问题。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罗尔斯顿不仅在自然所承载的价值中提到自然的审美价值,而且还对自然的审美评价提出独到的见解。可以说,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包含着对环境美的思考,并且在他那里,自然善与自然美有着共同的前提:健康的生态环境。
在罗尔斯顿眼里,自然不应理解为僵死的物质实体即物理学意义上的对象。自然与生长相关,如一个橡子的“自然”(性质)就是要长成为一棵橡树。虽然一个橡子自身有长成一棵橡树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但是它能不能实现这个潜能,则与外部环境相关。也就是说橡子的生长的状态如何与其生长的环境相关,自然要实现它的善和美也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关。在罗尔斯顿看来,健康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环境: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水源丰富、物种多样,并且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这种健康的生态环境中,自然的善与自然的美才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健康”的生态环境与自然“善”、自然“美”相关呢?
其一,从文字学上看,据竺原仲二考证,“健”与“壮”同义,“健”有“高壮”之意,“高壮”貌被认为是“善”(美)。“康”可训为“美”。可见,“健康”是一个与善、美相联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健康的事物的姿态中得到美的感受,人们往往也认为具有健康姿态的事物就是善的事物、美的事物。同样,“健康”的生态环境由于各种物种健康发展、生态系统健康运行而显现出勃勃生机,大自然所承载的各种价值才得以实现出来。
其二,从显现的角度看,自然事物都有美与善的趋向,自然事物的生长过程,就是美与善的显现过程。自然善的显现离不开健康的生态环境。不管是工具性的自然善,还是自然本身的善,其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健康的生态环境。狮子的生态环境是广袤的原野和适当的食物链。当狮子的生活领地被无限制地缩小、食物链条被人为破坏后,狮子的价值表达能力就会受到影响。狭隘的功利态度,往往使人们在满足自身的欲望时破坏了物种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自然善的发挥。如阔叶林的生长期比针叶林的生长期长,人们为了木材生产的需要往往把阔叶林地带改变为针叶林。针叶林虽然可以带来较快的经济效益,比如用来生产纸浆和新闻纸,但是原有的阔叶林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果实并形成了有序的食物链。如果把阔叶林移走,就会损害原有的野生动物种群的利益。如果原有生物种群的生存都受到影响,那它们又怎么能显现出自身的善呢?
同样,自然美的显现也离不开健康的生态环境。首先,自然物有属于自身的小环境。如雁排长空、驼走大漠、鱼游潭底、虎啸深渊……只有在适合于它的、健康的小环境中,自然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其次,自然美即自然环境美,它是整体性的美。醉翁亭的环境是美的,这种美不仅依存于优美的林壑与秀丽的诸峰、野花的芳香与鸟儿的鸣叫,而且依存于清澈的酿泉、肥美的鱼和甜美的山肴。正如王维在《山水论》中所说:“山藉树而为衣,树藉山而为骨。树不可繁,要见山之秀丽;山不可乱,须显树之精神。”山因树而显“秀丽”,树因山而显“精神”。山的美离不开茂盛的草木、清澈的泉水。在利奥波德眼里,埃斯库迪拉山与黑熊之间是不可分离的。当黑熊统治着埃斯库迪拉山时,山是美的;当人类消灭了黑熊,埃斯库迪拉山就失去它的灵魂,变得不再神圣,它的审美价值也大打折扣。
三、环境善与环境美的标尺:整体和谐
罗尔斯顿的环境保护主张不同于动物权利论者和动物解放论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关注动植物的价值与利益,而且也关注人类的生存与权利。面对自然,罗尔斯顿强调自然的法则,面对人类社会,罗尔斯顿强调文化的力量,并力图将二者统一起来。罗尔斯顿寻找自然价值不仅为自然环境的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能随意虐杀动物),而且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理论说明(人类为了生存必须要吃掉一部分动物)。罗尔斯顿不仅强调个体的价值,而且也强调系统的价值,系统价值在罗尔斯顿这里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通过对罗尔斯顿有关环境思想的梳理,我们发现,整体的和谐在他这里得到强调,并且这种强调源于对利奥波德思想的继承:一件事情,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它才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在罗尔斯顿看来,整体和谐不仅是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而且也是环境美与环境善的标尺。罗尔斯顿有关整体和谐的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共生
通过观察与聆听,罗尔斯顿发现,“共生”是万物生存选择的一种结果。共生不仅包括自然物种间的共生,而且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人的共生。
其一,人与人的共生。人与人的共生是和谐环境的关键。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之间的不和谐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使环境美、环境善成为不可能。据有关资料统计,造成环境破坏的最大力量是战争,如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大火极为严重地污染了中东地区的环境。
其二,物种间的共生。虽然物种都有追求与维护自身善的本能,但物种的生存都是通过共生而得以繁衍至今的。狼力图维护自身的善,鹿力图维护自身的善,它们都是拥有自身的“善”的有机体。狼与鹿之间既存在竞争,也存在共生之处。狼过多,鹿群就难以生存下来;反之,没有狼,鹿就会泛滥成灾以至威胁到自身的生存。狼与鹿在追逐与逃避中得以生存。有些植物为了生存能够以减少竞争的方式来达到相互适应,如植物生长的时间和开花的时间错开,植物对阳光、温度和土壤环境的适应力各不相同,不同的动物食用不同的食物或以前后相继的方式使用同一食物资源等等。个体的善应符合系统的善。“事实上,具有扩张能力的生物个体虽然推动着生态系统,但生态系统却限制着生物个体的这种扩张行为;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足够的但却是受到限制的生存空间。系统从更高的组织层面来限制有机体,系统强迫个体相互合作,并使所有的个体都密不可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3](P221)
其三,人与自然的共生。不仅自然物种在竞争中学会共生,人与自然也是这样。人体内的细菌种类众多,但很多细菌是有益于人体的。在帮助人类消化食物的过程中,这些细菌得以生存下来。即使是那些引起疾病的细菌,也确实拥有它们自己的“善”,而且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但是“一个好的(强壮的)癌细胞不是某种好的物种。……癌细胞不属于任何自然物种,它只是一个失去控制的好细胞,一种不适应人的身体的细胞。而且,在多细胞有机体那里,细胞的善对整体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物种的内在善不仅出现在物种层面,也出现在有机体层面。从细胞或个体的观点看,一个好的癌细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一个旺盛生长的癌细胞是在走向自身的灭亡。”[3](P141) 同样,一个只知道把自然视为征服对象、只能从经济的角度来利用大自然的人类,也只是一个强调个体善的物种,并最终会造成系统善的丧失而自食其果。
罗尔斯顿认为,和谐的环境有赖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物种之间的共生,而且认为和谐的环境有赖于个体善对系统善的臣服。
(二)动态变化
共生是物种间相互适应的结果,它包括选择与被选择、淘汰与被淘汰的过程。与共生相比,罗尔斯顿更强调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生生不息的冲突过程。他认为,生态系统须依赖竞争才能兴旺繁荣起来。
通过选择与竞争,有机体都能很好地适应它们生存于其中的小环境,并各自追求自身的善。但是,生态系统中,各种不同的善总是以互相补充、彼此交换的方式永不停息地相互竞争着。美洲狮在追求自身善的过程中消除了有疾病的鹿,快速敏捷的鹿在追求自身善的过程中剔除了体弱迟钝的美洲狮。衣原体微生物在追求自身善的过程中导致了黄石公园的加拿大盘羊角膜炎,红眼病的流行使加拿大盘羊的数量减少,但却使金雕的数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因为大量的盘羊尸体满足了金雕这一物种的生存需要。云杉芽虫在追求善的过程中造成了对森林的毁坏,但是它的数量却在短尾刺嘴莺追求自身善的过程中被大量削减。一种物种的善被其他物种的善代替。
也就是说,和谐的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和谐环境的实现是在动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物种之间“善”的交替,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替表现为美丑的转化。
罗尔斯顿认为,在生态过程中,丑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在生态系统那里,丑不再丑陋。自然中存在着丑,但是,还存在着把丑转化为美的恒常的转化力量,存在着以熵为代表的破坏性的力量,也存在着与之抗衡的以负熵为代表的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当消极性的力量暂时胜过积极性的力量时,大自然中就会出现局部的丑。所有的生命或早或晚都将毁灭。但是,个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衰老生命的毁灭,常常导致年轻生命的复兴。无序和衰朽是创造的序曲,而永不停息的重新创造将带来更高级的美。也就是说,丑虽然不时地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并不是大自然的全相。我们不仅看到丑在空间上的当下展开,还看到美在时间上的延续。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它一定能从丑中创造出美来。某个丑的自然物,如果在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它的丑就结出了甜美的果实(尽管丑并未消失),而且,它还对生态系统的美和后来产生的个体(不管是同种还是其他物种的)的美做出了贡献。如此看来,哪怕是力量凶猛的溶流和海啸,也不能说不具有美感特征(尽管对生命来说它们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因为,在灾难过后,植物和动物群落都会尽力重新繁荣,而在它们的这种再繁殖的努力中就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美。生命死而复生,美逝去还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生命的死亡,只要把它视为生命再生的序曲,就不再像人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丑了[3](P330)。
正是立足于这种动态变化的伦理观与审美观,罗尔斯顿一方面反对物种的“非善即恶”的二分观念,另一方面也反对“自然全美”或“自然全丑”的独断论。环境的美与善均来自于环境中各物种的相互争斗与相互适应。
收稿日期:2007—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