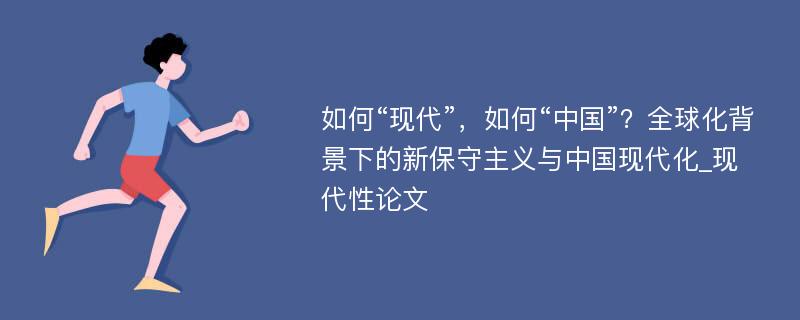
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保守主义论文,语境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1-0068-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症候之一,是回归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热情开始高涨。抑或如有的学者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地形图所作的概括,以回归传统文化为旨归的“新保守主义”,成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外的第三种社会思潮①。这种“新保守主义”,是艾恺所关注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一种表征。它关涉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一、“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1990年代出现的回归文化传统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实际上正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1980年代末的苏东巨变,一个所谓的“历史终结”时代已然来临。在西方学者看来,“历史的终结”并非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结束,而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色之后,一个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的终结,而一个人类向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世界已经一统天下。“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②。“历史的终结”宣告的其实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终结。在坚信西方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为唯一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同时,同样来自美国的学者宣告:“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至少我们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的开始,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因素。”③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貌似宣告冷战时代的终结,但是其浓郁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却是露骨的。“历史的终结”俨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了失败者“被淘汰”的“历史”。它再次证明了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陈词滥调。也正是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中,社会主义与极权、暴政乃至法西斯主义划上等号。“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被放大为血腥、暴力、杀戮和非理性。于是,在“历史终结”的背后,被否定、被无视乃至被宣判死刑的是曾经在极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所容纳的极为丰富的意义,是人类探索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的终结”遥相呼应的还有对革命和左翼社会运动的祛魅。在“历史终结”之处,回望历史得出的结论却是“告别革命”和寻找被革命压抑的“人性”,抑或是被革命压抑的“现代性”。“文明的冲突”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实际上也意味着一段冷战时代历史的终结。在战争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引发的宏大叙事的帷幕之后,悄然被掩盖的是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铁血定律在今日“民主、自由”大旗下推行的战争中难以推脱的责任。文化冲突论遮蔽了在今日世界日益突出的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性别压抑、种族变相歧视等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多持批判态度。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等论调实际上是以美国学术理论为参照,即以一种强势的西方话语方式参与后冷战思维构造所得出的结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后冷战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大陆学术界。
在“告别革命”的姿态下,重新回到中国的本土文化、回到传统之中成为了某种应然的选择。一批1980年代“新启蒙”的著名人物,纷纷从1980年代对“五四”精神的承续、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五四”精神的反思、批判与对传统文化的同情、理解乃至推崇。在这方面,甘阳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在回顾自己思想的转变时,他明确地意识到:“从我个人来说,1985年——1986年是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就是反传统’的阶段,但1987年——1988年已经不同,我1987年发表的《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着重强调西方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而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已经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明确为‘文化保守主义’辩护。”④ 曾经在1980年代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李泽厚,在1990年代也发出“新儒学的隔世回响”,并从最广义的角度指出“儒学是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行为、生活、思想感情的某种定式、模式”,即所谓的“活着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儒家最重要的是这个深层结构”⑤。也正是从1990年代开始,对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镜像的呼唤变得极为炽热。在所谓“新儒学”、“国学”的勃兴中,再加上港台乃至海外新儒家们的推波助澜,对传统的倾慕逐渐衍变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文化思潮——新保守主义。
以回归传统文化为旨归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告别革命”和“回归传统”的姿态下,“着手全盘反省本世纪(20世纪——笔者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由此抽绎出反激进主义的命题(思想纲领)——它不仅仅只具有学理的意义,同时也有更广泛的文化象征意义”⑥,于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思,便不再仅仅只是对“革命”的“告别”,而成为对历史的一种重新书写。20世纪的中国历史被书写成贯穿了一条有主线、有问题的“历史”,而这条主线、这个问题则是“激进主义”。“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激进主义在三次文化批判运动中达到的高潮,其规模之宏大与影响之深刻,是20世纪儒学重构运动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激进主义的口号远远压过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⑦,尤其是在1980年代还被整个中国知识界视作现代化思想资源的“五四”,转瞬之间成了孕育激进主义的摇篮。在一些人的眼中,“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诸如“打倒孔家店”——俨然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罪恶之源,它的所谓“全盘反传统”即使不是数典忘祖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背叛,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无限扩大,陷入极端的偏执,乃至无情的破坏主义,而这一切似乎正可以为半个世纪之后引发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付账买单。“五四”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似乎不仅没有得到清理,反而又延伸出更为严酷的“国民劣根性”。在这样的历史反思视野中,曾经被视若神明的“五四”启蒙精神最终被无情而又酣畅淋漓地瓦解了。
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反思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五四”与“五四”的启蒙精神也并不是不可以批判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展开对历史的省察与批判。“五四”是不是仅仅只有充满所谓的罪孽的“激进主义”?我们对历史的再解读,在充满后见之明的快感时,是不是恰恰遮蔽了历史本身的斑斓与驳杂?即使退一步而言,“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所引发的激进主义充满了非理性与破坏性等诸多弊端,是不是这种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失去了在当时所应有的(积极的)意义与(合理的)价值?这还牵涉到,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想象”(或者理解)“历史”?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是将其抽离复杂的历史语境而观之,还是应该将其重新置入充满问题的历史网络中打量?显然,将“五四”的激进主义无限放大,已经违背了历史反思的精神,更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学理态度。貌似的反省与批判已经变为抽离具体历史语境的上纲上线的大批判。
问题不应该仅仅到此为止。一方面,对历史的反思是以对历史的再解读与重写的形式践行的,但是这种以“告别革命”与“反思激进主义”的姿态对历史的再解读与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显然包含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告别与反思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重建新意识形态的过程。这个新意识形态的核心色彩就是重归文化传统。但是,到底这个文化传统抑或传统文化是什么,却又语焉不详。似乎它可以不言自明地存在,却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并非铁板一块,并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儒学”与“国学”。其内部的复杂与矛盾,历史演变的千回百转,良莠的交叠与耦合,都不是简单而热切的“回归”就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告别革命”与“反思激进主义”以貌似反思的姿态施行的却是拒绝对历史的反思。毋宁说,当它们对革命式的激进主义与激进主义式的革命大肆挞伐时,本身就是一种颇为“激进主义”的姿态。颇为吊诡的是,它们本身的批判立场与姿态实际上不仅仅没有颠覆原有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反而更为牢固抑或是建构了诸如“革命”与“人性”、“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中西”、“古今”等二元对立的权力等级结构。
二、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
19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实际上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一个命题密切相关。韦伯在分析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发现,新教伦理(主要是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这项世俗事业即追求财富——笔者注)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新教伦理“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⑧。于是,新教伦理催生出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便成了一个经典的韦伯命题。不过,当韦伯分析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时,却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儒家文化所产生的内在阻力没有形成特定的经济伦理。
极为吊诡的是,当韦伯命题作为一种西方理论旅行到中国时,它一再地被借用,同时却又被颠覆。与韦伯命题密切相关的是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的想象。在一些学者看来,尽管东亚地区在“国民性格、文化性格方面仍有差别”,但是“在器物、制度、精神文化等方面确实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素质,以至仍然有理由把东亚看成一文化的共同体(文化圈)”⑨。维系这个东亚共同体的文化被想象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指认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⑩,即将中国的地方经验普世化为亚洲经验甚至世界普遍经验,使儒家文化“突破跨越地方局限的问题意识,建立它的普世性”(11)。另一个一再被提及的事实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及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以及1990年代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大陆共同营造出了东亚地区经济繁荣的景观。于是,韦伯命题——文化形成经济伦理然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被借用为: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源自该地区的文化共同体,即儒家文化。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被认为得力于儒家文化所产生的经济伦理。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以经济腾飞为标志的现代化的成功被视为“儒教资本主义”的胜利。于是,韦伯命题中的另外一部分,即中国的儒教伦理阻碍中国形成经济伦理的结论被颠覆乃至改写。“通过把儒教与资本主义挂钩,中国的传统不再是阻碍现代化的历史负担,而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动力”,“儒教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作用如同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对于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作用一样”(12)。正是儒家伦理被解读为在整个东亚经济腾飞中起到了如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建构抑或对其意义的重新发掘与塑造便成了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新保守主义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便不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
在对韦伯命题的借用与改写之中,被忽视的是所谓的东亚共同体内部存在的文化差异,东亚各国经济腾飞的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内在与外在原因,乃至它们对儒家文化的实际接受与具体转化的复杂性。将东亚地区想象成一个以中国的儒家文化维系的共同体,此间可能隐含的文化霸权也并未为中国知识者所检省。
韦伯命题的中国之旅以及亚洲之旅,实际上还牵涉到有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团结在启蒙大旗下的中国知识界,“直接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思想的灵感,它把对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理解为对于传统和封建主义的批判”,那么,“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别有意味的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结果是:“把对中国现代性(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反思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13) 那么1990年代伴随韦伯命题的旅行而来的“儒教资本主义”,以貌似皈依传统本位来反省批判1980年代的唯西方为是的“中国现代性”,以“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历史观重新发掘中国历史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它“仍然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西方价值的拒斥,‘儒教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一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形态的彻底肯定,只是多了一层文化民族主义的标记”。
1990年代对1980年代的反省和批判变成了与批判对象的殊途同归。重新回归中国传统——“古”——以对抗“西(方)”的姿态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或者是重新塑造关于“中(国)”的独特性,恰恰又重新落入了“西(方)”的陷阱。表面上是对西方普世化模式的反思和质疑,实际上却变成了对西方普世化模式的佐证。
三、后现代与全球化
西方学术背景中的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为了宣告“现代性的终结”这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在西方的出现传达出西方学术界对自身的质疑与反省、检讨与批判。后现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反省和批判现代性。作为欧美学术界内部对自我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理论话语,后现代所针对的主要是现代性引发的诸多恶果。同时也是西方学术界“站在边缘的文化立场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所作的批判”。当这样一种理论旅行到中国来的时候,虽然在身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呈现出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姿态,但转瞬间又演变成对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乃至学术的自主性的追求。或者“强调‘从中国自身发现历史’”,在中国历史内部寻找一条自身生发、演变而成的现代性链条。或者以“中华性”来重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14)。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之内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对身处第三世界的中国大陆学者来说,批判现代性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显得极其必要。但是,是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就一定意味着对自己本土/传统文化的皈依?或者说,当我们为了批判西方现代性而选择本土文化时,是不是就可以真正地摆脱西方(现代性)的梦魇?当站在边缘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化的边缘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成为欧美学术界进行自我批判的话语方式时,置身在第三世界文化的边缘立场的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再次彰显出我们与前者不同的立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可能在于,当我们重归本土文化的传统,以突出第三世界民族文化属性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文化霸权时,采用的也许正是西方的话语方式,那正是“无法摆脱的西方思想资源和西方视点”。
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另一个语境是全球化。曾几何时受到人们欢呼雀跃的地球村,眨眼之间给我们带来了文化灾难,原本多姿多彩/文化多元主义的世界日渐变成趋向同质化的、单一化的世界。多元文化的逝去成为全球化/现代性的恶果之一。于是,在警惕全球化的陷阱的时候,更为本土、也更为传统的文化价值得以凸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捍卫(民族)文化价值的独立性成为最富激情的论辩领域”(15)。中国甚至世界出现的诸多问题,诸如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道德堕落,文化危机等等,都成为全球化现代性的不二罪证。因而,回归传统文化,就不仅仅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的重建,还会在中西之间重新确立优劣的价值等级。在艾恺看来,非西方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策略正在于,“倾向于将其本国的文化认作肩负着为人类全体带来救赎及改善的历史任务,通常这种理论是以向西方提供其救赎的方式出现的,也就是要将西方从自身挖掘的陷阱之中拯救出来”(16)。在与后现代主义反省的合谋中,1990年代以来中国新保守主义思潮显然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救世主的姿态。“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似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的中国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17)。“在目前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18)。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被无限放大的危险性在于,一方面,关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这样一个牵涉到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问题被简单化为温情的救赎故事:一个传统中国(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抑或是中国传统文化)救赎西方/世界危机的情节剧,在这出貌似温馨的关于东方/中国拯救西方/世界的危机的情节剧中,所有的问题只能被想象性地解决;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被赋予拯救者的角色之时,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特殊的中国现代性被乐观地建构了起来。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不仅仅是中国学者/中国人乐观抑或是民族主义的激情投射,而且还再次建立起一个关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结构。在这个充斥着等级观念的对立结构中,本土的传统文化,在危机四伏的西方现代性面前有着不言自明的优越性。颇有意思的是,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中国的特殊性的建构只不过是为了达到将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的目的。显然,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东方文化中的传统价值从地方性经验提升到世界性/全球化的普世理念的高度,那种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诉求,在强化“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时,已经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变成对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的论证。中国在貌似批判和反思全球化/(西方)现代性的背后却是对反思和批判的再次婉然甚至决然的拒绝。
也是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属性再次变成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身份。皈依文化传统不仅仅只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么简单。当西方学术界以重新反省现代性而青睐边缘文化时,无疑隐含着从他者之处寻找不同的现代性发展方向的企图。在西方学者看来,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真正显示出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意义。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成为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彰显自我身份的彩妆华服。此间的微妙之处却别有意味。回归本土文化的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自我身份得到确认,但最有分量的确认显然来自西方的目光。因为正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西方才从第三世界特有而古老的彩妆华服中认定了他者的存在。由于得到了西方的肯定,那些回归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容易获得来自西方的请柬,在所谓的世界学术圈中亮相登场,从而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上凸显出不同的他者来。只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想听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以便来印证他们对东方/中国这一他者的想象?我们又该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来印证我们的身份,以获得西方的再次认可?当我们迎合西方期待的目光,讲述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古老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宛如那只笨大的鸵鸟将脑袋扎进泥沙深处,对中国的当下/现实问题(显然也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置之身后而不顾?问题的悲剧性也许不仅仅是我们身陷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牢笼而不知,还有我们对我们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的忽视、无视、漠视乃至逃避。
注释:
① 许纪霖:《谈当代中国的三种社会思潮》,《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
②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④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⑤ 李泽厚:《新儒学的隔世回响》,《天涯》1997年第1期。
⑥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1994年第1期。
⑦ 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
⑧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彭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63页。
⑨ 陈来:《儒家思想与现代东亚世界》,《东方》1994年第3期。
⑩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期。
(11) 黄万胜、李泽厚、陈来:《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
(12)(13)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14)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5) 杜维明、黄万胜:《启蒙的反思》,《开放时代》2005年第3期。
(16)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17) 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东方》1994年第5期。
(18) 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东方》1993年第1期。
标签:现代性论文; 韦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激进主义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方论文; 开放时代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