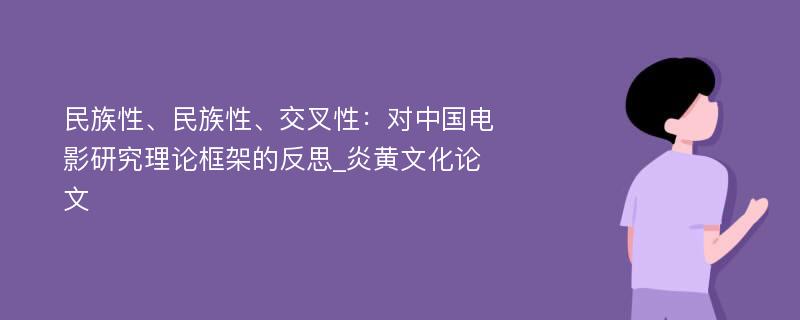
民族、国家与跨地性:反思中国电影研究中的理论架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架构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3-001-09
当前“中国电影研究”在理论架构方面究竟处于何种现状?该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理论”(theory)的概念很模糊。“理论”习惯性地被等同于“西方理论”,包括符号学、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有与性别、种族、阶级相关的诸多理论。①过去30年的中国电影研究以西方理论为圭臬,因此落入窘境。一方面,海外学者在分析当代中国电影时,极少采用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②另一方面,国内基于中国艺术观的电影研究则相反,走向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典型的例子是刻意强调中国电影的“中国性”,视之为民族文化内蕴的本质特征。③
而在刻意突显民族性的研究视域中,中国电影不过是民族构建的手段而已,最终为文化保护和文化承传服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电影在国内备受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青睐,在西方学界却不入法眼,其道理很简单,评价的理论与标准是西方的。④与此相反的努力同样费力不讨好,国内一些电影制作者鉴于国际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试图在电影中展现某些定型的“文化标识”,用来满足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式的期待和凝视,这样做招致更多非议,被斥之为迎合西方观众,兜售民族苦难等等。⑤
对中国电影研究中既有的理论架构予以反思之前,我们首先必须重新厘定“理论”的概念。这里的“理论”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代名词,而是涵括所有能帮助研究者针对各类电影和电影现象进行思考和表述的范式。“国族范式”(national cinema paradigm)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影响深远,它想象中国电影中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品质,热衷与其他国族电影进行比较,以彰显这种独有特质。然而,历史上中国电影内部充满了异质性和多元性,说它只具有几种共同特质纯属想象。所以本文的反思首在破除这一神话,⑥然后在分辨“国家”和“民族”这些标签之后,提倡超越某种简单的“跨国主义”的思维模式。
“跨国”(transnational)的正常规模应该在“国家之上,全球之下”,但所谓“跨国华语电影”的概念则强调“跨越国家、地缘政治和语言的界限”。⑦华语电影关涉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华裔聚居地,仅仅使用民族/国家的考察维度有很大局限。据此,本文提出“跨地性”的概念,用横向的“跨地”(translocality)取代纵向的“跨国”的思维框架。毕竟,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都发生在某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地点”,而不是在抽象的“国家”层面,尤其是在当前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
“跨地性”的概念契合阿尔法·德里克(Arif Dirlik)“立足地点的想象”(place-based imagination)的观点,它认为“全球化/地方化”(glocal)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表现为资本、观念、形象、风格和科技等在多地之间的流动。⑧如下文所述,这种流动不是单向的,因为“跨地”意味着不同地点的诸多模式之间进行多向度的博弈。以此观之,中国电影研究中用西方理论去套用中国电影,进行单向解读的做法理论上是不合适的。⑨总之,电影的生产和流通是多地的(polylocal)实践,中国电影研究在关注电影的跨地实践的同时,还需要把这种“跨地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延伸到学术研究中去。
“去中国性”的困境
从如何对待“理论”来看,电影研究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立场。第一种不妨称之为“唯理论”(protheory)立场,即认可一种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西方理论霸权,周蕾(Rey Chow)的研究典型反映了这一立场。作为华裔学者,她本身是西方学术界的“他者”,但她努力借助西方理论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第二种是以戴维·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和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为代表的“后理论”(post-theory)立场,他们反对“理论”高低的等级秩序和“理论在先”的研究态度,强调从经验出发。
周蕾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理论的时代”(或确切地说是“西方理论的时代”),[1]问题是,她本人的身份及研究对象却是非西方的。如何解决这一困境?请听其坦言:“西方理论赫然存在,非我掌控之内,但为了言说,我必须面对它!”[2]究竟如何面对?周蕾的策略是“执意”(perversely)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中国的叙事,挑战该领域的学术传统。”[2](Xii)她看来,这种学术传统源自专家把持的“汉学研究”(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尽管这两个学术领域都是西方学者开创的,但之所以遭致周的批评,是因为它们“生产出一个完全丧失了想象、欲望和矛盾情感的非西方。”[2](Xii-Xii)从所谓“经验事实”的“非西方”与“充满想象力”的“西方”这个二元对立出发,周蕾继续构建了几组其它的对立概念,如“东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批评”。她认为,“东方”和“文化研究”具有特殊性,根植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中并为其所累;而“西方”和“理论批评”具有普世性,是超然的,富于想象力和洞察力。毋庸置疑,她选择了后者。
周蕾在研究中由此出现一个模糊区或者说是盲点。因为她很少关注她研究对象的中文研究成果。⑩这种忽略或有意拒绝的原因之一,是她坚信,“对‘中国性’(Chineseness)习惯性迷恋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大中华主义,正是它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之间划出一条想象的边界”;换言之,“它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大中华沙文主义(sinochauvinism)”,“表现出法西斯的傲慢和自我膨胀”,“患有严重的大中华自我迷恋症和狂妄症”。[1](P5)周蕾后来还为1989年“六四事件”所触动,就“中国性”发表更激烈的看法:“劫后余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不过是幻象而已……因为,与生俱来的‘中国性’对于他们来说,从来就是一个‘他者’。更可怕的是,在特殊时刻,它成了知识分子遭致压迫和灾难的根源,此后人们只能力图幸存。”[3](P98)
周蕾用西方的理论细加检视,发现“中国”和“中国性”值得警惕。为了跨越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的界限,她在研究中用一种“执意”的解读方式“临时去除”(bracket)“中国性”,以便证明当代中国可以超越与那个“特殊的文化语境”的直接关联。[2]不唯她自己热衷于这种对“中国性”的“临时去除”,对其他学者与其不同的研究路径也大加挞伐。比如说,她认为白露(Tani Barlow)一篇题为《中国的妇女、国家与家庭》的论文“很值得批评”,因为它在中文拼音之后的英文副标题中加上了“中国”,所以“刻意强调研究对象的‘中国性’,表面上征引大量充满细节的文献和事实的求证方法,实际上阻拦了来自外部的批判与反思,从而削弱了本来可能更为激进的概念”,如“妇女”、“国家”等等。(11)
周蕾对“汉学”和“中国研究”注重细节的经验方法论极为不满,极力反对“中国”的民族/国家标志。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与其他用英文著述的华裔学者不同,她在前几本英文著作的封面上都要设计自己中文名字的印章。众所周知,印章源自中国传统艺术,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最具“中国性”的表征之一。周蕾虽然念念不忘告诫他人要“写在家国之外”(这是她一本英文书的书名),[3](P25)莫非她自己在无意识中早已“归顺”了某种大中华主义?更有意思的是,她执意从当代中国电影中发掘出“原始的情感”(primitive passions),这些包括现代意识、对死亡的敬畏、忧郁、自恋、反抗和忠诚等等的情感,之所以被周蕾认为是“原始”的,因为它们产生于某一具体的文化历史时刻,既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危机”。具体地说,“原始的情感”是一种对于已经失落的“原初的幻想”,因此必须“事后重建,即在‘后’的时间内臆造出一个‘先’”,在“充满想象的空间内”将“‘文化’与‘自然’这两种指意模式整合成矛盾体”。换言之,这些“原始的情感”被电影人和评论家制造成“中国的”,并作为中国的“原始的情感”在国际电影市场和学术界(包括周蕾的著作)中流通。反讽的是,周蕾一方面指责“中国性”是一种“民族性添加”(ethnic supplement),“最先在争取表述权力时产生”,因此常常在面对西方话语霸权中成为“受害者的逻辑”;[1](P3-4)另一方面在她试图通过理论跨越东西方的民族/国家的界限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重新陷入“民族性添加”的圈套。其著作的封面印章设计如此,“原始的情感”概念中的“中国”标志亦如此。
显然,要临时去除中国电影的民族标志并非易事。何况,在她自诩为“西方和东方的阅读政治之间”,周蕾自始至终定为西方,推崇“充满想象力的西方式解读”。不妨看一个细节,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的阅读政治》,副标题就特意把“西方”写在“东方”前面。她的策略是“在研究非西方作家和文本的时候,应该象对待西方作家和文本那样,追求在心灵体验、言语表述和理论把握上同样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具体来说,“应该采取这样的解读方式,即把非西方内涵的无意识、非理性和暴力的异质性元素发掘出来,如此一来,作为‘他者’,非西方就不再是如今经常被肤浅地认识的空洞、僵化和充满神话色彩的对应西方的概念。”[4]
周蕾近来把批判“中国性”的矛头从“原始的情感”中的非理性和暴力转向“温情的臆造”(sentimental fabulations),并将她这个新创的词定义为“一种趋于妥协和忍受压迫和不堪事物的心理倾向”。[5](P17-18)与“原始的情感”类同,周蕾的“温情的臆造”也蕴含着一些民族的标识,如忠孝、家族生活、贫穷等。她认为,温情主义的核心是理想化了的儒家伦理,这种主观臣服模式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忠孝之道被理想化为“坚忍”和“迁就”。[5](P18-22)然而,与过去热衷于临时去除“中国性”的态度不同,周蕾现在开始对香港、台湾和其他华裔社区的“中国”身份感兴趣,认为他们诉求“中国”的身份是正当的。此一立场的改变基于地缘政治的历史变化,如其所言:“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潮汹涌,与过去不同,它不是因为贫穷和被剥夺而激发的,而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势发展所推动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概念不应该自动地、在任何时候都被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使用。”[5](P24)
这些话听起来很动人,不过,当周蕾用几乎完全西方的言说方式来解读当代中国电影时,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她熟知西方理论的“游戏规则”,对此她毫不掩饰:“西方的‘批判理论’毕竟是一个培养(cultivation)的过程,尽管它声称具有彻底的‘他者性’和异质性,但它要求理论使用者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未予说明的种种规则来运行,这些规则不言而喻,说白了就是这样——你能怎么解构就尽力怎么解构,但要继续以西方为中心。”[4]周蕾对“温情的臆造”研究因此就遵循以西方为中心的原则,在分析《春光乍泄》(王家卫,1997)之前不得不谈到拉康(Lacan)和德里达(Derrida);在比较《吃一碗茶》(王颖,1988)和《喜宴》(李安,1993)的时候不得不从弗洛伊德(Freud)说起;在解读《盲井》(李扬,2003)之前,不得不大谈海德格尔(Heidegger)。
以上有关周蕾自我定位于西方理论的讨论,旨在凸现近来一种较为普遍的研究倾向,即认为理论的探索比资料、事实和文本的经验分析更为精致,更值得推崇。然而,理论跟事实和文本并非天然对立。其实,电影研究中早就存在一种“后理论”的取向,波德维尔和卡罗尔于1996年编过一本题为《后理论》的书,详细阐明了他们对理论的看法。与周蕾热衷于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做法不同,他们对“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进行激烈的抨击。所谓宏大理论,在他们看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结构主义的主体性理论”,以阿尔都塞(Althusser)的新马克思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梅兹(Metz)的电影符号学为代表;另一种是“文化主义的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为代表。宏大理论高屋建瓴,自上而下,但波德维尔对其教条式的学术前提和联想式的逻辑推理提出质疑。[6](P3-36)重要的是“后理论”并不意味着“不要理论”,如波德维尔所言,“宏大理论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多种的理论”。[7]为了同那种宏观的、总体性的宏大理论区分开来,卡罗尔主张使用那些“零敲碎打式的”(piecemeal)理论推理,波德维尔则提出“中层研究”(middle-level research)的概念,提倡在研究中同时兼顾经验实证与理论运用。[6](P27)他们列举许多这样受理论启发、但经验丰富的中层研究的范例,包括近期有关电影导演、类型、国族电影的研究,有关电影生产、发行、放映、接受的新电影史以及电影风格史等等。
必须指出,在北美学界,波德维尔、卡罗尔对“宏大理论”的批评效果甚微,而周蕾仍然以民族理论专家的高姿态进行书写。(12)我这里把他们两种对待理论的不同态度并置而论,主要想阐明这样的观点:正如“经验事实的非西方”是一种话语建构,“充满想象力的理论的西方”也纯属虚构。周蕾眼中那“精益求精的档案细节”的方法并不足以描述包罗万象的“中国研究”,因为这个领域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经验论的研究方法;相反,档案研究199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电影研究中却成为一个新的显学领域,成果累累,有目共睹。换言之,经验求证的研究并非必然会塑造出类似“中国性”这样的民族标志,因为中国的理论与文本是多元的,西方的理论和文本也是多元的,因此,多向度的经验研究的确可以穿透简单化的西方/非西方的对立格局。周蕾断言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理论的时代”,而波德维尔则针锋相对,认为这是“后理论的时代”。作为多产的电影学者,波德维尔抵制宏大理论的诱惑,清醒地认识到“宏大理论如过眼烟云,飘来往去,而学术和研究则是持续不断的。”[6](P29-30)
“国族电影”的神话
诚然,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电影研究中的理论往来消长。波德维尔本人从行业实践出发,通过对电影镜头和场景的逐一分析,建立了电影风格和电影叙事理论。[8]其他学者基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创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国族电影”就是其中的一种。国族电影滥觞于1915年左右的欧洲。一战以后,民族国家疆域的重新整合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心,电影研究与国族认同联系起来理所当然。[9](P259)但是,这完全是时势使然,因为时至1905年,电影与国家或民族文化并没有硬性的关联。理查德·阿贝尔(Richard Abel)指出:“直到1906年,法国公司百代(Pathé’s)所生产的电影,其最大的消费市场不在法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美国。尤其是‘五便士娱乐场’(一种可纳数百人的临街小影院)的兴起,让百代电影在美国广有销路。”[10](P184)阿贝尔进一步提醒我们,美国电影的“美国”身份是在不断驱除“对红公鸡的恐惧”(红公鸡是百代的公司标识)中建立起来的,它是美国电影导演、制作者、发行商、放映商、批评家和教育家等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美国电影也曾经历过一个民族化的过程,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斯蒂芬·克罗夫兹(Stephen Crofts)的学术观念的变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993年他把全球的国族电影分为七类(即欧洲艺术电影、第三电影、第三世界与欧洲的商业电影、忽视好莱坞的中国香港与印度等本土市场自足的电影、模仿好莱坞的英语国家的电影、集权国家的电影、国家之内的区域或族裔电影),而在1998年他却把美国电影作为第一类型补进了国族电影的世界版图。[11]
克罗夫兹阐明了全球范围内存在多种国族电影的事实,而安德鲁·西格森(Andrew Higson)则进一步指出,在国族与电影之间建立一种想象性关联主要依赖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外向的”,即通过与其他国族电影或好莱坞进行比对所建立起自己电影的国族身份;第二种是“内向的”,把本土的电影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或传统联系起来,赋予其独特的性质。[12](P42)从后者来看,西格森分析了英国电影构建国族身份的策略。其一,“通过从本土电影中识别出一些精心挑选的优质的电影运动,以揭橥国族电影的大旗”。[12](P22)其二,“生产出一些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现状的现实主义的国族电影”,“用一种被理解成民族和传统的方式去表现被认为是民族的历史、人物、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12](P16-17)其三,借助电影的动员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宣扬“国家是集体的大家庭,共同体利益凌驾于各阶层利益之上”的观点。[12](P274)顺理成章,“母亲的象征形象成为完美女性的体现,居于家庭-共同体-国家的中心”,母亲的受难是为了团结家庭成员,“她备受尊崇的原因不是因为其女性,而因为其体现出的抽象的普世人性。”[12](P264)
用西格森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电影史,其实并无不妥。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高举国族电影的大旗,传达“进步”与“革命”的观念,尊奉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通过塑造一系列受难母亲的形象,呈现乡土中国的式微,通过构建民族国家认同来进行社会动员。然而,国族电影的构建存在根本的问题,即一个国家的电影实践是多元化的,绝非一种类型和模式,把一国之电影简单化为某种固有的形态,必然引发诸多质疑。在这种意义上,西格森对英国电影的反思同样适用于中国电影:“作为国族电影的英国电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旨在整合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话语,表现一种矛盾的一体性,扮演着争取共识、遏制异见的霸权角色。”[12](P275)
各国的国族电影在构建国族认同上的策略大同小异,具体到某一国家的电影史编纂存在同样的问题。苏珊·海沃德(Susan Hayward)对法国以电影作者和电影运动为主导的研究范式颇有微词,批评其“站在精英艺术的立场,排斥通俗的大众文化”。中国电影史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取向,借用海沃德的话说,“国族电影绝对不止一种,而是多元实践”。[13](P7,14)中国地缘政治复杂,华语电影纷呈不一,更是如此。总之,国族电影中多元与异质的特性迫使学者以更开阔的视野中去考察一国电影的发展史,关注那些与主流政治文化不同或相对的国族认同的建构,这些建构可以来自很多先锋的、纪实的、甚至商业化的电影实践。
与银幕上的影像呈现不同,政府借助于政策,以推进、保护或承传本国文化为由,对国族电影进行整合。在伊恩·贾维(Ian Jarvie)看来,政府进行国族电影建构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产业保护论”、“文化保护主义”和“民族建设论”。其中第一种又可细分为三大理由:一、本国电影产业太弱小,需要保护;二、抵制外国电影是文化上的一种反倾销政策,合情合理;三、本国电影市场容量有限,不得不控制。贾维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说不太过去。“文化保护主义除了显示出文化上的不自信以外,不会有什么效果,只会弄巧成拙。而民族建设论更是极不体面,因为其倡导者想通过电影来完成一种特殊的民族与文化的联姻,这种联姻让诸多差异单一化,而拒绝了通过公民和法律制度促进多元共存的美国模式。”[14](P86)贾维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北美是一个移民国家,构建国家认同按理说更为切要,然而,其国族电影的诉求却很弱;相反,西欧国家历史文化悠久,却热衷于通过国族电影来凝聚国族意识。[14](P81)进而言之,在西欧国家,“电影是一项社会教化的事业,使人们远离激进主义,而趋向于接受政府和文化精英的道德、观点和持续的霸权。”[14](P81)
近来对国族电影范式的批评破除了民族建设所制造的共识(consensus)的神话,彰明一国之电影是多元而异质的。而对早期电影和当代电影的深入研究表明,电影的生产并非局限于一国,而呈现出跨国的一面,这一点在以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正如杰弗里·诺威尔·史密斯(Geoffrey Nowell-Smith)所言:“电影从来就是国际化的,无论从文化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如此。”[15](P48)诚然,电影发行和放映的跨国性尤为明显。照此看来,好莱坞当仁不让算是最国际化的电影了,因为好莱坞电影文化和电影工业的国际化实践从1900年代就开始了,而从1940年代以来越来越走向全球化。[16]
然而,如果说电影从来就是跨国的和国际化的,那么,为什么电影研究仍然要把“民族/国家”作为重要的考察维度?如果不是考虑到国际发行和管理归类的方便,对于大多数电影制作者来说,“国籍”是否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对于独立制片人来说,他们是否乐意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与外国公司展开合作?其实,现在应该是改变思维模式的时候了,我们不妨沿着人文地理学的路径从空间和跨地域的维度,而不是从民族和国家的维度,重构中国电影研究的理论框架。
“跨地性”与理论重构
从历史来看,电影并非从民族国家这个规模开始。早期中国电影无论是制作、发行,还是放映,都不是国家主导的事业。恰好相反,20世纪前10年主要是由地方(城市)来运作的,而到了20年代主要由跨地区的公司来主导。中国电影可溯源至1905年,因拍摄了一段京剧表演《定军山》而留名史册的“丰泰照相馆”,不过是北京城内一家私人照相馆而已。1909年,美籍犹太人本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在上海成立“亚细亚影业公司”,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拍过片子。黎民伟在香港地区与布拉斯基合作,以“华美公司”的名义在1913年拍摄了地方戏粤剧为蓝本的《庄子试妻》,该片据说1917年在洛杉矶上映过。1923年,黎民伟与两位兄弟一起在香港地区创办“民新公司”,三年以后,该公司前移到上海,黎氏作为制片人在这里经营了上10多年。比较而言,“长城公司”电影实践的跨地性更为明显。该公司成立于1924年的上海,创办者为一群爱国人士,他们早于1921年就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成立一家同名的影业公司。几乎同时,邵醉翁1925年在上海创办了“天一公司”,第二年就他很有远见地派两位弟弟——25岁的邵仁枚和19岁的邵逸夫到东南亚去开拓电影发行、放映的网络。[17](P19,31-32,47)
可见,在1920年代末之前,中国电影基本上不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于此叶文心(Wen-hsin Yeh)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观点:“华语电影在成型时期,不是拘于国家边界之内的一项民族事业,而是流散事业(diasporic venture),关联了上海、香港地区、新加坡、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地的中国人。”[18](P1501)1930年代,这种跨地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因为抗战爆发使得很多影业公司和制片人不得不重新定位,辗转各地,从上海到香港地区或重庆。[19](P65-87)的确,1930年代的这种跨地性源于失去家国的离散,但是足够史料证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不是故意逃离中心和自我边缘化,而是主动的跨地实践。因此,叶文心“流散事业”的说法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相比之下,彭丽君(Laikwan Pang)从“上海电影”和“国族电影”的双重视角,详尽分析了左翼电影思潮的复杂性。上海是左翼电影的大本营,因此,彭丽君认识到,“左翼电影是城市的而不是民族国家的特殊产品”,然而,“那种自觉的国族意识也体现得非常明显”。[20](P166)换言之,左翼电影在城市和国族之间保持着多层次的表述关系。作为1930年代上海电影主流的左翼电影思潮,自然迥异于叶文心以海外电影实践为取向而看到的“华语流散电影”。
与左翼电影类似,罗明佑创办的联华公司也根基于上海,但它发展出庞大的跨地区网络。早于1920年代,罗明佑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开创自己的发行公司,并合并了上海和香港地区几家大的影业公司(如民新公司);1930年代,联华公司的业务甚至计划发展到新加坡和旧金山。与“去国”和“离散”相反,罗明佑的策略是高调张扬自己电影事业的国族性,所以不难理解,他为联华公司特意设计的口号四次强调“国”字:“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13)联华影业公司的案例表明,电影实践中对民族国家的诉求和跨地实践并非互不相容,用文化民族主义来使自己的经济动机正当化,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市场策略,尤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更是如此。
再来看当代中国电影,那些被媒体刻意渲染的所谓跨国“大片”,准确地说,只不过是最新的电影跨地实践而已,与“民族国家”没有太多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联合投资和制作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遍布全球都市(如北京、上海、香港、台湾、东京和首尔)的商业公司,而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公司、演出和制作团队,并非理所当然地代表各自的国族文化。例如,陈凯歌导演的《无极》(2005)多国制作阵容可谓豪华壮观,打破当时国产片的投资纪录。但饰演奴隶昆仑的张建东并不代表韩国;饰演大将军光明的真田广之也不代表日本;同样,该片主题曲作者克劳斯·巴代特是德国人,其创作的乐谱并不反映德国文化。诚然,像《无极》这样的大片无疑是跨国合作的产物,但这样的“跨国”概念其实只在表面上承认“国籍”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标签,而忽略了当今资本和人才频繁的跨国界流动,这已经极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认同的中心地位,而在地理规模上增强了国家之下各个地方之间的联系。
最近一些学者开始用“跨地性”的理论视角,以观照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上的急遽变化。卡洛琳·卡地亚(Carolyn Cartier)建议重新思考全球、区域、国家、地区和地方之间的“规模关系”(scale relations),因为“跨地性”正在形成。“跨地性的形成是这样一个进程,多个地点之间因人们的不断流动而建立起依恋关系。”[21](P26)在卡地亚看来,“跨地性”把在流动中的“地点”(place)、依恋(情感)和“人们”联系起来(在当代中国,流动的人们包括往来于全球的商业精英和往返于城乡的农民工)。戴维德·古德曼(David Goodman)把“跨地性”定义为“对不止一个地方产生认同感”,而提姆·奥克斯(Tim Oakes)和路易斯·沙因(Louisa Schein)同时关注“多个地点”及彼此间的“流动性”,进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尽分析。[22](P1)对他们来说,跨地性不仅意味着人员的流动,还包括资本的循环,观念和形象、物品和风格、疾病和技术的传播等。总之,跨地性意味着对多个地点的认同和依附关系的易变性。
笔者曾在别处讨论过“跨地性”和电影之间的互动关联,[23](P1-12)这里再度重提只是想表明,中国电影研究如给予“跨地性”和“跨国主义”以同样的关注度,将会受益匪浅。不同于跨国主义那种宏大的民族国家规模,“跨地性”的理论视角从无数的细小点切入,从投资到拍摄到后期制作到播映到观众认同,电影在不同的空间地点中实践,里面呈现出许多有趣的细节。如前所述,除了那些国家规模明显存在的案例之外(如中国国内国家垄断的大片发行和世界上国际发行商以国家为对象的发行网),中国大多数电影主导性的生产模式是多地性的,即一点一滴地四处搜集资源,其运作方式与默片时代非常相似。
事实上,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不管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跨地性”,它们通过各种跨地机构与组织(如非营利性组织、电影节和海外传媒)在世界各地流传。[24](P179-192)可见,独立电影鲜明的特性不在于“跨国”声誉,而在于它的“跨地”实践,正是这种实践使中国艺术家跳过纵向的国家界限,通过与各个地方的联合,超越民族国家,直接与由许多个人或组织构成的全球网络建立起联系。
我们不妨联系地点、空间和权力的地缘政治想象,对本文题中民族、国家和跨地性等三个概念进行重新检视。在空间上,“西方”习惯性地被等同于“全球”,而“非西方”被视为“地方”;与此同理,理论被推崇为高度抽象,具有全球性,而文本被降格为地方性的,背负着历史与文化的负累。如同资本,西方理论占据了流动的空间,它可以轻易地在全球传播而被普遍采用;相反,非西方的文本只能凝滞在具体的地方,它的意义是被限定的。
近些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就此提出质疑。阿图罗·阿斯克比尔(Arturo Escobar)剖析这一成见,“全球性被联想为空间、资本、历史和力量,而地方则同地点、劳动力和传统联系起来,相关的还有妇女、少数裔族、穷人和地方文化等”。[25](P155-156)戴维德·哈维(David Harvey)则声讨资本和权力被指派给空间,而劳工阶层、少数族裔、殖民地人们和妇女被认定为地方,“其身份限制在地方”。[26](P302-303)
鉴于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不均衡,少数族裔必然被地方限制,而被地方限制的少数族裔学者就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摒弃作为弱势者的民族身份,向作为权利象征的西方理论的中心空间突进,用所谓复杂精致的西方理论去解读非西方的文本,这就是周蕾本人热衷的、并要求其他学者师从的研究套路。第二,完全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一边,编造国族认同的神话,在表征世界里建构强盛的国族形象,以抗拒西方霸权,这是国族电影所青睐的研究范式。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选择都没有真正对西方霸权构成挑战,因此并非最佳选择。
舍此以外,“多地性”是一种更有希望的范式。这一范式的关键不是要简单否认地方的弱势地位,而是对因资本和权力四处渗透而建立的全球网络进行反思。对此,德里克的疑问值得一提,“如果我们坚称‘地方的就是全球的’,这和‘全球的就是地方的’,在逻辑上有何关系?”[27](P24)显然,德里克不是要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玩弄平等的文字游戏,而是要“重新认识地方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跨地联盟和合作形式”。[27](P41)跨地联盟在德里克“立足地方的想象”中居于中心位置,这种想象鼓励我们去探索新的可能,在多地的世界中建立跨地联盟,开发连接不同规模和地点的地缘政治。
此外,朵琳·马西(Doreen Massey)试图在全球化的权力图谱中恢复“地方”和“空间”的平衡,借此寻求“地方的全球意识”(a global sense of place)。[28](P29)我最后不妨稍微改述马西的观点,以结束本文的反思:对中国电影研究而言,“理论的全球化意识”(a global sense of theory)意味着我们必须把非西方,而不仅仅是西方纳入全球视野中的理论化考量,而“理论的本土化意识”(a local sense of theory)则要求我们对理论的使用必须在本地的或跨地的范围内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作为新的理论架构,“跨地性”可以同时连接全球与本土之间任何规模的诸多地点,由此可望为中国电影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全新的视域和发展空间。
①关于电影理论的类型,参见John Hill and Pamela Church,eds.,The Oxford Guide to Film Studies,P51-5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②也有极少数例外,如以下的著作用专门的章节展开对中国艺术理论的讨论:Linda Erhlich and David Desser,eds.,Cinematic Landscapes:Observations on the Visual Arts and Cinema of China and Japa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③这一点在最近关于武侠片的研究中尤显突出。参见陈默:《中国武侠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④参阅Mette Hjort and Scott MacKenzie,eds.,Cinema and Nation(London:Routledge,2000); Alan Williams,ed.,Film and Nationalism(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2).Valentina Vitali and Paul Willemen,eds.,Theorising National Cinema(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6).
⑤遭受批评的著名例子包括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和贾樟柯的《小武》(1997)。参见Dai Qing,“Raised Eyebrows for Raise the Red Lantern,”Public Culture 5(1993):336;吴文光编:《现场》(第一卷),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⑥针对中国电影“同质性”神话的讨论,参见Zhang Yingjin,Chinese National 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1-10关于国族电影范式的批评,参见Zhang Yingjin,"Chinese Cinema and Transnational Film Studies," in World Cinemas,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edited by Natasa Dorovicová and Kathleen Newman(London:Routledge,2009).
⑦关于电影研究中的跨国主义,参阅Natasa Dorovicová and Kathleen Newman,eds.,World Cinemas,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London :Routledge,2009),ix-xv.关于跨国华语电影,参阅Sheldon Hsiao-peng Lu,ed.,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1-3; Chris Berry and Mary Farquhar,China on Screen:Cinema and 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⑧Arif Dirlik,"Placed-Based Imagination: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in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s.Roxann Frazniak and Arif Dirlik(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1),15-51.关于中国的跨地流动,参阅Tim Oakes and Louisa Schein,eds,Translocal China:Linkages,Identities,and the Reimagining of Space(London:Routledge,2006).
⑨对这一研究取向的批评,参见Zhang Yingjin,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
⑩周蕾在Primitive Passions:Visuality,Sexuality,Ethnography,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一书中分析了十几部中国电影,而在参考文献中鲜见中文书目。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参见Zhang Yingjin.,Screening China.
(11)Chow,Writing Diaspora,6.白露的文章见Tani Barlow,"Funü,Guojia,Jiating[Chinese Women,Chinese State,Chinese Family]," Genders 10(1991).
(12)周蕾突进西方理论的中心已经大功告成,其著作The Protestant Ethn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的封底刊有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推荐语:“该作视野开阔、理论性强,并充满挑战,周蕾对民族的问题进行完全的重构,往后相关的讨论都绕不开它。”
(13)参见Zhang Yingjin,Chinese National Cinema,60-62.另参加Hu Jubin,Projecting a Nation:Chinese National Cinema Before 1949(Hong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6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