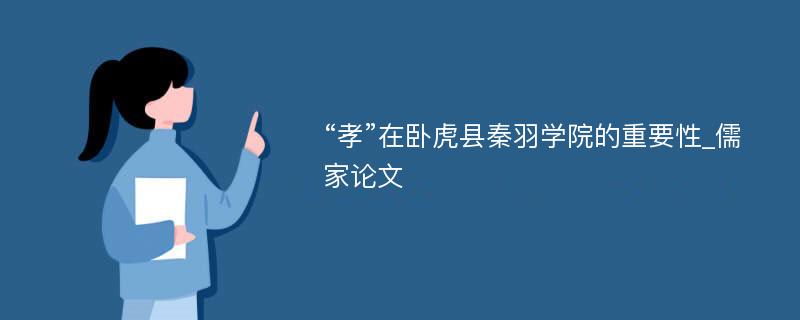
睡虎地秦簡所見對“孝”的重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一般認爲,秦王朝因嚴刑峻法而强大,並最終統一中國,秦王朝又因嚴刑峻法而“仁義不施”①、導致速亡。因此,在秦國這個法治國家,以及秦國(包括秦朝)所統治區域,爲儒家所積極倡導、尊爲一切人倫道德之根基的孝道不可能得到重視和推行。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殘,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既然“不別親疏”、既然“親親尊尊之恩絕”,那麽,孝道也就無從說起了。商鞅力主嚴刑峻法,將“孝悌”稱爲“六蝨”之一,“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商君書·靳令》)。②韓非子一派則把一切人際關係看作是純粹的利害關系,因此,所有的道德都是虛僞的,行“仁義”衹會喪國、“慈惠”衹會“亂政”。就孝道而言,“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難二》),韓非子一派不相信道德教化在調節社會秩序時的作用,在他看來,只有專任刑法纔能使天下爲治。因此,國家衹能獎勵那些耕戰有功的人,而不能去獎勵慈父孝子。
但事實似乎並非那麽簡單,從傳世文獻看,無論是法家類作品還是對秦國(包括秦朝)統治加以記載的内容中,“孝”並不是一個被完全否定的對象。例如,《商君書·境内》說“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就是說,《境内》並不反對“孝”本身,但認爲僅靠父母的感化教育並不足以培養孝子,還得靠嚴刑峻法。《韓非子·忠孝》說“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就是說,《忠孝》也提倡“孝悌忠順”之道,衹是反對孔子的“孝悌忠順”之道。《忠孝》還提出“孝子,不非其親”,但《忠孝》的“孝子”觀是和忠臣觀聯繫在一起的,這一點在後文中還將論述。從歷史記載看,《秦始皇嶧山刻石文》稱始皇“孝道顯明”,這說明秦始皇本人對“孝道”這份榮譽也極爲珍視。《史記·李斯列傳》中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胡亥假冒始皇詔書迫使其兄自殺的罪名就是“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白裁”。可見在秦人實際政治生活中,“不孝”是作爲一種不可饒恕的重罪看待的。
以“不孝”立罪,史書有載,如《呂氏春秋·孝行》載有《商書》佚文,“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誘注曰:“商湯所制法也”。《尚書·康誥》:“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就是說對“不孝不友”這類大罪要由周文王制定刑罰加以懲處。《周禮·地官?大司徒》也載“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但這些“不孝”罪分屬不同時代,有時被視爲重罪,有時也未必③,關鍵是具體如何處罰並不清楚④。然而,1975年至1976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用秦系文字書寫的法律文書⑤,其中即有“不孝”罪的具體案例及其處罰方式,爲我們研究秦人生活中“孝”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極好的材料。雲夢縣睡虎地原爲楚國領地,後被秦軍占領,秦國在此設置了南郡,因此,這些出現於楚地的秦人法律文書和秦對楚的殖民統治有著密切關係。睡虎地秦簡中還出土有與民間信仰相關的《日書》甲乙兩種以及發給各級官吏作爲爲政指導的《爲吏之道》,其中也涉及到“孝”。目前爲止,筆者尚未看到對睡虎地秦簡所見“孝”作出綜合整理的文章,“孝”或者被放在家庭問題中提及⑥;或者純粹從法律角度作出研究⑦;或者在論述爲政之道時有所涉及⑧。問題在於睡虎地秦簡在法律文書、在《日書》、及在《爲吏之道》中所見“孝”各有不同特色,應該如何結合當時的思想背景,對其作出整合的解釋,同時通過對這些出土文獻所見“孝”資料的分析,結合傳世文獻,對秦國(包括秦朝)時而嚴厲批判儒家的孝道,時而又以嚴刑峻法推行孝道的奇怪現象如何作出合理的解釋,這就是本文的目的。
一、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中與“孝”相關罪行
本節試圖對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中所見與“不孝”相關罪行加以整理和分類,由此分析、判斷出這些“不孝”罪行主要側重於哪些方面,當時的法律試圖維護的是怎樣的社會秩序。
1、毆打辱罵家長
從以下引文可知,秦律規定毆打父母或祖父母,要“黥爲城旦舂”。
“毆大父母,黥爲城旦舂”。今毆高大父母,何論?比大父母。(《法律答問》,第111頁)
這裹沒有直接談到不孝,但1983年出土的湖北荊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相似内容則是和“不孝”連在一起的。
子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⑨
這是說有人告發子女殺害父母、毆打辱駡家長、或父母告子不孝時,要受到“棄市”的處罰。
2、告子不孝
爰書:某里士伍甲告曰:“甲親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謁殺,敢告。”即令令史已往執。令史己爰書:與牢隸
臣某執丙,得某室。丞某訊丙,辭曰:“甲親子,誠不孝甲所,毋(無)它坐罪。”(《封診式》,第156頁)
這是說某甲控告其子丙不孝,要求官府將其處以死刑,官府馬上按其所告將其子拿獲,最後是否判處死刑不明。可惜的是沒有指出其子丙因何不孝。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不孝”之罪最高可以判處死刑,二是家長在家内具有決定性的、類似於國君的生殺大權。《封診式》中還有一段,雖未明確表明是否因子不孝,但也是爲父者要求官府查辦其子,將其子斷足,遷至蜀之僻地,而且讓其終身不得回來,官府也果然按其父要求執行了這一處罰。
爰書:某里士伍甲告曰:“謁鋈親子同里士伍丙足,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敢告。”告廢丘主:“士伍咸陽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謁鋈其足,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論之,遷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封診式》,第155頁)
再來看下面這則法律条文:
免老告人以爲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法律答問》,第118頁)
這是說六十歲以上老人告子女不孝,要求處以死刑,是否經過三次原宥的手續,回答是不必原宥,馬上抓起來,勿使逃走。可見因不孝而處死毫無商量之餘地。這又再次證明了秦對不孝處罰之嚴,對家長權威維護之切。
3、非公室告
“非公室告”即子孫不可告發父祖,告者有罪。如《法律答問》中有以下内容: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何謂“非公室告”?主擅殺、刑、髡其子、臣妾,是謂“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法律答問》,第118頁)
所謂“非公室告”,就是“家長擅自殺死、刑傷、髡剃其子或奴婢”,叫“非公室告”⑩,對這種告訴,官府不予受理,硬要上告者,告者有罪。這也充分反映出家長在家中的絕對權力。時代爲漢初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告律》中也有類似的内容:
子告父母,婦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聽,而棄告者市。(《二年律令》,第151頁)
也就是說,“非公室告”的法律形式一直沿續到了漢代初期,《二年律令·告律》更明確地規定了對告者的處罰方式,是將告者棄市。這種無条件維護家長權力的還見於睡虎地秦簡其他條文:
“父盗子,不爲盗”。今假父盗假子,何論?當爲盗。(《法律答問》,第98頁)
士伍甲毋(無)子,其弟子以爲後,與同居,而擅殺之,當棄市。(《法律答問》,第110頁)
“擅殺、刑、髡其後子,讞之”。何謂“後子”?官其男爲爵後,及臣邦君長所置爲後太子,皆爲“後子”。
(《法律答問》,第110頁)
“擅殺子,黥爲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殺之,勿罪。”今生子,子身全也,毋(無)怪物,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舉而殺之,何論?爲殺子。(《法律答問》,第109頁)
可見,家庭的概念在秦國(秦代)有著嚴格的規定,彼此間未必有真正的血緣關係,但必須在法律意義上得到承認。所以義父義子不能算父子,非直接血緣關係,但確定了後嗣地位的人(如弟之子,即侄子)卻可以承認爲父子關係。而且有爵位繼承權的“後子”最受法律保護,其父如果對其“擅殺、刑、髡”,就要被定罪,相對而言,其父對“後子”以外的其他子女有犯罪行爲,衹要無人告發,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最後一段說的是,如果生下來的孩子是怪胎或有疾病,可以將其殺死。但如果孩子並非怪胎或有疾病,而是因爲孩子太多殺嬰,則有罪,這可能和秦國保護人口增長政策有關。
上述各段引文雖然未涉及到孝,但有助於我們理解秦人的孝觀念。因爲這些材料反過來證明,秦人的孝不是主動的、自發的行爲,而是不得不爲之的、被動的行爲,因爲父祖在家中權力實在太大了。同時,何人在何種情況下盡孝,也有著國家的規定,必須和國家利益統一起來。例如,義子對義父哪怕不盡孝,國家也不會過問,因爲兩者沒有法律關係。“後子”即便對家長未盡孝,家長在處罰時也不能過於嚴厲,因爲“後子”是受國家保護的人物。這樣看來,孝成爲秦國(及秦朝)統治過程中維護家長權利、同時維護國家利益的一種手段。
我們常常說,古代中國家國一體,國就是家的放大,所以孝道可以成爲治國之本。然而,在儒家學說中,當盡忠和盡孝發生矛盾時,選擇雖然極其痛苦,但一部分先秦儒家允許做出抉擇,例如孟子甚至鼓吹選擇“孝”而放棄“忠”。(11)秦國(及秦朝)卻不是這樣,“忠”爲主、“孝”爲次,“孝”的最終目的是爲了“忠”,而放棄當兩者發生矛盾時,個人必須放棄對家長的孝,而選擇對國的忠。這一點從“非公室告”的局限中也能看出。
“非公室告”其實是有限制的。張家山《二年律令》爲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張家山漢簡中並沒有出現“公室告”、“非公室告”之類的術語,但秦律中處理這類行爲的法律原則在漢初的《二年律令》中仍然適用。張家山漢簡中也有禁止家人或奴婢控告家長的規定,上文已引。但如下文所示,張家山《二年律令》有以下条文,卻是鼓勵家人或奴婢控告家長的。
以城邑亭鄣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鄣,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其坐謀反者,能偏(遍)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二年律令》,第133頁)
劫人、謀劫人求錢財,雖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爲城旦舂。其妻子當坐者偏(遍)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二年律令》,第144頁)
盜鑄錢及佐者,棄市。同居不告,贖耐。(《二年律令》,第160頁)
就是說子女和奴婢雖然不可告發“家長擅自殺死、刑傷、髡剃其子或奴婢”,但當家長犯有針對他人、針對國家的謀反、盜竊、殺人等罪行時,子女和奴婢必須要向官府告發,以免受牽連,不告反而有罪,這其實屬於“公室告”。(12)因此,如果說“非公室告”是在保護家長的權力,那麽“公室告”則同時又削弱了家長的權力,標準在於怎樣做對國家有利,如果“不孝”沒有影響到國家利益,那麽法律保護家長,如果“孝”會影響到國家利益,那麽法律則鼓勵子女“不孝”。
可以這樣說,秦人及其在殖民地所推行的孝道是外在的、被强制的行爲,而不是出自内心的、自發自願的行爲。同時,“父慈子孝”不是双向的互動,而是子不得不“孝”,父卻未必需要“慈”。通過孝道,秦國(及秦朝)要建設的不是一個個温情脉脉的和諧家庭,而是表面上充滿秩序和効率的國家,衹要沒有人告發,家長可以隨意處置子女。因此,這是一種鉄腕之下的孝,目的在於保護以父權爲核心的家庭的穩定,進而維護以父權制家庭爲基礎的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在此,孝不是一種德行,而成了法治的工具和手段。
二、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及《日書》所見的“孝”
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幾乎都是四字一句,一般認爲是給秦國(包括秦朝)基層官吏使用的、指導如何爲官施政的格言警句。關於其中的核心思想,出土之際,正值上世紀70年代評法批儒政治運動大行其道,當時一些介紹和評論文章幾乎都認爲《爲吏之道》是秦始皇法家路綫的產物,其思想面貌呈法家特色。後來一些嚴肅的學術論文又提出新的看法,例如歐陽祯人的《〈爲吏之道〉的儒家思想發微》認爲《爲吏之道》主要反映的是儒家思想;魏啓鵬的《文子學派與秦簡〈爲吏之道〉》認爲其中的思想背景是先秦道家,說《爲吏之道》的基本思想與文子學派“循道寬緩”之旨吻合;俞志慧《秦簡〈爲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從其集錦特色談起》,則否定前人關於其思想主體的法家說、儒家說和道家說,認爲它雜取先秦各種思想于一體,具有集錦特色。俞志慧進而認爲,《爲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義,“它體現了那一時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趨勢,從草根文化層面體現得如此集中明顯,在此前的傳世文獻中尚未發現;這一特色也告訴我們先秦諸子有著共同的思想文化資源、相似的知識背景、話語平臺和相近的問題意識;在法術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爲吏之道》的思想基調與儒道思想更爲接近,證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13)筆者以爲,毋庸置疑,《爲吏之道》具有法家、儒家、道家的思想特色,但僅僅指出其中哪一種爲主流,其實並無太大意義。我們在觀察《爲吏之道》時,有兩個前提不可忽視,一是此文出現於基層官吏墓中,所以它所反映的並非最高的政治理念,而是處理現實、具體政務時所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則。其次,此文發現於秦人的統治下的楚地,因此,其目的在於如何使秦人官吏更好地展開殖民統治,以實現政治安定。因此,如俞志慧所言,此文具有草根文化特色,體現出思想文化的融合趨勢。所以,與其費力找尋此文的主導思想,不如關注其寫作目的,施用方向。我們在研究其中與“孝”相關内容時,也要從這一思想背景出發。“孝”在《爲吏之道》中共出現兩次:
戒之戒之,財不可歸;謹之謹之,謀不可遺;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綦【之】,食不可償。術(怵)悐(惕)之心,不可【不】長。以此爲人君則鬼(懷),爲人臣則忠;爲人父則茲(慈),爲人子則孝;能審行此,無官不治,無志不徹,爲人上則明,爲人下則聖。君鬼(懷)臣忠,父茲(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徹官治,上明下聖,治之紀也。(《爲吏之道》,第169~170頁)
從倡導“爲人父則慈,爲人子則孝”、“父慈子孝,政之本也”來看,這裹在强調“孝”的同時,也强調“慈”,並視這兩者爲爲政之本,的確與儒家理念極爲相似。但這有可能僅是形式上的相似,不等於它就肯定來自於儒家,因爲“慈”、“孝”等德目,在戰國中晚期,除儒家特別强調外,墨家、晚期道家(尤其是黄老思想家)也並不反對(14),具有濃厚法家色彩的《管子》中對包括“孝”在内倫理道德的重視,處處可見,而且時代越晚越受重視。(15)在筆者看來,《爲吏之道》作爲指導具體政治實踐的讀物,具有顯著的實用主義特徵,即它不拘泥於哪一家的理論,也不是在刻意宣傳哪一家的理論,祇要有利於現實政治,就爲我所用。④況且這裹在强調父慈子孝的同時,也强調君懷臣忠,因此和以《韓非子》爲代表的法家忠孝觀也是一致的。
但是,上一節在討論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時,筆者指出,秦人對於“不孝”治之甚嚴,子不得不“孝”,父卻未必需要“慈”,衹要他人不告,如何行使家内暴力,政府也不會干預。這是否和《爲吏之道》所提倡的“父慈子孝”相矛盾呢?筆者以爲並不矛盾,衹是著眼點不同而已,當家庭内部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時,秦的法律文書作爲一種具體的、可操作的規則、規范,鮮明地、毫無保留地選擇保護家長的絕對權利,因爲秦提倡分家別户(16),每一個家庭都是能够爲國家提供賦税、勞役、兵員的基本單位,秦的政治體制宛如一臺巨大的軍事機器,對家長的服從宛如士兵對上級的服從,對家長的“孝”等同於對國家的“忠”。衹有無条件地保護家長的至高地位,纔能强固秦國(包括秦朝)的每一塊基石,纔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這個軍事化社會的秩序。如果我們把着眼點移向國君或者各級官吏時,就能明白爲什麼《爲吏之道》爲時既重子之“孝”又重父之“慈”了,因爲他們關注的是社會整體的秩序,關注的是如何使每一個家庭不發生危及社會的矛盾。
從《爲吏之道》看,秦人統治下的楚地社會,秦人和楚人之間統治和被統治關係導致的矛盾,迫使秦人采取比較柔和的、與楚人傳統相協調的統治方式,從而不得不在表面上鼓吹“孝”、“慈”等與儒家接近的道德觀念,可能這也是《爲吏之道》導入“父慈子孝”的原因。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出土文獻對“孝”的論述極多,楚地曾受到儒家文化相當深厚的影響(18),因此,至少楚地知識階層是認同“父慈子孝”的。
那麽,楚地民間如何呢?《爲吏之道》和睡虎地秦簡《語書》反映出楚地的民風民俗很難接受秦人的專制管理,如《語書》說:“凡法律令者,以教導民,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於爲善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廢主之明法也,而長邪僻淫失(泆)之民,甚害於邦,不便於民……今法律令已布,聞吏民犯法爲閒私者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自從令、丞以下知而弗舉論,是即明避主之明法也,而養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則爲人臣亦不忠矣。”(第13頁)《爲吏之道》也說要“變民習俗”(第170頁),可見當時儘管頒布了法律令等强制手段,但楚人依舊惡俗難改,民風邪僻。那麽,這些惡俗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語書》並未明言,但可想而知一個“父慈子孝”的社會是不可能被看作“淫失(泆)”、“邪僻”的。因此,我們想像,在殖民地南郡,過去一直是、或者由於秦人的占領變成了一塊道德淪喪、民風敗壞的區域。
除與法律相關的文書外,睡虎地還出土了大批與民間信仰相關的文書,即《日書》甲乙兩種。這批材料來自楚地,因此是楚地社會面貌的反映。《日書》類似今天“皇曆”,是以時、日推測吉、凶、禍、福的占驗書,告知哪一天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什麼。因此,其中的希望、要求,往往正是現實中難以做到的部分,《日書》甲種有“生子”一篇,描寫的是父母對未來子女的期待,其中“孝”就是期待之一。
丁亥生子,攻(工)巧,孝。(《日書》甲種,第203頁)
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當時“孝”的缺失。因此,無論從《爲吏之道》和《日書》看,還是從法律文書看,秦統治下的楚地是重視孝道的。但這種重視非但不能説明當時孝道已經深入人心,毋庸强制便可自發踐行,反而說明當時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到了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强迫恢復或建立倫理道德的程度。
小結
最後,本文想將睡虎地秦簡所見“孝”和儒家及法家的孝道觀作一個簡單的對比,以突出睡虎地秦簡所見“孝”的時代特徵。
儒家的“孝”,有“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論語·爲政》)這種低層次的追求,孟子對“不孝”的定義是: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孟子·離婁上》)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離婁上》)
可見,孟子對“不孝”的這些定義也建立在世俗的層次上。但是儒家對於“孝”寄托著更高的理想和情懷。如《禮記·中庸》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曾子則將“孝”的層次由低到高,列出詳細的區分,其中既有“能養”這類低層次的“孝”,也有將“孝”的意義放大到足以覆蓋所有倫理范疇的至高的“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禮記·祭義》)
要達到這樣的人文關懷,“孝”僅僅作爲外在規范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必須是一種發自内心的道德行爲。與之相比,睡虎地秦簡所見“孝”衹落實在“能養”、“弗辱”這類低層次上,而且必須通過強制方式纔能得到保障。在“孝”的問題上,睡虎地秦簡表現出實用主義的態度,“孝”成爲維持社會秩序的外在手段。睡虎地秦簡不是由禮入法,實踐“孝”的目的,不是爲了實践禮,而是爲了更好地實施統治。賈麗英《秦漢不孝罪考論》一文概括了秦漢之際多種不孝之罪,除了“不養親”外,還有“不聽教令”、“輕慢尊親”、“毆殺尊親”、“誣告尊親”外,還有“居喪不謹”,這種漢以後比較流行的處罰,和儒家通過喪葬體現孝道的理念有直接關係。即居葬期間,如果子女做出“居喪奸”、“居喪嫁娶”、“居喪生子”、“父死不奔喪”、“匿父母喪”,就要受到相應處罰。然而,這類處罰在睡虎地秦簡中卻根本看不到,理由很簡單,睡虎地秦簡中作爲外在規範的“孝”保障的僅是活人的權益,死去的人已無法爲國家帶來實際利益,當然也就不需要過問了。
有一些學者認爲,睡虎地秦簡中的法律觀念或爲政觀念體現的是儒家刑法思想、直接引用的是儒家理論。(19)筆者認爲這種判斷過於簡單,因爲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雖然和儒家孝道觀在最低層次上有所重合,但睡虎地秦簡中的“孝”有著直接的目的性、實用的功利性,表現爲技術層面上的操作守則,體現不出對於大道、對於人文的關切,因爲儒家崇尚孝道,就說兩者相關,顯然操之過急。
如前所言,法家並不反對孝,當孝有益於国家時,更會使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支持,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就是極好的例子。但這支持的衹是儒家孝道中最低層次,當儒家孝道中的高層次闡發影響到法治無法推行,專制主義決策無法實施時,法家就要堅決反對了。所以,法家是否反對“孝”,一切以有用與否爲準繩,這也是《韓非子·忠孝》得以形成的原因,《韓非子》說的是忠孝一體、移孝入忠,以忠爲主、以孝爲次,以國爲主、以家爲次,爲了忠可以放棄孝。所謂的“孝悌忠順”之道,不過就是尊奉君父的絕對權威。因此這是功利的孝道,而非倫理的孝道。(20)睡虎地秦簡中的“孝”其實就是以這樣一種忠孝觀爲思想背景的(21)。
總之,“孝”雖然是儒家所倡導的德行,但與法治並不衝突,秦國(包括秦朝)用法律手段維護“孝”,其目的在於鞏固作爲國家基石的家庭,保障社會的安定,因而是功利的、短暫的行爲。秦國(包括秦朝)並非不接納、不贊賞“孝”,但僅將其當作一種外在的政治手段,這和儒家通過“孝”道的自發踐行,最終導致天下安定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秦國之所以會滅亡,不在於没有施行“孝”等倫理道德,而在於沒有將“孝”等倫理道德化作民眾主動的、自發的行爲。
睡虎地秦簡所見對“孝”的重視,反映出戰國末期倫理道德的嚴重喪失,其實是一種存在於民間的普遍現象,但漢初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卻認爲這是秦國暴政的結果,通過出土文獻的分析,我們得知這是一種遇於簡單化的推測,實際歷史現象要複雜得多。
注释:
①《史記·秦始皇本紀》,《賈誼新書·過秦》作“仁心不施”。
②高享認爲此文當作“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孝弟;曰誠信、貞廉;曰仁、義;曰非兵、羞戰。”今本衍三個“曰”字,其實是六項,全部可分爲二,故爲“十二者”。參見高享:《商君書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07頁。
③沈家本認爲《周禮·地官?大司徒》中的“不孝”罪不爲重罪。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31頁。
④文獻中有時也會透露出一些處罰方式,但不集中,也不系統。如《禮記·檀弓下》有“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周禮·秋官·掌戮》有“凡殺其親者,焚之”。
⑤本文所引睡虎地秦簡,均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以下引文不一一出注,僅標出頁碼。釋文采用寬式,對需要特別說明的通假字或异體字用括號表示。
⑥如吴小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觀念新探》,見《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岳麓書社,第325~326頁。
⑦如于振波:《從“公室告”與“家罪”看秦律的立法精神》,《湖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又見簡帛網2005年12月31日,http://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1。賈麗英:《秦漢不孝罪考論》,《石家莊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⑧如歐陽禎人:《〈爲吏之道〉的儒家思想發微》,簡帛研究網2000年8月29日,http://www.bamboosilk.org/Wssf/Ouyangzhenren3.htm。又見謝啓容編:《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魏啓鵬:《文子學派與秦簡〈爲吏之道〉》,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俞志慧:《秦簡〈爲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從其集錦特色談起》,《浙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又見簡帛研究網2007年6月23日,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7/yuzhihui002.htm。
⑨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第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139頁。以下引文不一一出注,僅標出頁碼。
⑩與“非公室告”相對應的是“公室告”,即非家族内部的犯罪行爲。
(11)例如《孟子·盡心上》說在“孝”與“忠”發生衝突時,舜爲盡孝寧可放棄天子之位。
(12)詳細論證參見于振波:《從“公室告”与“家罪”看秦律的立法精神》;賈麗英:《秦漢不孝罪考論》。
(13)見俞志慧:《秦簡〈爲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從其集錦特色談起》之“内容提要”。
(14)池田知久對此有遇詳細論述,他認爲戰國時代晚期道家對於能够維護父家長制基礎上郡縣制度的“孝”非但不予否定,反而認爲它是道家本來就倡導的東西。參見池田知久:《〈老子〉の二種類の)“孝”と郭店楚簡〈語叢〉の孝”》,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中文版見曹峰譯:《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15)谷中信一對此有過論述,參見谷中信一:《齊地の思想文化の展開と古代中國の形成》第二章《前期管子學派の法思想——經言諸篇を中心に》及第三章《後期管子學派の法思想——解諸篇を中心に》,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
(16)如果一定要比較論定哪家的色彩更濃厚些,筆者以爲,毋寧說是道家,因爲《爲吏之道》多次引用道家(老子、文子)之言,卻無對儒家之引用。準確地說,這種道家其實是以道家爲主體、綜合各家的黃老思想。
(17)《史記·商君列傳》說商鞅提倡“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賦”。
(18)郭店楚簡所見“孝”可參見池澤優:《〈孝〉思想の宗教學的研究》第五章第七節《〈孝〉思想とその他の儒家文獻の關連性——郭店楚簡を中心に》,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
(19)如崔永東:《金文簡帛中的刑法思想》,北京:清華大学出版社,第44~58、62頁。歐陽禎人《〈爲吏之道〉的儒家思想發微》也從多重角度討論過這個問題。
(20)參見康學偉:《先秦孝道研究》第七章《四、法家論孝道》,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1)當然,不可否認,從《論語》到《孝經》,儒家系統也一直有忠孝一體、移孝入忠的觀念存在,關於其對現實政治的影響,本文不作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