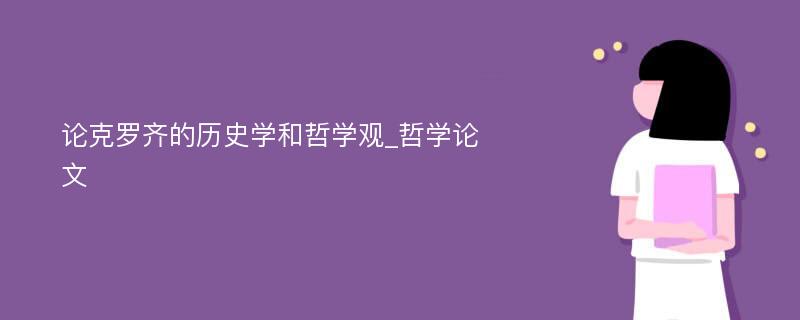
评克罗齐的历史与哲学同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罗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历史与哲学、历史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同一是克罗齐历史哲学中最为引人注目而又最令人费解的重要论点之一。卡罗吉诺(Guido Calogero)甚至说,历史与哲学的同一是意大利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 “这一标志使它与当代别的哲学和唯心主义趋向区别开来”。
(注:GuidoCalogero,On the So-called I dentity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载R.Klibansky&H.J.Patoned.Philosophy and History:Essays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3,p.35.)可以说,这一命题贯穿和渗透了克罗齐的全部史学理论, 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和把握乃是我们进入克罗齐史学思想殿堂的关键所在。
克罗齐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对历史学的性质和地位进行哲学思考,当时他已经以那不勒斯地方史的研究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世纪的欧洲,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自然科学的路数和方法因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深入人心,实证主义也因此而风靡一时。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不仅能够用于研究自然界,而且也能够用来研究全部的人文世界。实证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力图将历史学研究纳入自然科学的轨道,流风所及,以至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柯林武德还在孜孜以求,要使历史学摆脱“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注: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译序第9页。)克罗齐对历史学性质的思考, 就是直接由于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感而引发的。早年的克罗齐是以强调个别性作为历史学的特征的。自然科学虽然也研究个例,但其目的是为了归纳出适用于一般的规律,在这里,对个别本身的研究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历史研究中,不可重复的个别事件和个人本身就是研究的目的之所在,对个别的东西的研究并不以达致一般规律为其鹄的。就此而言,青年克罗齐这种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加以认识的方法,以及他所达成的结论,与新康德主义的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如出一辙。但是克罗齐把这种观点更推进了一步。由于维柯的影响,他很早就坚定地认为,艺术的领域属于认识活动(cognitive activity)的范畴,艺术就是直觉,是对于个别的东西的认识。既然历史也是对个别的东西的认识,那么历史就是艺术,而不应该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将它纳入自然科学的轨道。历史和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只涉及对于真实的东西的直觉,而艺术则兼及对于可能的东西的直觉,因而历史学就应该被纳入艺术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克罗齐1893年在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
克罗齐这种将历史置于艺术范围之内的观点,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后来虽然放弃了这种观点,但这其中所蕴涵的一些基本立场却是他终生不渝地坚持了的。那就是既反对实证主义将历史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的企图,又反对实证主义将艺术与快感联系起来,而强调艺术作为理论活动的开端而具有的认识性质。
更多地把历史与哲学而不是与艺术联系起来,是克罗齐在研读黑格尔以后所受到的启示。在他看来,历史作为人类生活,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经验事实,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不再被视为与事物的本质和理念相隔绝孤离,渺不相关的,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形下是对于理念的削弱和贬低”。(注:克罗齐: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the Philosophy of Hegel,London,Macmillan,1915,p.68.) 历史发展的本身就是理念的体现,就是哲学。比之笛卡尔以来,把历史驱逐于哲学之外,或者只赋予历史一个微不足的地位的近代哲学传统,这种观点乃是黑格尔哲学中仍然富于生命力的“活的东西”。但是真正促使克罗齐达到历史与哲学同一的立场的,则是来自他青年时期的挚友金蒂利(G.Gentile)的直接启发, 虽然金蒂利本人对于历史与哲学同一的阐发中,有着许多他所不能接受和同意的地方。
二
关于克罗齐对历史与哲学同一说的论证,我们得追溯到他在1909年的《逻辑学》中所阐述的概念论。在克罗齐的哲学体系中,理论活动分为两个阶段,艺术活动也即对于个别事物的直觉构成了它较低的一个阶段,而对于一般的东西的认识即逻辑活动构成了它较高的一个阶段,概念就是这第二阶段的活动的产物。克罗齐继承了黑格尔对于传统的形式逻辑的批评,认为形式逻辑所研究的不是活生生的思想的发展,而只是思想的文法形式,把思想当作尸骸来进行解剖。形式逻辑不能发现真理,只能从外在形式上来解释已被发现的真理。而真正的逻辑学则要力图去发现真理,把握全体实在的发展,这样的逻辑学就不再是关于思想的科学,而是正在活动的思想本身。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克罗齐认为概念乃是唯一的逻辑事实,是普遍性。在传统形式逻辑那种概念、判断、推理的序列中,概念只不过是构成了判断的一个端词(term),而对克罗齐而言,概念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本身,“是对于各个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而各事物就是直觉。概念不能脱离直觉,正如直觉不能没有印象作为材料。直觉是这条河、这个湖、这小溪、这阵雨、这杯水;而概念就是水,这不是这水或那水的个例,而是水之一般,无论它在何时何地出现”。(注: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译文有改动。)概念本身就是普遍性,但它却以对个别事物的直觉为前提。概念同时也就蕴含了判断和推理在内。当我们在思想中肯定湖水、溪水、河水、雨水是水时,这就是判断。当我们由彼水是水而断言此水也是水时,我们也就完成了一个推理的过程,并且这种推理同时既是归纳的又是演绎的,它既是从个别事物中见到普遍性,也是由普遍性出发而断定个别事物。准此而论,克罗齐以为概念就是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synthesis a priori),其中包含了直觉与概念、个别与普遍、经验与理性、后天与先天的成份。
克罗齐这种概念说的要害在于,概念必须包含直觉在内,并以直觉作为它的先决条件,普遍性的概念不能脱离个别性的直觉。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定义,它并不像形式逻辑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座空中楼阁,可以把给出这一定义的具体时间、地点、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情形略去不管。(注:克罗齐:Logic,London,Macmillan,1917.p.207.)相反地,任何思想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由具体的个人所完成的。对普遍性的思想不能脱离体现这普遍性的具体个例而成立。思想就是要进行判断,一切判断都是要针对某一具体情形下的某一问题来作出解答,因此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思想”的判断就其实质而论,就都只能是个别判断(individual judgment)。任何判断都是由主词和宾词所构成的, 判断中同时包涵了直觉的与逻辑的成分在内,主词乃是概念所要依据的直觉所产生的个别事物,宾词则是由直觉而发展来的概念的普遍性质,每一个判断因此就都同时既是普遍性的个别化,又是个别事物的普遍化。思想就是要从事实(直觉的个别事物)中看出理性(普遍性),又要从理性(普遍性质)中看到它须臾不可离弃的事实(个例)。事实与理性、事实的真理与理性的真理并非截然有别,而原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黑格尔的名言:“实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实在的”,正该从这意义上来加以理解。
一切历史知识在其最简单的表述形式中,都是由个别判断构成的,因此“直觉的成分与逻辑的成分对它来说就都是不可或缺的,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注:克罗齐:Logic,London,Macmillan,1917.p.279.)历史的判断可以归结为确定“某事已经发生”的命题,如凯撒被刺杀,但丁著《神曲》等。在分析这些命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每个命题都是由执行主词功能的直觉性成分和执行宾词功能的逻辑性成分结合在一起的。前者如凯撒、但丁、神曲等直觉物,后者如刺杀、艺术创作等概念。对于历史判断中主词和宾词的这种分别,使得克罗齐很自然地得出了这种结论:既然哲学思维是以研究逻辑性的概念为己任的,那么历史就是以哲学思维作为它的前提条件的,因而“所有哲学思维的进步都转变为一种历史知识的进步”。(注:克罗齐:Whatis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p.136.)例如,一旦我们对于艺术的本质,对于诗歌创作的性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时,对于但丁著《神曲》这一事实我们就会有更加清楚和正确的认识。
从哲学与历史、哲学思维与历史思维并存于构成了历史命题的个别判断而言,哲学思维所要处理的乃是历史判断中的逻辑性的成分,因而构成了历史学和历史思维的前提条件和一个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克罗齐后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断言,哲学乃是历史学的方法论阶段,“也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和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发”,就此而论,“如果一个哲学问题显得完全无益于历史判断,那就证明这个问题是无用的,是提得很糟糕的,事实上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问题即一个哲学命题的解决不仅不能使历史变得更可理解,反而使历史更加晦涩……那就证明那一命题以及与其有关的哲学是武断的”。(注: 克罗齐:
History: It's
Theory
andPractice . New York,Russell&Russell,1960,p.151~152.)可以说,哲学是统一于历史的。
但是哲学和历史、哲学思维与历史思维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统一的还是同一的,克罗齐由他的逻辑学说出发并没有能够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统一,或者是同一,二者必居其一而不可能同时既是同一的又是统一的。(注:当然,从别的哲学立场出发,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既不统一,又不同一,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同时兼有同一和统一两种关系。)当他认为由哲学处理的是判断中的逻辑成分,哲学构成为历史学的方法论阶段时,克罗齐显然是在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并且是哲学和哲学思维统一于历史和历史思维。但是,另一方面,克罗齐又提出,所有的概念都可视为一个下定义的判断或者说是界定判断(judgment of definition),而每一界定都是特定情形下的具体个人,对于向他呈现出来的具体问题作出的解答,就此而言,概念也即界定判断是与个别判断相同一的。(注:见克罗齐: Logic ,Part I.Section Ⅲ.Chap.I.)既然哲学所研究的概念与历史知识所由以构成的个别判断是同一的,那么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就是当然的结论了。但是这样的推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圆通无碍。克罗齐是爱好文学艺术的,在美学和文学评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哲学论著在文字风格上也是难得的清澈流畅。可是一旦加以仔细的省视,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有些似乎是水到渠成的结论,实际上并没有被严格地论证过。即如这里的论点而言,从克罗齐的逻辑学出发,固然可以说概念蕴含着判断,但这并不等于说概念本身就是判断或概念与判断同一。再有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历史知识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上来说,乃是个别判断,但是,个别判断是否就都是历史判断呢?如果个别判断并不就都是历史判断,那么克罗齐的结论就不能成立。而如果个别判断就是历史判断(克罗齐当然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岂不是一切真正的知识就都是历史知识的领域?照此思路,克罗齐自己的“概念乃是逻辑的先天综合”,黑格尔的“实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实在的”,这些通常只视为哲学命题的,也要被归于历史知识之列了。这样的历史概念如果成立,也和我们通常的(包括克罗齐本人在《逻辑学》一书论历史专章中的)历史概念大为不同了。
总之,历史与哲学、历史思维与哲学思维二者是统一还是同一,对于这两种可能关系之间所隐含的矛盾,克罗齐大概始终没有足够的意识。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三
如果说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必要前提,历史学没有逻辑的(也即哲学的)成分就不能成立的话,那么克罗齐在《逻辑学》中专门论证历史与哲学同一的一章中,主要是强调历史同样地乃是哲学的必要前提,没有直觉的(也即历史的)成分,哲学也同样无法成立。
每一个哲学体系或哲学命题,都归根结底乃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条件下由某一特定个人的心灵中所产生出来的,因而总是受到各种对哲学家而言外在或内在的历史条件所限制的。哲学的产生,乃是要解释呈现于哲学家心灵中的问题。而问题本身的提出,就受制于当时当地的各种历史条件。克罗齐举例说,康德的哲学在雅典伯里克利统治的黄金时代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因为它是以文艺复兴以来各门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就,作为它的前提条件的。康德哲学是以对自然科学的普遍有效性进行论证为己任的,构成他的哲学出发点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不可能出现在以前的时代。而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本身,又是以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为前提的,如此类推,不一而足。
任何哲学家都不可能使自己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外,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制约着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这些事件就活在他的骨髓之中,活在他的血肉之中,他不可能将它们撇在一旁。他必须顾及到它们,也就是说要历史性地去认识它们。他的哲学的广度就取决于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注:见克罗齐:Logic,PartI.Section Ⅲ.Chap.I.p.312.)哲学思想固然是人类精神的创造, 而不单纯是历史条件的消极产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不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哲学思想既受到哲学家所处具体历史情形的制约,又同样受到哲学家本人对于历史(包括哲学史)的认识深刻到了何种程度的制约。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说,有的大哲学家并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甚至是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史知识,却比一些博古通今的哲学家有着远为深刻的哲学洞见,这种情形又该如何解释?在克罗齐看来,这样的哲学家绝非完全对于历史是无知的,他必定在某些侧面仍有着过人的历史见识,而在他真正对于历史无知的那些侧面,在他的哲学中也必定体现为种种薄弱的环节。而肤浅的哲学家表面上的博学并非真正具有历史感的知识,只不过是一堆僵死的丧失了生气的教条而已。
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历史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哲学也因而永远不会有一个囊括了全部真理的体系而终结了哲学的发展,哲学如同历史一样每时每刻都是新的。即就同一个哲学家而言,人们对他思想的理解也会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个哲学命题的理解也不会完全一致,而必然是有差异的。哲学的连续不断的发展就是在连续不断地超越它自身,新的哲学命题是由于旧的哲学命题才成为可能的,而旧的哲学命题就活在后来的新的命题中,哲学的永恒就在于哲学思想本身的永恒发展中,就在于它永恒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完全消失,它会永恒地活跃在时时更新的哲学思想中。
一方面,历史学必定包含了哲学,不存在没有哲学的历史,历史知识和历史思维中必定有着思想和概念的因素。另一方面,哲学也不可能脱离历史,哲学乃是历史的产物,没有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会出现某种特定的哲学,一个哲学家的全部哲学就折射了他全部内在和外在的历史。这前一方面,是克罗齐在将历史归结为个别判断时所强调的;这后一方面则是克罗齐在专论历史与哲学同一的一章中所着重阐发的根本论点。由前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哲学制约着历史,哲学统一于历史;由后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历史制约着哲学,历史统一于哲学。但是克罗齐所力图论证的,乃是与金蒂莱有所不同的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前面已经谈到,他在认为哲学所要处理的是判断中的逻辑性成份,因而哲学是历史学的方法论阶段的同时,又由概念(也即界说判断)与个别判断相同一而推证出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在这里,他论证了历史制约着哲学之后,却又笔锋一转,认为历史与哲学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仍然多多少少是暂时性的(provisional)”,(注:见克罗齐:Logic, Part
I.SectionⅢ.Chap.I.p.324.) 它们之间根本的关系仍然是同一。 这里克罗齐所依赖的论据,仍然是简单的重申概念与个别判断的同一。这样的论断,就未免给人以过于牵强武断而又苍白无力的印象。他煞费苦心论证了的哲学与历史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何以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关系呢?这是他所没有恐怕也无法加以说明的。
四
历史与哲学同一的论点,是克罗齐在研读黑格尔和受到金蒂利的直接启发后提出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他在1909年出版的《逻辑学》中对这一论点的解说远不能说是成功的和一贯的。克罗齐对这一点也有所认识。在作为他全部精神哲学体系的结论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虽然并没有否认以前的论证,却明白地指出其中所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能够真正从精神一元论的前提出发,彻底消除那种把历史观不是当作活生生的当代史,而是当作僵死的编年史的历史观。(注:克罗齐: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p.61.)克罗齐曾在《美学》中把这种历史观称之为历史的主智主义(historical intellectualism)。(注:参见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第48页。)它实际上是将从事历史认识的个人置于历史之外来观察和研究历史,有如科学家是将自己与自然现象对立起来,以从事对后者的研究一样。但是这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这实际上是实证主义影响历史研究领域的产物。
克罗齐精神哲学的出发点在于,精神乃是唯一的实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外在于精神而存在。这样的立场很容易让我们中国读者想起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断言来,事实上,古今中外一切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都是由这样的前提而开始立论的。既然精神之外别无实在,一切认为存在着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历史事实的观点,包括黑格尔的历史观,就都不能摆脱二元论的窠臼,不能领会到哲学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哲学这一真理。在克罗齐看来,哲学与历史的同一乃是精神一元论的当然结论。在历史学家自身之外并没有所谓客观的事实,除却历史学家的精神而外,别无所谓客观的历史。历史乃是思想的产物。精神作为唯一的实在,乃是在生生不息地永远变化发展着的,由直觉而概念,由理论而实践,由经济活动而道德活动,而实践活动的产物又为作为理论活动起点的直觉提供了材料,如此循环往复而又不断上升。精神这种不断丰富自身和超越自身的活动就是历史,它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蕴涵了自身全部的历史,“精神自身就是历史,在历史存在的每一瞬间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且也是以往全部历史的结果。因此,精神就负载着它全部的历史, 历史是与精神自身恰相吻合的”。(注:克罗齐: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p.25.)它同时也就是哲学, 因为哲学唯一的内容就是全部实在也即精神的变化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克罗齐说:
“精神与世界是相吻合的。自然界乃是精神自身的一个契机或产物。因此它就超越了唯物主义的或者神学的原则,精神就是世界,是演化着的世界,它既是一,又是多,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它的历史就是它的哲学,它的哲学就是它的历史。”(注: 克罗齐: History: It's
Theory
andPractice,p.321.)
由这种绝对的精神一元论出发,生活与思想、精神与历史、历史与哲学就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原本就都是同一回事。回到历史知识的最简单的形式——判断上来说,一切判断都是个别与普遍的综合。就一般看法而言,个别是判断的主词,普遍是判断的宾词,判断因而就是个别物的普遍化。但在克罗齐看来,毋宁说判断的真正主词就是宾词,而真正的宾词则是主词,这样判断就表现为普遍性的个别化。(注: 克罗齐: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p.60.) 个别之普遍化与普遍之个别化原本是同一回事。哲学侧重在普遍性,而历史侧重于个别事物。但是个别不能脱离普遍,普遍也不能脱离个别。二元论所坚持的观念与事实,事实的真理与理性的真理的二分法在精神一元论这里就彻底崩溃了。一切真正的判断都是对精神活动某一具体的情势下断言,它同时既是历史,又是哲学,历史与哲学终究还是同一回事。另外,历史既然总是历史学家当下精神创造的产物,一切真正的历史就都只能是当代史,历史就不再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被提升为一种关于“永恒的现在”(the eternal present)的知识, 而哲学原本就是关于永恒的现在的知识,因此就二者都有关于“永恒的现在”而言,它们也是同一的。
五
克罗齐与金蒂利这两位年轻的志同道合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在力图扫清二元论的残余而建立起精神一元论时,都得出了哲学与历史同一的结论。但二人的意旨却有着很大的差别。金蒂利是反对克罗齐精神活动两度四阶段的学说的,认为肯定精神活动的多元性以及各种形式的活动之间的差异,最终会破坏一元论的立场。在他看来唯一需要肯定的乃是包容一切的当前的思想活动,哲学之外别无其它真正的精神活动,全部的历史因而就被哲学史所穷尽了。因此在金蒂利这里,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就可以被径直归结为哲学与哲学史的同一。(注: 参见 GuidoCalogero.On the So-called Identity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及Crespi,Contemporary Italian Thought,New York,Knopf,1926,chap.Ⅲ.)这样的思路虽然比之克罗齐而言似乎距离常识的看法更远,却也有着它在逻辑上的优越性,那就是它由于少了许多枝蔓而更加简洁一贯。
我们已经看到,克罗齐是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论证这一主题的。一方面,他由历史判断中必然包含逻辑性成分而得出哲学制约着历史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又由过往的全部历史都活在哲学家的血肉中,哲学家的思想乃是全部历史和他个人生活的结晶,而得出历史制约着哲学的结论。可以说,从克罗齐这两个方向的论证,都只能得出哲学与历史二者互相制约、互相蕴含,二者有着统一性的结论。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尤其是历史思维要以哲学思维为前提的论点,是当时颇为新颖而至今仍然富于启发性的。但是克罗齐却不满足于这样的结论,而进一步由概念与个别判断的同一而推论出哲学与历史的同一,这不但有牵强武断之嫌,而且与他在前一步已经得出的结论难免有矛盾冲突之处,毕竟互相制约与互相同一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同一(identity)只是指互相制约、互相蕴含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逻辑学》中对哲学与历史同一的论证就是成功的,而且能够为很多人所赞同。这个层次上的哲学和历史,是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和历史相当的,或者至少是相去不远的。这里的哲学乃是对于思想中普遍性、逻辑性成分的研究(相当于克罗齐整个哲学体系中与美学、经济学、伦理学鼎足而立的逻辑学),这里的历史乃是指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全部人类生活过去事实的总和(尽管在克罗齐看来它们只存在于我们当下的精神世界中)。 但是如果说同一乃是完全的等同(equation)的话,那么克罗齐在《逻辑学》中并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达到这个结论,相反他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所表达的观点却可以说是基本能够自圆其说。因为既然精神是唯一实在,精神的生展变化就是它的历史,而哲学所要研究的也正是这一唯一实在的生展变化,那么哲学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哲学,二者的同一就是顺理成章的推论了。只不过这后一层意义上的哲学和历史,与前一层意义上的哲学和历史就有很大的分别了。这里的哲学不徒是以概念为其对象,而是以全部实在即整个精神世界为它的研究对象,这里的历史也不徒只是有关人类过去的知识(虽然这种知识在克罗齐而言归根结底是对于当前的知识),而是对于整个精神世界各种活动形式的生展变化的知识,这样的历史知识“并不是一种知识,它就是知识本身,它全部充满并穷尽了人们认识的领域”。(注:克罗齐: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p.73,又见克罗齐: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45),pp.27-32.)这样的互相同一的哲学和历史(它们彼此就同时又都是对方)就已经把握和囊括了全部的实在世界,而远非第一层意义上的哲学和历史的概念所能范围的了。克罗齐本人似乎对于他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着哲学和历史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尽管他始终对于自己在《逻辑学》中对历史与哲学同一说的论证不满意,但也终究没有能够见出这一症结之所在。事实上他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论证后一层次上的哲学与历史的同一时,又在后来加上的附录中大谈哲学是历史学的方法论阶段,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其中所可能有的分别和抵牾之处。
实际上,克罗齐虽然早在1909年的《逻辑学》中就反复申说他的历史与哲学同一说,但是他所比较成功地论证了的,只是哲学与历史之互为条件,互相制约(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者的统一性)。这一点从别人对他这一论旨的不同理解也可以得到证明。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中评论说:“对于克罗齐,在他的思想的这一顶峰状态时(即《逻辑学》时期——引者),哲学的任务就限于思考各种概念的意义,这些概念作为思想的实际功能,仅只是作为历史判断的谓语而存在,……哲学仅仅是历史学之中的普遍的成份。”(注: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23页。) 卡尔则主要是从哲学乃是制约着哲学家的全部历史条件的结晶这一面,来理解克罗齐对历史与哲学关系的论述的。(注:见 H. W.Carr,The Philosophy of Benedetto Croce (New York,Russell,1969)中专论历史的一章。)本文认为,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与哲学同一(哲学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哲学),只有他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从精神一元论立场所作的阐发,才是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的。但正如柯林武德在别的地方所指出的,即使在这里,克罗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摇摆于历史与哲学的同一和哲学是历史的方法论阶段这两种论点之间, 使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模糊不清的。(注: G. R.Colling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W.Debbins ed.Austin,Univ.of Texas Press,1965.)对于不同意他的精神是唯一实在的哲学前提的人来说,历史与哲学的同一固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他所凸现了的历史与哲学、历史思维与哲学思维之互为条件,互相蕴含,却是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思考和研究的。
标签:哲学论文; 逻辑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哲学家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