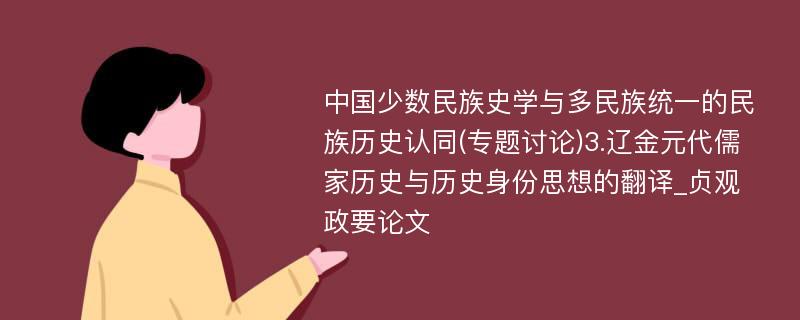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专题讨论)——3.辽、金、元的经史翻译与历史认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历史论文,史学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金、元时期,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汉文经史是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翻译的经史著作,不仅丰富了史书的表现形式,也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思想的发展。
辽代以契丹文翻译的史书见于记载的有三部:《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这三部书都是辽兴宗重熙年间契丹族史家萧韩家奴翻译的,其本传提及翻译的目的为:“欲帝知古今成败”[1](《文学传萧韩家奴传》)。也就是说,萧韩家奴翻译这三部史书的主旨在于历史教育,他想传播历史知识,弘扬史学的资治功用,使辽朝的皇帝能从历史学习中得到教益,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引人深思的是,在众多汉文史书中,萧韩家奴为什么选择《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这三部史书呢?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这其中的原因。从这三部书的内容看,《通历》是唐朝马总撰写的一部自“太古”至隋朝的编年体通史,着重记载历代君主的事迹;《贞观政要》是唐朝吴兢撰写的一部按专题记述的政治史,主要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君臣探讨治道的言论;《五代史》是宋初官修的史书,记述了五代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五十三年的历史,辽朝初年与这些政权有外交往来,彼此间也有冲突和战争。可以明确,萧韩家奴看中的这三部书,在当时看来,正好包含了贯通古今的历史内容,而且侧重于记述君主治国的事迹和言论。应该说,选择本身体现了契丹族史家萧韩家奴的卓识。进一步探寻萧韩家奴的思想根源,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萧韩家奴为使辽朝皇帝知古今成败而翻译这些史书,实际上是把契丹贵族为主而建立的辽政权视为唐、五代等政权的后继者。因此,往古的经验和教训,今世的历史演进都是可资鉴戒的。一定意义上说,萧韩家奴的思想代表了辽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对政治统治的继承性的理解,也是辽朝人古今观念的反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契丹族史家萧韩家奴对古今的认识与其他朝代的史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他所认为的“古”与“今”是从太古到唐、五代,并没有囿于族别的差异。透过他的古今认识,我们看到了契丹人的历史认同。辽道宗的华夷观也证实辽朝人在思想上是不自外于“中华”的。依据宋人洪皓《松漠纪闻》的记载,辽道宗时,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辽道宗说:“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又讲到“夷狄之有君”,而快读不敢讲,辽道宗则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2](卷上)这是从地缘上和文化上的历史认同。可见,辽朝虽然是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并且处在南北分治的时期,但是辽代的史家和政治家却有着强烈的历史认同意识。
金代以女真文翻译汉文经史是与其发展民族教育和选拔女真族人才相结合进行的。因而翻译工作得到了朝廷的重视,金代不但设有专门的译书机构译经所和弘文院,金朝皇帝还多次下诏令翻译汉文经史。据《金史》记载,金大定四年(1 164年),金世宗诏以女真字译书籍。金大定五年(1165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与《白氏策林》等书;金大定六年(1166年),又进《史记》与《西汉书》,金世宗诏令颁行。此后,参加译经史的人员越来越多,著作佐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忠、翰林修撰移刺杰及应奉翰林文字移刺履等都参与其中。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和《新唐书》,金世宗对宰臣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2](《世宗本纪下》)。同时译出这么多典籍,可以推断参与译书的人员应有一定的规模。是年,金世宗也以女真字《孝经》千部分赐护卫亲军。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又谕宰臣:“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云:“《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译《诗》、《礼》毕,试之可也。”[3](《选举志一》)由于金世宗时兴起的女真学是以教授女真文字和女真文翻译的汉文经史为主,金代仅金世宗大定年间以女真文翻译的汉文经史之书就有十几部。儒家的典籍大部分已经译出,如《尚书》、《周易》、《春秋》、《论语》、《孟子》、《孝经》等;《诗》、《礼》也纳入翻译计划;《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诸葛孔明传》等前代重要史籍也被译成了女真文。
那么,金代以女真文翻译的《尚书》与《春秋》等经史之书的影响又如何呢?可以说,金代经史翻译成效十分显著。其中,最直接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史翻译培养造就了一批女真族人才。金世宗的儿子显宗完颜允恭对此深有感触,他曾听完颜匡和驼满九住讨论伯夷、叔齐,对于完颜匡的言论很赞赏,并说:“不以女直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3](《完颜匡传》)也就是说,金朝统治者已经看到经史翻译对女真族人才培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二是把以女真文翻译的汉文经史作为金代女真学的教材,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儒家为主的学术传统与女真族古朴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提升了民族教育的层次,促进了女真民族的迅速进步,也加快了整个金朝社会发展的步伐。元代史臣对金代文治的肯定可以证明这一点①。实际上,金代经史翻译的影响不限于上述两点,其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分析金人经史翻译的思想渊源,可以知道,无论是发展女真学,还是教化女真人、提高女真人的素质,金人都是把汉文经史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来继承的。即金人从思想上承认历代陆续编撰而成的经史著作具有很宝贵的价值,所以,他们对这些经史教育所寄寓的期望很高,想从经史学习中增长见识,知晓仁义道德,提高女真人的整体素质。这种思想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所达到的效果是使传统的经史之书发挥其传承学术和教化民众的功用。同时,金朝经史之书在包括女真人在内的各民族受教育者中的传播,也推动了各民族历史思想的进步。金世宗时的女真族大臣唐括安礼就有着比较进步的民族观,他把女真猛安户和汉户视为一家,并指出:“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3](《唐括安礼传》)甚至特别强调保持女真国俗,极力主张维护女真人利益的金世宗,在某些时候也有“天下一家”的思想②。可以说,金代这种各民族“一家”观念的发展与经史的广泛传播有因果的关系,更为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金代情况大体相似,元代以蒙古文字翻译汉文经史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4](《世祖本纪二》)。这是忽必烈实行文治的一项重要举措。此后,元朝历任皇帝多效仿之。值得注意的是,元朝以蒙古文所译汉文经史选择性更强,就内容看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书:
一是选择传统史学中具有“资治”作用的史书。比如,元代皇帝多次诏命文臣翻译《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并加以刊行。据《元史》记载,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刊行蒙古畏兀儿字所书《资治通鉴》;元延祐元年(1314年),元仁宗认为《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元泰定帝统治时期,也曾命为之进讲的经筵官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译《资治通鉴》以进。《通鉴节要》更是被蒙古文译写后成为元代教授蒙古国子学诸生和诸路蒙古字学生徒的教材。《贞观政要》也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推崇而得到译刊和传播。元仁宗就认为《贞观政要》“有益于国家”,所以命译以国语刊行,使蒙古、色目人诵习。元文宗也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色目人察罕曾译《贞观政要》献朝廷。曹元用也译《贞观政要》为国语,行于一时。此外,察罕也曾受诏译唐太宗的《帝范》。元明善曾受命译《尚书》“其关政要者”。诸如此类的记载说明,“载前代兴亡治乱”和“有益于国家”的史书因深受蒙古族皇帝的青睐而先后被译为蒙古文。
二是当代史和一些重要文献(主要是实录和有关典章制度的诏诰及法规书)被指令译为蒙古文。按照传统的修史制度纂修的诸帝实录,往往要经过奏读才能纂定,而元朝的皇帝精通汉语者较少,因此要翻译成蒙古文后奏读,这在元朝从元世祖时开始逐渐成为制度。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这个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4](《世祖本纪十一》)。之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元世祖说:“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4](《世祖本纪十二》)可见,元世祖确实对进读的畏吾儿字文本的实录进行了审查。元元贞二年(1296年),兀都带等进所译蒙古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元成宗指出了其中记载错误和过细小之处。通过这样的奏读形式,元朝皇帝加强了对实录的监控,同时,促进了以蒙古文字翻译实录工作的深入开展,也推动了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同样,元朝以汉文编纂的一些《圣训》类的政书,在元泰定帝时期多数敕令译为蒙文,如《列圣制诏》、《大元通制》、《帝训》(《皇图大训》)和《世祖圣训》等,其目的大概是想要蒙古贵族遵循祖宗教诲,所以,《元史·泰定帝本纪》对泰定帝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责躬之实,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兹其所以为足称也。”[4](《泰定帝本纪二》)言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与其敕令翻译政书当有一定的关系。
还需要指出的是,元代也有以蒙古文撰著的史书被翻译成汉文的,如察罕就将蒙古文的《脱必赤颜》译为汉文,命名为《圣武开天纪》。这反映出元代的民族史学较辽金时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由上述元代所翻译经史的类别看,元朝的统治者是较为务实的,他们诏命翻译经史之书的目的很明确,即旨在为现实统治服务。所以,对有关典章制度的政书和有关治国安邦的经史尤为重视。这也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以往朝代统治方法和统治经验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同样是肯定了这些经史的价值。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与金人经史翻译为发展民族教育不完全相同,元人的经史翻译,受益最大的是蒙古族统治者,他们从历史上具有“资治”作用的史书中寻找了一些治理天下的良方,自忽必烈以后的蒙古族君主多注重沿袭前代的“宏规”、“定制”。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明确提出“奄四海以宅尊”,“绍百王而纪统”的政治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他把所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国历代政权之列,同时,也强调了其“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特色。此后,元代其他皇帝继续从这些经史中提取政治智慧,自觉向历史上圣明的君主看齐,遵循他们的为政之道。如元顺帝一次曾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监察御史绰台、宋绍明进谏,得到赐金币的嘉奖。绰台等固辞,元顺帝说:“昔魏徵进谏,唐太宗未尝不赏,汝其受之。”[4](顺帝本纪二)这些做法表明,元朝蒙古族皇帝通过学习传统的经史,已从思想意识上成为“中国之主”,以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维护者。在承袭与变通中维系和发展了君主治国之术,丰富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制度体系,出现了多种文化的交融与互补。
综上,辽、金、元时期的经史翻译,虽然并不等同于历史撰述,但是这三朝以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汉文经史直接促进了少数民族史学的进步,同时也迅速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尤其是其居于统治地位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进步最为显著。今天看来,辽、金、元时期经史翻译更有其思想的价值,尽管三朝经史翻译的主要目的各不相同,体现在翻译之书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但是,辽、金、元三朝对古与今、治与统却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即认为以往的朝代与当时的朝代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这种历史认同,使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多民族重新组合的辽、金、元时代得以延续和发展,多民族一体、一家与同为中华的观念和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使辽、金、元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注释:
①《金史·文艺传上》“序”有言:“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
②《金史·唐括安礼传》记载,金世宗对女真人有超迁格提出质疑说:“天下一家,独女直有超迁格,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