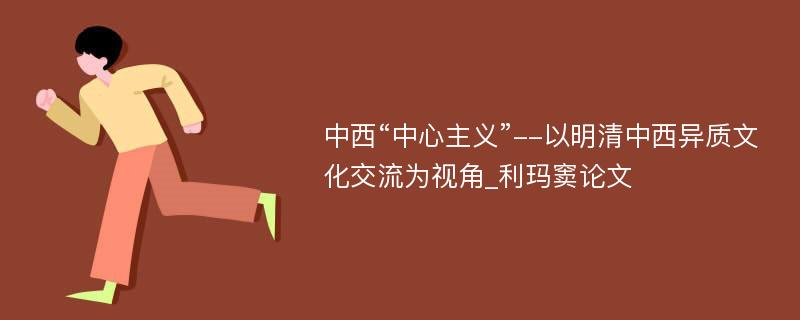
中西之“中心主义”——以明清之际中西异质文化交流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文化交流论文,明清论文,视角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5-0076-(08)
在谈到中西异质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中心主义”;而“中心主义”又总是无可避免地跟“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这一问题,我认为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去看,尤其是要将这一问题放在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交往的历史语境中来透视。这里主要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普遍的中心主义
中心主义是人类文化交往史上的普遍现象,人类文化交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和普遍的中心主义相伴随的过程。正确对待这一现象,能使人冷静地面对文化交流当中的种种不平衡甚至不平等现象,并从容地处理之。
生物特质的中心主义。中心主义之普遍存在与人类的生物本性是密切相关的。汤因比认为,自我中心是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本性,而这种自我中心又是各种中心主义的本质原因。从人的角度看,他认为:“当人注视宇宙时,他对宇宙的奥秘不过是投之一瞥,而且这甚至可能是不可靠的。人类观察者不得不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点上选择一个方向,这样他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成为人的一部分代价。因此他的观点必然是片面的、主观的。”就是说,人类观察世界总要有一个视角(perspective),而这视角的选择,往往体现人类的主观性,而这主观性,从哲学本质上讲,就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一个人选择这一个角度,而另一个人一定要选择另一个角度呢?其中起作用的就是这种主观性,而主观性的形成又是极其复杂的。在汤因比看来,这种自我中心不仅表现在人类身上,它也是整个生物界的共同特点。他说:“自我中心不仅是人类,而且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具有的一种内在限制和缺陷。”他把生物求生或生长的本能,也看成是自我中心的体现:“在地球的生命中,自我中心的作用是两相冲突的。一方面,自我中心显然是地球上生命的本质。的确,一个生物也许会被定义为宇宙间微小的和从属的部分,它利用狡猾的机巧,使自身部分地脱离了其他生物,并且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竭力使宇宙中的其他生物服务于它自私的目的。换言之,每一种生物都竭力使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所以,对于每个生物来说,“自我中心是生物存在不可缺少的,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之一”(比如狮子就会用尿液来“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坚决驱逐胆敢来犯者)。这是汤因比从纯客观的方面对自我中心所作的探究。
接着,他又从社会学的角度和伦理道德角度来看自我中心的问题。他认为:“自我中心成了生命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必要条件也是一桩罪恶。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一方面,自我中心是一种生物本能,另一方面,它又跟人类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就使得人类(且不管生物界)不得不在错误当中生存:“既然自我中心既为生命所必需又是会受到报应的一种罪恶,那么,每一种生物都发现自身处于终身的困境之中。”于是,作为具有理性的人类,就得面对自我中心这一问题。”[1](P11~13)汤因比对中心主义的探讨,虽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但其结论又让人们感到悲观;由此再一次认识到,人类的确是生活在一种“两难”(dilemma)当中。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人类的各种中心主义实际上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进一步延伸,是自我中心在某个群体、某个民族、某个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内的强烈的、偏颇的体现。生物界的进化发展,一般是以古生物学家所谓的“优势种”(dominant types)的一系列的演替来体现的,每一优势种都有相应的生存环境;其生存环境大小,取决于它的优势的大小;但优势种并不是恒定的,优势种可以演化或蜕化为劣势种。在其蜕化或另一物种取代它的过程中,自我中心(求生本能)就是起作用的因素;只是,这当中没有道德的成分。而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各群体同样也是在不平衡中发展的;其自我中心的本能或天性,自然就会发展成所谓的优势集团或群体。当人类处于隔绝状态时,这种自我中心并不会表现出什么危害性,但是当群体和群体交往时,这种危害性就表现出来,即表现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蔑视,或同化,或征服。总之,中心主义从一个角度看,是自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是畸形。
社会特质的中心主义。人类在以群体形式生存且和其他群体发生交往时,其自我中心的生物本能或禀性便表现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心主义”。正像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区别是靠差异来界定那样,差异也将群体和群体区分开来。日本学者福泽谕吉说:“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因此,所谓轻就是说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说比恶者善,如果不互相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恶的问题。”[2](P1)群体的强大或弱小,正是在这比较中见出。但是,重物之为重物,是人通过比较衡量得出;重物本身它不会瞧不起轻物,所以,物体间就不可能存在中心主义的问题。而人群就不一样;人是主观的人,自我中心的人。当人发现自己在群体中比别人高出时,由于其自我中心的本性,他就会产生偏见,而不能将他者放在跟自己同等的位置上来审视。这样,中心主义便由生物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上,中心主义的实际形成,跟经济和强力密切相关;近代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便属于这一类。地理上的隔绝,也会造成中心主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中,由于一个群体很少或没有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常常会产生一种既封闭又自大的心理,进而上升为一种区域性质的中心主义。中国与外界的长期隔绝,是形成华夏中心主义的原因之一。此外,宗教禀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像基督教,它就是要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它不可能自愿处于从属的地位。总之,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中心主义,由于它们形成的因素不同,在研究分析时当然应该区别对待。不应该将中心主义问题抽象化。
中心与边缘。事实证明,中心也是边缘造就的。在欧洲这个中心找到中国之前,中国绝对是一个中心;就是在这两个中心相遇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然是以世界的中心自居的。单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间200年左右的文化交流也属“旗鼓相当”的文化对话。耶稣会士进来时,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华夏中心者;但耶稣会士进来后的数百年的历史,却是欧洲逐渐成为中心、中国逐渐丧失中心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人由视西洋人为“西夷”最终转变成甘愿承认别人的比自己的好,到后来,就一切都以西方为标准了。这就是利玛窦在《札记》中所说中国人的一种“天真”脾气。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3](P34)这种“脾气”很容易导致中心位置和中心意识的失落。两个中心相遇的初期必然是对抗,一旦在对抗中分出“高下”,一个中心便成为边缘;而这个边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不自觉地去认可、服从、成全乃至拥护新的中心。当下,反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后殖民时代的热门,但很多学者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中心,用西方的理论来反西方,借用西方的话语试图发出东方的声音。退一步说,当他们提出反西方中心主义时,他们实际上已经以西方为中心了;换言之,他们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暗含着这样一种心态,即自己不是中心。
共时地看,在某一时间点上,在一个可供观照的空间中,中心只有一个,边缘可以有许多;当然,在某一时间点上,也存在着许多自认为的中心。中心是永恒的,平衡是暂时的;中心会受到边缘的挑战,边缘在向中心的挑战中,可能会成为新的中心。世界的不平衡状态从人类平等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但另一面也有它的积极性:不平衡状态也是促进世界发展的动力之一;人类历史就是中心和边缘的此消彼长的历史。当然,这不能成为人们维护各种中心主义的理由,毕竟中心主义表现出的是人性中的坏的方面。人们在反中心主义的时候,固然有反霸权的意味,但其中多少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愤愤不平的心理:因为我不是中心。
二、从明清间天儒交涉看华夏中心主义
华夏中心主义的形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长期在地理上处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隔绝的状态,使得中国很少有与外界交往的机会;二是儒家学说的正典化,接着就是由正典化而神圣化。其实这两者又是互为因果的:隔绝的地理环境促使中国人在没有外来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这一点又实际上为孔子的学说能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充分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等到孔子集古代儒家之大成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典之后,反过来又进一步使本来就不关心外界的中国人的脾性更趋于内敛。两者相互作用,可以说是良性循环,也可以说是恶性循环。总之,长此以往,中国人自然会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之外别无更好的东西。于是,华夷之见遂行世,夷夏之防便形成。华夏中心主义是实际上延续最长的中心主义之一。此外华夏中心主义的形成也跟中国在物质生产和科技上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有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物质生产和科技水平都是比欧洲先进的。
中心主义只有在群体和群体相遇时才能见出,或者说,只有在比较当中才能见出。华夏中心主义在有异质文化进入之前,它还只是一种夜郎自大的倾向。佛教之东披,没有对它产生什么威胁,更没有撼动它的地位,这反而增加了中国人的优越感。华夏中心主义得到凸现是明清间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时候。这期间两个“中心”相遇,碰得火花飞溅。这火花主要于两处最为炽烈,一是在破邪者那里,一是在清廷皇帝那里。就是在清代基督教传教的高潮过去之后,华夏中心主义仍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锋芒不减,可见,在中西文化的第一个回合后,华夏中心主义的大厦并没有被撼动;这可从当时的部分反教士大夫(破邪者)《四库全书》编撰者那里看出。
破邪者们破“西夷”之“邪”,其立场体现的是典型的中心主义特征。他们破邪的根据之一就是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夷变夏者,未闻变于夷者也。”[4]在他们看来,既然是“夷”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东西。在破邪思路上,他们认为中国的学术已经完备,凡世间所需要的中国都已齐备,无需外人多事,更何况是夷人;更何况,“凡人所信,唯耳与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5]于是,凡西人所传,判断其有理无理,根据就是中国已有的书籍;若是中国的古书中没有的,那么就是“诞妄不可考”,就是“不见于经”,就是不可信的,然后就加以驳斥、排斥;于是,中国的一切,学术、器用、王化,等等,无一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大明帝国、大清帝国,于是世界上就不能再有“大”字出现,连“大西洋”之“大”也是对我王化的蔑视。所以,沈榷参“远夷”的理由之一便是:他们“自称其国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炤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6]所谓“归化”,就是边缘向中心靠拢;然而,所来之人却是以中心自居的。利玛窦带来的万国全图其实是破中国天下观或华夏中心主义的一大利器。它的确使一部分士大夫认识到了世界之大,中国不是“天下”。所以,有人说是耶稣会士启蒙了中国人的“‘世界’观”。[7](P170)但万国全图也令华夏中心主义者们义愤填膺。官至户部郎中的魏涪指责道:“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8]这是极端的中心主义的体现,而且是一种盲目加愚昧的中心主义。的确,当一种中心主义过分膨胀,过分盲目时,它往往会带几分愚昧气的。
康熙是中国少数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热爱西洋科学,曾热衷于西洋历算,这使得他的胸襟比以往许多君主的心胸都要开阔得多,他的“世界”观比许多儒臣还要先进。但这位异族征服者在征服中国疆域的同时,也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征服。在激烈的“中国礼仪之争”中,这位满族皇帝处处维护的是儒家的道统。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发布禁令后,康熙毫不让步,只说:“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指教皇的使节),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9](P77)康熙还针对教皇使节严嘉乐说:“愚不识字,胆敢妄谈中国之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9](P65)在康熙看来,中国的经书是神圣的,他所统治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要在中国传教,就得按照中国的规矩办事,“他者”要适应“我”,而不是“我”去适应“他者”。据说,康熙不但待耶稣会士甚好,甚至曾经欲将天主教收入中国,成为中国自己管理的宗教,以脱离罗马的控制。[9](P69)这里所表现出的无疑是一个中心主义者的姿态。
此外,对于康熙帝之酷爱科学,也要做一辩证分析。康熙钻研数理一方面体现了他对科学的热心,但也不无旗人好玩物的嫌疑。尽管他那样认真地听传教士们给他讲科学,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信念他是没有动摇过的。雍正、乾隆肯留那么多传教士在朝廷,很大程度是因为那些传教士也是优秀的科学家、画师、能工巧匠,他们滞留京都,能给皇帝制造许多可供玩赏的器物。乾隆对马戛尔说的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心主义的心态,他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0](P254)
虽然耶稣会士输入的西方科学“启蒙”了一部分中国人,但并没有真正撼动华夏中心主义,更谈不上铲除它。在激烈碰撞过后的平静中,华夏中心主义还是稳稳地占据着中国意识形态的内核。这在《四库全书》的编撰方针中可以见出。
《四库全书》的编撰开始于18世纪的后半期,其时中国已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西潮冲击,但从这套《全书》的编撰中,可以看到,华夏中心主义仍然是岿然不动。人们都以为著书立说是阐明观点、表明立场的最好方法之一,但类书或百科全书之类的编撰同样能体现编撰者的观点立场,同样能体现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狄德罗、罗梭等“百科全书派”于启蒙运动期间编撰《百科全书》就是一例。《四库全书》作为中国的第一部最大规模的工具书,当然也体现了编者的政治观点,学术趣味,以及他们的世界观。这可以从他们对各地所采集上来的各种书籍的取舍上,以及对所收、所存目的书籍“提要”的撰写上见出。
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及西方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在200多年间,著译了大量的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流传也很广泛。传教士这期间所著约有数百种,涉及的学科或主题也相当广泛,除了宗教神学类之外,涉及最多的是西方科学;这些科学主要有天文历算、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农学、地理学、语言学、音韵学,等等。他们所著译,应占明清间全国著译书籍的相当大的比重,但能收入《四库全书》的,仅仅是少数,显然低于这时期收入《四库全书》著作的平均比例。
明清间西人著译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情况如下:
1.《新法算书》西人和中国人合译天文算法类
2.《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天文算法类
3.《测量法义一卷测量异同一卷勾股义一卷》天文算法类
4.《简平仪说》熊三拔述,徐光启笔录天文算法类
5.《圜容较义》利玛窦授 李之藻演天文算法类
6.《天问略》阳玛诺撰天文算法类
7.《表度说》熊三拔口授 周子愚等笔记天文算法类
8.《乾坤体义》利玛窦辑天文算法类
9.《同文算指》利玛窦撰 李之藻演天文算法类
10.《泰西水法》熊三拔说 徐光启笔录农家类
11.《奇器图说三卷诸器图说一卷》邓玉函述 王徵撰普录类
12.《职方外纪》艾儒略口授 杨廷筠笔录地理类
13.《坤舆图说》南怀仁著地理类
明清间西人著译《四库全书》存目者情况如下:
1.《七克》庞迪我著杂家类
2.《辩学遗牍》利玛窦撰杂家类
3.《寰有诠》傅凡际撰杂家类
4.《西学凡》艾儒略撰杂家类
5.《二十五言》利玛窦撰杂家类
6.《天主实义》利玛窦撰杂家类
7.《畸人十篇》利玛窦撰杂家类
8.《交友论》利玛窦撰杂家类
9.《灵言蠡勺》毕方济撰杂家类
10.《空际格致》 高一志撰杂家类
以上所列,一目了然,《四库全书》的编撰者收录西士所著译者主要是侧重于科学类的,共13部。科学类中又侧重于天文历法类,共8部,占科学类的一大半。凡涉及教理者,一律不收;即便其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者,也只是存目,且一律归入“杂家类”了之。而《西学凡》虽涉及到基督教的一些观念,但主要是述西国建学育才之法的,却也没有收入。《天主实义》虽然是一本流传甚广影响巨大的附儒排佛宣传基督教的著作,同样被拒斥,但因其影响甚大,流传甚广,而被收入杂家类存目。可见,从编选者对西士著译的选择上,就体现出他们强烈的主观性,维护传统思想的倾向性,以及他们对基督教的整体上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看出传教士200多年的努力,并没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留下深刻的印痕。
编选者的态度还可以从他们对所选或存目的西人著译所写的“提要”中见出。这些提要,有的能对所录书籍作近乎纯客观的评述和介绍;有的则辨其“正”、“邪”,提醒读者,取其“正”,舍其“邪”;有的是因为某些著作曾有著名的士大夫参与翻译,故肯收录;有的则完全从华夏中心主义的角度贬斥西人的著作,一切都是自己的好。条析如下:
第一类提要认为,西人所传之书确有可取之处,故而录之,这体现了中国人重西人所传科学的一面。这类提要往往行文上较为客观。如对《新法算书》的介绍:“书末历法西传,新法表异二种,则汤若望入本朝后所作,而附刻以行者。其中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罗巴历学之蕴。”[11]如其书中既有科学内容又有基督教观念,他们便对这两方面内容区别对待:“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有深意。”[12]阳玛诺著《天问略》,属科学类,但当中有基督教的说教,尤其是序言中;于是,便删略其序,录其正文:“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13]
第二类提要是表明某些书之所以收录或存目,是因为它们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之中国的史书上提及过,不录不妥(吸收它们实际上是为了体现他们对中国书的尊重);或者是为了“增广异闻”,姑且录之;或者是因为某些书中某种他们自以为的错误,录之是为了驳斥之。对傅凡际撰《寰有诠》就是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提要”说:“其书本不足以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或诬,故著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14]要是《明史·艺文志》没有提到过《寰有诠》,那它或许没有被收录的资格。《奇器图说》本属物理学方面的著作,但编撰者们觉得书中所述不过为器末之学,仅作存目处理;这也体现了中西方对所谓“实学”的不同认识。“提要”说:“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之溥,录而存之,固未当不可备一家之学也。”[15]
第三类是对一些影响较大姑且存之的书籍进行驳斥,指出基督教教可笑之处的同时,显示儒家的道术是何等的完备。像《二十五言》和《辩学遗牍》都遭到这样的待遇。我还不很清楚,既然这些书他们一律看不惯为什么又一定要收录或存目;而这类书明末清初时是很多的;他们收录这类书,是不是完全因为它们影响较大,还是故意为了驳斥它们呢?比如对利玛窦撰《二十五言》,在他们看来是一无可取之处,录之似乎就是要让中国人明白,基督教是多么荒唐而已。“提要”说:此二十五条“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姻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之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16]对于记录利玛窦与佛教界的辩论文字的《辩学遗牍》,《四库全书》也予以存目;“提要”编撰者以儒家这一“第三者”的身份看佛、耶相斗的姿态,很是耐人寻味:“是编乃其(利玛窦)与虞淳熙论释氏书,及辩莲池和尚竹窗三笔,攻击天主教之说也。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校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17]在《四库全书》编撰者看来,要辟基督教佛家不能胜任,惟儒家;要辟佛家基督教自己也不能胜任,惟儒家。在这里,儒家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
总之,尽管经历了西潮的第一次大冲击,从《四库全书》编撰者那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华夏中心主义的姿态。对中国之外的一切,仍然那样漠视。就是在那些比较开明的信教士大夫和那些同情基督教的文人那里,其实他们身上并不是没有华夏中心主义的痕迹。徐光启虽然竭力为传教士辩护,视基督教为敦风化俗的良方,但是,应注意到,在他那里儒家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基督教对他来说可以“益儒”而不可用它来“易儒”。儒家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应该说仍然处于中心位置;他对西方所持的绝不是一个边缘者的姿态。还有那些曾经对传教士趋之若鹜的闽中人士也是如此。以前只从他们的诗歌中看到传教士们“西来孔子”的形象,只看到传教士们的儒雅风度之类。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人们会注意到他们都是以主人、以中心者的视角去看西人的。《熙朝崇正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是如此。叶向高写道:“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从中可以看出,被赞颂的那位西儒,是向慕而来的;他来是因为中华的儒理是精湛的;他来是因为中华的风化是文明的;他来不是要用他们的道取代中华的理,而是要用他们的道印证中华的理;所以,中华自然是中心,他们是从边缘来。一句话,这些文人决不相信传教士们是要用他们的中心来取代中华的中心;何况,他们相信没有谁能超越中华。
三、从明清间天儒交涉看欧洲中心主义
今天所谈论的欧洲中心主义跟作为欧洲文化之一部分的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撇开基督教讨论欧洲中心主义的话,必然不得要领;基督教至少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源之一。这在明清之际在华基督教那里就可以证实。明清间的中华大地上同时有两个中心并存:一个是由来已久但其颓势已显露无遗的华夏中心主义,一个是上升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双方都以中心的形象出现而且各不相让,结果“不欢而散”。
利玛窦初到京城时承认自己是以“陪臣”身份“辞离本国,航海而来”的,来中国是“为贡献土物”,是因为“逖闻天朝声教文物,窃欲沾被其余”,并愿意“终身为氓”;总之,他是以边缘者的身份,向化而来,所以得到万历帝的许可在京城住下。利玛窦初来乍到时,首先“下榻”在“既无门,也无桌椅板凳,连床也没有的”[18](P344)四夷馆。这不是官员们“工作失误”,不是他们粗心,中华之外来的人都是住在这里的。就是说,利玛窦起初是被列入夷人行列的;就是说,他能住下来,是因为他是“边缘者”,是对“中心者”向慕的,是不会对中心构成威胁的。利玛窦在华近30年,一直非常谨慎。但是,他还是按捺不住,终于在《天主实义》等书中表现出他对佛教的排斥,对儒家阳褒阴贬之势呼之欲出;“中心”渐渐显露。经过一段策略性的伪装之后,传教士们必定要回归“正题”的。尽管我们充分肯定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肯定他们对部分士大夫的世界观的启蒙,但他们航海而来的真正目的是要传播基督的福音;而且,只要他们传播其一神宗教,他们就不可能以边缘者的身份出现,因为他们的宗教是唯一的,是属于万民的教,是属于普天下的教;不但犹太人是上帝创造的,欧洲人是上帝创造的,中国人——在他们看来——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中国人就得皈依基督教,至于儒家,它为基督教完成了“方便法门”的使命后,也得让路。因为《圣经》上说过:“他(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19](16:15-17)这“万民”当然包括中国人,中国人不受洗当然也不能“得救”,中国人不信当然也会被“定罪”。所以,基督教的禀性注定了要征服整个世界;要征服整个世界者,当然必定会以中心者的姿态君临边缘;所以,从这里就不难发现欧洲中心主义的“奥秘”了。
利玛窦曾记述他来到中国时所看到的情况及其他的看法:
中国偶像崇拜这个三首巨蟒较之莱恩纳湖的怪蟒更为恐怖,它数千年来不遭反抗地暴虐统治着亿万人的灵魂,动辄要把他们打入地狱的深渊,而我们耶稣会本着自身的宗旨,奋起与之战斗,跨越千山万水,穿过许多王国,从遥远的国度来此拯救不幸的灵魂,使之免遭永恒的天谴。我们耶稣会坚信上帝的慈悲和许诺,不为艰难险阻所吓倒,而我们进入这个帝国,原本极其危险而困难,因为中华帝国严严实实对外国人封闭,而且人口众多,他们个个都要维护自己的错误。其实,没有任何尘世力量或地狱力量抵挡得住圣十字的王国和武器。[18](P9)
因为利玛窦这是写给欧洲人看的,所以就毫不讳言他对作为异教文化的中国文化的看法;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坚定的乃至狂热的传教士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他相信中国人是生活在错误之中,另一方面他坚信自己的宗教的教义是无坚不摧的。由此可以看出,他早期以边缘者身份出现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
西方传教士逐渐露出他们中心者的姿态主要是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并在18世纪初“礼仪之争”最激烈时达到高潮。“礼仪之争”是中西这两个中心在双方都无法宽容的境地而最终大爆发的。一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福音,一方是千年一贯的儒家道统;双方都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凌驾于对方,且由于都认为自己是中心,偏见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固然可以认为,宗教是异质文化交流的载体,但至此,人们又发现,如果像基督教那样一味强调其自身的唯一性,宗教既是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媒介,同时也会是异质文化间交流的障碍;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清除异质文化交流的障碍,它也可以把交流之桥于瞬间砍断。明清间的在华基督教的交流方式有许多地方都是无可指摘的,它带来了西方的科学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最终问题的症结却出在基督教的禀性上。
所以,从这段交往中,我可以得出结论,欧洲中心主义的关键机枢是在基督教上。
收稿日期:2006-01-02
标签:利玛窦论文; 文化论文; 自我中心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明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传教士论文; 基督教论文; 儒家论文; 华夏集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