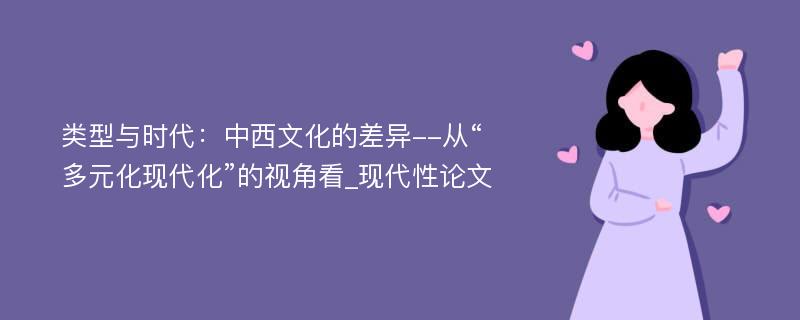
类型与时代:中西文化之别——“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现代性论文,之别论文,视野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性动向;当然,它首先从欧洲开始,就动力来源及展开时空而言,现代化过程无疑呈现了由西向东的延展性。在此意义上,现代化以及由此过程而来的“现代性”,首先是西方性的。无论在现代化发源地的西方还是在接受西方现代化影响的东方,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曾经认为这个现代化过程具有同一的模式,与之相应,“现代性”亦是一个单数概念(modernity)。然而,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许多不同区域都逐渐进入了所谓现代化阶段,而它们所呈现的现代性则各有特征,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现代性表现:这不仅存在于现代化的先发和后发世界之间,而且,即使在欧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之间,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它们的差异。似乎可以说,现代性从最初的单数成为复数,这一点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学术思想界,所谓“多元现代性”突显出来,日益成为一个关注焦点。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学术刊物DAEDALUS,在新世纪之交的2000年冬季号,专以“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为题,刊出一组包括艾森斯塔特(S.N.Eisenatadt)《多元现代性》在内的论文,清楚明确地质疑了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世界上普遍而同一模式的观念。
这一意识,对西方世界而言,确实需要在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逐渐成型之后才呈现出来,在此之前,它并不构成真正的问题性。然而,在非西方世界,比如说中国,却似乎已可窥见些许痕迹——虽然,20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思想者不会以“多元现代性”的名义展开论说。
一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根本处境,即中西的相遇和冲突。“西方”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而且,现代的这个“西”——欧美之“西方”不同于以往那个“西”——天竺之“西天”,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强大“他者”,对于中国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构成全面的压力,直接威胁到本土世界的存续。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双方在这样的一种基本是单向度的关系之中,极易形成一种单线性的观念反应。
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反应,依照梁启超1922年所撰《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清楚明了的解释,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最后是文化的逐步深入:“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合乎历史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认可。不过,如果仔细考虑这一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描述,可以清楚意识到它在中西之间展开多层面全面比较的后面所蕴含的单一性:即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根本上,中国比较西方,都“感觉不足”。而这正是现代认识的主流。
19世纪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虽然认为中国文化本身有欠缺,然而,西方的外来冲击尚不足构成根本性的动摇。在这个思路里面,还是传统的所谓“体”、“用”关系起作用。然而,19世纪中后叶一系列的失败,加以90年代末进化论观念的输入,使得中西之间的冲突高度尖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世纪中国思想在中西关系问题上的主流,是面对西方的进入而积极容受,用以实现传统的变革。一般的情况下,这一流脉的观念,往往从时间的维度上理解中西之异,以为两者之间具有历史阶段的先后之不同。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当然应该算是一个坚决认同西方历史、文化趋向的人。除了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原因,在思想资源上,陈独秀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自从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天演论》(1898年)之后,社会进化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自然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形成此地位的原因、乃至未来前途的焦虑相关:社会进化论成为他们强调中国的危机地位、呼吁全面变革以求保国存种的利器。陈独秀就曾表达过面对中国在西方神速进化的对比下大大落后的悲观意识:“欧美文明之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注:陈独秀《通信》,《新青年》1916年第11期。)以此为背景,观照中西文化之异时,陈独秀倾向将两者作历时性的定位,认为东西之异正是古今之别。他的《法兰西与近世文明》(1915年)分别了“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他概括两者的特征说:“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东方的中国与印度一样,两者“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而“近代文明”是西方“欧罗巴”所“独有”的:“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即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摩亚细亚者,皆此物也。”以“进化论”的眼光来看,西方“欧罗巴”文明之优越中国文明是毋庸言宣的。自然,需要做的就是抛弃属于过去的既有的旧文化,而投向新的西方文明:“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寖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而已耳。”(注: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如此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屡屡可见。即使不是陈独秀那样富有情感、议论风发的文字,而作较为客观平实比较中西文化的讨论,其论断也大抵如是。常燕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1920年)是当时在方法和观点上都很有典型意义的一篇文章。他举列了许多中西对比的特征后提出,东西文化的这种种特征之不同,“关系是前后的,不是对峙的”,也就是说它们呈现的不是一个历史时段之中的差别性,而是不同的历时层面之间的差别性,“我们现在所勉强可以叫做东方文明的一点东西,仍然就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那点东西,所以古代文明所有的特质现在仍然保存”,人们不过“误以古代文明的特质当作东方文明的特点”。
稍晚些,瞿秋白在表述上更为清晰,1923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东方文明和世界革命》,开篇就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以“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来诠说这种差异。在他看来,东西社会和文化之所以呈现不同面貌,是“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规律,“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为各有各的发展动力”,它们之间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具体来说,“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这种看法,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元模式为基本背景,指出差异是发展迟速的问题;显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时中西文化之别究竟在于类型还是时代的争执的明确回应,而他以经济社会形态分别中西之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冯友兰中西形态之别论的先驱。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领袖之一,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象征性人物。他在追求未来中国的具体的社会形态的目标上,与陈独秀、瞿秋白渐行渐远,为了替中国“再造文明”,(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4,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他始终以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度、文化移人中国为基本途径;但在以西方为先进、以西方式的现代建构为中国未来之前景这一方面,胡适的立场与陈、瞿并无二致。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胡适曾指出东西文化走的道路是一样的,都是“生活本来的路”:“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也就是说,无论东西,其历史、文化的差别,并非根本性质上异型。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何以能成立呢?胡适的回答是:“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在这样的视野里,文化的差异“都不过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而“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所以,自然的结论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用别人指责他的话说是“全盘西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分世界化”。(注: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后来,胡适更明白说过:“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机械和电气了”,“他们原来不过是进步之程度不同,后来时日久远,就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了。”(注: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人类的前程》,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这里,胡适再清楚不过地点出,所谓东西之别原来就是文化进步程度的差别而已。
冯友兰与胡适一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完成自己最初的研究;但他的思想与胡适显然有不小的差别,晚近甚至被作为现代中国新儒家的一位代表性人物。然而,与新文化主流意识保持契合,冯友兰基本是在主流的思想脉络中逐渐发展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念的。1982年9月,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仪式上的答词中,曾回顾自己的思想经历,对以往半个多世纪中的中西文化观作了一个简明的说明:“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个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个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1章《明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他的第一阶段,所谓“地理区域”并非真的只是指文化的不同空间问题,如果是这样,那根本谈不上对文化特征的真正说明。他的真正意思是指“当时一部分人,不承认这是古今、新旧的矛盾,而认为是东西、中外的矛盾。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4章《20年代》,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虽然这是冯友兰晚年的回顾之辞,但可以相信这是他最初想法的真实情形。他20年代初在美国时曾请教泰戈尔:“我近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东西洋文明的差异,是等级的差异(difference of degree),是种类的差异(difference of kind)?”(注:冯友兰:《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新潮》第3卷第1号。)他之提出“等级的差异”,说明其内心其实已经蕴含了发展差异(此自然涉及时间性)的种子。稍迟些,在冯友兰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讨论会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921年)一文中就清楚地写道:“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的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是旧的,而西方各国已经是新的。”这里,冯友兰虽然还是认为中西“不同类”,但“新”与“旧”的差别已经点出;这不妨看作他从东西之不同向古今之不同转折的观念交织的表现。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面归纳的所谓中西的不同在根本思想之别异的观点,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流行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对传统持维护态度者);而冯友兰对此的反对,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
到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冯友兰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超越以文化类型说明中西之异的趋向。他在这部名为《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地指出:“梁(漱溟)先生及现在一般人所说之西方文化,实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若谓希腊、罗马之思想,实与儒家之思想,大有相同之处。”因而,他“特意将所谓东西之界限打破,但将十样理想人生,各以一哲学系统为代表,平等的写出而比较研究之”。后来,他回顾说:“打破所谓东、西的界限,当时我认为,向内和向外两派的对立,并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人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不分东方与西方。”(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1章《明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一不以文化类型而以时代差别来看待中西的观念,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延续下来。比如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学术著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代划分上就只有“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阶段。1933年完成的下卷中,冯友兰说明,中国其实没有“近古哲学”的进展,基本尚停留在“中古哲学”;而这一情状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尚处中古,而西方则已经进展于近代:“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第2篇《经学时代》第1章《泛论经学时代》,中华书局1985年版。)
照冯友兰晚年的回忆,他有关东西之分不过是古今之异的明确表述发生在30年代。“三十年代,我到欧洲休假,看了些欧洲的封建时代的遗迹,大开眼界。我确切认识到,现代的欧洲是封建欧洲的转化和发展,美国是欧洲的延长和发展。欧洲的封建时代,跟过去的中国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或者大同小异。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章《30年代》,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其实,如上面已经引及的文字,可以说,东西之分为古今之异的意识早在20年代中期已经萌生,且有所透露。那么30年代,这一时间性的观察视野有如何实质的演进呢?或许可以说,这同时也就是他晚年所谓“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观念成立的时候。“现在世界是工业化的世界。现世界的文明是工业文明。中国民族欲得自由平等,非工业化不可”,而“中国文明,原来是农业文明”;而“工业革命可说是近代世界所有革命中之最基本者。有了这工业革命,使别的建筑在旧经济基础上的诸制度也都全变了”,“东方没有工业革命,就变成‘乡下人’了。”(注: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这是冯友兰当时接受马克思影响的主要例证。虽然他侧重在社会类型上,但如果认真分析,则这个社会类型的差别,背后依然是时代之别、古今之异,即中国没有经过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因而,社会类型没有进化到近代乃至现代。在这个视野里面,中国的未来前途依然主要是西方式的。30年代后期完成,1940年出版的《新事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见:“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一般人心目中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中间的差别就在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式”代替了“家庭为本位底生产方式”。到这时候为止,冯友兰的思想世界中,文化、历史的发展依然主要是一元性的,中国过去的独特历史和未来不同的发展可能,并没有成为他中西文化观的一个考虑维度。
二
与从一元立场秉持中西之别是时代之异的姿态不同,对于中国固有传统抱有同情、力图维护其生命的论者,则通常会努力论证中西之别乃各异的性质所致,难以作简单的价值高下之论,并且,正是因为中西各有其历史渊源、脉络和合理性,所以进入现代之后,固有传统仍将具有其现代价值。
20世纪初的国粹派,其中西文化的观念的变化,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最初如邓实等人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邓实曾将文明进化划分为“一统”(“群治限于一国”,“无有外境之感触”),“小通”(多国互通)、“大通’(“无此国彼国之界,吸取全球文明之新空气”)三个时代,“宇宙进化循天演之大圈日进而未已”,西方如今已由二期向三期过渡,而中国“方出第一期之一统时代”。(注: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政艺通报》1903年第8-11号。)在这个历史进化的线索中,中西比较的结果,自然是处于弱势的中国位于时间维度的过去,而处于强势的西方位于时间维度的晚近。在这一视野中,邓实对于中国人的评论,实在与后来的一些意见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注: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之《民智》、《民德》、《民力》,《政艺通报》1904年第6、9号。)黄节甚至还明确说过,如果在当下的欧化和保存国粹之间做一不得不有的选择,或许可以暂时牺牲国粹,“国粹稍损尚有恢复之望,国恶日长,将有危亡之虞;得自誉者,不如得一自毁者,其稍有进步之望也。”(注:黄节:《爱国心与常识之关系》,《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5。)然而,1905年之后,国粹派的文化观念经历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转变,他们开始日益关注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不同自然、历史的产物。在他们所考虑的因素之中,主要是地理、人种乃至风俗、宗教等等:“泰西之土地华离,吾国之土地方整;泰西之人种亚利安,吾国之人种巴克,则土地、人种之不同也。泰西之风俗习躁动,吾国之风俗习安静;泰西之政教重民权而一神,吾国之政教重君权而多神,则风俗、政教之不同也。土地、人种不同,故学术亦不同;学术不同,故风俗政教亦不同。”(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政艺通报》1903年第24号。)列举对比,总不能周全完善,重要的是背后所流露出的文化类型的意识。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时代前后的问题,而是不同类型、不同系统的问题。在这个观念中,不同类型文化的接触就存在一个是否相宜、是否相融的问题。章太炎曾指出:“文化犹各因其旧贯,礼俗风纪及语言,互不相入,虽欲大同,无由。”而“盛称远西,以为四海同贯,是徒知栌梨橘柚之同甘,不察其异味,岂不惑哉!”(注:章太炎:《驳皮锡瑞三书》,《国粹学报》1910年第3期。)两种文化之间完全的融纳、接受是不可能的,章太炎有一个比喻:“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注:章太炎:《原学》,《国粹学报》1910年第4期。)他们清楚表述了文化交通的原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知其宜而交通调和之,知其不宜则守其所自有之宜,以求其所未有之宜而保存之。如是,乃可成一特别精神之国家。”(注:黄节:《国粹保存主义》,《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5。)由此而形成的新文化自然不同于既往的旧文化,也不同于所接触的异文化,而是具有“特别精神”的新文化。如果聚焦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则这种将来的中国文化无疑是既具有传统性的,也具有现代性的。
邓实所谓“泰西”“躁动”、“吾国”“安静”的说法,在杜亚泉那里得到回应。杜亚泉在20世纪初积极参与东西文化论战,在当时,他是西化主流的对立面,陈独秀的文章主要就是针对他的意见以及他主持的《东方杂志》所发表的文字的。杜亚泉大抵认为中西文化之别在静动之间,而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它们之间无所谓优劣和时代之前后。这显然是一种类型论的文化观念。杜亚泉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从民族构成、地理环境等因素入手,分析了中西社会之不同的缘由,揭示了两者的差异特征;因社会之差异,而后导致文明之差异,“社会之发生文明,犹土地之发生草木,其草木之种类,常随土地之性质而别。西洋文明与吾国文明之差异,即由于西洋社会与吾国社会之差异。”有关中西文明的对比,杜亚泉的总体比较结论曰:“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注: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杜亚泉文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的不是同一类型在程度上的距离,而是不同类型在性质上的差异,故而才有取长补短的可能。所谓东西之间动静之不同这一意见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比如两年后李大钊发表了《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基本也是从东西文明的静、动之别讨论问题的。不过,李大钊虽然也提及“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向自杀之倾向”,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但他坚持认为它“临于吾侪则实据优越之域’,因而,所谓“调和”主要还是从中国文明自立图存的角度来讲的,所以他终究要说:“惟以彻底的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所以,他的归本还是以西洋文明为的,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努力自我改变以追求之——因而,与邓实、杜亚泉等的意见异趋。
梁漱溟早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的著作。当然,正如批评者指出的,在学理上,如果精细推求,它确有许多不完善、甚至根本矛盾之处。但它的重要性却不在一举解决了对中西文化的种种不同争执,而在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方向;在这个新的解释方向上面,梁漱溟给出了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系统解释,打开了新的思考路向。首先,梁漱溟对于文化的界定,指出它不过是人们生活的样法,而这个生活的样法之形成,其实在于所谓的“意欲”(Will),这是梁漱溟从叔本华那里援用来的。我们大可质疑这个“意欲”的设定,有太过强烈的心理主义倾向,不过,正是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梁漱溟分划了东西文化的不同路向,所谓意欲向前要求(西方)、意欲调和持中(中国)、意欲反身向后以求(印度)的三径。
在这个结构里面来考察中西文化的差异,梁漱溟便得以反对当时不少人的看法,“我记得有一位常乃德先生说西方化东方化不能相提并论,东方化之与西方化是一古一今的,是一前一后的,一是未进的,一是既进的”,“大多数的人就以为中国是单纯的不及西方,西方人进化的快,路走出去的远,而中国人迟钝不进化,比人家少走了一大半。我起初看时也是这样想”;但是在不同文化路向的视野来看,“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态度,与西方人不同的”。
这个诠说的意义在于,在现代中国思想界,梁漱溟再一次、可能也是最为清楚地层示了中西文化是不同性质的类型的观念,因而中国与西方过去走了不同的历史道路,而未来的现代性建构自然也将是不同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曾经直截了当地提出中西之间是无法融合的。这个意见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从他所谓中西异质、异类型的立场而言,这是比较好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将梁漱溟的论说视为多元文化性观念的表达。如他自己一再强调的,他并不是认为中国文化一定优越于西方文化,而是说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意义,具有同等的交互参稽的价值:“欧化即世界化,东方亦不能外;然东方亦有其足为世界化而欧土将弗能外者。”(注:梁漱溟:《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1日。)这也就是说,欧洲有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在,而中国也可以为现代世界贡献自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当然,在随后的论说中,梁漱溟显然抛开了这个文化差异且无法融合的观点,转而将基于不同意欲而开出的不同文化类型,作了历时性的排列。在这个序列中,中国文化从最初在物质、社会、精神三层面都不如西方的处境中超升出来,成为凌驾西方文化之上的未来方向:“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当人类面临的问题转移,“征服自然的路”走过之后,“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大约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大的矛盾之处,一再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或许我们可以从学理上解释这是近代线性进化观念的又一次呈现;但就梁漱溟乃至现代中国卫护固有文化传统的人而言,这个转折满足了他们的内心“意欲”。上文提及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它的最后部分说道:“西方是外向的,东方是内向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无论如何,中国的人生观也许错了,但是中国的经验不会是一种失败。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它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这种将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设置于未来加以确认的策略,在很大的程度上会让人想起梁漱溟——不过,当时远在美国纽约的冯友兰未必能看到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稿,这不过是一种心理攸同的表征。梁漱溟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五四之后最早论理明晰地提出了中西的历史、文化性质不同、路径不同因而未来趋向也自然不同的人,而且在此后的发展中,他直接投入了具体的乡村建设为核心的现代中国建构实践。这不仅与所有主张西方取向的主流中人物不同,而且在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间,也显得特立独行。40年代后期,梁漱溟进而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从社会结构和宗教结构两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化比较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从而指出西方式现代性的许多因素无法在现代中国立足而发展。回顾梁漱溟的道路,他无疑是现代中国坚持中西文化异型,历史路向不同,因而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势必不得与西方从同的重要论说者和实践者。
持中西文化类型不同的论者,往往从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思想路向上对论题加以论证,指出不同文化所应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梁漱溟之区别西洋、中国和印度文化那样。那么如何面对胡适在批评梁漱溟的时候提出的人类本质无异因而文化当无别的论说呢?或许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徐复观的中西文化观可以作为一种回应。他从两个层面来了解文化:“就第一层说,无论文明、文化,都是人造出来的,人在本质上没有分别,故文化在本质上没有分别”,在这一层面,他似乎是同意胡适的;“就第二层说,人的本质没有分别,但人在成长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条件,便出现许多形态不同的人”,因而“文化在发展中所遭遇的条件不同,便会发展成不同形态的文化”,“中西文化虽相同,但是它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重点、表现的方式,都有所不同,故就第二层来说,中西文化有所不同。”(注:《徐复观先生论中国文化》,载《徐复观杂文——记所思》,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徐复观在这里所谓的“不同形态的文化”乃至“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重点”等说法,自然是梁漱溟当年的回声。徐复观对“文化”与“文明”两者,依据英国JohnMacMurray所著The Modern Spirit的意见,作过自己的分别,以为“文明”主要是科学技术一类,而“文化”主要涉及“价值系统”。而科学与价值这两个系统是不同的,前者“只向前看,不回头看”,而“谈到价值问题,我们常常要回顾到历史中间来测定这个价值”,在他看来,“文化的价值方面,不能分古今;价值的基本精神,没有古今的分别。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只是在实践时有轻重缓急之不同及表现形式之各异”。这么说来,主要体现“价值”的文化,没有所谓古今进化的意谓,它相对恒定;而对于不同形态的文化来说,它们之间自然不具有时代上的比较性。早年,徐复观还曾明确批评过否认文化类型差异的观念,他说西方人之所以不承认,是因为“由西方哲学的一元论而形成的一元底历史观,拿一个东西作历史文化唯一底测量尺度,在其唯一底尺度下,世界的文化,都是同质的;只有时间上的前进或落后,而无异质底个性文化之并存。”(注:徐复观:《文化的中与西》,载《民主评论》第3卷第19期(1941年)。)这是很得要点的观察,其实不仅是对西方人,中国现代的不少论者的理路亦是如此。
以上所及的这些论者,他们当然不是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多元问题,他们往往关注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类型的差别,从而反对简单地以线性的历史发展路向来理解中西历史文化的对比,以为世界的现代建构只有一种模式,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只能是世界历史的晚到者,得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反之,他们因为相信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其与西方的传统很不相同的根源、性质和路径,所以在进入现代的历程之中,必然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而这不同,立足于固有的文化传统,必然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也是中国和西方的融会。
三
晚近,多元的观念日益兴盛,成为学术思想界的重要潮流。进一步的关键在于,不仅是承认文化多元性的观念,而且,由此多元文化观,进而明确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超越多元文化、多元传统的单一的现代性。这也就涉及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问题。首先,现代性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所谓现代性是具体文化类型之现代转变的结果。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就依据西方学界逐渐受到重视的多元文化观,对于“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是否是“两个截然不同而且互相对立的实体”,做出了自己的观察:“多元文化观即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尤不能以欧洲文化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另外,从现代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只有个别的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的、抽象的文化”,“普遍性的‘现代生活’和普遍性的‘文化’一样,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现代生活”,“而这些具体的现代生活都是具体的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表现”,在这个视野中,“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注: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次,建立在多元文化传统之上的现代性因而便是复数的形式,具有不同的多样多元的现代性。杜维明20世纪80年代努力论说儒家具有现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理论构架,就是从所谓古代轴心文明时期发展下来的几大精神传统如古希腊、印度以及犹太文明,几乎都有现代转化的命题,从而申明儒家现代转型的课题无疑也是值得探讨的。(注: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1讲第3节《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清楚显示了多元文明的视野,以及从多元文明的视角考虑多元现代性问题的进路。杜维明在最近的论文中指出:“现代化进程本身是由根源于各种特定传统的各类文化形式定型的”,“儒家东亚充分实现了现代化而没有完全西化,这清楚表明现代化可以采用不同的文化形式”,而“作为第一个现代化的非西方地区,儒家东亚兴起的文化意义极其深远”,“东亚现代性意味着多元论,而非另一种一元论。”(注:Tu Wei-ming: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Confucian"East Asia,DAEDALUS,2000年冬季号,第198、207页。)当代东亚和中国的现实,显示所谓多元现代性已不完全是一个理论性的论说,而成为部分的事实,由此,回顾20世纪中国思想界为建构未来中国现代性而展开的种种有关中西文化差别的争论,或许可以愈加把握其中的意义。
标签:现代性论文; 梁漱溟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三松堂自序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胡适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冯友兰论文; 陈独秀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