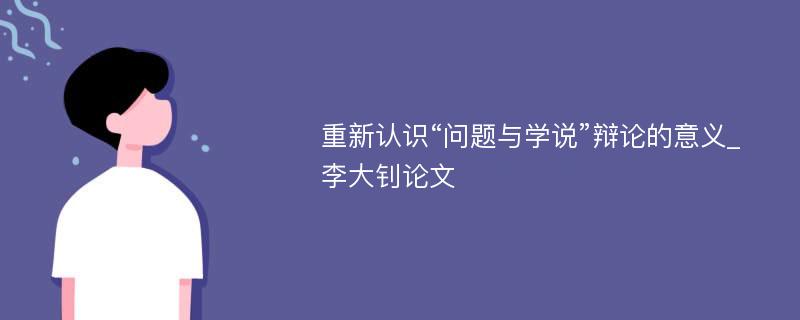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论战论文,意义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辩证的理解。我认为,对这次论战的评价及其意义的认识,既不能偏执于某一侧面,又不能用理想化的尺度去评判,而必须从20世纪20年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大背景和中国社会当时的时空条件出发,从参与论战双方的主观态度和客观效果等方面作出全面的分析与甄别。这样,既可以窥见胡适等实用主义者提出问题的意义及其失足之处,又可以了解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贡献及其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论战在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此是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完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永恒命题。
A
20年代末,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应革命时势的需要而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作为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利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有意识地谈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干将,应邀为之送上了几篇短篇小说之类的译稿。然而,随着《每周评论》谈论现实问题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胡适心里就产生了某种不快。因为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应当暂时撇开现实政治问题,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便为新中国的建设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但是到了1919年6月,在陈独秀被捕, 李大钊外出度假而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时,胡适面对国内政治界和思想界出现的新情况,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留美期间培养的政治兴趣故态复萌了,于是便写了一篇题目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这里,他采用了“谈政治”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这就拉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惟幕。这篇被胡适称之为“我的政论的导言”的文章,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观点:
第一,主义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容易的事,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第三,谈主义与研究问题的关系。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畏难求易”,虽然“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但应当“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第四,关于目前中国社会应“赶紧解决的问题”。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如此等等,都是火紧眉毛的紧急问题。”
此文发表后,首先予以批评的是蓝志先。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胡适“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紧接着李大钊写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意见作了全面的驳斥。其中既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又直言“我们的主义”指“布尔什维克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既要“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要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求得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针对李大钊的意见,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文中有修正,有补充,也有争辩。在“三论”中,胡适首先说明,李大钊拥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轻视”;紧接着则驳斥了李大钊所说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段话,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体现了“目的热”和“方法盲”的大毛病。为此,胡适还提出了打破“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的意见。
B
如果不是局限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就事论事,也不是沉湎于“是与否”的两值思维逻辑来作非此即彼的判断,那么就会看到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势相适应,胡适在这次论战中的思想言行也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状态。即其言行既有错误,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尽管其政治思想中消极的东西逐渐抬头,但毕竟仍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后期新文化运动的盟友。特别是提出了不能空谈主义,而要对主义抱“历史的态度”,实际上已内涵“宣传主义不能脱离实际”的重要思想。
首先,挑起“问题与主义”论争的针对性和出发点上的二重性。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论争的针对性有二:既是针对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又是针对北洋军阀的政客的假冒招牌,侈谈“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怪现象。如在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的后几年,他在回忆这段思想变化时作了如下追述:“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脏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际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想要谈政治。”[1] 又如,他在论及主义的危害时说:“因为‘某某主义’是”一个抽象名词’,它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容易被别人利用,容易假冒牌号。例如,王揖唐是北洋军阀的走狗,安福系的首领,他也高谈社会主义,还自称社会主义家,用社会主义这一抽象名词来骗人害人。”可见,胡适在思想逻辑上的错误,在于不加具体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北洋军阀政客的假冒招牌、侈谈主义混为一谈。
其次,对“问题与主义”相互关系理解上的二重性。如同胡适整个思想体系上的矛盾性一样,胡适对于“问题与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诠释与理解也存在二重性。一方面,他强调“问题”的意义而贬低“主义”的价值,进而否定宣扬“主义”的必要性,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指导实际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胡适的意见客观上体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强调了一种求实的精神和态度。如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谈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而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又进一步提出,对于一切学理和主义。应用“历史的态度”去研究他们,“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它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形的孤立的东西”,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这实际上已经主张宣传主义不能脱离实际,也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偏差的批评。这样的意见在当时是有某些合理成分的。应当看到,由于时间仓促和经验的不足,当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学说时,只强调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情况的共同性方面,忽视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他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2],希望不经过民主革命,立即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仅忽视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而且也否认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也有人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乃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地域的民族的色彩。”[3] 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些偏向和问题,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正视,李大钊当时就说过:“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4]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若干批评上的天真性。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若干批评,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知,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的针砭。例如他既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这一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性’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仇视心”,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表示赞赏,认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5]这表明,胡适当时“忍不住”要谈政治, 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不完全是从“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反对、压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政治立场”出发的,而是带着几分天真来搞“百家争鸣”的。因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确有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如当时由于客观时空条件的限制,加上当时所能读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毕竟是不多的。无疑在客观上影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的提高。因此,在他们的一些文章中,不但概念上常出现不准确的提法,而且内容上有时也“走形”了。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时,他们常常是复述马克思主义的几条基本原理,很少有理论上的深刻分析和创造性的见解。
C
面对胡适的驳难与挑战,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并在回击中匡正得失,按照他们所能达到的水平论证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以及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与改造的必要性;还首次提出并初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一事关我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
第一,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真理。针对胡适关于“谈主义危险”的论点,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宣布自己忠实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6] 李大钊针对胡适通过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的观点,明确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7] 在官僚强盗横行的中国,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资”[8]。
针对“假冒牌号的危险”,李大钊指出,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这“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9]。正是“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 我们愈发应该……宣传我们的主义”[10]。
第二,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及其对革命党人的迫切要求。针对胡适把研究问题与宣传主义截然分割开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论证了“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不能分割的相依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主义对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虽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11]在此基础上,他还特别突出论证了主义对解决具体问题的统摄作用。他指出,有了共同趋向的主义,才能掀起“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12]。如果按照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的主张去做,“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的多数人,却一点不发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没有解决的希望。 ”[13]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论证二者关系,已经看到并要求革命党人在运用“主义”解决具体问题时,尤其要研究具体问题的特殊性、差异性,努力搞好二者的结合。他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是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的。
李大钊、陈独秀等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新观点观察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工人阶级学习,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论证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针对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李大钊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决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4]而“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15]“在根本解决以前”,还必须进行经常的阶级斗争,为根本解决作“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16]。
综上所述,在“五四”前后,特别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胡适在中国竭力传播实用主义,虽然是借以反对和抵制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歪打正着,实际上却也向当时的中国输入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从反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胡适的论战中按照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具体问题。李大钊说过:“某些意见与胡适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17]这次论争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恰恰就在于提出问题本身及其所提问题的时代感。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把选择富强之路、救亡图存置于重要地位,意味着胡适与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由同盟者之间的一些具体分歧,而深入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根本分歧。它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了先河。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问题与主义”论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更加广泛,进而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带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历史性的课题,上下求索,潜心总结,不断作出新的答卷。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结合过程中,使党的队伍日益发展壮大,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释:
[1]胡适:《我的歧路》。
[2]《新青年》第8卷1号,1920年7月23日。
[3]《蔡和森文集》第78—79页。
[4][6][7][8][9][10][11][12][13][14][15][16]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5]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
[17]《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卷。
标签:李大钊论文; 胡适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每周评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