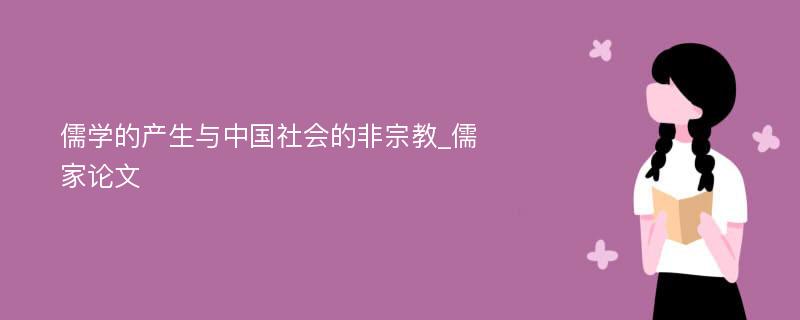
儒家的发生与中国社会的非宗教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宗教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学派是怎样产生的?傅斯年1927年在中山大学的讲义《战国子家叙论》中说道:
鲁是西周初年周在东方文明故城中开辟的一个殖民地。西周之故城既亡于戎,南国又亡于楚,而“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揖让之礼甚讲究,而行事甚乖戾(太史公语),于是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注:傅斯年:《战国子家叙伦》,载《民族与古代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傅斯年认为儒学的发生与鲁国的礼治传统有关。郭沫若写于1942年的《论儒家的发生》一文认为儒学发生于鲁国,是因为在列国中鲁国的文化发展程度最高:
儒在当时为什么不发生于其他的国家,而独发生于邹、鲁,这是值得考虑的。这有它的道理,因为邹、鲁在列国中文化最高。(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7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论者大都认同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儒学是鲁国礼治传统的产物(注:李启谦:《结合鲁国社会的特点了解孔子的思想》,载中国孔子基金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39-562页;郭克煜等:《鲁文化史》第13章《鲁国的礼乐传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德增:《礼与中国文化的再探讨》,《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笔者认为,儒家的发生是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经历了从巫文化到礼治文化的升华,其发生在鲁国则是基于鲁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
一、巫文化的盛行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巫术遗迹,是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的地下室发现的,那里是“山顶洞人”的一处墓地,埋有一男三女,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在尸骨的下面铺撒了很多赤铁矿粉末。考虑到世界上若干原始部族都有用红色矿土涂画身体和装饰尸体以象征灌注生命和力量的风俗,有人认为那些赤铁矿粉末象征血液。我们认为,也可能象征火焰,目的在于保护尸身不受侵犯。究竟用意何在,众说尚难统一。从此以后,考古发现的巫术遗存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在先民民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巫术的强烈影响。
仰韶文化广泛地分布于关中与中原地区,在当时的各种文化类型中,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最多,分布区域最广。仰韶文化中的巫觋可谓当时诸文化中巫觋的一个典型。
从“山顶洞人”到仰韶文化,时间跨度约12000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不断发展,巫术也越来越发达,在先民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历史时段,就是楚国人观射父所说的“家为巫史”的时代:
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注:《国语·楚语下》。)
观射父,楚国大夫。楚俗尚巫鬼,观射夫可能是楚人中精于巫术的一位,故楚昭王多次向他请教巫鬼及祭祀之事。在这个时期,人、神不分,纠缠一起。就像人人都有资格参与氏族的各项活动,都有权使用民族的各种物品一样,人人都可以参与、从事巫术活动,可谓“人人皆巫”。在仰韶文化中,也证明了巫术的普遍性、大众性。不过,到仰韶文化后期,一些特殊的人物开始出现,巫术正在向第二个阶段发展。观射父讲了“家为巫史”那个时期的情况以后,又接着说: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注:《国语·楚语下》。)
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观射夫认为在“家为巫史”阶段以前,本是“民神不杂”(注:《国语·楚语下》。)的,少皋之衰,九黎乱德,才出现了“家为巫史”的混乱局面,待颛顼继兴,又复旧常。这个发展线索有舛,“家为巫史”乃巫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颛顼起,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绝地天通”。到这第二阶段,从芸芸众生中分化出一批专职的巫师,巫术被他们所垄断。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绝地通天”这个阶段肇始于良渚——龙山文化时代。龙山文化分布地域极广,各地发生、延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时序上看,专职巫师的出现,南方的良渚文化早于北方的龙山文化,且在良渚文化中有最充分表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良渚文化土墩墓的墓主是一批凌驾于众人之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巫师。相比之下,龙山文化迄今尚没发现像良渚文化那样的特征鲜明的巫师。但是,龙山文化若干遗址发现了卜骨,是用猪、羊、鹿和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上面往往有火灼痕。考古学家们认为:“遗址中卜骨的存在,可能表明这时已有在社会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专职巫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了:为什么颛顼任命的专司神事者叫“南正”?据考古发现提供的资料,巫术的影响在各地有强弱之分,大别之,南方强于北方,沿海大于内地。太湖平原一带,即良渚文化分布区,巫术表现得最为强烈。南正主管神事,很可能与南方人精通巫术有关。
巫术不仅仅垄断了通神之事,更重要的是藉此控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巫术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并逐渐形成了一些程序化的范式。《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又云:“豐,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礼的本义就是以器皿盛玉以献祭神灵,王国维《释礼》一文考之甚详。(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诸家释礼往往忽视“履”字,“礼,履也”,何解?《说文解字》:“履,足所依也。”礼就是一种轨迹、规范,人人都得遵循之。礼最初就是把事鬼敬神的巫术活动程式化,不合程式的被否定。这项工作是由巫师完成的。巫术的程式化形成一种统一的规范,制约着民众的思维与行为,那些巫师也就向着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演化,民众与巫师组成的那个社会的一只脚也就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从夏朝起,中国社会正式进入文明时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是,民俗的变化远不如政治那么深刻。关于夏代社会与夏人的特征,孔子有一段经典性的评说: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弊,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注:《礼记·表记》。)
从这段文字来看,夏代社会的巫文化已大为减弱,民风朴实。对此,我们谨作两点辨析。
第一,夏人对巫术的态度与他们的发祥地的民风有一定关系。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人最初的活动区域在晋南一带。在这一地带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位于襄汾东北,俗称“塔儿山”的崇山西麓的陶寺村的陶寺文化,时代为公元前2500至1900年左右。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认为,陶寺文化与夏文化有渊源关系。如前所述,巫术的影响南方强于北方,东方大于西方。陶寺文化表现出浓烈的世俗性,巫术的成分相形见绌。这可能是夏人“事鬼敬神而远之”的根据所在。
第二,巫术在夏代没有被摆在冷板凳上,仍在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人在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借重了巫术。禹就是一个例子。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及遗传至今的扬雄《法言》等书中我们知道,巫师的步伐叫“禹步”;据国光红先生考证,《九辨》、《九歌》即禹所传的巫觋歌舞。(注:国光红:《〈九歌〉杂论》,载《九歌考释》,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3-18页。)禹之子启,在文献中也留下了事鬼敬神的记载,故此张光直先生说:“夏后启无疑为巫。”(注: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载《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2-280页。)国王与巫师一身两任,乃上古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英国人詹姆斯·弗雷泽指出:
在早期社会,国王通常既是祭司又是巫师。确实,他经常被人们想象为精通某种法术,并以此获得权力。(注:[英]詹姆斯·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夏代的国王也不例外,他们也是集政治权力与事神权力于一身。夏朝历史与民俗的具体情况,文献阙如,考古发掘也没提供多少资料。商代就不同了,文献记载之外,有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使得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认知商代民俗的特征。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注:《礼记·表记》。)
这是孔子对商人的一个评语。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诸如甲骨文、青铜器、人殉与人祭等等,无不为孔子此语作了最好的注脚。商代是一个鬼神统治下的社会,从甲骨文来看,商人的一切生产与生活活动无不乞求于鬼神,听命于占卜。故此,商代祭祀繁多,人们从甲骨文整理出来的祭祀名目就有一百多种。沟通人与神的巫享有崇高的地位,见诸文献的巫咸、巫贤、巫鼓都是国王身边的重臣。巫不仅仅从事巫术,还涉足政治;官吏也都兼通巫术,巫与官是二而一的。商王则被目为“群巫之长”,商王本人也兼通巫术,往往身体力行之。
二、从事神到治人
这一变革发生在商、周之际。
武王灭商的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把武王灭商的年代定于公元前1046年(注:《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重大》,〈夏商周年代〉正式公布》,《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2日。)。此后的第四年,武王病逝,他的儿子姬诵嗣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摄政。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认为:“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注:《尚书·召诰》。)他们从夏商的兴衰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天命无常,必须注重人的力量,国家大政方针从事神转向治人。孔子在谈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以后,又对周人的统治思想作了如此评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注:《礼记·表记》。)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人的第一次被发现。如何治人?周公等人提出了“礼治”的原则。西周以礼治天下,有两个意思,其一,礼是治国理民的原则、纲领;其二,礼涵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礼记·曲礼上》: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因此,宋人欧阳修说: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乎天下……,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乡射、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注:《新唐书·礼志》。)
把夏、商、周三代都划为礼治时代,是一种传统的观念,欧阳修也不例外。实际上欧阳修所说的那些礼仪及其原则是西周时期的。
所谓的“凡民之事,一出于礼”,实际上就是寓政于礼,藉礼行政。在原始社会,一些重大事情都借助传统习俗来办理,在形式上,周礼依然沿用了这种方式,把国家大政方针寓于礼之中,重大事情都借助从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礼来实施。因此,各项礼仪大都具有政治、军事、法令、教育等职能。对此,杨宽先生在《古礼新探》一书中有精深的研究。这种寓政于礼、藉礼行政的模式表明,直到西周,上层建筑还没有脱出原始习俗的窠臼,整个上层建筑还处于一种低级形态。此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不独中土如此,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很普遍。周礼是从原始习俗演变而来,这些原始习俗到西周时在各地仍有大量的遗存,民众安之若素;特别是周礼寓政于礼、藉礼行政的方式,贴近民间传统,易为民众所接受。
那么,周礼与夏礼、商礼相比,有什么不同?《论语·为政》: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这几句话,后人一般理解为三代之礼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本质的变化(注:如陈来先生说:“这说明,孔子明确肯定,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三代之礼虽有损有益,但都不是体系的、结构的变化。”(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7页))。对此,我们不敢苟同。从字面上看,“损益”之意为增减。但是,我们不能把孔子的话理解为三代之礼的演变仅仅是量的增减,还应当包括质的变化。孔子重点强调的是前后的变化都可以推知、预测。关于三代之礼的变化,在《礼记》等文献记载了有虞氏、夏后氏、殷、周四代在服色、乘舆、棺椁等方面的不同。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变化,三代之礼的变革核心在礼的内涵方面。
礼有“本”和“文”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注:《礼记·礼器》。)“本”是礼的内涵,“文”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礼记》所讲的那些礼仪和礼器。不论在何时,礼的内涵都是借助礼仪和礼器来表现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礼仪和礼器也有差别。但是,礼仪和礼器的变化有时并不影响礼的内涵,内涵相同,表现形式可以不同。《礼记》讲的有虞氏、夏后氏与殷人,礼仪和礼器都不相同,但礼的内涵是一以贯之的,都是事奉鬼神。商周之际,礼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内涵的变化。
1917年9月,王国维曾写了一篇关于商周之际变革的文字,起初他将这篇文字命名为《殷周论》,又在旁边写了第二个题目《殷周文化论》,后又拟题为《殷周制度不同论》,最后定名为《殷周制度论》。这几个题目反映了他研究的重点的变化。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尽管这篇文字带有某些政治色彩,但是,他论证的商周之际的变革,已成不易之论。就礼而论,商周之际礼的一个最大的变革是从事奉鬼神的手段转变为强化伦理的工具。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周礼中,伦理成为礼的基石,周礼也具有神秘性,但周礼的神秘性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对伦理性的神秘化。
周礼的伦理性表现在礼仪和礼器上,实际上是一种等级性。对此,《礼记》反复强调,如: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注:《礼记·曲礼上》。)
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注:《礼记·曾子问》。)
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政,礼之大者也。(注:《礼记·文王世子》。)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注:《礼记·乐记》。)
周礼是一套以具有神秘色彩的伦理性为基本内容,以等级性为表现形式的典章制度。
三、鲁国的礼治传统
鲁国的始封之君,文献有不同的记载。《诗·鲁颂·閟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閟宫》系春秋时的作品。诗中提到的“叔父”指成王叔父周公姬旦,“元子”指周公长子伯禽。《左传》定公四年也说周成王封伯禽于少昊之墟。春秋时期的文献大都作如是观。到了汉代,人们一般认为周公为鲁国始封之君。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皆如此记载。从各种文献记载提供的蛛丝马迹来看,周公应为鲁国始封之君,只是周公之鲁不在曲阜,而在河南鲁山。
鲁山,古称“鲁”。鲁的东北,有座鱼齿山,也叫“鱼陵”、“鲁山”。从这座山的三个名称来看,“鲁”与鱼有密切的关系。鲁、鱼齿山一带河道密布,汝水上游还有个鲁公波。远古栖息在这里的部族以捕鱼为生,是个“鱼族”。在甲骨文中,“鲁”字的形状上是一条鱼,下为一个器皿。“鲁”字的造形,是以礼器盛鱼来献祭神灵。鲁山一带为周公之鲁,这里迄今还有关于周公的逸闻、传说。大约在伯禽袭封就国之后不久,不满于周公摄政的管叔、蔡叔和霍叔纠合纣王的儿子武庚等起兵反叛,一些东夷人如奄国(今山东曲阜一带)等也遥相呼应。周公毅然出兵东征,战争一打就是三年,最后终于平定了叛乱。为了震慑东方,便把鲁国改封在今曲阜,命周公之子伯禽就国。周公为鲁国厘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公曰:‘尊尊而亲亲。’”(注:《汉书·地理志》。)伯禽至鲁,秉承父训,变革当地习俗,全力推行周礼: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问:“何近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注:《史记·鲁周公世家》。)
在列国诸侯中,鲁推行周礼最力,成为礼治秩序最好的地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独鲁“不弃周礼”(注:《左传》闵公元年。),坚持礼治,时人叹道:“周礼尽在鲁矣!”(注:《左传》昭公二年。)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鲁地处内陆,没有齐国那样的发展海洋捕捞、煮海水为盐的自然条件。但鲁地土壤较肥沃,洙、泗诸水足资灌溉。自大汶口文化以来,这一地带就得到开发。而重稼穑、尚耕织,是周人的传统。在自然条件与历史传统的双重驱动下,鲁国确立了男耕女织的经济方针。商业活动也是有的,但鲁国开国三四百年间,一直微不足道。自春秋后期以后,行商坐贾才渐渐多了起来。不过,直到社稷倾覆,鲁国的商业也未能在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与齐国相比,更是黯然失色。
礼治与农耕成功地塑造了“道德型”的鲁文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述鲁地风俗云:
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险啬,畏罪远邪。
《史记》对鲁地风俗的表述,基本上可以涵盖先秦鲁地文化的基本特征。
四、礼治传统与孔子思想
鲁国的礼治传统造就了“道德型”的鲁文化,也造就了孔子。
从直接的渊源来说,孔于思想是鲁国礼治传统的产物。《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这么一件事:孔子少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儿时的孔子爱玩“礼”的游戏,决非“天性”使然。儿童的游戏大多是对成人行为的模拟,古时尤其如此。孔子少时爱玩“礼”的游戏,是受鲁国深厚的礼治传统的耳濡目染。传统的伟力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正是鲁国“先辈们的传统”——礼治传统,造就了孔子思想。
在《礼记·哀公问》中,记有孔子这样一段话:
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在孔子看来,礼的用途有三:“节事天地之神”;“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此三者实即周礼的神秘性、伦理性和等级性。可见,孔子的礼观并没有脱出周礼的框架,只是在周礼的框架内略有损益,这就是:打破了周礼中神秘性与伦理性并重的格局,更加注重礼的伦理性。
孔子对天命迷信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当人无能为力时,他就寄情于天命。如: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注:《论语·先进》。)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论语·雍也》。)
然而,当人力尚可为之时,他就寄希望于人力,不谈天命鬼神。故当子贡请教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时,他训斥道:“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注:《说苑·辨物》。)在这种情况下,礼的神秘性被削弱。
孔子着重强调了礼的伦理性。他提出了“仁”的命题。泛泛而论,“仁”就是“爱人”。而人的仁爱是从孝悌这种父子之爱推衍出来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注:《论语·学而》。)孝悌乃仁的源泉。这种以孝悌为本的仁,构成孔子之礼的最基本的内在特质。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注:《论语·八佾》。)钱穆对孔子此语有精辟的诠释:
礼乐必依凭于器与动作,此皆表达在外者。人心之仁,则蕴蓄而在内。若无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去其意义。但无礼乐以为之表达,则吾心之仁亦无落实物送之所。故仁之于礼,一内一外,若相反而相成也。(注: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49页。)
仁是礼的内在特质,失去了仁,礼就不成其为礼;揖让周旋的仪式和各种器物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无此,仁也无以表达之。
孔子也很注重礼的外在表现形式。《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所谓的“告朔之饩羊”,是指行告朔礼用来作牺牲的羊。一向主张节俭的孔子反对去告朔之羊,原因在于这里的羊已不仅仅是一只有血有肉的动物,而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献给神派的牺牲。孔子又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注:《左传》成公二年。)所谓的“器”,是指车马、服饰、器皿等礼物;“名”是体现在这些礼物上的等级名分。“器’与“名”是等级区别的标志,不可假手他人,必须由君主亲自来掌管。在“器’与“名”上,孔子注重的仅是器物上的尊卑贵贱而已。
在礼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关系上,孔子认为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人而不仁,如礼何”一语,即表明礼之所以为礼,是由礼的内在特质仁决定的。又,《论语·学而》云: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有子名若,是孔子弟子。在他看来,守礼还是违礼,决定于孝悌与否。换言之,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等级性是由礼的内在特质决定的。有子此论,无疑是对其师观点的发挥。正是因为把礼的内在特质视为礼的决定因素,孔子才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注:《论语·阳货》。)
对破坏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等级性的行为,孔子深恶痛绝,但是,由于他视礼的内在特质为礼的决定因素,故他评价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是看他是否恪守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等级性,而是根据他的行为是否违背了礼的伦理性。如他说: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仲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仲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注:《论语·八佾》。)
所谓“塞门”,指天子、诸侯于其门外立屏风以别内外;“坫”,以土为之,可放器物,古礼两君相宴,主人醉酒进宾,宾饮毕、置爵于坫上,谓之“反坫”。管仲树塞门,立反坫,是潜礼,故遭到孔子的指斥。但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注:《论语·宪问》。)相比之下,树塞门、立反坫仅是小节,故孔子赞曰:“如其仁,如其仁!”(注:《论语·宪问》。)在他亲口评定的为数不多的仁人君子中,管仲是其中之一。
通过上面的考察不难看出,孔子思想深受周礼的影响,是鲁国礼治传统的产物。鲁国礼治传统造就了孔子,孔子继承了传统的礼治。
小结
儒家发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继承、强化了中国文化以伦理性为根本的世俗精神。如前所述,自西周起,人的作用被发现,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性被削弱,伦理性被强化。但是,这个变革是有限度的。首先,这个变革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南很少波及,那里巫风依旧强烈。其次,在黄河流域,关中、三晋、特别是鲁国,文化的神秘性大大削弱;而齐、宋、陈等地,巫术迷信大量地残存下来。
儒学的发生,进一步巩固了西周以来中国文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儒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进一步世俗化的过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文化世俗化的基础,避免了中国文化的宗教化。
佛祖乔达摩·悉达多年长孔子12岁,他35岁悟道时,孔子还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当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时,中土早已是儒学的天下了。当西方世界步入宗教文化的寺院、教堂,科学沦为教会恭顺的婢女时,中国却在崇尚现实的儒学推动下,持续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地区。中国文化没有像欧洲、阿拉伯国家和印度等地那样走向宗教化,而发展为崇尚现实的世俗文化。尽管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皆曾传入我国,但皆未“感化”国人,引导他们走向“上帝文化”。相反,外来宗教只有中国化才能在茫茫禹迹上找到一席立足之地。当世界文明起源较早的国家和地区走向宗教文化,文化发展受阻时,中国文化在崇实精神推动下持续发展,终于把早年的伙伴(如印度、埃及、巴比伦)甩在身后,走到世界文化的前列。
儒学发生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进一步巩固了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礼是汉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化特征,汉族的另一名称“华夏”即根源于礼,如果说“汉”、“华夏”是族名,“中国”是该族居住的区域,那么,“礼”就是该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化标志。但是,在儒学发生以前,礼的影响仅限于黄河流域;就是在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礼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如齐地。儒学以礼为思想框架,儒学的传播过程也是礼的传播过程,也奠定了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以礼为思想框架的儒学进一步铸造了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远在军事防御性的万里长城出现之前,就构筑了一道“文化长城”。
标签: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礼记论文; 国学论文; 周礼论文; 论语·八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殷周制度论论文; 周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