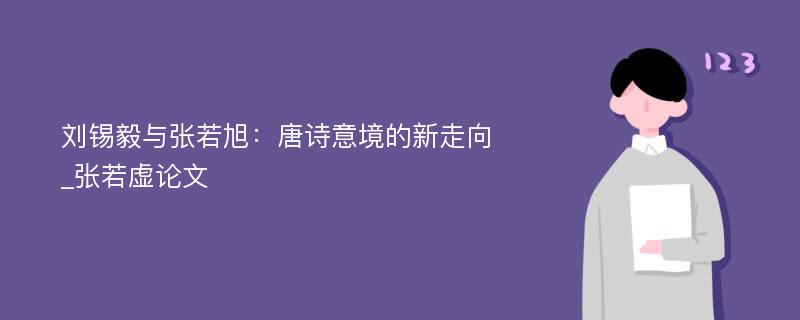
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的新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意境论文,张若虚论文,刘希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集论》中论唐前期诗云“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标明了入唐以来诗歌由沿袭前朝到自立体格再到艺术高峰的演化轨迹与区段,其中“颇能远调”的“景云中”,前承武后时代之末,下启开元盛世之始,显然属于一种过渡性质,所谓“远调”也正是对具有未来指向的弘远诗境的隐约体认。如若将眼光集中于具有模糊界划,过渡性质意义的诗境融造方面,则当以刘希夷、张若虚为主要代表。
从二人活动时间看,刘希夷大体与四杰同时,几乎比张若虚、张说大出一辈,但其诗歌创作风貌却殊异时人,而与活动于景云前后的张若虚诗境创造构成直接的联系,二人在唐诗史上的主要作用固然在于对新的诗境的追求与融造,但其具体的表现特点与方式又各有不同。大体说来,刘希夷主要借助闺阁情思展现纯美流畅之情境,张若虚则在对刘希夷诗境加以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又借助江南风月融造澄澈渺远的意境。
一
刘希夷今存诗作仅三十余篇,从题材上看,主要是从军、闺情之作,从体式上看,则大多为古体歌行,诗风表现或慷慨沉重,或哀怨悲苦。刘希夷在诗歌题材上一定程度地受到宫廷诗风的影响,而在意旨表现上,却显然具有如同四杰那样的对流行于当时的华靡浮艳诗风的改革愿望,甚至一定程度地表现出象陈子昂那样的复古意识。当然,与四杰、陈子昂相比,刘希夷在理论上既缺少明确的主张与强烈的呼喊,在创作上也不似那样意气风发与激烈豪壮,而是主要表现为接续着“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①,纯粹在实践性的艺术探索中以较为平静温和的方式表现出对新的文学理想的追求。从唐诗史嬗递流向的宏观角度看,这种独特的方式也显然表明了向着那一宏大的时代潮流汇融的趋向与特性。而正因其较为温静的表现方式,其真实趋向与内蕴特性往往难以引起人们的注目,因此,从刘希夷现存作品中掘发其时代性意蕴与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刘希夷生平未有从军出塞经历的记载,却多有从军题材之作,如《将军行》写道“将军辟辕门,耿介当风立。诸将欲言事,逡巡不敢入。剑气射云天,鼓声振原隰。黄尘塞路起,走马追兵急。弯弓从此去,飞箭如雨集。截围一百重,斩首五千级”,生动地描画出一位令胡兵丧胆的将军的威武形象;《从军行》写道“秋天风飒飒,群胡马行疾。严城昼不开,伏兵暗相失。天子庙堂拜,将军凶门出。纷纷伊洛道,戎马几万匹。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则又展现出秋风边塞的肃杀氛围与军容战阵的雄阔场景。从表现形式上看,刘希夷的从军题材善用古调,上引两诗就有意识地摆脱骈俪声限,诗意与诗语都显出一种质朴劲拔之感,风调似乎与边塞圣手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作品甚为接近。而其偶用律体,则显出与四杰同类作品的声气相投,如《入塞》:
将军陷虏围,边务息戎机。霜雪交河尽,旌旗入塞飞。晓光随马度,春色伴人归。课绩朝明主,临轩拜武威。如若将这首诗与杨炯的《出塞》、《从军行》以及骆宾王的《从军行》诸篇混同一集,是难以分辨的。
在人生道路上,刘希夷似乎从未得到一官半职,有关他的生平仅有“志行不修”、“落魄不拘常检”、“与时不合”以及进士及第后不数年即“为奸人所杀”②之类简略记载。在这一点上,刘希夷的遭遇比四杰更为不幸,因此其心中深蕴的功业愿望与进取精神的表达,也往往与四杰诗酷似。如《谒汉世祖庙》云“宛城剑鸣匣,昆阳镝应弦。犷兽血涂地,巨人声沸天。长驱过北赵,短兵出南燕。太守迎门外,王郎死道边”,着眼点即主要在于光武帝的中兴功业;又如《蜀城怀古》云“阵图一一在,柏树双双行。鬼神清汉庙,鸟雀参秦仓。叹世已多感,怀心益自伤”,不仅与王勃被逐出沛王府后流离蜀地“慨然思诸葛之功”③神通意合,而且直接剖白了“怀心自伤”的内心隐奥。除了怀古咏史的方式之外,刘希夷的内心世界时或以托物寓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孤松篇》围绕“孤松”孤直的形貌、出众的品格以及委弃的处境几方面进行描写,完全是诗人自身遭遇的喻比与心理感受的寄托。这种以外物托喻内心的方式,一方面承接着卢照邻《行路难》、骆宾王《浮槎》等诗中分别以对“枯木”、“浮槎”的寓言式描写所展露的人生遇合的盛衰感喟与岁月蹉跎的人生意气;另一方面又沟通着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书》中借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称赏而力倡“兴寄”的具有强烈复古意味的文学思想。这种基于时代性人生意义与复古性文学传统的结合的表现方式,恰恰是那一时代最具概括性的文学本质特性。至于在四杰乃至陈子昂诗中最强烈表现出的由人生遇合之理生发出的人世盛衰、历史变迁的具有广远时空涵盖力的哲理思索与历史感悟,在刘希夷其他作品中不难见出。如《览镜》诗云:
青楼挂明镜,临照不胜悲。白发今如此,人生能几时。秋风下山路,明月上春期。叹息君恩尽,容颜不可思。
借“青楼览镜”照出昔日佳人今已“白发如此”,在今昔的回忆与对比中以“不胜悲”的凄凉调联结着“君恩尽”的复杂涵义,从而发出“人生几时”的慨叹,已明显指向了人生意义。其《故园置酒》、《晚憩南阳旅馆》二诗则是以对自身情状的描写而构成情怀的直接抒发了。两诗分别写道“旧里多青草,新知尽白头。风前灯易灭,川上月难留……平生能几日,不及且邀游”“途穷人自哭,春至鸟还歌。行路新知少,荒田古径多……伤心不可去,回首怨如何”,不仅通篇都是今昔事物之对比,而且这种对比被诗人置入“行路”、“遨游”的征途环境与心理氛围,显示出刘希夷对这一时代性人生课题的思考的独特方式。
在刘希夷诗中,对这一感喟人生、叹息时光的时代性主题的最集中表现也即其最优秀的作品,自然还是那些闺情诗。这类作品在刘希夷诗中占有较大比重,如《春女行》、《采桑》、《代闺人春日》、《捣衣篇》、《公子行》、《代悲白头翁》、《代秦女赠行人》、《晚春》以及《江南曲八首》中的一些篇章等,大体都表现出情感真挚、哀婉动人的共同特点。然而细究起来,这一看似简单的表情特点的内蕴却甚为丰厚。首先,从这一题材本身看,刘希夷的闺情诗着重表抒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切感,语言较为朴素。这种重意轻辞的创作方法,与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诗一起,共同构成对梁、陈直至唐初宫廷艳情诗着重砌造华丽美艳的词藻外形、情意表达反而靡弱空虚之弊的改造,如《公子行》中的“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等语,表情刻挚而略无雕饰,与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诗的“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持。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卢照邻《长安古意》诗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几乎难以分辨。同时,在表情的性质方面,梁、陈、唐初宫廷艳情诗无不着重于声色淫乐的情态本身的描写,而刘希夷的闺情诗却无不着重于表现“词旨悲苦”④的情调,如《春女行》写道“春女颜如玉,怨歌阳春曲。巫山春树红,沅湘春草绿。自怜妖艳姿,妆成独见时。悉心伴杨柳,春尽乱如丝。目极千余里,悠悠春江水。频想玉关人,愁卧金闺里。尚言春花落,不知秋风起。娇爱犹未终,悲凉从此始”,《捣衣篇》写道“攒眉缉缕思纷纷,对影穿针魂悄悄。闻道还家未有期,谁怜登陇不胜悲。梦见形容亦旧日,为许裁缝改昔时。缄书远寄交河曲,须及明年春草绿。莫言衣上有斑斑,只为思君泪相续”,对处于分离与独守之中的少妇情思的描写,可谓既细腻入微又淋漓尽致。其次,从比较的角度看,刘希夷的闺情诗总体上的哀婉情调,不仅与其本人的从军题材总体上的雄健沉重情调大不相类,而且与四杰的艳情题材往往表现为慷慨激烈的人生意气明显有别。如《采桑》诗云“杨柳送行人,青青西入秦。谁家采桑女,楼上不胜春。盈盈灞水曲,步步春芳绿。红脸耀明珠,绛唇含白玉。回首渭桥东,遥怜春色同。青丝娇落日,缃绮弄春风。携笼长叹息,逶迤恋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树疑无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江南曲八首》之三云“君为陇西客,妾遇江南春。朝游含灵果,夕采弄风苹。果气时不歇,苹花日自新。以此江南物,持赠陇西人。空盈万里怀,欲赠竟无因”,这些具体的描写,不仅略无浮艳气息与华丽词藻,而且也平息了离怀忧思中的怨愤成份,在一片宁静的环境中完全沉浸于人物的内心世界,由平常的细微的行止之中透现出密腻悠柔的绵长情思。再者,从时代性特征看,刘希夷闺情诗以其完全的哀苦情调以及对昔日红颜的回顾与追想,构成强烈的警省意味,引发深切的人生思考,已显然汇入如四杰诗中反复表现的那种由功名未就、时光流驶的慨叹而引发出对盛衰久暂的人生与历史问题的思索这一时代性主题。如《春女行》中云“忆昔楚王宫,玉楼妆粉红。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容华委西山,光阴不可还。桑林变东海,富贵今何在。寄言桃李容,胡为闺阁重。但看楚王墓,惟有数株松”,《洛川怀古》云“昔时歌舞台,今成狐兔穴。人事互消亡,世路多悲伤”,《公子行》云“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览镜》云“白发今如此,人生能几时”等,无不是由红颜难驻的忧伤联系到人生几何的慨叹再推扩至于贵贱替嬗、桑海变易的整个人世与历史的巨大的时空感悟。然而,刘希夷的闺情诗又不同于四杰诗中将这一主题表现置放于各种复杂的盛衰现象的背景之上,而是完全建基于闺情题材的描写,从而显示出一种独有的纯情的表现方式。
刘希夷的闺情诗应以《代悲白头翁》诗为代表: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日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诗由“洛阳女儿”眼中写出,涵括了桃李盛开与纷飞零落、今年花落与明年花开、松柏摧朽与桑田变海、全盛红颜与半死白头、清歌妙舞与一朝卧病、宛转蛾眉与须臾鹤发等诸多今昔变易、盛衰对比之事物现象,凝聚提升出充满历史时空意识的人生暂促、时不我待的浓重的叹息与深切感悟。在文学的时代风会与艺术的渊源演进的联系与进程中,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不仅明显联结着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以至陈子昂的《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等诗的主题内蕴,而且更直接地成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张说的《邺都引》、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乃至清代《红楼梦》中的《葬花词》等诗的表现范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在显示出与四杰、陈子昂诗的相同的时代性主题的同时,艺术构思与造境又有所不同。四杰表现为在复杂的题材描写中显出风发的意气与昂扬的情调,陈子昂表现为在报国无门的境遇、时不我予的凄惶与宇宙亘古的体认中形成邃密哲思与慷慨悲歌,刘希夷则表现为在纯粹的闺中情思与细腻的心理感受的抒写中展现一片宁静的悠远的心灵的世界。在刘希夷的这一艺术世界中,排尽了具体的事件背景与功利心态,以全部注意力沉浸入具有普遍意义的纯粹的人类原生态情感的波流。这样的情感波流,也就既含具人类共通情感的抽象意味与涵盖力量,又消去一切烦杂与琐屑,呈现出一片晶莹与宁静的审美天地。同时,刘希夷的情感世界不仅立足于悲剧性质与警省意味,而且以全部的篇幅构成对四杰诗中由赋法的移植而造成的于篇末寓含的盛衰主题的推展与扩大,在对美好时光、生命历程的体认中既充满发现的惊喜,又渗透瞬逝的悲哀。在这里,一切具体的事件与思想都集聚到一点即对宇宙永恒、历史真谛的领悟。这样,审美的感受又进而升腾为哲理的思索。随着发轫于情感、净化于审美、升腾于哲思的进程,创作主体也经历着由情人到诗人再到哲人的演化,而这一切又都被纳入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花开花落”这样一种流畅飞动、明丽纯美的景境之中。因此,这一景境的出现,作为诗人复杂的创作构思进程与丰厚的主题思想内蕴的渗融与凝聚,无疑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境,它包容着情感、景象、哲思诸端,显然超越了此前诗人分别对情怀抒发、景物描摹、哲理思索等方面的各有侧重的努力,从而使得刘希夷成为唐诗史上第一个着力于营造诗境的诗人。而从其赖以建基的根源之地看,刘希夷营造的诗境又显然属于纯粹的浓郁的情境类型。
二
张若虚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八世纪初的神龙年间至开元初,比刘希夷几乎晚四十年,其创作活动的后期显然已经跨入了唐诗史的下一个阶段。然而,一方面,张若虚虽然作为吴中四士之一,但毕竟比其他三人创作活动早结束二十余年,贺知章与张旭卒年都迟至天宝年间,包融卒年不可考,但其子包佶生于开元十五年,故其卒年亦不至早于开元末,皆已属地道的唐诗艺术高峰期诗人;另一方面,从张若虚存留作品的主题表现之时代性特征看,也显然与刘希夷、陈子昂以至四杰等人更为接近。
张若虚今存仅两首诗,一首是五言排律《代答闺梦还》:
关塞年华早,楼台别望违。试衫著暖气,开镜觅春晖。燕入窥罗幕,蜂来上画衣。情催桃李艳,心寄管弦飞。妆洗朝相待,风花暝不归。梦魂何处入,寂寂掩重扉。
对于这首闺情题材,今人大多评为平庸之作并皆略而不论。我认为,此诗具体描写固然有堆砌华艳词藻、诗风绮丽靡弱之感,显见宫廷诗风影响,但此诗自有值得注意之处。其一,这是一首纯粹的闺情诗,表现了与“特善闺帷之作”的刘希夷有选材上的一致性;其二,这又是一首声律完全谐合的五言排律⑤,体现了与以沈、宋为标志的近体诗体格精密定型化的时代风会的吻合;其三,这首诗词藻虽华丽,意旨却是怨女旷夫于天涯远别中的哀怨悲苦之情的表达。这就一方面与四杰、刘希夷诗中盛衰主题隐约沟连,另一方面又构成其自身另一首杰出作品《春江花月夜》中思想闪光的朦胧预现。
张若虚仅存的另一首诗就是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春江花月夜》本是乐府旧题,曲调传为陈后主所创,据《旧唐书·音乐志》记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可见,此调创制之初乃是以艳情女色为描写中心的典型的“宫体”诗。然陈后主之作今已不存,现存歌辞被收入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者有五人七篇,在张若虚之前有隋炀帝杨广二首、诸葛颖一首,与张若虚同代稍后有张子容二首。在这些作品中,如杨广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诸葛颖的的“花帆度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拂船楼”、张子容的“林花发岸红,气色动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宜照浣纱人”等,显然已褪去了“思极闺闱之内”的“宫体”色调,集中于春江花月夜清丽景象的描写,甚至为张若虚之作提供了最初的设色布景之雏型。从诗的形制看,这些作品无不沿用五言短篇,且以大体相类的词语与形貌描画的方式渲染烘托题中之景物、则又显然不出梁、陈迄唐初宫廷写景咏物诗的构思定势与制作惯例。张若虚所作虽然同样采用这一乐府旧题,却在内涵及形制方面都显示出空前的创造性,不仅与梁、陈“宫体”更为彻底地划清界限,而且从宫廷诗程式惯例长期影响下的拘狭形制中超脱出来,首次将这一旧题改造为七言歌行的体式,以长达三十六句的篇幅,构成对自身内在情感与诗的情韵意境的淋漓酣畅的展示。
这种对旧题乐府仿制性的超越,使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体现出纯粹的个人创作的特点,而其对宫廷诗靡弱内质与拘狭形制的改造,则又显然与首先将诗坛中心由宫廷台阁移至江山塞漠的四杰诗风汇流融合起来。仅从诗的体格风调等外在表现方面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四杰诗的共通之处就极为明晰。首先,七言歌行体入唐以来消歇无闻,至四杰首倡其体并形成创作兴盛局面。同时,四杰歌行大多篇制较长,且多借用乐府旧题,如卢照邻《行路难》、王勃《临高台》、骆宾王《帝京篇》等,以此比照,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正完全相同。其次,四杰歌行达到“七言之体,至是大备”的成熟境地,在篇章上形成“平仄互换”、“加以开合”⑥的结构特色是一重要因素,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亦正如此,全篇三十六句,用韵平仄互换,且四句一转,具体地看句势流转,总体上看又规严整饬,这种结构特色显然是沈德潜所总结出的“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⑦的四杰歌行的构篇方法与规则。再者,四杰歌行固有承自诗赋二体互为影响的艺术渊源,并且时见骈赋对偶句式,但是由于分离古近体的自觉意识的形成,四杰歌行已有意识地以散间骈,兼采乐府风调,形成“传以神情,宏以风藻”、“偏工流畅”⑧的艺术特色。在这一方面,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也表现出完全的一致,其在采用骈散间行、以散为主的句式的同时,又“用《西洲》格调”⑨,而由此形成的流畅婉转的风格特征,就被明确判为“犹是王、杨、卢、骆之体”⑩。
然而,我以为,研究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及其与四杰诗的关系,更主要的应当在于透过外在形制,深入剖示其在诗歌内质建构方面的一致性。四杰在诗歌内质建构方面的主要贡献,首先就是对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传统的恢复并使之浓郁化,这不仅表现为近体诗内质的抒情化,而且在古体歌行中形成一扫宫廷诗缺乏真实情感基础的虚浮的程式化外形的充实的情感内涵,尤其在涉及艳情题材的作品中,更体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原生态情爱心理的真切畅达甚至放荡无忌的表达形式。同时,四杰诗中具体的情爱内容,又完全改变了南朝末期至入唐之初艳情题材纯粹局限于华靡淫乐生活情态的描写,而是或由眼前之凄凉冷落忆及昔时之繁华欢乐,或于离别之孤寂境地寄托恋情之至死不渝,在时光流驶、历史变迁与欢愉瞬逝的具有警世意味的心理感受中,发为深沉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与历史真谛的感悟。与此相比,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首先自然是对春江月夜景象的描画,但其情感内涵最集中最明显的体现正是人类情爱之情,而且在具体情感内容的选材上又恰恰是怨女旷夫别离相思哀苦之情,这就使得在其另一首存世之作《代答闺梦还》诗中朦胧透现的主题思想得到明晰的昭揭,显示出与四杰诗汇同合构而成的时代性主题的共同特性。从诗中的具体描写看,全诗显然如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的构思方式,略去一切具体的琐屑的人事背景与功利欲望,立足于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提升出一种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抽象力量,在“叙闺中怅望之情,久客思家之意”的深层,实际上表抒的是诗人因“月之照人,莫辨其始;人有变更,月长皎洁”而“睹孤云之飞而想今夕”,“所见惟江流不返”(11)的时空感悟与人生喟叹,从而在盛衰久暂的对比之中进而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对人世沧桑乃至宇宙奥秘的深邃的哲理思索。这种对人生暂促、世事变迁、宇宙亘古的意识与感喟,也就不仅与四杰诗的主题表现,甚至与陈子昂诗的思想内蕴完全融通起来。当然,这种人生思考与宇宙意识的产生,源于那一特定时代庶族知识分子在功业心理与现实经历的矛盾中滋生的年华瞬逝、时不我予的感伤慨叹,而张若虚虽然生平经历不可详考,但其身为江南寒士,又仅作过兖州兵曹之卑职,因而其思想的深层无疑可以追溯到那一时代士人精神风貌与心理特征的根源之地,只是在表现为艺术作品的形式时各各呈现不同的风貌与类型。
三
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相比照,两诗都是由对岁月流驶、青春难驻的人生慨叹升华到对万物长在、造化不息的哲理体认,又都借助清新明丽的景物环境,表现为一种流畅飞动的风调,营造出一种明丽纯美的诗境。可以说,两诗在构思方式、情感性质特别是在诗境融造方面,恰恰体现出完全的一致。也正因此,这两位实际创作活动相距数十年的诗人,在文学史上形成极其紧密的联系。然而,从具体的诗境特征看,张若虚显然在刘希夷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凝炼,将刘希夷所代表的一种新的艺术追求趋向推致于极境,将刘希夷初创的诗境提高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正是因此,在唐诗学史上,张若虚既被视为刘希夷之一体,其《春江花月夜》又被明确认为“出刘希夷《白头翁》上”(12),并且以其“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实际存在,使得“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13),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诗境范型,而这也就是张若虚诗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在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中,对人生历史真谛的思索感悟这一时代性主题的表现,固然已经略去了具体的人事背景与激烈的情绪冲突,创造性地营造出一片清新宁静、明丽悠远的诗境,然而从其诗境构成看,仅仅凭藉“花开花落”的节候景象的无穷往复以及“宛转蛾眉”、“须臾鹤发”、“清歌妙舞”、“黄昏鸟雀”的具有对比意义的具象联系,且杂有大量的对岁月流驶、青春难驻的直接感伤与叹喟,无疑使得诗境的涵溶力相对贫弱、空间感相对狭小。与此相比,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诗境构成显然有所不同,其独具的特征与价值也正是在对前者的改造、推扩与熔炼之中体现出来。首先是观察角度的转换,在张若虚诗中,诗境构成的景象因素已由刘希夷的“人”、“花”联系改变为“江”、“月”映照,诗人立足的着重点亦显然由情转移到境,从而促使明丽流婉之境得以进一步提炼升华而形成更为晶莹澄澈之境,这也就是闻一多所说的“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14)。其次是诗境容量的拓展,在张若虚诗中,由“江”、“月”映照本身的巨大张力,已经拓开无限广阔的空间距离与时间范围,而由诗人意旨与自然境象的环转相生,则又明显改变了刘希夷诗中尚较单调的物象成分,形成诗境容量的丰富感与充实感。正如清人王尧衢所云“于江则用海、潮、波、流、汀、沙、浦、潭、潇湘、碣石等以为陪,于月则用天、空、霰、霜、云、楼、妆台、帘、砧、鱼、雁、海雾等以为映”,“情文相生,各各呈艳,光怪陆离,不可端倪”(15)。更重要的是境象的融织,在张若虚诗中,固然围绕“春江花月夜”五字囊括了丰富的意象,但其成功之处恰恰在于舍去具象的描摹与刻划,着力于“五色分光,合成一片奇锦”(16)的诗境整体合成,诗中表现的对生命美好的感受体认,对月圆人寿的强烈向往,对人生暂促的惆怅伤感,对宇宙亘古的哲理思索,全都溶浸于既透明纯净又似有似无的春江月色之中,形成一种既明丽又静谧的梦幻般的美的情调与境界的融造。李泽厚认为,“永恒的江山,无限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的,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悲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闻一多形容为‘神秘’、‘迷惘’、‘宇宙意识’等等,其实就是这种审美心理和艺术意境”(17),这就一方面从哲学与美学的角度阐释诗境,另一方面又将这种诗境出现的根源,推溯到那一特定时代的士人精神风貌、审美心理及时代性文学主题的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上。
①(14)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
②有关刘希夷生平记载,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乔知之传》、《大唐新语》卷八、《唐诗纪事》卷十三、《唐才子传》卷一。
③《唐诗纪事》卷七。
④刘肃《大唐新语》卷八。
⑤今人大多未辨明此诗体属,甚或有称其为五言古诗者,乃疏于细察而
致误。
⑥⑧(12)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⑦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⑨(13)王闿运《王志》卷二《论唐诗诸家源流》。
⑩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
(11)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一。
(15)王尧福《唐诗合解》卷三。
(16)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引黄家鼎评语。
(17)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七章《盛唐之音》,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标签:张若虚论文; 刘希夷论文; 唐诗论文; 代悲白头翁论文; 诗歌论文; 长安古意论文; 行路难论文; 从军行论文; 唐诗宋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