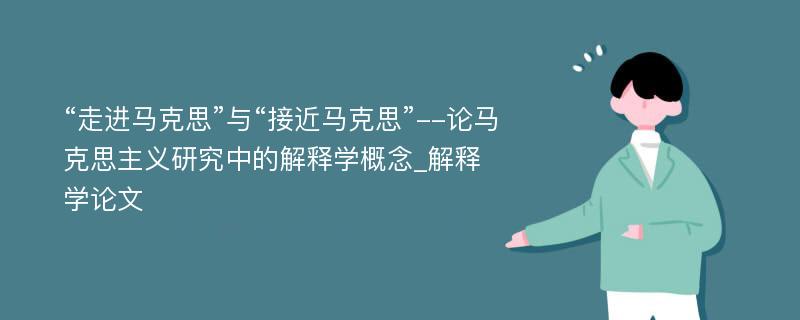
“走进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观念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解释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4)02-0005-05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视野
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极大地影响着现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全世界的人们,不 论对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赞同,都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
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三个不同的视野。一是文本意义(含义)研究,关注马克思的思 想是什么的问题;二是认识论视野的研究,关注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问题;三是价值论 视野的研究,关注马克思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价值意义问题。马克思文本意义的研究是 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研究和价值意义研究的必要的前提,因为不解决马克思的思想是什 么的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问题和价值问题。当然,核心的是价值问 题,人们之所以要解决马克思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和马克思思想是否正确的问题,都是为 了解决马克思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价值意义问题。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第一个视野中,又发生了一个如何看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问题: 在马克思思想的文本研究中,有没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文本对象?马克思文本的意义是马 克思赋予的还是读者赋予的?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目的是什么?马克思文本的意义能够为读 者正确把握吗?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有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把握 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等等。如何看待马克思文本研究(也就是如何看待对马克思思想的 理解),就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解释学是关于理解的学说,是对理解的理解。在解释 学视野中审视马克思思想研究,虽然并不直接解决马克思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却影响着 这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在解决马克思思想是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也必须注意解决马克 思思想研究中的解释学问题。没有清醒而正确的解释学意识,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能有 一个健康的发展。
近些年来,解释学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了重大影响,一些人自觉地在解释学 的视野中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但解释学是一门学科而不是一种统一的观点,在解释学 这门学科中,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学立场、观点,这些不同的解释学立场、观点,在我国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都有所表现。我们注意到当前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两个口 号,一个叫“走进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一个叫“走近马克思”或“接近马克思 ”。这两个口号,虽只一字之差,却代表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学 立场。通过对这两种解释学立场的分析比较,有利于我们确立正确的解释学立场,有利 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走进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客观主义”解释学立场
“回到马克思”的提法,较早见于南斯拉夫“实践派”。在我国,张一兵在20世纪末 正式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他的一本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著作就取名《回到马克思 》。他与孙伯揆先生共同主编的另一本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著作则取名《走进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的提法,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未有人正式提出,这恐怕与哲学史上 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提出过“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的口号有关,这 两个口号一直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为了避嫌,人们不提“回到马克思”。但是 “回到马克思”所体现的“客观主义”的解释学观念,却一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主 导的解释学观念,只是不叫“回到马克思”而叫“尊重原著”、“尊重作者”。我国在 1978年后则有“正本清源”、“重读马克思”、“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等提法 ,这些提法与“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提法,在坚持理解的客观性这一点上 是一致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
任何一个命题,它的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这 些命题也是这样。为了在确定的意义上讨论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本文所说的“回到马克 思”、“走进马克思”命题的意义。
“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一提出,立即就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批评。批评是在两 种不同的视野中提出的。一些人在认识论的视野中批评“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认为“ 回到马克思”有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犯教条主义之嫌,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与 时俱进”。身处21世纪的我们,不应在认识水平上完全回到身处19世纪的马克思,我们 应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这种批评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批评的正当性只有在“ 回到马克思”口号所表达的是一种认识论的意义的前提下才能具有,而张一兵提出的“ 回到马克思”口号的原有意义不是一种认识论的意义而是一种解释学的意义。张一兵所 说的“回到马克思”,是表达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要尊重马克思的原著,正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的实际思想。所以, 对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口号的批评并不是针对这一口号的原有意义的批评,因而是 无效的批评。
对“回到马克思”口号的另一种批评是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我们不 可能“回到马克思”而只能“走近、接近马克思”。这是一种有效的批评,但这种批评 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关于这种相对主义的解释学立场 ,我们到下一部分再给予具体的说明。
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看“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尊重原著”、“尊重作者 ”等口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口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种客观性的立场,即 批评者所说的“客观主义”。这一解释学立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肯定理解对象不依赖理解者而存在,肯定文本对象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肯 定文本意义的固定不变性。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理解。“回到马克思”、“走进马 克思”、“尊重马克思”,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著作,或马克思通过著作表达的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 解者的。文本的本质是文本的意义。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是马克思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 予的。马克思一旦赋予其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固定不变了,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 而变化和随着读者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肯定马克思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我们才能讲“回 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等。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理解。 只有肯定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可以为我们所理解,我们才可能讲“回到马克思”、“走进 马克思”等等,如果虽然肯定文本有原意,但文本的原意不能为读者所理解,就不应该 提出“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口号。
第三,肯定在理解者和文本的关系上,理解的目的是把握文本自身的原意。这是对理 解目的的客观性理解。“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这些口号,充分表达了对理解 目的的客观性理解:我们去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就是为了理解把握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 所表达的思想。
第四,肯定对文本的理解中包含着文本的原意。这是对理解结果的客观性理解。任何 有理解能力并忠实于马克思著作的原意的人,在阅读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时,总会这样那 样地把握到马克思的真实思想,总是这样那样地回到了马克思或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
第五,肯定理解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是有意义的,而衡量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标准在文本自身。这是对理解正确性的标准 的客观性理解。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有正确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理解 者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理解者那里。因此,在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中,争论是不可避 免的,不断地重新理解也是必要的。但是,争论也好,重新理解也好,都是围绕着马克 思著作的原意进行的,马克思著作的原意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理解是否正确的标准 、准绳。
三、“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
与“走进马克思”口号所蕴含的客观性的解释学立场相反,某些人所提出的“走近马 克思”(“接近马克思”)的口号表现着一种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
“走近马克思”或“接近马克思”的提法,仅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并不一定表达一种 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在人们通常的使用中,“走近马克思”、“接近 马克思”是想表达这样的一种观念:某种理解或某种观点这样那样地体现了马克思的思 想。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也就是说,“走进马克思”、“接近马克思”这 些提法,并不必然地表达一种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但是近些年来,有 些人利用“走近”、“接近”这些词的原初意义来表达一种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 释学立场。“走近”、“接近”这些词的原初意义,是指两种东西在空间上靠近而并不 达到,就是说,一物无论它怎样接近、靠近另一物,它永远处在另一物之外,不能达到 另一物。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走近”、“接近”一词,“走近马克思”、“接近马克 思”这些提法,就表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马克思的思想永远只能在理解者的头脑 之外,永远不能进入理解者的头脑,也就是理解者永远不能把握到马克思的思想,“回 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是根本上不可能的。这一解释学立场,就是相对主义的或 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
某些人所说的“走近马克思”、“接近马克思”命题的相对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主要表 现在:
第一,不承认理解对象的客观性,否认文本自身固有的、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俞吾 金认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以一个错误的设定为前提的,即设定了一个纯粹的 、完全不受理解者和理解活动‘污染’,而又能自动地说出自己学说的……马克思。事 实上,这样的……马克思是不存在的,回到(马克思)那里去是完全不可能的。”[1](p. 35)“实际上,我们只能回到我们所理解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去。”[1](p.35) 文本的本质是文本的意义。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没有独立于理解者的文本对象,本质上 是说,文本没有独立于理解者的意义。俞吾金说:“事实上,这种‘纯粹的意义’(即 独立于理解者的意义——引者注)只存在于我们的假定中,因为文本本身永远是沉默的 。”[1](p.35)朱宝信说:“现代解释学的基本观念,就是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 的,它永远处于开放之中;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同时代的不同解释者可以作出不同的解 释,即可以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朱宝信是赞成这种“现代解释学的基本观念的”, 所以他又说:“文本并没有一个原初的封闭的意义整体,它的意义内容是在间距化的作 用下,在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解释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2]
第二,即使文本有自身固有的意义,它也是不可把握的。“走近马克思”观念的提倡 者虽然没有明确地说马克思著作的原意(本真精神)不可理解把握,但是他的文本表达了 这种意义,不管他本人是否自觉意识到。(1)不是把不受“污染”的文本作为理解的对 象而仅把受读者“污染”的文本作为理解的对象,就表达了不受“污染”的“文本本身 的意义”不可理解的意思。(2)俞吾金认为在文本理解中有“把文本本身的意义严密地 遮蔽起来”这样一种“最坏的情形”[1](p.35),在这种“最坏的情形”下,“文本本 身的意义”完全不能被理解。(3)俞吾金明确地说,理解者要“回到他们(康德、黑格尔 、马克思等——引者注)那里去也是完全不可能的”[1](p.34)。他不说完全回到马克思 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回到马克思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恐怕不是一时的笔误。(4)他反对 “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这些口号而有意用“接近马克思”、“趋向马克思” 这些说法,就是为了表达了他对“文本本身的意义”不可理解的意思。无论是我们接近 、趋向马克思,还是马克思走近、趋向我们,都只是“接近”、“走近”、“趋向”而 已,马克思并没有走入我们,我们也没有走进或回到马克思。
第三,理解的目的不是把握文本自身的意义,而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创造文本的意义。 阅读理解马克思的著作,目的是“走近马克思”,目标似乎仍然是马克思。但所要“走 近”的那个马克思,并不是那个不依赖于理解者而写作《共产党宣言》等等的马克思, 而是“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就是我们创造的马克思,不是 那个不依赖于我们的马克思。俞吾金有意不用“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提法而用“重新理 解马克思”的提法,这也表明,在他看来,理解马克思的目的,不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去正确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只是“重新理解”而已。而所谓“重新理解”, 不是说要重新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原本的意义,而是根据我们时代的需要创造文本的意义 ,或叫“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
第四,我们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并不包含有马克思作品的原意,或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我们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至多只是“走近”了马克思,而不能“走入”马克思。我们 的理解不是“回到马克思”,而只是回到了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
第五,理解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争论是不必要的,也找不到评判理解正确与否的客 观标准。既然我们理解的对象并不是“自在的马克思”而是我们创造的马克思,既然马 克思文本的意义不是马克思赋予的而是由我们读者赋予、生成的,既然我们理解的目的 不是把握“自在的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把握自己创造的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必然的逻 辑结论就是,对马克思的理解无所谓谁对谁错,关于马克思思想的争论就是不必要的。 俞吾金认为,谁要用“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什么”这样的表达式,就是一种“朴素的僭 越”[1](p.32)。朱宝信说得更明确,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互相冲突的理 解,“对这些相互冲突的解释学观点,现代解释学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即认为各种 解释都是对文本新意义的挖掘、阐释和生成,它们之间并无优劣之分,每种解释都不拥 有‘解释的优先权’。”[2]
四、“走进马克思”:另一种意义上的“走近马克思”
上面我们考察了当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学立场。我们应当采 取何种解释学立场,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发展呢?我们认为,首先,在上述 两种对立的立场中,我们应当取客观性的解释学立场,反对相对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解 释学立场,另一方面,也应当吸取相对主义解释学中的相对性因素,坚持辩证的客观性 立场,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同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绝对主义 。从辩证的客观性立场来看,走进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是一致的:走进马克思就是走近 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就是走进马克思。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走进马克思”的命题虽然正确地坚持了客观主义的立 场,但这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同时具有一种绝对主义的倾向。必须剔除传统意义上的“走 进马克思”命题所具有的绝对主义意义,辩证地理解“走进马克思”,这样,“走进马 克思”才是一个合理的命题。
传统意义上的“走进马克思”命题中的绝对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理解对象理解上的绝对性。例如:把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或某些权威理论家的 著作看作是绝对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以为走进了教科书也就是走进了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完全和马克思的著作等 同起来,以为走进了斯大林,就是走进了列宁、恩格斯、马克思,走进了列宁,就是走 进了恩格斯、马克思,走进了恩格斯,就是走进了马克思;把马克思所有的著作都看作 是本质上统一的著作,忽视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的质的区别性,以为走进了“青年马克 思”,就是走进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把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原版的马 克思主义著作看作是完全同一的著作,以为读懂了中文版的马恩著作,就完全懂得了马 恩的思想,等等。
第二,对理解目的理解上的绝对性,就是把完全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的现 实目标。实际上,完全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作为指示理解前进的 方向才具有一定的意义,决不能把这一目标理解为可以在某些人或某一时代实现的目标 ,无论何人,无论哪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完全地走进马克思。
第三,对理解结果理解上的绝对性。人们以为(虽然不是以自觉的形式出现),权威的 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或某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 完全正确的理解,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全正确地阐 述了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理解结果理解上的绝对性还表现在,对不同于自己的 理解的理解采取一种排斥态度,例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 为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克服了传统意义上的“走进马克思”命题所具有的绝对主义倾向,有利于我们辩证地 思考“走进马克思”的命题。在辩证的意义上,走进马克思就是走近马克思。
前面我们曾指出,“走近马克思”这一语句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有些人利用“走近 ”一词的原初意义来表达一种相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认为人们只能走近马克思而不能 达到马克思。但是,“走近”、“接近”这些语词,在活的语言中,在话语中,通常表 达这样的意义:达到而不是完全达到,一致而不是完全一致。现在有些人研究马克思思 想的著作,就用“走近马克思”的书名,从这些著作的实际思想来看,讲的是如何更符 合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讲马克思的思想不可把握。平时我们讲,某人思想与某人的思 想接近时,我们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意义:某人的思想与另一人的思想比较一致而不是完 全同一。在辩证的意义上,走近马克思就是走进马克思。
在辩证的意义上,“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表达的主要解释学观念是:
理解有不依赖于理解者的客观对象,承认理解对象有不依赖于理解者的固有意义,文 本的意义是作者赋予的。同时也要看到,被理解者认定的对象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
对文本意义的正确理解是可能的,作者的思想可以为读者所把握。而所谓正确理解, 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理解一个文本的目的,从理解者和文本的关系来说,是正确把握文本自身固有的意义 ,即作者通过文本表达的思想。正确理解文本的意义这个目的,具有相对的意义,即就 现实的具体的目的来说,只能是以相对正确理解为现实目的,不能以绝对正确理解为现 实目的。绝对正确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作为指示理解运动的方向才有一定的意义,不 能作为可以实现的目的。
任何理解都是相对的,而相对之中总是包含着绝对的成分。因此,对文本的意义没有 绝对正确的理解,也没有绝对错误的理解,任何理解都与理解的对象既有一致的地方, 又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理解可以作正确与不正确的评价,评价的尺度在理解对象自身。由于这个尺度是通 过理解把握的,因此实际的评价是相对的,任何人都不拥有绝对的评判权。
关于某一理解是否正确地把握了文本的意义的争论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它通过实现 “视界的融合”而不断推进理解运动。
我们认为,坚持这些解释学观念,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发展。绝对主义的或 相对主义的解释学观念,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是 一个走进或走近马克思的历史运动过程。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活在人们走进或 走近马克思的理解过程之中,通过理解而得到流传,得到发展,也受到批判。
收稿日期:2003-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