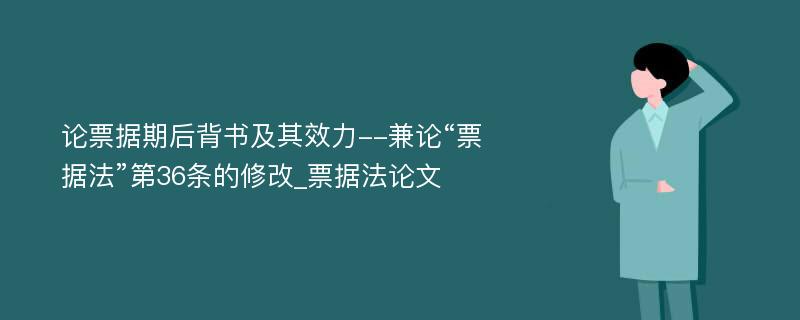
论票据期后背书及其效力——兼论《票据法》第36条之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票据法论文,票据论文,效力论文,期后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4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3)03-0065-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36条规定了期后背书:“汇票被 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 应当承担汇票责任。”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31条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8条作出了相同的规 定。这一规定不同于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及相关国际公约,有其显著的特点。本文试对其 合理性作一粗浅探讨。
一、期后背书内涵之比较分析
票据是一种流通证券,票据转让是实现其流通的方式。票据的转让方式有背书转让与 直接交付转让两种,记名票据须背书转让,无记名票据则可直接交付转让。依据《票据 法》的规定,汇票与本票必须依背书方式转让,因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无记名汇票 与无记名本票,汇票与本票均仅限于记名票据;支票的转让方式则有两种:如果支票上 记载了收款人的名称,则该支票为记名支票,须依背书方式转让之;如果该支票上未记 载收款人的名称,被授权人也没有补充记载的,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可依直接交付 方式予以转让。可见,票据的背书转让是我国票据转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
所谓票据的背书转让,是指票据的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依票据法规定在 票据背面或者票据的粘单上记载相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一种票 据行为。依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的转让背书分为一般转让背书与特殊转让背书。所谓 一般转让背书,是指依票据法规定进行相关记载,既不欠缺也不附加记载任何事项,在 被背书人方面以及背书的时间方面等也不具有特殊情形的背书,这是现实中最常见的转 让背书。所谓特殊转让背书,则是指背书转让时,在权利限制、被背书人或者背书时间 方面存在特殊情形的背书,例如对票据权利进行限制的禁止转让背书,或以票据上原来 的某个债务人作为被背书人的回头背书,以及在背书时间上有特殊情形的期后背书等, 均为特殊转让背书。
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票据立法对于期后背书内涵的界定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两种立法 例。其一,以票据到期日经过为标准。即票据到期日前,无论何时均可为背书转让,一 旦到期日经过再行转让,则为期后背书,也就是说,期后背书是指票据到期日后所为的 背书。例如《英国票据法》第36条第2项,《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304条即作如此规定 。我国《香港票据条例》第36条及台湾地区现行“票据法”第41条均有相同规定。其二 ,以作成拒绝付款证书后或作成拒绝付款证书期限经过后为标准。也就是说,当持票人 提示付款遭到拒绝并依法作成拒绝付款证书后,或虽未作成拒绝证书但法定的作成拒绝 付款证书的期限已经经过,此时所为的背书为期后背书。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 第20条、《德国票据法》第20条、《法国商法典》第123条及《日本票据法》第20条均 作此规定。
无论采取何种立法例的国家,其票据立法均规定,倘若背书未记载日期时,推定为到 期日前背书,以使背书有效。如《英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背书未记明日期的,推定 其作成于到期日前;《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20条第2款也规定:“如无相反证明 ,凡未载明日期的背书,视为在规定作成拒绝证书期限届满前在汇票上所作的背书。” 我国《票据法》第29条第2款规定:“背书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日前背书。 ”这一点与国外票据立法及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一致。
我国《票据法》中规定的期后背书与以上两种立法例均不同。依据我国《票据法》第3 6条的规定,期后背书是指持票人在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 限以后所为的背书。可见我国的期后背书包括三种情形:一为票据被拒绝承兑后所为的 背书;二为票据被拒绝付款后所为的背书;三为票据超过提示付款期限后所为的背书。 这一规定包含了国外上述两种立法例规定的各种情形,且更具合理性。其规定的前两种 情形,即票据被拒绝承兑或付款后所为的背书是期后背书,是因为一旦票据被拒绝承兑 或付款,就意味着付款人到期也不会对票据付款,此时,持票人应当依法进行追索,而 不应将该票据进行转让。若法律许可这种票据继续流通,对受让人并无多少实益,反而 增加了法律事实的复杂性,且极易发生纠纷,故此,法律将此两种情形下的背书规定为 期后背书,以限制该票据的流通性。其规定的第三种情形最为科学,以超过提示付款期 限为确定期前期后的标准,比其他国家规定的到期日标准更合理。因为票据不到期,持 票人不得提示付款,而只能在到期日或其后的法定提示期间内提示付款。持票人在到期 当日提示固然可以,但在法定提示期间内的任何一天提示亦无不可。故此,持票人在到 期日后转让票据,而新的持票人在法定提示期间内仍可随时提示付款,法律自无禁止之 理由。另外,就即期票据而言,出票日后,持票人随时可以请求付款,从理论上讲,出 票日即为到期日,若以到期日作为期后背书的判定标准,必然使即期票据的所有背书均 成为期后背书,实则限制了即期票据的背书转让。由此可见,将“提示付款期间的经过 ”作为期后背书的界定标准的科学合理性。正因为此,我国台湾“票据法”第41条规定 到期日后的背书为期后背书,但有学者认为,对“到期日”不宜做文义解释,而应做论 理解释,以提示期间经过后为准(注:梁宇贤:《票据法新论》,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 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页。)。
综上所述,在我国,期后背书的构成要件有三:其一,时间上的要求,票据已被拒绝 承兑或拒绝付款或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届满;其二,款式上的要求,持票人以背书方法 转让票据权利并记载了背书日期;其三,形式上的要求,持票人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 。具备上述三者,期后背书成立。
二、期后背书效力的立法例考察
尽管各国票据立法对期后背书内涵的界定不同,但对于期后背书的效力的规定却是一 致的,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立法,都规定期后背书不具有票据上的效 力,仅具有通常债权转让的效力,即只具有民法中规定的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这是因 为,票据已经到期,持票人随时可以提示票据请求付款;从理论上讲,持票人不必再转 让票据,而应当直接请求付款,若是持票人不直接请求付款,而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 利,与常情相背;票据已经被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持票人即应依法行使追索权,若是 持票人此时背书转让票据,则有违事理之常。所以,各国各地区之票据立法虽承认期后 背书,但对其效力却不约而同地作出了不同于一般转让背书的特别限制,均规定期后背 书仅有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而不具备票据法上的效力。如《英国票据法》第36条第2 款规定:“过期汇票如流通转让,其流通转让应受到在其到期时该汇票之有瑕疵所有权 之制约,并在此以后,任何人都不能取得或给予较其前手所拥有之更优越之所有权。” 我国《香港票据条例》第36条有相同规定。《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20条第1款规 定:“汇票到期后的背书与到期前的背书有同等效力。但因拒付而作成拒绝证书后,或 规定作成拒绝证书的期限届满后的背书,只具有通常债权转让的效力。”《德国票据法 》第20条、《法国商法典》第123条、《日本票据法》第20条及我国台湾“票据法”第4 1条等均有相同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票据法》对于期后背书的效力做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 区票据立法的规定。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 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中国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58条均作出了相同的规定。这是一条令人费解的规定,仅从字面上看,前半段 否认期后背书的票据上的效力,但后半段却又规定背书转让人承担票据责任,等于承认 期后背书的票据法上的效力,反映了“立法者的矛盾心态”(注:杨忠孝:《票据法论 》,立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这一规定的初衷是要加重期后背书人的责任, 但是,让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并不比其承担民法中的违约责任为重,且在举证责任方面 不利于被背书人。因此,这一规定不仅与国际惯例不符,与票据法理论相悖,而且在实 务上也并不能使被背书人从中获益,但却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混乱。学界对此的理解可 以说五花八门,有学者认为“本条的规定,实际上认可了期后背书的效力,这就是,持 票人对期后背书人有票据权利,而对其他票据债务人无票据权利。”(注:黄赤东、梁 书文主编:《票据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叶 东文主编:《票据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条自相 矛盾的规定(注: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 22页以下;刘心稳:《票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这一规 定“既不符合理论,又无实益,作这样的规定,并无必要。”(注:王小能:《票据法 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更多的学者是对这一规定本身不加评论 ,而径直以国外立法及国际公约中的规定来叙述期后背书的效力(注:参见武靖人主编 :《中国票据法律与实务》,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姜建初、章烈华著:《 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赵新华:《票据法论》,吉林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第36条的规定的确存在逻辑上 的混乱。其第一句话实质上肯定了期后背书具有“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其规定“不 得背书转让”,是对期后背书在票据法上的效力的否定;尽管没有像其他国家票据立法 那样明确规定期后背书只具有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但从理论上分析可知,持票人进行 背书的目的,是为了转让票据权利,由于属于期后背书,不能产生一般背书的票据法上 的效力;但是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的行为,自然会产生民法上的效果,这一效果无疑 就是一般债权转让的效果。但其接下来的第二句话恰恰与此相反,规定期后背书的背书 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显然与前一句话矛盾。既然不能产生票据法的效力,背书人需要 承担的责任当然不属于票据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应当果断摒弃其第 36条自相矛盾的规定,采取与国际接轨的立法规范,明确规定期后背书仅具有一般债权 转让的效力。
三、期后背书“一般债权转让效力”解释
关于期后背书效力的具体含义,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所谓“ 通常债权转让效力”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与票据法中的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有何不同 ;二是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取得的权利性质如何,究系票据权利拟或普通债权;三是除 背书人之外,票据上的其他债务人的责任是否免除。现分而论之。
(一)“通常债权转让效力”的具体含义
所谓通常债权转让的效力,应当是民法中规定的债权转让效力。其与票据法中票据权 利转让效力的根本区别有两点。其一,票据上债务人的抗辩不因期后背书而切断,票据 的债务人对于背书人所能主张的抗辩,无论经过多少次背书,均可以之对抗被背书人。 依据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背书之被背书人,因前手的背书而中断人的抗辩,票据债务 人不得以其与持票人的任何前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 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亦即,权 利的受让人不承受其所有前手在权利上存在的瑕疵。但是,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则因 期后背书仅有通常债权转让效力而不得适用人的抗辩中断理论,所以,票据债务人可以 对抗期后背书人的事由,均可以之对抗被背书人,且不因被背书人的善意而有例外;但 票据债务人与除期后背书之背书人之外的被背书人的其他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则不得 以之对抗被背书人。以例示之,A出票委托甲付款给B,B在到期日前将该汇票转让与C, C在到期日前转让于D。那么,D在主张票据权利时,债务人甲不能以其与出票人A或背书 人B、C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D。但是,如果C是在该汇票提示付款期限届满之后背书转让 与D,则属于期后背书。那么,债务人甲就可以其与期后背书人C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D ,但不得以其与持票人D的非直接前手B或A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D。其二,期后背书的背 书人对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上的担保责任,即其对被背书人不承担担保票据承兑和付款 的责任。依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的背书人对被背书人及其后手,承担担保票据承兑和 担保票据付款的责任,在后手不获承兑或付款时,背书人应当根据其要求偿还一定的金 额。但是,期后背书因只能产生一般债权转让效力,背书人并不像一般转让背书那样对 被背书人及其后手承担担保承兑和付款责任,而只承担民法中一般债权让与人的责任。 如果被背书人不获承兑或付款,其只能依民法的规定向背书人请求承担违约责任或损害 赔偿责任。
(二)被背书人取得的权利的性质
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通过背书所取得的权利,究竟是一种票据权利,拟或是一种普通 债权?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既然期后背书仅产生通常债权转让的效力, 那么,“被背书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只能取得‘通常债权’即‘普通债权’”(注: 刘心稳:《票据法》,第173页;徐学鹿:《票据法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 002年版,第204页。);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期后背书产生的是通常债权转让效力, 但被背书人取得的仍然是票据权利(注:梁宇贤:《票据法新论》,第194页;施文森: 《票据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121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194 页。)。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被背书人取得的权利,乃由背书人享有之票据权利移转 而来,被背书人取得的这一票据权利,并不因系期后背书而变为一般债权,只是这一票 据权利移转时,与民法上依一般方法转让权利具有同一性质,仅产生通常债权转让的效 力,被背书人不得请求背书人偿还票款,或者说,背书人不承担担保责任而已,并不能 说明移转的票据权利的性质因而发生改变。这一权利的移转仍然适用票据法对票据权利 转让的规定,而不适用民法关于民事权利转让的规定,并不需要像移转一般债权那样以 通知债务人为必要,而仅以持票人背书为已足,不过,为了体现法律对这一背书行为并 不提倡的态度,法律对这一背书行为的效力作出了特别规定,否认其具有票据法上的效 力,仅赋予其通常债权转让的效力。背书人通过背书受了让了票据,自然就取得了该票 据上的权利,不必另行举证证明。正如梁宇贤先生所言,“按期后背书之被背书人所取 得之权利,性质上仍属票据上之权利,并不因之而变为一般债权。”(注:梁宇贤:《 票据法新论》,第194页;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 页。)
(三)背书人之外的前手债务人的责任是否免除
期后背书的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背书人的担保责任,已如前述。但是,背书人之外的其 他前手债务人是否承担票据责任,学者见解不一。有学者认为,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只 能向背书人主张权利,而无权对其他债务人为权利主张(注:曾世雄等:《票据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黄赤东、梁书文主编:《票据法及配套规定 新释新解》,第387页;叶东文主编:《票据法》,第112页;刘心稳:《票据法》,第 173页。);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背书人以外之前手债务人的责任并不因期后背 书而免除”(注:梁宇贤:《票据法新论》,第193页。),“被背书人享有对债务人请 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在期后背书之前的背书人仍然要对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负 担保付款和担保承兑的责任”(注: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194页。),期后背书 并不能成为“发票人所得据为免责之依据”(注:施文森:《票据法新论》,第121页。 )。笔者认为,期后背书的背书人之外的其他债务人不能免除票据责任。从票据债务人 角度讲,其进行了一定的票据行为,就意味着应依票据法规定承担票据责任,除非有正 当抗辩事由存在。因此,其他债务人对持票人的担保责任,并不能因期后背书而获免除 ,其仍然要对被背书人负担保付款和担保承兑的责任;当然,他们可以其与期后背书的 背书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被背书人。如果被背书人或背书人在提示付款期限届满后提 示付款,或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被拒绝付款,那么,作为持票人的被背书人就会丧失对 出票人以外的前手债务人的追索权,此乃票据法的规定(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53条。),而非因前手债务人免除担保责任所致。从被背书人角度而言,既然其通 过背书所取得的是票据权利,自然可以依法对票据上的所有债务人行使该票据权利,只 有期后背书的背书人因不承担票据责任而除外。倘若被背书人只能对背书人主张权利, 那么,这一权利即不成其为票据权利。
综上所述,期后背书仅具有通常债权转让的效力;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仅承担民 法上规定的权利让与者的责任;但被背书人通过背书所取得的仍是票据权利;仍可依法 对背书人之外的所有债务人主张该票据权利,当然,票据债务人可以其与背书人之间的 抗辩事由对抗被背书人。
标签:票据法论文; 背书人论文; 汇票到期日论文; 汇票承兑论文; 瑕疵票据论文; 票据权利论文; 票据背书论文; 票据承兑论文; 票据记载事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