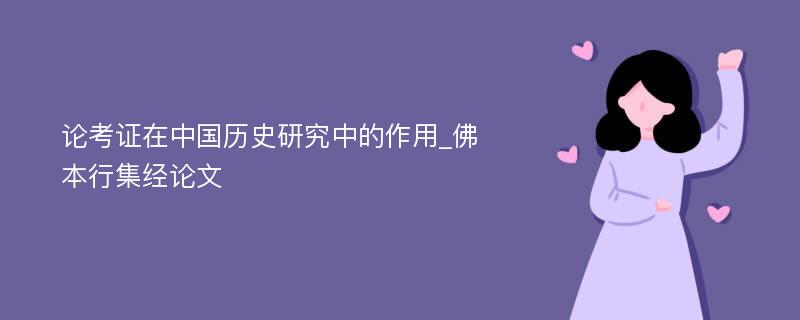
略论文献异文考证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汉语论文,文献论文,史研究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史主要以文献语言为研究对象,而古代文献的异文则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佐证资料。这些异文带着各自时代的印记,蕴含着丰富的汉语史信息。汉语史的研究旨在“弄清汉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了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揭示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1]本文拟就汉语史研究中利用文献异文考证字的始见年代、语音的动态描写、词义的演变线索方面略作论述。
一、字的始见年代
研究汉语史,尤其是考探一个字或词最早产生的年代,同一文献各本异文的鉴别和确定十分重要。日本学者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曾说到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注意避免“时代的错误”,即错误地把后一时期的语言现象当作前一时期的语言现象,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2]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往往是对同一文献不同版本的异文未作考证,没有选择好的版本,而使用了时代较晚的已为后人改动过的本子。
如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标点本《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载显德二年五月甲戌诏曰:“每年造僧账二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攒账,至五月终以前文帐到京。”上引文中既用了“账”字,也用了“帐”字。《辞源》(修订本)[3]2969、《汉语大字典》[4]3645和《汉语大词典扩》[5]222释“账”皆以此为“账”字的最早用例,似乎“账”和“帐”在薛居正编著《旧五代史》的宋代已可并用。考《旧五代史》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本,据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称,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时的辑本,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全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中华本以此为底本,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缮写的武英殿刊本、1925年嘉业堂刊本及其他抄本等参校,还参校了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底样、旧抄本《五代会要》、《永乐大典》残卷等,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然据我们查考《四库全书》所收《旧五代史》,上所引文中皆作“帐”,并未用“账”字。又查考光绪戊子季春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的乾隆四年校刊本、光绪壬辰年武林竹简斋石印本和吴兴刘氏嘉业堂依四明卢抱经楼旧钞本校刊本《旧五代史》皆同。因此,《辞源》、《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所引《旧五代史》盖出自中华本而未就其不同版本的异文加以考证,实际上中华本所用底本中并无“账”字,上引《旧五代史》中的“账”字很可能是后人抄写时的改字。后人抄写时将“帐”改为“账”也见于《旧五代史》的其他版本中,如中华本《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四》:“三司积欠约二百万贯,虚系帐额,请并蠲放。”例中“帐”字,《四库全书》所收《旧五代史》、光绪戊子季春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的乾隆四年校刊本、光绪壬辰年武林竹简斋石印本亦皆作“帐”,而吴兴刘氏嘉业堂依四明卢抱经楼旧钞本校刊的校刊本《旧五代史》中则写作“账”。
《汉语大词典》释“账”所引另一例为冯梦龙《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将昔日岳父所授财产,并历年收积米谷布帛银钱,分毫不敢妄用,一一开载账上。”《醒世恒言》的最早刻本为明叶敬池刊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书前有天启丁卯(1627)陇西可一居士序。台湾世界书局1958年出版了李田意所摄日本内阁文库藏叶敬池原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以影印。考《汉语大词典》所引文中的“账”,叶敬池原本中作“帐”。《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账目”、“账簿”等词中也举有明代《醒世恒言》的用例作为书证。如“账簿”下所引《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为:“房中桌上更无别物,单单一个算盘,几本账簿。”“账目”下所引为“孝基将钥匙开了那只箱儿,箱内取出十来本文簿,递与过迁道:‘请收了这几本账目。’”例中所引“账”字,叶敬池原本中亦皆作“帐”。因此,根据对《旧五代史》和《醒世恒言》各本异文的鉴别,我们可以推断,“账”字出现的最早年代绝不会早于明代。[6]
二、语音的动态描写
同一文献各本异文中的有些异切与语音的演变有关。王士元先生《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一文指出:“音变向来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在有关音变机制研究领域中首先作出解释的是“词汇扩散理论”。这个理论明确提出,音变对于词汇的影响是逐渐的。当一个音变在发生时,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词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地变化的。整个音变是一个在时间上以变化词汇的多寡为标志的一个连续过程。即所有应该变化的词中,有变的,也有未变的。王士元先生认为:“历史材料不过是某一个时间点上的记录。我们难以根据历史材料来重构音变的整个过程,也难以对整个音变的过程作出连续的动态描写。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有了词汇扩散这样一个假设,音变的具体详细的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要对音变的全过程有个连续的观察,我们就不能依靠历史材料。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材料不可能提供时间上的连续性。从另一个方面讲,语言学家也极少有机会对一个音变连续不断地观察上几十年或几百年。因而,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克服这个困难,从而获得连续性的音变的材料。”王士元先生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的时间,不同年龄人的语言状况也就代表了不同时间上的语言状况”,进而对不同年龄人的语言音变状况所反映的词汇扩散过程作了连续的考察。[7]受王士元先生对不同年龄的人的语言音变状况所反映的词汇扩散过程所作考察的启发,我们认为语言是一个代代口耳相传的交际工具,语言的变化是语言传递过程中的误差,而语音不能脱离词汇而存在,因而语音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完成,同一文献不同年代的版本异文反映的词汇变化也就代表了不同时间上的语言状况,并不似王士元先生所说“要对音变的全过程有个连续的观察,我们就不能依靠历史材料。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材料不可能提供时间上的连续性”。如《玄应音义》各本反切的异切就可以说是考察中古语音的可贵材料。由于《玄应音义》各本的时代先后不一样,各个时代的语音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反映语音的实际变化,各本的传抄者可能对原传本的反切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据我们比勘统计,《玄应音义》各本反切的异切共有1180多个,其中有200多个异切不仅是反切用字之异,而且其反切的音韵地位也不同。这些异切与语音的演变有关,根据词汇扩散理论,在音变的过程中,每一个在变化的字都会产生双重读音,已变的和未变的读音。一个音变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发音的传播。这种传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逐步的。《玄应音义》版本的繁杂形成的各本异切可以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前后相近的几个时间点上相同词汇的语音变或未变的现象,有时正好反映了其时词汇扩散过程中未变至已变的动态发展状况,提供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可据以考察音变的连续过程。《玄应音义》各本对同一词所释反切的这些异同对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上古舌头与舌上不分,在《切韵》时代,三等与二等在介音的影响下,舌头音开始分化出舌上音。这种音变当时正在词汇的扩散过程中,有些字还停留在舌头音的阶段,一直到现代,像“地、打”这些字还保留着舌头音不变。下表为《玄应音义》各本有关舌头与舌上声母的异切:(注:据我们比勘研究,《玄应音义》各本异切大致分为丽藏和碛砂藏本两大系,本文表中主要就丽藏、碛砂藏本和慧琳转录的异同进行比较。表中所注声韵据《广韵》,以平声韵赅上、去声韵,a、b、c、d分别表示平、上、去、入。玄应所释佛经名省略书名号,下同。)
表1 舌头与舌上声母的异切
词广韵声韵丽藏碛砂慧琳出处
声韵异同比较
勅历勑历体历 卷十二释杂宝藏经第一卷惕惕 彻锡d;透锡d
惕他历透锡d
勅历勑历汀历 卷十三释佛大僧大经惕惕 彻锡d;透锡d
耻击他击 耻击 卷十二释贤愚经第十一卷灼惕 彻锡d;透锡d
谪陟革知麦d
都革都革陟革 卷十一释增一阿含经第二十二卷谪罚端麦d;知麦d
谪陟革知麦d
都革都革猪革 卷二十五释阿毗逹磨顺正理论第十一卷谪罚 端麦d;知麦d
擢直角澄觉d
徒卓徒卓憧卓 卷三释放光般若经第九卷拔擢 定觉d;澄觉d
月带 竹例知祭c
竹世竹世竹世 卷二释大般涅盘经第九卷?下 知祭c;端泰
咤陟驾知麻竹格丁各丁格 卷二十二释瑜伽师地论第一卷咤迦
知陌d;端铎d
洟他计透齐c
勅计勑计他计 卷十七释阿毗昙毗婆沙论第二十一卷洟唾彻齐c;透齐c
从表中可看到《玄应音义》的反切知组与端组混用,(注:《玄应音义》所载一些字的两读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如卷四释《密迹金刚力士经》第一卷淳湩:“上音纯,下竹用、都洞二反。乳汁曰湩。今江南亦呼乳为湩也。”湩,竹用反,知母东韵;都洞反,端母钟韵。)处在舌上音正从舌头音分化的动态状况,而《慧琳音义》的改切则表明其时知组与端组的区别已由同一音位的变体逐渐演变为两个不同的音位,故慧琳转录时多将其由类隔切改为音和切。
又如清浊声母的异切是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有别而混用的语音现象。唐代浊声母在西北方音中可能已经开始清化,[8]从慧琳转录《玄应音义》的异切中可看到慧琳的改切往往清浊声母混用,反映了慧琳撰音义时浊声母清化的趋势。[9]
三、词义的演变线索
汉语词义演变和词义系统的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词义演变,尤其是常用词词义演变的研究是汉语史研究中一项十分繁重和难度很大的工作。语言中的任何变化都是首先在口语和个人言语活动中发生的,词义也不例外。词义的演变是一种逐渐地变化,往往或多或少会在历代文献,尤其是同一文献的不同文本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考证词义的演变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如明成化本和清康熙刻本《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公孙丑上之上》载:“他心本不曾动,只是忽然吃一跌,气打一暴,则其心志便动了。”例中“气打一暴”,以光绪刻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为“气才一暴”[10]1238。异文“打”与“才”的并存表明“打”在“打一X”的结构中已逐渐失去实义,虚化为介词,与“才”义近。[11]
又如语言中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于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而往往是表达这些事物的语言形式有所不同。据《方言》载:“茫,矜,奄,遽也。吴扬曰茫。”郭璞注:“今北方通然也。”从《方言》郭注可知“茫”的“遽”义本为吴扬方言,后传入北方。又据《玄应音义》卷十五释《五分律》第九卷“狼朚”引《通俗文》曰:“时务曰茫。”可知东汉时“茫”已由吴扬方言成为当时的俗语词,“时务”即“遽”。《说文》:“务,趣也。”段玉裁注:“趣者,疾走也。务者,言其促疾于事也。”又据《玄应音义》卷六释《妙法莲华经》第三卷“不务”之“务”引《广雅》:“务,遽也。”可知“时务曰茫”亦即时务是急遽的事。茫,《说文》未收。《广韵》:“茫,沧茫。”《玉篇》云:“茫,速也。”速亦遽也。据《方言》所载,表“遽”义的“茫”实际上是个记音字,而由有关文献异文的记载可知此义后来为“忙”所取代。
据北宋云门宗禅僧宗演的编刻本《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载:“如庐山和尚,自在真正,顺逆用处,学人不测涯际,悉皆忙然。”又“三法混融,和合一处,辨既不得,唤作忙忙业识众生。”例中“忙”明藏本则皆已改为“茫”。由《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不同文本记载的“忙”和“茫”的异文可知“茫”又可写作“忙”。又据《玄应音义》卷十九释《佛本行集经》第五十八卷“苍茫”之“茫”云:“经文从心作恾,非体也。”据玄应所释,“茫”在唐代所见《佛本行集经》中亦写作“忙”。忙、茫音同,皆为明母唐韵平声,故可相假。
考《玉篇·心部》载:“恾,忧也。忙,同上。”《广韵,唐韵》:“恾,怖也。忙,上同。”由《玉篇》和《广韵》所载可知,“忙”又作“恾”,本义为“忧虑、害怕”。就人的心理活动而言,当人们感到无法应付或无计可施时才会忧虑和害怕,故“忙”可表示一种内心茫然不知所措的慌乱心态。如《敦煌变文集·燕子赋》:“雀儿怕怖,悚惧恐惶;浑家大小,亦总惊忙。”例中“惊忙”一词形容了雀儿一家大小惊惶不知所措的慌乱状貌。又如唐汪遵《采桑妇》:“为报踌躇陌上郎,蚕饥日晚妾心忙。”例中“忙”亦表示内心一种慌乱的心态。
由于人们处于茫然不知所措时难免会手忙脚乱,故“忙”由表示心理上的“茫然不知所措”义引申又有行动上的“慌张、忙乱”义。如隋辍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五十八:“我于尔时,作事苍忙。”例中“苍芒”亦即仓促忙乱。考《集韵·唐韵》云:“忙,心迫也。”盖人们在慌张、忙乱之时往往会感到急迫,故“忙”又引申有“急遽、匆促”义。如东汉王充《论衡》卷二十八《书解篇》:“著作者思虑间也,未必材知出异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或(何)暇著作?”[12]例中“汲汲忙忙”意谓急迫匆促,忙得没有空闲。又如杜牧《郡斋独酌》:“屈指百万世,过如霹雳忙。”例中“忙”亦为“急遽、匆促”义。
由于“忙”、“茫”可音同相假,故“忙”由表示“忧虑、害怕”的本义引申有“急遽、匆促”义后,表“遽”义的记音字“茫”渐为“忙”所取代。考《玄应音义》卷七释《渐备经》第四卷“惶恾”之“恾”云:“莫荒反。茫,遽也。”据玄应所释,表“遽”义的记音字“茫”在佛经中已写作“恾(忙)”。茫、忙二字由相通而分工各司其职。如上文所说玄应指出《佛本行集经》中将“苍茫”的“茫”写作“恾”已为“非体也”。
由“忙”的“急遽、匆促”义进一步引申则有了现在常用的表示“事情多,没有空闲”义。如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祗律》卷十五:“时偷兰难陀比丘尼乞食到其家中庭,见檀越妇洒扫地荡器办诸供具,即问言:‘优婆夷,汝作何等?’时妇人营事忙懅不得应,如是第二第三问不答。”例中“忙懅”谓妇人营事紧迫匆促而无空回答。又如《齐民要术》卷七《笨曲并酒》:“大凡作曲,七月最良,然七月多忙,无暇及此。”例中“忙”与“无暇”对文,“忙”亦即“无暇”。因此由有关文献异文的记载可考知现代汉语中表“急遽,匆促”和“事情多没有空闲”义的常用词最初为西汉时吴扬方言的记音词“茫”,宋以后“忙”原所表“忧虑、害怕”义渐罕用,而成为表“急遽、匆促”和“事情多,没有空闲”义的常用词。
四、余论
上文探讨了同一文献的异文考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作用,从广义上说,不同文献(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或域外的文献)对同一事物或词语的不同记载也可以说是异文,这些记载也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佐证。如笔者在探讨“帐”的词义演变时指出至迟在唐代,今词“帐”代替了古词“计”。至于“帐”何以会有“计”义,清人翟灏在其所撰《通俗编·货财》中说“帷幄曰帐,而计簿亦曰帐者,运筹必在帷幄中也”。此说颇有点想当然,未能揭示出指“帷幄”的“帐”与表示“登记人户、赋税等的记录和记账的书册”的“帐”之间词义上的联系。朱起凤《辞通》卷十六释“治中”云:“官名。犹主簿,州刺史之佐吏也。”认为“中字古读如张。《匡谬正俗》卷七:古艳歌曰‘兰草自生香,生于大道傍。十月钩簾起,并在束薪中。’中,之当反,音张,谓中央也。今山东俗犹有此言。据此是汉魏间读中如张。张、帐古通,计、治同义。后人呼簿书为账,商家因此有计帐名目,而不知实滥觞於治中两字也。”[13]此说因治中犹主簿,而谓计帐滥觞於治中,亦未中肯綮。天锁先生《从“弓”“矢”谈起——关于汉语基本词汇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一文则说“至于‘账’,是由‘帐’来的”。并说“看来最初‘计帐’是一个名词,是掌管民事文案的一个方法,又用来记载居民赋役。至于和帐幕有什么关系,是否是把这些文案等按类挂在帐幕上呢,未有详载。不过,看来当时不是记在一种簿子里的。”[14]天锁先生认为“帐”用来记载“居民赋役”义的产生和官府掌管民事文案采用的记帐方法有关,颇有独到见解,可惜难以证实,亦未能揭示出指“帷幄”的“帐”与表示“居民赋役”的“帐”之间词义上的联系。
笔者认为实际上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射猎,帐篷是这些民族的主要居室,每户住一顶帐篷,帐也就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计算人户的单位。如《后汉书》卷七十八《西域传·车师》:“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后汉书》为南朝宋范晔所撰,例中“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是解释“三百帐”中的“帐”,似为作者自注。盖五胡十六国时的北方政权也要统计其所管辖的帐数来征派赋役,“帐”的词义与中原及南方一带所用的“户”相当。其时“帐”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已由“帐篷”义引申有“户数”义,然而“帐”的“户数”义在中原及南方一带尚很少使用,以至范晔撰写《西域传》说到“帐”的“户数”义时需要加以注释。“帐”的“户数”义在南朝宋以后的文献中亦有用例。如《张义潮变文》:“有背叛回鹘五百余帐,首领翟都督等将回鹘百姓已到伊州侧。”又《新唐书·崔之温传》:“境有浑、斛萨万帐,数扰齐民。”《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臣昨据熟吐浑白承福、赫连功德等领本族三万余帐自应州来奔。”笔者由此推测在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语言记载的史料中也许会有“帐”的“户数”义用例,[15,16]近年来我们又查考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和有关文献的记载,冀就此作进一步的论证,寻检所获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据冯继钦先生等所撰《契丹族文化史》第八章《契丹族的家庭》说,史籍中的“家”、“户”,“还有时而使用的‘帐’,一定意义上都是‘家庭’的同义语。由此可见,最迟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契丹人就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社会活动,并用家庭的数量表示部落大小和人口多少。”[17]562黄时鉴先生在《元代札你别献物考》一文中亦说,“蒙古人普遍使用毡帐。蒙古语原有ger一词,义为‘帐,家’。”[18]1630考《北史》卷九十四《契丹传》载有“其后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契丹》亦载有“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19]3128,[20]1881例中的“家”即上文《后汉书》和《张义潮变文》中说的“帐”这同一词语的不同记载,透露出“帐”的“户数”义来源之端倪,而“帐”的“计簿、记帐”和“计算帐目”等义则由其所表“户数”义引申而来。王艾录等先生《汉语的语词理据》一书论述汉语的理据学特点时曾说到汉语中有少数“双重错误”的现象,“这是指一对通假字换个儿使用,即二字在两个复合词中互为借字。”[21]183-184并以“记帐”和“混账”为例,认为应作“记账”和“混帐”。实际上“记账”写作“记帐”并不误,就其理据而言,“记账”和“混账”原本就写作“记帐”和“混帐”,王艾录等先生因未明“帐”的“记帐”义的理据,反而认为“记账”写作“记帐”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可知文献异文不仅在辨析字词正误、推断古书撰作年代、鉴别版本优劣等古籍整理研究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在考证字的始见年代、语音的动态描写、词义的演变线索等汉语史研究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