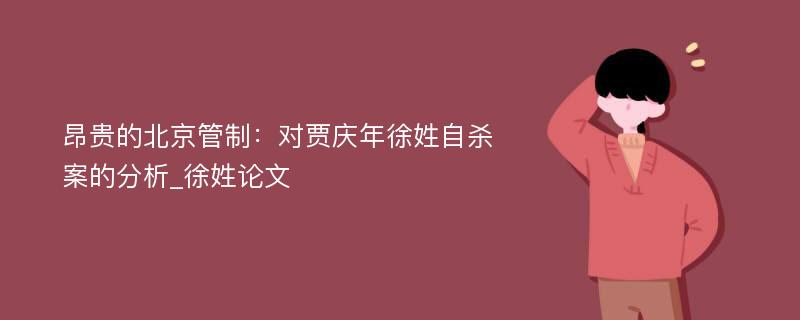
昂贵的京控——嘉庆朝徐姓自戕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庆论文,昂贵论文,朝徐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718/j.cnki.xdsk.2015.04.021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4-0172-09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安徽泾县民人徐玉麟为其兄徐飞陇命案赴京鸣冤,并于刑部门前自戕身死。这一激烈的京控①自杀行为,令道光帝重审该案。经调查,孙玉庭最终认定此案前经安徽省官员审出的徐姓合谋杀害徐飞陇以图赖章姓之案情,及徐玉麟京控所指章姓劫杀徐飞陇之情节,均为大错。命案正凶实为案中紧要人证李象,其先因半夜疑贼而将徐飞陇殴毙,后又畏罪混扳,利用徐章两姓宿怨,混淆视听。同时,孙玉庭还审出泾县差役妄拿教供,及安徽省复审官员刑逼原告妄认等不法情事。该案情节离奇,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中有较详尽记载。②据此剖析该案,可以深化对清代司法审判弊端及京控制度③实际运行效果诸问题的理解,也可以窥见清朝嘉道期间国家与社会互动之一斑。 一、分化与竞讼的地方社会 徐飞陇命案被安徽办成错案,有社会和司法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案发当地社会的利益分化,竞讼的社会风气,紧张的族际关系,边缘化的人群,为该案布下重重迷雾,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当属铸成错案的社会原因。 近年研究成果表明,明清时期人口规模迅速扩张,人均耕地面积下降④,而商贸活动日趋活跃,城市化进程持续发展⑤,尤其是南方一些工商业市镇的繁兴,对乡村城市化的发展起到很大带动作用。⑥此四者相互伴生,使得土地资源愈加稀缺,脱离农业、追逐工商利益的人口增多,而消费习惯则由简朴走向奢靡,人际关系由古淳走向争竞。 泾县位于今安徽省东南部,在清代属宁国府,处于长江南岸平原与皖南山区交界地带,“长山大谷,枕徽襟池”[10]卷1,形胜,p87,自古便是“风物繁华之地、舟车辏集之乡”[11]卷2,风俗,p79,在明清社会变迁大势中,其民风习尚亦随波逐流。诚如嘉靖《泾县志》所载: 明初新离兵革,地广人稀,上田不过亩一金。人尚俭朴,丈夫力耕稼,给徭役,衣不过土布,非达官不用纻丝;女勤纺织蚕桑。居室无大,厅室高广惟式。成化、弘治间,生养日久,轻役省费,民称滋殖,此后渐侈。田或亩十金,民居或僭仿品官第宅。男子衣文绣,女子服五彩、衣珠翠、饰金银、务华靡。……商贾亦远出他境,嫁娶奢靡。[11]卷2,p80 逐利和奢靡的习尚,冲击着旧有尊卑贵贱观念,百姓对官府的陌生与敬畏感逐渐消退。而经济发展与利益多元化使得百姓之间发生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讦讼、健讼成为清代地方官眼中泾县风俗标志性的“弊俗相沿”。嘉庆《宁国府志》引乾隆《泾县志》云: 泾民刚满而竞,往往鹬蚌结于睚眦,听断所及,讼牒麏集,甚至济北之树、汝南之水,累年浃岁,剌剌不休,盖其风使然。大率一人险健,则主文佐斗,实繁有徒。一事愤争,则蔓引株连,纠缠靡已,废时破产,举弗遑恤。[9]卷9,舆地志,风俗,p338 泾县民风好讼,被地方志解释为“山民”的“强劲”所致[9]卷9,舆地志,风俗,p338。“山民”的脚下是稀缺的土地资源。方志称该县地土“十分之中,山居其四,水居其二,平地无几”[11]卷二,舆地纪,水利,p68。确实,因为该县地属山区,土地资源本来稀缺,而便利的水路交通却更增高了其经济价值,再加之风水观念的影响⑦,田土山地之争往往成为当地人聚讼的焦点。与泾县地理相同的邻邑旌德县,有着相似的“健讼”之风,民众“勇于私斗,健于讦讼”。方志作者认为勇斗健讼之风的形成,“盖由地窄人稠,阴阳二基,实所难得,每于造屋、造坟之时,或称税亩未清,或藉界址相连,或假售主分业,种种嫌隙,鼠牙雀角,在所不免”[9]卷9,舆地志,风俗,p341。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本文所介绍京控案的主角,即是居于安徽泾县铜村的徐、章二姓,因连年山场之争结有宿怨。正是这一宿怨在该案中被真凶李象利用,为原告徐姓所执念,从而将控案引向了歧途。 徐、章两姓之嫌怨,最初结于乾隆十年(1745)的山场之争。泾县铜村淡字473号高坪坑起至483号牛背石止,共十一号山场,章徐两姓于其中各有置业。乾隆十年,两姓因争其中滑石坑、牛背石等山场结讼,曾经山邻议息立界。嘉庆十九年泾县荒歉,徐姓族人赴山挖取蕨根时,因伤及树木而被章姓禁阻,两姓互殴,讼端复起,诉至县衙。山场之争,因其牵涉风水和巨大经济利益,往往任意影射、诈伪百出,属于较难断解的土地纠纷。而复杂的买卖关系,为产权判定更增加了一层难度。该处山场,徐章两姓原本于其中各有持业。但时间一久,两姓子侄支派众多,互相间买卖山场频繁,造成彼此之间山场界址模糊,难以条分缕析。因此,时任知县断案时,误判前述十一号山场之中的“剪刀交徐姓未卖之产,作为滑石坑徐姓已卖之业”[5],将两姓相争之地判归章姓所有。对此有欠平允的判决结果,徐姓始终不肯输服,而两姓因山场之争所生嫌怨亦日渐加深,并埋下命案发生后徐姓执认章姓为真凶的伏笔。 二、贫弱的基层司法能力 利益日趋分化、纷争诉于竞讼的社会,对国家司法服务提出了更多更高需求。国家如不能相应地增加基层司法官员数量、提高司法效率,仍以既往有限的司法审判能力应对较以往远为复杂难解的案件,那么错案、冤案出现的几率无疑会随之增加。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泾县知县清宁⑧接到民人徐道生报案,称其父徐飞陇在八门口地方受伤身死,呈请该县勘验。人命重情不能耽延,清宁于初三日抵达,并于当晚提讯人证李象,因其供词不确,拟带县再审。初四日一早查验尸所,因见尸伤均在下部,亲填“受伤追贼,戳落墈下,跌断命门细筋而死”[2]。随后堂审阶段,为求实情,清宁曾刑讯李象,但因其屡次妄供,且查无确据,遂推断徐飞陇之死“或系他处争殴,死后移尸”,将前后见证、嫌犯人等全部释放,详请另缉正凶。[6] 据清代司法制度,若原被两告或其亲属认为州县衙门初审不公或对初审结果存有疑义,可以按照府、道、司、院的层级逐级上控,直至赴京,在都察院或步军统领衙门呈控。徐飞陇命案初审后,其家属对该县审判结果不满,遂逐级上控至京。由其上控呈词及最终复审结果来看,该县在勘验、审讯和详文诸环节都存在疏漏。 其一,在命案至关重要的尸检环节出现遗漏与错检。清宁初审时,督同仵作洪椿相验徐飞陇尸伤共十三处[6],其中左脚踝处有骨损现象,余下伤处均属轻浅;致命伤在腰眼穴处,经检验属石块垫伤,导致徐飞陇命门处筋脉断裂而死亡[1]。但孙玉庭复审时,督同熟谙验伤之宝山县知县周以勋对尸身重新检验后,却发现徐飞陇尸身仅喉骨与脚踝两处有伤,其中咽喉骨呈淡红色,结喉骨呈红紫色,左脚外踝骨呈红色但并未骨损,上述各伤处并不轻浅;因初检时认定致命伤位于腰眼穴处,其尸身尾椎骨倒数第七节处应有伤痕,但复检时却发现不仅该处并无伤痕,原验命门骨受伤之处亦无损伤,仅脊背骨第二、三节呈青色[1]。 经孙玉庭查明,李象因当晚疑贼,在徐飞陇经过时,取钉有铁齿的磨楪向其下身打去,并顺势将其摔倒,使之“扑跌门前沟旁,半著水沟,半在沟旁地上”[1]。随后,李象即脚踏其背脊殴踢。徐飞陇因倒地时面部朝下,且上身跌入水沟内难以应声,以致窒息而亡[1]。根据李象对当晚情形的供述并结合周以勋的尸检结果,复审断定,徐飞陇尸伤多集中于下身且呈不规则分布,是由铁齿磨楪殴打所致;其左脚踝及背脊处瘀伤,为殴踢所致。在徐飞陇停止挣扎后,李象曾抓住其后衣领将之翻转提起,故在咽喉处留有勒痕,并于尸检时验明咽喉骨与结喉骨处均呈红色。 由此可以推知该县初次验尸环节确实存在疏漏,仵作洪椿因未能悉心查验伤处,导致咽喉处关键伤痕被漏检,且多处尸伤检验不准确;而知县清宁也因缺乏相关医学知识而不能纠正仵作错误,只能凭仵作勘验报告推断徐飞陇为“跌断命门细筋”而死,导致人命案件审理中最重要的尸检环节出现错漏。 其二,清宁审案能力不足。徐姓得知徐飞陇死讯之后赶赴现场,发现李象碓房门外及河沟边均有血迹,死者族侄徐长发即将李象看守控制。清宁勘察现场后,亦当将李象作为重大嫌疑对象。而且案件经由县府详办缉凶后,李象又远逃浙江,显有畏罪潜逃之意[1]。但清宁审案中并未彻查这些疑点,而是过于依赖刑讯,致使李象肆意混扳,淆乱了案情。同时,清宁对其所用差役监管不够,使得差役董庆及舒元等因敲诈章姓不遂,而教唆李象之子李笋混供徐飞陇为章姓八人围打身死[1],从而导致本因山场之争结怨的徐章两姓更由这一命案而互相猜疑,讦讼不休。 其三,清宁呈报案情及审讯情况的详文有不当删节。清宁审讯李象时,李象初供章姓与徐姓结讼,章姓有“欲打徐姓之语”。而差役向章姓索贿不遂,教唆李象14岁子李笋于堂审时证供亲眼见到八人围打徐飞陇,其中四人为章姓族人。知县清宁随后提质李象,李象即扶同混供。及加以刑讯,李象挟徐长发看守之嫌,妄供“是晚闻声出看,撞见徐长发嘱其勿管闲事”,将嫌疑对象又引向徐姓。后经对质徐长发及章姓族人,证明李象所供或系仇扳或系无中生有。但撰写详文时,清宁“因图简净,删去李象先供章姓争殴一节,即以李象供扳系先徐后章,叙详通报”,致使死者亲属无法知晓所谓章姓围殴致死乃差役教唆伪供,仍坚信章姓为凶手,不断上控[1]。而徐姓对误认凶手的固执,也招致安徽省复审官员强烈怀疑徐姓有“自行致死人命图赖章姓”的动机。 所谓“万事胚胎皆由州县”[12]772,作为清代司法审判机关的最低层级,州县的地位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案件均需由其初审。从案件初审过程看,清宁本人对该命案并非不重视。清律对印官亲验命案有明确要求:“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亲往相验。”[17]卷851,p1236同时也规定了明确的检验程序:“其果系斗杀、故杀、谋杀等项当检验者”,“务须于未检验之先,即详鞫尸亲、证佐、凶犯人等,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亲诣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定执要害致命去处”,“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17]卷851,p1235清宁对该案的处理,基本遵循着上述律例要求。其于死者家属呈报命案后的第二日当晚即赶到现场,不可谓不速;随后,并无耽延于当晚即提讯人证李象,查问死者家属并了解大致案情,不可谓不勤;再后,于次日一早带同仵作、刑书人等亲临尸所勘验,并有徐飞陇之侄随同相验,不可谓不公开透明;在整个过程中,也不存在受贿及贪赃枉法诸事。由此可见,并非贪渎不法的清宁在初审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重大纰漏,更多应归因于案发当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清宁本人断案能力的局限和专业法律知识的欠缺,尤其是法医检验知识的不足。徐姓居住之铜山村地处偏僻、群山环绕,八门口地方为其出村进城必经之路,距村仅五里之遥,但李象碓房所处八门口地方永寿巷路边,邻近溪河,位置偏僻且并无近邻[7],而当时在场的吕斌系奸对象,受凶手嘱咐隐瞒[1],这样的客观条件造成该命案很难寻求第三方人证,审讯中李象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见风使舵、任意混扳,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同时,也正是由于自身能力局限及缺少相应法医学知识,使得清宁没有怀疑李象混扳的动机可能与作案有关,也未觉察到仵作尸检报告的错漏,进而造成案情推演出现错误,放过了嫌犯。 三、丧失公信力的监司 徐姓族众因以往争山讼嫌,坚信徐飞陇之死系章姓围殴所致,不认同“详请另缉正凶”的初审结果,先后赴臬司、巡抚衙门上控⑨。时任安徽巡抚胡克家在将嫌犯证人等提省审讯时,参审委员凤颖同知陈斌、候补宣城知县聂绍祖、怀宁知县董梁等,发现人证李象得有徐姓所给盘费近百两,遂怀疑徐姓是因之前山场讼争而谋杀徐飞陇以图赖报复章姓,并贿嘱人证李象,从而改变审讯方向,对徐姓原告及族证严加追问,施以刑讯,但终因徐姓坚不承认而未能审明。因见在本省上控翻案无门,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徐飞陇之子徐荣生进京呈控。步军统领衙门接收呈词后,上奏奉旨,交继任安徽巡抚康绍镛审办。 京控案件发回该省督抚审理后,一般先查照刑前事由,分饬藩臬两司行提人证、卷宗到省。随后由两司饬委人员(一般为该省知府、知县或署府、署县等官员)查办审讯,厘清初步案情上报。再由两司督同提审,核对犯证口供及诸证据,并按律拟罪。最后再由藩臬两司招解至督抚衙门,由各该督抚亲提严鞫。由于此时案件已经过多层审理,案情基本清楚,督抚对案件的审理,大多为对案卷与人犯口供的再次提审与查核,在斟酌拟律定罪并无不妥之后,具折奏闻。历尽千辛万苦的京控案件被发回省审,参与承审各官员的态度与办案能力非常重要。若出现偏差,无疑会对京控申雪冤抑的实际效果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导致国家司法权威性与公信力遭受质疑。徐姓京控案的发展,即印证了这一点。 康绍镛于首次提审过后,即饬委臬司,将案件交由安庆知府申瑶、凤颖同知陈斌,督同怀宁知县任寿世、候补宣城知县聂绍祖审办。由于前有徐姓给予李象贿银一层,诸委员等遂坚信徐飞陇致死根由必在徐姓。为得到定案口供,陈、聂两员对徐长发等熬审刑拷五十余日,将其屈打成招,逼其诬认做伤图赖。该委员等将审明情由上报臬司,但臬司提审时,徐姓复翻前供,致使仍未定案。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徐飞陇三子徐芝生再次京控,案件被步军统领衙门仍咨回安徽省审办。因该案已迁延日久,新任巡抚吴邦庆曾督促藩、臬两司,饬委安庆知府申瑶、已委署宁国府印务陈斌、署安庆知府钱兴等赴省会同加紧审办。审办过程中,陈斌再次严加刑审,徐姓涉案人等畏刑妄供,诬服做伤图赖。由于所供致伤之处与原验致命伤痕处所不同,须重新尸检以得确证。但吴邦庆委派官员提取徐飞陇尸棺时,却遭遇徐姓聚众对抗,导致丁役七人受伤,二人被捆,安徽地方当局的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 之所以出现此种局面,与下列因素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第一,安徽省过于重视口供,以致审讯过程中接连发生严重的刑讯逼供。古代刑案审讯极重口供,为获得切实供招,对嫌犯等施以适当刑讯是允许的。清律规定:“强窃盗、人命及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后竟改供者,准夹讯外,其别项小事概不准滥用夹棍”[15]故禁故勘平人第一条律文,p1040。但为防止官员滥刑毙命草率结案,对刑讯程度加以限制,并对违法刑讯的官吏施以惩处。“若将案内不应夹讯之人滥用夹棍,及虽系应夹之人因夹致死并恣意迭夹致死者,将问刑官题参治罪。若有别项情弊,从重论”[15]故禁故勘平人第一条律文,p1040。同时,《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亦有“刑逼妄供枉坐人罪”条,明确规定滥刑官员的处罚:“凡大小衙门问刑官员,于命盗案件不能虚心研鞫,刑逼妄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以致枉作凌迟斩绞者,革职;枉坐发遣军流者,降四级调用;枉坐徒杖笞罪者,降三级调用;俱毋庸查级议抵”[16]卷48,审断下,刑逼妄供枉坐人罪,p1013-1014。 徐姓一案关涉人命重情且疑点颇多,为求嫌犯口供,适当用刑势所必须。但是,陈、聂两员刑讯的酷烈程度显然已超出朝廷法令的规定要求。在徐玉麟身带冤状中,曾称刑讯极为残酷,熬审刑拷长达五十余日,不但将徐飞陇之妻锁押班房,并且对其子侄等施以跪链、上枷、加绷、提耳等刑,致使有人酷刑成废,而徐飞陇之侄徐广也在酷刑之下畏惧乱供。此种呈诉内容虽或有夸大,但孙玉庭后来的复审奏折中建议将陈、聂二员“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是因为他们“于人命重案并不虚衷推鞫,因疑误致先后率意刑求,几成冤狱”[1]。这也说明,陈、聂二员的滥刑逼供,确为事实。 第二,泾县差役舒元教唆徐姓痴呆族人徐兆作伪证,伪造亲见徐姓合谋杀害徐飞陇以图赖章姓情节。舒元之所以教唆徐兆做伪证,是因为拘拿关键证人徐孝芳不到,其家属被收禁[1]。而伪证之所以被采信,则在于问刑官陈、聂二员只希图锻炼成狱,无视了证人的有限行为能力。 第三,在重做尸检、获取关键证据前,由巡抚吴邦庆主持的安徽省第二次复审以揣测替代严格的证据审查,罔顾证据之间的矛盾,妄参原泾县知县清宁。吴邦庆亲审时曾发现陈、聂所报案情有两个重大疑点,一是“据委员等,亦以该县原验尸伤不确,请提尸棺检办”[6]。所谓“原验尸伤不确”,是指原泾县知县清宁提供的验尸报告所描述的伤情与徐长发等人的口供描述不符[1]。二是“供情狡展,忽认忽翻”。虽然存在这两个重大疑点,但吴邦庆未待重新尸检,即断言“其为徐姓自行做伤致死情由,已属显著”。并以未能据李象伪供“是夜曾见徐长发在伊门前站立”究出徐姓自行做伤致死真情,参奏知县清宁“初审草率”、“更恐有故纵情弊”,请将其革职提讯[6]。吴邦庆参奏清宁,无异于宣布该案已有结论,徐姓即是凶手,重做尸检,不论结果如何,不过是走形式,与该案结论无关。 安徽省的刑讯逼供和徐姓有罪推定,让徐姓感到灭顶之冤即将降临,正如徐长发弟徐德荣赴都察院报告所称:“可怜人非铁石,何求不得!若候抚宪奏结,有死无生。”[2]为避免坐以待毙,徐姓一方面派人第三次进京,分赴刑部和都察院控告,另一方面“于各要隘口垒放石块,村内预备器械”,凭险抗拒巡抚吴邦庆饬派前去提取徐飞陇尸棺的官兵[3],以保全证据,可见安徽省院司各衙门在徐姓家族内心已毫无司法公信力可言。 四、成本昂贵的京控昭雪 徐姓第三次京控赴刑部控告者徐玉麟采取了最为激烈的“自戕”方式,震动了朝廷。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晨,刑部门皂发现刎颈自杀的徐玉麟及其随身所带冤状,刑部堂官即据此上奏,请求令安徽巡抚吴邦庆及原审各委员俱照例回避,该案交钦派大臣或两江总督亲提检审。奏折中称:“徐玉麟系已死徐飞陇无服族弟,事非切己,何肯远涉来京控诉,甚至以身相殉,殊非情理!”[8]新继位的道光帝极为重视该案,令两江总督重审[14]卷5,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庚辰,总第33册,p138。此时正值吴邦庆报告徐姓自行做伤致死、参劾清宁之折“甫经入奏”[8]。 徐姓得知案件交由两江总督复审后,采取配合行动,交出了徐飞陇的尸棺。此次检验与复审官员,全由两江总督孙玉庭自江苏省干员中遴选。检验发现尸伤与原检差别甚大,既与徐姓所控情形不符,亦与安徽省所审图赖情节不合。而审讯后发现此案实情与安徽省所讯情节迥异,罪名出入悬殊。徐飞陇实被李象黑夜疑贼殴毙,章徐两姓均非凶手;并究出差役舒元、董庆等先后诱骗李象之子李笋及徐姓族人徐兆到案狡供诸情节,进而发现徐姓坚指章姓劫杀,以及安徽省委员审出徐姓谋命图赖等情,皆为大错。经孙玉庭奏报定案,将李象依斗杀律科断;差役舒元等因教供导致委员误审,照“诬良为盗治罪例”发边远充军,不准援免;该县仵作相验不实,并于原验尸伤任意增减,发往乌鲁木齐,以示惩儆;知县清宁因相验草率,不能审出正凶且任意删节犯供,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安徽省委员凤颖同知陈斌、候补知县聂绍祖于人命重案并不虚衷推鞫,因疑误致先后率意刑求,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余相关审理人员,也因各自审理不力而分别受到革职与降调惩处[14]卷12,道光元年正月戊辰,总第33册,p234-235。孙玉庭因能“审明正凶、据实平反”,加二级[14]卷12,道光元年正月癸酉,总第33册,p239-240。此时已是道光元年正月,该案自案发、初审,期间三历京控,到定案,历时约五年。 开放京控曾被清廷寄予整顿吏治、为民申冤的厚望。嘉庆帝曾指出:“朕勤求治理、明目达聪,令都察院、步军统领等衙门,接到呈词即行奏明申理,以期民隐上通,不使案情稍有屈抑”[13]卷70,嘉庆五年六月乙亥,总第28册,p938。他还曾乐观表示:“百姓果受有司屈抑,何难向督抚衙门呈诉?即或不为审理,亦可赴京控告。方今纲纪整饬,断不令小民有覆盆之冤”[13]卷80,嘉庆六年三月庚辰,总第29册,p34。就徐姓京控案看,该案最终冤情得雪,表明清廷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开辟的京控渠道仍可被视为有效。但是,在清廷对官员司法行为有严格制度约束的条件下,该案却于前两次京控审理中办成冤案;京控既然被清廷开辟为百姓申冤的渠道,呈控者却在付出生命代价,甚至不惜以暴力与官方相抗后,方获得较为公允的审判结果,这说明,京控并非百姓可以方便运用的诉讼途径,其成本相当昂贵。京控也并非朝廷可以简单用来为百姓申冤的工具,其运作复杂,效率低下。可以说,开放京控的实际效果与清廷的期望相去甚远。之所以如此,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京控制度本身蕴涵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就是地方司法能力的贫弱与朝廷司法监控力的片面强化不相适应,这种不相适应使得国家的司法能力无法随着民众司法服务需求的增加而获得实质性增强。 开放京控必然会给清朝各级政府,尤其是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司法压力。嘉庆五年,嘉庆帝上谕中曾指出:“乃近日来京呈诉之案,殆无虚日。其中多有以闾阎细故、琐屑上控。甚或挟嫌图诈,任意诛连。并闻有不肖之徒,以不干己事,挺身包揽,科敛钱文。”[13]卷70,嘉庆五年六月乙亥,总第28册,p938-939细绎该上谕,当时京控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控案数量巨大。京控事件并非都是朝廷所认为的大事,而是多有琐屑“闾阎细故”。二是审理难度不小。既有原告的“挟嫌图诈,任意诛连”,也有包揽词讼者的参与,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 嘉庆帝应对京控压力的办法是申严赴京越诉治罪条例。该条例要求诉讼必须逐级上诉,规定:“若未经在本籍地方及该上司先行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经结案,遽来京控告者,即所告属实,仍当治以越诉之罪”[17]卷816,p904。这一新例的目的在于将诉讼事务向地方政府分流,以减轻朝廷的司法压力。 除了申严越诉禁例外,嘉庆帝还将简派钦差为主审理京控案件的做法改为发回各省督抚负责重审。同时,要求督抚必须率同司道主官“亲行研讯”,不得转委属员,更不得发回原问官审理或会审。又要求地方主官担起亲审之责,勤于断案,及时审结,不得任意延宕,逾限未结者有罚。 总的来看,嘉庆帝改革京控案审理的诸多办法,都指向加大地方官的司法责任,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督,但并未相应增加地方司法资源以强化其司法能力。限期结案、逾限有罚的规定就已给地方官莫大压力,让他们感到“京控之案均系奏交、咨交要件,例限甚促”[18]刑政例下,“各属解省命盗、洋匪、会匪各案议定章程”条,p1002。由于地方行政和司法资源有限,嘉庆后期,逾限未结的京控案无省无之,少者三四案到十案,多者直隶三十二案,而山东竟有八十九案之多[13]卷289,嘉庆十九年四月乙丑,总第31册,p947。虽然违限之罚不能避免违限行为相当程度上存在,但并不意味违限之罚从不落实。地方有限的行政司法资源,也使原问官回避制度沦为具文。原问官回避,势必要调用其他府县甚至他省官员,但对于各有职司的官员来说,均有其本任职事,一经调动,本任职事亦不能及时处理,耽延积压在所难免⑩。因此,在实际的京控复审中,委用原问官的情况就比比皆是。(11)即就本文所涉案件而言,前两次京控复审,原问官陈斌与聂绍祖均被委用,并对案件审理结果起着主导作用,但委用他们的安徽藩臬二司主官之受罚,并非因为这一违例行为,而是因为“未能虚衷研鞫,几至酿成冤狱”[14]卷12,道光元年正月癸酉,总第33册,p240。就徐氏京控案来看,规避违限之罚及原问官回护,未尝不是安徽省前两次复审致误的重要原因。违限之罚的压力,促使地方官员将办案责任层层下压,导致相关执行人员以极端甚至非法之道为对策。本案中差役舒元之所以教唆痴呆徐兆做伪证,就在于他久拿要证不获,其家属被泾县拘禁。而陈斌、聂绍祖等问官偏重刑讯而疏于物证勘察、忽视证据间的矛盾,急于结案是其重要动机。当被违例再次委以同案问官时,维持之前的案情判断就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因为一旦翻案,由刑逼妄供被追究“故勘平人”之罪,将是他们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当该案再次发回安徽省重审时,安徽审案各员的措施就是进一步刑讯恐吓原告,将该案做成铁案。此时的参审各员已不再能以中立的立场公允办案,其角色俨然转变为徐姓京控者的对立方,其司法公信力在徐姓心目中已消失殆尽。 地方行政和司法资源的不足,不仅让限期结案、原问官回避等京控改革措施沦为具文,也让越诉禁例难以落实。据上文所引嘉庆五年例规定:“或现在审办未经结案,遽来京控告者,即所告属实,仍当治以越诉之罪。”本文所涉案件中,徐姓三次京控都是在“审办未经结案”之时,但孙玉庭最终结案时,并未追究徐姓的“越诉之罪”,这等于事实上否定了越诉禁例的有效性。其背后的原因,相关文献并未明言,但考量整个案情的发展,则可以发现,不懈的越诉在徐氏京控案中实为申冤之关键。而其中的关键之关键则为第三次京控中徐玉麟在刑部大门前的自刎控诉和徐姓宗族的抗官。徐玉麟的自刎,提升了京控重审的实际级别,督促了原问官回避制度的落实,而徐姓宗族的抗官则保全了最重要的物证,不然徐飞陇尸棺若让巡抚吴邦庆获得,则其不难按照“徐姓自行做伤致死”的先行结论制造尸伤、伪造证据,那么徐姓之冤将覆盆永戴。 反过来看,为了提高京控案复审的级别,督促落实原问官回避制度,求得相对公正的司法裁决,原告必须付出极高的诉讼成本,从自戕式控诉到冒着被朝廷以“乱民”罪名镇压风险的聚众抗官的极端方式,都是其中极昂贵选项。聚众抗官毕竟风险过大,分寸和时机拿捏不妥,即可能阖族遭受镇压,而自戕式控诉,已足可以唤起朝廷的重视,给地方督抚的重审施加足够压力。徐姓自戕案后不久,因争控坟山,又发生同县民徐行以抱告身份自刎身亡于都察院门前的事件[4]。清廷甚为警觉,为儆效尤,于道光二年通过新例,规定京控自戕主使者和自戕未死者,将被处以最高为“杖九十、徒二年半”的刑罚,以“保全民命”,并预杜借人命而妄自图赖、敲诈的风气[17]卷815,p894。但是,与可将被告方置于死地以及原告方重获新生的预计结果比起来,这一处罚仍是很值得的。即使自戕者身死,只要能将被告置于死地,也可获得一个平手,而冤抑得以申雪、本家族社会地位得以维持,尚在平手之上。所以,京控中不仅屡有原告宗亲的自戕式控诉,而且乡族发达之区,在地方纷争中,强势宗族也会惯于出现“贿买亡命、轻生变诈”的现象[19]161。 总之,清朝的京控制度,以及嘉庆帝的相关改革,都指向加大地方官的司法责任,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督,而并未相应地增加地方的司法资源以强化其司法能力,真正优质的司法资源只存在于朝廷和朝廷能够加以直接监督的总督。换言之,优质司法资源一般只存在于清朝司法体系的顶部。在清朝集权体制里,顶部的优质司法资源,犹如金字塔的塔尖,必定是稀缺的,当然也必定是昂贵的。 五、结语 本文所述徐姓自戕京控案,只是嘉庆、道光时期上千件京控案中的一例个案,无法说明京控案诉讼中错案和冤案发生的比率。但是,一叶知秋,不同的个案都有着相同的京控制度基础,从一例个案的解剖也可以管窥清代京控制度面临的问题。分化与竞讼的地方社会,增加了司法服务需求;而开放的京控,尤其是嘉庆帝也希望借京控和相应的改革来整饬吏治、改善民生,高度重视京控案的审理,也积极适应了社会的这种需求。然而,实际效果离清廷的期望却有着相当距离。究其原因,在于清代京控和司法制度,与行政体制同轨,都是一种“金字塔”构造,优质司法资源仅集中在司法体制顶部。嘉庆帝的改革措施,只是强化了顶部的纵向司法监控压力,而地方司法资源和能力并没有增强。就徐姓京控案来看,县级初审明显存在主审知县司法能力贫弱的问题,而司道的复审,存在违法委用原问官、刑讯逼供、不顾证据间矛盾等严重问题,京控相关法例成为具文,反映出可供使用的司法资源不足和审讯程序中问官权力缺乏制约。虽然经原告不懈京控,直至以自杀的极端方式控告,促动清廷动用级别更高、程序更加规范的司法力量,最终纠正了安徽省的错误。但是,纠错的成本极其高昂。原告家族不仅多人“酷刑成废”[2],而且付出了生命代价;安徽地方政府方面,不仅司道府县相关人员受到了不同处罚,地方政府的司法公信力也遭受严重损失,省级和跨省司法资源被多重消费。该案徐姓冤情最终得雪,则清廷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开辟的京控渠道仍可被视为有效力,但高昂的成本却说明京控作为解决社会日益增长的诉讼纠纷的方式并不令人满意。在朝廷权威仍在时,京控案件的多寡实与地方吏治的良窳成反比。推论之,则京控的效力与效率实相背离。而当这种背离达到一定临界点,则朝廷权威一并受损,连京控的效力一并失去。这一点,在清代闽粤乡族性械斗中也得到了印证。闽粤乡族性冲突之解决,诉诸京控途径,在嘉庆二十年以后明显增加,一方面是出于闽粤乡族力量对朝廷权威的信服,但同时也是地方吏治不良、处理讼案不力的表现。道光年间闽粤京控案的数量增加明显,而吏治更加腐败。咸丰、同治年间,受太平军影响,地方吏治尚不可问,京控案件亦不能得到尽心处理,人民赴京亦难,闽粤京控案件显著减少。但至光绪年间,军事已平,而闽粤京控案件则依然少见,其原因在于闽粤乡族对地方吏治和朝廷一并失去信任,对纠纷的处理直接诉诸乡族间的私斗[19]164-167。 注释: ①“京控”一词始见于清代,可视作“赴京控告”、“来京控诉”的简称。《清史稿·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对“京控”含义及京控案件受理情况有如下说明:“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与“京控”类似的有“叩阍”。“叩阍”本意指叩打宫门,引申为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冤屈。该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并为其后各代沿用。《清史稿·刑法志》对其解释如下:“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同上)。“叩阍”是一种直诉于皇帝的上诉行为,其地点可在京师,也可在皇帝出行时的任一地方。其缘起可追溯至尧舜时期设立的“进善之旌”与“诽谤之木”,其最初是作为统治者了解施政得失,而向臣民开放进言以陈利弊的渠道,后逐渐发展演变形成“邀车驾”、“击登闻鼓”、“上书言事”三种形式。清代制度,“京控及叩阍之案,或发回该省督抚,或奏交刑部提讯。如情罪重大,以及事涉各省大吏,抑经言官、督抚弹劾,往往钦命大臣莅审。发回及驳审之案,责成督抚率同司道亲鞫,不准复发原问官,名为钦部事件”(《清史稿》第4212页)目前学界对“京控”的理解仍存分歧,其焦点主要在“京控”与“叩阍”异同上。从程序上看,京控须经中央相关部门受理诉状后方可诉诸皇帝,而叩阍则是直诉皇帝,诉诸中央相关部门非其必要程序,这是两者的差异。但无论京控还是叩阍,最终都要奏闻皇帝,并且受理后的审理程序都一样,所以当时人与学界往往将两者等同视之。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认为叩阍形式之一的“上书公府言事”与“今之京控相似”(《历代刑法考》第1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生于光绪间的史学家连横也认为,民人自州县经府、道、省逐级上控,仍不服,“则控之京,谓之叩阍”(《台湾通史》卷12《刑法志》,第15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②嘉庆、道光两朝相关档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04-01-26-0039-028、04-01-01-0608-034、04-01-01-0608-036、04-01-26-0039-029、04-01-01-0623-036、04-01-01-0619-011;录副奏折,档号:03-2337-042、03-2338-022、03-2265-030、03-2266-016、03-2266-017;禀状,档号:03-2265-031。 ③以往关于清代京控制度的研究,多注重从制度形成及沿革层面分析,而就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仍缺乏较为具体的解释。京控制度相关研究较为主要者有:欧中坦(Jonathan K.Ocko)的《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收录于(美)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第566-61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此文侧重将京控作为社会问题来考察,对影响该制度运行的各种社会因素进行重点探讨。李典蓉的《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利用台湾地区保留的清朝档案资料,对京控制度的流变与实践进行探讨;胡震《最后的“青天”——清代京控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清代京控制度与晚清京控演变,尤其注重将晚清与民国时期处理类似案件的审判方式进行对比。阿风:「清代の京控―嘉庆朝を中心に」((日)夫马進编:『中国訴訟社会史の研究』,第333-379页,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年),利用清代上谕档中的案例资料并结合《清史稿》等文献,对清代京控制度的概念、渊源以及嘉庆朝京控制度的完善,嘉庆朝京控扩大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④根据(美)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估计:1650年时,中国总人口约为1-1.5亿;1750年时,约为2-2.5亿;到1850年时,已上升至约4.1亿。参见:(美)王业健《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9页。 ⑤参见: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350-355页、第403-404页;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09-417页。 ⑥参见:(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8页。 ⑦乾隆《泾县志》称泾县“敝俗相沿,大端有三,曰停葬,曰溺女,曰健讼。”(嘉庆《宁国府志》卷9《舆地志·风俗》,第33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⑧道光《泾县续志》中并无“清宁”其人,但有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清善”任知县的记载。“清善,字撰堂,镶黄旗人,举人,敬避御名,下一字改今名”。在“安徽巡抚吴邦庆奏为特参泾县知县清宁审办命案草率以致尸亲逞刁诬赖案延莫结请革职事”一折中,吴邦庆将其写作“清宁”;但在“两江总督孙玉庭奏为遵旨审明安徽泾县民徐玉麟呈控族兄徐飞陇被挟嫌围杀委员诬审反坐一案按律定拟事”一折中,则将其写作“清凝”。故本文推测“清凝”原为“清宁”,为避讳道光皇帝名讳旻宁而改。 ⑨清代所谓上控,指案件涉讼者对审理或判决不满时,向其所控司法机构之上级衙门呈控的行为。京控作为向中央司法机关的呈控,是清代上控的最高层级。 ⑩美国学者施坚雅曾观察中国每一王朝极盛时期县级区划的数目,发现根据史籍记载,贯穿帝国时代的历史中,县级区划的数目极为稳定。由此,其推断“如果说随着边境的扩展,新县也相继建立,那么很明显,在原来定居的地区中,县数却有规律的在减少。中国历史上县级区划的稳定性,恰恰说明中国历史从中唐以后直到帝国结束,出现了政府效率长期下降,基层行政中心职能一代比一代不断缩减的情况”。(详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例,三帝均曾对督抚司道等将上控之案仍批交原审之府州县审办的行为严加申斥,并惩处个别官员。如嘉庆二十五年六月壬辰,安徽巡抚姚祖同因将特旨交办之案仍发原审之府州县覆审被交部议处。(《清仁宗实录》卷372,《清实录》总第32册第912页)但总体看来,这一现象仍继续存在,在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乙丑的上谕中,道光帝曾指出:“该督抚等复不为亲提究办,仍发原审之员。该员等明知审断错误,意存回护前非,又焉肯力为昭雪”。(《清宣宗实录》卷419,《清实录》总第39册第25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