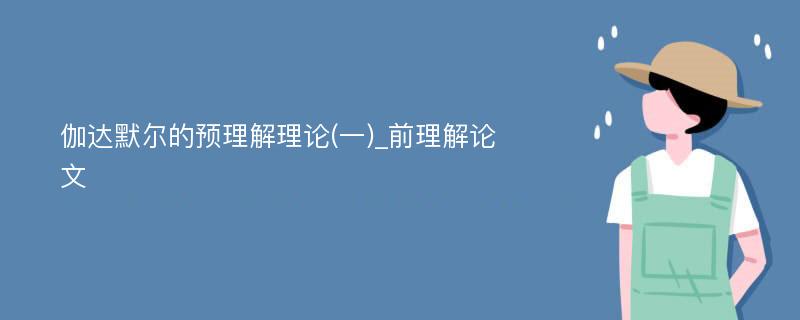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伽达默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1-0053-10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是从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理论发展而来的,但由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使之超出了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而转入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诠释学。
一、诠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精神科学的循环结构①在诠释学里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解释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在诠释学里被称之为诠释学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古代修辞学早就认识到整体与部分所谓诠释学循环,即要理解语句,首先要理解其中的语词,而要理解语词,又必须先理解语句。宗教改革派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曾把这种从古代修辞学里所得知的观点应用于理解过程,并把它发展成为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当从上下文关系以及整体所目向的统一意义,即从scopus(整体结构)上加以理解;反之,整体结构的统一意义又必须从一切个别细节去理解。当把这一原则用于对《圣经》的理解时,他们反驳罗马教会独断论对《圣经》的解释,认为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关系乃是对《圣经》理解和解释的唯一正确原则:一方面对《圣经》的整体理解指导着对个别细节的解释,另一方面,《圣经》这一整体也只有通过对个别细节的理解才能获得。从这里,新教改革派提出《圣经》是自身解释自身的所谓《圣经》自解原则(Schriftprinzip)。
对于古代修辞学这种整体与个别的诠释学循环,伽达默尔在他的《论理解的循环》(1959)一文中写到:“我们必须从个别理解整体并以整体理解个别这一诠释学规则,来自于古代的修辞学并经由近代诠释学而从一种说话艺术转变为理解的艺术。不管是在修辞学中还是在诠释学中,它都是一种循环的关系。整体得以被意指的对意义的预期是通过以下这点而达到清楚的理解,即从整体出发规定着自己的部分也从它这方面规定着该整体。”[1](P57)伽达默尔曾以外语学习为例,说明人们在理解一句外语的意义时,必须首先理解该句子的成分即语词,但在理解该语句的语词意义时,人们又要先理解整个语句的意义。按照传统的诠释学,理解的运动就是这样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到整体。“所有个别和整体的一致就是当时理解正确性的标准,而缺乏这种一致则意味着理解的失败”[1](P57)。
施莱尔马赫曾经把这种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循环区分为客观的(语法方面的)与主观的(心理方面的)两方面:从语法方面看,正如个别的词从属于语句的上下文一样,个别的文本也从属于其作者的作品的脉络关系,而作者的作品类集又属于当时有关的文字类或文学整体;从心理方面看,同一文本作为某一瞬间创造性的表现,又从属于其作者的内心生活的整体,而作者的整个内心思想又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但不论是语法解释,还是心理解释,我们都可看到这种循环总是处于理解对象方面,即处于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或作品方面,以及同样也作为理解对象的作者思想或精神方面。这就是说,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诠释学循环只是处于理解对象方面的循环,即使施莱尔马赫也谈到一种预期或预感,但那也是作为理解对象整体理解的部分。
施莱尔马赫这种只涉及理解对象的诠释学循环,使他把理解只看作与作者处于同一层次的活动,这样一来,文本就被解释为其作者的生命的特有表现。伽达默尔曾以施莱尔马赫所谓“自身置入作者的内心中”来解释施莱尔马赫这种理解对象上的循环,他说,施莱尔马赫这种自身置入并未真正把我们自身的观点置入理解对象之中,而是把自身置入理解对象的意见之中,即自身消失于理解对象的意见之中,也就是说,“我们试图承认他人所说的具有事实的正确性”[1](P297)。对于施莱尔马赫和以后的狄尔泰来说,诠释学循环始终是在理解对象方面进行的,它并未出现于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因此它是单方面而非双方面的。另外,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也主张循环消失,这样才能达到正确的理解。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施莱尔马赫之所以主张这种单方面的诠释学理解,是因为他认为要理解的东西,只是过去作者的意图,而忘记了对真理内容的理解。这种错误正如历史学家所犯的错误一样,历史学家只像肖像画家那样仅在自己作品里寻找历史原型。伽达默尔写道,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文献类似于肖像画家,他们“好像到处在艺术作品上找寻模型,也就是说追踪那些被汇入作品里的历史联系,尽管这些联系尚未被他的时代的观众所认识,而且对于整个作品的意义并不重要”[1](P151)。伽达默尔认为,把过去历史地重构为过去——这就是说,把过去重构为与现在中介相反的东西--乃是历史学的错误。与此相反,他认为接近过去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现在与过去的中介。在这里,伽达默尔认为,施莱尔马赫的直接先驱语文学家阿斯特在这方面超出了施莱尔马赫,他对诠释学的任务有一种十分坚定的内容性的理解,即要求诠释学应该在古代和基督教之间,以及新发现的真正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传统之间建立一致性,也就是说,诠释学理解需要在古代与现代、过去与现在、陌生性与熟悉性之间进行调解。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这就和启蒙时代相比有了新意,“因为如今已不再涉及到对传统的权威为一方和以自然理性为另一方的两方之间作调解,而是涉及到两种传统因素的调解,这两种因素都是通过启蒙运动而被意识到,从而提出了它们之间和解的任务”[1](P151)。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理论对于诠释学现象具有一种真理要素,可惜施莱尔马赫和他的后继者却把这些抛弃了。对此,伽达默尔评论说:“阿斯特通过他的思辨能力防止了在历史中只找寻过去而不找寻当前真理的做法,从施莱尔马赫继承下来的诠释学相对于这些背景就显得比较浅薄地流行于方法的诠释学了。”[1](P59)
与施莱尔马赫相反,海德格尔从生存论出发对诠释学循环的描述与论证,使理解的循环结构重新获得内容和意义。海德格尔写到:“循环不可以被贬低为一种恶性循环,即使被认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也不行。在这种循环中包藏着最原始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这就是解释理解到它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及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1](P270-271)。显然,这是一种新的理解循环,或者说新的理解的诠释学循环。伽达默尔说:“我们将必须探究海德格尔从此在的时间性推导理解循环结构这一根本做法对于精神科学诠释学所具有的后果”[1](P270)。
伽达默尔怎样解释和接受海德格尔这种以前结构为出发点的理解循环观点呢?伽达默尔首先说,海德格尔在此所讲首先并不是一种对理解实践的方法论要求,而是描述理解性解释的进行方式本身。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海德格尔诠释学反思的成就并不在于指出这里存在一种循环,而在于指出这种循环具有本体论的积极意义”[1](P59)。伽达默尔所说的这种本体论的意义,我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把理解的主体性赋予了理解的循环,使理解的循环从单纯理解对象方面的来回跑着发展成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之间的辩证运动;另一是以事情本身作为理解的预设标准,所有理解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未曾注意的思维习惯的束缚,从而把目光指向“事情本身”。
如上所述,诠释学循环在古典诠释学里是一条重要解释规则:要理解语句,首先要理解其中的语词,而要理解语词,又必须先理解语句。同样,要理解文本,首先要理解其中的语句,而要理解语句,又必须先理解文本。在古典诠释学家看来,解释总是处于这种循环之中。自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后,古典诠释学的这一诠释学循环发生了某种本质的转变,即循环不仅是指研究对象里的语词与语句,语句与文本之间的循环,而且也指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循环,这也就是说,理解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前结构与理解对象的内容的一种相互对话和交融的结果。伽达默尔说:“诠释学循环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获得一种全新的含义。迄今为止的理论总把理解的循环结构局限于个体与整体的形式关系的范围内,亦即局限于它的主观反思:先对整体作预测然后在个体中作解释。按照这种理论,循环运动就仅仅围绕文本进行并在对文本完成了的理解中被扬弃。这种理解理论在一种预感行为中达到顶点,这种预感行为完全从作者的角度着想,并由此而消除掉文本所具有的一切陌生和疏异性。海德格尔则正相反,他认为对文本的理解一直受到前理解的前把握活动支配。海德格尔所描写的不过是把历史意识具体化。这项任务要求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前意见和前见,并努力把历史意识渗透到理解的过程中,从而使把握历史他者以及由此运用的历史方法不只是看出人们放置进去的东西。”[1](P61)。另外,他还更富有哲理地写到:“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对诠释学循环的描述和生存论上的论证,表现了一种决定性的转折。19世纪的诠释学理论确实也讲到过理解的循环结构,但始终是在部分与整体的一种形式关系的框架中,亦即总是从预知推知整体,其后在部分中解释整体这种主观的反思中来理解循环结构。按照这种理论,理解的循环运动总是沿着文本来回跑着,而当文本被完全理解时,这种循环就消失了。这种理解理论合乎逻辑地在施莱尔马赫的预感行为学说里达到了顶峰,即一个人完全把自身置身于作者的精神中,从而消除了关于文本的一切陌生的和诧异的东西。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则是这样来描述循环的: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在完满的理解中,整体和部分的循环不是被消除,而是相反地得到最真正的实现。”这样,“这种循环在本质上就不是形式的,它既不是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而是把理解活动描述为传承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2](P298)。所以,按照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看法,理解的循环“不是一种'方法论'的循环,而是描述了一种理解中的本体论的结构要素”[2](P299)。
其次,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们不能避免理解对前理解的依赖,但理解不能恶性循环,还必须要证明前理解中的前结构。海德格尔说,前理解里的前结构必须建立在事情本身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流俗意见之上。这也就是说,支配我们对某个文本理解的那种意义预期,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而是由事情本身所规定的。伽达默尔曾写到:“谁想进行理解,谁就可能面临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意见的干扰。因此,理解的经常性任务就是构造正确的、与事情相符合的筹划,这叫做先行冒险,而且这种先行应该不断'由事情本身'得到证明。除了构造出自我保证的前意见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客观性'。这有其很好的意思:解释者并非从自身业已具有的前意见出发走向'文本',而是检查本身具有的前意见是否合法,亦即检验它的来源和有效性。”[1](P60)。伽达默尔进一步分析说,这种事情本身就是那种把我们与传承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是在我们与传承物的关系中,在经常不断的教化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共同性并不只是我们已经总是有的前提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因为我们理解,参与传承物进程,并因而继续规定传承物进程。所以,理解的循环一般不是一种'方法论的'循环,而是描述了一种理解中的本体论的结构要素”[2](P298-299)。这两方面可以说是海德格尔对诠释学循环的重要贡献,前一方面构成了哲学诠释学经验理论所谓的“前理解”,后一方面则构成这一经验理论所谓的“事情本身”。
此外,诠释学循环在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那里,是一种要被理解克服的东西,似乎理解完成了,诠释学循环就消失了,但对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的循环是不可消失的,前一循环解决了,可能又会出现后一循环,正如理解是一无限过程,诠释学循环也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理解过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决定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进入循环”。伽达默尔曾这样来描述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则是这样来描述循环的: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在完满的理解中,整个和部分的循环不是被消除,而是相反地得到最真正的实现。”[2](P298)对于诠释学循环,伽达默尔比海德格尔具有更深的看法,海德格尔主张诠释学循环不应是恶性循环,甚至可容忍的恶性循环也不行,伽达默尔则主张诠释学循环可以是恶性,他曾表示要为恶性循环恢复名誉:“我从一开始就作为‘恶’的无限性的辩护人而著称,这种恶使我同黑格尔处于似乎是极为紧张的关系之中。不管怎样,在《真理与方法》那本书中处理反思哲学的界限并转为分析经验概念的那章中,我都试图清楚地说明这一点。”[1](P8)在那里,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循环正表明一种真正的经验,而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的经验”[2](P363)。我们对存在东西的认识并不意味是一种完全性的认识,而是意味着对这样一种界限的洞见,“意味着有限存在的一切期望和计谋都是有限的和有限制的。真正的经验就是对我们自身历史性的经验”[2](P363)。这种经验概念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诠释学效果历史意识原则。在1983年所写的《文本和解释》一文中,伽达默尔更深刻地谈到他所谓的诠释学循环:
海德格尔在分析理解时怀着批判和论战的目的,他以诠释学循环的古老说法为依据,把诠释学循环作为某种积极的因素加以强调,并在他的此在分析中用概念对此加以表达。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里讨论的并非作为一种形而上学隐喻的循环性,而是在科学证明理论中作为恶性循环理论而有其特有地位的逻辑概念。诠释学循环概念只是表明,在理解领域内根本不能要求从此物到彼物的推导,所以循环性的逻辑证明错误不代表理解程序的错误,相反,诠释学循环乃是对理解结构的恰当描述。所以把诠释学循环作为对逻辑推理理想的限制这一讲法是通过狄尔泰被引入施莱尔马赫的后继者中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与从语言用法出发的理解概念相适宜的真正范围,那么诠释学循环的讲法实际上就指明了在世存在的结构本身,亦即指明了对主-客二分的扬弃,这正是海德格尔对此在先验分析的基础。正如懂得使用工具的人不会把工具当作客体,而只是使用它,同样,此在在其存在和世界中得以领会自身的理解也绝不是与某种认识客体打交道,而是实现它的在世存在本身[1](P331)。
正是基于这一点,伽达默尔始终坚持诠释学循环的固有内在性(Immanenz),他说:“实际上我觉得,要想突破诠释学循环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甚而矛盾的要求”[1](P335)。
二、前理解(Vorverstaendnis)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对理解所描述的循环开始其新的探索,他认为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理解过程是“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2](P272)。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曾指出,理解的前结构是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他说:“这种解释一向奠基于一种前有之中。作为理解的占有,解释活动有所理解地向已经被理解了的因缘整体性去存在。对被理解了的但还隐绰未彰的东西的占有总是在这样一种眼光的指导下进行揭示,这种眼光把解释被理解的东西时所应着眼的那种东西确定下来。解释向来奠基于前见之中,它瞄准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前有中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并且前见地被瞄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解释可以从有待解释的在者自身汲取属于这个在者的概念方式,但是也可以迫使这个在者进入另一些概念,虽然按照这个在者的存在方式来说,这些概念同这个在者是相反的。无论如何,解释一向已经断然地或有所保留地决定好了对某种概念方式表示赞同。解释奠基于一种前把握之中”[3](P150)。
据此可知,前有是指此在的理解存在与它先行理解的因缘关系整体具有一种先行的占有关系,也就是说,此在在去理解之前,对已经被理解了的因缘关系整体先就具有了某种关系,我们把要理解的东西置入这种先有的关系中,例如,我们先具有了的历史处境与传统观念,我们不是一无所有地进行理解,而是有所东西地进行理解。所谓前见是指前有中的那些可以在这种特殊的理解事件中被解释的特殊方向,也就是对被理解了的但还隐绰未彰的东西总是在这样一种眼光的指导下进行揭示,其实就是解释者理解某一事物的先行立场或视角。所谓前把握是指我们进行理解时事先所具有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是我们在进行理解之前先要具有的,所以海德格尔说解释奠基于一种前把握之中。概括地讲,前有、前见与前把握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结构,即“被理解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并且前见地被瞄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海德格尔认为,一切理解都具有这种前结构。那么,伽达默尔是怎样解释和发展海德格尔这种前结构呢?
第一,伽达默尔肯定这种前结构是理解的必要条件,并且把这种前结构叫做前理解(Vorverstaendnis)。理解开始于前理解,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观点,它起源于古希腊。在柏拉图的回忆说里,这种观点就有其最初的神秘的烙印,以后亚理士多德在其《后分析篇》中直接用这样的话开始:每个合理的学说和教导都依赖于以前得来的认识。伊壁鸠鲁还以更明确的方式说,要在“前概念”(πρoληψεισ)里去认识真理标准,我们经验的一切将根据我们已经认识的东西去衡量,没有前概念,也就不可能对一个新事物进行评判。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曾采用胡塞尔的看法,即任何对对象的理解就是把某物视为某物的那个对象的理解,也就是说,一切理解都包含对我们的知觉筹划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并不严格包含在我们的知觉本身中,例如,我们的视觉本来只有一向的经验,但我们能对迎面的桌子有三向的经验,并把所看到的东西视为三向中的一个向。胡塞尔将之称为一种“意义赋予的意向性行为”。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这里所说的意义赋予就是意义的筹划、预期或解释。他说:“毫无疑义,观看作为一种对那里存在的事物的解释性的了解,仿佛把视线从那里存在的许多东西上移开了,以致这些东西对于观看来说不再存在。但同样,观看也被预期引导着‘看出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单纯的观看和单纯的闻听都是独断论的抽象,这种抽象人为地贬低了可感对象。感知总是把握意义。”[2](P96-97)。观看事物是这样,理解文本更是这样。人们阅读文本并不是一无所有地去阅读,总是先有一种筹划或预期,或者说是前理解,人们总是带着前理解去理解一个陌生的文本。伽达默尔说:“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如下观点,即在听某人讲话或去参加一个讲座时绝不能对内容带有任何前意见并且必须忘记自己所有的前意见,相反,应该一直坦率地把对他人或文本的意见包括在内,把它们置于与自己所有意见的一种关系,或把自己的意见包括在内,把它们置于与自己所有意见的一种关系之中,或把自己的意见置于它们的意见之中”[1](P60)。伽达默尔曾以此观点重新解释施莱尔马赫所谓“自身置入”的意思,他说,什么是自身置入呢?这无疑不是丢弃自己,相反,“我们必须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这个他人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实现了自我置入的意义”[1](P310)。因此,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人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他还说:“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特殊期待去读文本。作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就是对这里存在的东西的理解。”[1](P271)。筹划或预期,本身皆属于意义的成分,因为意义总是解释与对象的视域融合,因此前理解是理解意义的必要条件。
第二,为了牢固地树立理解的前见观点,伽达默尔转向对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批判。启蒙运动曾以批判前见为出发点。他们把前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人的威望而来的前见;另一种是由于过分轻率而来的前见。按照启蒙运动者的看法,这两者皆由于未能正确使用理性:轻率是错误地使用自己理性,而权威则在于未使用理性,他们因此而认为任何前见都应当受到批判。浪漫主义尽管与启蒙运动不同,它承认权威和传统的力量,但它仍分享了启蒙运动的前提,认为权威与理性相分离[2](P278)。对此,伽达默尔批判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权威信仰和使用理性两者之间的对立,尽管具有合理性,但这并不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权威首先是人的权威,但“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与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领先,即他的判断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2](P284)。这样,权威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权威,伽达默尔着重论述了无名称的权威——传统。伽达默尔说:“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2](P286)。从这里伽达默尔得出精神科学的研究“不能认为自己是处于一种与我们作为历史存在对过去所采取的态度的绝对对立之中”[2](P286),在他看来,我们经常采取的对过去的态度中,真正的要求无论如何不是使我们远离和摆脱传统,而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2](P286)。为了与同样承认传统力量的浪漫主义相区别,伽达默尔特别指出浪漫主义只是颠倒了启蒙运动对前提的评价,他们不是否定过去和传统,而是无批判地赞赏它们,以致“对理性完满性的信仰现在突然地变成了对'神话的'意识的完满性的信仰,并且在思想堕落(原罪)之前的某个原始乐园里进行反思”[2](P278)。伽达默尔强调理解中前见与理性批判的结合以达到过去和现在的中介,他说:“理解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得以中介。”[2](P295)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运动反对前见本身就是一种前见,他们就是根据这一前见而反对前见的。因此,他们对前见的否定本身却证明前见的存在。
第三,伽达默尔肯定前见或预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从事情本身出发,他说:“一种受方法论意识所指导的理解,不只是形成它的预期,而是对预期有意识,以便能控制预期因而从事情本身获得正确的理解。”[2](P274)同样,如果理解是筹划,那么筹划也必须从事情出发。伽达默尔说:“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作出正确的符合于事情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2](P272)伽达默尔不仅强调了我们的前见必须从事情本身出发,而且对事情本身也作了解释,他说:“支配我们对某个文本理解的那种意义预期,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而是由那种把我们与传承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Gemeinsamkeit)所规定的。但这种共同性是在我们与传承物的关系中,在经常不断的教化过程中被把握的。”[2](P298)。事情本身就是由那种把我们与传承物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性所规定的。这里的要点是:(1)意义的解释性筹划根源于解释者的境遇。伽达默尔说:“海德格尔曾经正确地坚持说,他称之为被抛状态(Geworfenhei)的东西和属筹划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根本不存在那种使得这种生存论结构整体不起作用的理解和解释——即使认识者的意图只是想读出'那里存在着什么',并且想从其根源推知'它本来就是怎样的。'”[2](P266-267)这种被抛就是我们的处境,在伽达默尔看来,任何理解都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客观,所有理解都包含由我们自己境遇而来的意义的筹划并超出了要观察的“事实”。当然,我们得以理解作品或历史事件的“被抛”境遇本身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或任意的境遇。伽达默尔说:“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就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2](P301)(2)我们的理解也得自传承物本身以前曾被理解的方式,根源于历史的和解释的传统的发展过程。因此,这种前见不是个人的单独财产,非个人的主观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前见其实就是“再现传统的陈述”。为了说明这种历史产物,伽达默尔引证了古典型概念,古典型作为一种规范的美和完美的理想,一直保持它的力量并继续指导我们的审美理解,伽达默尔说:“古典型之所以是某种对抗历史批判的东西,乃是因为它的历史性的领域,它的那种有义务要去流传和保持已经先行了的历史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中继续存在的有效性的力量”[2](P292)。此后,伽达默尔把这种历史力量称为“效果历史”。另外,伽达默尔也讲到,我们虽然不能没有前理解,但这种前理解必须对作为事情本身的他人或文本持开放的态度。他说:“正如我们不能继续误解某个用语否则会使整体的意义遭到破坏一样,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坚持我们自己对于事情的前见解,假如我们想理解他人的见解的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我们倾听某人讲话或阅读某个著作时,我们必须忘掉所有关于内容的前见解和所有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文本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2](P273)。
第四,伽达默尔还强调说,只有从前有、前见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注意对象的他在性。伽达默尔说:“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文本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谁想理解一个文本,谁就准备让文本告诉他什么。因此,一个受过诠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文本的另一种存在有敏感。但是,这样一种敏感既不假定事物的'中立性',又不假定自我消解,而是包含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和前见的有意识同化。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使得文本可以表现自身在其另一种存在中,并因而有可能去肯定它实际的真理以反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2](P274)
第五,当然,前见有正确与不正确和真与假之分,如何区别它们呢?对此,解释者自己是不能事先区分的,而必须由时间距离来决定。伽达默尔说:“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和前见解,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和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2](P301)真正作出这种区分的就是时间距离。伽达默尔说:“只有时间距离才能使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说,才能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区分开来。”①另外,伽达默尔也谈到“对自己的前见作基本的悬置”,他说:“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理解借以开始的最先东西乃是某事能与我们进行攀谈,这是一切诠释学条件里的最首要的条件。我们现在知道这需要什么,即对自己的前见作基本的悬置。但是,对判断的一切悬置,因而也就是对前见的一切悬置,从逻辑上看,都具有问题的结构。”[2](P304)
三、事情本身(Sache selbst)
海德格尔说:“循环不可以被贬低为一种恶性循环,即使被认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也不行。在这种循环中蕴藏着最原始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这就是解释理解到它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3](P153)
伽达默尔指出,海德格尔在这里描述了理解性的解释得以完成的方式,“所有正确的解释都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觉察的思想习惯的局限性,并且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这在语文学家那里就是充满意义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则又涉及事情)。的确,让自己这样地被事情所规定,对于解释者来说,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勇敢的'决定,而是'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因为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必须克服他们所经常经历到的起源于自身的精神涣散而注目于事情本身。”[2](P271)这里,伽达默尔一方面维护了海德格尔要从事情本身出发这一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他又对事情本身作出解释,他说“事情本身”在语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那里就是指富有意义的文本所涉及的对象(事情),我们一般可以以文本所表现的事理或真理内容来理解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说的事情本身。
“事情本身”这一概念应当说来源于胡塞尔。大家知道,胡塞尔的名言就是“面向事情本身!”胡塞尔曾把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与他那著名的要求“面向事情本身”相联系。他写到:“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事情与问题”,哲学作为科学一定不是开始于以前的各种哲学的结果,而一定是在事情里发现其绝对开端。他继续这样澄清事情的意义:“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放弃彻底的无前见性(Vorurteilslosigkeit),例如不可从一开始就将这样一些'事情'(Sachen)等同于经验的'事实'(Tatsachen),即在那些以如此大的范围在直接的直观中绝对被给予的观念面前佯装盲目”[4](P69)。
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里,胡塞尔称赞经验主义这一动机,即为了发现知识的真基础,我们需要批判地抛弃盲目迷信、传统信仰和偶像。他写到:“合理地和科学地判断事情就意谓着朝向事情本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ten),或从话语和意见返回事情本身(auf die Sachen selbstzurueckgehen),在其自身所与性中探索事情并摆脱一切不符合事情的前见。”[4](P75)返回到事情意指返回到知识的绝对基础,返回到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开端点。另外,它也不意味无批判地接受传统的哲学观念。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事情本身从积极方面意味着研究的开端点,因而是真知识的实在的或实际的基础。“面向事情本身”这一名言的消极意义包含对以前接受的出发点的怀疑。
不过,事情本身对于胡塞尔而言,并不就停留在这里。一当经验主义接受经验事实为基础而忽视它们在意识中的概括时,胡塞尔就认为经验主义在此停滞不前。胡塞尔批判说:“经验主义论证的基本缺点是,把对返回'事情本身'的基本要求与一切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论证的要求相等同或混而一谈。经验主义者通过他用来约束可认识的'事情'范围的可以理解的自然主义限制,干脆把经验当作呈现着事情本身的唯一行为。但事情并不只是自然事实。”[4](P76)。因此,胡塞尔在其研究中,当他转向事情时,特别强调对现象认识的主观方面,即意识的意向行为。
同样,海德格尔也谈到事情本身,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定义为表现“面向事情本身”这句名言的哲学的方法或方式[3](P27)。事情本身的对立面是无根据的建构,偶发奇想和无根据的思想。因此,“面向事情本身”这句名言就意味着“反对一切飘浮无据的虚构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不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虽然它们往往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其为‘问题’”[3](P28)。而现象学意味着:“让人从显现的东西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3](P34)。所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事情本身就是那种表现自身为自身的东西。
显然,对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来说,事情本身在广义上都意指理解的正确基础[3](P153)。这是哲学必须发现的基础。但海德格尔也使自己与胡塞尔有所区别,这在于他怀疑这种事情本身是否能意指意向性意识,有如胡塞尔所认为的那样,海德格尔指出,表现自身为本质的事情本身的存在(Being)。
在理解事情本身方面,伽达默尔确实跟随海德格尔的想法而离开胡塞尔,他不把事情本身理解为意向性意识,而是理解为存在的揭示(revelation)。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事情本身就是建立合法前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秉承了事情在胡塞尔名言里原来广的意义,即事情是真知识的基础。不过他也秉承了“事情”的消极意义:它们不是以前的各种哲学的先设想的概念。伽达默尔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显现自身的东西就是事情。因此,伽达默尔把“事情本身”理解为在存在中和通过存在展现自身的东西。存在是语言,所以事情本身就是展现自身于语言中和作为Ansicht的东西。伽达默尔与胡塞尔一样,并不认为单纯感觉对象是事物(Sache),尽管这种经验的基础是事物。而且很清楚,像公正这样的观念也建基于事情。因此,作为aletheia(无蔽)的真理就是认识事情在语言中的自我表现。在此意义上,事情本身就是被讨论的主题、真认识的“对象”以及正确理解的基础。
关于这种作为事理或真理内容的事情本身,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有一解释,他说:“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两个人之间进行的谈话模式来考虑诠释学现象,那么,这两个表面上是如此不同的情况,即文本理解(Textverstaendnis)和谈话中的相互理解(Verstaendigung im Gespraech)之间的主要共同点首先在于,每一种理解和相互理解都涉及到一个置于其面前的事情。正如一个人与他的谈话伙伴关于某事情取得相互理解一样,解释者也理解文本对他所说的事情”[2](P383—384)。因此,事情本身就是我们要理解的文本或谈话要取得理解的对象或内容。
在这里,事情本身首先是作为一种制约主体前见任意性的客观性而出现的。当伽达默尔讲到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理解过程是开始于前理解,而后前理解被更合适的理解所修正,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他说:“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了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解的干扰。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作出正确的符合于事情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2](P272)。伽达默尔还特别说强调,“理解完全地得到其真正可能性,只有当理解所设定的前见解不是任意的。”[2](P272)或者说,“一切理解的目的都在于取得对事情的一致性”[2](P297)。为此,“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使得文本可以表现自身在其另一种存在中,并因而有可能去肯定它实际的真理以反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2](P274)。事情本身设定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真理发生,使某些陌生意义的内容可能开放;另一方面,它启示了我们的前见,因为他人的真理经常被放在与我们的真理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它不设定不可扬弃的前知识。
这样,“诠释学的任务自发地变成了一种事实的探究”,“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文本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直到文本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且取消了错误的理解为止。谁想理解一个文本,谁就准备让文本告诉他什么。因此一个受过诠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文本的另一种存在有敏感。”[2](P330)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事情本身就是一种陌生性、对抗性。他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熟悉性和陌生性的两极对立,而诠释学的任务就是建立在这种两极对立上。”[2](P330)。在这里,伽达默尔讲到诠释学的对立两极,熟悉性这一极指理解者与传承物所具有的共同性以致传统连续方面,显然是指理解者的前理解或主观性方面,而陌生性这一极指传承物与理解者的时间距离以致传统可能中断方面,显然是指文本或他人的事情本身。伽达默尔认为,事情本身就是这种对理解者主观性起制约作用的陌生之物,他说:“传承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2](P330)。如果我们以前见作为熟悉性,而以事情本身作为陌生性,我们似乎就看到这样一种辩证法,即只有前见告诉我们事情,而只有事情才产生对前见的修正,这正是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所讲的诠释学循环。
伽达默尔还从谈话过程来揭示这种事情本身对理解的制约性,他说:“把诠释学任务描述为与文本进行的一种谈话,这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是对原始东西的一种回忆。”[2](374)为什么是一种回忆呢?因为最早的柏拉图的对话便是说,“服从谈话伙伴所指向的论题的指导。进行谈话并不要求否认别人,而是相反地要求真正考虑别人意见的实际力量。因此谈话是一种检验的艺术”[2](P373)。检验艺术就是提问艺术,而提问就是暴露和开放,伽达默尔把这种艺术称之为辩证法。他说:“辩证法并不在于试图发现所说东西的弱点,而是在于显露它的真正强大。辩证法并不是那种能使某个软弱东西成为强大东西的论证艺术和讲演艺术,而是那种能从事情本身出发增强反对意见的思考艺术。”[2](P373)
不过,如果我们深入研讨伽达默尔所解释的事情本身,我们则可以看到,这种事情本身尽管是作为陌生性与客观性的预设,以与我们理解可能主观性和任意性相对立,但是,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事情本身却不是完全客观和中立的,它不假定自我消解,而是包含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和前见的有意识同化。他说:“确切地说,在成功的谈话中,谈话伙伴都处于事情的真理之下,从而彼此结合成一个新的共同体。谈话中的相互理解不是某种单纯的自我表现和自己观点的贯彻执行,而是一种使我们进入那种使我们自身也有所改变的公共性中的转换(eine Verwandlung ins Gemeinsame hin,in der man nicht bleibt,was man war )”[2](P384)。
因此,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事情本身可以是相对变化的。正如我们不可认为前见自行消失,同样也不可认为事情本身能纯粹自我展现。事情本身其实总是被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问题所制约。在《真理与方法》里,伽达默尔曾讲到理解“对象”,实际上,对象可以作为事情本身来理解:“虽然对象确实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但对象只是通过它在其中向我们呈现的方面而获得它的生命。我们承认对象有在不同的时间或从不同的方面历史地表现自身的诸不同方面;我们承认这些方面并不是简单地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被抛弃,而是像相互排斥的诸条件,这些条件每一个都是独立存在的,并且只由于我们才结合起来。我们的历史意识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能听到过去反响的声音。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声音中,过去才表现出来。这构成了我们所分享和想分享的传统的本质。现代的历史研究本身不仅是研究,而且是传统的传递。”[2](P289)
关于事情本身的这种变化关系,伽达默尔在谈到历史诠释学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认识,即在精神科学里所进行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在这里仅当文本每次都以不同方式被理解时,文本才可以说得到理解。这正表明了历史诠释学的任务,即它必须深入思考存在于共同事情的同一性和理解这种事情所必须要有的变迁境况之间的对立关系。”[2](P314)同一事情本身却随着不同的境况而有不同的理解。
研究对象是这种不断变化的东西,这就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固定对象不同,在这里,伽达默尔讲到精神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不同,他说:“我们不能在适合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即研究愈来愈深入到自然里面……讲到精神科学的固定的研究目的。其实,在精神科学里,致力于研究传统的兴趣是被当代及其兴趣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激发起来。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因此,历史的研究被带到了生命自身所处的历史运动里,并且不能用它正在研究的对象从目的论上加以理解。这样一种‘对象’本身显然根本不存在。这正是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当自然科学的对象可以理想地被规定为在完全的自然知识里可以被认识的东西时,如果我们说某种完全的历史知识,就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正因为这种理由,我们也根本不可能讲到这种研究所探讨的‘对象本身’。”[2](P289—290)
事情本身这种不断变化的现象,伽达默尔是以事情本身的语言表达(das Zur-Sprach-Kommen derSache selbst)来说明的,当他解释了事情本身是每一种文本理解和每一种谈话相互理解所涉及到的一个置于其面前的对象,正如一个人与他的谈话伙伴关于某事情取得相互理解一样,解释者也理解文本对他所说的事情的时候,他马上说:“这种对事情的理解必然通过语言的形式而产生,但这不是说理解是事后被嵌入语言中的,而是说理解的实现方式——这里不管是文本还是那些把事情呈现给我们的与谈话伙伴的对话——就是事情本身得以语言表达。”[2](P384)伽达默尔还进一步肯定地说:“诠释学的问题并不是正确地掌握语言的问题,而是对于在语言媒介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当地相互了解的问题。”[2](P388)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联系到伽达默尔与《真理与方法》同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事情的本质和事物的语言》。伽达默尔之所以分析“事情的性质”和“事物的语言”这两个表达式,是因为这两个表达式都指称那种被认为能修正意见与建立真理的基础。在第一个表达式里,人们认为事情的性质可以被用为真理的基础。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黑格尔就是事情性质的最伟大的解释者,因为在真正的哲学思辨里,事情起着告知我们的作用。“面向事情本身”这一现象学名言意指类似的意思——“不符合事实的,充满偏见的和任意的建构和理论”[1](P67)需要加以排除和克服。另一方面,“事物的语言”这一表达式,意指我们应当倾听事物已经说的东西,并且倾听它们的语言将修正错误的意见。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这是海德格尔的立场。
这两句话意指有某种超越“任意的专横”的东西。但伽达默尔在这两个表达式里看到一种重要的哲学区别。他认为,“事情的性质”这一术语的问题是,它保留了主—客二分,即一方面是主体性,意志;另一方面是客体和物自体的二元论[1](P71)。跟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反对这种二分。伽达默尔指出,在古典形而上学里,灵魂与事物的原始一致说(这构成真理的基础)是在神学上加以证明的。因为伽达默尔不接受这种古代的神学证明,他追问是否为这种建立真理的一致说还有另一种基础。他发现这种基础在语言中。在语言中——语言就是事物的语言(die Sprache der Dinge),这种灵魂(主体)与事情(客体)的原始一致是为人类的有限意识而出现的。正是在我们的语言表达式里,事情才被认识,并能与意见对立。伽达默尔结论说:“我认为,和我们的有限性相适合的那种一致性经验不能依靠反抗其他意谓并要求注意的事情的本性,它只能依靠像事物自身表达出来那样被听从的事物的语言,形而上学曾把这种一致性说成被造物互相之间的原始符合,尤其是被创造的灵魂与被创造的事物的符合。”[1](P76)
因此,在语言里所表达的事物(就其广泛的意义)就是《真理与方法》里被称之为事情本身的东西。事情本身是构造宇宙并为人来到存在(当它们进入语言)的基本实在。事情本身的本体论状态的讨论构成《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不是事情的本性或本质,而是事情的语言,才能被要求去修正意见。正是这一点,伽达默尔一开始就引用了施莱尔马赫的话:“诠释学的一切前提不过只是语言”[2](P387),最后他还明确地说:“这种关于事情本身的行动的说法,关于意义进入语言表达的说法,指明了一种普遍的—本体论的结构,亦即指明了理解所能一般注意的一切东西的基本状况。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Sein,das verstaenden werden kann,ist Sprache)”[2](P478)。
不过,“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一伽达默尔中心论点表现了这样一个解释问题:究竟是在其完满性中的事情本身,还仅是事情本身的某个方面,或表现自身于语言的表述中。一方面,伽达默尔写到,好像事情本身来到语言表达(Zur-Sprache-Kommen)是一个完全的表述,例如我们读到,没有第二个存在被创造在自我表现的思辨事件中,伽达默尔说:“来到语言表达并不意味着获得第二种存在。某物表现自身为的东西都属于其自身的存在。因此,在所有这些作为语言的东西中所涉及的是它的思辨统一性:一种存在于自身之中的区别,存在和表现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恰好又不应当是区别。”[2](P479)但另一方面,在语言作为语言观(Sprachansicht)的讨论中,伽达默尔曾认为,在语言表达中仅只有事情本身的某个特殊的Ansicht才得到表现,伽达默尔说:“对传承物的每一次占有或领会,都是历史地相异的占有或领会——这并不是说,一切占有或领会只不过是对它歪曲的把握;相反,一切占有或领会都是事情本身某一‘方面’的经验。”[2](P476—477)
注释:
①精神科学的循环结构指精神科学在他物中重新认识自身的普遍本质,伽达默尔说:“在异已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已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本质运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身的返回”(《真理与方法》,第1卷,1986年德文版,第19-20页)。精神在于运动,首先是它离开它的家园到陌生的世界中去,如果运动是完全的,精神在他物中找到自己的家,使自己重新返回到自己,因为陌生的世界不仅是新家,而且也是它自己的真实的家。正是由于精神的这种普遍本质,使研讨精神活动的精神科学总是离开一切熟悉的东西而到陌生的东西中生活,而正是在这种自身异化过程中,我们才重新发现我们自身。因此,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是一直在外漂泊,回不到自己的家,那么精神科学的独特性质就犹如圣经所描述的故事一样,它是浪子回头,重返家园。这是一种通过外出而重新回到自己家园的旅行者感觉,它说明精神科学具有一种普遍的循环结构。
标签:前理解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 循环语句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马赫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