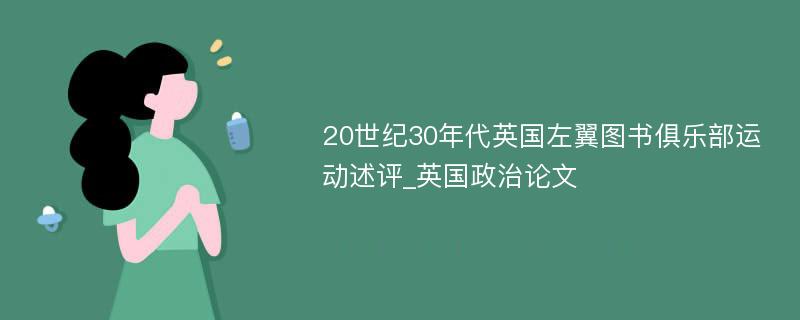
30年代英国左翼读书俱乐部运动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述评论文,英国论文,俱乐部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翼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以下简称俱乐部)是本世纪30年代下半期英国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组织,其宗旨是唤起公众对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切,如法西斯的本质及战争危险,以及用社会主义方法疗救英国社会的弊端,并倡议在英国组成人民阵线,在国际上与法、苏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在俱乐部的全盛时期, 它拥有会员57,000人,学习小组1,500个(包括海外英国人社群)〔1〕,从1936年到1939年,共出版150种书籍(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反映中国革命的名作《西行漫记》和《中国在反抗》都是由这个俱乐部首次出版的)。俱乐部的活动还包括:召集会员或群众大会(规模有时在万人以上)宣讲时事和政治问题;散发传单;举办各种文化和学术活动进一步宣传俱乐部的宗旨,用舆论和物质支援帮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以及组织成员赴苏联考察等等。
实际上,这个俱乐部活动的性质和规模已远非其名称所能体现。30年代的西欧在经济危机和法西斯威胁的笼罩下风云变幻,但同时左翼思潮和力量也十分活跃。在这“红色的10年”中,一些国家的左派建立了政治联盟,而英国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于是“左翼读书俱乐部”的产生和发展便成为英国左派力量高涨的最突出的标志,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它“孕育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运动”〔2〕, 成为“在英国为建立人民阵线而奋斗的最大最活跃的组织”〔3〕。 本文拟就俱乐部的产生、发展、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及其社会影响、历史地位等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俱乐部的建立和发展
要介绍俱乐部的缘起,首先必须介绍其创始人和主持者维克多·戈伦茨(Victor Gollancz,1893—1967)。戈伦茨出身于犹太人家庭,青年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和同时代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戈伦茨对于群众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有特殊的热情,在其自传中他认为在一个动荡的充满歧见的时代,群众的政治教育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生死攸关的。〔4〕这个基本信念贯穿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一次大战时他与人合办了一份杂志:“公立学校眼中的世界”,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被战争部下令停办。1918年他出版了《公立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和《学校与世界》阐述在学校中开展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为充分实现其志向,他20年代投身出版业,并于1927年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维克多·戈伦茨出版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直到70年代,仍是英国有影响的出版商之一)。戈伦茨始终不懈地探索以低价推出政论和学术书籍以达到教育大众的目的的途径。他曾经出版过一本由各领域名人合撰的《现代知识大纲》,共1000页,竟然销出7.5万册,售价从8先令6便士降到6先令,堪称当时出版界的奇迹。
进入30年代中期,戈伦茨教育和启蒙群众的使命感在新形势下变得更加强烈。当时的英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国际挑战,但相当一部分公众中却弥漫着消极自保的苟且心理,所谓“安定、安全第一和绥靖”(tranquilty,safty first and appeasement)流行一时, 在实践中它们意味着消极地认可社会弊端并不惜代价地维持和平。戈伦茨回顾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说:“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答案是:你可以去帮助启蒙群众,你可以让他们知道,如果资本主义存在下去,这种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的结果将是战争”。〔5 〕他断言:“我们的拯救取决于群众的政治教育。”面对当时多数出版商抵制左派书籍的情况,戈伦茨决定由自己的公司单独承担起出版左翼书籍的使命。为了让这些书籍所代表的政治教育能为广泛的公众所接受,他坚持低订价(平均2.5 先令),但同时又必须考虑适当的赢利,于是他想出了组织读书俱乐部的主意:一方面,只有会员才能享受低价书的优惠,另一方面,作为会员又必须承担购买这些书籍的义务。戈伦茨认为只要会员人数达到2,500 人这个计划便是可行的。为使俱乐部具有一定的声望,戈伦茨决定邀约几位学术权威兼社会活动家组成评委会,每月请特定的作者撰写一部书稿(称“每月一书”)。
戈伦茨请了拉斯基和斯特雷奇作为自己的合作人。哈罗德·拉斯基是英国工党主要理论家,英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30年代的一些重要活动正是在“左翼读书俱乐部”这个舞台上展开的。他为俱乐部写了一本《信念、理性、文明》以及大量的评论文章。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也是工党活动家,20年代曾任议员, 大危机中一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解释从而成为工党的左翼,与英共关系密切,曾定期为英共“工人日报”写专栏。他精力充沛,为俱乐部写过几本书及大量的评论。他们与戈伦茨都有私交(拉斯基还是戈伦茨牛津大学的同窗),在主要现实问题上意见相合。他们的声望和活动能力无疑对俱乐部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1936年5月,俱乐部宣布成立。出乎戈伦茨的意料,当即便有5,000人加入,到年底会员人数便达到20,000人,1937年3月达到39,400人,1939年最高峰时达57,000人。至于会员以外的读者有人估计至少在50万以上。〔6 〕会员的社会结构涵盖了各个党派(工党、共产党、保守党、自由党)和各个阶层。例如,在伦敦的工业区之一哈克涅(Hackney )有一个俱乐部的学习小组,其成员组成是:6个工人、5个家庭妇女,2个办公室文员,2个银行职员、1个铁路扳道工、1个经理和1 个化学工程师。估计在其它地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比例要高一些。〔7〕
不但俱乐部成员的扩展远超出戈伦茨等的预料,更重要的是随着会员政治热情的高涨,俱乐部的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也远超出原先的规划,逐步演变成一场群众性的宣传和教育为主的左翼政治运动。
在出版方面,除原来的“每月一书”,针对越来越多样化的阅读要求和变化的政治形势,俱乐部又推出了以下几种(每月出版其中的部分):附加类、增补类、主题讨论类、教育类和经典重印类,这样每月出版的书籍平均在4种左右。拿1937年5月为例,当月出版了6种书, 除《苏维埃民主》为“每月一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督教与社会革命》、《公民面对战争》、《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个宗教代表团西班牙之行的报告》(反映西班牙内战)等都属于新增的种类。此外,俱乐部的通讯刊物“左翼新闻”(半月刊)成为出版方面的另一重要阵地,它除了书评以外,增加了社论、专栏、以及时事评论等。
俱乐部的组织形式中,地区和基层学习小组是其基干部份。1936年5 月俱乐部出版了第一本书以后,立即有会员提出就近组织学习和讨论小组,6月成立了第一个,到年底以每月平均50组的速度增加。 小组成员从10人以下到500人不等,视其地处偏僻村镇还是繁华都市而定。 在伦敦,每个邮政小区(postal disrict)都起码有一个。〔 8〕俱乐部小组有的设在成员家中,有的租借咖啡馆或左翼书店,在条件最充分的22个城镇中甚至有自己的房产。
俱乐部的影响扩展到了海外。到1938年,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新西兰、加拿大、挪威、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锡兰和中国的英国人社群中都有了小组,成员超过6000人。在印度的小组与国大党关系友善,尼赫鲁曾致电俱乐部的年度大会表示祝贺。印度的英印政府将俱乐部的书籍和“左翼新闻”列为违禁品严加查缉。此外美国麻州的剑桥市也有一小组。
随着学习小组普遍建立,各地区进一步组织了地区联合会,俱乐部总部也设置了一个“小组部”(Group Department),戈伦茨雇用了专职部长和秘书协调和指导各地区的活动。
除了学习小组,俱乐部还有多种活动形式。影响较大的有年度大会,通常在伦敦几个最大的戏院如阿尔伯特厅、帝国厅举行,参加者在万人以上。俱乐部办起了夜校、周末学校和夏季学校,即向文化程度不高的成员进行理论启蒙,又组织知名人士作深度研讨。俱乐部拥有众多的艺术界会员,办起了自己的戏剧协会,拥有250个分支, 指导各地开展左翼戏剧活动。此外俱乐部还有2个电影放映队, 一个专门放映反映俄国革命和西班牙内战的影片,另一个则放映反映英国国内社会问题的纪录片。
戈伦茨不但是出色的宣传家和组织家,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深知如何既激发会员的政治热情和参预意识,又使俱乐部和出版公司保持赢利。俱乐部的财政开支是十分可观的,戈伦茨和拉斯基、斯特雷奇之间经济上实际是雇佣关系,每年要向他们支付数百镑的佣金。此外俱乐部还有一批雇员。至于各类活动和稿费的开支更是庞大。所有这些都来自购书款、学费和一些活动的入场费。例如,一本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影片“西班牙的土地”在剑桥区放映了一周就为俱乐部筹得了1,000镑。 这种种可靠的财政来源有力地保障了俱乐部的发展。
俱乐部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虽然英国深受绥靖主义和保守思想的影响,但并不等于公众对于世界事务和国内形势漠不关心,特别在都市和受过相当教育的阶层之中。正如斯特雷奇在解释为何俱乐部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时所说:相当一部分公众“渴望了解1936年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正是出于对公众需求这种了解,使得戈伦茨等有把握去发起这样一个俱乐部。另一方面,英国的主要传媒被绥靖气氛所笼罩,不能提供给公众所需要的信息和舆论;英国工党虽然拥有众多支持者,但受领导层中的主流派(拉斯基和斯特雷奇不属于这一派)反对搞人民阵线(工党的担心是与自由党结盟会影响工党的社会主义纲领,与英共联合又会导致工党基层被控制或渗透),因此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缺乏明确有力的对策;而英共的主张虽与俱乐部的宗旨十分接近,但其成员和影响均十分有限(英共是西欧大国中最小的共产党,其声誉还受到20年代“季诺维也夫信件”事件的打击,其发展远逊于法共、意共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下俱乐部作为一个跨党派的左翼政治宣传组织或论坛,无疑迎合了广泛的社会需要。同时,俱乐部只以宣传和教育为目的,不承担任何直接政治行动,也不属于任何党派,这也免除了很多会员的顾虑。
二、俱乐部的主要活动
俱乐部的活动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是唤起英国公众的反法西斯和用积极措施防止战争的意识,在国内形成有利于人民阵线建立的气氛,在国际上则呼吁建立英法苏集体安全体系。俱乐部建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法共总书记莫里斯的《今日法国与人民阵线》,书中认为德法两国之所以在法西斯势力进攻下出现不同的结果,其原因便在于有没有一个广泛的以左派力量为主导的人民阵线。接下来数月中接连出版了《马前卒希特勒》、《世界政治1918—1936》及《在法西斯的斧钺下》等书,揭露法西斯统治的实质,意在澄清西方很多人的认为法西斯统治恢复了秩序、克服了危机、保证了就业的片面认识。其中英共领导人杜特(Palme Dutt)的《世界政治1918—1936》一书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法西斯产生的必然性,并提出只有英法苏结盟才能防御和遏阻法西斯势力的扩张。随着形势的发展,俱乐部多次大声疾呼制止绥靖政策,例如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俱乐部在伦敦女王厅(Queen's Hall)举行了两次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呼吁“制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提醒公众“和平取决于你的行动。”为扩大影响,俱乐部采用了散发传单的方法,如1938年9 月的一份反对希特勒并吞捷克的传单达200万份, 两个月后的一份题为“严重危险”的传单达800万份,〔9〕戈伦茨同时还写了《张伯伦先生在拯救和平吗?》的小册子广为散发。1939年4 月俱乐部在伦敦帝国大厅举行万人集会为建立集体安全再次呼吁并散发了最后一期传单。
俱乐部把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视为用实际行动遏阻法西斯并进一步教育英国公众的机会。他们出版了《叛乱下的西班牙》、《纳粹在西班牙的阴谋》、《保卫马德里》、《西班牙的内战》等书,最有影响的是匈裔英共成员阿瑟·库斯勒(后因在《正午的黑暗》一书中批判苏联的大清洗而在国际上颇知名)的《西班牙的证明》一书,俱乐部还为他按排了巡回演讲。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俱乐部发起了援助西班牙的活动,如发运食物,募捐购买救护车,领养战乱中无家可归的巴斯克儿童,为“国际纵队”缝织衣物等等。
第二是广泛反映英国社会的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和贫富分化的根源,进而展开社会主义宣传。
俱乐部出版了大量书籍揭露英国社会的现实,如《被谋杀的城市》反映在经济危机下一些造船和纺织业中心衰落并造成严重失业和贫困的后果;《贫穷与公共健康》出自公共卫生专家之手,它以翔实的数据揭示了贫困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联系;《童工市场》暴露了仍然存在的童工现象。此外《不列颠的状况》、《英国的农业政策》、《我们的街道》、《英国的正义》等从更广泛的角度反映和分析了社会问题。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成名作《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也是由俱乐部在1937年出版的,它对当时工人生活的描绘被认为堪与狄更斯和左拉的作品相提并论。
除出版书籍外,俱乐部还建立了专门的“贫困地区小组”去调查存在已久但在危机下更形突出的所谓“贫困地区”(the distressedareas)的问题。他们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作家庭收入调查, 其结果是用英国医学协会所制定的标准来衡量,有1/3的工人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10〕
在揭露现实的基础上,俱乐部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或是在“左翼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普及教育。俱乐部出版了《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和《为什么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等书,另一方面则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手册》等。斯特雷奇在这方面尤其活跃,他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以及著作《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为什么你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甚至被有人称为俱乐部的非正式纲领。
一些左翼科学家,如中国学术界熟悉的贝尔纳(J.D.Bernal.《科学的社会功能》的作者)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积极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他们认为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利润而偏离了为人类服务的根本目的。此外,剑桥大学的科学家还在俱乐部之下组织了一个“剑桥科学家反战小组”,积极参加反战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
第三,与以上两点相联系,俱乐部把介绍和赞扬苏联作为重要内容。1936年至1939年,俱乐部出版了15种有关苏联的书籍,影响较大的如韦伯夫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苏维埃的民主》(作者派特·斯隆在苏联生活过5年,此书我国建国初即有中译本)、 《俄国革命简史》、《改造人:苏联的教育制度》、《苏联妇女的处境》以及《苏联医疗事业的社会化》等。此外,“左翼新闻”有专栏介绍苏联,一度还请苏联大使麦斯基撰文。俱乐部办有俄语进修学校,定期放映苏联电影,等等。另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较有声望的人士访苏,戈伦茨本人就于1937年访问过苏联,这项活动直到1938年底由于国际形势紧张苏方取消签证申请方告结束。
毋庸讳言,在俱乐部对苏联的宣传中存在着片面性甚至一边倒的情况。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大清洗的态度上。斯特雷奇曾在“左翼新闻”1938年7 月号上撰文说:“人类的全部未来取决于这些人(指审判对象)的拘押和判决”。面对很多人对罪证的可靠性和审判的公正性的怀疑,俱乐部出版了德国著名左翼作家费希特万格(Lion Feuchtuwang-er )的《莫斯科1937》,这是作者赴苏旁听审判后写就的,认为整个审判是真实可信和公正的,此书1937年7 月由戈伦茨出版公司出版后,苏联方面立即译成俄文在国内发行。这样的选题清楚地表明了俱乐部主持人的态度。此外,戈伦茨还退回了奥威尔以亲身经历披露苏联和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奉行宗派主义和迫害异已的政策的《向卡塔隆尼亚致敬》的书稿,甚至没有给评委会中态度较为客观的拉斯基看一下,引起了奥威尔极大的不满〔11〕(奥威尔后因《动物庄园》和《1984年》两书被西方认为是反斯大林主义的代表作家)。当然,这并非表明戈伦茨等人对苏联现状的毫无保留的认同,只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如罗曼·罗兰所说,左翼人士把反法西斯同支持苏联视为一体,因此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压制了对苏联的怀疑和不满。这种情况直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才有了根本改变。
三、俱乐部与共产党和工党的关系
30年代左翼阵营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共识和联合,也有矛盾和相互利用,还掺杂着历史恩怨和旧帐。俱乐部成立时,戈伦茨和拉斯基、斯特雷奇商定:俱乐部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宣传教育组织,既不是政党,也不倚靠任何政党。但作为一个兼容各党派成员的组织,俱乐部不可避免地会卷入政治纷争之中。以下分别分析俱乐部与英共和工党的关系。
毫无疑问,俱乐部与共产党人在政治倾向上的相近是有目共睹的,而英共领导成员在俱乐部各项活动(如出书、演说)中的活跃也是一目了然的,因此甚至有论者说:“在多数人心中俱乐部与共产党根本无法区别”。〔12〕但这种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组织背景则是另一个问题。一方面,很多人视俱乐部为共产党组织所控制的宣传机器,其证据是俱乐部出的书中1/3是由共产党人写的,剩下的也是由亲共的三人委员会选出的。〔13〕英工党甚至说苏联通过英共资助了俱乐部。〔14〕此外也有人称英共是利用俱乐部为自己招慕成员,例如1935年英共只有党员6,500人,1938年便达16,000人, 很多俱乐部的小组被英共基层支部所控制,他们不讨论“每月一书”而常常走上街头呼喊党的口号。〔15〕另一方面,戈伦茨的助手,俱乐部“小组部”负责人约翰·刘易斯在其《左翼读书俱乐部》一书中反驳了这种“共产党控制论”。他统计说俱乐部作者中真正属于共产党的远少于1/3;很多亲苏亲共的作者当时只谈了苏联和共产党一致之处而略去了分歧;俱乐部的基层与英共支部并无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俱乐部成员更多的是加入了工党而非共产党,等等。〔16〕
戈伦茨本人曾坦言他一度与英共之间密切的关系“像两根头发丝那样近”。〔17〕英共甚至利用其声望为其机关报“工人日报”作促销广告,将其照片登在促销传单上。但戈伦茨从不承认他的公司和俱乐部与英共之间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而持“共产党控制论”的人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毋宁这样认为:在俱乐部与英共之间,除了政治倾向一致外,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相互支持和利用关系:俱乐部从英共那里得到了最活跃的作者和基层会员,而英共作为一个小党则从积极参预俱乐部的活动中扩大了影响,增加了党员。双方的分歧直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才充分暴露并导致分手(下文将加以分析)。以研究西方左翼知识界而知名的英国学者戴维·科特(David Caute ,在这方面著有《Fellow Travellers 》一书)曾这样描述戈伦茨:他搭上了莫斯科的快车但却知道该在那里下车。〔18〕
同与英共的关系形成对照,俱乐部与工党的关系是紧张甚至对立的。拉斯基与斯特雷奇和当时英共领导层(阿特里,C.R.Attlee和戴尔顿Dalton Hugh 等)意见不合,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俱乐部的。俱乐部建立时工党主席阿特里发了贺电,但分歧很快就产生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工党不同意建立人民阵线;第二,认为俱乐部奉行的是亲英共的路线;第三,工党对大量党员被吸引进俱乐部不满,工党领导人之一贝文甚至说俱乐部的目的就是瓦解工党的基层。〔19〕为缓和关系,俱乐部于1937年7月向工党提出提供两期“左翼新闻”作为专刊, 请工党人士撰稿阐述其路线,并表示增加工党人士书籍的出版。但这个建议被阿特里所拒绝,他反过来提了三个条件:要求在以后各期的“左翼新闻”上增加工党意见的篇幅;在俱乐部总的路线上平衡共产党和工党两种倾向;以及图书评审委员会向工党领导层开放。〔20〕戈伦茨有保留地同意前两条,但拒绝了第三条,这样便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破裂。为和俱乐部对抗,工党组织了自己的“工党读书俱乐部”并声称要开除加入“左翼读书俱乐部”的成员。这场对抗当时称为“读书俱乐部之战。”
俱乐部与工党的矛盾,既有路线、政策的因素,也有工党领导层对俱乐部与英共关系的猜忌和对俱乐部迅速发展导致工党影响削弱的担忧。考虑到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西方左派所奉行的宗派主义和分化利用的策略,工党领导人的这种担心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的来说,俱乐部在工党和英共两种政治力量之间企图保持中间立场,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种有益于团结各党派建立人民阵线的气氛,但其结果是其舆论过多地反映了英共的立场,而工党的声音则相对较弱,同时俱乐部与英共和工党领导层的关系也截然不同。但一方面,这并不表明俱乐部被英共所控制或成为其传声筒,另一方面也并不是说在工党领导层与俱乐部形成对立后,俱乐部与整个工党势成水火。实际上,俱乐部的多数会员仍由工党党员所组成,同时俱乐部也仍然继续出版工党人士的书籍。这主要因为工党并非中央集权化的对普通成员有强大约束力的政党;而俱乐部若无工党成员的参预则更是无法开展活动的。
四、俱乐部的衰落和立场的转变
1939年是俱乐部活动规模的鼎盛时期,但同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却给了俱乐部以意想不到和难以承受的打击。在3 年多的宣传中,“俄国像征所有善良的、理性的、人道的东西,而德国则代表所有邪恶的、非理性和反人道的东西”。〔21〕这种不可调和的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是俱乐部的基本信念,而苏德条约无疑是釜底抽薪。多数俱乐部成员无法理解和接受苏联立场的突然逆转,而俱乐部主持人自己也陷入震惊和困惑之中,根本无法给予会员令人信服的解释,于是大量会员退出俱乐部,很多学习小组自动解体。约翰·刘易斯回顾说:“苏德条约因此而成为俱乐部思想和政策发展中的转折点,它事实上是俱乐部消亡的开始。”〔22〕
一周之后二战的爆发进一步使俱乐部的决策层发生了分裂。与英共立场最接近的斯特雷奇接受了所谓“帝国主义战争”的解释,在“左翼新闻”上撰文号召各参战国的工人对本国政府展开斗争来帮助解放捷克人民”。〔23〕相反,拉斯基在同一期“左翼新闻”上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可能是苏联用它的全部力量支持工党所主张的和平(恢复波兰战争以前的状态)。这种争论在向来只有“一个声音”的俱乐部内掀起了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辩论。大量的会员写信给“左翼新闻”,表示俱乐部失去了一致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戈伦茨在1940年第一期“左翼新闻”上撰文提出任何会员都有权自由选择对战争的态度,并说对有争议的问题俱乐部将不再可能有一致的立场。这无疑宣布俱乐部已变成了一个自由论坛而不再是具有共同目标的宣传组织。
但事实上,这种意见的分歧和多元意味着戈伦茨等人对英共和苏联的立场的逐步转变。应该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苏德条约是外交问题,但实际上却引发了对苏联政策的全面重审,这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20年来面对苏联体制下的高度集权、个人崇拜、用强制手段推行政策和大清洗等现象,西方左派所争论不休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苏联政策的辩护者认为目的决定手段,目的的正义性决定了任何手段的正当性。另一派则认为目的的正义性取决于手段的道德质量,手段并非仅仅是工具,它的效果直接影响了目的的性质。戈伦茨属于后者。尽管他从不接受反苏的托派的文稿并退回过奥威尔批评苏联和第三国际的书稿,但随着有关苏联的信息的累积,他内心深处对苏联的怀疑和不满在滋长。1938年11月他在“左翼新闻”发表了“慕尼墨以后的思考”一文,强调俱乐部的道德原则是决不承认“目的使手段变得正当”的实用主义,这是他第一次间接表达对苏联的另一种态度。而苏德条约的签订在俱乐部内引起的反响是,它“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的为达到目的不惜手段的典型,即使这个目的是为了保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认识下被压抑已久的对苏联国内政策的批判得到了认可。1939年11月,俱乐部出版了《野蛮人就在门口》(Barbarians at the Gates )一书,把苏联与法西斯国家并列为反文明的极权和非道德的“野蛮人”。这是俱乐部的书刊中第一次公开攻击苏联。在讨论此书是否应出版时,戈伦茨和拉斯基赞成,斯特雷奇反对,最后以同意他在“左翼新闻”上发表批评文章为交换条件。
俱乐部决策层由分歧再次走向一致是在西线战事再起之后,斯特雷奇放弃了苏联和第三国际的路线而采取了捍卫西方民主和拥护战争的立场。1940年5月,俱乐部号召成员积极参战, 并提出“俱乐部的任务是打败希特勒”。这表明俱乐部重新确立了某种共同目标。1941年2月, 俱乐部出版了戈伦茨、拉斯基、斯特雷奇和奥威尔四人的专论集《左派的背叛》,书中对苏联和第三国际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进行了总批判。它的出版标志着苏联以及英共在俱乐部影响的终结。〔24〕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分歧和论战下,俱乐部的影响急剧衰减。1939年俱乐部拥有57,000会员,到1941年只剩15,000人。〔25〕很多人虽保留会籍但已不参加活动。由于战争的关系,伦敦的俱乐部机关迁到戈伦茨的乡间别墅,工作人员多数从军或改行。因此,尽管俱乐部在二战期间仍继续存在并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但一般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布之后,俱乐部实际上已丧失了影响力(其正式解散是在1946年)。
五、俱乐部的历史地位
两次大战之间西方左翼力量的发展和30年代的人民阵线运动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要课题。在这一方面,英国左翼读书俱乐部不应受到史学界的忽视。虽然与法国等国的人民阵线运动还不能相比,但考虑到英国并没有严重的法西斯威胁,又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俱乐部能发展到如此规模应视为左派力量的巨大成功。在这一点上,是否建成了人民阵线并不能成为取舍标准,而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来分析。
俱乐部倾全力与绥靖政策及和平主义思潮作斗争,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不懈地揭露法西斯的实质,并展开群众性的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活动,这一切对于唤醒公众意识,打破妥协幻想,驱除苟安心理,从而为参战作好精神准备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倘若没有俱乐部的大声疾呼,英国舆论界很可能便是绥靖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外俱乐部广泛介绍了西班牙内战的情况,使英国公众对未来战争的新特点有了一定的了解,如科学家霍尔顿出版了《怎样在空袭下生存》一书,提倡广修掩蔽部,引起了广泛注意。
俱乐部调查和反映英国社会的现实,号召进行社会改革,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使得改革意识有了一定的传播,为战后工党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说,一些后来广泛的流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词汇就是由俱乐部的出版物所倡导的,如充分就业、医疗的社会化、城镇规划和社会平等等。大批会员战争年代服役或服务于军队和民用企事业,进一步扩展了改革意识。此外,一批作者战后进入内阁,直接规划和推动了改革,如斯特雷奇就曾担任过食品和国防大臣,洛德·爱迪生(前述《英国的农业政策》一书的作者)和艾伦·威尔金森(曾因《被谋杀的城镇》而出名)也进入了内阁。另外,一些作者进入了议会。
俱乐部的出版选题既围绕主要宗旨,又兼顾一些尚在西方公众视野之外的新发展,如中国红军的长征以及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据约翰·刘易斯回忆,斯诺和史沫特莱的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它们不但为俱乐部巩固了已有的会员,而且引来了一批新成员”。斯诺的书出版后,“左翼新闻”在1937年10月和11月连续发表两篇长文介绍中国革命,并请文章的作者在全国作巡回演说。除政治和时事问题外,俱乐部还出版了许多学术和科学著作,如李约瑟和贝尔纳等著名科学家的著作,又如中国学术界所熟悉的《人民的英国史》(A.L.莫尔顿著)等。
此外,俱乐部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戈伦茨应该在英国现代史和欧洲左翼运动史上占有相应的位置。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他早期出版的论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中他主张由工人控制各行业,再由各行业的联盟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但他所留下的影响并非来自他的思想或观点。他对群众政治教育的信念和热情,他所独创的多种多样吸引和组织群众参预政治活动的方式,他的出版商和群众运动组织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的成功结合,使得他所领导的俱乐部成为一个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宣传组织和群众运动。在欧洲左翼运动史上这是少见的既独立于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又能取得巨大影响和成功的例子。虽然有很多客观因素造就了俱乐部,但正如约翰·刘易斯所说:“如果没有他(指戈伦茨,本文作者注),俱乐部的存在将是不可思议的。”〔26〕
注释:
〔1〕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 John
Lewis,The Left Book Club.An Historical Record),维克多·戈伦茨出版公司,伦敦,1970年版,第12页。
〔2 〕克拉涅克和谢尔曼:《哈罗德·拉斯基:作为左派的一生》(Isaac Kramnick and Barry Sheerman,Harold Laski :A Life on the left)企鹅出版社,纽约1993年版,第365页。
〔3〕约翰·考拉汉:《1884年以来的英国社会主义》(John Callaghn, Socialism in Britain Since 1884), Basil Balkwell Ltd.
〔4〕维克多·戈伦茨:《自传》(Victor Gollancz,《More for Timothy (Biography)》),维克多·戈伦茨出版公司,伦敦1953年版,第316页。
〔5〕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记录》( John lewis,The,left Book Cluh,An Historical Record)维克多· 戈伦茨出版公司,伦敦1970年版,第20页。
〔6 〕乔治·摩塞等主编:《两次大战之间的左翼知识分子》 ( George Mosse and Walter Laqueur,Edited.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1919—1939),Harper & Row ,纽约,1966年版,第67页。
〔7〕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28页。
〔8〕乔治·摩塞等主编:《两次大战之间的左翼知识分子》,第73页。
〔9〕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88页。
〔10〕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59页。
〔11〕克拉涅克和谢尔曼:《哈罗德·拉斯基:作为左派的一生》,第368页。
〔12 〕乔治·摩塞等主编:《两次大战之间的左翼知识分子》第78页。
〔13〕约翰·考拉汉:《1886年以来的英国社会主义》第134页。
〔14〕克拉克和谢尔曼:《哈罗德·拉斯基:作为左派的一生》,第370页。
〔15〕乔治·摩塞等主编:《两次大战之间的左翼知识分子》,第79页。
〔16〕约翰·刘易斯:《左派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23—24页。
〔17〕维克多·戈伦茨:《自传》第357页。
〔18 〕戴维·科特:《同路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朋友》(Daw-id Caute ,The Fellow—Travellers,Intellectual Friends of Communism),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1988年版,第172页。
〔19〕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94页。
〔20〕克拉涅克和谢尔曼:《哈罗德·拉斯基:作为左派的一生》第370页。
〔21 〕乔治·摩塞等主编:《两次大战之间的左翼知识分子》等81页。
〔22〕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115 页。
〔23〕《左翼新闻》(Left News,Pubhlished by the left Book Club),1939年12月号。
〔24〕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120 页。
〔25〕同上,第132页。
〔26〕约翰·刘易斯:《左翼读书俱乐部:历史的纪录》,第 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