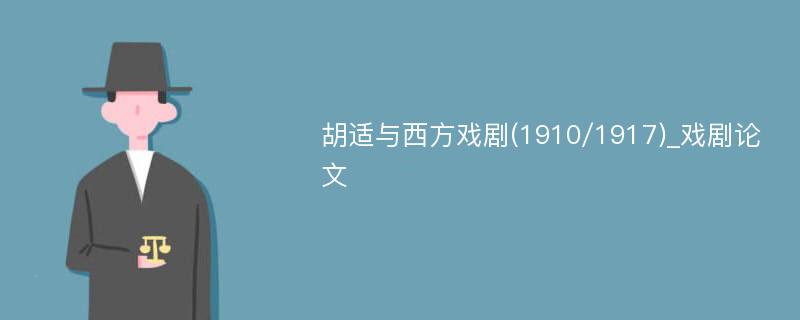
胡适与西方戏剧(1910—191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2)03-0082-08
胡适(1881—1962)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贡献早为学术界所瞩目[2][3],然而,人们 评论他在“五四”时期的戏剧理论批评与译著活动,却每每忽略了他留美期间(1910—1 917)对西方古典和近现代戏剧的选择、汲纳,这就难于对他倡导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作 出富有历史感的描述与客观的评价,也无法全面地揭示20世纪初叶中国话剧前驱对泰西 古典和近现代戏剧的借鉴与接纳。
在清末民初引进域外戏剧的潮流中,胡适堪称是继王国维、齐如山而崛起的又一前驱 。王国维运用西方戏剧美学思想,研治中国戏曲历史;齐如山以欧西戏剧观念与实践为 参照,致力于改良戏曲艺术;胡适则注重西方戏剧名著的解读、观摩,力求为新剧提供 可资借鉴的“范本”。诚如他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 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4]留美期间, 胡适伊始解读、观摩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古典戏剧,后延展到易卜生所创建的近AI写作实 派戏剧,再到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等人的现代派戏剧。这一程序不仅把捉到欧洲戏剧思 潮兴衰嬗变的发展轨迹,也顺应、驱动了中国戏剧借鉴欧美戏剧的历史进程。
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早期话剧以日本新派剧为中介,“间接学习了欧洲浪漫派戏 剧的创作方法”,至“五四”时期又“直接学习了欧洲近代剧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5 ]。早期话剧借鉴的是欧洲浪漫派雨果、萨都、斯克里布等人的作品;当时虽广泛上演 莎氏的幕表戏,然其编剧的蓝本,系据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文言译本《沨外奇谭》、《吟边燕语》,“这几种译本,只保留了莎士比亚原著的故事梗概 ,而且又采取了小说的形式,因此很难看出莎士比亚作品的真面目”[6]。上述看法对 于国内剧界而言,允称基本契合史实,然对于旅外的中国留学生及话剧团体来说,却当 别论。1913年刘艺舟流亡日本,次年创立了光黄新剧同志社,并联络朱旭东主持的开明 社赴日,打出“中华木铎新剧”的旗号,效法日本新剧,在大阪、东京成功地创作、演 出《西太后》、译剧《复活》等,率先进行了西方近AI写作实派戏剧的艺术实践[7]。而 辛亥前后留学欧美的王文显、胡适、张彭春、宋春舫等人,也先后涉足欧美戏剧艺术研 究。其时欧美小剧场运动蓬勃兴起,他们不但阅读了泰西古典和近现代戏剧的大量作品 ,而且观赏了一批剧目的舞台演出,并从事剧评或创作实践,为其日后引进西方戏剧的 理论批评、译介教育活动创造了条件。然遗憾的是,从现存史料看,除了胡适17卷《留 学日记》[8]外,人们已无从具体了解其他话剧前驱的海外戏剧活动。
1910年胡适赴美国纽约康乃尔大学农学院留学,其所修英文、德文系以西方文学名著 为教材,课余又耽爱中外文学、哲学著作,至1912年秋转入该校文学院深造。1915年秋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1910年留学日记因已散佚,无从稽考。自1911年起他广泛 接触欧美古今文学、戏剧名著,同时观摩校内外的戏剧演出,撰写剧评,读剧日记、札 记。留学初期(1910-1912),胡适侧重研治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戏剧。据留学 日记卷1-2,他始读莎氏生平传记史料,后陆续解读《亨利四世》、《罗密欧与朱丽叶 》、《哈姆莱特》、《无事生非》、《李尔王》、《暴风雨》、《麦克白》等剧,至19 11年8月下旬,“连日读萧士璧戏剧,日尽一种”。与此同时,他还读了古希腊索福克 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英国J·德莱顿的《一切为了爱》等悲剧,德国莱辛的《明娜 ·封·巴尔赫姆》、俄国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喜剧,观赏了《罗密欧与朱丽叶》、 《哈姆莱特》、《无事生非》、《钦差大臣》等剧的演出,并撰写了《‘Romeo and Ju liet’一剧之时间的分析》、关于《哈姆莱特》的两篇剧论。留学后期(1913-1917), 尽管他将研治重点移向易卜生以降的欧美近现代戏剧,但仍耽读、观摩莎氏戏剧,又接 触了法国高乃依、莫里哀、拉辛的古典主义戏剧,观看了英美名演员霍·罗伯逊(F.Rob ertson)主演的《哈姆莱特》等,并撰写了《伊里沙白朝戏台上情形》、《莎士比亚剧 本中妇女之地位》等札记。胡适将借鉴视域自19世纪的浪漫派戏剧上溯到莎氏浪漫剧及 其他古典戏剧,从一个侧面透露了他企盼阻遏早期话剧间接学习欧洲浪漫派戏剧,却跌 落为“佳制剧的方法”、“闹剧的形式”[9],同时也是一种提升,可让国人窥见西方 浪漫主义戏剧的原生貌及其变迁,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从现存史料看,胡适堪称 中国莎学史上全面地解读莎氏英文原著,并从戏剧本体层面评论莎氏戏剧的第一人。国 人对莎剧的观赏、阅读、评论不自胡适始。早在1879年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纪泽, 遂应邀观摩英国名演员亨利·厄尔文于伦敦兰心剧院主演的《哈姆莱特》[10][11];而 辜鸿铭乃最早阅读莎氏英文原著的中国人,然而他并不从事莎剧评论[12]。嗣后,严复 、梁启超、汪笑侬、鲁迅等人在其译著、诗文中曾给予莎氏及其戏剧很高的评价[1], 然上述论者大凡并未阅读莎氏英文原著,且仅从文学、文化或名学等视角来评骘莎氏, 却未能深入莎氏戏剧的本体层面。即使后出的孙毓修的《莎士比之戏曲》(1913)[13]一 文,也粘滞于莎氏生平与创作分期的译介,其评述莎剧艺术特色非独简略,且未逾越文 学之阈域。鉴此,胡适从群体性的综合艺术的角度评价莎剧的本文及其舞台演出,在史 上遂有开创性的意义。
胡适1912年所撰有关《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等剧论已无从寻觅,然从留 学日记中仍可窥其莎剧评论之丰采,尤其是1912年9月观摩名演员Southern(萨瑟恩)和M arlowe(马洛葳)公演《哈姆莱特》所写的剧评,可以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篇莎剧名著 及其演出评论。它比茅盾的《莎士比亚的<哈姆勒特>》(1935)早了20余年,篇幅长一倍 多,内容也更为丰赡精湛。胡适释读、观赏莎氏其他剧目时,也发表了不少精辟独到的 见解,并比照莎氏与萨克雷、狄更斯、易卜生、托尔斯泰诸作家笔下人物之异同。其莎 剧评论的主要观点、内容有三个方面。
其一,莎剧的人物塑造。胡适辨识古今人物描写之异趋,指明莎剧擅长刻画人物独一 无二、不可移易的鲜明个性。盖欧西古AI写作生重类型,如古希腊泰奥弗拉斯忒斯之《谄 人》,“其所写可施诸天下之谄人而皆合,以其题乃谄人之类,而非此类中之某某谄人 也”。文艺复兴后则不然,“其所写乃是个人,非复统类。如莎士比亚之Hamlet(汉姆 勒特),如易卜生之Nora(娜拉),如Thackeray(萨克雷)之Rebecca Sharp(丽贝长)。天 下古今仅有此—Hamlet,—Nora,—Rebecca Sharp,其所状写,不可移易也。”莎氏 写人不独摒弃了“举一恶德或一善行”[4]的类型化,也超离了“褒之欲超之九天,贬 之欲坠诸深渊”的绝对化。其剧中人物类似后起的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皆亦善亦恶, 可褒可贬……汉姆勒特王子、李耳王、倭色罗诸人物,皆非完人”[4]。莎氏所以能写 出人物性格、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推究其因,一方面在于准确地把握人物独特而丰 满的性格特征,同时善于设计与人物性格相对立的规定情境。以莎氏“最有名”的舞台 形象哈姆莱特言之,莎氏紧紧擒住人物“寡断”的核心性格,为之建构了最佳的戏剧情 境:其“以仁人之心,而处天下最逆最惨最酷之境;以忠厚长者,而使之报不共戴天之 仇:其仇又即其母与叔也,其事又极暗昧无据。荒郊鬼语,谁则信之?不知者方以为觊 觎王位耳。”王子“寡断”的主导性格在此规定情境中获得了淋漓尽致、浓墨重彩的表 现。例如,“当其荒郊寒夜,骤闻鬼语,热血都沸,其意气直可专刃其仇而碎砾之。及 明日而理胜其气:一则曰鬼语果可信耶?再则曰此人果吾仇耶?三则曰吾乃忍杀人耶?至 于三思,则意气都尽矣……”[4]这一论述与周作人1918年对哈姆莱特的“人性之弱点 ”[14]、茅盾1930年对哈姆莱特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的剖析[15]堪相媲美。
胡适以为莎氏善于运用“独语”(Soliloquy,通译独白),剖露人物在规定情境中复杂 的心理情感。剧中“王子之人格全在独语时见之”。从写实主义的艺术规范看,“独语 为剧中大忌,可偶用而不可常用”,然《哈》剧独多用此法,这与其浪漫剧的剧情、体 式有关,盖“以事异人殊,其事为不可告人之事,其人为咄咄书空之人,故不妨多作指 天画地之语”。胡适还以莎剧的独语对照旧剧的自白、新剧的演说,指明莎剧独语“声 容都周到”,而旧剧“自白姓名籍贯,生平职业,最为陋套,以其失真也”。由是进而 认为“吾国之唱剧亦最无理。即如《空城计》,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4]这 其实是以西方的模仿写实为标尺,来衡量戏曲的虚拟写意。“五四”时期胡适主张废除 戏曲,以白话剧代之,其偏激主张于此可见端倪。胡适还明示莎剧人物构架中必有丑角 ,其戏谓之插诨(Comical part)。如《哈》剧写潘老丈(即波洛涅斯)“蠢态可掬”,堪 谓“神来之笔”,其形象从侧面烘托了王子的愤世嫉俗与佯狂的畸形心态。莎氏悲剧设 计丑角及其插诨,有其多维度的审美功能,胡适虽未一一论及,然指出创造丑角“要在 俗不伤雅”[4],可称透辟之见。
其二,演员的表演艺术。胡适十分注重演艺,以为优秀的演员必须善于凭借动作与表 情、对话与独语,惟妙惟肖地展露人物的性情、人格及复杂心理。1911年3月,他在兰 息院观看悲剧《White Sister》,为演员表演的“神情之妙”所折服,从中窥见了“西 国戏剧之进化”[4]。随着舞台艺术观摩的深入,他对演员表演技艺的评判既细密、深 致,又饶有分寸。1912年秋他称赞萨瑟恩主演哈姆莱特的技艺“大佳”,胜于去岁所饰 罗密欧一角。第一幕王子独语时形体动作和脸部神情“佳绝”;其串王子对潘老丈“种 种藐视之态,尤为毕肖”。“盖王子极鄙薄潘老,而潘老偏不知趣,故王子每戏弄之, 冷嘲热讽,以佯狂出之,皆恰如其身分。”马洛葳饰奥菲利亚亦相当成功,比起她所饰 朱丽叶毫不逊色。第四幕奥菲利娅发狂一场,“声容凄惋,哀动四座。其狂歌数章,声 细仅可辨,然乃益哀。若放声高歌,则未免不近人情矣”。至第五幕奥氏散花给王后及 其兄雷欧提斯,“尤(令人)伤心”。显然,非熟谙人物及其表演术,断难作此等细致入 微的评析。涉及其他配角,胡适以为“亦多佳者”。除潘老外,串篡王克劳狄斯者,“ 奸状如绘,亦殊不易得”。不过,饰雷欧提斯者“乃不甚出色”,串霍拉旭者“亦不大 佳”[4]。
第三,结构艺术与舞台场景。胡适评论莎剧的舞台设计与布局,倾重运用横向与纵向 比较。1913年7月他特地翻译《亨利五世》的“开场白”,率先向国人绍介伊利莎白时 代的戏台。它只用“几块破板搭成”,却能“演出如此轰烈的事件”;好比“一个小小 的圆圈,在数字的末尾,就可以变成个一百万”。它凭借这点渺小的作用,来激发观众 无穷的想象力:“假设在这圈的墙壁内有两个强大的王国,国境紧接一片高地,却叫一 道海峡的波涛从中一隔两断。……一个人,把他分身为一千个,组成了一支幻想的大军 。我们提到马儿,眼前就仿佛万马奔腾,卷起漫天尘土……凭着想象力,搬东移西,跨 越时空,叫多少年代的事件都挤在一个时辰里。”胡适敏锐地领悟这样的戏台,“盖与 我国旧日戏台相似”[4]。显然,他尚未能辨识莎剧采用开放式结构,其舞台时空仍具 有相对集中的审美特性,它与中国戏曲的时空自由、流动,事件有头有尾,其各个侧面 皆可搬上舞台,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胡适以为戏剧的结构与场景设计,必须顾及剧场性。他说,“莎氏著书之时,远在17 世纪初,舞台尚未有布景。所谓景者,正如吾国旧剧悬牌为关门,设帐为床而已,故不 妨多其幕景。”[4]至其布局,《罗密欧与朱丽叶》“有楔子(Prologue),颇似吾国传 奇”;而以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遭际为主线,设计了“初遇”、“窥艳”、“晨别”、 “求计”、“长恨”等专节[4],与戏曲点线组合的结构方式亦有类同点。然重要的是 ,胡适对莎剧原著与现代演出本的结构比较,表明他十分重视剧场性与尊重当代观众的 审美情趣。依他看来,现代舞台上演莎剧,由于剧场及当今观众对舞台布景的要求不同 于伊利莎白时期,导演势必对原著诸多场景加以删削、拼接、组合。盖今日剧场,“布 景皆须逼真……决不能刻刻换景,则择其可合并者并之,不可并者或仍或去,其所换之 景,皆必不可不换者”。他深入比较《哈》原著与萨瑟恩演出本的结构,既肯定了后者 对原著场景的现代处理,也指出其个别场景之合并与剧情相悖[4],从中透露了他对幕 场划分与场景设计的精心研究。可以说,胡适留学期间对莎剧的解读、观摩与评论,不 仅书写了中国近代莎剧研究最有光彩的一页,也使他跻为中国莎学的奠基者之一。
如果说胡适解读、观赏、评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戏剧,突破了当年新剧奉1 9世纪欧洲浪漫剧、佳构剧为圭臬的畛域,那么他将借鉴视野转向易卜生以降的欧美近 现代戏剧,则为“五四”时期戏剧运动的发展趋势作了策略规划。这一调整、转移,既 受制于他那“有助世道人心”的戏剧观,进化论、个性主义的人生观,也表明了他企图 紧跟迅猛崛起、方兴未艾的欧美近现代戏剧潮流。1915年胡适给《甲寅》编辑部的信函 云:“近50年来,欧洲文学最有势力者,厥唯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 挪威之Ibsen、德之Hauptman、法之Brieux、瑞士之Strindbury、英之Benarolshow及Ga lswortiy、比之Maeterlinck,皆以剧著声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期,需世 界名著为范本。”[16]在欧美近现代戏剧的诸多派别分支中,胡适、宋春舫咸将易卜生 所开创的近AI写作实剧列为首选对象。宋氏发表《近世名戏百种目》、《世界名剧谭》[1 7][18],推崇以易卜生为鼻祖的泰西近现代戏剧,尤其是写实剧;胡适则首推易卜生为 代表的写实剧,尤其是社会问题剧。学术界向来以为胡适只是举荐易氏一人,且偏重思 想家的易卜生,而疏略艺术家的易卜生。其实,胡适的《易卜生主义》(1918)一文独推 易氏及其社会问题剧,乃是他对西方写实派剧作家长期权衡遴选的结果。他在《欧洲几 个‘问题剧’巨子》札记中称:“自伊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 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业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 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肖伯纳氏,在法为白里而氏。”[4]据《留学日记》等,胡 适不仅“读过易卜生所有的戏剧”[19],而且读了霍普特曼、白里欧、肖伯纳、高尔斯 华绥及斯特林堡等人的问题剧,撰写了一系列读剧札记,并着手翻译易卜生的《娜拉》 、《国民公敌》,以为我国过渡期剧界之范本。此外,他还接触了王尔德、泰戈尔等人 的剧作。事实表明,胡适解读、观摩、研治霍普特曼诸人的社会剧,其付出的时间、精 力并不少于易卜生的剧作。他不仅索解社会剧的内容意蕴,也考究其独特的表现艺术, 对热衷于描写中下层劳动者的霍普特曼尤为青睐。
胡适提摄了易卜生始创的社会问题剧的三大特征。一、剧本“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 之问题”[4],揭橥社会的种种弊端祸害。如白里欧的代表作《梅毒》,“以花柳病为 题,写此病之遗毒及社会家庭之影响”,“不独为一家绝嗣灭宗之源,乃足为灭国弱种 之毒”。其题材“最不易措手”,然著者却“以极委婉之笔,曲折达之。全剧无一淫亵 语,而于此病之大害一一写出,令人观之,惊心动魄”。胡适将此剧与易氏的《群鬼》 作比,指出后者虽“亦论此事,惟不如此剧之明白”。盖易氏写剧时,“花柳病学尚未 大明”,其犹以为“流毒仅及其身及其子孙而已”。晚近30年医学大进,白氏此剧“盖 得花柳病学巨子之助力,其言不独根据学理,又切中时势,宜其更动人”[4]。由是不 难窥见社会剧客观地描绘社会问题之显著特征及其与实证哲学之密切关系。社会剧观照 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蕴含的思想亦峻切精警。斯林特堡的社会剧《连环》(The Link) ,“论法律之弊,发人深省”;易氏之《娜拉》一剧“亦切齿法律之弊,以为不近人情 ”,娜拉与克洛司达的一场对话即为显例[4]。霍普特曼“最著之作”《织工》系以184 4年作者故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为题材,胡适将究诘文本内在意蕴与剖析人物动作、冲 突、情境结合起来,不仅概括了此剧演示织工不堪忍受苛刻虐待与非人境况而奋起罢工 的主题,而且提摄了“工人知集群力之可以制资本家死命”的深刻意旨,并将批判锋芒 指向“谁实迫之而使至于此”[4]的社会恶势力。字里行间,盈溢着对资本家为富不仁 的无比愤慨,对织工群众悲惨境况的深切同情。在胡适看来,优秀的写实剧恰是凭借讨 论各种社会问题,揭露了当今西方社会的家庭、婚姻、法律、宗教、道德、习俗等弊病 ,表达了剧作者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
二、描绘了中下层的日常生活,塑造了芸芸众生的特异的舞台形象。胡适以为社会剧 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真实地描绘了特定社会的人生图画,生动逼肖地刻画了各式 各样的人物形象。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虽“意在戒饮酒”,诤谏“德国人嗜酒,流 毒极烈”,然“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Loth and Helen尤有生气 ”[4]。其喜剧《獭皮》不独映现了19世纪末俾斯麦政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社会现 实,也将洗衣妇沃尔夫大妈的机警狡狯,警察局长韦尔哈恩的颟顸糊涂,“穷形尽致” 地描绘出来,其笔法“大似《水浒传》”[4]。胡适还特地援引康乃尔大学散蒲生(M.W.Sampson)所言:读此剧,“虽10年以后,必不能忘剧中贼婆伍媪(即沃尔夫大妈)及巡检 卫而汗(即韦尔哈恩),犹读《汉姆勒特》者之不忘剧中之王子也。”至其《织工》的性 格刻画又别开生面,“不特无有主人乃无一特异之角色”。盖作者“所志不在状人,而 在状一种困苦无告之人群”,致力于塑造织工的集体群像。然散蒲生之论亦不无阶级偏 见,如云织工“皆如无头之蛇,丧家之犬,东冲西突,莫知所屈。”[4]这与胡适的评 价大相径庭。胡适论《织工》等剧人物,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盈溢着人道主义的思想 光芒。他还充分肯定霍氏善于描写“新旧二时代之工人心理”。剧中老织工信天安命, 旦夕祈祷,竟为兵士所击毙。而其子、媳义愤填膺,奋起抗争;他们以为“贫富之不均 ,人实为之,人亦可除之”,最终取得罢工之胜利。“两两对映,耐人寻味”[4]。
三、淡化情节,不求布局严整之趋势。胡适解剖了《织工》等剧的布局,赞同霍普特 曼首创了“不以布局胜”的编剧术。易卜生受斯克里布等人佳构剧的影响,过于讲究情 节结构;霍氏之剧却“无有一定之结构经营,无有坚强之布局,读者但觉一片模糊世界 ,一片糊涂世界”,然“一一逼真,无一毫文人矫揉造作之痕”。胡适敏锐地指出,此 种“不以布局胜”的体式,“近人颇用之,俄国大剧家契诃夫(Tchekoff)尤工此。”[4 ]这些评述不独把捉到西方写实剧结构艺术的衍变轨迹,对当年新剧竞相追逐情节曲折 奇离与传奇性也是一大棒喝!总之,胡适对写实派戏剧的评论与上述“中华木铎新剧” 的演出,将中国话剧借鉴写实剧的历史提前到民元初年,是当年海外华文剧坛的一大景 观。
胡适还评介了爱尔兰的民族戏剧与欧美现代派戏剧。“五四”和20年代,沈雁冰、余 上沅、郭沫若等人十分关注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竞相译介,将它作为建设中国新剧的 楷模[20][21][22][23]。然评介爱尔兰民族戏剧的始作俑者却是胡适。早在1911年10月 ,他就读了辛格的《骑马下海的人》和《峡谷中的阴影》,誉称辛格乃爱尔兰“近代戏 曲巨子”,表现“爱耳兰贫民状况极动人”;其《骑马下海的人》“写海滨一贫家,六 子皆相继死于水,其母老病哀恸,絮语呜咽,令人不忍卒读,真绝作也。”[4]。嗣后 ,又读了W.B.叶芝的神秘主义道德剧《沙漏》、格雷戈里夫人描写民族历史生活的《月 亮上升》及丹山尼(通译邓桑尼)的五部剧作:《山上的诸神》、《金色的毁灭》、《阿 基米尼国王和无名勇士》、《失落的丝帽》等。爱尔兰的民族戏剧虽生成于近代,然与 易卜生派的写实剧迥异其趣,它融写实与浪漫为一体,大凡是世俗讽刺的,或宗教哲理 的,既盈溢着民族精神和地方色彩,又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因素。沈雁冰指出,它是“ 近代文学的反流”,“若以现代而论,怕反是合流呢!”[20]
现代主义戏剧如象征派、表现派也为胡适所酷爱。易卜生的《海妲传》(通译《海达· 高布乐》)等后期象征主义戏剧,为胡适展示了一个不同于社会问题剧的鲜活的审美境 界。胡适称赞“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这个具有恶魔般天性的女人,“其可 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但有过之无不及也。”[4]两年前,他读《麦克白》 “初不见其好处”[4],这时却发现了麦克白夫人、海达·高布乐一类人物所蕴含的邪 恶美。显然,他的戏剧观念正向新的广度、深度掘进。同年,黄远生介绍了泰西“仅以 精神上起伏之物而剧化之”的“静剧”[24],胡适也解读了梅特林克的《阿拉季纳与巴 罗米德》、《入侵者》、《室内》、《丁泰祺之死》等剧,盛赞梅氏乃“比利时文学泰 斗”、“世界大文豪之一”[4]。于此前后,他还探究了斯特林堡的表现派戏剧,指出 他的《梦剧》(通译《一出梦的戏剧》)“全无结构,但以无数梦景连缀成文,极恣肆诙 奇之妙。”[4]堪称擒住了斯氏表现派戏剧运思与布局之特色。显然,正是留学后期对 现代派戏剧的耽迷与择取,促成了胡适“五四”时期在提倡问题剧的同时,弘扬“专以 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象征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 解剖的‘心理戏’”[25]。
胡适对于西方戏剧的解读、观赏与批评,不仅结束了王国维诸人对西方戏剧的隔膜状 态,为国人打开了通向西方古典和近现代戏剧的一扇大门,也体现了他那新的戏剧观念 ,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戏剧理论批评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早在1904年,王国维遂提 出“唯诗歌(并戏剧小说言之)一道,虽藉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然其价值全存于 其能直观与否。”又言“诗歌之所写者,人及其动作而已。”这透露了他对文艺原质的 深入体认,但也表明他对戏剧的本体特征尚欠理知。他没有将戏剧的直观归入“呈于吾 人之耳目”[26]的建筑、雕刻、图画、音乐之列,而是让它厕身“藉概念之助以唤起吾 人之直观”的文学之俦。显然,戏剧尚未被他视为以角色的动作直观地诉诸观众的综合 艺术,而是被等同于戏剧文学。嗣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1912)中,科学地总结 中国戏曲实践,一面界定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同时提出元剧 “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的论断。不过,他对元剧“代言体”的确认并不彻底,以为 元剧“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27]。其实,元剧科白除“自报家门”、念“ 定场诗”、“交代前情等少数形式外,大凡还是代言。相比之下,上述胡适1912年有关 《哈姆莱特》的评论,显露了对戏剧动作性、直观性的深刻悟识。他不仅顾及戏剧是群 体性的综合艺术,从剧本、演员、观众、剧场诸要素给予综合评判,而且强调戏剧文学 的可读性、可演性的双重特性。诚如他说,“凡是丑角之戏,非在台上演出,不能全行 领会,即如掘坟(《哈》)一节,匆匆读过,初不着意,及演出始知为妙文。”他从文本 断言《亨利四世》的著名丑角福斯塔夫“当极佳”,以不得在舞台上观看福斯塔夫一角 的表演为憾[4]。在他看来,剧艺精湛的演员可令原著锦上添花或弥补其不足,如《消 失的光芒》虽非名剧,然经英美当今名演员J.F.罗伯逊主演,“正如仙人指爪所着,瓦 砾都化黄金。”[4]
其次,胡适基于对戏剧本体及其生成机制的自觉体认,总是将动作、冲突、性格、情 境看为一个有机的文本体系。上述有关哈姆莱特的性格论述即为显例。对奥菲利亚的形 象剖析亦从规定情境入手,紧紧擒住人物的独特动作、内外冲突及其一生行为,“始则 婉转将顺老父,中则犹豫不断,不忍背其父之乱命,终则一哀失心,绝命井底”,从而 提摄了奥菲利亚“颇似东方女子”的柔顺凄惋的特异性格。奥菲利亚不同于莎氏笔下“ 皆有须眉巾帼气象”的女性形象,素为西人所不喜,胡适曾特地撰文为之辩护[4]。可 以说,当年能以戏剧本体特征批评西方戏剧者,除胡适外,并世无第二人。
胡适的现代戏剧观念也表现在类型意识方面。上世纪初王国维、蒋智由引进西方的悲 剧、喜剧观念,春柳社输入“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的“新派演艺”[28],由是传统戏 剧观念面临着挑战与解构。不过,王国维虽运用叔本华的悲剧分类学说返观中国戏曲, 却欠缺西方悲剧的审美体验。相比之下,胡适的悲剧视野更为开阔,他对悲剧类型的艺 术体验也更为深入。上自古希腊命运悲剧、文艺复兴的性格悲剧、法国古典主义悲剧、 英国王政复辟期的悲剧,下至浪漫主义悲剧、批判现实主义悲剧、现代主义悲剧,无不 进入胡适的审美场域。虽然他尚未能辨识上述悲剧流派、类型不同的艺术特征,但凡有 评述,大多精警有力,浅显明了。胡适对欧美喜剧的博览并不逊于悲剧,莎士比亚、莫 里哀、莱辛、果戈里、霍普特曼、肖伯纳、王尔德、契诃夫、格雷戈里夫人、邓桑尼乃 至战后美国的喜剧佳作,都成为他解读、观摩之对象。如果说胡适确立现代悲剧观念还 得留待“五四”时期,那么他对新的喜剧观念的开创,民初期间已趋于成形。王国维对 笑的认知一直沉滞于鄙笑。诚然,他认为喜剧的审美对象“非事实”[26],创作主体遂 可超离物我利害之关系,但因他漠视笑的讽谏、巧智、幽默等多维功能,又未能深究客 体之可笑性,其笑的内涵与外延仍显得相当褊狭,喜剧遂沦为滑稽剧。胡适却不然。尽 管他未能分辨谐剧与喜剧之不同,更谈不上区分不同流派、类型的喜剧,但他以中国戏 曲为参照,颠覆了西方的纯喜剧观念,率先提出并探讨莎氏悲剧中的丑角及其插诨。其 次,胡适以为喜剧并非只写些插诨的丑角,它还须塑造具有独特性格、使人难忘的人物 ,如《獭皮》中的沃尔夫大妈、韦尔哈恩。最后,他在喜剧诸审美形式中更为器重讽刺 (Satire),曾褒扬《钦差大臣》描写“俄国官吏现状较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尤为穷形 尽相”[4]。在他看来,“西方所谓‘Satire’者,正如剧中之‘Comedy’,乃是嬉笑 怒骂的文章”[4]。可见,他将喜剧类同于讽刺,这与他日后提倡“用嬉笑怒骂的文章 ,达愤世救世的苦心”的“讽刺戏”[25]是一脉相承的。自王国维、姚华诸人将喜剧混 同于滑稽剧,迨胡适将喜剧等同于讽刺剧,不难窥见国人喜剧观念逐渐向喜剧本体层面 位移的明显轨迹。
收稿日期:2001-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