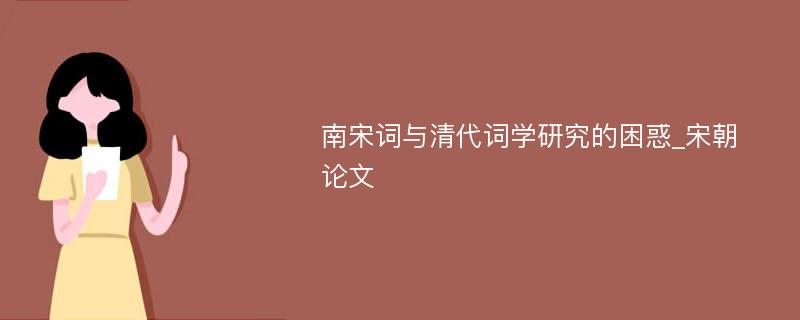
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词论文,南宋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清代的词学研究,是清词繁荣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清词的历史走向,词风的转变,词派的兴潜消长,均与此密切相关。就词史的发展演变而言,清代词坛虽然产生过许多重要词人、重要作品,但其整体成就却没有超过词史兴起期的唐、五代、北宋和词史高峰期的南宋,而是继元、明词史衰落之后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态势。但是,就词学研究史这一学科系统本身而言,清代的词学研究、清代的词论却无疑是词史长河中最辉煌的一页。词学著作之多,质量之高,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均超过清以前所有其他历史时期。因此,视清代词学研究为词学研究史中之第一个高峰,亦不为过。
尽管如此,倘从学术史发展的阶段性考察,清代之词学研究仍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难以消解的困惑与迷失。其主要困惑之一,便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所表现出的缺欠与失误。
中国词中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四个阶段。纵观此四个阶段,南宋恰值其高峰时期。它的时间虽短,但数量、质量、价值、地位与影响,都远远超过词史上其他三个历史时期。首先是词人众多,名家辈出。按现有《全宋词》(包括补遗),两宋词人可考者1494人,其中南宋词人约占75%(注:据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统计。)。不仅如此,词史上伟大杰出的词人也多出现于南宋,如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张元干、叶梦得、陈与义、朱敦儒、范成大、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史达祖、高观国、刘克庄、刘辰翁、周密、王沂孙、张炎、蒋捷等;同时还出现了岳飞、文天祥这样彪炳千古的民族英雄词人;中国词史上最杰出的两位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也同时辉耀在南宋词坛。正是这些风格各异、俊彩纷呈的词人,像秋夜晴空中的繁星一样,璀璨夺目,熠熠生辉。不论从词人的艺术个性,还是从词史阶段的群体性来考察,在词的创作上能够从整体上掩盖他们的辉光,或者超越并凌驾于他们之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到晚清以前的词史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其次是文质并茂,佳作如林。南宋以前的词史,是南宋词人之所以能攀登词史高峰的级石,自然有不少文质并茂、意境浑融、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但因时代的局限,整体上仍以娱宾遣兴、剪红刻翠、诗酒留连之作品为多。故文胜于质。南宋以后的词,又因文与质的游离或跌落而成衰颓之势。至清,为挽救此颓势而奋起矫敝,力促复兴。由此观之,则文质并茂,形式与内容、艺术与思想完美结合的历史阶段又非南宋莫属了。南宋词在题材的广阔,感情的深细,技巧的精致,风格的多样,词体的完备等诸多方面,都是它以前和它以后各历史时期难以企及的。最后是风韵独绝,千古传诵。“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北宋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获得了新的土壤并得以复苏。辛弃疾通过大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将豪放词创作推向词史的峰巅。姜夔、吴文英致力并完成了婉约词艺术的革新、深化与提高。他们与辛弃疾鼎足而三,共同屹立于词史的高峰之巅。他们(包括南宋其他优秀词人)作品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多样、完整、齐备,已达历史极致。宋以后的词人几乎无一不笼罩于南宋这一词史高峰的阴影之下,不论他们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大发展变化,均未能超出他们的范围,也始终未能走出他们的阴影。从以上三方面着眼,把南宋词归结为词史的高峰期,应当说是顺理成章,当之无愧的。
然而,清代的词学研究对上述现象的考察和描述并非清晰完整。所谓研究,其实也就是理论困惑之消解或者是迷失后的重新发现。清代的词学研究消解了前人的许多困惑,并有新的发现,但在南宋词的研究中却产生了新的困惑与迷失。首先,始终存在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其次,始终存在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这已成为清词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两大焦点。
(二)
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是与清代整个词史的发展相始终的。如果追溯这一论争产生的历史渊源,又与两宋对苏轼评价时提出的“本色”论和后来提出的“正变”之说密切相关。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而胡仔却辩解道:“余谓后山之言过之矣。子瞻佳词最多……,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谓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193页。)同样,胡仔对李清照在《词论》中批评苏轼词是“句读不葺之诗”也甚为反感,认为“此论未公,吾不凭也。”(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193页。)从南宋早期的向子諲 直至后期的胡仔、王灼均充分肯定苏轼,这既是宋室南渡以后的时代要求,也反映了当时审美情趣的变化,是对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豪放词风的高扬与肯定。
然而就在这同时或稍后,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与张炎的《词源》又明确提出:“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页。)这实际上已首开尊北宋的先声。张炎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辛弃疾及辛派词人:“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7页。)张炎强调骚雅,贬抑辛词,掀开了清代尊姜、张与尊辛之争的序幕。
迨至明代,上述争论仍在继续进行。杨慎对南宋豪放词作了很高评价:“近日作词者,唯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3页。)他评陆游词的结论是:“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稍后的王世贞,其观念又与此不同,他不仅强调《花间》的“香而弱”,贬抑豪放词“雄壮固次之”,而且首倡“正宗”与“变体”之说,认为:“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王世贞的“正变”之说,既含有对豪放词的贬抑,又包括有独尊北宋与贬抑南宋的观念在内。这一观念直接影响有清一代的词学研究。与此相关,另一影响深远的词学观念,便是张綎提出的婉约与豪放之分:“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注:《诗余图谱》,引自徐轨:《词苑丛谈》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从此“正变”又明朗化为婉约与豪放之争。
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尊南尊北之争,正是在宋、明以来有关论争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所处时代诸因素而逐次展开的。
明末清初,南唐与北宋词最先受到推崇,云间派领袖陈子龙在《幽兰草词序》中说: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伦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焉(注:《陈忠裕公全集》,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页。)。
对南宋词的整体否定,情见乎辞,无以复加。宋征壁后来在《倡和诗余序》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认为“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陈子龙提倡“天机偶发,元音自成”,从艺术审美方面讲,虽然强调了审美的主体意识,对纠正明代具有“台阁体”特色的词风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却过分忽视了南宋词的社会功能与强烈的时代特色,包括同样具有“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的词篇。其片面性不言而喻。后来,作为阳羡派后起之秀的蒋景祁在《刻瑶华集述》中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今词家率分南北两宗,歧趋者易至角立。究之臻其堂奥,鲜不殊途同轨也。”然而他这一折中的观点却未引起足够重视。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宗法南宋,独尊姜、张,来势甚猛,影响极大,很快就掩盖了陈子龙等人的主张。茱彝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陈忠裕公全集》,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3页。)简洁明快,要言不烦,短短33字,成为浙西词派的纲领。其针对性明确指向明代广泛流行的《花间集》和《草堂诗余》所代表的唐、五代北宋词,认为这两部词集“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朱氏不仅在为其他词集作序时反复申明上述基本观念,浙西词派其他成员又不断补充发挥,致使浙西词派的理论及其创作从康熙延续至乾隆以后百年时间。浙派的理论推动了清初词坛的发展和词的创作,同时又逐渐显示出其片面性所带来的弊端。
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为了补救浙派末期所产生的门径狭窄,脱离现实,陈陈相因,了无生气的流弊,提出了比兴寄托之说,同时还通过《词选》来区分“正变”,大量选入唐五代北宋词,以贬抑姜、张的作品(姜夔三首、张炎一首、陈允平、周密、吴文英等词人作品一首也未入选),表现出与朱彝尊截然相反的尊北抑南的价值取向。与张惠言同时的常州词派成员及其后劲不断充实张氏的理论,补偏救弊,完善其理论体系,使常州词派尊北抑南的词学主张得到广泛传播,影响迄今未稍有消歇,直至现当代仍有一定的市场。
持有尊北抑南观念的词人、词学理论家甚多。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仅举主张最力、影响最大的词学批评家王国维的观点来加以论述。王国维并不属于常州词派,但因他吸收西方美学思想与理论概念,又能同传统诗论、词论完美结合而形成新的体系,影响力很大,覆盖面很广,很有代表性。他在《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删稿》中不断表达他崇北抑南的观点: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6页。)。
王氏之所以崇北抑南,还有其文学发展之理论为基础,即“文体始盛终衰论”,也就是“今不如昔”。他说: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2页。)。
这一段话,主要是就词的发展而言,但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南宋的。“后不如前”是王氏对南宋词的总体评价。为了使这一观念能建立在牢固的理论根基之上,他还系统总结了有清一代词学研究中崇北抑南的各家代表论断:
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垞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德舆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庵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9页。)。
为了牢固树立崇北抑南,推尊北宋之说,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这一观点:
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0页。)。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4页。)。
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2页。)。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5页。)。
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3页。)。
不仅如此,王国维在评价其友人沈宏(字昕伯)寄自巴黎的《蝶恋花》时,也不忘记对南宋词的抨击:“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3页。)。至其将周邦彦推尊为“词中老杜”,意亦在推崇北宋之词。
因为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现当代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所以他的崇北抑南论更易为人所接受。如果对南宋词缺少全面理解和整体观照,一般是很难鉴别其所论之偏颇与片面的。
纵观尊南尊北之争,无论是朱氏尊南还是张氏崇北(包括以后诸家主张),均充分表现出艺术审美与价值取向的狭隘性,均有明显的缺欠,其后果自然影响到清词的创作实绩。
(三)
尊姜、张还是尊辛弃疾,是清代词学研究中长期困惑的又一焦点。
清初,最先推尊辛弃疾的是阳羡派词人陈维崧,他在《词选序》中一方面反对学步《花间》、《兰畹》,反对“矜香弱为当家”而极力推崇辛弃疾,认为“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广泛采纳,很快便被浙西词派独尊姜、张的主张所取代。
朱彝尊虽然推尊南宋,但并非指南宋所有词人及其整体成就,其目光只聚焦于姜夔、张炎及其同派词人而已。对中国词史高峰人物辛弃疾,实际上仍采取排斥态度。首先,他强调“醇雅”以排斥辛词。他多次标举“以雅为目”(注:《陈忠裕公全集》,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3—756页。)、“以雅为尚”(注:《陈忠裕公全集》,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5页。)。汪森在《词综序》里发挥“醇雅”之说曰:“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注:《陈忠裕公全集》,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2页。)。联系前朱氏所说“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及其所撰《词综》,辛弃疾便很明显地被浙派以一“伉”字打入另册。其次,通过“欢愉之辞易工”之论,排斥辛弃疾。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说:
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注:《曝书亭集》卷四十。)。
上面这一段论述,是想在词学领域里推倒韩愈带有普泛性的“欢愉之言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的文学观念,目的是将辛弃疾等南宋爱国词人大声疾呼、昂扬愤发、感怆悲慨的作品,一概以不“工”之作视之。第三,借助总结姜、张在词史上的影响以排斥辛词。他在《黑蝶斋诗余序》里说: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注:《曝书亭集》卷四十。)。
汪森在《词综序》里重复这一段话之后说:“譬之于乐,舞箾至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正因为浙派对姜夔的极端推崇,清代前期才出现了“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
然而,狭隘的门户之见,并不能涵盖所有词人,不能涵盖千“家”万“户”。独尊姜、张,不仅难以代表南宋词之整体成就,而且创作路径也越来越窄,几乎进入了死胡同,所以后来连浙派自家也有人站出来对此提出异议了。吴锡麒就反对“欢愉之辞易工”说,他重新强调“穷而后工”。他在《张渌卿露华词序》中说:“欧阳公序圣俞诗谓‘穷而后工’,而吾谓惟词尤甚……若夫大酒肥鱼之社,眼花耳热之娱,又岂能习其铿锵,谐诸节奏?”他在《董琴南楚香山馆词钞序》中又说:
词之派有二:一则幽微要眇之音,宛转缠绵之致,戛虚响于弦外,标隽旨于味先,姜、史其渊源也。……一则慷慨激昂之气,纵横跌宕之才,抗秋风以奏怀,代古人而贡愤,苏、辛其圭臬也(注:《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八。)。
吴锡麒反对独尊姜、张,兼容两派,其中自然含有尊辛之意旨。其后,郭麐在《无声诗馆词序》中进一步张扬辛派词人:“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愤之音作。”他一面批评浙派末流的颓敝:“性灵不在,寄托无有,若猿吟于峡,蝉鸣于柳,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梅边吹笛谱序》)一面主张“极玩百家,博涉众趣”(《词品序》)以重振词坛。张其锦的《梅边吹笛谱序》在肯定词“盛于南宋”的同时,还称誉“稼轩为盛唐之李白。”
旗帜鲜明贬抑姜、张而同时又兼崇辛弃疾的是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周济。他在《词辨·自序》里曾表示:“白石疏放,酝酿不深。”“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之后,他不断申明这一观点:“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寻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71页。)“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支处、复处、不可不知。”(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4页。)评张炎时,他说:“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4页。)“玉田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5页。)周济对姜夔、张炎的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其目的却着眼于推倒浙西派的旗帜,扫荡“家白石而户玉田”的流风。推倒,自然需要重新竖起。在词学主张与词派之间的论争中,没有旗帜,便没有方向。周济通过《宋四家词选》的编刊,竖起四面大旗,这就是: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和周邦彦。他论辛弃疾时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4页。)稼轩“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3页。)苏、辛历来并称,但在《宋四家词选》里,辛弃疾却被视为一派之领袖和旗帜,苏轼在周济眼里却成为辛的附庸,可见其对辛的推崇已无以复加。他晚年自我反思时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龠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3页。)周济对吴文英的评价亦甚高,他说:“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4页。)就表面看,周济竖起的四面大旗南宋独占其三,其实,他在此四家中却首尊周邦彦,认为:“周清真,集大成者也。”所以他提倡的学词途径是逆向式的溯北穷源:“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4页。)可见他肯定南宋词人并不离常州派推尊北宋这一核心。不带偏见的刘熙载对辛弃疾推崇备至。他认为辛弃疾是“豪杰之词”,“风节建树,卓绝一时”,“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夐异。”因此,他认定辛弃疾是词中的杜甫:“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陈廷焯对辛弃疾也极为推崇,他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沈郁。”他也充分肯定吴文英,认为“梦窗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沈郁之意”,“梦窗精于造句,超逸处则仙骨珊珊,洗脱凡艳。幽索外,则孤怀耿耿,别缔古欢。”(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3页。)由上可见,常州词派及其他词学家词学观点在不断发展变化。
然而,作为后来居上的王国维在反对独尊姜、张及其他南宋词人这一方面,走的比前人更远,他只对辛弃疾一人备加推崇。他说: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1页。)?
王国维还多次贬抑或攻击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其他南宋词人: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词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0页。)。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6页。)。
梦窗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词以评之,曰:“玉老田荒。”(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1页。)。
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稿”。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62页。)。
在崇北抑南、尊辛黜姜这一方面,王国维的态度坚定而又鲜明,是讲得最清楚、最偏激的一位词学家了。
(四)
清代词学研究之所以长期在南宋词的研究中困惑迷失,从理论上看,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对豪放词婉约词的新变认知不清;二是对南宋词的研究缺乏整体观照。
首先,在清代多数词学研究家的心中,还横亘着“本色”论以及正与变等陈旧观念,他们不清楚词至南宋已出现豪放与婉约两种词风之间交融互渗这一深层次变化。
刘勰在评价“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义,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南宋词的变化自然也与此相同。
“靖康之变”像空前巨大的雪崩,将无穷劫难降临人间。北宋政权被颠覆了,词坛也自然随之崩解。当时词人亦随宋室仓皇南渡,朝中的爱国之士奋起救亡,元戎武将们拼搏于沙场,逃亡的词人士子饱受流离之苦。经过这场血与火的磨炼,剪红刻翠、浅斟低唱的词风一时被涤荡净尽。“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代主旋律自然得以高扬。由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曾一度消沉。但在南宋这狭小局促的半壁河山里却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南宋词坛重建期的爱国豪放词获得空前的丰收,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粗疏与概念化的缺点。这一方面是缺乏经验,出手太快;另方面则是还不善于或来不及吸收婉约词的艺术经验为己所用。但这一时期的成就与不足都成为后来登上词坛的名家们的借鉴。
继之而起的张孝祥、陆游,特别是起义南归的辛弃疾,他们承继了南宋词坛重建期的传统并扬弃了其明显的缺欠,成功地融入了婉约词的艺术经验,使爱国豪放词的创作出现了一次飞跃。在稼轩词里,雄豪与悲婉并存,寓雄豪于悲婉,雄豪涵盖悲婉;或者展博大于精细之内,行隽峭于清丽之外,其变化繁富,有过前人。刘宰说:稼轩词“驰骋百家,包罗万象。”(注:刘宰:《漫堂文集》卷十五。)陈廷焯在《云韶集》中以赞美的语气说:
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飞将军也(注:《云韶集》卷五,引自《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92页。)。
在“东南妩媚,雌了男儿”(注:陈人杰:《沁园春》(记上层楼)词序中引友人语。)这一令人消沉与失望的时代氛围中,稼轩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英风豪气,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稼轩词的成功并非仅止于雄豪,而是完美地融合了婉约词传统的艺术经验。他的某些词就明确标出“效花间体”、“效李易安体”、“效朱希真体”等等。最早编刊稼轩词集的范开就曾用形象化的词言概括稼轩词的特点:
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注:《陈忠裕公全集》,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在“稼轩体”中,不仅形式、体裁、题材与风格丰富多样,而且一首作品中就往往能成功地融会豪放与婉约两种不同风格和审美情趣。如名篇《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原是以词人早年起义抗金的战斗生活为基础,描绘出整军校阅、沙场点兵、往来驰突的画面,气势雄浑,情辞慷慨,令人鼓舞。但结拍“可怜白发生”一句,却将美好的希望击得粉碎,雄豪化为悲凉。另首被视为婉约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表面上写得幽窈宛转,曲折尽致,实际上却外柔内刚,绵里藏针,字里行间流注着雄豪之气。陈廷焯评曰:“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沈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回来,真是有力如虎!”(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3页。)缪钺明确认为这首词“能融合豪放与婉约为一者”,又说:“在宋词的发展中,形成婉约与豪放两派,但是这两派并非水火不相容的。”(注:《论范仲淹词》,见《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谢章铤所说:“学稼轩词要于豪迈中见精致”(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0页。),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正因为“稼轩体”能融豪放与婉约二家之所长,加之以崇高的人品,博大的创作,所以清代词学研究中很少敢于全面否定稼轩在词史上的成就。但从深层次上分析,对辛词的评估仍有某些迷茫与困惑。其一,推崇南唐、北宋或推崇南宋却独尊姜、张,其实质都在贬抑辛弃疾,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其二,辛弃疾在词史上的高峰地位难以动摇,于是对辛派其他词人如陈亮、刘过(包括陆游)等,却多有微辞,其中有的是针对他们作品本身的不足而发,有的则似乎旁敲侧击地指向辛弃疾。
重建期的南宋词坛虽然以爱国豪放词为其主流,但同时又不乏婉约之作。不过此时之婉约词已与北宋婉约词有明显不同了,其主要表征之一便是在不知不觉中向豪放词风倾斜或与之相互渗透。南渡之前,李清照的作品只局限于咏叹自然景物和抒写离情别绪的狭小范围,但因她有着女性的艺术敏感,在写其少女、少妇心灵感受时,笔调轻灵,音韵和谐,清新自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其自我形象也显得特异而清出。如果没有“靖康之变”,没有仓皇南渡与“漂流遂与流入伍”的颠沛流离,李清照的成就也许只不过是另一魏夫人而已。南渡,对李清照来说是一极大不幸,但这不幸又促使她成为历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她后期所写的忧愁烦恼与深悲巨痛,已不仅是她个人的一己之悲,而是融入了家国之恨与南渡臣民百姓的共同心声。南渡后的“易安体”已不可避免地向豪放词风倾斜,同时又不失女性文学“别是一家”的本色。这一点不仅在《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中有充分体现,同时也贯穿在其他南渡作品的字里行间。李清照之所以能登上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高峰位置,其原因也正在这里。前人评语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注: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直欲压倒须眉。”(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1页。)“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为词家一宗矣。”(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玩其笔力,本自矫拔,词家少有,庶几苏、辛之亚。”(注:陆昶:《历代名媛诗词》卷十一。)这些话,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易安体”向豪放词风倾斜的某些信息。
浙派词人推崇的姜夔、张炎,因为他们是继辛弃疾之后登上词坛的,所以免不了要向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倾斜。周济对此已有所发现,他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骋为疏宕。”(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4页。)刘熙载说:“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13、110页。)即使理论上贬抑辛弃疾的张炎,在南宋灭亡以后也身不由己地向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倾斜。其《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壶中天》(扬万里)等,均具有明显的豪放特色,即使杂入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作品之中,似也毫无逊色。其他许多作品,也都程度不同地沉潜有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悲,或身世飘零与悲今悼昔之感。张炎的创作实践已突破了他在《词源》一书中所表现出的某些局限。第一,经历南宋灭亡的沉重打击,张炎从思想上已与辛弃疾等人趋于一致,因此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辛弃疾词风的影响。第二,张炎受姜夔影响最大,并有意效仿白石,因白石自身也不免接受辛词影响,张炎自然也随之向豪放词风靠近。第三,南宋灭亡的现实与长期漫游的遭遇充实了张炎的人格力量,深化了他的审美能力并强化了笔力。第四,形式上大量运用豪放词人惯用的词牌。据不完全统计,张炎词中共用《壶中天》(即《念奴娇》,其中有全用苏轼《念奴娇》韵者)九次,《木兰花慢》十一次,《甘州》(即《八声甘州》)十二次,《满江红》四次,《水龙吟》三次,《桂枝香》二次,《水调歌头》一次。这些词牌在周邦彦《清真集》、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以及王沂孙、周密等人词集中均极为罕见。有以上四点,张炎反而成为宋末元初婉约词人(或被称之为格律派、骚雅派)中向豪放词风倾斜最突出的词人之一。张炎的《山中白云词》标志着豪放词风与婉约词风在南宋最后阶段的交融互渗。这一点,在清代词学研究中却很少有人道及,只有周济似乎触摸到了这一词史发展的脉搏:“稼轩则沈著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4页。)
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尊南尊北之争,尊姜、张与尊辛之争,均未能从词史发展变化的深层次上来把握这一重要现象。浙派过分强调“骚雅”,而不见南宋婉约词向豪放词风的倾斜。常州派则不见南宋末期姜、张等词人的深层寄托,直至全盘否定,而把他们的比兴寄托与学词重点投放到温庭筠及其他北宋人身上,凡此,均给人以东向而立,不见西墙的感觉。
(五)
另一困惑迷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词学理论上缺乏对南宋词作整体观照,很少有人强调其溶涵历史时空的巨大规模效应,对辛、姜、吴三足鼎立以及由他们牵动的词史高峰形态缺乏具体理解。
清代词学研究对南宋词缺乏整体观照,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南宋词本身缺乏整体观照;二是缺乏从中国词史的整体观念上来把握南宋词。
如上所述,宋室南渡以后,是抗金复国、收复失地、重整河山,还是偏安一隅、不图恢复、置沦陷于敌人铁蹄下的北中国大片领土于不顾?这一民族生死攸关的头等重大问题,在朝廷中表现为和战之争。南宋的最后灭亡,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南宋小朝廷畏敌如虎,始终执行妥协投降路线,步步退让,最后终于退入南海之中而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南宋绝大多数词人则与此相反,他们的作品不论其风格体式如何,都自始至终响彻反对妥协投降、极力主张反攻复国的强音。面对北宋灭亡与南宋岌岌可危的现实,由母系社会集群、父系社会集群、部族集群为抗敌求生而沉潜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很快便被激活,形成巨大强烈的“楚虽三户必能亡秦”的爱国精神力量。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像南宋那样,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为所有词人共同关注的大主题。只是因为这种精神力量遭到统治集团的压制、摧残与打击而未能得到充分集中与有效释放,于是又重新潜回心底,或分流解体。有的坚持抗争,至死无悔;有的被谪蛮荒,全节以终;有的被投闲置散,啸傲林泉;有的插花醉酒,白眼人生;有的皈依佛道,了此尘缘。然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各式各样表面上四散开来的射线,实际上都在朝向一个共同的焦点,这就是爱国抗金(包括南宋后期的抗元)。此即南宋词的整体优势,也是其他历史时期难以比拟的规模效应。
所谓整体优势,也就是要始终把握南宋词的全局,不犯或少犯片面、偏激或无知的毛病。而体现这一优势,至少要注意三个层次,即:从南宋的整体和中国词史的整体上来把握南宋词人及其作品;既注意彪炳千古的大词人,也不忽视中小词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时代链环;深入考察词的发展变化与时代、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社会风习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整体观照必然有助于克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其风格体式的对立而不见其相互融通转化与相互生成。例如浙派独尊姜、张而排斥辛弃疾,这本身就是在挖南宋词的台柱,抽去了南宋词的灵魂。同样,独尊辛弃疾而贬抑甚至否定其他所有南宋重要词人,也必然抹杀了南宋词的整体优势,使辛弃疾成为光杆司令,失去南宋词缤纷多彩的辉光。南宋词是一个按照历史逻辑程序逐次展开的动态过程,而并不是一个个词人的机械拼合与作品的堆累相加。所以,研究者必须对南宋词作整体把握,而不能随意褒贬取舍。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已经证明,只强调任何一个词人,一种词风,一种技法,或法个人的兴趣、爱好与感情偏向取代词史的科学评价,都不能全面概括南宋词的整体面貌,也无法全面继承其优秀传统以开拓创作的新疆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出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三人领袖一代而鼎足屹立于词史高峰之巅这一历史结论。所谓高峰,简单说来,也就是前人达到的,南宋词人达到并有所超越,南宋词人在思想艺术上所占领的词史制高点,元、明、清三代却未能超越,突破。所谓“宋以后的词人无不笼罩于南宋这一词史高峰的阴影之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这段话虽可适用于文学史上其他文学现象,但对南宋词的评价来说,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变”字是南宋词史的逻辑起点,也是这段词史的归结。南宋词之所以能登上词史的高峰,正是在这个“变”字中完成的:一是功用的变化;二是题材的变化;三是风格的变化;四是境界的变化;五是形式的变化;六是语言的变化(注:参阅拙著《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525页。)。以上六方面的变化不仅是南宋以前词史未能完成的,也是南宋以后之词史难以企及的。因为这种变化是全面的,多层次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如果豪放与婉约这两种词风中,只有一种词风发生巨大变化并由此登上词史高峰,那在此前或在此之后,都可以容许别的时代与别的词人来填充这词史高峰上另一词风的空白。同样,如果上述六个方面还留下几个方面不曾发生变化,不曾开拓创新,后人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南宋词人实在过于争强好胜,他们不仅挤满了高峰上的席位,而且也没有留下其他可以令后人大加发挥的事情。争夺词史制高点的难度实在太大了。至此,独尊北宋或“词至南宋而敝”之说的片面性,已无需多言了。
应当说,清代的词学研究在词韵之学、词乐之学、图谱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目录之学、批评之学、词史之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词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南宋词”面前,却显示出其力不从心,因而在困惑与迷失中长期徘徊。究其原因,首先是时代的制约。振衰救敝,人人有责,主张各异,法出多门。其次是清代的国情与南宋既有近似点却又有巨大差异。清代不可能像南宋那样有一条爱国统一的主旋律与聚焦点贯穿始终。第三,清代文字狱的高压不仅影响了词人的创作,而且也波及到词学研究领域。第四,门户之见与派别之争影响到冷静的思考和理智的取舍。毫无疑问,地域特色、家族传统与师友唱和均有助于推动词史的发展。但这一近亲繁殖也有重大缺欠,它往往限制了词人与学者的眼界,甚至因此被捆住了手脚,出现用“近亲繁殖”的关系和个人审美偏见来代替科学的价值判断。王士祯从地域乡土关系出发,对辛弃疾、李清照推崇备至:“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注: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5页。)字里行间流溢出作为同乡所感受到的骄傲。厉鹗在追溯浙派词的艺术渊源时,特别推尊周邦彦:“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注:《吴尺凫〈玲珑帘词〉序》,《樊榭山房文集》卷四。)朱彝尊为浙派先河曹溶《静惕堂词》作序时,署称“同郡年家子”。被刻印在一起的《浙西六家词》,李良年、李符等均为朱氏同乡。常州派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合编词选,书末所附基他词篇均为其友人(如黄景仁、左辅、恽敬等)所作。不难看出,门户、乡邦、师友关系对词学观念、词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第五,个别人还存有借前人以自重的潜层因素。如果一个人拼命推崇并夸大前人的某些我们明知并不太重要的东西,那就会引起人们怀疑他是否在借前人以推重自己。这一点在门户之见日深的清代词学研究中几乎难以完全避免了。在以上五种环境氛围与思想境界之中,如果想对前代词人、词史作出科学分析与正确评价,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了。清代词学家并非没有远见卓识之士,他们有所发现,也提过一些正确意见,只是被强大的门户之见所掩盖而未能左右全局。难怪蒋景祁在批评尊南尊北之争以后深有感慨地说:“吾皆不谓之知音。”(注:《刻瑶华集述》。)
1500年前的刘勰就曾感叹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注:《文心雕龙·知音》。)1100年后的清代词学研究继续证明这一段话的科学性与现实针对性。词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贴近古代词人的真实存在,把握他们留下的信息,做他们的“知音”。而欲达此目的,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和前代词人发出的信息处于同一波段之上。只有如此,才能收听(或收视)到前人发出但因损耗而变得十分微弱的电波,破译他们留下的符号与密码,以获得心灵的沟通,消除隔阂与误解,减少判断上的失误与冤假错案的发生,引导词人在历史的链环之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因为到目前为止的文学研究工作证明,我们的工作几乎陷于没完没了的纠正前人的冤假错案之中,当然,这是一项十分困难而又艰巨的工作,因为即使我们能够跟前代词人处于同一波段之上,收到的信息也会因积年耗损而模糊不清,不可能把收到的信息原样照搬地转播给今时的听众(或观众),因而要做许多破译、整理、归纳、编排、补偏、纠谬直至填补空白的工作,以使之还原成历史本来面貌。困难在这里,创造在这里,冤假错案也出现在这里。所以,科学、公正、理智与献身是绝对必要的。清代的词学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其难以消解的困惑与迷失,有其明显的缺欠与失误。这些都将成为当代词学研究的借鉴。
事实证明,不论何种学术研究,只有站在当时文化思想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如果用这话来衡量清代的词学研究,他们似乎已经登上了他们那一特定时代的顶峰。然而在后人看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距离那个顶峰至少还差一两个台阶。理智的最后一个台阶告诉我们,在这台阶上看到的是还有许多事物是那个时代人们力所不及的。这个道理,似乎适用于其他任何一个时代。
(1995年4月上海“清词研讨会”论文,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研讨会论文集)
标签:宋朝论文; 辛弃疾论文; 姜夔论文; 南宋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词话丛编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吴文英论文; 唐圭璋论文; 张炎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