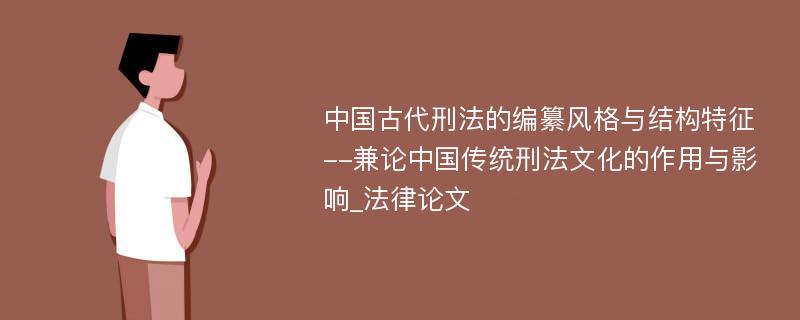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特点——兼论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典论文,体例论文,刑法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4-0066-07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从奴隶社会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西周的“九刑 ”、“吕刑”,春秋时期郑国的“刑书”、“竹刑”,晋国的“刑鼎”,宋国的“刑器 ”开始,就具有刑法的性质与特征。封建社会战国时期魏国的《法经》、韩国的《刑符 》、赵国的《国律》,因“皆罪名之制”[1](《晋书·刑法志》),在法典性质上应属 于刑法;秦朝的《秦律》,汉朝的《九章律》,三国时期曹魏的《新律》,两晋的《泰 始律》,南北朝的《北魏律》、《北齐律》,隋朝的《开皇律》、《大业律》,唐朝的 《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开元律》,皆属于“律以正刑定罪”的刑法 典范畴[2](《唐六典·刑部》);唐末的《大中刑律统类》,五代的《同光刑律统类》 、《显德刑律统类》,宋朝的《宋刑统》,也因“刑名之要,尽统于兹”[1](《旧五代 史·刑法志》)的缘故而具有刑法典的特征;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律例》 ,由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定律以绳顽”[1](《明史·刑法志一》)的需要而具备 了刑法典的功能。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个朝代甚至每一个帝王统治期间, 国家的主要法典只有一部且这部法典的性质和特征可以说是天然的相似,这就是刑法典 的性质和特征。本文主要就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的特点,及其所反映出的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近代法治的作用和影响谈一些看法。
一、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从整体上由总则和分则两部分组成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总则篇名称叫“名例”。它渊源于《法经》的《具法》,作用在于 “具其加减”。到商鞅变法时,为了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贯彻执行,开始“改法为 律”,因此商鞅在秦国变法期间制定的《秦律》中的总则部分应该叫“具律”。这是因 为“商君受之以相秦”[1](《晋书·刑法志》),在秦国主持变法之前,商鞅在魏国就 对《法经》进行了深入的研读,了解和掌握了它的体系和结构,并在变法和制定《秦律 》时采用了它的六篇体例和结构,所不同的只是改“法”为“律”罢了。应该指出的是 ,无论《法经》还是《秦律》都把作为总则篇的《具法》或《具律》放置到了法典的最 后一篇。这反映出古人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方法,而尤其是对立法、司法经验的总结与 吸取、立法技术的创新与提高。到萧何奉汉高祖刘邦之命制定《九章律》时,他仍然以 《法经》的六篇为基础,并参照了秦律的体例结构和篇目名称以及内容中对自己有用的 部分,从实际出发形成了九篇的体例结构,其总则篇的名称继承了《秦律·具律》的传 统,仍然把其排在第六篇。这时的《具律》在法典中的位置不像《法经》、《秦律》那 样放在最后一篇,而是位于整部法典的中间。这说明到两汉时,我们的古人对总则篇在 整部法典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晰和科学,对立法技术和法律理论仍在进 行探索和总结。到三国时期魏明帝在位期间,立法者已经初步认识到总则篇在整部法典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们一方面把总则篇的名称由《具律》改为《刑名》,另一方面 一改过去把总则篇放置在末尾或者中间的传统作法,径直把《刑名》置于首篇,使其具 有支配和统领整部法典的地位和作用。这反映出古人对法律理论研究的深入,对立法技 术的提高,对法典体例和编纂结构科学性认识的渐趋成熟。到西晋杜预等律学专家受命 立法制定《泰始律》时,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魏新律》把总则篇放置在首篇的立法成果 ,另一方面继续探索,为总则篇名称和构成的合理化与科学化而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他 们从《刑名》中分离出《法例》一篇,专门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而《刑名》则主 要规定刑罚体系和处罚犯罪的刑罚名称。这样中国古代刑法典的总则篇就名副其实地具 有了“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 纲领”的地位和作用了[1](《晋书·刑法志》引张斐《律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政 权任用律学世家出身的封述主持制定《北齐律》时,对中国古代刑法典总则篇的名称和 构成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将《刑名》和《法例》两篇的内容进行有机的调整,并 最终将中国古代刑法总则篇的内容合并为一篇,名称确定为《名例》。之后,隋文帝制 定的《开皇律》,在立法体例和编纂结构上,撇开北周《大律》之旧而改承北齐定律之 新,将《北齐律》的《名例》作为自己新定律典《开皇律》的第一篇,这足以说明《名 例》的合理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以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刑法典均以《名例 》作为其总则篇的名称并放置在第一篇,到清末制定《大清现行刑律》时,其第一篇的 名称仍然叫《名例》并且继续具有总则篇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情况到西学东渐、制定《 大清新刑律》时才告结束,并被“总则”的名称、结构和体例所代替。
中国古代刑法典的分则篇,从《法经》的《盗法》、《贼法》、《杂法》开始,到《 九章律》新增的《户律》、《兴律》、《厩律》,再到《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 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 、《杂律》,以至于《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吏律》、《户律》、《礼律》、《 兵律》、《刑律》、《工律》等均属于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当然《唐律疏议》、《宋刑 统》的《斗讼律》和《大明律》、《大清律》的《刑律》等均含有一定程序法的内容。 依现在刑事法的理论衡量,这些内容应不属于刑法分则的组成部分)。由于同样的原因 ,到清末制定《大清新刑律》时,中国古代刑法典的分则篇才被以“分则”的名称、结 构和体例所代替。
中国古代刑法典这种从结构上划分为“总则”与“分则”二部分的做法,有利于贯彻 明刑弼教、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法制指导思想,有利于古代刑法理论、刑法思想的发 展和完善,有利于刑法原则(包括定罪和量刑二个方面)的高度概括并指导分则具体规定 的实施和适用,有利于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对于清末的法制 改革和近代刑法典的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也许对西方近代的刑事立法体例起了 难以想像的作用[4]。
二、中国古代刑法典采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一的编纂体例
中国古代刑事实体法的篇目和内容,如前所述的中国古代刑法典的总则篇和分则篇, 均属于这方面的规定。中国古代刑事程序法的内容,渊源于西周中期穆王命吕侯重定刑 书时制定的《吕刑》[5],而明确列有刑事程序法篇目名称和内容的刑事法典则应该从 战国时期魏国的《法经》及其《网法》、《捕法》二篇开始。这时的立法者已经认识到 刑事程序法对于刑事实体法实施的重要性,“盗贼须劾捕,又著盗、贼两篇”的历史记 载[1](《晋书·刑法志》),已充分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二 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刑事程序法对刑事实体法重要性的认识水平。以后的《秦律》、汉代 的《九章律》继承了《法经》的这种传统,只不过是把《网法》、《捕法》的名称改为 《网律》、《捕律》罢了。当然,这反映出当时的立法者对于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 在法典中的前后顺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着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认识,因为 汉《九章律》竟然把《网律》、《捕律》这些属于刑事程序法的篇目和内容放置到了《 盗律》、《贼律》与《杂律》、《户律》、《兴律》、《厩律》等这些刑事实体法的篇 目和内容的中间,使刑事程序法的篇目和内容在整个刑法典中处于不前不后、不伦不类 的地步。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者们应该说已经认识到以前在刑事立法体例、结 构诸方面的这种不足和不当之处,开始改变以前把刑事程序法的篇目和内容放置在刑法 典的中间、处于刑事实体法篇目和内容的两面夹击的局面。三国时期的《魏新律》,西 晋的《泰始律》,南北朝的《北魏律》、《北齐律》等都是把刑事程序法的篇目和内容 放置在刑法典后边。到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成熟和完善的隋、唐、宋的刑 法典制定时,不仅刑事程序法的篇目名称定名为《捕亡律》、《断狱律》,而且均把这 二篇的内容放置在法典的后边。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合一的刑法 典编纂体例与结构,不仅表现在上述的篇目组成排列上,而且在有些篇目内部的构成上 也表现出来了,如在《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斗讼律》、《大明律》及《大清律 例》的《刑律》中就反映出了这种现象。
这种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合一的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反映出中国古代的法律 家和律学家们对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先实体后程序、重实体轻程序的认识水平和思 维方式,从而严重影响了刑事程序法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制约了刑事程序法体例和结构 的改进与完善,也使得刑事程序法的内容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到西法东渐之前的清朝中 期时仍然不能从刑事实体法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并独自成典,也当然使我们的古人更不 可能对刑事程序正义论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进行深入地探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编纂体例 和结构,是因为这样做简单、直接、实用、有效,有利于维护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 基础上的家长统治而尤其是拥有立法、执法、司法等一切大权的君主专制的统治。
三、中国古代刑法典在编纂体例上具有从低层次的“以刑统罪”向高水平的“以罪统 刑”的方向转变和发展的特点
悠久古老的中国从夏朝进入文明社会开始,史籍就是用“夏刑三千条”[6](《名例》 引《尚书大传》)、“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7](《周礼·秋 官·司刑》郑氏注)来记载其法制和刑法的基本情况。从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夏代刑 法的大致概貌,即有三千条的刑法内容(注: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无从可 考,有人说并不可信(参见叶孝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版;曾 宪义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陈顾远主编的 《中国法制史概要》,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笔者的看法是不能随意 怀疑史籍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应注意到每种刑罚所属条数对这三千条的印证作用;并 且,学界基本上同意“禹刑”或者“夏刑”的内容属于习惯法,即认为三千条的夏刑属 于一事一例的事例案例汇编,这样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的夏王朝日积月累有三千个典 型事例案例,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夏代刑法典的汇编体例、 刑罚体系及其刑罚种类,即夏代刑法典的汇编体例为“刑名 + 罪名”,也就是说以刑 名为纲、罪名为目,把处刑相同的罪名汇总在同一种刑名之下以形成夏刑的法典编纂体 例,这样“墨、劓、膑、宫、大辟”既是夏刑的纲(相当于以后封建王朝刑法典中的篇 名),也是夏刑所规定的刑罚种类和刑罚体系。之所以形成“以刑统罪”或者叫“刑名 + 罪名”的刑法典汇编体例,笔者认为是因为步入文明社会不久的夏朝的刑法还处在习 惯法的水平,比较原始,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经验教训还不多,立法技术水平还不高;夏 朝还是部族国家,氏族血缘纽带对自己的影响仍然很大,而实行宗法血缘等级统治的社 会和国家在客观上就限制了“以罪统刑”的刑法编纂体例的发展;夏朝的刑法还处于秘 密状态,“以刑统罪”有利于保持刑法对广大平民和奴隶的威慑作用,有利于奴隶主贵 族对被统治者擅断刑罚。以后以“墨、劓、刖、宫、大辟”为刑法体系、刑罚体系和刑 罚种类的商朝刑法典,以“汤刑”而载入史册;以“墨、劓、剕、宫、大辟” 为刑法体系、刑罚体系和刑罚种类的西周刑法典,以“九刑”、“吕刑”命名,且在编 纂体例和结构上沿袭了夏朝的上述做法。
到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新兴的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后 ,他们要求打破贵族凭借优越的血统无能而任官、无功而受禄的垄断政权局面和旧体制 下“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刑法秘密状态,主张限制旧贵族“刑不可知,威不可测” 的擅断刑罚特权。郑国的“铸刑书”、晋国的“铸刑鼎”、邓析的“竹刑”等公布成文 法的活动和事件,则体现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代表了法制发展的方向 ,同时也促进了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向合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变化。这个发展变 化以战国时期在“撰次诸国法”[1](《晋书·刑法》)基础上制定的《法经》为标志, 其成果就是“罪名 + 刑名”或者叫“以罪统刑”的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形成,也 就是以罪名(即《盗法》《贼法》《杂法》)为篇目名称,在具体条文中先规定犯罪、后 规定刑罚的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这种编纂体例和结构,被以后从秦朝到清朝的刑 法典所继承和沿用。如上所述《九章律》的六篇,《唐律》、《宋刑统》的九篇、《大 明律》、《大清律例》的五篇等刑事实体法内容就是明证。
这种体例和结构,便于在总结刑事立法、司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刑法的理论进行 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比较高度的抽象与概括;便于国家对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尤其是 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便于法律内容的宣传和适用。
四、中国古代刑法典分则的篇目在结构上是依据犯罪行为对中国古代刑法所保护的社 会关系危害大小的原则,从重到轻依次排列的
中国古代的刑法从战国时期魏国的《法经》开始,统治者就注意运用刑法的特殊功能 和工具作用来维护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从 《晋书·刑法志》对《法经》的追述来看,李悝制定《法经》的指导思想是“王者之政 莫急于盗贼”。按照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况的“窃货曰盗”与“害良曰贼”的解释 ,《法经》的《盗法》应是关于危害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它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及其刑 罚的规定,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和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法经》的 《贼法》应是关于杀人、伤害等严重侵犯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利、健康权利以至于封建统 治集团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及其刑罚的法律规定。在这里经济利益、经济 秩序是地主阶级及其特殊利益集团的基础,而政治特权、政治秩序则是地主阶级及其特 殊利益集团的上层建筑,二者是同等重要、不可分离的,因此《法经》的制定者把《盗 法》《贼法》放置在整个法典的前二篇予以规定。至于“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 、淫侈逾制”等犯罪行为[1](《晋书·刑法》),虽然对当时刑法所维护的社会关系的 危害性也相当大,但与前述的牵涉到地主阶级及其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相比,其重要性还是稍次一些,因此《法经》的制定者只能把它们放置在《杂法》之中 ,而《杂法》不仅放置在《盗法》、《贼法》之后,且在《法经》的法典编纂结构和篇 目排列顺序上排列在旨在保证《盗法》、《贼法》实施的程序法的篇目《网法》、《捕 法》之后。以后的《秦律》、汉《九章律》沿用了《法经》在分则排列顺序上的这种做 法,并对以后历代刑法典分则篇目的排列顺序及其内容安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 封建王朝的刑法典如曹魏《新律》,西晋《泰始律》,南北朝的《北魏律》、《北齐律 》,隋朝的《开皇律》、《大业律》,唐朝的《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 《开元律》,宋朝的《宋刑统》,元朝的《大元通制》,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 大清律例》等均是如此。比如唐律的十二篇除了第一篇《名例律》是属于总则的篇目和 内容,第十一篇、第十二篇《捕亡律》、《断狱律》是属于刑事程序法的篇目和内容外 ,其余九篇均属于刑法分则的篇目和内容。唐律的第二篇《卫禁篇》,是关于惩治危害 以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官僚的人身安全和封建国家的边防安全与领土完整的犯罪行为的法 律规定;第三篇《职制律》,是关于惩治危害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管理秩序 的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第四篇《户婚律》,是关于惩治破坏封建国家的户籍管理秩序 、土地管理秩序、税收管理秩序、婚姻家庭继承关系等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第五篇《 厩库律》,是关于惩治危害国家的车马驿传和仓库物品出入的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法 律规定;第六篇《擅兴律》,是关于惩治破坏封建国家军队的调动、征集、军事供给、 驻防等军事管理秩序和工程的兴建、手工业的开设、丁夫的征发使用等为主要内容的经 济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第七篇《贼盗律》,是关于惩治危害皇帝以外的社 会成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第八篇《斗讼律》,是关于惩 治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因故意或过失的原因通过斗殴的形式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以及因非法 提起诉讼所构成犯罪的法律规定;第九篇《诈伪律》,是关于惩治以隐瞒真相或者虚构 事实的手段破坏封建国家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第十篇《杂律》 ,是关于惩治破坏前述八篇没有规定的其它经济管理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 法律规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刑律各篇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依统治者对其在国家生 活中作用的评价来确定顺序”,并且“封建社会历代的刑律总是把与皇帝有关的内容作 为最重要的部分放在前面”[8]。
中国古代刑法典分则每篇的条文也是依据犯罪行为对中国古代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危害的大小,按照从重到轻的次序进行排列和规定的(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一一赘 述)。
从上述内容可知,在中国古代刑律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利 益和地位优先并明显高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地位,皇帝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优先并 高于各级贵族官僚的人身安全和各种利益,贵族官僚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优先并明显 高于普通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也优先于社会秩序的 维护,并且在某种具体社会关系的保护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轻重缓急。这有利于君主专 制制度的巩固和加强,有利于以皇权利益为核心、以等级秩序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的调整 与维护,当然也同时加强了对于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刑事镇压。
五、中国古代刑法典的编纂体例和结构具有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
从上可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一个朝代甚至于某一个朝代的每一个帝王统治期间, 国家的主要法典只有一部,这部法典的性质和特征可以说是天然的相似,这就是刑法典 的性质和特征。这种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引发对其内容、编纂体例和结构 、形成原因等进行探索,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的社会关系只有刑事法律关系这一种 ,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也只有刑法规范这一类。中国古代还有着丰富的民事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关系,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民事法律 规范、行政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规范、婚姻家庭继承法律规范,只不过由于农业经济自 给自足的单一性、社会组织构成的血缘宗法家族性、国家政治体制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 权性,尤其是国家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性等原因,使得法律关系向刑事方面畸形发展,法 律规范体现刑事方面的一枝独秀。因而也使得刑事之外的各种法律关系没有条件得到系 统的发育和完善,调整刑事之外的各种法律关系的其它各种法律规范得不到独立的发展 ,更不用说如刑事法律规范那样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了。在中国四千余年的古代社会,就 始终没有孕育和制定出一部独立、系统且内容丰富的民法典来。因此,在国家的基本法 典中,中国古代的民事法规采用了与刑事法规合一或者叫混编的体例和结构。在中国古 代社会虽然出现过诸如《周礼》、《唐六典》、《明会典》、《大清会典》等这些被后 人尤其是现代人称之为行政法典的文本,但在国家的基本法典中仍采用了刑事法规与行 政法规合一编纂的体例和结构。这样,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确认和维 护社会成员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规范社会成员日常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 契约签订、担保和履行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规,均以禁止性、惩罚性为特征的刑法典 的性质和形式表现出来;违犯民事法规的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是以肉刑、身体刑 、自由刑、财产刑为种类的刑事责任而不是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原 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为方式的民事责任。中国古代法律对 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也如同对民事法 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一样,以禁止性、惩罚性为特征的刑法典的性质和形式表现出来, 对违犯行政法规、经济法规、婚姻家庭继承法规的行为均采用了法律责任的刑事责任承 担方式而非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的承担方式。这样,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民事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还是经济法律关系、婚姻家庭继承法律关系,均具有刑事法律关系的性 质;也无论是民事法规、行政法规,还是经济法规、婚姻家庭继承法规,也均具有刑事 法规的特征。于是,民事法规与刑事法规不分,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婚姻 家庭继承法律均采用刑事法律的形式并与刑事法律一起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也就成了顺 理成章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刑法典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呈现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 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刑法典的这种体例和结构特征影响了多元法律体系的发育和形成,不利于刑法以外各 个部门法的发育、发展和独立体系的形成;不利于平等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发育、规范 、调整与维护;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泛刑法”的观念和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顺从 服从的心理和习惯,对于近现代中国在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重视刑法、轻视民法 的惯常作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六、与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特征相脱离,中国古代刑法典所 规定的法律责任类型及其实现方式是单一的,即刑事责任的类型和刑罚制裁的方式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部门,按现代法学理论来讲刑法所规定的法 律责任的性质和类型应该是刑事责任,而不应该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其它别的什 么法律责任类型与刑事责任混在一起加以规定。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明起源条件、发 展途径的特定性和特殊性,经济结构的单一性,社会组织结构的宗法性,中央集权统治 的极权性,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在性质和法典编纂体例与结构上具有以刑为主、民 刑不分、诸法合体的鲜明特征。这样的法律性质和法典编纂体例、结构的特征,从理论 上讲肯定要求规定一定的法律责任类型及其实现方式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刑 法典的法律责任除了主要规定刑事责任及其实现刑事责任的刑罚制裁方式外,应该与其 内含的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等规范相适应,规定相应的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法律责任类型及其实现这些法律责任的民事、行政等制裁方式。 而中国古代法制和刑法典编纂体例、结构演变的事实,是中国传统刑法典所规定的法律 责任类型及其实现方式,与中国古代将刑事法律、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婚 姻家庭继承法律等各个法律部门规定在同一种性质的法典中的实际情况相脱节,只规定 一种法律责任类型,这就是刑事责任的类型,只规定一种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这就是 刑罚制裁的方式。
从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传说中舜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刑罚种类和刑罚体系 ,并“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7 ]。史籍记载“夏刑三千条”,“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说 的也是刑罚种类和刑事制裁方法,当然也隐含了对违法行为所追究的法律责任就是刑事 责任的意思。以后的商、周继承并完善了这一传统,并将以断人肢体、刻人肌肤为特征 的墨辟、劓辟、刖辟、宫辟、大辟的刑罚方法和种类作为国家最基本的刑罚制度、刑罚 体系确立下来,同时也成为当时最基本的法律责任类型和制裁方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规定的法律制裁方式和种类仍然是诸如宫刑、膑 刑、刖刑、诛(死刑)、族刑和笞刑等刑罚制裁方式和种类,而没有规定独立且系统的民 事、行政制裁方式和种类,更没有专门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规定[9]。秦汉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的刑法典继承了这一传统。封建社会中后期的隋唐宋元明清的情况,从《 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元通制条格》、《大明律》、《大清律例》等传世法典 来看,可以说刑法典规定的法律责任类型只有一种,这就是刑事责任;规定的法律制裁 方式也只有一类,这就是以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为体系和种类的刑罚制裁方 式,并且均放置在法典第一篇的前列[6]、[10]、[11]、[12]。
中国古代的刑法典还规定对民事违法、行政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并实行刑罚制裁措 施。从目前能够看到的有限资料来讲,中国奴隶社会的法律只规定了一类法律责任形式 (即刑事责任)和一种法律制裁方式(即刑罚制裁),而没有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 与它们相适应的系统的民事制裁、行政制裁方式。《法经》对路上拾东西这种显然属于 不当得利的行为,认为都有偷盗的意念和动机,并规定处以刖足的刑罚[9]。到了秦代 ,本来属于最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如偷采桑叶的行为,秦律也规定行为人必被处以强制 服劳役三十天的刑罚[13](《法律答问》)。类似这种民事侵权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处 以刑罚制裁的规定,在以后的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以至于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的 法律而尤其是刑法典的规定里面可以说是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太平御览》卷411记 载西汉有一个叫董永的人“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 还君,当以身作奴。’”[14]汉代这种允许将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债务人沦为债权人的 奴隶的法律规定,实质上是对民事违约行为采用了刑罚处罚的制裁方式。这种以人身作 质押、以劳役抵偿债务或者将债务人沦为奴隶的做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上仍有规 定[15]。《唐律·杂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 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6](《杂律》) 这种对于不能按时偿还到期债务的行为,采用笞刑惩治债务人人身、要求其偿还债款, 而不是强令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交纳滞纳金并偿还债款的制裁方法,被以后的宋、明、 清代的刑法典所沿用。
对于行政违法行为,历代法律也都追究了刑事责任并处于刑罚制裁。早在夏朝的法律 上就曾规定:“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14]商代制定有具有行政法律性质 的《官刑》,对于官吏违纪与失职的行为如“巫风”、“淫风”、“乱风”等,一律给 予刑罚制裁[7](《尚书正义·商书·伊训第四》)。西周则有类似于后世行政法规大全 性质的吏典《周礼》,它一方面规定了国家机构的设置、职责、官员的选拔标准、程序 、考核、黜陟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了以墨、劓、剕、宫、大辟 为内容的刑罚体系和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制裁方式。秦代一方面制定了《置 吏律》、《除吏律》等十余种单行行政法规,另一方面对于行政违法行为均采用了刑罚 处罚的制裁方式,如规定管理饲养耕牛工作的官员在考核时被评为最低等级即“殿”, 则要被处于“笞三十”的刑罚[13](《秦律十八种·厩苑律》)。汉朝基本上继续沿用了 秦代的行政法规和刑罚制裁方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部分刑法典和隋朝的《开皇律》 都规定了《违制》律,唐五代宋元的法典也都有《职制》律,明清的法典则专门设置有 《吏律》,这些都是兼有刑事法和行政法色彩的篇目,且它们对于行政违法行为,基本 上都采用了刑罚处罚的制裁方式。《唐律·职制》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 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 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诸在官应直不直,应宿不宿,各笞 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6](《职制》)。以后宋、明、清的刑法典与唐朝一样都规 定了国家官员的“署置过限罪”、“不应置而置罪”、“应值不值罪”、“应贡举而不 贡举罪”和“贡举非其人罪”等这些本来应该由行政法规范并由行政制裁的行为。
总之,由于中国传统文明起源条件、发展途径的特定性和特殊性,农业经济结构的单 一性,社会组织结构的宗法性,国家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性,国家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性 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古代刑法典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呈现出上述特点。这些特点体 现了“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1](《晋书·刑法志》)的立法宗旨, 贯彻了明刑弼教、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法制指导思想;对于巩固君主专制统治,调整 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维护历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起到了异 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特点反映出古人在刑事法律方面重视对于立法、司法尤其是法典编 纂体例、结构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具有高超的立法技术和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对 刑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总结和高度概括,便于刑事法律的宣传与适用以及人们对 于刑事法律的了解、理解、遵守和执行。这些特点对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的形成,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第一,影响了清末法制改革中近代意义刑法典的制定;第二,限制和阻碍了民事 、行政、经济、程序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等部门法理论在古代的深入研究和系统发展,阻 止甚至扼杀了这几种法律规范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独自成典了;第三 ,严重制约了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法律责任类型以及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等法律制 裁类别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同时也使刑事责任和刑罚制裁的研究停滞在简单、直观、 形象思维的阶段,至于宪法责任和宪法制裁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更是难以想像 和无从谈起的;第四,影响了多元一体法律体系的形成,使闻名世界的中华法系具有明 显的刑法特征;第五,使古代中国形成了程序与实体不分、先实体后程序、重实体轻程 序的立法传统和执法、司法作风,而这些传统和作风对于近现代乃至于当代的中国可以 说已经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重大的消极影响,当然也严重减弱了人们对于程序正义理论 研究的重视程度;第六,使社会成员养成了“泛刑法”、“畏刑罚”和违法与犯罪不分 、违法等于犯罪的法制观念,这一方面使国家的执法、司法官员在处理政务、审判案件 时,实行简单粗糙、官僚主义甚至蛮横无理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另一方面使老百姓 畏法如虎、谈法色变,形成了厌讼、惧讼、息讼的无讼心理;第七,使社会成员形成了 国家本位、集体本位、义务本位的法律意识和顺从、服从、盲从的懦弱心态,而不可能 滋生和形成自由平等民主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这必然对近现代法制观念 的形成和当代法治社会的建立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2-09-17
标签: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法律特征论文; 古代刑法论文; 实体法论文; 程序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