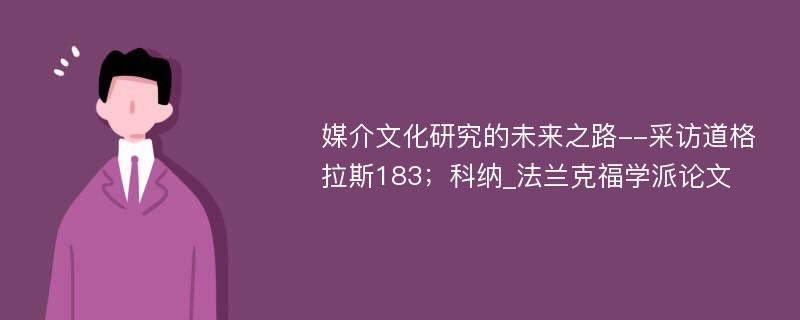
媒体文化研究的进路——道格拉斯#183;凯尔纳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道格拉斯论文,访谈录论文,媒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1943年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乔治·奈勒教育哲学讲座教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凯尔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媒体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他试图整合德国与法国的哲学传统,提倡一种多视角文化研究方法,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同时,也建构批判的媒体文化理论。其在媒体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波斯湾电视战争》、《电视与民主危机》等。本刊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王蔚博士对其进行访谈,在邮件往来基础上改定本文。 王蔚 凯尔纳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我曾在学生时代阅读了您关于媒体文化的相关著作,对您的批判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您是著名的批判理论家和文化分析学者,对中国的文化批评界具有很大影响。您的学术思想和专论也经常见诸学术刊物。相信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中国学者希望和您深入交流。 凯尔纳 我也很高兴!我曾经到过上海、南京、香港和台湾。我一直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国际顶级电影中的中国电影印象深刻。 一、碰撞与融合:走进欧陆哲学 王蔚 您的学术履历很清晰地表明,您早前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以及后现代理论,尤其在马尔库塞研究方面著述颇丰。那么,您一开始是如何进入这些研究的?是什么特别的原因让您对马尔库塞的理论倍加重视呢? 凯尔纳 我于196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那时我对哲学的热情主要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上。尽管我当时并未对学生运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好应对准备,但还是在新左派运动中非常活跃,时常参加反战示威游行。事实上,为表达反对越南战争,遍布全美以及欧洲的学生运动已经占据了大学的楼宇甚至校园。1968年5月的巴黎,看起来像是即将爆发一场新的法国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事件,我重新阅读了马尔库塞的著作。随着我对学生运动的兴趣与日俱增,且更多地参与其中,到1969年《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一文发表时,我对马尔库塞的著作以及学生运动的哲学基础都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到了1969年,一些学生欲将1968年的游行示威故伎重演,但学生们在短时间内被驱散,整个活动很快以失败告终。部分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成员幻想破灭,继而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地下气象组织(the Weather Underground)。几次爆炸事件之后,地下气象组织的头目开始真正转入地下。同年,马尔库塞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次座无虚席的夜间演讲。哲学系在第二天为其举行了一场宴会,由于哲学系教员无一参加,哲学系研究生获得了与其面对面交谈的好机会。宴会上,他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弗莱堡跟随海德格尔学习的经历,并开玩笑说他听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已经成为石头,以此讽刺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的保守。一小时后,马尔库塞提议到西尾酒吧小酌。那里曾经是金斯伯格、凯鲁亚克及“垮掉的一代”出没的地方,也是我晚餐和小酌常去的地方,所以我乐于陪同他一起穿越校园,前往酒吧。半路上,一些激进分子冲着我们喊道:“我们要跟马尔库塞辩论!”我认出他们是地下气象组织的成员,常在哲学图书馆学习。我和朋友们也经常去哲学图书馆,曾跟一些更为激进的民主社会学生会及地下气象组织成员有过数面之缘。于是,我们在哲学图书馆附近席地而坐。那些激进分子告诉马尔库塞,他们正在计划烧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办公室,这位教授正在做有关美国政府介入越南事务的研究,因而在学生中非常不受欢迎。马尔库塞强烈反对他们的计划,他认为大学是个乌托邦,激进分子可以在其中学习、组织、甚至采取某些行动,而校园犯罪必将招致警方镇压,这将伤害左派。 王蔚 从您的描述看来,马尔库塞虽然认为激进分子是革命者的一部分,但他鲜明地反对暴力。 凯尔纳 可以这么说。就在这一年,我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德国政府机构的资助下开始撰写学位论文——《海德格尔的真实概念》(Heidegger’s Concept of Authenticity)。我选择在图宾根大学继续研究这个课题。图宾根是德国西南部一个充满了激进主义气息的小镇,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及其他杰出人士曾在此治学,是个研习德国哲学传统的好去处。在图宾根大学,我阅读了许多哲学著作,包括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著作。同时,我还参与批判理论学习协会的活动,参加了恩斯特·布洛赫研讨班,讨论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以及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话题。从布洛赫那里,我意识到哲学是一门高度政治化的科学,而政治也同时需要哲学分析及批判。 在我的海德格尔研究临近结束时,我读到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还发现了一些早期马尔库塞评论老师海德格尔的文章。文章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建议将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结合,以克服传统中的局限性。我认为,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很具说服力,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结合的提议也非常有吸引力。同时,在彻底研究了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之后,我对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奥特(Heinrich Ott)等人著作中揭露的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也就不那么意外了。 在德国学习的两年中,我基本完成了关于海德格尔的学位论文,并建立起了良好的德国哲学基础。那之后,我开始对法国哲学和文化感兴趣,并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法语能力。1971—1972年间,我在法国巴黎停留了13个月,其间专攻法语及法国哲学,并完成了我关于马尔库塞的著作的初稿。至今,我对马尔库塞的著作仍然非常感兴趣。 王蔚 马尔库塞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他强烈批判了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对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这种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应用与发展在中国影响很大。您刚才提到的其他重要著作,在中国也被广泛阅读,并应用于阐释现实。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大众文化逐渐占据了人们文化生活的中心。从那时起,学界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应用于大众文化批判就越来越常见了。事实上,包括福柯、德里达、巴特、波德里亚等人在内的法国哲学思想,都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批判中获得深入阐释。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哲学思想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却显示了共通之处。以您在法国期间的学术体验,是否更深切地体会到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凯尔纳 在巴黎期间,我有幸听到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勒兹及利奥塔的授课,并阅读他们最新的著作。同时,我还阅读了波德里亚、德里达及其他著名哲学家的文章。福柯授课时喜欢在安静昏暗的礼堂里照着笔记本宣读,让人感觉仿佛置身教堂一般。列维-斯特劳斯比较有活力,也非常友善。德勒兹则更为活跃,喜欢用潦草的板书在黑板上表达他的主要思想。在197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会议上,我目睹了德勒兹在黑板上演示现代分析思想与块茎思想的对比。利奥塔是一位极具吸引力的教授,总是穿着蓝色牛仔裤,叼着香烟,跟学生谈论时事,拿政治取乐,然后开始讲康德或其他哲学理论。他的课通常没有笔记,只是让学生参与讨论,这在当时的法国是非常少见的。 最初,我认为德里达的著作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种奇妙版本,而福柯、波德里亚及利奥塔的著作则是以当代批判哲学和社会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的一种拓展和补充。在当代德国和法国哲学思想中,我看到它们的共通之处,即尝试将马克思、弗洛伊德与批判哲学融合,而忽略了今天它们之间显示出的许多明显分歧。因此,哲学对我来说并不是简单地在德国哲学或法国哲学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借助此二者以形成新的融合。 王蔚 您和马尔库塞深入交流,在图宾根研究德国哲学,在巴黎亲耳聆听法国思想家们的授课,这些已成为难以复制的学术经历,实在令人羡慕!那么,您早先发表的文章,是否就是对这些精彩的学术经历的总结? 凯尔纳 有一定关系。在即将结束欧洲三年的学习时,我邂逅了一本相对较新的致力于激进理论的期刊《泰劳斯》(Telos),我很高兴看到,美国有这样一群人对我曾在欧洲学习的欧陆哲学理论同样感兴趣。所以,我给期刊编辑保罗·比克尼(Paul Piccone)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对这份期刊很感兴趣。他很快就回复,让我帮忙介绍并翻译马尔库塞的《论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这篇翻译刊登于1973年夏天的第16期杂志上,是我首次发表的文章。大概也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新德国批评》的编辑。因为他也在同一期《泰劳斯》发表了文章,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有了联系。之后,我在1974年冬天出版的第4期《新德国批评》中发表了一篇名为《重访法兰克福学派:对马丁·杰的辩证想象的批判》(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A Critique of Martin Jay’s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的论文。在这篇回顾式的长篇论文中,我阐述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的基本看法,以及我与马丁·杰的哲学思想的不同。 王蔚 德、法哲学家们的思想和著作,甚至他们个性鲜明的批判气质,被您“融合”为宝贵的学术资源。这体现在您后来许多关于德国、法国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中,也体现在对于媒体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中。您有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是否能对您的学术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凯尔纳 在德国和法国学习的三年时间里,我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源,才得以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创作出一系列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和当代法国哲学思想的文章、评论和专著。我撰写的关于批判理论的著作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危机》(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1984),《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Critical Theory,Marxism,and Modernity,1989)及《批判理论读本》(A Critical Theory Reader,1989,与史蒂芬·布朗纳合著);还有《卡尔·柯尔施:革命理论》(Karl Korsch:Revolutionary Theory,1977),《激情与反叛:表现主义的遗产》(Passion and Rebellion:The Expressionist Heritage,1983,与史蒂芬·布朗纳合编),《后现代主义/杰姆逊/批判》(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1989),以及许多其他讨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著述得益于我在德国及其后的研究经历。我与史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合著的两本著作《让·波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其他》(Jean Baudrillard: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1989)和《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我自己撰写的《后现代主义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1997),也都得益于我在法国及重返法国与德国的那些年里对法国理论的研究。 二、媒体文化的确认:技术与文化新批判 王蔚 您在《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下简称《媒体文化》)、《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媒体奇观》)两本著作中的理论主张,对当代媒体文化研究极具启发性,也确立了您在媒体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从批判理论的研究转向了媒体文化和媒体奇观的研究呢? 凯尔纳 我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涉猎文化研究,至今仍然活跃在这个领域之中。大概在1976年,我给时任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斯图尔特·霍尔写信,询问关于他的著作及项目的相关情况。当时,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鲜为人知。霍尔给我的回信一共三页纸,还寄来了传说中他们中心“用模板印刷的文章”,我的媒体研究小组把它们读了个遍。由于我的研究涉及哲学、社会理论及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我后来撰写了一系列综合类型的文章。1983年夏天,我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厄巴纳出席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文化机构举办的会议,会上遇到了霍尔。霍尔是一个非常活跃、大方、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家。我听了霍尔、佩里·安德森、杰姆逊在会前的暑期班课程。这次的暑期班和会议让人十分兴奋,其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讨论对我接下来数十年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会议也真正向美国学术界阐述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 20世纪80年代,我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媒体文化,媒体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通过商业广告及宣传)影响我们的经济,影响我们日益媒体化的政治(罗纳德·里根是当时的总统,因此当时的政治中,有些部分是作秀、形象工程和奇观),影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在逐渐转变为媒体文化,所有的文化形式都由媒体直接或间接地建构(比如,我们通过媒体了解到歌手或音乐的流行程度)。这个想法影响了我未来数十年的研究。 这种观念部分源于麦克卢汉。他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一书中说道,伴随着新的媒体形式,我们将有新的文化形式、感官体验和日常生活。这种观念也同时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产业观点的影响,即资本与技术正在催生一种能够支配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所有生活方式的综合事物。后来我更赞同葛兰西的观点,即文化是一个争夺的领域,而非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是支配与操纵的工具。在那个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观点也是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者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媒体理论的观点。 因此,我开始研究一种媒体与技术的批判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表明的观点有两方面:其一,媒体作为工具被用于权力、统治和社会控制;其二,如何将媒体用于抵制霸权,如何将媒体用于提供新的教育模式、政治模式及交流模式。同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媒体的强大,无处不在、极其迅速的扩散能力,想要真正完全了解媒体的复杂、奇特和不可思议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一直对后结构主义的媒体理论保持开放的原因)。 王蔚 虽然您认为完全了解媒体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您的许多观点对我们具有启发性。在《媒体文化》中,您强调了“媒体文化”的概念,从而取代了学界常用的“大众文化”,利用批判理论建设了一种批判的大众文化研究。在《媒体奇观》中,您在后现代语境中继续推进了媒体文化的思想,通过具体的媒体奇观个案,展现了“诊断式批评”的研究方法。您能否多谈一谈您关于媒体技术与媒体文化的一些主要观点? 凯尔纳 如前所述,我一直尝试将德国与法国的传统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将他们对立起来。这样的想法促使我与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共同出版了《摄像机政治: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Camera Politica:The Politics and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Hollywood Film,1988)。这本书的初衷是结合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方法,对好莱坞电影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莱恩和我都将电影视为一种新兴的、异常强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使当代的人们可以通过录像带租赁商店在家就看到海量电影,甚至建立自己的“电影资料馆”。后来,我在奥斯汀买了一台Betamax①录像机。我早就看到过关于这个产品的信息,知道那就是我做电影和媒体研究所需要的工具。在那个时候,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正风靡全美。我记得,作为第一批在奥斯汀使用有线电视和HBO产品的用户之一,我在HBO上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出租车司机》(马丁·斯科西斯导演,1976年),这也是我最早录制和仔细研究的电影之一(后来,我把录下来的这部电影用于课堂,和学生们反复讨论其中的场景。因此,磁带录像机成了教学和研究的工具,也成了一种乐趣)。当然,我的录像机不久就被各类VCR取代了。我就像那些一开始购买计算机的消费者一样,遵循着淘汰的轨迹,每年都更换设备。 王蔚 既然您认为电影是一种新兴的文化形式,同时您又认同葛兰西的观点,那么您应该会认为,电影也是一个争夺的领地吧? 凯尔纳 是的。在撰写《摄像机政治》一书的过程中,我和莱恩一致认为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性别、阶级、种族、性等在其中展开政治斗争,同时,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都被转码,我们的著作也因此得名。我们看到,那些主流的电影类型、导演和具体影片,将当下社会和政治的斗争与情感等进行转码,通过他们的解码和阐释,提供当下的观点,以及主流的想象、恐惧、希望和梦想。 王蔚 与电影相较,电视更为大众化,从而成为媒体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您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电视媒体的研究成果,其中您将批判的着力点放在了电视媒体与民主问题的关系上。能否谈谈您对于电视文化批判的一些观点? 凯尔纳 我在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撰写了两本关于电视媒体的著作,分别是《电视与民主危机》(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1990)和《波斯湾电视战争》(The Persian Gulf TV War,1992)。这两本书借鉴了德国和法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但试图通过具体研究美国电视媒体,重新思考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批判问题。《电视与民主危机》中谈到,在里根时代,电视媒体是有力的统治工具和权力工具。这一时代,资本、形象工程和奇观在社会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随后制造了民主危机。我借助结构主义的经济模式、国家模式和媒体模式,提出大公司即将控制整个国家和媒体的观点。民主社会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而媒体以“第四种权力”的身份出现,起到监督与制衡作用。媒体可以批评权力滥用和腐败,提供参与观点和参与形式。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巨头公司通过控制媒体尤其是电视,借助商业广告以及大肆渲染消费、娱乐社会等手段,为公司本身谋取利益,同时大力支持代表其利益的政党。也是在同一时期,正是里根和老布什为富人提供了税收减免、放松管制,以及任何为减轻负担和筹集政治资金所需要的政策。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分歧,但是里根和老布什的政治体制极大地促进了大公司的利益,无情地忽略了普通人、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 我在《波斯湾电视战争》一书中提到: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是直接针对伊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的。当他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精心策划了一场电视战争,用以提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和霸权,证明美军是全球军事力量中的佼佼者,帮助老布什从再次竞选中受益。尽管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之后获得了90%的支持率,看起来在竞选中也稳操胜券,但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新星,被誉为“希望之子”的比尔·克林顿,最终击败了老布什,赢得1992年大选。肮脏的海湾战争就此宣告结束,整个战争以及军工行业耗费的数十亿美元显得毫无意义。在这次战争中,媒体扮演着啦啦队长的角色,它将老布什政府和当时五角大楼的一切谎言和宣传传达给民众,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从而获取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这一切看起来如同一场体育盛事,公众如同主队的啦啦队。此次事件的整个过程,无不揭露日益恶化的民主危机、主流媒体的腐败,以及媒体在推动主流政治和企业精英所推崇的议程时表现出的惊人能力。 王蔚 您在《媒体文化》一书中提出:这是一个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时代,您用融合的哲学理论批判了前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文化现象。新千年之后,尤其是近十年来,媒体技术及媒体文化的发展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您的哲学批判又应当如何展开? 凯尔纳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将哲学和批判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和分析的工具,而这些武器和工具均可应用在实际的事件和问题中。因此,哲学不应该被当作供人膜拜的抽象教条,而应该作为一种应对当代问题和事物的方法。最好的大陆哲学是批判的和对话的(如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等)。大多数思想家通常会借鉴先贤富有创造性的元素,摒弃不再实用和不相关的部分。因此,我认为哲学是辩证的。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杜威、葛兰西和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哲学会将新的理论和思想纳入其理论和批评资源中,在社会存在、文化和观念等不同领域间制造联系,展示实体社会和观念世界的主要矛盾,摒弃某些令社会、政治和文化现实受到压迫的思想和批评,提供理论与政治之间新的融合。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说法,哲学可以在当下明确指出事物之间的区别、事物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同时,哲学抵制具体分析中的任何完整的、确定的或者封闭的概念,因为历史总是敞开的,会一直经历新的解释和新的事件。正如鲍勃·迪伦所说,时代一直在改变。 王蔚 时代一直在变,一个重要的变化维度就是由技术驱动的。今天,伴随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新媒体时代,带给我们更多需要认识和处理的媒体文化问题。 凯尔纳 21世纪,博客、维基百科、Facebook以及其他新兴媒体和社交网络媒体,如YouTube和Twitter,进一步扩大了原本就无处不在的媒体矩阵。媒体奇观的政治经济和传播技术造就了有线和卫星电视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媒体等新科技的爆炸性使用紧随其后。互联网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不断扩大的新媒体和社交网站表达观点,传递新闻和信息。如果你能够负担得起并懂得使用的话,其他的新技术会使每一个人成为奇观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无论是好莱坞或政坛的明星,还是埃及、突尼斯的网络行动者,又或是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都可以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媒体奇观,参与到今日的媒体奇观中来。比如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动乱,欧洲抵制全球资本的运动,以及2011年全球范围大规模爆发的“占领运动”。所有这些,在我最近出版的《媒体奇观与暴动,2011:从阿拉伯动乱到占领天下》(Media Spectacle and Insurrection,2011:From the Arab Uprisings to Occupy Everywhere,2012)中都有涉及。 三、媒体奇观与多视角分析:重构互联网语境下的媒体文化批判 王蔚 您在《媒体奇观》中谈到,克林顿/小布什时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过去十年看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和跨国集团奇观的完全胜利。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互联网几乎入侵了全部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社会力量的分布格局,也翻开了控制与抵抗、合作与竞争新的一页。这使得国家和媒体企业对于互联网重要性的认识超越了以往任何媒体。那么,从宏观层面来看,您怎样理解近十年美国甚至世界媒体文化的变化? 凯尔纳 与国家和媒体企业相较,互联网和新媒体为公共领域的民主振兴赋予了潜力。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使更多的受众更轻松地获得信息。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信息传播工具相比,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信源更为广泛。它不停地揭示海量资料,毫无遗漏地表达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观点,持续不断地提供新闻和意见,以及多样化与差异化的资源。此外,互联网有益于实现双向沟通,有益于实现民主参与公共对话,有益于实施那些生产民主政治至关重要的基本行动。 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矛盾在于,至少对于有线世界和不断增长的大规模公众而言,丰富多样的信息环境在不断扩大,这个信息环境由以下不同部分构成:广泛的广播电视网络、印刷媒体和出版物,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建构的地球村。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单一媒介集中了更为丰富多样的信息和娱乐资源。由于可以向全世界即时发送不同类型和信源的信息与图片,各地互联网越来越多地被各类进步和反对组织所利用。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的新闻和信息来自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和信息流通不畅的国家,或者来自美国媒体企业。这就在当代的信息获得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制造了一个显著差异。进一步来说,互联网是一个进步力量、保守力量、国家和企业的必争之地,他们必须使用技术去赢得彼此相悖的目标。 王蔚 互联网确实具备了扩大公共领域影响、推进民主实践的功能,用户对互联网交互性的活跃应用,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似乎使前互联网时代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消失了。那么在现阶段,您认为互联网促进民主的这种功能,究竟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发挥? 凯尔纳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还不是有线世界,许多人甚至不识字。各地居民获取信息和文化的方式各有不同,导致得到的信息类型和质量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正确理解信息和将其情境化的能力。 然而,民主需要的是能够掌握信息的公民和信息访问权,因此,民主是否可行,取决于能够不断寻找关键信息的公民,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访问和评价信息的能力,是否具备介入重要事物的公共对话的能力。这样,面对强大的企业势力和政治势力,媒体的民主改革和另类媒体的存在,对于振兴甚至保存民主计划而言至关重要。媒体如何能够被民主化?可以发展怎样的另类媒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世界各地当然有所不同。但是,没有民主的媒体政治,没有另类媒体,民主本身也不会生机勃勃地存在下去,大面积存在的社会问题也不会被解决,甚至都不会被关注。 另类媒体需要与进步的运动相联系,振兴民主,并结束目前保守力量的霸权。过去几年,在纪录片领域、数字视频和摄影、社区广播、公共开放电视、不断进步的印刷媒体、一直在增长的自由和进步的互联网和博客圈,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 王蔚 正像您提出的那样,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一样,也是充满竞争的领域。近年来,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运动甚至暴乱、战争中,互联网政治显示了越来越强大的正向与反向的影响力,也形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奇观。 凯尔纳 到2011年,北非阿拉伯国家动乱、欧洲抵制全球资本的运动和占领运动,都使用了新媒体、社交网络和媒体奇观,用以促进民主议程,推进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中东的专制独裁统治的运动。正如我在《媒体奇观与暴动,2011:从阿拉伯动乱到占领天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动乱、利比亚革命、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的暴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欧洲运动、占领运动,以及其他政治暴动,通过广电媒体、印刷媒体和数字媒体进行串联,攫取人们的注意力和情绪,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效应。2011年,或许就像1968年一样,成为社会动荡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些事件表明,媒体和媒体奇观是当下的一个必争之地,有时会有助于民主和进步运动,有时会支持资本家的权力和反动的议题。未来的政治斗争将转战媒体,因为媒体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正在成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王蔚 在您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辩证逻辑,辩证地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资源的洞见与局限,辩证地分析媒体文化本身的控制和抵抗等等。因此,您提倡一种多视角的研究方法,旨在形成更有穿透力的分析。在我看来,多视角方法也存在削弱单一理论的激进性、尖锐性与普遍性的可能,而您所强调的情境主义的理论研究取向,针对具体媒体文化案例进行的批判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又恰好可以回避多视角研究方法的局限。 凯尔纳 我一直认为,应该将哲学见解和方法应用到规模浩瀚的文化现象中。我的著作《媒体文化》,试图通过使用这些哲学与批判社会理论工具,将文化研究工作重新概念化。在文化研究中,我一直认为多视角方式结合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受众接受和媒体效果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这些不同的哲学立场,能够应用于对文化和政治现象的解读和批判,同时有助于推动一种批判的、多文化的、政治的文化研究。 有时候,对于分析如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等某一视角下的具体现象,使用多视角的方法恰恰非常有价值。由于人们可以从多种立场做激进的批评,因此,在分析和批判具体现象时引入更多的批判性理论,将使我们的工作更为有力。 王蔚 您的批判大多围绕美国的媒体文化现象展开,但正如您所说,美国的媒体文化正在影响全球化的消费者。在互联网时代,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理论话语层面,技术资本主义的影响都是跨越地域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您认为美国媒体文化与其他媒体文化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凯尔纳 美国媒体文化长期以来是全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电影、音乐、文学和时尚领域。但和历史情况相比,今天的全球文化更容易使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得以传播。 四、媒介素养教育:媒体文化批判的一种实践 王蔚 从您的著作中,我感觉到您是一个温和的批判家,感觉到您对解决媒体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媒体文化中呈现出的抵抗的积极性,抱有乐观的态度。如果说今天的奇观思维依然在主导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么您认为媒体文化研究本身可以在这个议题上发挥怎样的作用? 凯尔纳 由于媒体文化的不断扩展,在媒体和文化研究方面总是会有更多事情可做。我自己近期的工作中就包含了媒体和技术素养研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作为乔治·奈勒教育哲学讲座教授已逾十五年。我曾重点研究与教育、政治和日常生活相关的新技术,也一直关注哲学、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教育工作中,我一直特别关注素养概念的扩展,以容纳媒介素养和多重的技术素养。随着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迅速发展,谈话广播和广播频道也在膨胀,他们都成为互联网吸纳的视频、音频、图像的文化奇观,作为新媒体和新技术不断扩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是媒体文化,媒体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化工具、政治教化工具和意义与认同的来源。 王蔚 您在《媒体文化》一书中谈到过媒介素养教育,这非常具有启发性。或许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媒体文化批判的一种具体实践,视为理论教育影响社会生活的一条有效路径。 凯尔纳 我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媒介素养。在20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任期内,我曾得到一大笔资金,用于为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高中的低收入教师讲授媒介素养课程。授课持续了几个月时间,这些课程可以让他们教育学生批判地阅读并解码媒体信息,包括性别、阶级、性和种族的表征,帮助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在寻找正面的形象、意义、角色榜样和媒体策划的同时,也能够辨别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阶级歧视者和其他媒体中的负面表达。在德克萨斯州,我设计了一个名为文化传播哲学的课程,介绍媒体理论、文化研究,并讲授批判的媒体素养,旨在推广媒体所有权和媒体策划的知识,讲授文本分析、媒体权力的前沿理论,以及在政治、教育、社会转型中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另类媒体使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将这门课程转变为一个文化研究导论研讨会,使用我的著作《媒体文化》和与吉吉·达拉姆(Gigi Durham)合编的《媒体与文化研究:关键作品》(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Key Work,2001),后者汇集了当代媒体文化和传播方法的主要内容,范围从罗兰·巴特到居伊·德波,再到最近关于YouTube、Facebook和社交网络的研究。 王蔚 在中国,媒介素养相关研究约在2000年开始兴起,目前也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有些观点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致力于缩小“数字鸿沟”,创造“数字机遇”。而您所描述的媒介素养教育,则是从媒体文化批判的立场,强调加强对媒体文化的深入理解,这一点令人深思。 凯尔纳 当我20世纪90年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和新的数字技术大大改变文化、意识和日常生活。我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研讨班,探讨技术和新媒体问题。在此期间,我在《教育理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媒体和新素养的论文。同时,其他相关的论文和著作还包括一系列互联网与政治的研究,以及新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的研究。我认为新技术需要新的素养,拥有技术素养不仅涉及懂得如何使用计算机和新技术,而且涉及理解新技术和新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功能,理解他们是如何改变了传播、社会互动、学术研究、政治、文化和经济。 在探索如何在教育中应用新技术方面,我曾与我的学生为技术和社会、文化研究、教育哲学等课程建立了三个网站,此外还协助开发了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网站,这些都显示在我的主页上。我是最早建立网站的学者之一,我的文章甚至著作在刊发之后,都可以在我的网站上访问。我最终想要将这些研究汇集为一本著作,名为:《新技术与新素养:新千年的挑战》(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Literacies:Challenges for the Millennium)。 许多主流文献对于新技术往往不是赞美就是贬低,鉴于此,我计划对开发新技术的得失进行一次平衡的评估。当代教育的基础和源泉究竟是书籍还是电脑数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我将特别对这两个极端进行调解。我认为今天的教育应当以书本资料、新计算机和多媒体资料的平衡为基础。同时,我也认为传统的印刷文化素养、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技巧,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是,我们需要传授新的媒介素养,来作为既有技能的补充。 王蔚 日新月异的媒体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纷繁复杂的媒体文化现象。您曾提出,媒体文化不是构建某种像主体的东西,或者探究个人对主体的认同,而是要构建认同性以及主体性的立场。今天,各类新媒体一方面成就了令人惊奇的媒体奇观,开辟了一种文化控制与抵抗的新路径;另一方面,网民通过实名或者匿名的方式集结,进行社会事务的讨论、批判,甚至影响政府决策以及国际政治。其中交织的各种权力关系、制度选择、身份认同,为人们理解和营造互联网时代的新的社会秩序带来障碍以及新元素。这些现象出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中,成为东西方共同面对的新问题。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媒体文化研究的历程,我相信随着互联网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您的相关研究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注释: ①Sony公司早期开发的盒式录像机,上市后引发了录像带租用业的产生。——采访者注标签: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媒体文化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媒体奇观论文; 哲学家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