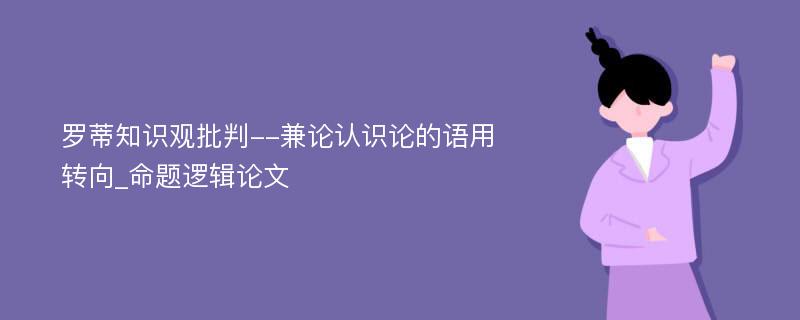
罗蒂知识观批判——兼论认识论的语用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知识论文,语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Rorty-Allen之争
罗蒂和Barry Allen之间关于认识论和人类知识的问题有过一场争论,(注:Cf.Barry Allen,“What was epistemology?”Richard Rorty,“Response to Barry Allen”,in Robert Brandom ed.Rorty and His Critics,Blackwell,2000,pp.220-241.)本文就从 这场争论说起。尽管罗蒂公然宣布了认识论的终结,Allen却认为,罗蒂对传统认识论 的批判实际上预设了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简单地说,传统认识论可以被描述为围绕着 “knowing-of”或“knowledge-of”为中心而展开,把知识看作是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而罗蒂的知识观则专注于“knowing-that”或“knowledge-that”,把知识看作是人 和命题之间的关系。罗蒂说:
洛克和一般17世纪的作家根本不把知识看作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是因为他们不把 知识看作是人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洛克不认为“knowledge-that”是知识的基本形式。 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他认为“knowledge-of”先于“knowledge-that”,因此把知识看 作是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注: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141-1 42.本文对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引述,参照了李幼蒸先生的中译本,但对译文有 所改动。)
和“knowledge-of”密切相关的,是传统认识论的表象主义、基础主义、辩护和因果 说明相混淆等特征。而“knowledge-that”则强调对信念的社会辩护、整体主义以及对 话等等。Allen认为,罗蒂对传统认识论的反驳以及对自己的立场的论证并不令人信服 。不仅如此,Allen还指出,罗蒂的知识观和传统认识论分有了一些共同的偏见:命题 偏见(把知识看作是有真假的命题)、信念加其他(认为知识是信念加其他因素)、商谈偏 见(把知识看作是可以在理性的商谈和对话中加以推理地辩护和反驳的对象),以及错置 的知识之善(即未能很好地阐明我们何以偏爱知识的问题)。在Allen看来,罗蒂的“命 题性的信念加其他的认识论所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商谈性的知识观。知识被限制在能经受 方法论的、逻辑的和对话的检验的命题。”(注:Barry Allen,“What was
epistemology?”in Robert Brandom ed.,Rorty and His Critics,Blackwell,2000,pp .229、228、232.)这种对知识的理解无法对知识的价值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由于不满 于罗蒂知识观对语言和对话的偏执,Allen提出了一种强调“knowing-how”或源始于“ knowledge-how”的认识论。他特别强调这种“knowing-how”或“knowledge-how”体 现在各种形式的人工制品(artifacts)当中:
认为知识必须是真的,或者认为知识的最重要的例证是命题性的这个预设,使得
knowing-that和knowing-how之间的差异大于它的实际所是。当然命题、句子、陈述都 是人工制品,在我们知道它们是真的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做成它们。而且,知道一 个命题是真的所需要的知识本身不是命题性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那样的,建立 在操作性的、有效的know-how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我们知道如何使用的人工制品(包括 但不限于概念性的、交往性的人工制品)之上。(注:Barry Allen,“What was
epistemology?”in Robert Brandom ed.,Rorty and His Critics,Blackwell,2000,pp .229、228、232.)
他的下述一段话说得更为明确:
如果你需要一个关于知识的明确的例子,不要考虑一个明显的真的句子。考虑一个显 然是复杂的人工制品,或者任何一种人们老练地、技艺高超地、出色地加以使用的人工 制品。正是行动的品质把知识和信念区分开来了,并且证明了是人工制品而不是句子或 信念,是知识的单位,是所有我们的知识实践及其结果聚焦的所在。(注:Barry Allen ,“What was epistemology?”in Robert Brandom ed.,Rorty and His Critics,
Blackwell,2000,pp.229、228、232.)
简言之,如果说罗蒂用“knowledge-that”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knowledge-of”, 那么,Allen的目标是通过强调“knowledge-how”对于“knowledge-that”的优先性, 以此来克服罗蒂的知识观。
罗蒂则这样回应Allen的批评:真正能够标识出人之为人的特征的,是“
knowledge-that”而不是“knowledge-how”:
当我们……仅仅谈论know-how的时候,属人的东西和非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就渐渐隐 去了。因为know-how可以顺着巨大的存在之链一直贯彻下去。(比方说,考虑一下那些 阴险狡诈的病毒)。当我们想要聚焦于属人的东西时,我们必须关注命题性的东西,开 始谈论knowing-that。这是因为,只有语言的使用者才具备那类知识。(注:Richard
Rorty,“Response to Barry Allen”,in Robert Brandom ed.Rorty and His Critics ,Blackwell,2000,pp.238、235.Allen承认这种联系,在注释中,他把Gilbert Ryle和
Michael Oakeshott与Wilfrid Sellas作了对照。)
罗蒂的意思是,仅仅聚焦于knowing-how,我们会看到人和动物之间的连续性,但要把 握人和动物之间的非连续性,进而把握人的独特性,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
knowing-that之上,忽略knowing-how。
面对罗蒂和Allen之间的往复辩难,笔者基本上站在Allen一边。Allen的论说与赖尔(
Gilbert Ryle)关于knowing-how和knowing-that的著名区分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注:Richard Rorty,“Response to Barry Allen”,in Robert Brandom ed.Rorty
and His Critics,Blackwell,2000,pp.238、235.Allen承认这种联系,在注释中,他把 Gilbert Ryle和Michael Oakeshott与Wilfrid Sellas作了对照。)knowing-how是一个 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具有不同的形式。显然,Allen强调的是一种技术性的、制作性 的knowing-how。在笔者看来,可以把Allen关于人工制品的一般理论看作一种试图复兴 古典的亚里斯多德式的“techne”观念的努力,以挑战西方哲学中根深蒂固的受“
episteme”支配的主流的知识观。我相信,Allen的努力会得到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劳动 生活研究中心(Swedish Center for Working Life)二十多年来出色的研究工作的强有 力支持。此外,我想指出,我们还可以诉诸伦理的know-how的概念,比如亚里斯多德的 phronesis来质疑西方传统主流的知识观。对此,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展开过详细的讨论 。(注:参见郁振华,《挑战西方传统主流的知识观——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Phronesis 》,《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在本文中,我想通过调动其他思想资源来支持Allen,反驳罗蒂,论证“knowing-how ”之于“knowing-that”的优先性。我认为,Allen的立场可以由关于人类知识问题上 的波兰尼式的进路和维特根斯坦式的进路而得到加强。
二、对罗蒂知识观的一个波兰尼式的批判
西方哲学知识观中的命题偏见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拉 凯斯篇》的主题是勇敢,篇中提到,苏格拉底说:“凡是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一定能够 言说”。(注: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5.133、137.)而拉凯斯 是一个著名的将军,他说:“我自以为我是知道勇敢的本性的,但是不知怎么地,它从 我这儿溜走了,我不能抓住它,说出它的本性。”(注:Plato,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5.133、137.)按照苏格拉底的标准,既然拉凯斯不能说出勇 敢的本性,他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注:关于传统知识观的命题偏见在希腊哲学中的起 源,我受到了挪威哲学家Harald Grimen的启发。Cf.Grimen,“Tacit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LOS center working paper,Bergen,1991.)认为知识 必须能够用语言来表达,不能言说的东西就不能算是知识,这种思想到了近代就发展为 波兰尼所说的“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the ideal of wholly explicit knowledge)。 伽利略认为自然之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到莱布尼茨的普遍语言的理想即其万能算 法,再到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命题导向对知识的理解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渐成为一 种主导性的看法。秉承维特根斯坦传统的挪威哲学家约翰内森(Kjell.S.Johannessen) 指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框架中:
知识和语言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知识应当有一种语言来表达变成了一种无条件的 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不能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知识的可能性,完全是不可理喻 的。(注:Kjell S.Jonhanessen,“Rule Following,Intransitive Understanding,and Tacit Knowledge”,in Essays in Pragmatic Philosophy,Ⅱ,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4-105.)
显然,罗蒂分有了这种对知识理解的命题偏见的。罗蒂和近代认识论的差异只是在于 如下事实:命题偏见在罗蒂那里是和对话主义(conversationalism)相联系的,而在近 代认识论那里,它是和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相联系的。
当波兰尼在1958年提出“默会知识”这个概念时,他的矛头所向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 命题导向的对知识的理解。他的名言“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和前述苏格 拉底的“凡是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一定能够言说”正相反对。
波兰尼说:“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地图和数学 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 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注:Michael Polanyi,The Study of 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12.)波兰尼把第一类知识称作明确知识, 也称言述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把第二类知识称作默会知识,也称非言述知识 (inarticulate knowledge)。默会知识不采取语言的表达形式,它是我们在行动中所拥 有的关于某事物的知识。作为一种内在于行动或构成行动的知识,默会知识就是赖尔所 说的“know-how”,它是指体现在认识和行动中的人的能力。因此,在许多场合,波兰 尼谈论的是默会能力。
人类在获得语言之后,智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把动物远远地甩在后面。可以说 ,人和动物的智力的分水岭在于语言的获得;人之于动物在理智上的优越性在于语言的 使用。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事实支持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我觉得,罗蒂认为只有
knowing-that或命题性知识才能标识出人之为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但是问题在于这并不全面。仅仅强调这一点,人类认识的一些重要方面就被遮蔽在黑 暗之中。在充分肯定人在理智上优越于动物是由于语言的获得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波兰 尼有力地证成了如下主张:在明确地得到表述的知识领域中,默会能力是主导性的:
我们毕竟能够阐明语言表达的巨大的理智优势,却一点儿也不贬低人的默会能力的优 先性。尽管人之于动物在理智上的优势还是由于他对符号的使用,但是,这个使用本身 ——以符号的形式对各类主题的积累、思考、再审视——现在被看作是一个默会的、非 批判的过程。(注:Michael Polanyi,The Study of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p.25、22、21、22.)
语言的使用是一个默会的过程。具体来说,这种使用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环节:即对于 语言符号的赋义和理解。缺乏这两个环节,明确知识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而这两个环 节都是默会的。一方面,“没有一样说出来的、写出来的或者印刷出来的东西,能够自 己意指某种东西,因为只有那个说话的人,或者那个倾听和阅读的人,才能够通过它意 指某种东西。所有这些语义活动都是这个人的默会活动。”(注:Michael Polanyi,The Study of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p.25、22、21、22.)各种符 号形式的意义是由认识者的默会认识所赋予的,如果剥去其默会的因素,所有的文字、 公式和图表等,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要真正实现明确知识还取决于我们对语 言符号的理解,而“对文字和其他符号的理解也是一个默会的过程。”(注:Michael
Polanyi,The Study of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p.25、22、21 、22.)数学公式、文字、各类图表等会传达各种信息,但是不会传达对这种信息的理解 ,“只有借助于他的这种理解行动,他的这种默会的贡献,接受者在面对一个陈述时, 才能够说获得了知识。”(注:Michael Polanyi,The Study of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p.25、22、21、22.)
所以,波兰尼的结论是:“默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确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 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一种完全明确的知识是 不可思议的。”(注:Michael Polanyi,Knowing and Being,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p.144.)婴儿和动物生活在纯粹的默会的领域中,成年的认识者则被赋予了 语言的手段。然而,甚至在明确知识的领域中,默会能力也是决定性的和主导性的。任 何一种明确知识都有其默会的根源。默会能力是人获得和持有知识的终极的机能。对于 知识的默会维度的揭示,瓦解了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和命题导向的知识观。而罗蒂尽管 口头上承认Allen的“知道一个命题是真的所需要的知识本身不是命题性知识”的主张 ,但还是拘执于传统的命题导向的对知识的理解,拒绝深入人类知识的非命题性的或者 默会的维度。
如上所述,罗蒂之所以拒绝承认knowing-how的优先性,是因为在他看来把人和动物区 分开来的是knowing-that而不是knowing-how。但是,这又是一个片面的观察。确实, 就knowing-know而言,人和动物之间确实存在着连续性,所以波兰尼能够把默会能力追 溯到婴儿和动物的非言述的智力。但同样真实的是,动物的knowing-how和人的
knowing-how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对婴儿/动物的纯粹默会知识与成 人的以语言为中介的默会知识作出区分:
公认地,我前面已讨论过的科学家的认识的技艺,和小孩的和动物的相比处在一个更 高的层次上,它只能和作为正规学科的科学知识一起获得。其他高级的理智技能同样也 是在持续的正规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的。确实,我们的缄默能力(mute abilities)随着我 们的言述能力的行使而增长。(注:Michael Polnyi,Personal Knowledge,Routledge,1 958,p.70.)
在波兰尼的阐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知识中缄默的东西和言述的东西、默会的东西 和明确的东西之间富有成效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产生了以语言为中介的严 格意义上人的默会知识。而罗蒂认为,专注于knowing-how我们只会看到人和动物之间 的连续性。与此不同,在波兰尼那里,就默会的knowing-how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人 和动物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非连续性:“地图、图表、书籍、公式等,为 我们不断地从新的角度来重组我们的经验提供了各种极好的机会。而这种重组本身,原 则上说是一种默会的行动,是和我们在前语言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环境获得一种理智的控 制的活动是相类似的,因此也类似于那种创造性的重组过程,新的发现就是由此而作出 的。”(注:Michael Polanyi,The Study of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p.24-25.)总起来说,一方面,重组我们的经验的默会活动贯穿于所有的层次(从 前语言的层次到语言的层次),因此我们可以谈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科学 家以语言为中介的认识技艺的创造性活动,和在前语言层次上的默会能力毕竟处在不同 的层次上,它们有质的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连续性。罗蒂只看到了前者,却没 有看到后者,所以他所拥有的关于人类知识的图景是不完整的。
三、维特根斯坦传统中的认识论的语用学转向
波兰尼关于默会知识的概念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所接受,并得到了进 一步的阐发。在关于默会知识的维特根斯坦式的研究进路中,挪威哲学家约翰那森是一 位领军人物。基于以实践为核心的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诠释,约翰那森提出了认识 论的语用学转向(the pragmatic turn in epistemology)的主张。
1980年代以来,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主题被认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 心。和Gordon Baker更着重于遵循规则的规则方面的诠释不同,约翰内森强调的是遵循 规则的实践方面:
遵循规则的活动远比所要遵循的规则丰富得多。在维特根斯坦对遵循规则的现象的分 析中,规则本身是最不重要的东西。正是遵循规则的活动本身以及如何确立它的同一性 才占据了他的兴趣的中心。(注:Kjell S.Jonhanessen,“Rule-Following and
Intransitive Understanding”,in Bo Goeranzon and Magnus Florin eds.
Aritifical Intelligence,Culture and Languange:On Education and Work,
Springer-Verlag,1990,p.40.)
要理解遵循规则的行为的实践方面,重要的是要看到规则及其应用的差别。维特根斯 坦认为,一条规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因此它不能决定它将如何被应用。但是我 们能否提出另一条规则,来规定前一规则该如何被应用呢?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是 一种无用的努力。因为对于第二条规则来说,同样的问题会再次发生,因此如果诉诸进 一步的规则来解决一条规则的应用问题,我们将陷于无穷倒退。一句话,一条规则的应 用不是由它自身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其他的规则所决定的。(注:关于约翰那森对维特 根斯坦思想的这一诠释的文本根据,建议读者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84、85、 86节。)约翰那森把这一论证的要旨概括为:“规则的应用原则上是无规则可言的。”( 注:Kjell S.Jonhanessen,“Rule Following,Intrasitive Understanding,and Tacit Knowledge”,in Essays in Pragmatic Philosophy,Ⅱ,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90,p.122.)
这里蕴涵着一种语用的意义观(a pragmatic view of meaning)。关键的问题是:是什 么赋予了语词以意义?是什么使得各种符号成为人类交往活动的意义载体?在维特根斯坦 看来,不是解释,而是实践决定了赋义活动。在讨论遵循规则的行为的脉络中,维特根 斯坦把解释界定为:“用对规则的一种表达来替代另一种表达。”(注: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lated by G.E.M.Anscombe,Blackwell,1967,第 201节。)约翰那森指出,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解释是有意识的理智活动,作出一个解释 就是构造一个假说。解释作为一个构造假说的理智活动不能决定意义。关于这一点,维 特根斯坦说得很清楚:“任何解释都和它所解释的东西一样悬在空中,而不能给它提供 任何任何支持。解释本身不能决定意义。”(注: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lated by G.E.M.Anscombe,Blackwell,1967,第198、201、202 节。)因此,如果认为根据规则行动是一个解释问题就会面临如下的困境:一方面,根 据一种解释,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行动符合某条规则;另一方面,根据另一种解释,我 们也可以使它和这条规则相冲突。这样我们将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这里既不存在符合 也不存在冲突。维特根斯坦走出这个死胡同的办法是:“这表明,存在着一种不是解释 的对规则的把握方式,它体现在我们所说的‘遵从规则’和‘违反规则’的各种实例中 。”(注: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lated by G.E.M.
Anscombe,Blackwell,1967,第198、201、202节。)这种非解释性的对规则的掌握,就 是行动(遵从规则或违反规则的活动),就是实践:“‘遵从规则’是一种实践。”(注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lated by G.E.M.Anscombe,
Blackwell,1967,第198、201、202节。)回到是什么赋予各种符号以意义的问题。我们 已经看到,解释不能决定意义。这是一个消极的结论。那么,积极地说,是什么决定了 语言符号的意义呢?维特根斯坦诉诸实践这个概念,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实践给予语词以意义。”(注:Wittgenstein,Remarks on Colour,edited by G.E.M.
Anscombe,Basil Blackwell,1977,第317节。)
语用的意义观和语用的概念观(a pragmatic view of concept)紧密相关。概念的本性 是什么?约翰那森认为,传统的对概念的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把概念看作是能够 完全用语言来表达的:“一个正当的、科学上值得尊敬的概念的确立,当且仅当我们能 够确定使用这个概念的语言表达式的充分必要条件。”(注:Kjell S.Johannessen,“
Action Research and Epistemology”,in 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Vol.1,No.2 /3,1996,p.292.)时至今日,一般逻辑教科书就是这么论述来概念的本性的。这种看法 受到了语用的概念观的质疑。语用的概念观强调实践在概念的形成和应用中的构成性作 用。它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我们对世界的概念性的把握并不完全体现在我们能构造正确 的关于世界的命题,在一个根本的意义上,它体现在某些形式的行动中。假如某人自称 掌握了一个概念,他必须被认为是包含了该概念的某些既定行动的一个胜任的实施者。 语用的概念观关于概念性把握的原则是:“一个给定的概念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世界的 把握,在根本上和最充分地是表达在实践之中的。”(注:Ibid.,p.293.)
某种实践的实施被认为是一个给定的概念的基本的表达模式。约翰那森用椅子概念为 例,来说明语用的概念观。对这个概念的掌握,与其说是体现在用语言来构造关于“椅 子”命题的能力之中,不如说体现在以恰当的方式和真实的椅子打交道的能力之中,比 如自在地坐在椅子上,把它们当作家具,如此等等。(注:Kjell S Johannessen,“
Knowledge and its Modes of Ariticulation”,in Uniped,Vol.22,No.3,2000.此文原 来是用挪威文发表的,这里引述的是此文的英译本。)
语用的知识观,和语用的概念观、意义观是一气贯通的。约翰那森指出,传统的命题 导向的知识观的一个重要预设是:“知识只有作为一种产品才是有意义的”(注:Kjell S Johannessen,“Knowledge and Reflective Practice”,手稿,2004.)。拘泥于把 知识看作一种成品,主流的知识观完全丧失了关于知识的过程视角(即把知识看作一种 嵌入在具有特定目的的人类活动之中的过程)。与此形成对照,语用的知识观强调了知 识的过程方面(注:在我和约翰内森教授的交谈中,他指出,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波兰尼 对人类知识的过程方面的重视和强调。):“采纳了过程视角的各种知识观通常被称作 是语用的——这个词来自希腊文pragma,它的一个涵义是行动。”(注:Kjell S
Johannessen,“Knowledge and Reflective Practice”,手稿,2004.)
在约翰那森看来,我们通过实践获得的关于实在的知识具有一个复杂的结构。他从语 用的过程视角出发,试图来刻画包含在人类知识中一些重要因素:
1.我们通过实践获得的对实在的概念性把握中用语言能够表达的内容(linguistically articulatable content)。就这种内容实际上能够用语言来表达而言,谈论命题性知识是正当的。它是对我们关于实在的实践性把握进行抽象所得到的产物。2.所实施的包含某种概念内容的实践的施行方面(performative aspect)。它构成了上述抽象的基础。约翰那森称其为知识的技能方面,或直接称之为能力知识(competence knowledge)。3.我们通过实践获得的对实在的概念性把握的熟悉性方面(familiarity aspect)。这是通过对概念化了的现象的特定接触才能够获得的。约翰那森称其为知识的熟悉性方面或者直接称之为熟悉性知识(familiarity-knowledge)。4.我们通过实践获得的对实在的概念性把握的明断的方面(judicious aspect)。在此,约翰那森指的是在知识的确立、应用和联结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判断力。
对知识的语用分析表明,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不只是一桩纯粹理智的事情。我们通过 实践获得的对实在的概念性把握,不能为命题所穷尽。像“在处理概念化了的现象的活 动中所包含的技能,我们对它们的反思性的熟悉——这种熟悉体现为我们对这些现象的 行为中的自信——,以及在特定情形下应用或者不用一个给定的概念的判断力”等因素 ,“都是和知识的确立相关的,但是它们自己不能被充分地和直接地用语言的方式来表 达”(注:Kjell S Johannessen,“The Concept of Practice in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Inquiry,Vol.31,No.3,1988,p.357.)。我们已经看到,语言可以 表达的方面,是对通过实践获得的关于实在的知识的非语言方面进行抽象的产物。能力 知识、熟悉性知识和判断力是命题性知识的前提,它们使得命题性知识成为可能。约翰 那森说:
命题性知识不能独立于知识的其他因素而获得。一整套的东西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在导向知识形成的所有情境中。……命题性知识根本不能在缺乏 能力知识、熟悉性知识和某种程度的判断力的情况下确立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把 下面这句话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所有的命题性知识都建立在能力知识、熟悉性知识和判 断力这个不可避免的基础之上。(注:Kjell S Johannessen,“Knowledge and its
Modes of Ariticulation”,in Uniped,Vol.22,No.3,2000.)
约翰内森接受了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这个术语,用它来指称通过实践获得的对实在 的概念性把握的那些非语言的方面。在另一个地方,在讨论掌握自然语言的问题时,他 对上述语用知识观的洞见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掌握语言的活动比起能表达为一个规则体系或者一个命题体系的东西要更为丰富 。这种默会的、“剩余的”知识正好体现于在所有语境中应用或者避免应用语言的行动 之中。……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认识到如下推理是一个有说服 力的论证:因为命题性知识本质上是语言的,因为默会知识体现在所有掌握语言的活动 中,所以,命题性知识本质上依赖于默会知识。(注:Kjell S Johannessen,“Action Research and Epistemology”,in Concepts and Transformation,Vol.1,No.2/3,1996 ,pp.294—295.)
不难看出,约翰内森从维特根斯坦传统出发所得到的关于人类知识问题的这个结论, 和波兰尼关于明确知识的默会根源的主张并无二致。
四、结论
总结本文的讨论,笔者想强调下面两点:
首先,在关于人类知识问题的讨论中引入默会维度,揭示了对知识的理解中传统的完 全明确知识的理想或者命题偏见是片面和肤浅的。命题导向的知识观的不充分性,在于 它看不到明确知识的默会根源,进而看不到人类知识中明确的东西和默会的东西之间复 杂的动态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把认识论的研究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同时也只是 触及了知识问题的表层。当罗蒂强调knowledge-that的核心地位并且拒绝承认
knowledge-how的优先性时,他事实上还是陷于传统知识观的命题偏见的窠臼之中,因 此无法逃避上述批评。
其次,引入默会维度,并不是要在知识问题的讨论中引入神秘主义。要明确这一点, 考察一下与人类知识相关的三个层次也许是有帮助的:心理的层次、语言的层次和实践 的层次。默会知识不是心理的、主观的、私人的东西。默会知识常常是个人知识,但是 个人的(the personal)不同于主观的(the subjective),这是波兰尼的巨著《个人知识 》要证明核心命题之一。在波兰尼那里,主观的意味着私人的,而认识者的个人的参与 ,则是“一种主张普遍有效性的负责任的行动。在与一种隐蔽的实在相接触的涵义上, 这种认识确实是客观的。”(注:Micheal 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p.vii.参见郁 振华:《克服客观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1期,以及YU Zhenhua,“
Two Cultures Revisited”,in Tradition and Discovery-Polanyi Society
Periodical,Vol.28,No.3,2001—2002.)在严格的意义上,默会知识是指由于逻辑的理 由而无法充分地用语言来表达的知识。(注:在关于默会知识问题的讨论中,维特根斯 坦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强的默会知识论和弱的默会知识论作了严格的区分。参见 Grimen,“Tacit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LOS center working paper,Bergen,1991,Kjell S Johannessen,“Knowledge and its Modes of
Ariticulation”,in Uniped,Vol.22,No.3,2000,郁振华:《从表达问题看默会知识》 ,《哲学研究》,2003年第5期。)在一些情况下,当我们谈论默会知识时,比如在对技 能(skill)和鉴别力(connoisseurship)加以分析时,我们会撞上语言的界限。默会知识 这个概念标识出了语言表达的不充分性,而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知识,却可以用非语言 的方式来表达。在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广义的表达概念,不仅包括语言的表达,而且 包括非语言的表达。在各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中,我们要强调的是行动。正是在这里, 实践的概念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不能说的东西可以通过做来显示。这里没有任何神秘 的东西,因为行动的领域和语言的领域一样是公共的、透明的。简言之,在我们的概念 地图上,默会知识的概念既不在心理的层次上,也不在语言的层次上,而是在实践的层 次上。这就是认识论的语用学转向的意义所在。
在这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中,本文着重于后面两者,即语言的层次和实践的层次。认 识论的语用学转向指向了这样一种知识论,它试图公正地对待这两者。从语用的角度来 讨论默会知识,无意于贬低语言在人类知识中的重要性,它的目标是要在人类知识的整 体性结构中为明确知识或命题性知识寻找正确的位置。笔者认为,可以把波兰尼和约翰 内森所勾勒的关于人类知识的图景称为一种“厚实”(thick)的知识观,而把传统的命 题导向的对知识的理解称为“单薄”(thin)的知识观。显然,罗蒂所拥有的是一种商谈 的、对话版本的“单薄”的知识观,而以强调内在于行动的洞见或者通常所说的默会知 识为特征的“厚实”的知识观尚在他的视野之外。认识论的语用学转向,就是旨在克服 这种“单薄”的知识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