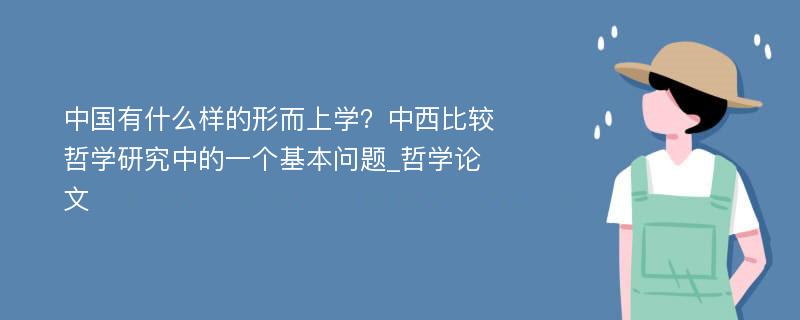
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中西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的两大潮流。这一潮流在学界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比较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上。哲学研究也处在这一潮流之中。哲学包括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分支。在这些分支中,形而上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地位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形而上学是哲学唯一真正与其它学科相区分的特征。因此,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课题。
与所有比较研究一样,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或者自我取消,或者自我发展。如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或西方根本就没有形而上学,比较就失去对象;如果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都有形而上学,而且是相同的,比较就失去意义。在这两种情形之下,这一研究自我取消。要是研究结果发现,中西都有形而上学,而且存在不同,这些不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这一研究就是自我发展的,因为它为自己设定了进一步的课题:这些不同如何产生?怎样在各自的发展中借鉴另一方的优势,等等。本文力图表明,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是自我取消的。即,这两种形而上学之间要么不存在差异;要么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微不足道。现有的任何一种研究,如果旨在证明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为自我发展式的研究,终将遭遇失败。形而上学只有一种,它在中国和西方各自发展,通常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或者不是形而上学,或者是形而上学,却不够成熟。对于不是形而上学的“中国形而上学”,它也许价值重大,但没有形而上学的价值。
一、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吗?
有些人主张,中国没有形而上学。这一派可以说是激进主义者。他们认为,与中国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一样,中国也没有形而上学。我们需要全盘引入西方形而上学。也许,他们并不否认,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资源做出形而上学的解释,但那只是一种解释而已,这种解释是我们研究者添加上去的,而且,这种添加只有在引入西方形而上学之后才得以进行。
这一派最为臭名昭著的代表,想必是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在哲学史课堂上,黑格尔虽然以“中国哲学”为名谈到了中国的思想,但是,他的态度却几乎是反讽的。他说:对于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我们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以及它对思想,对于真正的哲学有何种关系。”①言下之意是,这些思想并不是“真正的哲学”,而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②。一些学者据此就认为,黑格尔主张中国没有哲学。例如,卿文光就认为,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哲学以纯粹思想为对象,以精神自由为前提……这一哲学观当然会把东方哲学排除在外。”③如果中国连哲学也没有,作为哲学根本分支的形而上学,更无从谈起了。
这一派除诉诸黑格尔的理论之外,尚有别的论证路径④。比如,他们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研究。这一研究与西语文法密切相关:“是”字判断句发达。中国古汉语并不以“是”来表达判断,如果不以“是”来表达判断,就无法过渡到“是什么”之“什么”。而西方形而上学,正好是对存在者之一般的研究,“什么”就是这个存在者之一般。因此之故,中国并没有形而上学。张东荪就持这一看法。他的论文《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⑤从语言学上给出了理据。在《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的讲演中,他更明确地说道;“哲学是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的学术中找不到哪一种学问是与它完全相同的”;虽然“胡适之先生和冯友兰先生都写过‘中国哲学史’。从这名称上看,中国似乎也有哲学,但其实这是很勉强的”⑥。
首先需要指出,虽然黑格尔“中国无哲学论”流毒甚广,不过我们可能是在误读。因为,鉴于东方宗教与古希腊、罗马宗教以及基督教的不同,即东方宗教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黑格尔认为,“我们很可以把它认作是哲学的。”而且,他肯定地说:“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⑦针对看似最没有哲学味的孔子,黑格尔的结论是,孔子的教训“是一种道德哲学”⑧。黑格尔对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的正面态度鲜少有人提及⑨。如果黑格尔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主张中国无形而上学的学者试图以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来作理据,就是失败的。
其次,我们看到,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西方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为范本。凡不符合西方关于哲学与形而上学之范本的,就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如此,激进派们就不是在做一个描述性的判断,而是在做一个规范性的判断。因为,如果说这种观点在主张一个事实:中国没有形而上学,那就不过是在主张: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如果形而上学已然被规定为西方意义上的,那么,中国由于是非西方的,所以,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就是在主张一个重言式:中国没有非中国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者,非西方的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这其实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要让这一派的主张有见地,只能将其视作规范性的判断:形而上学只能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国所谓的形而上学不符合西方规范,所以,中国没有形而上学。甚至一些主张中国有形而上学的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如果以西方形而上学为标准,无论就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概念的原理系统而言,还是宽泛意义上的普遍性知识而言,中国哲学都不存在那种形而上学。”⑩
这样一来,问题的焦点就成了:为什么要以西方的形而上学为形而上学的规范呢?回答自然要涉及到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历史。应当说,几乎所有分支学科,都是西学东渐以后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一历史并不直接表明,西方模式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坚持这一合法性,实则在因循近代的旧路。总不至于说,西方传统的羽毛笔是笔,而中国传统的毛笔就不是笔吧?事实上,西方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也存在着异议,例如,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哲学家的界定就极为不同。可见,范式本身就有不合范的危险。亚里士多德曾经将形而上学看成是关于第一原因的研究和对存在之为存在的研究;而中世纪学者则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上帝的本性。至于现代的海德格尔等人,观点就更不相同了。他们的看法迥异,却又认为这些内容都从属于同一学科。其实从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些内容,的确可以归入西方形而上学的范畴之中。比如,关于第一原因的研究,中国传统中显然是有的,有学者就认为,“这些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思想中‘本’与‘体’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大致相当”。可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形而上学的任务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11)。
二、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不同吗?
既然无法论证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明智的做法是承认中国有形而上学。这一承认马上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有形而上学,它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差异何在?这一问题预设:中西形而上学必定是有差异的。这一预设看上去十分合理:它完全符合我们对文化差异进行解释的需要:中西文化现象差异明显;现象上的差异需要得到根源上的解释;哲学是文化之根,而形而上学又是哲学之根,所以,形而上学必定是不同的。那么,这里的不同,是种类上的不同,还是程度上的不同呢?
中国哲学界主流的回答出人意料地一致:种类上的不同。这一回答首先就回避了激进派们的规范性主张:只有西方的形而上学才是形而上学。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也是形而上学。但是由于中国形而上学跟西方形而上学的种类不同,所以,中国形而上学并不符合西方形而上学的规范。但是,这无损于中国形而上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
首先来看看中西具体的差异。这方面说法很多,比如,俞宣孟以为是道论与是论的差异。“中国哲学以道为目标,决定了中国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形而上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意味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上下求索,这一求索决不仅仅是认识的过程,更是变换人自身生存状态的过程,变换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人的生存活动与其生存环境的契合,以使生命得到顺畅的展开,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12)这一差异又被学者说成是“境界形而上学”同“实体形而上学”的差异(13)。何丽野则认为,中西形而上学的差异是象与语言的差异。海德格尔借以走出西方形而上学危机的“诗的语言”、“直接能够呈现事物‘存在’的语言就是中国《易经》中的‘象’”,正是因为有了“象”,我们才可以“说不可说”(14)。象跟西方正统语言观是判然有别的。还有学者认为,中西差异是重变化还是重存在的差异。“中国哲学史中的形而上和形而下、道与器的问题,主要关注的是道济天下的问题。而其主要考虑的就是变化问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形而上学是主要研究变化的意义及其根据的。”而在西方形而上学看来,“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变化本身要存在。……因此,形而上学或存在问题,应该是比变化更为源始的基本问题。”(15)
这些差异的提法,其理论的更早源头几乎皆在牟宗三关于中西哲学对比之分析中。牟氏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其重点在‘自然’”(16)。重生命则重体悟,重自然则重知识。重体悟则有语言所不能言说者,如此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西形而上学在语言上的不同;重生命必定重人生意义的实现,从而体现为境界形而上学。生命生生不息,重变化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我们需要重点考察牟宗三就中西哲学差异所做的论述。
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牟宗三先表明,中西哲学的差异一定是存在的,然后又具体指出了这一差异。中西哲学差异的存在性论证,在第一讲中。牟宗三先提出了针对哲学的生命差异化原则(17):
针对哲学的生命差异化原则:凡是生命主体不同的哲学,必定存在着差异。
然后,根据常识,我们可以认定:
中西哲学生命主体不同。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论:
中西哲学存在着差异。
这一论证相当基本,事实上给出了中西比较哲学的工作前提。与大多数今天的学者不同,牟宗三并没有一上来就去指认中西差异何在,换句话说,他并没有预设中西存在差异。相反,他在为差异的存在提供理由。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就算牟宗三对中西哲学差异的具体指认错误,只要我们接受这一论证,就得在牟氏的思路下工作:去寻找正确的差异。反观包括今日学者成果在内的许多比较研究,一开始就热衷于指出中西具体差异。他们的观点往往采用如下句式:中国是A,西方是B。由于他们未从理论上证明中西差异是存在的,所以,就难免让人怀疑:在他们主张中西差异是A与B的差异时,其实中国也有B,西方也有A,只不过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无知),他们忽略了这一点而已。
针对哲学的生命差异化原则在中西差异的存在性论证中起着大前提的作用,那么,这条原则是否是可接受的呢?我们知道,生命差异化原则并非总是适用的,比如,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真理就跟生命主体无关,不管你是黑人、白人,哪怕是蚂蚁,二加二等于四都是适用的。这一原则对哲学有效,需要给出特别的解释,要说明哲学的特殊性。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牟宗三区分了两种真理(18):
两种真理的区分:内容真理是需要用生命来表现的真理,其肯断是主观的;外延真理是不
需要用生命来表现的真理,其肯断是客观的。
根据这一区分,内容真理“系属于主体,如我相信什么什么(I believe so and so),我想怎么样怎么样(I think so and so),是系属于我这个主观的态度……如我相信上帝,但你不一定相信。因上帝的存在不能被证明,这就不是外延真理,因其不能被客观地被肯断,而是系属于我相信”(19)。又由于,牟宗三认为:
哲学真理是内容真理(20)。
所以很自然,哲学真理要系属于主观的态度,不是客观的,所以,不同的主体可能会有不同的哲学真理。
如果我们承认两种真理的区分,并且又接受哲学真理是内容真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接受了中西哲学的差异必定存在呢?并非如此。以牟所举的上帝存在的例子(21)为例,在基督教徒之间,就算是生命不同,主体不同,“上帝存在”也是被接受了的。可见,主体不同不足以表明他们所拥有的内容真理必然不同。或有反驳说,基督徒之间的比较,是相同主体的比较,因为在相信上帝这一点上,他们都是相同的。这一说法看似有理,实则有循环论证之弊。在此,对主体的划分,求助于各自所持有内容真理的同一性,即言,主体由内容真理决定。而在前面,两种真理的划分,又需求助于主体肯断的差异,犹言,内容真理由主体决定。事实上,牟宗三正在借用这一循环:中西哲学不同,因为中西生命主体不同。为什么中西生命主体不同?因为他们的哲学不同。要跳出这一循环,需要不诉诸哲学的差异,来表明中西生命主体的不同。在这方面,实在难以看出牟宗三有任何成功的迹象。生命主体的不同要么只是一个自然事实,要么还涉及到文化因素。如果生命主体的划分只是自然事实,则任何人的生命主体都不同于其他人,从而每个人的哲学都跟别人的哲学不一样。这样的结论将差异绝对化,要么没有用处——世界上的确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要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持有相同的哲学观点这一事实。如果生命主体的划分涉及到文化,则必然涉及到哲学,这样,就又进入到循环之中。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必承认两种真理的区分。内容真理在何种意义上是真理,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牟宗三并没有真正解答这个问题。从他的例子来看,由于内容真理跟主体的态度相关,其真假取决于主体的态度,就此而言,与其说是内容真理,不如说是有内容的意见。凡一主张之真,必有标准,如果缺乏标准,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当代之真理学说,或持符合说,或持冗余说,或持融贯说,或持实用说等等。除符合一说需要主观跟客观相符之外,其余诸说并不预设真理的客观对象存在。虽然如此,认为一种主张是真理,还是有其公共的标准的。牟宗三两种真理的区分,难逃特设假说(ad hoc)之讥。此其一。
其二,就算我们接受两种真理的区分,也未必接受哲学真理就是内容真理。内容真理一说,实类于趣味判断。你觉得这菜好吃,我觉得不好吃,都没有错。品味不同而已。若说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只是趣味判断,单单取决于主体的态度,无疑将哲学相对化了。为了指出中西哲学的差异而不惜将哲学相对化,这一代价太大。仍以牟所举过的例子为例,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断不会因为我主张他存在,他就在我这里存在;你主张他不存在,他就在你那里不存在。也许,相信与不相信上帝,会造成你我在生活态度上的不同。然而,当我主张上帝存在的时候,并不是在主张,上帝存在于我的信念中;而你主张上帝不存在时,也并非在主张,上帝不存在于你的信念中。只存在于信念中的上帝,并不会引起我们讨论的兴趣。根据牟宗三的相关论述,关于上帝存在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在主张上帝存不存在于主体的信念中。从而,所谓的内容真理,不过是个人信念的表白。信念的表白并不是真理,哲学如果有真理,那就一定不是信念表白。这是共识。
要从理论上证明,中国哲学或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相当困难。于是,大多数研究者干脆放弃这一路径,直接进入牟宗三的第二步,列举中西形而上学的众多差异。他们的思路是:因为中西形而上学存在着这些差异,所以,中西形而上学是不同的。这一路向虽然便捷,却另有危险潜伏。例如,方东美认为,“自远古至西元前十二世纪,中国形上学之基调表现为神话、宗教、诗歌之三重奏大合唱。”(22)如果方氏所言无误,那么任何一个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人都会认为,中国形上学并不是形而上学,而是文学与信仰的混杂。又如,有学者认为,“由于文化心灵与语文结构之不同,中国形上学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质与精神风格,中国形上学探讨的意向系以自我生命的感受、理解和安顿为主轴,其特质系以天人关系为着眼点,本体、工夫和境界有三合一的不可分割性。”(23)这分明是宗教中的灵修,跟形而上学无涉。次如,有论者指出,“‘本体’不同、方法不同、形态不同,这才是中西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根本区别所在。”(24)对象、方法和形态均不相同的学科,居然是同一个学科?简直匪夷所思。复如,“西方的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同中国的形而上学有着根本的区别。”(25)再如,沈清松以为,中国的形而上学是“隐态的”,西方的形而上学是“显态的”;中国形而上学是“生自忧患”,西方形而上学是“生于‘悠闲’和‘安逸’”等等(26)。这些夸张性的说法也许于凸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有益,却于比较研究无功。中西形而上学纵然有差异(目前这一差异的存在还欠缺一个理论的说明),其差异也需恰当。如果差异太大,中国形而上学就不再是形而上学。然而中国存在形而上学,否定这一事实的理据并不充分,所以,对差异的过分强调不得不滑向赵敦华指出的“现代相对主义”(27):你有你的形而上学,我有我的形而上学。在赵敦华看来,由于中西形而上学范式不同,比较研究“不是用西学格中学,就是用中学格西学”(28)。牟宗三、唐君毅等一代名家,概莫能外。
三、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相同吗?
我们绕不开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不同,那就已然预设,中国是有形而上学的。如果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形而上学,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都称作形而上学呢?要是只强调差异研究,我们根本得不到共同的形而上学界定。牟宗三隐隐约约地承认哲学具有普遍性,却疏于论证(29)。在这种局面之下,赵敦华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30)。赵敦华应用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区分,将中西原初形而上学区分为宇宙发生论和本根论两个部分,由于这两个部分都具有共同的特征,所以,中西形而上学同源。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西方形成了“自然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中国则形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传统。
可以判定,这一方案比前述各方案为优。它成功地阐明了中西形而上学为什么是相同的。在此前提之下,又解释了相同的形而上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面貌。这一解释,明显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因为中西形而上学相同,所以,赵敦华就拒绝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先入之见,比如,中西思维方式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些先入之见,是解释中西形而上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所必须的。尤为难得的是,赵敦华“根据现代达尔文主义和进化心理学,对中西形而上学的同源和分流的原因作出解释”,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人类心理机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解释了中西形而上学的同源;而“概念的语言载体和社会作用等具体的历史条件”则成为分流的主因(31)。对达尔文主义和现代心理学的引入,让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不再流于空洞的概念玄思。
问题在于,中西形而上学分流一说,颇值得商榷。首先,作者告诉我们,这一分流的观念来自于康德对自然和道德两种形而上学的区分(32)。如果西方形而上学家康德已有这一区分,想必西方也有道德形而上学。赵文所谓的中西分流,实际上正是西方内部的分流。其次,从哲学史来看,不论是柏拉图以善的理念为最高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知德”和“行德”的区分,都表明,西方形而上学是自然与道德并行的。甚至就算是在所谓的古希腊哲学衰退期的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虽然以伦理学说为主,但为了表明自己伦理学说的正当性,还不得不辅之以严整的自然哲学理论。到了中世纪,灵修工夫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基督教哲学家同时也负有解释自然的责任。康德明确区分这两种形而上学,不过是西方形而上学内部的一次分化。
可见,赵敦华以西方内部的分化来指称中西形而上学的分流,困难重重。于是,他不得不在文章的末尾这样提醒读者:“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使用‘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学’分别表示中西形而上学的成熟形态,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西方不研究道德问题,或中国没有自然学问。”(33)这无疑是正确的。当他说“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人的精神(灵魂)和社会、政治、道德也是自然生成的事物,可以用研究自然物的方法和知识体系,获得关于人的精神和社会的确定知识。在中国形而上学传统中,自然界具有人和社会的伦理属性,‘格物’(研究自然物)和‘格心’(净化心灵),同属道德修养过程”(34)时,也没有错误。因为,他并没有说,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只用”研究自然的方法和知识体系去获得精神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中国“只用”研究人和社会的方法和知识去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当他把“这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传统”归结为“人类心理‘降低复杂性’机制的两种倾向”,即,要么将外部世界向人化简,要么将人向外部世界化简,并进而指出,“中西形而上学的分流的普遍意义在于,两者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表明了人类心理机制的这两种倾向”(35)的时候,显然已将前文的“可以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研究偷换成了“只用”某种特定方式来研究,从而得出他的结论:分流后的中西形而上学分别体现出人类心理机制的两种倾向。这样一来,从理论实质上,赵敦华还是走上了他所反对的牟宗三的旧路:中国的道德文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种简化当然不对:无论从西方哲学史还是西方宗教思想史来看,西方形而上学对道德的处理都绝非只有将其简化成自然一种路向。道德上的自然主义固然在西方有它的市场,道德上的反自然主义也大行其道。
因此,如果赵敦华的主要解释是正确的,我们将不得不说:中西形而上学同源,但后来中国形而上学走上道德形而上学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就不得不成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局部。相类似的说法,我们还可以在沈清松的著述中找到。他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是……以物理之后的姿态提出的,其后一直为西方形上学的主流,并在此主流的支持之下,兼及于伦理之后,美感之后”。反观中国的形而上学,从开始“便以伦理之后(儒家)和意境之后(道家)为主要特质”。后一种形而上学的缺点在于,“无法兼及物理”(36)。西方可兼中国,中国不可兼西方。中国实为西方之局部(37)。
四、一个平凡的结论
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对这个问题,还有这样一个可能的回答:形而上学是家族相似概念,不要求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本质。所以,中国可以有在本质上跟西方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这一回答的优点是,可以涵盖几乎所有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的成果。但缺点也同样突出:由于不要求存在共同的本质,所以,中国形而上学跟西方形而上学可能完全是两码事。这样,就彻底陷入相对主义。或许有人愿意接受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然而,借助家族相似来为这一立场作出论证,根本行不通。因为,家族相似虽然不要求所有成员有共同的本质,却依然要求两两之间具有相似性;而在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中,只有两个对象,所以,要么这两种形而上学直接具有相似性,要么它们各自跟第三种形而上学具有相似性——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一个相似的家族。如果中西形而上学直接具有相似性,这就表明它们在具有相同特征的同时,又具有不同的特征。这样一来,麻烦绕了一个圈,又回来了:我们需要知道,相同在何处,不同在何处。如果它们各自跟第三种形而上学,比如说,跟印度形而上学相似,在中西形而上学之间,麻烦消失了。然而,消失的麻烦并没有得到消除,反而倍增:我们需要说明中印与西印之间形而上学的相似。由于它们间两两直接相似,因此它们必然既相同又不相同。如此绕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必须找到两种形而上学问的相同与不同,并给出解释。
余下来的唯一可行选择是,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完全相同,只有一种形而上学。严格讲,并不存在中国的形而上学或西方的形而上学,只有形而上学在中国或者形而上学在西方。结合上文的分析,这一回答的理据如下:基于事实,我们承认中国存在形而上学;基于对牟宗三论证的反驳,我们知道,中西哲学或形而上学真理存在差异的理论论证并不充分;根据对种种中西形而上学差异具体指认的分析,包括对赵敦华“同源分流说”的分析,所谓的差异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存在,但不是形而上学间的差异;同时,我们还论述了形而上学的家族相似概念为什么行不通;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说需要应付一个难题:中西形而上学表面上的差异如何得到解释?我们可以提供的解释是,将所谓的差异区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这些差异存在但不是形而上学问的差异,比如,中国形而上学使用的概念跟西方形而上学不同,中西形而上学根本概念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翻译(尤其是,西方的being无对应中文译名;中国的“道”也无对应西文译名)。这样的差异是一个自然事实或语言事实,是跟形而上学相关的差异,却不是形而上学间的差异。
二是,这些差异存在并且是形而上学间的差异,但这一差异是程度的差异,而非种类上的差异。比如,就形而上学的表达方式而言,中国重言外之意轻概念表达,而西方重概念表达而轻言外之意。一个普遍看法是,重言外之意轻概念表达是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古希腊形而上学中,有许多神秘的言论,但随着形而上学在西方的发展,神秘言论越来越少(当然,神秘主义者还是存在的,但他们所用的语言越来越不神秘),学术研究和文明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解密。所以,中西形而上学这方面的差异是程度的差异。
三是,这些差异不存在。比如,张岱年认为中国的“本根论相当于西方的Ontology”(38)。而中国本根论“与西洋哲学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不以唯一实在言本根,不以实幻说本根与事物之区别”,二是“认为本根是超形的,必非有形之物”,三是“本根与事物有别而不相离”(39)。西方的本体论在第二点上跟中国的本体论并无不同。而又由于西方本体论并非只有一元论,也有多元论,可见本体非一;就算持一元论,就算本体是一个,比如上帝创世说,也有持续创造说的解释,这一解释肯定本体与事物有别而不相离。由此可见,张岱年举出的中西三个“根本不同”,根本就是相同的。再如,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是道德形而上学,强调本体与工夫合一;西方是知识形而上学,对本体的认识跟个人修身分离。这样的差异其实也并不存在。在西方基督教信徒中,他们的本体与工夫是合一的:对上帝的认识和个体的修身并不分离也无法分离。
在这里,好像有某种因素在暗示我们,至少存在着中西文化间的种类差异:中国主流文化为无人格神背景下个人的修身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是世俗而超越的。但西方主流的基督教义要求一个人格神作为背景。然而,就算泛化到文化间来比较,这一结论也成问题。因为,基督教哲学的某些异端解释,已经(接近)没有人格神,比如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可见这里绝非种类的不同,而是发展方向的不一致或发展程度有所区别。总之,通常所谓的中西形而上学的差异,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存在;如果存在,存在着的差异或者是跟形而上学无关的差异,或者是形而上学间的程度差异。总之,只有一种形而上学。
只有一种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平凡的结论。但我们无需担心因此而掉进西方中心论的陷阱。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学科是在西方范式下建立起来的,是以西方范式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形而上学”概念,虽然取自《易经》,却不是一个中国固有的概念。它只不过是“metaphysics”(物理学之后)这一西方概念的中国名字。形而上学的内容是什么,完全不可以在中文语境下通过顾名思义或者考查词源来获取。如果像有的学者(40)那样,去考查“形而上学”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使用,并以此界定“中国的形而上学”,这无异于将所有的重担都压到了当年以此词译“metaphysics”的日本人西周身上。如果他的翻译有稍许误差,所有类似研究的意义就将土崩瓦解。所以,反倒是后面这类研究,暗从了西方中心论:他们试图以西方的术语来框定并不属于这一术语的内容。已有学者指出,当近世以来的学者痛感传统学术“一半断烂,一半庞杂”,而“主张用西方现代的科学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整理古代的学术”时,由于他们未能考虑中西学术分类体系差异的根本原因,从而也就忽略了中国学术“自身的内在合理性”(41)。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平凡的结论,倒还具有一个意料不到的优点:它让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不再拥有西方的名字,从而有助于这些特有内容的呈现。而这正是当前国学复兴所需要的。
注释: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15页。
②《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15页。
③卿文光:《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④这一派学者常引的另一经典文献是葛瑞汉的经典论文——《西方哲学中的Being与中国哲学中的“是/非”,“有/无”》,载《场与有》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载宋继杰:《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⑥张东荪:《科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8页。
⑦《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15页。
⑧《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19页。
⑨当然也不是没有。卿文光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他却认为,这是黑格尔“放宽哲学的标准”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哲学,只是些“抽象的哲学”(参见卿文光:《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4~315页)。这有强辞之嫌。若以黑格尔自己的具体哲学为哲学,这一严苛的标准恐怕会导致只有黑格尔一人有哲学。
⑩俞宣孟:《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15页。
(11)《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第113页。
(12)《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第138~139页。
(13)宁新昌:《中西形而上学的异通发微》,载《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
(14)何丽野:《象·是·存在·势——中西形而上学不同方法之比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7页。
(15)薛立波、李蜀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32页。
(16)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17)《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3~4页。
(18)参见《中西之哲学会通十四讲》,第6~7页。又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5~35页。
(19)《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7页。
(20)《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6页。
(21)参见《中西之哲学会通十四讲》,第7页。
(22)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的宇宙与个人》,载黄克剑、钟小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之五: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23)曾海春等:《中国哲学概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6页。
(24)余为国:《论中西形而上学本体论及其特征》,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4页。
(25)《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问题》,第27页。
(26)沈清松:《物理之后/形上学的发展》,牛顿出版社1988年,第387~388页。
(27)赵敦华:《中西形而上学的有无之辩》,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206页。
(28)《中西形而上学的有无之辩》,第206页。
(29)参见《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3~4页。
(30)参见赵敦华:《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31)《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第19~20页。
(32)参见《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第13页。
(33)《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第20页。
(34)《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第20页。
(35)《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第20页。
(36)《物理之后/形上学的发展》,第388页。
(37)这里也许有个难点。依沈清松某些地方的提法,西方似无意境之后。比如,当他谈到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时,说道:“但他总是不敢以美为超越属性之一。此为其缺陷。但在中国哲学,却全然无此种迟疑。儒家重视人格之美,亦重视天地之大美。道家的庄子甚至要援天地之美以达万物之理。”(参见《物理之后/形上学的发展》,第391~392页)此种说法如果正确,则中国必有西方所无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说法忽略了中西“美”的概念的差异。当阿奎那不敢以美为超越属性时,这里的美是肉体感性的美。儒家所谓大美,庄子所谓天地之美,显然也不是什么肉体感性之美。在这里,中西实无分别。
(38)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39)《中国哲学大纲》,第16页。
(40)参见《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41)方朝晖:《从Ontolog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载《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第115页。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牟宗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