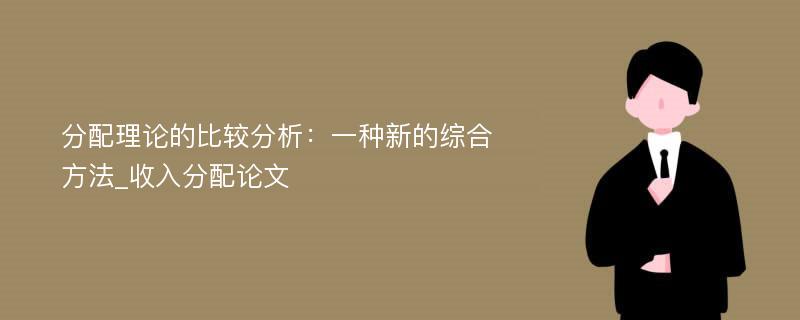
分配理论的比较分析:一种新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2-0071-10
分配理论研究的是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从实证分析的纯理论角度来说,它基本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收入分配本身主要受到经济中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按照怎样的机制运行;其二是分配过程又会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哪些影响。套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不仅要研究“蛋糕”是如何分割的,而且要研究“分蛋糕”对于“造蛋糕”的影响。由于财富的生产与财富的分配乃是经济学的两个恒久性主题,显然分配理论在整个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历史起源与当代发展
(一)早期的分配理论
早期的分配理论主要关注国民收入在工资、利润(在古典的均衡假定条件下,企业家的职能被舍弃,故其所谓利润实质等同于利息)、地租等几大范畴之间的划分,即所谓“职能收入分配”问题。由此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学说:古典的分配理论,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古典的分配理论源于斯密而完成于李嘉图,他们构筑了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古典学派用生产力与财产所有权双重因素来解释收入分配。他们认为,虽然产品(或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在私有产权出现之后,资本与土地也构成了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所以总产品需要在三个要素之间分配;归于劳动的收入——工资,只能占有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其数量标准在劳动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条件下通常将确定在社会必要生活费用的水平上,而总产品扣除工资后的剩余则或者作为利润、或者作为地租归于资本或土地所有者。这反映了古典学派对于非劳动收入的解释有些暧昧,涉及双重因素,不过它实际上表明古典学者认识到了分配要受到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①古典分配理论的这种双重因素解释使得它与其价值理论发生了矛盾,以至于从斯密到以后李嘉图学派的麦克库洛赫等一些人又不同程度地从原来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了多元的成本价值论。但即便如此,非工资收入范畴作为对总产品扣除工资以后的“剩余”的痕迹依然存在,这就隐含了分配过程所体现的阶级利益冲突,它在李嘉图那里直接以动态的形式展现出来。就理论的逻辑结构看,古典的分配论显示了某种“非对称性”:一是收入分配机制与价值决定机制缺乏对应性,二是各种收入范畴的决定机制缺乏一致性。这些成了后来分配理论发展的突破口。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是在对古典理论进行重大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把生产力因素完全排除在分配机制之外,唯一地用财产权来解释分配过程。他彻底地发展了一元化的劳动价值理论,以此证明利润或地租等非工资收入范畴与资本等要素的所谓“生产职能”毫无关系,从而公开地揭示了先前在古典派那里只是以暧昧的形式存在的利润等收入范畴作为对劳动产品的一种扣除所具有的“剩余”占有性质——即剩余价值。至于工资的决定机制,马克思基本上沿袭了古典传统,不同之处在于他强调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就把剩余价值的占有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因此,单就逻辑结构而言,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克服了古典分配理论的第一个非对称性,实现了分配决定机制与价值决定机制的逻辑对应性。当然,根据这种理论,分配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剥削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利益冲突,也更加昭然若揭了。
如果说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关注古典分配理论的第一个逻辑瑕疵,那么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则试图完全变革古典的分配理论传统。新古典的分配论诞生于“边际革命”的浪潮中。它原本具有尖锐的反古典主义倾向,但到了马歇尔那里,为了体现其“大一统”的特征,又部分地吸收了古典理论的某些因素,故名“新古典”。②新古典学派对古典分配论的变革与马克思所做的正好相反。他们完全把财产权因素排除在分配机制之外,单纯地用生产力来解释收入分配。他们超越了古典派关于只有劳动才具有生产能力的观点,认为资本、土地等物质要素也具有生产力,从而产品是三种要素共同生产的结果。根据这种对生产过程的认识,便可以得出分配过程的决定机制:总产品将按照各要素在生产中的实际贡献(在均衡条件下即是边际生产力)在工资、利息(或利润)、地租等范畴之间分配。在这种所谓“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下,古典分配论所具有的两个逻辑缺陷都得到了解决:分配机制现在严格地对应于价值或产品的生产机制,并且各种收入范畴都统一地决定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源自私有权的“扣除”机制消失了,非工资收入作为“剩余”的概念不复存在了,从而收入分配也不再体现阶级利益的冲突,而是成为市场价格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过程的一部分。
(二)当代的发展演变
上述三种分配理论在后来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演变。古典的分配理论经由后凯恩斯学派的“复兴”而被赋予新的现代气息,马克思的分配思想则在新马克思主义等激进派的体系中得以延续。相比之下,新古典分配理论的发展最为令人瞩目,它不仅取得了更为丰富多样性的进展,而且日益居于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1.古典派分配思想及马克思分配思想的发展
古典分配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中。从20世纪50年代起,琼·罗宾逊、卡尔多等人就致力于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宏观原理填补微观基础空白的工作。他们经由卡莱斯基、斯拉法等人的著作发现了古典分配思想的巨大价值,将其纳入到有效需求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便提出了“新李嘉图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③这些后凯恩斯学者坚持了古典派关于资本所有权参与收入分配、从而非工资收入——主要是利润(利息)是对于劳动产品的一种“扣除”的思想,而反对用资本的生产力来解释利润(利息)范畴。他们用一种包含两个阶级(工人和资本家)、两种收入(工资与利润)、两种储蓄(消费)倾向、三个部门(资本品生产、资本家消费品生产、工人消费品生产)的抽象模型,证明在宏观经济维持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利润的多少主要由投资量决定,利润率则由投资增长率决定,从而资本家的投资决策便决定了总收入在工资与利润各范畴之间分配的格局。这个结论被以数学方式概括为“剑桥分配等式”,通常又称为“帕西内蒂定理”④。它是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宏观框架下对于古典分配理论的现代演绎,既代表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微观基础方面的新建构,也代表了古典分配理论向宏观与动态分析领域的新拓展。
后凯恩斯学派对古典分配思想的这种复兴曾经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与当代新古典主义所展开的分配理论大论战曾引起广泛关注。尽管如此,该理论却始终未能赢得主流的地位,这或许与它重又恢复了古典分配理论中的某种“非对称性”从而难以纳入现代的均衡分析体系有关。近年来,新一代后凯恩斯学者试图从不同方面来拓展“剑桥分配等式”,诸如:通过引入经济行为人更现实的储蓄(消费)倾向、引入政府税收与支出活动以及金融市场债务因素等来进一步证明帕西内蒂定理的普遍有效性⑤;通过运用不同部门总需求的差别来解释不同部门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来扩大剑桥分配理论的适用范围⑥;通过将劳资双方工资谈判因素引入分配理论模型,来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剑桥分配理论。⑦虽然这些新进展在具体的理论细节与表现形式方面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在总体上都体现了强调资本所有权因素、强调阶级利益冲突的古典分配论基本思想。
至于马克思分配思想在当代的发展,情况则比较复杂。一方面,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由于坚持以往的“剥削”论调而日益被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边缘化”了。另一方面,在比较正规的学术探讨上大致出现两类文献:其一是围绕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特别是所谓“转型问题”等等而展开的,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波及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的学术界,它们大多处于狭义的分配理论范畴之外。其二则是近三十年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教授等著名学者为代表。他们运用现代经济学中流行的正规化分析方法把马克思关于社会政治条件、阶级利益冲突决定生产结构和收入分配的核心思想纳入微观和宏观经济模型,强调只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利益冲突关系的基本视角出发才能阐释清楚企业的技术选择问题以及内部制度安排问题,而这些无论是在无制度因素分析的原始新古典理论那里还是在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厂商理论中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对传统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发展,是与下面将要论述的新古典分配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并肩而行的。它与新古典主流派的理论对接较多,故也被称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学派”。⑧
2.新古典分配理论的发展
虽然凯恩斯革命曾一度削弱了新古典传统的影响,但是当它最终与凯恩斯经济学融合起来以后很快就恢复了主流地位。所以,新古典思想构成了当代分配理论发展的主旋律。这种发展涉及诸多方面,其中至少有三条主要的理论线索值得予以特别的强调。
一是分配理论的宏观化。以边际生产力为基础的新古典分配理论本是一种微观分配论,它最初就是作为要素定价而与市场交换均衡同时决定的。这种分配理论在当代的最重要发展,就是在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融合的过程中由微观扩展到了宏观领域,并成为所谓“新古典综合”的重要基础。罗伯特·索洛等在发展凯恩斯主义动态学的过程中,利用了总量生产函数(特别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这一重要工具,在一系列完美性的假定条件下,并借助于均衡分析技术,得出了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按照要素边际生产力来调节各种收入份额的过程,最终会实现经济稳定状态增长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索洛模型”或新古典增长模型。它把单纯基于要素生产力来解释职能收入分配的新古典分配思想以更加程式化的方式发挥到了近乎极致的程度,不仅使国民收入在工资、利润等等之间的分配与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源有效配置融合起来,而且也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国民收入决定、稳定增长等联系在一起。所以,尽管这种模型也曾遭到过挑战,且它利用总量生产函数工具来实现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简单过渡遭到过逻辑上的严重质疑(两个剑桥的资本争论或“反边际主义革命”),但是由于其理论在形式上的完美对称性和均衡、优化分析的内涵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仍然牢固地占据了现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一种标准的理论信条。⑨
二是分配理论的“微观化”。所谓分配理论的微观化,是指新古典分配思想由职能收入分配领域向个人收入分配领域的延伸。它是由20世纪50年代末“人力资本理论革命”的出现所引发的。以往的分配理论主要是以总收入在工资、利润、地租等几大范畴之间的分配为考察对象,而较少涉及每一收入范畴内部的收入分布问题,尤其是不同个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别问题。现实中虽然不同的物质资本一般具有收益率等同的趋势,但是不同个人劳动的工资却往往是具有差别的,这构成了收入分配领域里一个长期令人迷惑的现象。尽管以往曾经有人试图从“补偿性差别”(例如,斯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差别(例如,马克思)、制度因素等等不同视角对此加以解释,但终究未能形成理论气候,只是当明塞尔、舒尔茨以及贝克尔系统地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形成一种关于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新的分析范式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公认的解决。⑩
人力资本理论是将新古典的资本理论应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它将人的生产能力视为主要是由后天学习、培训与实践等等这些被称为人力投资活动的产物即人力资本。一个人的人力投资(例如教育)越多,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生产能力就越强,对总产品的贡献就越大,从而个人收入水平也就越高。于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差别,都可以归结为其人力投资进而人力资本的差别。通过这种论证方式,人力资本理论的新范式不仅把新古典的分配思想在工资范畴上做了更为具体化、微观化和普遍化的推广,而且还实现了将工资范畴(作为人力资本收入)与利润范畴(作为传统的物质资本的收入)二者决定机制的直接同一性,这标志着新古典分配理论的重要拓展,使得它可以在诸如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企业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学分支领域大行其道。不仅如此,人力资本理论还通过系统性的有关人力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将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纳入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最优配置体系,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原有的微观市场价格机制一般均衡分析的理论体系。(11)
三是基于“激励”视角的分配理论的发展。如果说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分配理论标志着新古典分配思想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的一种重要拓展,那么近年来基于激励视角的分配理论发展则代表了新古典分配思想在这一领域里的一种新的理论再造,从而具有更为深刻的创新意义。我们知道,人是生产诸要素中唯一具有思想和情感的能动性要素,人在生产过程中对于总产出的贡献(亦即其实际的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其生产能力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其努力程度的高低。在一个信息完全对称、无不确定性的理想经济世界里,人的要素的这种特点并不会导致他(她)与其他物化要素在分配决定机制上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时生产者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就像其他物化要素一样都是清晰明了的,故简单的新古典分配论行之有效。然而,一旦进入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时,如果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总产出(或总收益)要受到生产过程之外某些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雇佣双方的信息非对称又导致雇主难以准确地认定雇员的实际生产投入程度,那么先前的理论所理想化地假定的个人生产投入与总产出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便不复存在了,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完全性在这二者之间加上了“楔子”。由于楔子的存在,激励问题便产生了:“好”的工资制度(能够准确反映雇员实际的生产投入)将会导致雇员努力工作,而“差”的工资制度(未能准确反映雇员的实际生产投入)则会导致雇员怠工和偷懒。(12)
严格说来,这种基于激励视角的个人分配理论已经大大超出了原始的新古典理论模型,这不仅表现在它广泛引入了以往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或舍弃的各种有关现实世界不确定性、不完全性等等因素,而且还体现在它的理论着眼点是关注个人薪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与激励功能。并且,这种分配理论与以往的各种分配理论相比,也更加贴近于经济运行的具体层面,在更为现实的层次上揭示了个人收入分配决定机制以及个人收入分配对于经济运行绩效的影响。当然,就基本的方法论而言,这种分配理论并没有脱离新古典的窠臼,而是始终贯穿着基于成本—收益比较的新古典效率分析与均衡分析思想,并且其所关注的薪酬制度的实现形式,乃是个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一基本新古典分配机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代表了新古典分配思想在当代个人收入分配领域的一种重要发展和创新。
二、不同分配理论的相互关系:替代还是互补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分配理论?这是我们在研究现代经济学时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以往人们在考察各种分配理论及其争论时,往往将它们视为不可调和的,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能够长期并存这一事实本身也蕴涵着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互补性。例如,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过马克思分配理论与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根本对立性,却鲜有人去考虑它们之间的互补可能性。因而,坚持一种理论似乎就意味着必然要完全排斥另外一种理论。这种方法论倾向在中国学术界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且它还与相当一部分人盲目追捧“主流”或“正统”的思想倾向交织在一起。这种简单化、极端化的思想倾向不仅不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现代经济学积累的丰富的分配理论成果,而且也难以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复杂多样的现实分配问题给以科学分析,甚至导致政策调节方面不时地出现摇摆不定或前后矛盾的尴尬局面。
导致上述偏颇思想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学者在政治倾向以及价值判断准则方面的差异肯定应该对此负责任。然而,如果抛开价值判断因素,仅从实证分析方面来探源,那么显然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人们由于缺乏对于经济现实多样性必然会导致经济理论多样性的认识,未能深刻地理解各种相互竞争的分配理论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相互替代关系,而是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相互补充关系。实际上,现实世界是多层次、多侧面、多维度的复杂体系,人们往往是从不同层次、侧面或维度去考察这种现实,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产品。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曾指出,关于资本的分配问题就像一座房子,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它,就会把它描绘成不同的样子。(13)而现实的分配过程又岂是简单的房子结构所能比拟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不同的分配理论乃至经济学的不同流派,都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尽管现存的各种理论观察现实的视角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对于解释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某一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同的分配理论之间的差别本质上乃是体现了某种“理论分工”。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一种新理论常常是为了取代某种旧有的理论而诞生的事实,但是在长期的相互竞争中能够保存下来的各种理论,必然具有互补性。不仅如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相互“沟通”和“调和”的。
那么,就本文所概括提炼的主要分配理论流派或分支而言,它们究竟具有怎样的互补关系呢?首先来分析职能收入分配领域。乍一看来,古典的、马克思的、新古典的三大理论在这里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调和的,但是经过深入的思考之后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三种理论都承认,除了蒙昧时期的人类原始社会以外,每个社会的总产品都不可能完全归于劳动者,而是要部分地归于非劳动要素。同时,它们也都承认,资本等要素与劳动一样也是产品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因素。不同之处在于,古典派与马克思看到并强调了劳动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点,即活劳动的能动性,而新古典派则只看到和强调劳动与其他各种要素的同一性。造成这种视角差别的真正原因则在于,古典派与马克思看重并强调社会政治条件诸如私有财产、劳动者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的相对社会地位与力量对比关系等等对分配格局的影响,而新古典派则关注于劳动与非劳动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技术关系对分配的影响。实际上,在现实中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在不同经济条件下显示的相对作用强度有所不同而已。历史地看,在产业革命初期,劳动供给严重过剩而资本相对稀缺、劳资双方对比关系处于强弱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社会政治条件对分配的影响占了主导地位,这时工资直接被压缩到生存费用的水平,总收入的其余部分则作为财产权的体现全部归于资本等要素。古典派与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本质上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而到了后来产业革命的尾声或完成时期,劳动与资本等物化要素的对比关系相对趋于均衡,这时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技术关系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决定作用(通过成熟的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凸显出来,由此才导致了新古典分配论的出现。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社会政治因素和物质技术因素也往往以相互补充的形式影响着要素收入分配。例如,假若要素比例和技术条件相差不多的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职能收入分配格局差别较大,那么这种较大的差别无疑显示了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就为古典或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提供了解释空间。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下,如果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差别,那么它显然决定于不同产业部门的要素比例或物质技术关系,从而对此只能用新古典理论来给予回答。由此可见,在解释不同条件下的职能收入分配方面,古典及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是完全可以和新古典的分配理论相互补充的。进一步地说,根据古典分配理论和新古典分配理论在当代宏观分析框架下的推演——即后凯恩斯学派的剑桥分配方程和新古典综合的总量生产函数模型,我们还发现,在经济维持稳定增长的均衡状态下,这两种理论模型所蕴涵的变量关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各自对实现稳定均衡的调节机制的看法不同而已。(14)
上面是把古典派与马克思的理论绑定在一起来与新古典相比照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与古典派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差别和相互补充关系。虽然他们都坚持非工资收入范畴是“被扣除的”“剩余”这一基本思想,但是分析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故马克思试图用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来完全取代李嘉图经济学的预期目标并未能实现。概要地说,二者的相互补充关系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抽象的层次不同。古典派很多情况下是在价格或交换价值这些较为具体的层面来考察职能收入分配,而马克思则严格地坚持在价值的纯粹抽象层次上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两种逻辑思维层次在关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上可以相互补充。其二是就工资、利润、地租等几大收入范畴的数量关系而言,古典学派与马克思都揭示了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但重点却不尽相同:古典派特别是李嘉图着重分析了利润与地租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其动态,而马克思则重点分析了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由此也形成了某种理论解释上的分工与互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职能收入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之间所存在的相互补充关系。如果说对于职能收入分配领域中不同学说之间所具有的互补关系需要通过深入缜密的思考才能认清楚的话,那么关于职能收入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之间存在着的理论分工与互补关系则相对来说较为清晰可见。首先,就思想基础来说,虽然历史上也曾闪烁过一些有关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的思想火花,但是当代系统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主要还是新古典分配思想发展的结果,它体现了新古典分配思想从以往较为宽泛的职能收入分配领域向更为细密的个人收入分配领域的一种微观化延伸。因此,这里不存在不同思想学派之间的竞争问题,自然可以直接显示出新理论与旧理论之间的继承与互补关系。其次,就理论内容来说,基于人力资本分析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与基于边际生产力分析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在对于现实收入分配中两个不同层面问题的解释上也确实形成了比较密切的相互配合关系。现实中,既有总收入在工资、利润、地租等基本范畴之间的分配问题,也有每一种收入范畴在同类要素内部的划分问题。新古典的边际分配论关注于前一层面,但在后一层面上却留下了理论空白。
但是一旦引入要素的差异性、特别是劳动要素生产力的差异性,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便提上日程了。人力资本理论所完成的正是这个工作。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投资的内生视角来考察劳动这一要素的生产能力形成机制,这就决定了它是以个人生产能力差别作为分析的前提,从而也就把理论研究的视角从职能收入分配转移到个人收入分配。同时,这种转移又贯穿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一般思想,因为人力资本理论关于个人收入分配过程(包括不均等程度)的分析始终是以新古典有关资本生产力的原理为基础的,或者说毋宁说这种分析就是直接将新古典的资本理论应用于劳动要素的结果。所以,从分析视角上说,二者形成了明确的理论分工与互补关系。从思想基础来看,后者又是前者的自然引申。总起来说,人力资本理论开创的个人收入分配分析,弥补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不足,将其基于物质技术关系的边际分配论由原来的职能收入分配领域扩展到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从而使得新古典分配理论对于现实收入分配的解释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了。
如果说以人力资本分析为基础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与新古典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二者之间体现了一种在分析范围或理论外延上的互补关系,那么近年来蓬勃兴起的基于激励视角的分配理论与以往的分配理论(不论是职能收入分配理论,还是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之间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在分析层次或理论内涵上的互补关系。按照是否考虑到分配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完全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将分配理论基本上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一是以确定性和完备信息为前提假设的较为抽象化的层次;其二是以不确定性和不完备信息为前提假设的较为现实化的层次。就与劳动相关的收入分配而言,前一个层次上并不存在激励的问题,工资范畴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作为劳动投入回报的补偿功能。而在后一个层次上则不然,这时激励问题出现了,故而工资所具有的激励功能也显现出来。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所有的分配理论主要都是在第一个层次上展开的。新古典学派这样做,是直接与他们关于经济世界的各种完美化理想假设相关的。而倡导动态分析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以及强调不确定性的古典传统的当代继承者——后凯恩斯学派之所以也如此,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缺乏不完备信息的思想与分析技术而未能将这种对于现实不完全性或非均衡性的认识有效地纳入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更为关注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政治因素、始终着眼于阶级利益关系,却轻视甚至完全忽视个人收入分配的缘故。因而,他们也就看不到作为“有情感的工具”的劳动与其他物质生产要素相比,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投入程度具有“情绪依赖型”的特点,从而不了解工资收入所具有的激励功能以及不同工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两章专门论述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但是他更关心如何论证清楚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而没有看到这两种工资形式从激励安排的角度所具有的功能。(15)实际上,自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以来,这两种工资形式就被企业主依据不同的环境相机地采用着,人们在实践中多少是了解到不同工资形式的激励作用的。(16)只不过马克思(还有古典学派)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把这类问题给遮蔽起来了,因为对于考察国民总收入在几大主要阶级或收入范畴之间的分配来说,把劳动者视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已经足够了,据说资本家有能力促使劳动者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和“通常的强度”来工作,所以没有必要去思考劳动者也可能是“不听话”或者“会偷懒儿”的工具的问题。(17)当代美国具有新古典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虽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仍然拘泥于阶级对立的范畴,也未能实现真正的激励理论建构。
但是,就完整的分配理论体系建构而言,将工资收入分配的研究仅仅限于上述这种层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现实是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性为其本质特征的,而这种特征恰恰决定了劳动这种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投入程度不再像以往的理论通常所假定的那样具有单纯的技术给定性。发现和认识劳动要素的这一新特点对于分配理论研究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因为它不能不促使经济学家去关注这一特点对实际的收入分配过程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说,现实的分配机制是怎样应对和解决劳动者这一“有情感的工具”可能出现的实际投入程度不足问题的,进而开始重新思考收入分配的社会功能到底是什么。这样,分配、主要是工资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便凸显出来了,工资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这个早先曾被视为无关宏旨的问题也变得至关重要了。而一旦沿着这一思维线索来展开,分配理论的面貌必然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层次。近年来基于激励视角的分配理论的发展,正是体现了上述现代经济学分配理论分析层次提升与理论内涵深化的过程。这种分配理论摆脱了以往各种分配理论所共有的分析模式,它将理论的中心从收入分配的补偿功能转向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从收入份额的不同数量划分转向收入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并借助于信息经济学等新兴的思想观念与分析技术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的现实条件下收入分配的运行过程与内在机理。这就填补了以往分配理论在逻辑层次上的一大空白,极大地丰富了分配理论的内涵。
所以,毫无疑问,这种基于信息不完全和以激励为导向的分配理论与以往所有各种基于完全信息从而“激励缺失”的分配理论,都具有一种总体上的逻辑互补关系。就具体的理论内容而言,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性更是随处可见。例如,与人力资本的分配论相比,它们之间在分析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决定上形成了“努力”因素与“能力”因素的互补视角;与新古典的职能分配论相比,它们之间在工资份额决定机制分析与工资份额实现形式分析两方面是相互补充的;与此相联系,它们双方在舍弃还是包含制度因素方面也是相互补充的。与古典派及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传统相比,也体现出许多具体的互补关系。这里仅指出一点,即它们在制度分析上的互补性。古典派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用社会政治条件诸如财产权来解释收入分配)体现在职能收入分配上,而激励理论的制度分析则体现在个人收入分配、主要是工资收入上。前者包含着大的社会政治、阶级或集团之间的关系,后者只包含普通经济活动中任意两个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稳定与不稳定问题,后者只涉及微观组织形式是否有效率的问题。所以,那种因为二者都包含制度因素就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是现代制度经济学鼻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至于试图用马克思的分配论去取代激励的分配论,或者相反,因为偏好激励的分配理论的解释力就将马克思的分配理论视为过时的无用之物,就更是与科学的态度相去甚远了。正确的观点只能是:它们在理论分析的不同逻辑层次上体现了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三、政策应用的科学思路:兼容并蓄与择适而用
不同分配理论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相互补充关系,要求我们不仅应该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采取综合比较的方法,而且也需要在政策研究与应用方面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
具体来说,对于现实中那些由非市场价格因素引起的,或者说外在于市场机制的收入分配不均等或不公平现象,必须借助于古典派和马克思分配理论所蕴涵的调节机制来加以减轻或者消除。如果撇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所包含的那种极端化的政策含义不谈,那么从古典派与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中还能引申出一种具有历史现实性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这就是通过建立与健全有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以及由政府实施一系列相关的旨在弱化劳动者与非劳动收入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收入不均等问题。这种调节机制的理论基础是古典派及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主要受社会政治制度条件决定、并且非劳动收入由于是作为一种被扣除的“剩余”而反映了各社会集团利益对立关系的思想,故而它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便是着眼于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换言之,古典及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对于处于市场运行领域之外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必须用市场调节机制以外的办法来解决。从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情况来看,近年来这种处于市场运行领域之外的收入不均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至于成为导致中国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显然,解决此类问题只能运用古典派及马克思的调节机制,而中国政府近年来也正是这样操作的——对于贪官和不法老板的绳之以法,对于“黑砖窑”、“黑煤窑”和“血汗工厂”的取缔,以及各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的出台与完善等等,本质上都体现了古典及马克思分配思想在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上的应用。
另一方面,对于现实中那些在市场运行领域之内所出现的各种收入分配不均等或不公平现象,则应该主要依据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思路来实施政策调节。如前所述,新古典分配论的基本思想是市场价格机制按照要素供求亦即边际生产力规律来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如果在这一领域出现收入分配不均等或不公平,只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市场环境不完善;其二是各要素供求比例不均衡。从前一方面说,垄断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近年来石油、电力、电信等行业从业人员与其他竞争性行业人员在平均收入上所形成的悬殊差距,就是这种市场环境不完善的一种反映。此外,市场的分割与缺乏统一性也是一个重要表现。例如,城乡之间、主要与次要劳动市场之间的分割和缺乏统一性,也造成了城乡不同区域或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扩大。与市场分割相关联,市场信息不完全与摩擦性因素还会导致同一区域内部发生职位空缺与人员失业同时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无疑也会助推国民之间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加大。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完善市场环境入手,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旨在促进市场机制调节功能完善化的政策措施,诸如产业规制与监管、消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来实施干预。这种干预不是替代市场,而是要通过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均等,促进收入的均等化。
从后一方面来说,主要与要素禀赋有关。例如中国劳动者平均工资率与资本所有者的平均收益率相差悬殊、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的现象,完全是由中国劳动力过剩从而其平均生产力低下造成的。而劳动力内部简单操作者与高技能人才的收入差别则除了原始禀赋以外还取决于后天的人力资本差别。缓解此类收入不均等程度同样可以遵循新古典理论的思路,即人力资本的思想。政府通过制定有效的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职业培训计划等等旨在提高普通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人力政策”,可以逐步改变原有的要素禀赋格局,使原来大部分的“原始人力”提升为“人力资本”,这样就会增进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起点”均等。因此,如果说前一方面的政府调节措施是从市场机制运行的过程方面来弥补其不足的话,那么这后一方面的政府调节作用则在于为市场调节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前提条件。
上述两个基本层面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古典及马克思的分配思想还是新古典的分配思想,它们对于政府实行收入调节政策以促进收入分配的均等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参考借鉴意义。当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导致收入不均等程度扩大的主导性因素可能不尽相同,从而不同分配理论的社会实践意义与政策借鉴价值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越完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时,新古典分配理论的作用空间就更大些;在相反的条件下,古典派及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传统则更有影响力。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可以说综合了发达与不发达社会的各种特征,收入分配上的各种矛盾既源于经济运行的市场化,也源于市场体制的不成熟。因此,每一种分配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面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政府如何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除此以外,政府政策还面临着如何协调和权衡收入均等化目标与其他经济目标关系的问题。在这方面,同样可以从不同学派的分配理论中汲取思想养料。就促进收入均等化与保持经济高效率的关系而言,各种学派基本上都持有一种“两者兼顾”的立场,即使是强调市场机制作为唯一调节手段的新古典理论也不例外,因为根据其货币收入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同是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收入分配越均等将意味着国民总福利越大。当然,如何来具体地实现“两者兼顾”,不同学派却显示出不同的理论与政策倾向,以至于究竟是以均等优先而兼顾效率、还是以效率优先而兼顾均等,往往被视为经济政策领域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加以思考,将会发现,其实在收入均等与经济效率这两大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像以往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着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比如,从上面我们关于政府促进收入均等化所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措施大多都是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至少是与经济效率的目标不矛盾的。例如,惩治贪官,遏止“权钱交易”等“寻租”、“创租”活动,将有助于社会资源在生产领域的有效配置;消除市场分割、完善信息流通,也会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所以严谨地说,不同学者在如何兼顾实现收入均等与经济效率这两大社会目标上面所存在的差别,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究竟哪一个目标在前、哪一个目标在后这样一种简单排序上的差别,而是体现在他们为实现这两大目标所主张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调节方式的不同上。比如,古典派及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传统就比较倾向于采取政治、法律手段等等“外生”的、直接干预的、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激进的方式,而新古典的分配理论传统则更热衷于采取完善市场机制调节环境等等“内生”的、往往是政府间接干预的、比较温和的调节方式。因此,各派分配理论在实现收入均等与经济效率两大目标的政策选择上,也是可以实现互补的。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势相机地采取不同的调节措施:当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比较平稳、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不突出时,一般采取较为温和的调节方式来保增长、促均等即可。而当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矛盾突出并由此导致社会经济运行不稳定时,则需要采取作用程度较为强烈的各种干预措施。
在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收入调节政策与实现资源充分就业的总需求调节政策之间,也存在着与上述情况类似的问题。作为古典传统当代发展的后凯恩斯学派,由于通过部门结构分析直接把工资、利润等范畴的分配与总需求联系起来,实际上蕴涵着收入分配向工资倾斜将有助于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含义。这意味着,当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相对有利于资产者而不利于劳动者的情况下,也就是存在结构不均衡状态时,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收入均等的收入调节措施来实现。而当代的新古典主流派——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综合则是直接由微观市场引申出总需求,没有考察分配因素与总需求的相关性。这种分析视角差别也为政策措施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基础。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突出时,政府通常可以采取主流派主张的单纯的总量调节措施来管理总需求。而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时,则需要采用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与刺激总需求并举的政策。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在国际市场需求缩减、国内城镇居民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来扩大国内总需求的做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政策思路。
最后,关于基于激励的分配理论的政策含义也值得关注。我们知道,激励理论的核心是如何使分配制度的安排达于“激励相容”的理想境界。而所谓激励相容,说到底就是通过经济当事人合作分享经济收益来实现既定经济活动效率的最大化。总收益在各经济当事人之间分享得越公平,对于代理人特别是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就越大,其劳动生产率进而整个经济效率就越高。因此,激励理论蕴涵着“合作比竞争更好”、“分享比独占更佳”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也为公共政策干预和补充市场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因为,尽管合作可以实现共赢,且实现激励相容也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美好状态,但是单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有时往往是难以确立有效的促进合作共赢的制度安排的,至少在个体当事人经过漫长的、成本高昂的“学习过程”之前是如此。现实中我们所屡见不鲜的经济当事人不愿意合作、反而偏好机会主义行为方式的现象,正是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在实现激励相容方面作用有限或调节失灵的表现。所以,就像在促进收入均等化等等方面通过公共干预活动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一样,政府也需要通过各种必要的政策措施在促进经济中合作共赢的激励相容制度安排的建构方面发挥积极的职能,这将包括有关正规的法律制度建设、道德环境建设、诚信与声誉机制建设等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因而,与所有其他方面的收入政策乃至公共政策相比,这将是一项最为复杂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S.Weintraub,Modern Economic Thought,1977,pp.409-410.
②[美]布莱克等:《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第183-210页,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③N.Kaldor,Essays in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1960,pp.255-256、295-296。[英]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第3编,第2章,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④L.Pasinetti,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ssays in Economic Theory,1974,pp.121-141.
⑤P.Commondatore,"Inside Debt,Aggregate Demand,and the Cambridge Theory of Distribution:A Not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6,2002,pp.269-274.T.Palley,"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the Cambridge Theory of Distribution",2002,pp.275-277.
⑥R.P.Holt and S.Pressman,A New Guide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1,pp.33-41.
⑦T.Palley,"Macroeconomics with Conflic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No.3,1998,pp.329-342.
⑧J.E.King,The Elgar Companion to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3,pp.182-184.S.Bowles,"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Walrasian,Neo-Hobbesian,and Marxian Model",AER,Vol.75,1985,pp.16-36.S.Bowles and R.Boyer,"Labor Discipline and Aggregate Demand:A Macroeconomic Model",AER,Vol.78,1988,pp.395-400.S.Bowles and H.Gintis,"Walrasian Economics in Retrospec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2000,pp.1411-1439.
⑨张凤林:《西方资本理论研究》,第4章,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⑩[美]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第25-102页,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G.Becker,“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0,No.5, 1962,pp.9-49。
(11)I.Ehrlich and K.M.Murphy,"Why Does Human Capital Need a Journal",Journal of Human Capital,Vol.1,No.1,2007,pp.1-7.
(12)G.Baker,R.Gibbons,and K.J.Murphy,"Subjec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9,No.4,1994,pp.1125-1156.E.P.Lazear,Personnel Economics,pp.13,24.E.P.Lazear,"The Power of Incentiv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2000,pp.410-414.
(13)J.R.Hicks,Capital and Growth,1965,p.v.
(14)张凤林:《西方资本理论研究》,第162-170、232-246页。
(15)(1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94-612、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英]波斯坦、科尔曼、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册,第187-193页,王春清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英]马尔科姆·沃纳:《国际工商管理百科全书》,第4卷,第2323-2325页,卢昌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标签:收入分配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微观经济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产品层次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凯恩斯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