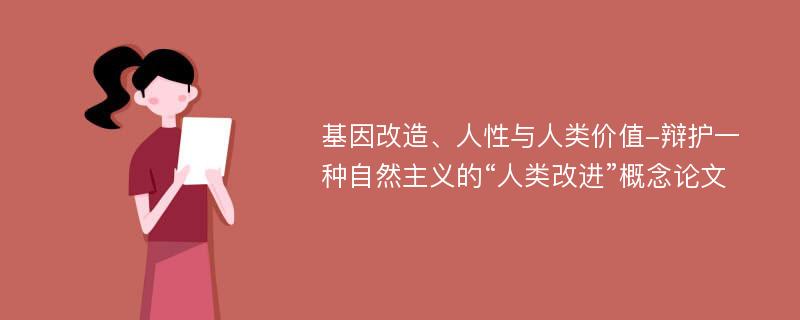
基因改造、人性与人类价值
——辩护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改进”概念
王凌皞*
摘 要 基因改进技术的迅猛进展所带来的争议需要得到道德、伦理与法律上的回应。作为回应的基础,首先必须界定妥当的“人类改进”概念。“人类改进”是对人类而言的真正改进,以基因工程技术为手段,以人类生理与心理的表观性状的优化或改善为目标。这种理解体现了自然主义人性论的观点。人的生命形式设定了人的基本境况,限定了人类价值的基本内容。基于此,人类改进必须满足“人性相关性”“人性完整性”“全局适应性”及“帕累托改进”四个基本要求。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改进”既约束了改进的范围,同时又提供了支持改进的致善主义理由,为立法与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的概念基础。
关键词 人类改进 基因改造 人性论 人性发展观 致善主义
近年来,随着基因筛选、治疗和改造技术的迅速发展,“婴儿定制”也从科幻题材成为现实。胚胎种植前基因诊断(PGD)和遗传学筛查(PGS)已投入医疗实践,商业性机构也已着手开展基因筛查和胚胎性状定制。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自2017 年开始着手进行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并成功制造出世界第一对基因改造婴儿。〔1〕 参见肖思思、李雄鹰:《广东初步查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载《人民日报》2019 年1 月22 日 第12 版。 在向弗兰肯斯坦末路狂奔的道路上,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工程师也不甘人后。继宣布基因敲除获得了五只生物节律紊乱的克隆猴之后〔2〕 参见王佳雯:《中国科学家育出世界首例生物节律紊乱克隆猴》,来源:http://science.caixin.com/2019-01-24/101373885.html, 2019 年5 月20 日访问。 ,又将人脑与认知功能相关的人类基因片段MCPH1 植入猕猴胚胎,培养出智力超常的猕猴〔3〕 参见《如果将人脑基因转给猴子,会发生什么?》,来源:https://tech.sina.com.cn/d/a/2019-04-19/doc-ihvhiqax3930517.shtml,2019 年5 月20 日访问。 。这表明,基因工程的技术进展和应用将挑战人的身份认同,深刻地重塑人际关系,相应地带来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都间接地与我们通过基因工程追求生物学上的人类改进从而“成为更完善的人”这一观念有关。那么,在法律上,我们是否应该通过基因工程追求“人类改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伦理和道德领域的深层观念反思。由此,合理的思考顺序似乎是先大致厘清伦理与道德上的诸多考量,在此基础上再探讨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应对策略。然而,即便在伦理与道德领域,给出明确的回答似乎也困难重重。
再次是建立预算管理过程的信息化控制。设计合同、预算、资金三个维度的控制要素,将协同办公平台与其他系统对接,设定多节点审批流程。以预算和合同管理作为第一层控制策略,以预算审批流程作为第二层控制策略,使费用报销符合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两个层面的控制策略相结合,使整个预算管理体系建立在内控制度下。
一、三个困难
初步看来,关于基因改进的争议是个简单的应用伦理学问题,但在伦理与道德的层面回答这一问题存在以下三个困难。首先,概念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对何谓“人类改进”有一个相对精准和确定的看法或定义,才能够回答“是否允许改进”这个问题。根据构词方式,需要依次考虑:何谓“改进”?什么又是对“人类”而言的“改进”?何谓“改进”就存在诸多标准或尺度。筛选胚胎进而选择出父母(或社会)偏好的性状是否属于“改进”?预防性治疗到底属于“治疗”还是“改进”?对于这些问题,一旦界定清楚改进的概念或用法,就可以展开后续的实质性分析。然而,更困难的问题在于,改进的对象是人类或“就人类而言”的改进。我们如何界定怎么样的基因改变“就人类而言”更好?这看上去是个更为复杂且困难的问题,蕴涵着规范性判断,而不只是概念使用上的约定。
除了概念上的不确定性之外,我们还面临着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另一种不确定性,即道德设定(moral profile)〔4〕 对道德设定的讨论,see Mark Greenberg, “The Moral Impact Theory of Law” 123 Yale Law Journal 1308 (2013).的不确定性。所谓道德设定,大致是指,某种道德相关的实践处于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性背景或语境之下。需要注意的是,道德设定并不仅仅是人们讨论某个道德问题时给定的背景或语境,道德设定本身也可以并且应当成为规范性或评价性判断的对象。例如,是否由政府积极主导并运用国家福利性公共医疗资源提供改进服务,这一设定既会影响我们对“应否改进”问题的答案,同时,改进是否应当由公共财政负担这一设定“本身”也是道德争论的焦点。类似的道德设定问题还有,如果改进技术是由市场提供,即私人自己承担相应医疗负担,是否应当允许?在不同的道德设定下,反对与支持改进的理由将有很大的不同。在私人市场提供改进的情况下,人们会提出强有力的基于“平等”的理由来反对私人的基因改进实践〔5〕 See Allen Buchanan, et al., From Chance to Choic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0-222.,而同样的理由在前一个道德设定中似乎并不成立或其作为理由的力量并不那么强。在国家提供改进服务并向所有公民开放的设定下,出于保全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理由似乎会比私人市场提供基因改造技术更强有力。就如同商品市场的多样性,基因改进技术的市场也可能塑造出不同的多样基因偏好。这两个例子表明,在反对或支持人类改进这个一般性问题上,必须要明确在怎样的道德设定下来展开讨论,然而同时,讨论的结果也将对这些道德设定提供批判性的看法。这显然又进一步增加了讨论的复杂性与困难程度。
除了概念、道德设定的不确定性之外,对“是否改进”的反对或辩护还面临着多元价值(或理由)结构复杂性的挑战。由于这些价值(或理由)性质的差异很大,有些是出于伦理或道德的,伦理上牵涉到德性论(aretaic)自我追求的价值〔6〕 在自我慎思考虑(prudential considerations)这一边,可能包括节制和自我管理、专注力等相关心理能力的提升;在道德考虑(moral considerations)这一边,可能涉及同情、勇敢和同理心、决断力等心理能力的提升。尽管并非以德性论的面目出现,也有论者从结果论角度支持提升人的(心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能力。See Ingmar Persson and Julian Savulescu, Unfit for the Futu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10.,个人道德上牵涉到自主(autonomy)的价值〔7〕 See 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 Polity Press, 2003.,政治道德上牵涉到包括社会正义、资格平等在内的诸多价值。上述诸多价值或理由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这就意味着,对单一价值的集中讨论许多时候只能让我们在局部上获得一个倾向于支持或反对的初步结论。有一些理由——例如出于保有人性的人文主义价值的考虑——或许是全局性的,但恐怕即便是这种理由也需要和其他理由相权衡〔8〕 See Matthew Liao, “Selecting Children” 35 Philosophy Compass 982-983 (2008).。考虑到上文讨论的概念和道德设定的不确定性,理由的结构会进一步复杂化。在道德设定不确定性这边,社会正义这一理由的强度取决于我们预设由市场来供给私人基因改进服务还是将基因改进纳入公共福利、医疗保险。这些价值和价值或理由和理由之间的结构是如此庞大且复杂,使得讨论的参与者很难给出一个考虑周全的终局性判断。
二、何谓人类改进?
由于上述三个困难的存在,对“人类改进”这一主题的伦理、道德讨论很难获得确定而有效的结论,更遑论确定法律应对这一实践的总体原则与具体策略。人们的伦理道德关切与具体法律制度设计总是基于一定的独特“人类改进”概念和相对明确的道德设定,同时,为了得到相对可靠的结论,通常只能集中地考虑其中一种或几种价值。因此,本文也必须(1)界定并辩护一种“人类改进”的概念,(2)确定与人类改进相关的诸多道德设定,并且(3)就某一种或几种特定价值与理由展开规范性反思。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大致确定相关的道德设定(人类改进实践的方式以及相关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语境),然后试着在概念上界定并在规范性层面上辩护一种与自然主义人性观相适应的“人类改进”概念。最后,为了展现这种概念的规范性力量,本文将初步展现自然意义上“成为更好的人”的致善主义理由具有相当的强度,并给出四个约束人类改进的基本条件。
从科技史角度看,有效的现代医疗技术起源和发展相当晚近〔12〕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医学至少晚至19 世纪才出现。See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Chap. 11.,更不必说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这就导致人类非常擅长于改造自然以便满足自身需要,但比较缺乏对自身直接进行生理改进的经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人类对其他生物进行生物学上生理改进的能力。时至今日,品种狗就体现了我们无与伦比的改造能力。仅从体型、毛色来观察,很难相信不同品种的狗都属于犬科,更难以相信它们会是灰狼的亚种。对于需要看家护院并帮助驱赶羊群的牧民(改进发起者)来说,狗的诸多区别于野生灰狼的生理和心理性状当然是一种改进,然而,对狗(改进对象)本身却并不一定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人类驯化的狗不是好狼。当我们说某只品种狗——由于毛太长、四肢太短、呼吸系统机能不健全——不是一匹“好狼”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标准并不是针对人类的需要和偏好,而是对于改进对象狼“自身而言”。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改进,可以将其称作“发起者而言的改进”,是指改进发起者对改进对象生物学性状的改变满足了改进发起者自身的需要和偏好。而对于后一种意义上的改进,我们可以将其称作“对象而言的改进”,是指改进对象生物学性状的改变对被改进对象自身有利或对其自身而言是一种积极的“好”。
在初步厘清道德设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处理最核心的概念以及相关的规范性问题:何谓“人类改进”?在概念上,“基因改造(genetic modification)”并不等于“基因改进(genetic enhancement)”。但在实际事例中,清晰地区分“改进”和“改造”却并没有那么容易。比如,将认知功能相关的人类基因片段MCPH1 植入猕猴胚胎,从而培养出智力超常的猕猴,对于被改造的猕猴而言是否是一种“改进”?
出于论证次第的需要,本文先大致限定“人类改进”这一实践相关的道德设定。本文所要讨论的人类改进大概有以下四个前提。(1)以法律上的“核心家庭”形式组织家庭,通常而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极强的抚养义务,同时在生育权与抚养权等领域也享有较大的特权或自由。(2)通过基因工程实现的人类改进主要是由私人部门提供服务,换言之,我们所讨论的人类改进并非公共福利或社会保障的一部分。(3)这里所讨论的“人类改进”是由父母决定对其所有的胚胎实施基因改造,从而某种程度上“提升”即将诞生的孩子在诸多方面的能力或表现。〔9〕 这就排除了某种曾经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优生学(eugenics)”顾虑。本文将放弃使用“优生学”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在语义上已包含强烈的规范性倾向并承担了太多的历史包袱。对优生学历史的简要介绍,see Allen Buchanan, et al., From Chance to Choic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2(4)这里的“基因改进”是指基于对现有胚胎进行基因改造的技术来实现,而并非在多个胚胎中筛选拥有最佳基因的胚胎。〔10〕 对这一区分及其意义的讨论,see Matthew Liao, “Selecting Children” 35 Philosophy Compass 973-974 (2008).当然,以上这四个要素也许并未穷尽所有道德上的重要因素。这些初步的限定只不过大致框定实质性讨论的界限,以便将一些道德考虑——比如家长主义政策、优生学等排除。此外,这些作为讨论前提的预设也并不表明笔者在规范性评价上支持这些设定,而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讨论起点,以便限缩需要考察的问题域,有利于更集中有力地展开后续的实质讨论〔11〕 比如,尽管设定私人部门通过市场的方式提供人类改进服务,这并不表明笔者总体上支持人类改进的商业化。考虑到社会正义或平等的价值,国家至少应当在范围上限制基因改造的选项。反过来,设定公共部门通过社会福利性质的医疗服务提供人类改造也会面临很多问题。在类似义务教育的强制改造的情形下将面临家长主义干预过度从而损害自主价值的责难,而在自由改造的情况下又面对社会正义的顾虑——比如公共资源在治疗疾病方面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要优先满足额外的改进。 。
第一,“人性相关性”要求。我们大致上可以确定,和“人性”或人的生命形式关键要素无关的基因改造并非人类“改进”。这里的重点落在“改进”上。对人类皮肤、瞳孔和毛发颜色的基因定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人类“改进”,因为皮肤、瞳孔和毛发颜色并非人的生命形式的关键要素,类似地,身高的改进也并非人类“改进”。相反,人的理性、生理或情感能力的提升则满足这个标准,因为人性包含了理性认知、身体运动和情感能力这几种生物性状。如果改进的范围不属于这些关键的性状要素或和这些要素无关,则我们很难说这是对于“人”这种生物来说的改进。这个标准可以解释下面这个有关基因改造的强烈直觉:我们似乎倾向于反对改造胚胎以便筛选和改变孩子皮肤、瞳孔、毛发颜色和性别。真正的理由在于这些额外的改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出于孩子自身而言的好”的改进。这种做法并不存在道德上的任何理由来支持,只不过是父母主观偏好的投射或社会性偏好的反映。
“基因改进将会改变人性”这一前提难以成立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它预设了单线条的“基因决定论”。基因与环境互动的过程是复杂的,表观性状是基因和环境两种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32〕 See Norman Daniels ,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and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0. 而“基因改进将会改变人性”这一主张似乎预设了基因和表型之间直接而充分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这显然是对生物基因功能的误解。我们可以设想:人类基因a 在环境B 下的表达是表型1 (疾病),基因a 在环境C 下的表达是表型2 (健康),基因b 无论在环境B 和C 之下都表达表型2 (健康)。假设科学家运用药物阻断了基因a 在环境B 之下的表达,我们似乎并不会说科学家改变了“人性”;同样地,运用基因改造技术将基因a 人群改造为了基因c,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也并没有改变“人性”。
电阻抗成像中图像重构时,电极采集数据的精度影响图像重构的质量。微通道截面电极不同的结构、数量和排布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电势分布。先前的研究考虑到微流控芯片的加工工艺,电极排布到菱形微通道的两侧(图3(a)),这种排布方式中利用8个电极实现了电阻抗成像检测[11]。本研究采用圆形横截面,电极数目为8电极、12电极与16电极,电极的排布方式及尺寸如图3(b)所示。
三、自然意义上的“好”
在关于人类改进的现有讨论中,基于人性的论辩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桑德尔和福山为代表的人类改进反对者忧虑一旦放任这种“普罗米修斯式野心”,我们人类也许会出于主观目的和欲望改变人的本质(human nature)〔14〕 See 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6-27., 进而丧失人性(humanity),也就是那些“界定了我们是谁并应向何处去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property)”〔15〕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p.101.。简单来说,他们主张“必须捍卫人性”。其论证的简单结构是“改变人性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基因改进将会改变人性,因而不允许基因改进”。〔16〕 See Matthew Liao, “Selecting Children” 35 Philosophy Compass 982 (2008).
然而,这个过度简单化的人性论证是失败的〔17〕 如果说人的性状(内隐的基因以及其他外显的生理、心理与行为性状)独特性界定了人性,并且我们应当保全或发展如此被理解的人性,就会出现威廉姆斯(Williams)所讥讽的状况:“如果人们不加思考地执迷于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典型差别入手来界定人性,并出于这样的人性原则而行动,人们最后将会面对这样的一套道德要求: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生火;保持并拉大人类自身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理差异;不分季节地发生性行为;戕害生态环境;杀生取乐。” See Bernard Williams, Moralit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64.:问题的关键并非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基因改造后的人类还是不是人类或是否还保有人的本质。如果说人性等同于我们晚期智人现有的生物学属性,我们会有“为什么不允许改变人性”这样进一步的疑问。要回应这个疑问,关键的推理必须是一种规范性论证。基于简单人性论证的基因改造批评者必须从无数种生物学属性中识别出那些在规范性层面上重要的人类既有属性,并且通过这些属性的道德重要性来说明我们有真正道德上的理由来保有这些既有属性。盲肠与回肠之间有阑尾或许是人的普遍生物学属性,但由于阑尾并不承担生理功能,反而可能导致疾病,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通过基因改造让人生下来就没有阑尾或许会更好。这么做并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障碍,甚至可以说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这样做〔18〕 如果实施此类手术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笔者相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切除阑尾。 。因此,基因改进的支持者完全可以主张,基因改进的重点在于增进人类的好(human good),至于是不是突破了某些现存智人种群的生物学属性使得被改进后的人群成为“转基因人类(transhumans)”,这并不是关切的焦点。只要存在道德上强有力的理由,可以通过基因改造“保障安全、提升能力、改善健康并且提高生活品质”,我们就有理由甚至有义务这样去做。〔19〕 J. Harris, Enhancing Evoluti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8.
如果上述判断是对的,那么主张简单版本“保有人性”论证的基因改进反对者和主张“成为转基因人类”是一种道德义务的支持者之间或许并不存在真正的“理论分歧”。他们大概都会认可曾任布什政府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的利昂·卡斯给出的一个类比:“无须卡夫卡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把人变成蟑螂这种做法减损了人性(dehumanizing)。而把人变得远高于人(more than a human)恐怕也一样。”〔20〕 Leon Kass, “Ageless Body, Happy Souls” The New Atlantis 1 (2003),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agelessbodies-happy-souls, accessed May 20, 2015.蟑螂的生存方式对蟑螂来说或就蟑螂而言是一种好,但对人这种生物来说,似乎不好;同样地,如果一种生存方式或状态使得人的生活即便“远高于人”,但如果“过得不像人”,当然也未必是好的。因此,并不是自然赋予的既定属性本身是好的,而是自然赋予的既定属性提供了某种看待“好”和“坏”的根本视角或基本约束。“保有人性”论者和“转基因人类”论者完全可以接受这同一个一般性主张。只不过他们或许对哪些自然属性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及重要性的分量存在分歧。例如在基因改造反对者利昂·卡斯那里,这个列表包括“自然生殖、人类有限性、生老病死(human life cycle)、对性的渴望和追求” 〔21〕 Leon Kass, “Ageless Body, Happy Souls,” The New Atlantis 1 (2003) ,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agelessbodies-happy-souls, accessed May 20, 2015.,而在基因改进支持者那里,他们或许会认为生老病死并不能视作不可更易的人性,相反,他们可能会认为从人的角度看,或许超越人的固有寿命限度也值得追求,而长生不老也未必是坏事。〔22〕 J. Harris, Enhancing Evoluti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 4.在这里,他们双方或许都能同意通过基因改造消除了阑尾的人类还保有着人性或依然有着一样的人类本质;而对于从“生老病死”到“长生不老”的这种基因改变,他们恐怕会有严重的分歧。他们的分歧恐怕并非在生物学属性这一经验的层面上,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阑尾和所有人都极端长寿都是对全体人类某一生理性状的改变。他们的深层次分歧可能是在具体内容上的分歧,是针对“对于人类这种生物而言哪些生理和心理性状在规范性评价上重要”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他们对哪一些生物学性状“关于”或“构成”某种具有规范性意义的“人性”有着不同意见。其中一方会主张,人类“生老病死”这种肉体凡胎的生物学属性构成了基本的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在生命短暂和脆弱这一境况下才能令许多我们人类一直珍视和看重的事物富有意义和价值。〔23〕 类似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类具有了不死的能力,那么许多人类冒险将失去意义。亚历克斯·霍诺尔德(Alex Honnold)徒手攀登酋长岩或乌里·斯特克(Ueli Steck)以阿尔卑斯风格横跨珠峰和奴子峰就不再属于英雄丰碑式的人类壮举。对人类生命短暂这一境况的深入探讨,see Thomas Nagel, Mortal Question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1-12.而另一方则会主张,长生不老并不会取消这些已有的人类价值,也不会改变人的基本境况,只是使已有的就人而言的价值获得了增进。借助这种带着自然主义色彩的初步“人性”观念,我们会发现利昂·卡斯的类比推理并不一定成立。从人这种生物的角度看,将人变为蟑螂是泯灭人性;但从人这种生物的角度看,将人变得“远高于人”或许并不见得是坏事。毕竟比起十几万年前的“人”——我们的智人祖先——确实“高”很多。21 世纪的我们在身高上确实远远高于十几万年前的人,也拥有甚至几倍更长的寿命。直觉告诉我们,寿命远高于(过去)的人,似乎是好事;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对称地主张(未来)的人类远高于现在的我们,似乎同样是好事。
到这里,我们发现,保有人性论者与人类转基因论者在根本的理论层面上似乎并不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他们或许会就“寿命”“生育方式”等具体问题有规范性判断上的分歧,但他们都会承认,人的某些生物学性状或特征以某种方式决定了人类价值或对于人而言的“好”。人性概念桥接起了人的生物学性状和对于人而言的“好”或人类价值。只有那些决定了人类价值或对于人类而言的“好”的生物学性状和特征才是“人性”。我们对于人性的关切,并非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兴趣,而是受到这个深层规范性问题的驱动。这并非道德哲学家的理论建构或甚至虚构。我们日常的道德话语就隐含着类似的基于人性的规范性判断: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禽兽”的时候,我们并非是在主张形而上学命题——“某个人是禽兽”。我们真正在做的是展开严厉的道德批评或指责,并且这种批评和指责具有其他道德话语或伦理概念所不具备的深度,意指被批评者过着“非人”的“禽兽式”的生活,完全放弃了人类生活,远远离弃了对于人而言的“好”。〔24〕 孟子所说的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可能就传达了类似的看法。饱食、暖衣、逸居尽管对人而言也确实是一种“好”,但这些“好”对于非人的飞禽走兽也一样适用。而对人类而言的诸多“好”的集合肯定不同于对禽兽而言的“好”的集合。如果一个人仅仅追求与禽兽重合的“好”,这就表明这个人已经放弃了身为人的自我修为和提升(无教),离弃了至少一部分对人类而言的“好”。
一个并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在识别并判定人类价值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人性为人类价值提供了一个锚点,舍弃了这个锚点,小船就将在价值的大海上随波逐流。〔25〕 当代伦理学上最早表达类似看法的应该是安斯库姆(Anscombe)。See 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33 Philosophy 1-19( 1958).
前文对基因改进这个概念的初步厘清已经表明,(1)基因改进中的“改进”显然是要增进对于被改进生物“人类”而言的“好”,且(2)这种“好”不能是社会或文化建构意义上的“好”,而必须是真正的“好”。我们所初步界定的自然意义上的“好”恰巧满足这两个条件。
四、表观性状、基因与“人性”概念的进一步界定
为了对“人性”概念做进一步的准确刻画,让我们再次考虑简单版本的保全人性论证:“改变人性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基因改进将会改变人性,因而不允许基因改进。”〔26〕 See Matthew Liao, “Selecting Children” 35 Philosophy Compass 982 (2008).在上一节中,我们对“改变人性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这个前提展开了批判性处理,我们有理由去保全特定的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人类生物学性状或特征——也就是那些锚定了人类价值的性状或特征。这些生物学性状界定了人的基本境况,进而决定基本的人类价值。在法律哲学中,这个问题常常和“自然法”相关主题联系在一起。霍布斯的道德、政治和法律理论似乎就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然主义倾向的“自然法”之上〔27〕 See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 ed. R. Tu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0-63.,哈特将其称作“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正是人的这些生物学的性状或特征以自然必然性的方式要求我们遵守某些固定内容的法律(同时也是道德)要求:“人的脆弱性”是法律规定不得杀人的自然依据:倘若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天然地覆盖着厚厚的甲壳,那么法律就无需禁止残杀同类〔28〕 See H. L. A. Hart,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 The Clarendon Press, 1983, pp. 79-80.;同样,倘若人类无需外在资源来维持生存,那么财产规则也将不再必要〔29〕 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The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193-196.。不同的理论家对哪些生物学性状归于“人性”“最低限度自然法”或与“人的基本境况”有关或许有内容上的分歧。〔30〕 比如孟子似乎侧重人的道德心理性状部分,而Foot 和Hursthouse 则更多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角度着手进行分析。参见Phillipa Foot, Natural Goodness , The Clarendon Press, 2001; also see 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但诸如肤色、身高、有无阑尾这些生物学性状无关人性,我们也没有道德理由或义务去保持这部分人的生物学性状。
基于上述两个命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和拓展,来界定自然主义“人性”概念进一步的三个特点。首先,“人性”是种群概念,适用于整个人类种群,〔33〕 See Norman Daniels ,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and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0-33.表达的是对人(晚期智人)这一生物学种群的一般判断。〔34〕 See Michael Thompson, “Apprehending Human Form” 54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s 48 (2004).这一概念并非描述或表征某个人类个体生理、心理性状或特征,相反,它给出一般性的总体判断,反过来解释和说明某个智人个体的具体生理、心理性状或特征。这个判断是一种概念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而不是对某个现实个体生物性状的个别描述,也不是对现实的某一群个体或全部个体的统计学刻画〔35〕 这里笔者同意一部分论者在描述性和规范性“正常状态”概念之间的区分。描述性正常状态是在统计学意义上理解“正常”,但不太同意规范性的正常状态包含有文化或社会的标准。在笔者看来,和“人性”规范性那部分相关的“正常状态”概念应该是一个具有真正规范性的用法,取决于是否真的“正常”,而非社会或文化意义上的“视作为正常”。参见陈景辉:《有理由支持基因改进吗?》,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5 期。 。正是因为人性概念的这个特点,在有关人性善恶的论辩中,以个体特征作为反对某种一般人性论的主张并非是有效的反驳策略。“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36〕 《孟子·告子上》。 无论是主张人性善还是恶,人们总是可以找出个体的反例来。
竹林年龄结构保留在3度竹以下,1度、2度和3度竹比例以1∶1∶1为宜,立竹量为140~180株/667 m2,竹子眉径为7~9 cm,最大不超过11 cm。竹子全部钩梢,留存盘数为12~15盘,第1盘开枝越低越好。区块内留竹不宜过度均匀,最好预留2~3个 3 m2 以上的空档地带,以便透光通气,为集中育笋创造条件。
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主张,基因的人为改造或许改变了生物分类学意义上的“人性”。然而,这并非我们的探究兴趣,我们关注的点并非自然演化的谱系或生物分类学。我们的兴趣在于:当考虑到基因改造,我们有没有理由保持全部或一部分人类性状?出于这样的兴趣,当我们试图界定人性的时候,侧重的并非人这种生物内隐的基因层面的性状,而是人这种生物的外显性状或表观性状(phenotypic trait)。例如,人类的发色有着复杂的基因决定机制,有200 多个基因来决定头发的颜色。我们可以设想两个有着相同发色的人,其决定性的基因并不相同。这种基因表达的外部可观测的性状“发色”就是表观性状或表型(phenotype)。遗传生物学家出于寻求科学解释的兴趣,会试图弄明白这些基因发生作用的机制;然而对于我们的这一类兴趣在规范性方面的探究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表型的差异。人们或许对于寿命的长度、头发的颜色和有限的记忆力这三者之中究竟哪些人的上述特征属于“人性”相关的特征依然有分歧。但确定的是,和人性相关的部分并非基因,而是外显出来的这部分生物性状和特征。〔31〕 See Norman Daniels ,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and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0. 对于受到不同基因调整因而显出相同表观性状的生物X 来说,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具有相同“X 性”,而人性也不例外。因此,基因改变并不必然改变人性。在概念上,与自然主义的“人性”概念相关的人的性状与特征是表型,而非基因。
所以保健品的维生素C和药用的维生素C成分完全不一样,保健品只是添加了维生素C的食品,而药品维生素C已经是精确到了分子结构的维生素C了。所以如果真的只是想补充维生素C,建议购买药店药字准的维生素C。如果是送礼或者自己吃着玩,你开心就好。
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简单保全人性论证的批判性处理。这部分讨论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简单人性保全论的批评,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部分讨论为我们揭示自然主义“人性”概念的两个重要命题:(1)人性相关的生物学性状并非基因,而是基因与特定环境互动造就的人的生理、心理等最终显现出来的表观性状;(2)并非人的任何生理、心理性状都与人性相关,只有那些构成人的基本境况从而塑造人类价值的生理、心理性状与人性相关。
接下来,我们将审查这个简单版本的保全人性论证的第二个前提“基因改进将会改变人性”。我们将考虑“基因”和“人性”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保全人性论者看来,一旦改变了基因,就改变了人的生物学性状,进而改变了人性。粗看上去这个连续的推论并无多大问题。基因或DNA 的结构当然是人的生物学“性状”或“特征”的一部分。但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改造基因就改变了人性么?
小乌龟怎么钻得出乌龟壳呢?大林回到女儿身边。他是乌龟啊,乌龟就一定要有乌龟壳的。厚厚的壳,他不能选择要或者不要。
其次,“人性”还是一个趋向性概念。〔37〕 See Norman Daniels,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and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0-34.人性是对智人种群的一般判断,并且要为种群中的不同生物学表观性状提供解释,这个判断就必须对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下发展的趋势进行说明。孟子在这一点上富有极为深刻且准确的洞见:人性并非等同于我们在现实中在具体约束条件或环境下所观察到的人性的某些现实表达。人是一种生物,就如同其他生物一样,人类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也有其稳定的趋向。〔38〕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表现在其内在的潜在发展能力,并不必然等同于一部分人所展现出来的现实性或现实属性。〔39〕 对孟子人性观点的自然主义阐释和进一步理论建构,参见王凌皞:《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1 期。 生物学对基因和表观性状的研究也确证了孟子的“人性发展观”:给定人的基因在多种外在环境与约束条件下不同表观性状表达的可能性,为了对每一个个体的生理和心理性状提供一般的说明和解释,人性也必须是一个趋向性概念。
至此为止的讨论表明,人类改进必须符合以下两点:(1)就改进对象自身而非改进发起者偏好而言的改进;(2)这种改进是一种独立于社会文化建构的真正的“好”(或“更好”)。而这两个初步结论并非是出于讨论清晰性的需要而对“基因改进”概念的人为语义设定,更是探求何谓真正的“基因改进”活动或辩护一种“基因改进”的合理理解。现在的问题就转化为何谓“真正的好”?在本文中,笔者将建议一种自然主义的理解,将真正的好理解为自然的“好”。这种对“好”的独特理解和“人性”的观念有关。
对相应的研究过程进行检验发现,结果显示符合构建模型的要求,此外,利用A-MOS17.0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结构模型。通过该种方式进行产业扶贫影响的探究,看扶贫参与人员是否对产业扶贫有间接的影响。
最后,“人性”是一个选择性的概念。〔40〕 See Norman Daniels,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and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0-34.如果我们描述一个生物X 的本质属性或“X 性”,我们并不会全局性地列举这种生物的所有生物学性状,而只会挑选其中和这种生物“生命形式”息息相关的生物学性状。〔41〕 See Michael Thompson, “Apprehending Human Form” 54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s 48-50 (2004).例如,头发颜色似乎就不构成人类生命模式判断的一部分,即便全人类头发的颜色变了,我们似乎仍然是人类,而并没有变成其他生物。然而,如果像哈特所设想的,假设人类拥有甲壳因而无法互相伤害,或者能够像植物一样从环境摄取营养繁茂而自足地生长,那么似乎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人性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们可以想象这类生物性状的改变会引起人类基本价值体系的根本变动。对于这样一种人类来说,亲子关系将不再重要,许多禁止性道德规范也将失去意义。这些改变,似乎就是和生命模式有关的种群性状改变,他们改变了我们对智人这种生物的“关键描述(vital description)”。〔42〕 See Michael Thompson, “Apprehending Human Form” 54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s 48-50 (2004).因此,就如前文所主张的,人类无数的生物学属性中哪些构成人性,是一个理论性的判断。一些论者主张有限的寿命是人生命形式的一部分,另一些论者会反对这个看法,但他们恐怕都承认,有限的寿命确实是人类的生物学性状之一。他们的争议将是一个和规范性判断相关的理论争议而非纯粹生物学上的经验争议,争议点的焦点是,当我们刻画人类的生命形式,“有限的寿命”究竟是不是对人的生命形式的关键描述。
五、对于人而言的“好”和生命形式
由于人性的概念具有一般性,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人性的概念来说明和解释某个特定人类个体具有的生物学性状。更重要的是,人性概念的一般性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个特定个体作出评估。人性概念的趋向性特征会在评估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会对这些趋向性作出一些规范性判断。比如,在正常环境因素中基因正常表达出来的那些性状将是“正常”的,而受到不正常的环境因素影响、基因变异或表达出错时表达出来的那些异于前述性状的性状将是“反常”的。另外,由于人性概念的选择性特征,我们并不会说所有“反常”或与现行人类种群具有的性状相悖离的性状是“不好”的。例如,假设有一些人类个体拥有天生蓝色的发色,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样的性状是“生理反常”的,但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人类个体是“不好”的人类个体。然而,对于先天近视、耳聋或智力障碍的人类个体,我们或许会使用“生理缺陷”这样的概念。从“反常”到“缺陷”意味着从统计学意义上的描述变为规范性判断,更一般地说,这是一种从“是”推出“应当”的推论。但这种推论并非休谟所质疑的那种简单而直白的推论方式。许多时候,甚至统计学意义上所有人类都具有的生理性状也可能是一种缺陷。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医学上的例子,除了阑尾之外,人类视力中的盲点也是如此。尽管所有的正常人类个体都有盲点,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视力”这一人类眼睛视觉功能的角度看,把“盲点”认定为视觉上的缺陷。在这其中扮演重要一环的就是对构成“人”这一生命形式的关键要素的判断。从人类具有的无数生理、心理特征中挑选出来的那些和人类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关键”性状。肤色、发色并非和人类生命形式密切相关的性状,但视力、听力和理智能力则构成了和人类生命形式相关的关键性状。人们或许可以就人的某些性状是否可以纳入生命形式的关键性状有争议〔43〕 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就提供了一种对高级动物生命形式的关键描述。她认为高级动物的关键性状大概包括“(1)身体部分、(2)运行和反应、(3)行为和(4)情感/欲望”,而用以评估某一个动物个体“好坏”的标准大概包括:“(1)个体生存、(2)种群延续和(3)典型的快乐与享受/典型的免于痛苦。”对于社会性动物,则还包括“(4)群体的良好运行”。See 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 9.,但没有人可以否认自然意义上的“好”和生物生命形式的这种密切联系:“不同形式或种类的生物适用不同的评价性标准”〔44〕 Michael Thompson, “Apprehending Human Form” 10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s 54 (2004).,对这某一物种中的某个体“好”和“坏”的规范性判断来源于这种物种的生物学性状,而并非凭空凌驾于对该物种的事实性判断之上〔45〕 Phillipa Foot, Natural Goodness , The Clarendon Press, 2001, p. 24.。事实上,当我们识别出一种生物X 的生命形式或X 性,并且将某一个体识别为这种生物并置于该生命形式之下,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给出评价该类生物某个体好和坏的标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如果某个人类个体典型的以人的生命形式生存,或合乎人性地生存,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好”的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自然意义上对人类而言的“好”的界定。现在就可以回到本文的主要任务:在概念上界定并辩护一种通过基因改造进行“人类改进”的概念。
在本文开头的阶段,我们对“人类改进”设定了两个概念上必须满足的条件:(1)就改进对象自身而非改进者偏好而言的改进,且(2)这种改进的标准是一种独立于社会文化建构的真正的好(或更好)。我们所界定的自然意义上的“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为何谓“人类改进”提供了确定的标准。
利益分配模式与文献[4]中第一阶段实验采用的方法相同,即在引用链上的节点之间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对最终获奖方案给予一定比例的权重倾斜。利益分配方法经所有参与者讨论一致决定。
这种自然主义的“好”是从某种“客观”角度进行的评价,因而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好”的标准。这种“好”不但独立于社会性的评价标准,也独立于基因改造对象自身的主观好恶判断。根据这样一种建立在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好”基础之上的“人类改进”概念,我们大致可以对哪些基因改造活动属于真正的人类改进做进一步的界定。
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改变人的瞳孔、皮肤和毛发颜色满足了父母对孩子生物学性状的偏好,或许在“发起者而言的改进”意义上对孩子的父母而言是一种“改进”;但对孩子自身而言,这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改进,我们看不到一个孩子瞳孔、皮肤和毛发颜色的改变对其自身有任何意义的“好”。〔13〕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瞳孔、皮肤和毛发的性状可能在某些自然生存环境下是一种好。例如在阳光强烈的热带,深肤色有助于应对紫外线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在这里,我们需要判定的是这些性状在一般意义上是不是好的。 或许有人会反驳,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当然不是“对于孩子自身而言”的一种好,但从社会文化建构的角度看,却可以是一种社会习俗或文化构成性的“好”。不难想象,假设在一个习俗上尊崇黑肤色的社会中,以社会的标准看,黑肤色这个生物学性状将赋予拥有这一性状的人以高贵的社会地位。对于拥有这一生物学性状的个体来说当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好”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好”。
第二,“人性完整性”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致确定,那些通过基因改造方式改变了“人性”或对人类生命形式完整性造成较为严重破坏的基因改造,也并非“人类”改进。这里的重点落在“人类”上。因为“人类改进”的概念预设着这种改进的目标是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将人类改造为其他物种。〔46〕 其他论者也提出过近似看法,但未如此体系化。See Nicholas Agar, “There is a Legitimate Place for Human Genetic Enhancement”, in Arthur L. Caplan, and Arp Robert ed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Bioethics , Wiley-Blackwell, 2013, pp.349-350.因此,如果有一些基因改进将人变得“不像人”,这也并非“就人类而言的改进”。这也解释了我们对于基因改造拥有的另一个强烈直觉:我们拒绝通过基因改造的技术转化为“非人”的物种——尽管从这种非人物种本身看,他们的生物学性状正常、机能完善的话或许是一种“对于这种非人物种而言”的“好”。在科幻作品中,人们恐惧于自身感染某种生化病毒之后成为“丧尸”,甚至以终结自身生命的方式来拒绝变成丧尸〔47〕 此处的“丧尸”概念是技术性的,仅仅指具备非人生命形式的生物体。从丧尸的“生命形式”看,“丧尸”的生存方式似乎并没有那么坏,就如同从水母的生命形式看,水母随波逐流的生存方式——“不用忧虑下一顿在哪里”——看上去也没有那么坏一样。 。放弃了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好”视角之后,这种人类反应变得不可理解:“身为丧尸”并且“像丧尸那样生存”难道不好吗?答案当然是相当明确的否定。我们所真正害怕的,并非是成为丧尸之后过的生活不是一个“好丧尸”的生活,而是害怕我们人类变成丧尸之后过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类”或“好人类”应该过或值得过的生活。
第三,“全局适应性”要求。通过基因改造方式获得的新性状必须满足跨生存环境的全局适应性(global adaptedness),而不能偏向于某一些特定的生存环境。晚期智人大概是地球上地域分布最为广泛的哺乳动物。从酷暑的热带到苦寒的极地,再到数千米海拔的高原,我们人类展现出了惊人的环境适应性。有一些生物学性状或许在某些正常的人类生存环境下是一种“好”,但在另一种尽管也同样正常的人类生存环境下却是一种“坏”。比如人类个体的体型和肤色,在光照不足的严寒环境下,较大体型(有助于保暖)和较浅的肤色(吸收更多紫外线)能让人类有较好的环境适应性因而是一种“好”;但在光照强烈的酷暑环境下,较大的体型(不利于散热)和较浅的肤色(容易晒伤)却变成较差的环境适应性因而是一种“坏”。因此,我们不能一般地说,浅肤色和大体型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好”,这种性状的获得当然也就不是改进。真正的人类改进,改进之后的性状必须满足跨自然环境的全局适应性。这一要求对于社会环境来说也一样适用。我们至少要求改进后的性状在诸多“正常的非极端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都是一种对被改进者而言的“更好”。
第四,“帕累托改进”要求。类似于前面这个全局适应性要求,我们还会要求通过基因改造实现更好性状的获得或能力的增强不能以其他好性状的丢失或能力的减弱作为代价。不妨借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刻画这个要求:“帕累托改进要求”。这个约束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性或人的生命形式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由人类的诸多性状或能力构成,如果其中一些能力得到加强,而另一些能力或许因为这些能力的加强而被削弱。一旦这种变化在程度上超过合理的限度,我们会说人性或人的生命形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例如,假设我们对人类的下一代实施基因改造从而造就“新人”,他们具有远远超过现有人类的同情心水平,但这个情感能力的提升极大地压制了自我利益的心理驱动力。这时候,我们会说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自我利益为主并有限利他”的社会性动物变成了“活雷锋”式的真社会性动物(eusocial animal) 〔48〕 对人类的社会性心理性状与蚂蚁、蜜蜂等真社会性性状的论述,see Edward O. Wilson, 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 Liveright, 2012.。而根据前面第二项约束,人性性质上的改变或生命形式的改变在概念上就不是“改进”。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能力实现不同的“好”,我们很难在不同能力实现的“好”之间进行折算。这是一个价值不可共量或不可比较的问题。〔49〕 对这两个概念的深入探讨,see Ruth Chang ed., Incommensurability, Incomparability, and Practical Reas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比如,假设理性反思能力和感性感受力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理性反思能力增长的“好”是否可以取代或者压倒感性感受力的“好”?答案是否定的。
前两个要求体现了“人性”概念的约束:“人性相关性”要求是说基因改造后性状的改进必须是就“人类价值”而言的真正的改进,而不是在规范性意义上中立的琐碎表型的改进,这就排除了社会、文化性的标准以及针改造发起者而言的利用性基因改造;“人性完整性”要求是说对人性相关人类生理、心理表型的改造其造就的生物必须仍然属于对“人”,而不是其他的生物,因为在概念上,假设改造的结果改变了人的基本境况或生命形式,这将不再属于“改进”。
后两个要求体现了“改进”概念的约束:“全局适应性”的要求源于自然意义上的“好”所具有环境相对性特征。来自基因改造的“好”许多时候是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基因改造后的人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具有的表型或许是一种“好”或“更好”,但在其他特定环境下,或许是一种“坏”或“更坏”,这就不是真正的改进。“帕累托改进”的要求来源于改进所追求的“好”所具有的价值不可共量性或不可比较性特征。并且,“人性”的概念之中也蕴涵了某种不同人类能力之间的均衡或和谐的要求,一旦这种均衡或和谐被打破从而改变人的生命形式,那么这就算不上对人而言的改进。
应该说南通水路和公路运输已相对比较健全,但铁路和航空运输相对较差,这也导致南通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就目前而言,南通多式联运路线主要限制于水水联运、水公联运,这也导致可供开发的联运线路偏少。
本文不会对何谓人类改进作出完备的定义,也不会给出一个人类改进相关性状的完整列表。但上面这四个要求已经大致捕捉到“人类改进”概念的关键要素和核心内容。本文到此为止的讨论不仅是在界定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类改进”概念,同时也是对这样一种“人类改进”概念的规范性辩护。我们对“人性”、人的“基本境况”或“生命形式”及“人类价值”的分析表明,真正的人类改进是一种自然主义式的“就人类而言的自然意义上更好”的理解。对人类改进的上述理解把握到了有关基因改造与人类改进深层次的规范性直觉。这一直觉就是我们有普遍且有力的理由去“成为更好的人”。如果舍弃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方案,我们无从说明或辩护为什么我们有真正的理由去进行人类改进。当然,这种致善论的(perfectionist)普遍道德理由并非是绝对理由或压倒性理由。这一理由的分量会随着道德设定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对“是否应当允许改进”的回答也取决于这一理由与其他理由——比如社会正义、资格平等、自主——之间形成的复杂权衡结构〔50〕 这里的复杂权衡结构并非指“利益衡量”式的平面性比较,也涉及理由和理由之间的复杂结构。在法律中,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复杂结构权衡上,参见王凌皞:《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双维度限制——从公共利益的平等主义构想切入》,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3 期。 。
六、基因改进真的特殊么?
“成为更好的人”是一种普遍的不偏不倚理由,似乎对任何人都具有规范性力量。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完善自我从而成为更好的人的自我责任或要求。〔51〕 托马斯·霍尔卡(Thomas Hurka)就提出过这样的一种“人性致善论(Human Nature Perfectionism)”。See Thomas Hurka, Perfection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然而,在我们所预设的道德设定下,人类改进的实践主要是指父母在市场中购买私人基因改造服务对双方的胚胎进行改造来造就更好的子女。在这种语境下,基因改造并非只是让未来的孩子“成为更好的人”,同时更是父母以他们自己的偏好和选择来“造就更好的人”。许多论者因此看到了“成为”与“造就”性质上的差别造成的规范裂隙(normative gap)——对“成为更好的人”的辩护无法当然扩大到“造就更好的人”。“成为”和“造就”之间的差异在概念上当然是成立的,成为和造就之间也确实存在一定的规范裂隙。然而,基因改造真的特殊么?由于本文的主要任务在于提出一种合理的人类改进概念,篇幅所限,无法对此问题展开具体的讨论。但初步的反思表明本文所发展出来的自然主义进路“人类改进”观不但在概念上站得住脚,其蕴涵的“成为更好的人”这一致善主义理由也具有相当有力的规范性力量。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的原因,京津地区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不断向其集聚。京津两市对环渤海经济圈甚至全国的人才形成“虹吸”效应。河北省受到严重影响,难以吸纳人才,自己培养的人才也源源不断地流出,尤其是技术人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端人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北京、天津、河北省3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每10万人中,北京有3.2万人,天津1.7万人,河北省仅为0.72万人左右。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全国2 000多位“两院”院士,北京市有600多人,天津、河北共43人,与北京相比差距很大。
人类改进是指对于人的表观性状的改进,而基因改进只是实现表观性状改进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因此,基因改造可能并不特殊。人类生理和心理性状并不完全由基因单方决定,而是基因和环境的复杂互动塑造了人。就社会而言,人类一直在对我们生存的环境进行坚持不懈的改造,让我们获得更为友好的自然、社会甚至政治环境以促成人性的充分发展;就家庭而言,父母也竭力为子女创造支持性的物质和情感环境,以实现孩子的最大潜力,成就蓬勃焕发的人生。父母不但有理由这样做,似乎还可以进一步主张他们有义务这样做。用更具有生物学意味的术语来表达,我们甚至可以说,父母有义务改善孩子成长的环境,以便使孩子获得对他们身为人类个体而言更好的生理与心理性状,改善环境或是改善基因只不过是实现改进手段的差异。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也即,我们允许甚至要求父母通过某些方式来“造就更好的子女”,那么我们有何种理由去拒绝父母改变孩子的基因同样将其作为手段来实现子女更好的生理与心理性状?
许多反对基因改进的理由(例如“自主”)在面对这种自然意义上的致善主义考虑时,恐怕很难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对“是否应当允许改进”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将是“允许改进,但改进的范围必须受到极为严厉甚至近乎严苛的限制”。真正可称得上“人类改进”的改进必须满足“人性相关性”“人性完整性”“全局适应性”及“帕累托改进”四个要求。这四个来自“人类改进”概念的要求不但有助于深化伦理和道德层面的讨论,也能够为法律与公共政策回应“弗兰肯斯坦式科学家”的挑战提供强有力的概念资源和极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
④切实加强河道砂石资源费的征收与使用。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认真抓好砂石资源费足额征收工作,要保证“三江”河流100%、其他河流20%的砂石资源费缴入市级金库,其他河流80%的砂石资源费缴入区县级金库。 同时,要切实用好河道砂石资源,将砂石资源费首先用于河道管理。
* 王凌皞,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贯彻机制研究” (项目号17VHJ00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浙江大学2019 年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科学伦理与法律规范”资助。
目 次
一、三个困难
二、何谓人类改进?
三、自然意义上的“好”
四、表观性状、基因与“人性”概念的进一步界定
五、对于人而言的“好”和生命形式
六、基因改进真的特殊么?
(责任编辑:马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