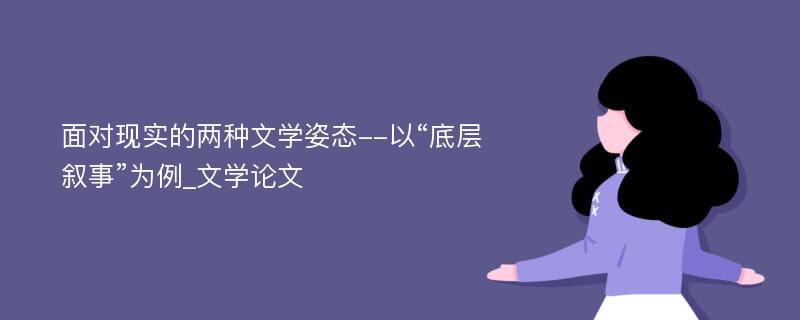
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为例论文,底层论文,姿态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6)05-0051-06
“底层叙述”是不是当前文学的“主流性叙述”还有待考察,但近两年来,“底层”问题的确已“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1]。王晓明断言:“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素材的。”[2] 说得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这句话点明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与“底层叙述”的关系,也就是文学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弱势群体”、“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概念在散文随笔、社会评论和报刊用语中频率很高地被运用了一阵子之后,“底层”作为一个问题在小说创作和评论中凸现出来,说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已到了文学不能不关注的地步。文学和文学家(包括评论家)从来就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寄以特别的同情,倾注富有感情色彩的笔墨,因之以“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素材也就本无特别之处,然而当“底层”成为一种“叙事”,也就是一些人文学者需要借“底层”和“底层叙述”来说事,那就说明文学已经形成一股思潮,而这在实质上是惯以社会良心自命的人文知识分子正被迫对他们生存其中的严重现实作出了反应。王晓明就点破了作家(不如说是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知识分子)借文学以自赎的玄机:
眼前的这个全世界人都没有领教过的巨大而艰难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的压迫和挑战,给了文学取之不竭的活力,刺激我们的作家瞪大眼睛直面人世,用自己的笔狠狠地戳破这现实。[2]
什么是“巨大而艰难的现实”?这正是要由文学(主要的小说)描绘和呈现给我们的。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昏乱怪诞程度愈来愈超出人们的理解能力,甚至超过了作家的艺术虚构与想象,但是要想对令人惊诧或喟叹的社会和个人的生存景况有真切的了解,对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生存事件进行品味与审视,还得依赖文学叙事去重构充满因果关系的生活戏剧。也就是提供一个经验化了的事序结构,以象征实存世界里真实而坚硬的逻辑关系。
然而,当“底层叙述”升级为“底层叙事”,即文学写作的话语性加强以后,文学的分化也就产生了,或者说在文学(小说)的身上,寄予了不同的愿望主体。要是套用莫言的话来说,就是有人着意“为老百姓写作”,有人甘心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3] 这两种写作,体现了不同的写作伦理,自然也表现为不同的文学姿态,反映出在复杂而沉重的现实面前,文学家选择了不同的角色自认。
“为老百姓写作”,就是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没有人代言,“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失语,他们的生存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而在掌控社会命脉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处在社会底层的沉默者,他们的痛楚无法表达,攲侧的社会车轮给予他们的将是更沉重的碾压。弱者的生死不被顾及,受伤害的就不仅仅是这些不幸的人,社会严重失去公正既久,谁也难以保证路基已经沉陷的历史列车不会倾覆。畸形的社会层构为社会自身带来了危机,底层的挣扎与僵硬的车轮发生摩擦的事故前兆让人揪心,这时,处在特殊位置上、最富有人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不挺身而出,为底层人呼喊,向公众发出警告。在专制制度延续最久的中国社会,历代都有文学家坚持为生民歌哭,这并不是传统自身可贵、有效、值得骄傲,而实在是知识人绕不过现实的苦苦询唤。一方面是同情怜悯的人之本性使然,一方面是现实危机的促逼,知识分子爱管闲事,且不改悔,只能说明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里,都更多地保留着人性,更为理智。所谓担当,原义就是这个行当应该挑的担子。在社会分工里,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言论、思考、质疑和批判的职业,这一职业决定了为弱势群体表达集体诉求以维护社会公正以及社会的平衡稳定对于他义不容辞。
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否则他就会丧失在人类社会中已历史地生成的知识分子的规定性。可以有所选择的,仅仅是为弱势群体代言时的表诉方式。文学是与政论相区别的一种更有感染力、更容易为人接受的表诉方式。但对于以文学为手段来表达某种社会意愿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文学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陷阱,它会诱使你从关注、思考并急欲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紧张焦虑中缓解出来,心态、看法与意向都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从社会批评聚焦于当下到从历史轮回中接受教训,从注意阶级冲突到发现矛盾双方的关联与同一性,从急于解决问题到寻找问题的根源特别是文化和人性的根源,从坚持护佑群体的伦理立场到笃信个人本位和热爱生命姿态,从批评纯文学到欣赏语言和想象创造世界的神奇,从拯救苦难到拯救灵魂,等等。如果这种诱惑被抵制,那就显示了进入文学领域的知识者的人格力量与道德修养,因为人生情态越真实、越是具有超越品格的文学,越能消磨人与现实抗争的意志,而关注个体生存形态和生命自身的价值。自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继续充任代言人无关乎人格,而是在特定文化情势中,话语主体依靠审度后选择的姿态收取话语效益。不管由哪一种冲动决定为老百姓写作,都可以说,这样的写作主体应得的和他愿意得的名分,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作家”。“知识分子”与“作家”并不存在等级关系——尽管有包容关系(作家是知识分子的一类),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为社会和文化做出贡献,两者不必要互相排斥。但实际情况却是,新世纪文学就在现实关怀上,不仅现出了两类写作主体的分野,并且让人不明就里地存在以另一方为对立面甚至否定对方的现象,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在知识分子内部遭到轻视。
正是针对这一现象,在创作上具有很强的历史批判精神的小说家莫言,公开表白自己信奉“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表现出另外一种写作姿态,一种丝毫不减损其小说的现实批判力量的低姿态。其实莫言并没有能够、也没有必要做到以一个普通老百姓、弱者、社会底层人的身份去进行文学创作。张清华很有见地地指出,“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写作的,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和条件去写作”,他解释,“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到他们的心声”,所以他“在事实上仍然愿意将其看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种形式”。[4] 在我看来,莫言清醒、自然而执著地保持着知识分子中的一类——作家的角色,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社会改革开放后经过二三十年的艺术实践在思想上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唯其成熟,才不需要端着姿势,因为已经熟谙文学批判现实、支持人生的门径,懂得了语言艺术的力量及有限性。评论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文学态度给以肯定和认同。陈晓明对“小叙事”的意义作了充分揭示,其独到的发现建立于对文学的特有存在方式及其特殊的精神价值以及由这种价值决定的在现今文化语境和社会意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的基础之上。[5] 孙郁十分冷静地看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文学姿态的积极效果,说:“大凡在写作中盛气凌人地教训别人者,文本都有点做作。倒是以普通人的视角进入创作的,给人留下了真切的印象。”“这一些人的写作姿态是自然的,非道德说教者的宣言。”“作者们作为百姓的一员的叙述口吻,它拉近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人们接近于它们,是感到了亲缘力量的。”[6] 之所以有这样的做法和效果,首先是作者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因而可以自信而无愧地为人民代言的人,相反他认识到作家和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样反而使创作收效更大。“一个作者敢于正视自我的有限性时,文本的张力就自然呈现出来。”“消解自己和低调地看待自己,至少把叙述者的精神和对象世界拉开了距离,那是有着重要的不同的”。[6] 证之以近两年的“底层叙事”,同样是现实关怀的写作,高昂的代言人的宏大写作和低调的贴近普通人的“小叙事”意义互见。
近几年的“底层叙事”最富有“为老百姓写作”色彩,并且作为一个涌浪复活了“现实主义”的,莫过于曹征路发表于《当代》杂志2004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那儿》。这是一篇在艺术性上被许多人质疑的小说。但它在文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响,与文学整体上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上的边缘状况显得不太协调。小说发表后的两年里,囊括了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家的专题研讨会开了就不止一次,《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在现当代文学界有影响的刊物,都开辟了研究专栏。对这部直接描写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命运的小说,提倡人文精神的中年学者和带有新左派特色的青年学者反应最热烈,这已经说明“底层”被书写并作为一个“问题”引起强烈关注,它既是小说正在调整自己和现实的焦距的一种文学现象,同时又大大超出了文学的一般审美范畴。《那儿》的写作、发表与对它的讨论,倾注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丰沛的现实批判激情和溢于言表的忧患意识,它满足了文学对“现实主义”回归的呼唤,更展演了一批未被名利收买和犬儒主义化的思想者抵抗现实的激越文学姿态。
曾经作为领导阶级的产业工人群体,一夜之间沦为失去了起码的生存保障的社会弃儿(有些命不好的下岗女工还要靠卖淫维生),并且在历史进步的名义下一再被欺骗、被玩弄、被剥夺,每一次试图维权的挣扎都不过是落入权力阶层和资本勾结设下的圈套,作为他们的真正代表的工会负责人的悲壮努力,在权力机器的威逼利诱和工人兄弟的误解的夹击下一塌糊涂地溃败,终至无路可走,只有带着巨大的困惑、茫然、无奈和悲愤,用自己的生命殉了那个远去了的辉煌理想——他是用自制的气锤砸去自己脑袋的,死前还打了一大堆镰刀斧头。他的自杀最后成了一个筹码,稍稍改变了一场生意的结局。这就是《那儿》给我们讲述的令人震惊的底层现实。这触目惊心的现实,对读者的同情心、正义感、良知和道德感都构成了挑战,使那些与底层相隔绝的人一下子严肃起来,认真关注这种现实并思考它的前因后果。作家的创作目的非常明显,虚构一个惨烈的故事,不是为赚取泪水,而是要让大家正视、思索,拨开市场意识形态的迷障,看清与概念化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严酷的生活真实,从习惯和麻木中警醒起来,共同抵抗和改变现今社会已经非常不合理的现实。也由于创作目的过于明显,由于表达对另一阶层的伦理态度的心情过于急切,《那儿》在实现思想主题时留下了生硬的痕迹。为了掩盖这些痕迹,作家不惜在各种场合对作品以及自己的创作追求进行阐释。一些与曹征路持同样的现实批判态度的批评家,也对小说进行了过度阐释。“为老百姓写作”的问题——阐释大于创作,在这里暴露了出来。对这一现象加以考察,有助于认识知识分子的伦理立场和担当意识的可靠性及其在文学活动中的限度。不处理好创作意图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思考与写作都可能成为一种僭越,既无助于激起道德愤慨的现实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文学独特社会作用的发挥。
曹征路明确表白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意图:“写小说是表达我个人对时代生活的理解和感慨。”[6] 他把自己定位在“真实地记录下我能感受到的时代变迁”[7]。在他的文学选择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占据着中心和主导位置,他说:“我认为文学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作家倘若对社会进步不感兴趣对人类苦难无动于衷,是可耻的。”[7] 有这样的角色自认和文学选择,势必排斥过分专业化的、与底层人民隔绝的知识分子和突出审美价值的纯文学。他知道“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总体上是得益群体,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对底层人民的苦痛是很难感同身受的,至多也就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已”,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不能满足于“退回书斋从事更加专业的活动”,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精神溃败的表现。[7] 对于纯文学,他也有看法,指出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倡纯文学,主张心灵叙事是对的,但90年代以后把它推到极端,说文学担当了社会责任就不叫艺术则离谱了”[7]。出于对现实批判功能的确认,他质疑“文学回到自身”这一文学史判断。这种由“巨大而艰难的现实”激起的愤怒情绪所左右(曹征路说他写底层就是为了愤怒一回,在写《那儿》时写着写着就被愤怒左右了)的不无褊狭的文学观,被他带进了小说创作。小说的叙述者“我”在为“小舅”的悲剧撼动后,央求“写苦难的高手”西门庆写一写“小舅”,已经被“小舅”的遭遇修改了文学观的西门庆,在拒绝请求后,一边撒尿一边不无恶意地调侃、揶揄、讽刺了现代派主题的纯文学。作者写道:“他甩着他的家伙笑起来,说你呀你呀你呀,你小子太现实主义了,太当下了。现在说的苦难都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苦难,是抽象的人类苦难。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那还搞什么纯文学?再说你小舅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还有性能力吗?没有精彩的性狂欢,苦难怎么能被超越呢?不能超越的苦难还能叫苦难吗?”[8] 这是一段带有侮辱性的很不雅的文字,是小说作品的硬伤。可见非文学的情绪对作家和文学都会产生伤害。
为表达“对时代生活的理解和感慨”去写“底层”,不见得就已经消除了跟“底层”的隔阂。为写底层而写底层,小说就可能成为愿望和概念的产物。事实上,小说以《那儿》为题,就是对一个象征一种已逝理想的概念的诠释,他试图传达作者的一个理念,即工人阶级的命运与共产主义理想相依存。工人阶级从领导阶级一下子堕入社会底层,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被抛弃;理想被抛弃,工人阶级才无处存身。这一概念的循环在逻辑上就有悖谬。在小说的故事里,自杀并不是“为民请命敢于担当”的工会主席朱卫国的唯一结局,即使因为一次次好心办坏事无以做人,自杀方式的选择也不符合这位并无太多政治关怀的工人的思想行为逻辑。作者明明知道“在我国说‘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也许只是一个幻觉”,还硬要让在社会改革的乱石滚落中看清了自己和所属阶级的能耐,仅仅挂着工会主席头衔的干粗活出身的一个工人,“真诚地迷失在概念里”[7],是不是有欠真实。如果说,“小舅”朱卫国以死抗争时被强加进那么多的政治想象,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作者为了制造骇人的悲剧效果,把这个工人利益的维护者推上了断头台!从小说的理念化命名,到主人公悲剧结局的创新,这个作品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它很快被一批洞察以企改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改革背后的政治黑幕的人文学者看中,作为他们表达社会判断的契机和依据,因为不管作品怎样呈现不足、叙述有余,但比起类似汪晖的谈企业改制的有理有据、逻辑严密的论文表述来,小说无疑是批评者更好的思想容器。看一看韩毓海、旷新年等思想型学者对《那儿》的精彩阐发①,我们感到,《那儿》的备受关注,引起热评,主要不是小说为文学把握现实提供了多少新经验,而是它成功地促成了一次思想者的集会。《那儿》思想大于形象的特点,跟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相似之处。其实他们本来有血缘关系,有人把这类创作称为“新左翼文学”并非没有道理。概念化、公式化、以性爱为人物行为的内驱力(《那儿》不例外,旧日恋人杜月梅是朱卫国性格爆炸的火药引子),是左翼文学的通病,原因很复杂。从一个方面看,文学是载离愁装别恨的舴艋舟,塞不进攻城略地的兵马,硬要把乌托邦的秩序强加给人情欲望撞击的世界,文学的自然风景也就变成了打仗才用的沙盘,目标明确,路线清楚,但毕竟与实战不是一回事。
倒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提供了“底层叙述”的理想形态。这类写作,作者不高高在上,不摆出悲天悯人和拯救者的姿态,不为别人的生活和世界做什么设计,不为改变现实改良社会提什么方案,而是站在底层社会的同一地面上,邻居般地关心摄入他的小说世界里的主人公的命运遭际,跟他们一起体味生活的苦乐悲欢,对不幸者的悲哀即使掬一把同情的眼泪,也娓娓道完那仿佛命运安排的人生故事,决不用自己的好恶打断它、扭转它。例如排在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前三名内的两个短篇,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和黄咏梅的《负一层》。
《负一层》明显是底层叙事,作者把视点放到了比楼房底层更低的地下车库,追摄一个无人肯予听取的“失语者”的生命的低弱声音。因为无人倾听,她才“失语”。因为无处诉说,她才一次次在暗夜里升上楼顶,把一个个问号——那是无人肯为解答的生的疑问和困惑——挂在天上,这是沉默者的无言的“天问”。她并不是没有沟通能力,是社会没有给她沟通的机会,在地下看车场,有车的有钱人,谁也没把她看成是能说话、有感情、需要沟通的人。在无人可与沟通的情况下,她只能听车子与车子交谈。车子与车子都需要交谈、沟通,何况是人。这个不屑于与她沟通的社会,跟她早已没有共同的语码。一次仓促间偶尔的沟通,出了致命的错,她因语言的误会得罪了老板,被辞了工,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只有最后一次升上楼顶,从三十多层的楼顶上飞了下来……作者始终不为她代言,所以她至死沉默,无人知道她的心愿和委屈。连她的父亲也不理解她,导致在她冤死后连赔偿的权利也被剥夺掉。小说不是没有一点观念性,但作者就是不把叙事意图说出来,而让读者去领悟。《锦衣玉食的生活》的主人公艾芸,也是个不幸的女子。她本来有丈夫,有儿子,有工作,生活中不乏指靠和欢乐,她向来自尊自爱,有上进心,不虚掷生命。但不知为什么——其实是为了生计,那些属于她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似的失去了。因为生存压力加大,她失去了性趣。由于不能满足丈夫的需要,导致丈夫偷情,她与丈夫离婚,丈夫走了,儿子也被带走了。在说不清来头的商业交易中,单位散伙,她丢了工作。当所有的挣扎都失效后,她把希望交给了来世。但残酷的是,生命被夺去后连在来世过锦衣玉食生活的卑微愿望也被打破。作者没有出面指责现实,但从一个弱女子只能以虚妄为希望,不是可以窥见现实是多么令人绝望吗?这篇小说已列入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笔者在即将出版的排行榜作品汇编为该小说写的短评中,认为《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当下十分引人关注的底层叙事中,提供了新鲜的创作经验:
小说没有直接反映转型期经济调整、社会分层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社会不公,而是聚焦于特定的生命个体,逼真地刻画社会政治与经济运作给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造成的严重后果。小说虽然也涉及弱肉强食的无理与蛮横等社会现象,写到职工不仅经济上受到盘剥,而且人身受到伤害,但是,作品更多的是写艾芸这一个女子在遭遇到命运的不公时产生的情感反应,突出她的生活意志不断被外部权力所否定产生的尴尬、无奈和悲伤,以及人生愿望被嘲弄后自我突围的虚热与疼痛。小说多次写到艾芸为自我、为亲人流泪伤心的细节,尤其写到她深夜里准备孤身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忍不住打电话与已离婚的丈夫凄然告别的情景(其实对原本属于她的那些多么不舍)。这种弱者在历史过渡期的混乱脚步踩踏下的无声辗转,远比叙述者站出来愤然抗议有艺术感染力,因为它不事张扬地表达了对现实的拒绝与批评,它引起我们思考是什么改变了艾芸们的生活。这是一种纯文学的写法,一种更有艺术生命力的表现方式,一种相信读者的悟性和判断力的文学态度。
注释:
①请参见韩毓海的论文《狂飙为我从天落——为〈那儿〉而作》,吴正义,旷新年的论文《〈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均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