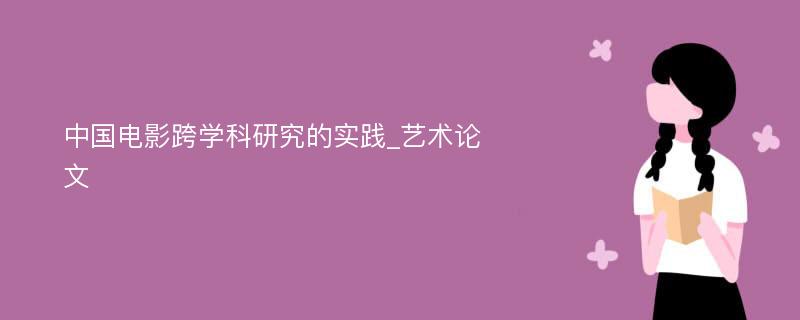
华语电影跨学科研究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5)01-0001-8 学术前沿:华语电影跨学科研究 主持人的话(张英进):2013年11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宋炳辉教授邀请我为《中国比较文学》主持一个电影研究专辑,我欣然同意。首先想到的焦点议题是我近年努力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我曾在《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发表过《比较文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其实电影研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本专辑包括5篇论文,第一篇回顾中西电影研究的跨学科发展,然后以其后的4篇论文为例,简述华语电影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并指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视觉艺术课题和方向(张英进);第二篇论文论述早期中国电影与都市视觉文化、明星身体政治(陈建华);第三篇辨析电影与话剧的艺术媒介特质的区分与互动(包卫红);第四篇分析电影重拍与好莱坞-上海-香港的地缘政治和艺术再创(王亦蛮);第五篇梳理台湾录像艺术与实验电影的谱系(孙松荣)。这个专辑力图在电影与文学之外,开拓电影与其他艺术媒介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电影研究的跨学科特性① 电影的诞生至今不过一百多年,但这个艺术—技术—产业—市场的综合体制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电影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从学术角度来说,电影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是1950年代后形成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电影研究一直努力扩大自己的学科范围,构建自己的学科特点,其结果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科,而是一个开放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电影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表现在学科本身的发展历史、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近几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的总体互动趋向。 首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电影研究在欧美学术界的发展。1950年代以前,电影渐渐进入欧美的大学课堂,其最早的形式是附属的选修课程,在英文系、戏剧系、历史系或综合人文学院开设,所关注的内容是传记式的电影史料(人物、作品、产业),或者电影与其他邻近学科的关系(文学、戏剧、历史、哲学)。电影研究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要到1960年代,其主要理论来源于相对美国而言的所谓欧洲大陆理论,即后来占学术主流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对电影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创造了一套以影像、情节为分析对象的电影理论,如缝合理论(suture,即观影者的主体性形成)、叙事理论(整合俄国的形式主义)等。与这些理论同步发展的是欧美大学电影研究所的建立和电影博士的培养。当1970年代第一批电影博士进入学界时,电影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并迅速扩展电影理论的视野,从传统的经验主义对文本细读、产业数据(生产、发行、放映、接受)的重视,到电影与意识形态、政治、历史、社会语境的互动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大大推动了电影研究的学科发展[1:14]。到了1980年代,电影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形成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又对更新近发展的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比如通过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凝视(gaze)理论分析大众文化现象(流行音乐等)[2]。1990年代以来,新电影史从文化理论的角度重返早期电影,探讨电影与都市现代性、视觉文化、科技生活的重叠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了电影对现代生活各方面的影响[3][4]。鉴于电影学科在欧美大学跨学科的发展,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学科在体制建构上可以同时隶属于文学、艺术,甚至传播学院。 其次,只要考察一下电影理论框架下的内容,我们就更能了解电影研究的跨学科性质。除了所谓的经典理论(即结构主义以前对电影的论述,包括巴赞[Bazin]、克拉考尔[Kracauer]等),电影理论所包含的符号学、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5],以及近来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跨国主义、全球化批评,这些分支几乎都不为电影研究学科独创或独占[6]。当然,电影作者论(auteur)和缝合理论可以算作电影研究的首创,但这些并不是电影理论的主流。从这点来看,波德维尔(Bordwell)在《后理论》中对当代电影研究中的两大“超理论”(主体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批评,正说明电影研究本身没有独一无二的理论系统,而他所推崇的介于理论与文本之间的经验(empirical)研究更说明了电影的跨学科性质,这方面与传统的文学和历史研究相去不远[7]。其实,新电影史正是在传统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电影产业、制度等进行了更为理论的分析,使电影研究与相关学科(城市历史、科技历史、视觉现代性)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严格说来,波德维尔所擅长的以电影文本为基础的批评(作品分析、叙事研究[8]、风格系统[9]),在很大程度上也吸收了结构主义以前及以后的文学研究传统。 最后,我们可以参照电影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显然,在以文学为主导的人文学科中,电影研究长期不受重视,其真正发展是在1980年代中期,当时一批美国学者在暑期到北京讲学,带来了最新的西方电影理论成果,使中国与世界在隔绝了30多年后重新接轨[1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电影理论的接受是有选择的,其中巴赞的现实主义理论独受青睐,而后结构主义的电影理论并没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今如此。1980年代的理论热促使中国学者重新面对电影本体论,有些学者因此提出“丢掉戏剧拐杖”、废除“谢晋电影模式”等相对激进的主张,试图重建一个电影美学体系。当然,其后界定的电影学其实还是电影美学,基本属于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并非独一无二的学科。从电影批评来说,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电影美学,而是重点各异的文化研究,尤其是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在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的中国的民俗电影(或所谓的张艺谋模式)。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研究在中国逐渐形成,大量援用传播学、媒体研究的方法,分析国产大片在跨国市场的运作,以及中国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贡献。总之,在中国学界,虽然10多年来电影研究的学科地位得到了巩固,电影博士点不断产生,但电影研究仍然保持其跨学科的性质。 从以上三方面考量,我觉得电影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而这个跨学科特性一直在推动电影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互动,使其发展迅速。也因此,我们在强调电影的艺术特征时,不必抛弃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反而应该重视电影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边缘(或称前沿)课题,如表演、音乐、明星、观众等[11],这样才能从新的角度挖掘电影跨学科的综合艺术的特性,整合电影与艺术、传播、媒体的政治经济体系,更快地发展电影研究。 电影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现在回到本期电影跨学科研究专辑的其他4篇论文。提到电影的跨学科研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电影与文学,而电影改编自然是个主要方向,这方面虽然还有广泛的发展空间,但已渐渐得到应有的重视[12]。文学之外,电影的跨学科视野还应该考察戏剧(表演艺术)、绘画(视觉艺术)、录像(实验艺术)及当今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电脑、网络、手机等)。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4篇论文涉及的部分议题。 第一篇的作者陈建华教授先后获得上海复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文学博士,在美国师从中国现代文化史专家李欧梵先生。陈教授长期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致远讲座教授。陈教授尤其擅长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研究,由文学旁及电影,重点是都市研究中的上海视觉文化。《从影迷到银幕情缘》一文涉及了电影与绘画、电影与表演、电影与媒体等跨学科的课题,切入点是从好莱坞到老上海的跨文化明星现象。中国的明星塑造借用好莱坞话语策略,强调银幕内外的表演,凸现当年女明星的摩登女郎/新女性的诱人形象,其中的现代性内涵大致来源于西方文明(如汽车、骑马、网球、游泳、时装等)。然而推崇银幕上西化新女性形象的但杜宇却又得益于典型的中国仕女画传统,曾以其畅销的海上《百美图》著称。殷明珠的明星现象因此体现了但杜宇中西合璧的现代性追求,一方面打造类似好莱坞“白珠娘”Pearl White的“宝莲”健美形象,另一方面又指涉第一位中国女明星诞生过程中难言的苦衷。陈教授根据新挖掘的资料,描绘了殷明珠在婚姻上屈从家庭所遭受的难言的身心痛苦。殷明珠不是五四作家所憧憬的娜拉,她一开始像大多数传统闺秀那样并不敢走出包办婚姻,但却出乎意料成为当年以西化而扬名上海的交际花,其别称FF乃英文Foreign Fashion(外国时尚)的缩写。作为明星,殷明珠面对报刊媒体的表现相当成熟。她自己用文言写成《海誓》(1922)电影的故事梗概,与其说在炫耀她的文才,毋宁说要表明女性身体“可看性”(the to-be-looked-at-ness)背后,同时拥有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内涵。女明星既不躲避男性对女性的窥视欲,也不放弃追求女性的主体性。从传统“美人画”的静态展示,到现代电影女明星银幕内外遥相呼应的动态表演,都市视觉文化呈现了新的概念转化。 无疑,明星是现代都市文化的一个新现象,体现了新的身体文化、视觉文化、物质文化和商品文化。如果说但杜宇跨越了绘画与电影的界限而创造自己在上海电影界的艺术品牌,那么周瘦鹃、朱瘦菊等文人的实践则跨越更多的媒体,从文学、戏剧到电影、报刊。主流学术界往往将所谓“鸳鸯蝴蝶派”列入传统的旧派,但这批文人却在五四、左翼作家之前率先闯入当年代表新媒体的现代都市文化,从印刷、舞台到电影(甚至体育,如徐卓呆),还有后起的广播、音乐。应该承认,在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性背后亦有新概念。陈教授的文章点明了当时上海影评中所用“表情”一词,既评点好莱坞明星的表演成就,也沿用于描述京剧或新剧的演艺标准。从殷明珠新女性的表情到梅兰芳“京剧精神”的“表情”体现,电影话语跨越,但又多层面地关联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媒体和都市传媒文化。这里的跨媒体创意转换不仅是海派戏剧从电影偷招,而且源自电影本身受益于戏剧艺术。对学术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一艺术媒介固定的本质,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中诸多艺术媒体如何重新整合、探索新颖的表现方式。 第二篇论文的作者包卫红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学兼电影与媒体研究博士,师从以早期电影理论中“白话现代主义”著名的汉森(Hansen)和以科技现代性著称的甘宁(Gunning)。包教授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最近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十年磨一剑,第一本英文专著论述情感媒介,在华语电影史研究领域引进最新的媒体理论和电影与戏剧的跨媒体互动方面的论述[13]。专辑中这篇文章其实包含了包教授目前第二本英文专著的思路,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广度;既参考西方理论,又立足中国的艺术实践和批评,应该说是非常及时地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新的跨学科研究议题。包教授在本土的历史框架内,梳理了1920到1930年代电影从默片到声片发展时期中国影人对电影与戏剧表面分离、暗中连接所表现的矛盾纠结,他们对媒体特质论和媒体进化论的认可跨越了当时“软性”与“硬性”的意识形态分野,而刘呐鸥强调电影本质的理论既表现了当年国际现代主义的影响,又显示了驱之不散的戏剧阴影。 包教授认为,电影中戏剧的回归在社会主义时期集中体现在“舞台艺术纪录片”这个特殊类型的创立,表面上二元对立的电影具象、写实与戏曲的象征、写意需要理论上重新辩证统一,但这一话语重建也需要在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中加以考察。包教授指出,戏剧的“假定性”这一概念来自苏俄的戏剧理论,表达“虚拟的”、“程式化”的含义,而同样来源于苏俄的蒙太奇电影理论又在“舞台艺术纪录片”的讨论中进入戏曲民族性、现代性的实践,在冷战背景中产生地方主体性(即传统艺术)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交错[14]。另一个理论话语的意识形态交错,出现在新时期初电影界“丢掉戏剧拐杖”的激进口号和与其平行的对早期中国电影“影戏”理论的探讨,其中对电影本体论或本土性的强调虽不尽相同,却都受到艺术媒体进化论的现代化话语的钳制。这一系列问题值得读者深思,因为斩钉截铁的媒体二元对立并不辩证,教科书式的艺术本质描述也不尽合理。包教授提醒我们,媒体特质是一种话语而非原真本质,更不可能亘古不变,所以我们对媒体必须持开放的态度,考察其不同时期的艺术发展和话语演绎。 第三篇论文的作者王亦蛮教授是美国杜克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长期专攻电影研究,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论文改自她英文专著的一章[15],其实也考察电影和戏剧的关系(电影中的戏剧),但更多关注某一戏剧化的故事多次重拍背后的政治历史和地缘文化的复杂因素,涉及电影类型和电影改编方面的诸多问题。华语电影研究中恐怖类型片是个相对的空白,王教授通过细读3部拍摄于好莱坞、上海和香港的魅影电影,一方面梳理恐怖类型片中一个重要文本的跨文化传播,另一方面探索重拍影片中地缘文化的传承与协商。细读的方法既使叙事、造型、声音、表演等层面中不那么明显的意义得以显现,又使原先似乎确定的意义不再那么单一。王教授以“底层重拍”的概念入手,重新建构《夜半歌声》重拍片中原版(老师)和新版(弟子)之间的关系,分析后者如何继承、抵抗或重写历史和记忆。毁容后带面具的魅影暗示了被压抑的创伤性历史无法清晰、平静地显现,但又不可能完全消失,因此舞台背后的声音建立了新的形声统一体。通过台前显现的失语与台后隐藏的高歌所凸现的冲突,王教授进一步挖掘出转换修辞而产生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以及中心与周边、主导与底层之间的张力和互换可能。香港重拍《夜半歌声》(1995)中的新创意既表达1997年回归前香港电影的文化自信,但也暗示香港文化资本对大陆电影市场的重新想象。王教授的分析沿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突出后续创作对原有文本的延续意义,其结论不仅建立了重拍片的主体性,也有益于我们重新审视电影改编——重要的不再是改编或重拍必须忠于原著,而是前者如何调动新的创意,同时既重现后者被压抑或被遗忘的意义,又重申前者作为再创者在历史、艺术等方面后来居上的主动性。 第四篇论文的作者孙松荣将我们从中国香港带到中国台湾。孙教授是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电影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动画艺术与影像美学研究所,对华语电影与当代艺术及当代法国电影理论与美学等有深度研究。《论台湾实验电影简史:一种扩延式的影像艺术观点》表达了与美国理论界不尽相同的观点,因此尤其可贵。相对恐怖类型片,影像艺术(video art)更是华语电影与艺术史研究中的空白,因为影像艺术既不是纯粹的电影,也不属正统的艺术史。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影像艺术更应该成为跨学科电影研究的一个方向。孙教授探询影像艺术到底是一种类别、特殊的流派,抑或实验精神。在早期电影时期,电影的类型边界尚未完全确定,实验影像游离于剧情片(虚构)和纪录片(纪实)之间。1920年代的“都市交响曲”或所谓的“诗意纪录片”就包含明显的影像实验精神,尤其是维尔托夫(Vertov)《带摄影机的人》(1929)所凸现的肉眼见不到或看不清的交错、繁杂的都市影像。1930年代进入经典电影时期后,剧情片类型逐渐完善,纪录片也以解说型为主流,所以影像艺术慢慢融入先锋艺术,全然退出主流电影研究的视野。然而,孙教授指出,影像实验或实验影像在电影范式的体制化与论述的正典化之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出现的实验电影、独立电影、地下电影,乃至艺术电影等范式提供了创意的先例。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更多的新科技(如电影特效、电脑艺术、多媒体环境与全像摄影等)和影像传播平台(电视、录像、电脑、网络、手机等),实验影像与影像实验在当今日常生活中似乎无所不在,而学者问津甚少。孙教授回顾台湾实验电影,梳理了近几十年来艺术、文化、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由此建构一种超越电影与视觉艺术、导演与艺术家、电影院与美术馆之明确分野的台湾影像艺术系谱。 相比之下,有关大陆实验电影和影像艺术的学术研究尚不多(至少英文出版如此),尽管这方面有些作品其实早已扬名海外。欧宁、曹斐的实验纪录片《三元里》(2003),既回应1920年代的都市交响曲范式,又凸现了全球化时期都市影像的噪音而非谐音,暗示人类文明从20世纪初对机械的信赖转入世纪末对技术发展的焦虑。杨福东的黑白影片《竹林七贤》(2003-2007),以诗意化、仪式化的模式再现早期电影的氛围和水墨风景诗画的意境,既包含先锋戏剧和行为表演的程序化因素,又融合艺术摄影的静态捕捉技巧。与杨福东的水墨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艺术家朱利安(Isaac Julien)的艺术电影《万重浪》(2010)的亮丽色彩,从老上海的弄堂街景(模拟吴永刚的默片《神女》)到新上海的摩天高楼(浦东未来世界般的景观),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南方乡村田野、竹林、水流,迥异的风景、文化、历史影像相映成趣。该片启用电影明星张曼玉(饰妈祖)、赵涛(饰神女)、诗人王屏、书法家巩法根、艺术家杨福东,中国意象无处不在[16]。在展映厅里,别出心裁的多屏幕影像装置同时,但稍加错位地放映《万重浪》,让观众产生新颖的动态观赏经验。 本文在结语部分提及这些艺术案例,说明艺术家的跨媒体创作经常走在学者的思索之前。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从早期以夸张动作诱人的默片,到以完整叙事为主的经典时期,再到新好莱坞以来以景观取胜的大片和以边缘文化著称的独立制作,电影吸取了戏剧、小说、绘画、表演和概念艺术的精华,不断完善技术表现手段(从早期的灯光、声音到当今的数码特技)。面对不断演进的电影(或后胶片电影),我们必须打破原有划地为牢的学科界限,综合相关学科不断扩展的知识,进入更广阔的电影跨学科研究领域,开创新议题,探索新方向,实验新方法,阐述新意义。 ①这一部分改自张英进:《电影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6日,第12版。标签: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殷明珠论文; 戏剧论文; 电影理论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