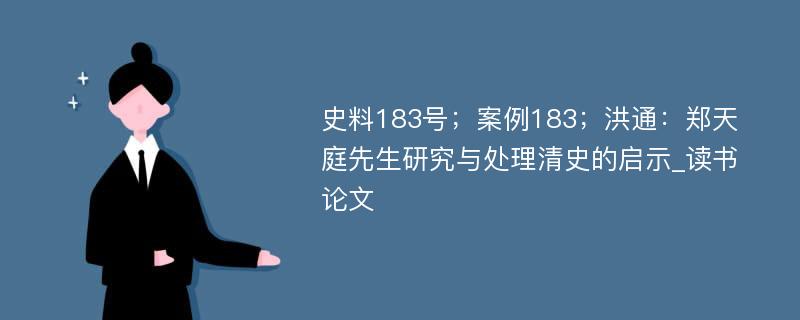
史料#183;个案#183;宏通——郑天挺先生研治清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史料论文,个案论文,启示论文,郑天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0)04—0014—05
出身书香门第的郑天挺先生,一生历经清季、民国、新中国三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郑先生不惟孜孜于求学问业、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传衍学术,而且激励于时事之维艰、民族之危难、国家之更新,系心世运,献身教育事业,展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淑世情怀!
在其充满波折、忧患的人生历程中,郑天挺先生对国家、教育、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就郑先生的著述而言,如《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等,已足以体现其治学严谨、学识精深、视野宏通的为学风范。而先生之钟情于清史研究,亟亟于清史学科的发展和提升,则为清史教学、科研的推进和深化、人才的培养等,奠定了重要而影响深远的根基,从而继孟森、萧一山诸先生之后,为学界树立了一个典型航标。中外学人之誉之为“一代师表”、“当代的泰斗”、“当代‘完人’”、“当代的硕儒”等,洵为称情。而郑先生孜孜研治清史的学术历程,既彰显了其学术注目点所在,又体现出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为后学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有益启示。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能体现郑先生的为学理念、方法和精神,值得学界同仁镜鉴。
一、对史料文献的高度重视
当郑天挺先生尚读中学时,即开始阅读父亲遗留的文史藏书,从而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为其此后治学理念的形成打下了重要根基。而1921年读研究生时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更进一步奠定了郑先生重视史料的自觉性。不久,《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的成书,即郑先生认真研读、利用汉文资料的结晶。1928年,与朱谦之关于中国史料问题的讨论,彰显出郑先生对史料的一种认识。郑先生回忆道:“他认为:中国史料无一可信。我则认为:在未发现新史料之前,只能勉强用之。他又认为,旧史以本纪为纲,视皇帝过重。我说,这是古人无法编排年代之故。他还认为,甲骨文字可为史料。我则认为,其材料虽然丰富,但时代尚难断定。当时两人观点均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及今思之,还是满有趣的,但也表现出某种幼稚。”[1](P382—383)而《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文的写作,既是郑先生运用校勘方法的体现,也体现出其对史料文献的注重。至40年代,郑先生开始开设“清代史料”课程。
1950年,郑先生负责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工作,当时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一、已清缮的明题行稿,分类整理印行,未抄齐的补抄。二、整理题本的摘由,凡不明确、不详细的加以补充,并尽可能的指出每件内容的特点。三、过去整理题本,全按内容分类,有许多混淆不清,现在改按机关的职掌从新分类。四、系统地整理、研究本所所藏黄册——报销册及其他档案”,当时“辑录了许多史料,有十种之多,但后来公开印行的仅有《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等数种。”[1](P400)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中,郑先生更表示:“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研究所(当时称为国学门)同人在城南龙树寺抱冰堂开第一次恳亲会席上,我们曾经宣布:‘国学门搜集及整理所得之各种材料——当然不限于档案,完全系公开的,供献于全校,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学者,可以随意的作各种的研究,绝对无畛域之限制,这是应该请大家特别注意的。’(稿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一览》——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五章第十一页。)现在我们不但还维持着这个传统,而且更加强向这方面去作。”[2](P297—298)此可见郑先生等对史料整理及其利用的取向和胸襟。
郑先生执教南开大学后,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摸索着开设了“史料学”这一全新的课程。在《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一文中,郑先生就开设这门课的难度和意义做了如下阐述:“‘史料学’这门课程,我们过去很少开设,是比较生疏的,没有什么经验。关于苏联的史料学著作,苏联大学史料学教学大纲和讲义,也没有见过,只看到《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的史料学和谢列兹聂夫专家一篇论文(《教学与研究》,1955年,5期)。究竟这一课程应该如何讲授,如何与中国史料相结合,现在就个人初步摸索所及,写出来请同志们指正……我们根据史料来研究历史,但史料不就是历史。史料能够给我们提供研究个别具体历史问题所需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根据它再现或恢复这个历史事件的特征;但不是将史料堆积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多数史料不经过深刻、仔细和全面地分析研究,并与其它史料联系比证,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因此,研究史料不仅在搜集,而更重要的是批判分析;史料学不是史料的记录,而是史料的研究方法和利用方法。”[2](P277、280—281)此一对史料的定位,既是对传统认识的承继,更是一种升华。之后,郑先生还于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主编了全国文科教材《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八册《封建社会》(七)和南开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主办的明清史进修班的教材《明清史资料》。其主要取向,前者为:“尽可能选录完整的资料……注意了资料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尽量多选原始资料,不用转手资料……资料原文不作任何改动,只对某些少数民族称呼的用字按照解放后通用汉字作了改变……引用书籍尽可能选用较好版本……收集的以汉文原始资料为主,也有很小部分的译文”[3](《前言》);后者为:“对于原始资料的选录,力求完整、系统、扼要……资料原文均不作变动,只将旧史书中关于少数民族的侮辱性字样,一律改用解放后通用的汉字。”[4](《说明》)凡此,均可见郑先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
在《漫谈治史》一文中,郑先生还对史料的取舍做了整体概况。他指出:“我们在应用史料时,凡是同样的材料,我们则选用时间较早的;时间早,一定是第一手的材料;要用第一手的材料,不用转手材料。如果是同时的材料,则选用最典型的;典型的,是指比较完整、全面、鲜明、突出的;要用典型材料,不用泛常的材料。至于孤零的材料,则应有旁证,即间接证明;无证不信,孤证难立。此外,对于记载矛盾的材料,则应有交代。交代材料对不对和自己取舍的理由。要多闻阙疑,择善而从。”并强调:“史料必须经过甄别才好用,这就不免流于考证。小考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连篇累牍的烦琐考证,时间精力费得很多,往往得不偿失,并不可取。”[5](P468)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郑先生为了引导后学对原始史料的重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种读书方法,其关键点则在于“要精读一本书”。据郑先生称:“我到处强调要认真读书,要做到‘博、精、深’三字,即‘博览勤闻’,‘多闻阙疑’。同时我还强调要精读一本书。我觉得:‘精读要一字不遗,即一个字,一个名词,一个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读是细读,从头到尾地读,反复地读,要详细作札记;精读一书不是只读一书,是同一时间只精读一本,精了一书再精一书;精读可以先读一书的某一部分;精读的书可以一人一种’。‘精读与必读还有不同,精读的书不一定人人必读,如有人可以专读《山海经》,但《山海经》不一定人人必读;必读的书可以精读而不一定人人精读,如《通鉴》。’”[1](P402)此一指引,既是郑先生几十年治学的甘苦所得,也确实对学人为学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正由于郑先生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所以解放前被目之为“史料派”,甚至在50年代后期被视为“唯史料论治学方法的典型”,然就实而论,郑先生之高度重视史料,既是对传统治史路径的继承、受20世纪初期新史料发现时代潮流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同时又能有所更新、兼取其长,形成一种新的特色。前述郑先生对史料的定位,即是其证。而蔡尚思先生所记郑先生的如下一段话,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郑先生说:“有论无史是空话,不能令人信服;有史无论,是烦琐考据那老一套,在现在也还不能令人信服。清代朴学家是有益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也要占有全面史料,但光占有全面史料不行,还要有理论。即在史料中也还是要有观点的,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必然要用封建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了,这一点我在解放前是不充分理解的。”[6](P280)所以,常建华先生总结郑先生的史料学特色说:“郑先生的史料学,上承乾嘉朴学,也多少受到近代史学观念的影响,理论体系主要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而史例和经验则是自己的文史研究实践。”[7](P248)洵为笃实之论。
二、注重个案研究
郑先生研治清史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清史探微》、《探微集》、《及时学人谈丛》诸书中。《清史探微》有两种本子,一是1946年初由重庆出版者,收文12篇;一是郑先生去世后由其子郑克晟先生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本子,收文40篇。《探微集》为郑先生亲定,以《清史探微》为基础,计收文43篇,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其中有关清史的文章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及时学人谈丛》则是郑克晟、冯尔康、陈生玺三先生编辑整理,由中华书局于2002年出版,清史文章亦占了相当大的部分,皆为《清史探微》等论文集所未收者。
在为《清史探微》所撰序中,郑先生述成书情形日:“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6](《原序》)又其为《探微集》所作《后记》称:“一九四五年我在昆明,为了归偿借款,印行了一本《清史探微》,叙目写了这样几句话……今天安定潜研的读书环境,远远不是当年所能想象比拟,但是我请求指教的心情仍和往年一样。因此,我把这本小书,仍称《探微集》,既表明书的内容微不足道,也表示我学无所成的惭愧。”[2](P466)其实,这是郑先生的谦仰和虚怀,《清史探微》不仅其时足记,其文亦足存,《探微集》之内容也并非微不足道,恰恰体现了郑先生不断的探索精神;而这些著作则反映出郑先生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一直潜心治学、孜孜进取的为学个性,乃其几十年治学心血的结晶和不断升华。
郑先生对清史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方面:“(1)清代制度史研究的开启。即对奏章、宦官、包衣、兵制、科举考试、职官、幕府、礼俗等制度开展研讨。(2)清朝开国史和清初史研究,讨论的问题有清朝皇族姓氏源流、皇族血系、满洲统一、开国重要人物多尔衮、清入关前社会性质、清初三大疑案等。(3)强调对清代通史的研治。由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将鸦片战争定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水岭,造成清史研究的割裂,郑天挺先生强烈主张对清代历史进行整体研究。(4)清代历史定位,流行的说法是‘封建末世’,郑天挺先生提出‘晚期说’,与末世说形成对峙。”而罗继祖先生《读〈探微集〉》亦指出:“毅老这本《探微集》共分六个部份……和同时学者的著述如陈垣先生的《陈垣学术论文集》,陈寅恪先生的《春明馆丛稿》相比,篇幅都少,但几于篇篇精粹……有人说毅老在解放前是以‘史料派’闻名的,这话差不多。在《探微》这本书里,主要是清史上礼俗、典制、名称的考证,但都非常细谨,一笔不苟下,对于我们阅读《东华录》、《清史稿》等书,帮助很大。”[9](P675、677)李侃先生则揭示道:“清亡以后,治史者多攻元、明以前古史,致力于清史者为数寥寥。郑老虽然深通古史,但却把注意力移向清代,实为有识之见。郑老研究清史,重点在清王朝入关前后时期,但是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缺乏,官方文献又多篡改,因此对于清代前期,特别是清入关以前诸多史事,往往众说纷纭。郑老的研究,就是先从考辨史事、制度入手,在此基础上,再进而论述满族统治者建国的历史渊源以及满族与汉、蒙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重要历史课题。”[9](P668)即此可见郑先生研治清史的视野和注目点之所在。
就郑先生有关清史著述来看,其对清史问题的探究,主要方式方法是注重个案的研究,而其特色乃在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人手,或大题小作、小题大作。郑先生之所以有此取向,是因为在他看来:“写论文和写专著不一样,写专著着眼点要大,要做到处处照顾,事事联系;写论文则要求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史学界过去写大东西占得力量太多了,而小问题没搞清,往往以讹传讹。我们应该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出发,一个个解决小问题,向前推进。做到对自己有收获,对别人有帮助,对历史有发展,所以叫‘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也就是郑先生“探微”的独特之处。王处辉先生就此“恍然大悟”道:“先生提倡‘探微’,决非随意选些什么小题去作,而是要研究那些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小问题’。先生之倡‘小’,似小而非小,先生之探微,似微而不微。”[1](P287)冯尔康先生亦深有感触地说:“先生的‘探微’,是一种方法,是从具体问题着手,一个个地进行研究,以期对历史的某一个方面作出说明。说起来是‘微’,其实并不微末。‘探微’可以说是先生研究方法的形象表述。”[1](P304)
与个案研究紧密相联,郑先生对选题亦非常重视。在《漫谈治史》一文中,郑先生强调道:“每讨论一个问题,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然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三、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应当广泛联系,从各个方面都来比较一下,然后决定是否研究这个问题和怎样研究。研究历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得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应当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追下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规律。”[5](P462—463)观之郑先生的著论,确实体现了这一治学理念。
有必要提及,也是众所熟知的,郑先生之能在清史研究领域取得坚实而富有创新性的成就,与其长期坚持抄录、积累学术卡片密不可分。这既是郑先生治学的深厚根基,也形成其讲课的风格。尽管郑先生花费很大心血积累数十年的卡片,曾一度在十年浩劫中大多散失,但他并未因此而灰心,而是依然日夜勤奋,从头做起。值得庆幸的是,郑先生留存下来的卡片,如由王晓欣、马晓林先生整理的《郑天挺元史讲义》,已经中华书局于2009年9月出版问世,而《隋唐史讲义》、《明清史讲义》亦将陆续推出。这上百万字的文献资料,为我们体认郑先生治学历程、方法和思想认识的不断升华,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凭依。而郑先生的这一治学方法和风格,则深深地影响了众多学者。如常建华先生曾回忆说:“郑先生重视充分占有史料,认为这是研究的基本要求,50年代他曾对青年人说,积累资料没有两万张卡片不要写文章,要求青年人坐下来读书,在充分掌握资料后再写作,也就是说才算得上是研究。”[7](P247)此可见郑先生治学之扎实、谨严。
三、宏通的学术视野
郑先生不惟致力于清史繁难问题的个案探析,而且亦具有宏通的学术视野。这主要表现在:
1.注重从大的方面和较长时段把握清代问题。如在《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一文中,郑先生通过对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薙发、衣冠等礼俗变迁的考辨,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以上所举的清初几种礼俗,有的强汉人法效,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上均有所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由于政令的强制而是文化的自然调融。”[2](P87)又如探讨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问题,郑先生不同意将1840年以前的明清时期定性为“封建社会的末期”说,而提出“封建社会的晚期”或“封建社会的后期”说。他认为:“晚期和末期,不是两个词的差异问题,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衰败,即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的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这就是说一定要照时代的特征,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才能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在习惯上也可以称之为后期,盖‘后期’一词,包含封建制从衰败走向灭亡的全过程。中国封建制的后期只有它的衰落的一段,而这一段与我们所说的晚期相一致,在这里它们成了同义词,反映同一的历史实际。”[5](P12)再如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郑先生先于1962年发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提出这样一种认识:“在我的不成熟的看法: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制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在封建制的初期,它的封建化是以后逐步深化的,逐步上升的……它在初期,除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以外,还有农奴制集体生产,还有奴隶制生产的残余;同时也还有氏族制的残余……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符合多数民族的一般发展规律的。”此后,鉴于这一问题“关系到满族历史的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内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的经过和对清初历史的解释”,郑先生继续收集材料,再加探研,并于1979年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从“清入关前满族的生产和社会情况资料零拾”、“努尔哈赤建国前的思想意识属于封建领主范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满汉两族人民在东北杂居已久”、“努尔哈赤最初建立的政权就是封建制国家的政权”四个方面,申述了“满族在清入关前的社会发展已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接近事实”的观点。凡此之类,皆体现出郑先生学术视野的宏通。也许有的学者不一定认同郑先生的观点,却不能不予以重视。
2.对1644年清兵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历史,做了宏观而高屋建瓴的勾勒,著成《清史简述》一书。郑先生述该书成书经过曰:“一九六二年,我还到中央党校讲授过清史。因为该校学员与大学要求不同,我只能简明扼要地介绍清朝入关后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后来我根据记录稿加以整理,以《清史简述》为名,于一九八○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P402)之所以选取1644年至1840年这段时期,郑先生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年。一八四○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一六四四年以前的不讲,一八四○年以后的不讲,只剩下一六四四年到一八四○年这一百九十七年的时间。这就是中国通史上关于清朝历史这一阶段的年代。”[10](P2—3)
《清史简述》由“概说”、“清代前期的政治和经济(一六四四~一七二三年)”、“清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一七二三~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文化”四部分组成,既从宏观上探讨了关于清史的年代问题、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的特点、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一阶段的分期问题等重大问题,又对1644年至1840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做了详细阐述。周远廉、朱诚如二先生曾撰文评价是书的特色称:“一、高度概括,重点突出……二、不囿旧说,颇多创见……三、比较研究……四、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此外,全书脉络贯通,繁而不乱,史论结合,有叙有论,深入浅出;体例新颖,语言通畅。这些也都是本书的明显特色。”[1](P339—343)可以说,郑先生此书,尽管篇幅不大,但“简”而有要、“述”而有见,似“简”而体大、似“述”而实创。与同类著作相较,郑先生是书,至今仍不失为研治清史者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郑先生还曾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高校清史教材。但遗憾的是,郑老刚选好写作班子、拟定编写大纲,便遽归道山。然郑先生在天之灵可欣慰的是,此一编写计划在既定框架的指导下,后来取得了圆满的成果。于此,清史学家王锺翰先生曾撰文评价道:“新出版的《清史》一书,编写大纲悉出之郑老手定,而各章各节的具体撰写均由门弟子与哲嗣分别承担,一以郑老的《清史简述》与《探微集》两书及其文章和讲课笔记为准则。虽不能说全书已经浑成一体、天衣无缝了,然书出众手,众腋成裘,仍不失师承之旨,洵可谓为一部传授有自、难能可贵的书了。”[11](P1929)
3.主张整体清史研究,讲授和研治范围涉及清入关前至清季的全过程。冯尔康先生在谈郑先生为学内涵时,曾将“强调对清代通史的研治”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并特别指出:“由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将鸦片战争定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水岭,造成清史研究的割裂,郑天挺先生强烈主张对清代历史进行整体研究。”郑先生所著《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简述》,所撰《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及《续探》、《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等文,以及开设的“中国近三百年史”、“明清史”、“清史研究”、“清史专题”课程等,即此一特色的体现。这反映出郑先生宏通性的治学大视野、大理念。
在《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一文中,郑先生曾说:“争论的问题大,涉及的面广,关心的人多,讨论起来一定热烈;但问题大就不容易照顾周到,不容易处处深入,往往存在薄弱环节。问题小可以深入,但面窄就不容易通贯全局,不容易引起注意,而且往往陷入繁琐考证。似乎应采用点面结合比较好些。围绕一个中心问题,一面进行全面探讨,一面就其中某一小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全面探讨为重点研究指出方向,指出关键;重点研究为全面探讨提供资料,提供论证。全面探讨不排斥某些方面的深入,重点研究也不离开中心问题的方向。”[2](P304)此一“点面结合”的史识,正彰显出郑先生以上三种为学取向乃一有机整体、彼此关联,而且是相得益彰的。
总之,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以个案探讨为突破,以宏通视野为涵摄,既是郑天挺先生长期潜研清史探索出的一种新治学模式,也是他留给学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有益启示,值得学界同仁认真学习、体会和发扬。
如果给郑先生的治学做一概括地话,用郑先生自己凝练、提升的“深、广、新、严、通”五个字,再恰当不过了。郑先生于《漫谈治史》中揭示其要义道:“深:包括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追下去。广: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新:要求不断提出新资料、新问题、新见解,核实新资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严:要严格,不虚构,不附会,要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代,要说清楚,不回避问题。通:找出规律,前后一贯。”[5](P463)诚哉斯言!
虽然郑天挺先生很谦虚地以“探微”名集,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则是非常“显著”的。“微”、“显”之间,正体现出郑先生高洁的人品、大师的风范!
[收稿日期]2010—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