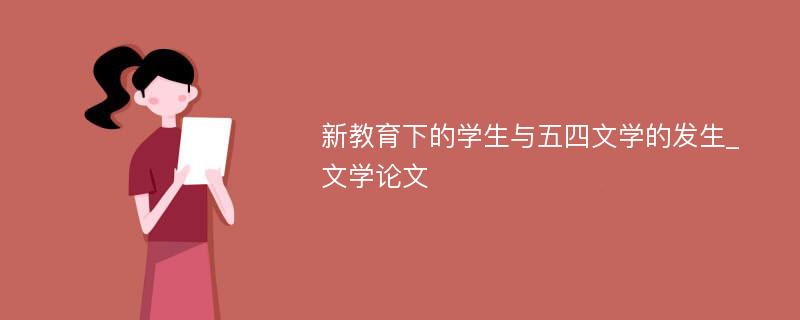
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和五四文学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生论文,学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文学的主要接受主体并不是在传统教育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士子或市民,而是在新式教育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由学生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的通俗文学如“旧式白话小说”,依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他们的‘太平皇帝’的宝座上”①,而新文学本身则“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②。有鉴于此,他们认为,“‘新文学’尽管发展,旧式白话的小说,……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这几乎是表现‘新文学’发展的前途已经接近绝境了”③。因为五四文学作为“新文学”,从其诞生伊始就和“旧式白话小说”有着很大的分野;“旧式白话小说”的接受主体则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士子或粗识文墨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缺少了新式教育熏染这一环节。如鲁迅的母亲喜欢中国传统小说,“几乎中国的小说她都看过了。鲁迅经常要给母亲找小说,过不了几天,母亲又说:‘老大!我这几天看完了,还有别的小说吗?’”④ 这说明,即便是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接受主体是那些“新读者”;或者说,在他们创作文本之前,就已经明确地把接受主体设定为那些在新式教育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由此看来,新文学“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并不是新文学本身的过失,而是源于作为接受主体的“群众”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缘故,这就使诞生于自由、科学和民主等现代意识基点上的五四新文学和群众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反差太大,以至于二者缺少了对话的平台。这实际上彰显了新文学启蒙文化语境的艰难性、复杂性和多元性。
新式教育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学生群体。这批学生用其接纳的西学知识建构起了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使他们对五四文学产生了亲和力。张之洞不无忧虑地说过:“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⑤ 这表明,晚清既然已经打开了通向西学的主渠道,就无法按照自己设想好的方式来框定学生的思想。尤其是“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⑥。事实上,接受新式教育而觉醒了的学生为救亡图存的“同一处境所激发”,并具有了接纳西学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相同的倾向性”。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既在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有所“表述”,更在接受主体那里也有所“表述”,使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结构”具有同构性。
陈独秀、胡适作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实在是生逢其时,这是他们比前辈学人的幸运之处。在他们之前不止一人,曾用饱满的激情和炽热的鲜血,在“铁屋子”一般的社会中呐喊着。然而,这结果却是“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对此,鲁迅切实地感受到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⑦。这说明鲁迅早就意识到了接受主体的重要性和接受主体的匮乏。对此,他不无感触地说过:“凡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⑧。其实,鲁迅这样的感喟并非没有道理,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已经为五四文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中,热烈地期待着在中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以此打破中国文化上的“萧条”,这种思想完全可以和五四文学革命思想有机地衔接起来。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文学并不是特别迫切与热心。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革命和改良等政治问题凸现为主要问题,而文学则被这政治所遮蔽。正如鲁迅所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的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⑨ 由此可以想见,在同是具有留学背景的身边都如此难以找寻到“同志”,要到社会上找寻“同志”自然就更难了。既然鲁迅的思想在留学生中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在国内的一般学生中就更难指望有什么回应了。所以,鲁迅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在“无可措手”中被延宕了下来。
这就是说,时代还没有为先觉者铸造出与其思想合拍的接受主体。没有接受主体的回应,就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文学运动。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发生,重要的并不在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学诉求是什么,而是这种文学诉求是否拥有更为广泛的接受主体。这一切昭示我们,要对五四文学的发生作出很好的言说,不仅需要我们到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去寻找,而且还要到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那里去寻找。
在五四文学运动期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则很快就获得了接受主体的认同。如寄身异域的陈丹崖给陈独秀的书中就肯定道:“日者得读左右主撰《青年》,雒诵再三,至理名言,诚青年之药石,其裨益中国前途者,云岂有量!”⑩ 这种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向往”之情,对陈独秀来说,自然提供了外在的动力。而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形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当年的先驱者不但形影相吊,而且还深为人们痛恨。如孙中山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1)。当然,对孙中山的革命持同情和理解的只能是那些接纳了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而普通的民众依然和这革命有着深深的隔膜。这成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反思历史的绝好“标本”。如鲁迅的小说《药》提供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对清末革命的“记忆”,以及由这“记忆”而来的对当下“文学运动”的价值指向。清末的革命党人致力于推翻清政府,救民众出水火。然而,这并没有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未觉醒的夏三爷们还会为保全自我而出卖了参加革命的侄儿。更令人深感痛惜的是,夏三爷的这种愚昧行为,不仅未受到应有的鞭笞,反而在他者的视阈中成了精明的举动;而夏瑜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则不仅不为康大叔所体认,也使花白胡子这样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还使“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发了疯了”(12)。其实,他们从小接触的是传统教育,这教育所宣示的是造反者要株连九族、满门抄斩,所以,夏瑜的革命行为在他们眼里无疑就是造反行为,只能用“发了疯了”来解释。正是这样的传统教育强化了他们对封建威权的依顺和对反抗封建威权的排斥。然而,夏瑜的文化背景和那些“二十多岁的人”是相似的,但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同,才使他们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说明了二者产生转换的中介是新式教育。然而,鲁迅的这一隐喻意义,却一直未能被我们很好地阐释过。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文学尽管旨在对下等社会那些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进行启蒙,但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启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因为五四文学的启蒙话语无法抵达到被启蒙者那里。这就是说,在辛亥革命中,如果阿Q还有参加革命的朦胧意愿的话,那么,到了五四文学运动时期,他们就连参加这一革命的朦胧意愿也没有了。在五四文学中,阿Q这样的被启蒙者完全处于“缺席”的位置。退一步讲,阿Q即便“在场”,也只能成为五四文学运动的“反对派”,他捍卫的是自己所信奉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等纲常名教的神圣性,这种坚决的态度恐怕一点也不逊色于赵太爷。这原因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13) 此为其一;其二是阿Q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其惯性的作用下,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而具有统摄其行为与思想的异己力量了。阿Q在革命前,“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14)。那么,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这革命也是与他为难,因为这将使他所喜好的“手执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剧也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然而,鲁迅这样深刻的启蒙话语,却没有抵达阿Q头脑中的有效途径,这由此构成的悖论更深刻: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竟然连有效的对话都无法展开,这又何谈什么“思想革命”呢?他们只能是“各唱各的戏,各念各的经”。这样的话,五四文学的发生就必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参与的文学运动,它和辛亥革命一样,离那些被启蒙者甚远,只能局限于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和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熏染过的知识分子,它无法成为被启蒙者共同参与的新文化运动。
鲁迅曾对天才和民众的关系这样形象地比喻道:“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15) 天才的产生离不开民众,只有民众成长起来了,天才才会找到自己诞生所需要的土壤。鲁迅在20世纪之初就致力于文学启蒙,但最后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他的《域外小说集》仅卖出了十几本,反响寥落;而事过境迁,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所写的《狂人日记》却一炮打响,成为无心插柳的经典之作。对此,鲁迅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16) 这就是说,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之所以会在那一时代“呼风唤雨”,其根基在于“民众”,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众”只不过是由学生或从学生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组成,在这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是受过新式教育后的知识分子,有些是正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
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主要是由接纳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但如果由此认为所有接纳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是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那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并不都是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也存在着尖锐的对峙。对此,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杨振声曾有过描述:“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大家除了反唇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17) 由此说来,这些学生以各自所认同的理性和情感,在“一方的憎恶”和“另一方的鄙视”中,隐含着价值尺度的大碰撞,特别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居然这分属于不同文化阵营的两派,差点把“文争”演变成“武斗”。由此可见,对峙的双方对自我所捍卫的文化价值体系都怀有神圣的使命感。
其实,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如陈独秀针对何谓新青年就指出过,“慎无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显然,陈独秀把《新青年》的接受主体定位于“新青年”上,这些“新青年”不但在生理上具有健壮之体魄,而且在“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具有“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18) 的现代文化人格。当然,陈独秀对新旧青年的辨析,还深藏着他对接受主体的一种期待。《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因为缺少必要的接受主体的回应,还一度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使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未能如期而至,而一些无关紧要的回应倒是不期而至。如求教于陈独秀一些问题竟是“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之类的问题(19)。这和陈独秀所期求的读者反响大相径庭,这也正是《青年杂志》缺少预设的接受主体的证据。然而,当《新青年》迁入北京大学后,其情景就截然不同了。由于《新青年》的主编和撰稿人大部分是教师,他们了解作为“新青年”的学生的思想和情感,他们也有意识地诉求“新青年”创造“新文学”,这促成了新式教育下的学生这一接受主体对《新青年》积极回应。
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的熏染下,经过“同化”和“顺应”,最终完成了自我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那么,五四文学接受主体又是怎样建构了这一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呢?
其一,五四文学所宣示的新思想作为一种触媒,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情感,促成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新建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一直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恰恰是在婚姻不能自主这一点上,很多学生具有深刻的体验。因为在晚清社会中,早婚风俗非常盛行,北京大学的很多学生就已结婚育子。杨振声就曾经这样描述过:“来自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20) 这就是说,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对社会和人生切实体验以及新思想和新文化启蒙的有机结合,复活了他们的个性意识,发现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导下,作为婚姻主角的自我则处于缺席的位置,这就使个性解放所宣示的婚姻自主和“新青年”们的婚姻不自主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如北京大学法科哲学部学生、文学研究会最早的成员之一的郭梦良,在家庭的包办下结婚。后来他和庐隐相恋数年后,“毅然决然”地和发妻离婚,庐隐也解除了家庭包办的婚约,两个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这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原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21) 自然,“张口发出这叫声”的话语便成为五四文学的中心话语。杨振声的文学创作实践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
杨振声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其个性意识在时代的呼唤下觉醒了,他在以五四文学的新观念烛照过去的生活中发现了“从来如此”的非合理性的一面,由此“起了苦闷”,“顺手”创作了记载这苦闷和叫声的小说,从而使之在五四文学史中获得了独特的价值。这从杨振声所作的《贞女》小说中可略见一斑。贞女即女性捧着牌位和订婚后的死亡男性结婚。对这种扼杀人性的婚俗,人们却“一点也不感稀奇”(22)。杨振声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贞女现象中发现了其非人道的一面,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叙事:“一个晚秋的傍午,天上飞着几片轻淡的薄云,白色的目光射在一条风扫净的长街上。……风送过一阵很凄楚的喇叭声音”(23)。在这种凄楚的氛围中,贞女从幕后走向幕前。贞女“婚后”在“暮春”时节因思春而“脸上一阵发烧”;最后,贞女以上吊自杀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的皈依,这就把纲常名教吃人的本质凸现了出来。对此,鲁迅称杨振声是一位“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24)。然而,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杨振声小说所宣示出来的意义和价值却被我们既有的观念遮蔽了:杨振声从学生成长为小说家,又从小说家转化为教育家,显示了杨振声的兴趣并不在文学上,也没有要继续做文学家的意愿。后来,杨振声在美国留学时便以教育心理学为自己的研读方向。但是,像杨振声这样一个并没有把文学奉为圭臬的学生,能够迅即地在五四文学运动的感召下,一举成为现代小说家;而那些孜孜矻矻砣地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晚清作家,却没有顺势成为现代作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卓有成就的晚清作家要想成为一名现代作家,为什么会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还要艰难?其实,在这一复杂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经由新式教育重构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使他们由此基点出发,找寻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突破口。这说明了五四文学在本质上是因新式教育而发生的;同时,正因为他们从新式教育出发因应了五四文学的发生,所以,很多人在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认同之后,又最终彻底地远离了文学,他们在文学史上成为五四文学的“客串者”。这样的事例,也体现在“作家而兼学者”的陈衡哲那里。陈衡哲说过:“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它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25) 这样的表白,正可以看作五四文学发生带有独特的规律性的象征。即正是对没有遵循“文学家的规矩绳墨”,才可能创造出一代新文学。
其二,新式教育下的接受主体,对西学的接受固然构成了他们接受五四文学的重要基点,但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基点直接奠基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所确立的文学基点上。这既是他们区别于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方面,也是他们未来的文学创作始终未能逾越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所设定的疆域的重要原因。
从认知发展的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认知都必须回到人类认知的原点上去重新经历认知的起始过程。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省缺了从认同西学到认同文学的转换过程,而是径直地把自我的文学创作基点奠定于五四文学所确定的现代意识基点上。如从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作家,像冰心、俞平伯、台静农、巴金等作家,都没有像鲁迅、胡适、郭沫若那样的文学之外的诸如医学、农学、地质学等现代科学造诣。这就是说,作为五四文学接受主体的学生,在接受老师熏染的过程中,直接地确立起现代文化观念,实现了和他们所追随的老师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同质同构。但这造成的弊端是,因为缺少了对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的认知过程,所以,他们对五四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往往就出现了民主挤压科学的倾向,而其所认同的民主又负载了过多的政治话语。这也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倾向于凸现政治性的主要根据。
尽管如此,这些在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在接纳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教师的现代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同时,也直接引发了他们和带有守旧色彩的教师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隶属于不同思想派别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如杨振声和俞平伯因为参加了《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显然,这些先生是那些和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持不同“政见”的老师。然而,作为已经接受了西学中个性解放和自由观念的学生,则在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那里获得了支持和鼓励,这就使学生强化了“我们不怕作叛徒”的决心。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自己所认同的价值尺度,百般奚落自己的老师:“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正是对这种理论的抵触,他们竟然在课堂上如此地“咬耳朵”:“他的皇帝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把他的辫子同他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26) 这恰好说明学生对皇帝、辫子为代码的那套文化符号,已经弃之如敝屣了。与辜鸿铭被拒斥形成比照的是,胡适进入北京大学后却迅即获得了青年学生的迎纳。如在1919年初夏,胡适充当杜威演讲的翻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胡适在人们心目中的镜像是这样的:“上海的年青知识分子们一提到他的大名都激动不已,尽管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他,甚至连他的像片也未看见过”(27)。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文学运动期间,作为“新青年”的学生所倾慕的已经不再是古文家,而是那些操持着白话文的“新派”文学家了。
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中,跨过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直接地接触了带有西学学科特点的文学史观的熏染。如在北京大学,鲁迅就开设了中国小说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把小说史作为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这对于学生确立新的文学发展史观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此,鲁彦这样回忆道:“大家在听他的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28) 鲁彦的话语,显示了他在接纳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在耳濡目染中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皈依。这促成了他们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对鲁彦走上现代文学创作的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
陈平原在对京师大学堂的文学史教学分析中指出:“此前讲授的‘词章’,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位、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29) 这就使大学文学史教学对文学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实,那些真正受过文学教育的人固然是五四文学运动的接受主体,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触到文学教育、只受过西方现代知识的文人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以自己既有的西学根底,完成了对五四文学所昭示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的认同。如丁西林,本来从事物理学研究,他在留学英国期间以攻读物理为主,业余也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认为学科学的人未尝不可以接触文艺,而搞文艺的人更不能狭隘,兴趣应该尽可能地广泛(30)。这实际上说明了,五四文学和西学中的科学和民主思想具有紧密的关联,而文学史教育的作用则只能是由此基点而衍生出来的作用。
在五四文学发生的过程中,一方面,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在新式教育的作用下,初步完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对接,这使五四文学从个人主张转化为群体主张,激发并释放了群体的文化动能;另一方面,接受主体也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回应,而是在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积极回应中,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创作实践的深入,确保了五四文学获得源源不断的创造动因。
事实上,五四文学正是经过接受主体的接受和传播,使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话语被进一步放大,在接受主体的“同频共振”中找寻到了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同频共振”,使之具有“群体”的特点,这使他们得以创造五四文学的历史重要原因。戈德曼说过:“在某一特定的时代或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就有数不清的群体正在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行动。而在这不可胜数的群体之中,某些群体却表现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们的行动和行为意欲从整体上组建社会。”(31) 五四文学的发生正是“数不清的群体正在进行成千上万次行动”的结果。
实际上,这里还隐含着五四文学是被延宕了的现代文学这一命题。20世纪初期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晚清最后的历史时期,本已具备了产生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条件,但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却没有被孕育出来,这就使那些具有五四文学思想的引领者,虽然已经握有点燃现代文学的火把,但却没有引燃社会的干柴,不得不使那些燃烧得通红的火把最终窒息于历史的荒原中,最后只余留下点点的火星。如鲁迅早在日本求学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并把这样的一种热情付之于文学实践,但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性思潮的聚焦点却不在这里。当时的新式教育不仅没有提供必要的接受主体,而且也没有提供必要的创建主体,从《新生》的最终夭折就可以看出,希冀创建新文学的同仁团体是极为松散的。这和五四文学诞生时既有同人性的团体,也有主导的核心团队(教授团体轮流编辑),还有被大家认可的“总司令”,更有大批的支持者和随从者,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学生作为五四文学庞大的接受主体对五四文学的发生所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确保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启蒙功能的实现。五四文学之所以在文学史中获得了独特价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五四文学文本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很多接受主体建构自我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营养源和肇始点。实际上,正是在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文学文本的影响下,一大批深受五四文学影响的“新青年”获得了新生。由此说来,五四文学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运动之后走向文坛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深受其影响和滋润的。
五四文学固然离不开学生这一接受主体的支持,但还应该看到,五四文学还反过来促成了学生思想的进化:“五四以来,大西洋的新潮流,一天一天的由太平洋流到中国来,在东洋文化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32),这一切说明,五四文学从根本上重构了学生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他们从前鄙陋的思想被新思想所取代,他们最终所认同的主义尽管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说,在反对旧礼教和专制政体、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科学等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事实上,学生是五四文学革命口号的坚定拥趸者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回应者,这确保了五四文学的社会启蒙功能的实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新青年》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杂志。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33) 正是在五四文学运动的鼓舞下,学生们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意识:“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34)。“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35) 这尽管是从政治的视点审视五四文学后得出的结论,但也未尝不可以看作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获得了确立的表征。自然,这里所显示出来的国民性,已经和过去的那种奴隶性格有了泾渭分明的区别。
因为五四文学的策源地就在北京大学,这就使那些正在就读于北大的学生们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他们亲炙这些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格、接纳他们所传承的西学等现代知识,因此他们迅即成为五四文学的呼应者和响应者,这就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得以展开。像俞平伯、杨振声、朱自清等人,都是在这种情景下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们追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获得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奖掖。如俞平伯就说过:“我还写过两篇白话小说:《花匠》和反对妇女守节的《狗和褒章》。《花匠》曾被鲁迅先生编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里。”(36) 北京大学的学生固然有亲炙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现代人格熏染的便利,但北京大学之外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则随着《新青年》的传播,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的人生选择。如朱湘在南京工业学校求学时,是《新青年》把其思想和情感赢到了五四新文学这一方面来:“记得我之皈依新文学,是十三年前之事。那时候,正是文学革命初起的时代;在各学校内,很剧烈的分成了两派,赞成的以及反对的。……是刘半农的那封《答王敬轩书》,把我完全赢到新文学这方面来了”(37)。
新式教育固然是五四文学传播的平台,但这一平台本身所具有的辐射力,则使五四文学得以进一步传播。如巴金就是借助于其兄长接受新式教育的便利而获得了接触《新青年》的机会。巴金的兄长“尧枚买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而且还多方设法补买了自1915年创刊以来的《新青年》的前五卷。这还不够,只要是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去买来”(38)。这使巴金“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39)。
五四文学在新式教育的平台上获得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它唤醒了那些虽然受过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并没有完成自我人生重塑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如老舍作为一个小学教师,之所以成长为现代作家,“这就不能不感谢‘五四’运动了!”(40) 这正说明,五四文学作为一场由创建主体所发动的文学运动,正是借助于新式教育这一平台,在迅即壮大了其接受主体的同时,也发展了其创作队伍,从而使五四文学真正地演变为磅礴于整个时代的文学大潮。
其二,促进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创作文本的积极性,使其文学潜能获得了最充分的释放,成为他们创作出更为杰出的文学文本的外在助力。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固然深受创建主体的影响,但他们反过来又规范和制约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创作方向,驱使其文学诉求和文本创作向着其接受主体所认同的基点位移。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文学而言,读者群变了,作者的对象和态度也随之而变了。……于今作者的写作对象是一般看报章杂志的民众,作者与读者是平等人,彼此对面说话。”(41) 这正清楚地说明了读者群对作家的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这种情形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来说,亦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五四文学的发生置于其具体语境中,就会发现,五四文学作为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既有一个自我孕育的过程,也有一个其赖以存活的文化土壤的培育过程。离开了前者,我们就无法说明五四文学为什么会以这样的面貌而呈现着;离开了后者,我们就无法说明五四文学为什么会获得延续和发展。当然,我们强调了接受主体在五四文学发生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低估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既是五四文学新思想的体载者,也是五四文学文本的创造者,还是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如陈独秀慧眼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也迅即得到了同仁们的回应,诚如刘半农所说:“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于前,复有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于后”(42)。并且,他们在回应中,还有诘问,如陈独秀在该文后指出“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一曰改造新韵,一曰以今语作曲”,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效应。
五四文学运动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本范型,而且也基本上确立了中国20世纪主要文学大家的构成。他们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已经“粉墨登场”,并和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一道确立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整体格局。这标明了中国古典文学经过了五四文学的“洗牌”后,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牌局”,这是一个已经失却了威权的时代,也是一个任人跑马圈地的时代。他们这代人,正是在历史所提供的这种机遇下,迅即成长为五四文学所拓展的文学领地的领军人物,并几乎成为五四文学之后中国20世纪文坛的威权式人物。巴金则依然用他那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宣示着五四文学和深受五四文学熏染而成长起来的那代作家的“在场”。“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以其群体的方式,在确立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基本风貌的同时,也以巨人般的影子,一直笼罩或涵盖着中国20世纪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话语具有了某种霸权话语的特征,成为人们惟马首是瞻的文学风标,这在确保了五四文学精神延续的同时,也对文学的多元化发展空间形成了一定的挤压。
注释:
①②③《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33、863、632页。
④周建人:《回忆鲁迅的学习和教育活动》,载顾明远《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⑤《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47页。
⑥(31)[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5页。
⑦⑧⑨(12)(13)(14)(15)(2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17,417、446、214—215、513、166—167、322页。
⑩(18)《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43—44页。
(11)孙中山:《建国方略·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16)(24)《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239页。
(17)(20)(22)(23)(26)杨振声:《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246、245—246、7、247—248页。
(19)辉暹:《致陈独秀》,《青年杂志》1卷6号。
(25)陈衡哲:《小雨点·自序》,《小雨点》,新月书店1928年版。
(27)程天放:《我所亲炙的胡适之先生》,见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8)鲁彦:《活在人类的心里》,《中流》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5日。
(29)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30)《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1分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32)《群众运动的母——五四运动》,《杭州学生联合会报》第31期五四号增刊,1920年5月20日。
(3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34)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
(35)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1919年8月4日。
(36)俞平伯:《回忆新潮》,《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37)《朱湘自传》,载贺炳铨:《新文学家传记》,上海旭光社1934年版。
(38)陈丹晨:《巴金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39)《巴金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
(40)《老舍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6—87页。
(41)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杂志》(上海)2卷8期,1948年。
(42)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标签:文学论文; 陈独秀论文; 鲁迅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