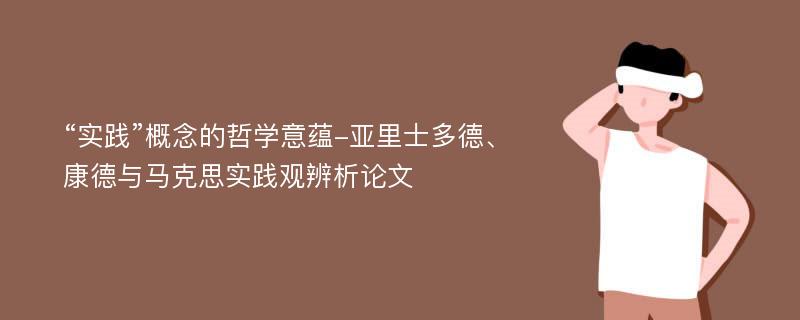
“实践”概念的哲学意蕴——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马克思实践观辨析
双修海 肖凤良
(东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 实践概念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置于最为高贵的思辨活动和最为低贱的创制活动之间,使之兼具二者的某些特性但又在实质上有所不同。康德一方面取消亚里士多德生产创制活动的独立地位,使之成为理论思辨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把实践仅仅限定于道德实践,并将其推向独立于且高于理论思辨的彼岸。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实践观,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作为实践概念的基础性内涵,进而把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实践观深刻揭示了实践概念的本质,开创了一种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基本内容、囊括一切人类活动的广义的实践哲学。
关键词: 伦理—政治实践;道德实践;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实践哲学
一、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
在西哲史上,亚里士多德最先把实践同道德联系起来,不过其实践概念的内涵是丰富的,并不仅仅限于道德实践。深入理解亚氏实践概念的内涵,需要首先从他对人类知识的分类谈起。亚氏把人类活动分成三类,即思辨(theoria)、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相应地,人类拥有三类科学(或知识),即思辨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关于三种科学的地位问题,亚氏认为,思辨科学地位最高,创制科学地位最低,实践科学则居于二者之间。之所以如此排序,是因为亚氏有自己的一套衡量标准,即“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智慧”[1]4。
在思辨活动中,追求真理本身即是目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目的,并且追求真理的活动是个人独自进行的,与他人和外界自然无关。与此相反,创制活动的目的不在自身之中,而在它产生的对象或结果上,并且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按照上面的衡量标准,思辨科学高于创制科学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在思辨科学内部,研究那“既不运动又不可分离的东西”的第一哲学或神学,比其他思辨科学如物理学和数学更为可贵。“思辨科学比其他学科更受重视,神学比其他思辨科学更受重视。”[1]121概而言之,在亚氏看来,越是远离经验缺乏实用的知识,越具有更高的智慧和地位,因而更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
刘诚龙笔下,既有广为人知的热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也有鲜为人知的冷门人物汤斌、陈廷敬;既有清官或者说好官,也有贪官乃至庸官,官场百态,或浓或淡、或明或暗呈现出来,挑拣的是文史,映照的则是现实,是竖立在反腐路上、大官小官面前的多棱镜。
实践科学兼具思辨科学和创制科学的某些特征,但在本质上又与二者有所不同。先看实践科学与思辨科学的关系。一方面,就实践自身即为目的而言,实践科学同思辨科学是类似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思辨也被称为一种实践,而且是最高的实践。然而,就实践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而言,实践科学又不同于思辨科学,既然后者是人独对真理的活动即沉思活动。用亚氏的话说,“思辨知识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知识以行动为目的。尽管实践着的人也考虑事物是个什么样子,但他们不在永恒方面进行思辨,只虑及关系和此时。”[1]33实践“只虑及关系和此时”表明,实践科学在必然性程度上要比思辨科学低一些。
再来看实践科学与创制科学的关系。就实践自身即为目的而言,实践科学不同于创制科学,既然后者以生产活动的后果为目的。如果说实践科学是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活动,那么创制科学则是人处理与“物”关系的活动。可见,实践科学的对象是人事,它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束缚,是自由的活动;而创制科学的对象是物件,其受自然必然性的制约,成为不自由的活动。不过亚氏有时也强调,实践科学同创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实践,即二者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只不过一个为了“实现活动本身”的善,另一个则为了“活动以外的产品”的善。“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目的之中也有区别。它有时是实现活动本身,有时是活动以外的产品。当目的是活动以外的产品时,产品就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2]3-4引文中所说的以“产品”为目的的实践即为创制活动,其与“技艺”密切相关。
在亚氏看来,“实践”有两种,即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在《政治学》中,亚氏把“实践智慧”等同于“明智”(吴寿彭的中译本《政治学》将其译为“明哲端谨”),并将其作为唯一适用于统治者和政治家的德性。这样,实践智慧或明智便主要体现在国家事务上。亚氏谈道:“全体公民不必都是善人,其中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是否应为善人?我们当说到一个优良的执政就称他为善人,称他为明哲端谨(即明智,下同——引注)的人,又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明哲端谨。”[3]127此外,亚氏还进一步指出,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德行与被统治者截然不同,“‘明哲’(指明智——引注)是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被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则为‘信从’”。[3]128
亚氏认为,在实践理智中灵魂肯定和否定真的方式有五种,分别为“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着重分析了“明智”即“实践的智慧”。为了说明什么是“明智”,亚氏首先说明什么是“明智之人”。“明智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方面善和有益……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2]172人们会问,难道一个明智之人就是只关心自己所得而不顾家庭和城邦的人吗?对此,亚氏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明确指出:“人们都追求他们的利益,并且觉得这样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意见,那些关心自己的所得的人就是明智的人。但事实上,一个人的善离开了家庭和城邦就不存在。”[2]178
到了《尼各马可伦理学》,“明智”的含义有所扩展,不再仅仅限于政治活动,也包括道德或伦理活动。亚氏区分了两种理智德性,即“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前者思考始因可变的事物,后者思考始因不变的事物,二者属于有逻各斯的灵魂的两个部分。关于这两种理智德性,亚氏谈道:“理智本身(沉思的理智——引注)是不动的,动的只是指向某种目的的实践的理智。实践的理智其实也是生产性活动的始因。因为,无论谁要制作某物,总是预先有某种目的。制作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属于其他某个事物。”[2]168-169在此,亚氏强调了两种理智德性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使得实践的理智更多地与创制活动联系在一起,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始因”或“目的”。
混凝土振捣工艺主要要求振捣的频率、力度、均匀度、振捣范围,这四项基本要求都会关系到混凝土施工中是否会出现裂纹。在混凝土施工中,混凝土振捣面积很大,如果采用以往的人工振捣方案,只能安排多人同时振捣,会让振捣工作变得混乱、难以管理,导致混凝土振捣不均匀,在施工中出现裂纹。
亚氏对“明智”的正面说明是通过与“科学”“技艺”的对比展开的[2]173-174。明智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其一,“明智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而科学只考察不变的事物;其二,明智不包含证明,因为“对于那些其始点可变化的事物无法作出证明”,而科学则恰恰相反。明智与技艺的不同在于:首先,明智与技艺在始因上是不同的;其次,“技艺中有德性,明智中却没有德性”,明智无德性是指,明智与德性不可分离;第三,“在技艺上出于意愿的错误比违反意愿的错误好”,而在明智上出于意愿的错误则更坏。正因如此,明智被称为一种德性而非技艺。
既然一切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可以奠基于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之上,那么一切人类生活在本质上就都是实践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8不难看出,马克思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将人类生活割裂开来的传统,认为人的生活世界进而人的实践活动是统一的。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经济领域的活动可以称为实践,而且其他一切领域的活动也都可以称为实践。但是,在所有实践中,经济领域的物质生活生产的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
以上讨论了亚氏的两种实践概念,即城邦的政治实践和个人的伦理实践。在亚氏那里,这两种实践虽然有所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离。个人的伦理或道德活动考虑具体的事实,而城邦的政治活动则考虑普遍的事实。由此便形成两种知识,即“关于具体的知识”和“关于普遍的知识”。亚氏认为,我们尤其需要前一种知识,但同时,前一种知识也还需要后一种知识作为指导。“明智也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它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明智既然是与实践相关的,我们就需要这两种知识,尤其是需要后一种知识。不过这种知识,还是要有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2]177这里提到的“更高的能力”即一种政治学的智慧。可见,亚氏一方面认为个人的伦理实践独立于城邦的政治实践,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城邦的政治实践要高于个人的伦理实践,因为后者需要前者的“指导”。
既然没有单独的生产创制活动(即“技术地实践”活动),那么相应地,康德自然不会像亚氏那样,把人类活动分为彼此不同的三部分,而是分为两部分即理论哲学的部分和实践哲学的部分。关于这两个部分的地位问题,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专门予以讨论。他认为,人的每一种内心能力对应着一种兴趣,这些兴趣是被作为原则之能力的理性所规定的。理性有两种运用,即思辨的运用和实践的运用。“思辨运用的兴趣在于认识客体,直到那些最高的先天原则,而实践运用的兴趣则在于就最后的完整的目的而言规定意志。”[5]164问题在于,究竟哪一种“兴趣”具有优先地位?对此,康德予以重点分析。
二、康德基于善良意志的道德实践
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导言中开宗明义,将哲学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并指出前者是以自然概念为基础的自然哲学,而后者是以自由概念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哲学被划分为在原则上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即作为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和作为道德哲学的实践部分(因为理性根据自由概念所作的实践立法就是这样被称呼的),这是有道理的。”[4]5不过康德认为,人们对实践概念的使用存在失误,即不加区分地使用基于自然概念的实践和基于自由概念的实践。“由于人们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等同起来,这样就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些相同的名称下进行了一种划分,通过这种划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划分出来(因为这两部分可以拥有同一些原则)。”[4]5-6
为避免误解,康德着重对上述两种实践概念作出区分。在康德看来,赋予意志的原因性以规则的,既可以是一个自然概念,也可以是一个自由概念。如果是前者,涉及的就是一种“技术上”的实践;而如果是后者,涉及的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道德上的实践规则属于实践哲学,这正是康德道德哲学探讨的内容。技术上的实践规则属于理论哲学,尽管只是作为对后者的补充。技术上的实践“为的是产生按照因果的自然概念所可能有的结果”,因而“不能要求在一个被称为实践性的特殊哲学中有任何位置”;与之不同,道德上的实践则“完全建立在自由概念之上,同时完全排除意志由自然而来的规定根据”,因而其规范“构成哲学的一个被置于理论部分旁边的特殊部分”。[4]7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0]374-375引文中提到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正是所谓的“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
综上,亚氏把人类活动分成三类,即思辨、实践和创制。其中,实践活动包括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应该说,亚氏关于人类活动的三分以及他对实践概念之丰富内涵的阐释,包括将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开创性做法,对后世康德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产生深远影响。下面先转向康德的实践哲学。
康德谈道:“如果实践理性除了思辨理性单独从自己的见地出发所能呈献给它的东西之外,不再能假定任何东西并把它思考为被给予的,那么思辨理性就领有优先地位。但假设实践理性自身拥有本源的先天原则,与这些原则不可分割地结合着的是某些理论性的肯定,而这些肯定却仍然是思辨理性的任何可能的见地所见不到的(虽然它们也必定不是与思辨理性相矛盾的),那么问题是,何种兴趣将是至上的兴趣(而不是:何种兴趣必须退出,因为一种兴趣并不必然地与另一种兴趣相矛盾)。”[5]165在此,康德假设了两种情况,一是实践理性没有自己的先天原则,其先天原则是思辨理性单独给它的,此时思辨理性的兴趣具有优先地位;二是实践理性自身就拥有本源的先天原则,此时何种兴趣具有优先性便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康德否定了前一种情况并试图对后一种情况所引出的问题给出解答。
不过,在回答何种兴趣优先的问题之前,康德先考虑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对于实践理性交给它去采纳的东西一无所知的思辨理性是否必须接受这些命题,并且即使这些命题在思辨理性看来是过甚其辞的,它也不得不力图把它们作为一笔外来的转移给它的财产与自己的概念一致起来”[5]165?在康德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从他如何沟通“自然领地”与“自由领地”的尝试中可以看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道:“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了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那么毕竟,后者应当对前者有某种影响,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4]10
不难看出,由于自由概念“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必须对自然概念的领地产生影响,即必须“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所以自由的领地优先于自然的领地。相应地,实践理性的命题优先于思辨理性的命题。或者换句话说,思辨理性“不得不力图把它们作为一笔外来的转移给它的财产与自己的概念一致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实践理性的兴趣优先于思辨理性的兴趣。“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为一种知识时,后者领有优先地位……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纯粹实践理性从属于思辨理性,因而把这个秩序颠倒过来,因为一切兴趣最后都是实践的,而且甚至思辨理性的兴趣也只是有条件的,惟有在实践的运用中才是完整的。”[5]166-167
但是在垄作坡耕地的样点 7Be含量变化出现减少与增加并存的情况。不同坡位与坡度的耕作垄样品 7Be含量具有一定程度的顺坡变化。耕作垄的不同样点间的含量差异较为显著,与种植垄的微坡形态和坡度变化特征有关。主要是由于增加了垄作措施,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土壤吸收降雨水分的能力,并改变了坡面径流形成的方式和机率。
坚定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四个自信”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出发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13]“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13]树立和坚定人民自信,就是要坚定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这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客观需要,是新时代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当今,在世界发展迅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国家的硬实力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及国防实力。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我国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国家的重视。而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取决于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我国企业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以提高自身在世界竞争潮流中适应市场的实力。
可见,康德一方面取消生产创制的独立地位,使之成为理论思辨的补充;另一方面则把实践仅仅限定在伦理、道德实践,并将其置于理论思辨之上。后者体现了康德试图改造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努力。康德把道德实践抬高到无以复加的位置,但也因此使他的道德理论流于形式,给人高高在上、无法企及之感。
康德道德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源自人的理性的“善良意志”(good will)。善良意志并不因为外在的事物而善,而仅仅因为它本身的意愿而善,因而其善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善。“就它自身来看,它自为地就是无比高贵。任何为了满足一种爱好而产生的东西,甚至所有爱好的总和,都不能望其项背。”[6]9善良意志又可称为“绝对命令”。绝对命令的一种表述是所谓“普遍律原则”(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即“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也可以表述为,“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6]38-39康德的这种道德实践观被人们称为“道义论”(Deontology)。由于道义论的上述原则流于形式化的说教,因而对人们的实际生活缺乏具体的可应用性。
康德认为,一个人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或好处去行善,他依然是不道德,因为他的行为的动机并非出于行为本身的善。可是,我们在现实的具体行动中对利益或好处的考虑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点上,即使是康德的“绝对命令”也概莫能外。例如,要使前面提到的“普遍律原则”中的“普遍规律”有意义,即能够使之成为所有理性的人都遵从的规律,那么它一定是符合集体的利益或好处的。正如密尔(J. S. Mill)所说:“康德提出的原则要有意义,就必定含有这样的意思:我们的行为应当遵守的规则,是所有的理性人都会采纳的有益于他们集体利益的行为规则。”[7]53正因如此,当代伦理学的一大趋势是道义论与功利论的结合。
盖尔达耶古城的建筑和街道围绕着中央的清真寺大致呈放射状排布,但由于街巷尺度狭小,城市建筑密度极大。在沙漠地区,建筑的朝向对室内温度的影响很大,从当地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不同朝向的立面接受太阳辐射的强度变化很大,朝向为正南或正北的房子受到太阳辐射最少[1]。盖尔达耶的建筑并没有固定的朝向,但却能保证室内热环境的稳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材较好的热惰性和紧凑密集的排布秩序。除了狭窄的街巷尺度,相邻建筑之间往往还会通过共用围护结构的形式来减少建筑的体形系数,最大限度地避免与室外环境的直接接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更加紧密。
马克思、恩格斯对康德的道德哲学也给予了批评。马克思评论道:“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了彼岸世界。”[8]211-212恩格斯则从认识论角度反对康德在“现象”之外假定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做法。他谈道:“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9]317我们知道,康德假定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是要为道德留出地盘。既然恩格斯否定康德的自在之物,这等于否定了他的道德哲学,进而也是对其“实践”概念的疏远。
三、马克思作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为三类即思辨、实践和创制;康德则分为两类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其中理论哲学对应于亚氏的思辨和创制活动,而实践哲学则对应于亚氏的伦理实践。然而,无论是亚氏的三分还是康德的二分,这种分类都造成人的不同活动之间的割裂。康德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通过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试图弥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鸿沟。今天人们普遍承认,康德的努力并不成功。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找到一种使人类不同活动得以统一的基础,即“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
需要注意,康德并不认为技术的实践也是一种实践,但为了照顾人们习惯的用法,他姑且将这种实践称为“技术地实践”。在他看来,技术主要涉及在制作和生产上的实用性的技艺,而这种技艺是从属于“知识”的。正是在这种理解之下,康德主张将“技术地实践”归入理论哲学。“技术地实践”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前面提到,在亚氏那里,创制活动远不及思辨活动和实践活动那么高贵,在三者中它的地位是最低的,因为它与变动不居的事物打交道。现在康德把生产创制(技术地实践)作为理论哲学的补充,这使亚氏创制活动的本性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
究竟马克思是如何得到这个“基础”的?理解获得这个“基础”的过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个“基础”本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回忆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历。马克思本来的专业是法律,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哲学和历史。在实际工作和研究中,马克思遇到了不少让他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经济或物质利益上的纠纷。为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其分析的结果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1]8。像黑格尔那样,马克思把“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称为“市民社会”。而如何理解市民社会,这又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探个究竟。为此,马克思继续把精力投身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8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引文中提到的“原理”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无论对于经济学还是一切历史科学都称得上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1]526。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顶岗实习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并且顶岗实习大多针对就业安排。当被问及顶岗实习的重要性时,多数毕业生认为顶岗实习重要,并且对就业有影响,但同时也承认项岗实习内容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来说很不够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些实习岗位与就业岗位关联度不大;实习内容受实习单位生产需要限制,工作性质单一,不能完全符合培养应用能力的要求;实习效果缺乏恰当的考核方式等。今后应重视顶岗实习管理,完善规章制度,明确指导教师职责,实习项目的选择要尽量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教学规律,把顶岗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实践课来实施,从而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为说明经济领域的实践即“物质生活的生产”对其他领域实践的基础地位,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前提的解释给予佐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8]31总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是马克思实践概念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其他部分的比重或形态则由它来决定。
最后,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稍作对比,以此凸现马克思对前两者的继承和超越。
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为三类,即思辨、实践和创制。尽管他也讨论实践,并将实践分为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但实践问题只是亚氏关心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亚氏最关心的是思辨活动,因为它最为纯粹和高贵。相应地,最不纯粹、最为低贱的活动是创制活动。实践活动的纯粹性和高贵性则处于二者之间。对人类活动做出如此排序,在亚氏那个年代是不难理解的。在奴隶社会,为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创制活动主要是由奴隶和牲畜完成的。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并不把奴隶当人看,而是视它们为会说话的牲畜或工具。因此,奴隶所从事的劳动也被看作最为低贱的工作。可是,恰恰是这种低贱的工作为那些高贵的人类活动提供了“闲暇”和物质基础。正因为看到这一点,马克思不再像亚氏那样轻视生产创制活动,而是把它作为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当然,尽管马克思不同意亚氏对生产创制活动的定位,但他依然接受后者关于人类活动的三分法。只不过,亚里士多德只把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称为实践,而马克思则把人类一切活动都称为实践。其实,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已经蕴涵于亚氏的思想中。前面提到,亚氏认为实践活动兼具思辨活动和创制活动的某些特征。实践同于思辨之处在于,它们都以自身为目的。实践同于创制的地方在于,二者都以实现某种“善”为目标,虽然一个为了“实现活动本身”的善,另一个为了“活动以外的产品”的善。可见,这已经存在着试图把思辨、实践和创制统一起来的趋势了,但由于亚里士多德对创制活动抱有轻视态度,致使他所区分的三大人类活动始终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
康德倒是试图摆脱这种割裂状态,但也面临诸多理论困境,尤其对实践采取了一种过于褊狭的理解。康德取消了生产创制活动的独立地位,使后者从属于同道德实践相对的理论思辨。由此,摆在康德面前的任务就只是如何沟通理论思辨和道德实践这两大领域。康德的策略是论证理论思辨的兴趣最终从属于道德实践的兴趣,并通过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实现二者的统一。然而,这样的尝试一方面使康德的道德理论面临空洞和形式主义的指责,另一方面把实践仅仅限定为道德实践的做法也使其实践概念的内涵失之狭窄。马克思的实践观启示我们,实践不仅仅只是道德实践,而且还应包括科学实践。科学实践又可分为自然科学的实践和社会科学的实践。
道德实践、自然实践和社会实践这三种实践有何实质区别?自然实践和社会实践属于科学实践,其目的是利用、改造自然或社会。与之不同,道德实践的目的是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协调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这三种实践对应着三种实践自由或自由意志,而后者又是以对三种规律的认识为基础的,即相当于康德所说的“自律”。具体而言:关于道德的自由意志基于对人性的认识;关于自然的自由意志基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即自然科学);关于社会的自由意志基于对社会规律(历史规律或社会科学)的认识。
出租车非常少。好不容易盼来一辆,却被不远处的男人拦下。车子紧擦着艾莉驶过,又在前方刹住。男人的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去哪?
“可恶!你到底是谁?跟着我到底要干吗?!”唐小果对着空气喊道,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挣脱开。一获自由,他便飞奔着往家里跑。
前面提到,康德认为除了实践理性的兴趣之外,其他一切兴趣都是有条件的或不完整的,进而都是以实践理性的兴趣为归宿的。尽管马克思并不认同康德赋予实践理性的形式主义内涵,但他确实接受了后者将实践看得更为根本的观点,只不过他选择了把全部人类活动奠基在其所谓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之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6这句话是颇具仪式感的,马克思借此宣告了一切传统哲学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基本内容、囊括一切人类活动的广义的实践哲学。
参 考 文 献
[1]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康德. 判断力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 约翰·穆勒. 功利主义[M]. 徐大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n Analysis of Aristotle, Kant and Marx’ s View of Practice
SHUANG Xiuhai XIAO Fe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is a philosophical category with rich meaning. Aristotle put the status of practice between the noblest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lowest level of creative activities, making it hav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but it is also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m. On the one hand, Kant canceled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Aristotle’s production creation activities, making it a supplement to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limited practice to moral practice, and pushed it to the other world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Marx inherited and went beyond the practice view of Aristotle and Kant, and used the labor of producing material life materials a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nd then connected the whole social life of mankind into an organic whole. Marx’s view of practice fully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nd has created a broad practical philosophy, which takes human productive labor as the basic content and encompasses all human activities
Key words ethics-political practice; moral practice; practice of producing material life materials; practical philosophy
收稿日期: 2018-10-16
基金项目: 东莞理工学院课程体系建设项目“工程伦理课程体系建设质量工程 ”(GC100113-34)。
作者简介: 双修海(1986—),男,湖北荆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0312(2019)02-0015-06
标签:伦理—政治实践论文; 道德实践论文; 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论文; 实践哲学论文; 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