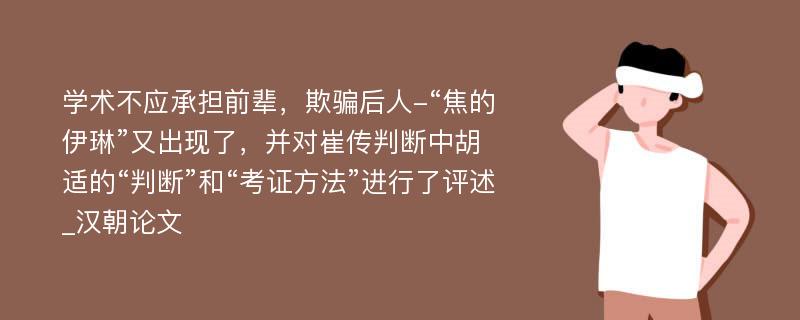
学术不可负前人,欺后人——《焦氏易林》产生时代再考,兼评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中的“考证学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判决书论文,前人论文,后人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2年9月,胡适先生卸任驻美大使后,于次年2月28日写成《〈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以下简称《判决书》)的长文(注:此文发表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48年第20卷上册,见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第14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31页。 ),据说,“一般被认为是他回到学术工作后的第一件成果,他自己也称作是:‘离开大使馆后第一篇考证文字。’”(注: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6页。)我生也晚,于胡适先生早期的学术及考证性的著作,拜读甚少,倒是从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批判胡适的文章里,得知他在考据学方面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到80年代末自己也从事学术工作后,在研究实践中,觉得他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后来在拙著《诗学·诗观·诗美》的自序中,曾这样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这一治学方法,我不敢附和某些批评家责其‘大谬不然’。为建构某个理论的设想,广求各种资料以确证这一设想的可能性或正确性,正如建筑师先有蓝图再选择各种建筑材料付诸施工,其‘谬’何在?如果其资料达不到‘求证’要求,‘假设’自然要撤消,以伪证坚持其‘假设’那就令人嗤之以鼻了。”(注:陈运良《诗学·诗观·诗美》,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近读胡明先生《胡适传论》,又得知先生于1952年12月所作的《治学方法》(三讲)的讲演中重申:“至于具体的治学方法,千言万语,归结起来仍是那一句讲了几十年的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谈到“方法的自觉”时,他认为:“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原则是“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要时时刻刻地检讨自己,完成生命的自觉,一靠严格的试验室态度,二靠做学问的良好习惯”。(注: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8~959页。)我以为这一理论的表述是非常正确的,不容置疑,对做学问者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既然他“离开大使馆以后第一篇考证文字”特加上副标题“考证学方法论举例”,那么,他对今见本《易林》(即《焦氏易林》)作者到底是焦延寿还是崔篆的考证乃至最后的“判决”,当属他的“考证学方法”的典范之作了!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凭后学者如我,对今本《易林》及其作者多年的考察研究,对作者之争多方面材料的辨识比较,只能说,胡适先生的“判决”作得太仓促了。他所使用的“证据”大多数是“不可靠”的,过于自信那些“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对一个自己也未完全弄明白而已争论两百余年的学术问题,竟轻率地运用“法庭”判决的形式一刀两断地解决,剥夺自隋唐以来就确认了的今见本《易林》焦延寿的著作权,归之自北宋以后失传的另本《易林》(即《崔氏周易林》)作者崔篆,全文处处以“法官”的口吻或问或判,这难道是他自谓的“严格的试验室态度”吗?
本着前贤“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我已写了《一桩历史迷案的探索——从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逆推》(以下简称《探索》)试图推翻先生的判决,继而又作《京房〈易〉与〈焦氏易林〉》(以下简称《东房〈易〉》一文证今本《易林》必是西汉中叶京房《易》派中人作,决非王莽或东汉时人崔篆所能作。余意未尽,本文将对今见本《易林》产生的时代作些补充论述,并对适之先生“求证”之可能误导后学,发表一点以实证为依的浅见,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一、以《刘向传》等补证《易林》产生的时代
判断某一历史时代流传下来的某部书之真伪,判断此书当出自什么样的人物之手,若无其他充足的历史资料可作旁证,那么也须大致弄清:那个时代能否产生这样的著作?处身于什么样的思想、生活境遇中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孟子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注:《孟子·万章下》)。要了解“古之人”,首先是要“读其书”,结合其书而“论其世”,这就是中国文人沿用了两千多年的“知人论世”说。或反过来说,“论其世”而“知其人”。因为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他所处身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思想意识、政治经济状况、生活习俗等等,都会影响乃至渗透他的思想、言行,如果有著述传于世,那么一定会有或浅或深的思想与生活经历的痕迹留在其中。
要探索今本《易林》的作者之谜,到底是姓焦还是姓崔,首先必须深入而仔细地研读它,4096首繇辞(实际还多一首,《节》之《无妄》目下存两首)不放过一首,把握它们整体的思想倾向,观其表现的社会面貌及反映的民情风气,乃至细察它的实际作者在字里行间或隐或显的心态呈示……这些,都在《易林》中确实地存在着。可是,胡适先生在《判决书》开头就说:“《易林》这部书,本来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他本身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如此轻而易举的一言判断,以我研读数年《易林》的体会,不能不怀疑适之先生在作此判决前已仔细认真地“读其书”。他注意到了“这些繇辞往往有很美的句子,读起来颇像民间的歌谣,朴素里流露着自然的俏丽”,被赞赏的繇辞仅仅是美的形式吗?实际上都有“决定形式的内容”,有内容即有“思想”,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对后人来说就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适之先生引用了明朝文艺批评家钟惺的话:“其语似谶似谣,似诨似隐,似寓似脱,异想幽情,深文急响。”较全面地概括其思想艺术的价值,实可否定胡适的断语!《易林》作者自述:“楚乌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大有》之《随》)明白地宣称不少繇辞是“哀诗”,蕴含着非同寻常的忧患意识。
为什么要“告孔忧”?《易林》辞中有大量揭露奸佞乱政的内容,而“浊政乱民”,造成社会下层百姓无穷无尽的苦难,以至似由作者代言,发出“仁道闭塞”、“生不逢时”的悲号。西汉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秩序,用班固《汉书·佞幸传·赞》的一句话是:“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汉元帝在位16年(前48—前33年),全是石显、五鹿充宗、弘恭等奸佞一手遮天,结果形成《易林》作者愤然而称的“苛政”、“乱政”、“虐政”、“蠹政”、“浊政”;成帝即位后,石显等奸臣“失倚”,被匡衡等“条奏旧恶”,逐出了朝廷,但豺狼去了虎豹来,汉成帝母亲王太后让她的家族大量进入最高统治集团。成帝在位27年(前33—前7年),王氏家“凡十侯,五大司马, 外戚莫盛焉”(注:《佞幸》、《外戚》、《刘向》三传,分别见《汉书》卷97。)。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 王太后之侄王莽取代其叔父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自此,逐渐对刘氏皇权取而代之,至孺子婴居摄三年,西汉王朝终于换成了王莽的“新朝”。
“衰于元、成,坏于哀、平”,西汉政局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剧性转换,汉代皇族的刘向完整地经历了这一过程,《汉书》中附于《楚元王传》的《刘向传》(注:《佞幸》、《外戚》、《刘向》三传,分别见《汉书》卷36。),用刘向充满痛苦的奏疏,凸现了由“元”而“成”衰落的明显迹象。
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字子政,本名更生,汉高祖刘邦少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他于汉宣帝时入朝,曾讲论《五经》于石渠阁,汉元帝即位后,受到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的重视,“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当时,中书宦官石显、弘恭已大肆“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遭石显等诬陷,周堪与刘向均下狱,萧望之被免官。当时,因“灾异—政治”因果关系说正在流行,汉元帝被“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吓怕了,诏赐萧望之关内侯,周堪、刘向也随之出狱,元帝欲封二人为谏议大夫,石显等阻拦,仅为中郎。这年冬天又地震,刘向以“外亲”匿名“上变事”,勇为萧望之辨冤而提出:“臣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这封匿名上书闯了大祸,弘恭、石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刘向再次下狱,萧望之被迫自杀。汉元帝对自己老师冤死感到负疚,“甚悼恨之”,赦刘向出狱,“免为庶人”,提拔与萧望之同道的周堪为光禄勋,周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石显嫉妒堪、猛“大见信任”,又“数谮毁焉”。此时已身为“庶人”的刘更生,担心他们又被奸邪陷害,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封事”再谏汉元帝。这篇近三千字声讨石显等奸佞的檄文,力陈奸佞之害,从“幽、厉之君”时代“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说起,继而痛陈:
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愬,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谓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藉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者也。
这封奏书作于元帝登位后第六年(前43年),五年后,京房面谏汉元帝之语,与之同出一辙,真可谓同声相应!(注:京房面谏语见《汉书》卷75《京房传》。拙文《汉代〈易〉学与〈焦氏易林〉》(《中州学刊》1998年第4期)已引,此略去。)这位忠直的“宗正”, 以“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暗示要对奸佞开杀戒,“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然而,汉元帝没有听进这些忠言,反在六年后把持同样意见的京房推上了断头台。
汉成帝即位后,“显等伏辜”,终于结束了一代奸佞的横行,“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官至光禄大夫。此时刘向已46岁,但他又遇上了“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在此以后26年中,刘向又有两篇著名奏章留载青史,一是谏汉成帝造昌陵,一是力陈外戚操纵国柄之害。后者作于成帝登位20年后(前14年左右),“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他以汉初吕后家族专权造成刘氏皇权之危为当朝之戒,继而敞言:
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在此奏章中,他对处理外戚提出了与“诛”奸佞的不同策略,那就是“厚安外戚,保其宗族”,即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取代其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从而使“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刘向临死前几年,还用“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等自然界灾异发生,警告汉成帝有丧失政权的危机。但是,他的竭忠至诚之言,上“终不能用”,班固如此结束《刘向传》:“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刘向不幸而言中!
刘向一生经历和他留下的前后奏章谏疏,可作元、成两个朝代“凌夷厥政”(唐·王俞《易林原序》语)的实证、确证。现在回过头来看今本《易林》,其中有大量反映“谗佞乱政”、“奸佞施毒”、“仁道闭塞”、“浊政乱民”的繇辞,主要是汉元帝16年间的政治、社会现实的反映,尚未涉及外戚专权的状况,可知其写于元帝在位之时,其时京房、匡衡等人的言论行为也可作为主证或补证(已见《探索》、《京房〈易〉》两文所论)。《易林》反映现实状况的上限可溯及汉武帝时期(如“兵征大宛”),中及昭帝、宣帝,使后世读者颇感触目惊心的则是对元帝时代的近距离反映,下限可延及汉成帝前十年内,这也可以提出多个证据:
(一)竟陵元年王昭君出塞(该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太子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始”),至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王昭君第二个丈夫复株絫来朝,《易林》有两首反映此事:“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萃》之《益》)“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萃》之《临》)。
(二)汉成帝初即位,匡衡与御史丈夫甄谭共奏石显等“旧恶”,并及党羽,石显、五鹿充宗等皆被逐出朝廷,《易林》有“沐猴冠带,盗在非位;众犬共吠,仓狂蹶足。”(《剥》之《随》)。
(三)匡衡等处理汉元帝时陈汤擅自入侵西域康居国,查明其杀害康居王子等事实,推翻元帝封陈汤关内侯的褒奖,“出汤夺爵为士伍”。《易林》中有“征不以理,伐乃无名;纵获臣子,伯功不成”、“续事康域,针折不成;婴儿短舌,说辞无名”两首繇辞(均在《节》之《无妄》目下)述其事。
(四)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易林》有“新作初陵,逾蹈难登,三驹推车,跌顿伤颐”(《明夷》之《咸》)言及此事。(注:以上四事,分别见《汉书》卷94《匈奴传》、卷81《匡衡传》、卷70《陈汤传》、卷10《成帝纪》。)
汉成帝朝中后期及至王莽篡汉时事,在《易林》中难以找到可作确证的相应繇辞,可推测其作者已不在人世,而这位作者,极可能就是京房(与刘向同年生)的老师焦延寿,汉元帝时的朝政黑暗,他亲身全程经历、耳闻目睹;从武帝至昭君出塞前的征战西域以及在战乱、浊政下百姓痛苦不堪的生存状况,同期贾捐之、贡禹等留存正史的奏章疏谏可作主证(已见于《中国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焦延寿》引述),《易林》中此类内容的大量繇辞,更是近距离反映。这几个方面内容的展示,是《易林》“思想史料”主要价值所在。论其世而知其人,晚生于这一时代的人,不可能如此真切地反映、表现出来。
二、再考崔篆不可能作“断归”之《易林》
胡适先生判定《易林》的作者是崔篆。是或不是,也需找到“论其世”、“知其人”的确证。
适之先生推测崔篆死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约活了70岁。依此上溯,崔篆当生于公元前30年左右,即汉成帝建始年间。《后汉书·崔骃传》(注:《崔骃传》之前为崔篆传略,《慰志赋》附其中,见《后汉书》卷82。)说崔篆祖父崔朝在汉昭帝时(前86—前74)曾为侍御史,其父崔舒历四郡太守(当在宣帝、元帝两朝)。其兄崔发在汉平帝即位(公元1 年)后与南阳陈崇等“皆以材能幸于莽”;(注:《汉书》卷99《王莽传》,以下引与莽有关之文均出此传,不再注。)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当在20多岁至30多岁之间。这一推测,我以为是可以成立的。
若说今所见之《易林》是崔篆所作,按《后汉书》记载,他在王莽垮台、其兄崔发被杀之后,“自以‘宗门受莽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那么他著《易林》在55岁之后,所历15年全在光武帝刘秀的新政时期,是刘氏汉朝中兴再造的起步阶段。当时,朝内没有奸佞乱政,光武帝对经历过农民大起义后的社会,实行了一些让步政策,使饱经苦难的庶民百姓休养生息(如释放民间奴婢,救济鳏寡孤独和无法生活的贫民,试图改变土地占有情况等等)。刘秀自称:“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176—179页。 )崔篆以“伪莽”遗臣的罪身,能够无中生有地虚拟出那些揭露、批判“凌夷厥政”的繇辞吗?他“临终作赋以自悼”的《慰志赋》中,有对光武帝的歌颂:“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建武;运搀枪以电扫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披兮,黎庶恺以鼓舞。”由此可知,他绝对不会大作有违光武之治的繇辞。那么,他是运用昭、宣、元、成间的历史资料,用以充实那些“用决吉凶”繇辞的内容?也不可能!这不是尽揭前汉的历史疮疤?根本不合于“惭愧汉朝”的心态。他在《慰志赋》中有涉及王莽篡汉之辞:“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漼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嫚藏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他要揭露和批判的也应该是自成帝以后的外戚专政及王莽新朝的浊政、乱政,可是今见本《易林》缺少这方面的明确内容。
胡适先生可能也已觉察《易林》大部分内容不合于光武中兴的现实状况,因此亦认为此书不可能作于建武年间,但他没有直说,而是说:“可以推想《易林》写成的时代是王莽声誉最高的时代。《易林》里好像没有王莽建国以后的史事,王莽始建国元年是西历纪元九年,所以我推想,《易林》成书在西历纪元最初八九年。到了王莽‘新室’时代(西历纪元九至廿三),这部书渐渐流行。”在“判决书主文”中又说:“其著作年代,据《后汉书·崔骃传》,是在东汉建武初期(西历二五至三五);但据本书内容推断,此书的著作大概经过颇长的时期,而成书的时代大概在平帝元始二年(西历二年)之后,王莽建国初期匈奴大人塞寇掠(西历十一年)之前。”两个推断不完全一致,后者向后延伸了两年。那么让我们再考证一下,崔篆是否可在这一段时期创作出《易林》4096首繇辞。
据《崔骃传》和《东观汉记》中“崔篆”小传记载,他的秉性修养有别于他“佞巧”的哥哥崔发,有一定的正义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他拒绝了与崔发同幸于王莽的甄丰举荐他为步兵校尉,“遂投劾归”;在《王莽传》中有崔发效忠王莽的多条记载,没有崔篆“助纣为虐”之迹。如果他关注朝政状况,对成帝之前奸佞乱政有那么尖锐的揭露描写,那为什么他对成帝以后外戚专政不置一词,好似视而不见呢?王莽篡汉前,王氏外戚操持国柄已30余年,可也未显示王家人会取而代之当皇帝的迹象,尚留可以揭露批判的一线余地。如果说,“王莽谦恭未篡时”,不易识破他的真面目,但王氏其他“侯”或“司马”已坏事做绝,刘向奏章中就曾大加揭露。在外戚内部,也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被班固列为有汉一代八大佞臣、名在石显之后的淳于长,是王太后姐姐的儿子,因助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有功,“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亦累钜万。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后欲取代王莽叔父王根的大司马票骑将军之位,被王莽告发,死于狱中。(注:《汉书》卷93《佞幸传·淳于长》像这样的事,崔篆若写入繇辞中,当不至于触怒王莽,有旁敲侧击外戚势力之功,何故而不为呢?
汉成帝初建初陵于渭城延陵亭,《易林》中有“新作初陵”辞反映民工建陵之苦。汉成帝后来嫌初陵规模太小,于鸿嘉元年(前20年)改在新丰戏乡造昌陵。这次规模极大,耗费民力财力甚钜,刘向在《谏造昌陵疏》中说:“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昌陵作造五年未成,永始元年(前16年)成帝自己也后悔了,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解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注:语出《成帝纪》。)新作初陵时,崔篆尚未出生或刚出生,胡适先生说:“成帝起初陵,又造昌陵,又回到延陵(初陵)的十多年的大工程,正当崔篆少年时代,在他著《易林》之前不过二十年光景;他记得这件大工程,用在《易林》里,更不足奇怪了。”但还是有些“奇怪”:他尚不晓事时“新作初陵”已写进《易林》,可他晓事之后(10—15岁)营造昌陵之事更大,为何又只字不提?看来胡适先生把“新作初陵”与后来造延陵混淆为同时同事了,如果指的是最终汉成帝所葬之“延陵”,那就不是“新作”而是“续作”,较之昌陵,也不值得特书一笔。这只能证明,“新作初陵”之辞决非崔篆所作,是此时尚在世的人——或为焦延寿所作,后造更不得人心的昌陵时他已不在人世,故不能言及。
推测《易林》作成于王莽篡汉之前(或后延两年),实在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而说“到了王莽‘新室’的时代这书渐渐流行”,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崔篆即使不与“佞巧”的崔发同道,也不至于与其兄更与王莽对抗。他岂不知“莽嫌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伤之”(注:《后汉书·崔骃传》中语。);在王莽命他为建新大尹时,说了“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能独洁己而危所生哉”的无可奈何之语,表明他没有与王莽公开对抗的胆量和决心。我在《探索》与《京房〈易〉》中已充分论列“灾异”说是贯穿《易林》多数繇辞的主线,而王莽信奉“符命”说,崔发是“符命”说维护者和权威解释者(被封为“说符侯”),王莽对“灾异”说深恶痛绝,《京房〈易〉》已举之例此不重复,从《王莽传》再举另外几例:
(一)(天凤二年二月)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万数。莽恶之,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
(二)(地皇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恶之,下书曰:“乃者日中风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适见于天,以正于理,塞大异焉。”
(三)(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王莽不信灾异之变,凡“上变事者”皆获罪,以致术数家们反将灾异当作吉兆骗谀王莽,而善“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左将军公孙禄揭露王莽身边佞臣语)的“说符侯”崔发,动辄发动“群臣皆贺”。如此逆境之中,若果有崔篆之《周易林》“渐渐流行”,岂不是自招本人及全家灭顶之灾?他的“说符侯”哥哥绝不会容许其弟保留此类书,更不会允许其流行。此事比不受命作建新大尹更危险百倍,崔篆岂敢上不顾老母,下不顾兄弟,擅自独行而“危所生”?
还有另一个案:始建国二年,王莽狂妄地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竟下令将匈奴国王传统名号“单于”改成带侮辱性的“降奴服于”,从而惹恼匈奴,导致“大入塞寇掠”。今见《易林》本内,“单于”之词未变,如“鸣条之灾,北奔大胡,左衽为长,国号匈奴。主君旄头,立尊单于。”(《屯》之《无妄》)若果为崔篆所作而又不作修改,不也是抗王莽之命!且此繇辞所述,有投奔敌国之象,若被王莽发现,百口不能辩。
胡适为了把《易林》著作权判给崔篆,一是不仔细分析、甚至毫不顾及《易林》主导的实质性内容,把它当作与当时现实社会毫无利害冲突的纯粹的“神庙签诗”;二是不顾史传关于崔篆的确切记载和崔篆在《慰志赋》中的自白。如前所述,尽管他表面屈服于王莽,但他良知未泯,对王莽篡汉心存异见,“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纵;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到晚年还有深切的恨悔之心。他出任建新大尹时,虽然“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也做了一件被《东观汉记》、《后汉书》作者特书一笔的好事:“门下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人于阱,此者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掾吏叩头谏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过申枉,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遂称疾去。”这是对抗王莽草菅人命之酷政的勇敢行为,也许就因此事,人们把他与崔发区别开来,建武初,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胡适先生为迁就他立论的需要,毫无根据地将《易林》中两首称颂远古唐虞和周公旦的繇辞(“方啄广口,圣智仁厚;释解倒悬,唐国大安。”“讽德诵动,美周盛隆,旦辅成周,光济冲人。”),说成是“恭维王莽”、“歌颂王莽德政”,两千年前的崔篆若地下有知,不知会如何辩解。
我们冷静地对崔篆也“论其世”而“知其人”,知他在光武中兴后不可能作干预朝政的作品,亦不会凭历史资料大揭前汉的疮疤(有违他“惭愧汉朝”之心);更不应妄测他作《易林》于“王莽声誉最高的时代”,若如此,那么对《易林》全书及各条繇辞关系的解释,便会一片混乱,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胡适先生因不见已失传的《崔氏周易林》,而把署名焦氏的《易林》之著作权判决给崔篆,实在是强加于他,崔篆地下有知,我想他会断然拒绝,因为这不但没有给他增添光彩,“恭维”“歌颂”王莽等臆测之语,实是往他的脸上抹黑!
三、“考证学方法”之辨思
胡适先生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方法到底有何等程度的“自觉”?对他大量的学术著作,后学者我拜读甚少,不敢一概而论(对他的《水经注》案判决我亦疑窦丛生,因未深入研究不便多言),现只就《判决书》中对“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一条再作些检验,归纳一下,有如下数条,敬请当代学者辨思。
第一,运用不确凿之证,本不可作确凿之结论。对于古代留传至今的文本,因历代传抄刊刻,不少字句有讹误,有异文,应从多种版本考证,辨异求真,这是历来认真治学的学者正确的治学方法,可是《判决书》中使用了多种不确之证。《汉书》多种版本的《京房传》中“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句,经过严格校勘的乾隆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本均如此,也有的版本在“京房”词前有“必”字(如1962年的中华书局校点本)。此应是存疑之处,可是适之先生就凭这个“必”字判定焦延寿死于京房之前,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断定焦延寿未活到汉元帝时代,因而不可能作《易林》,这能令人信服吗?又如凭“昭君死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萃》之《临》)中一个“死”字,不容置疑地断定作于“前汉末年,当然更不是焦延寿能知道的了”。可是经查多种版本的《易林》,“死”均作“守”,根据此辞所依“卦变”之象,也不当作“死”。此类异文本来只能存疑,不宜确论。
第二,有原始文本的应核对原文,不应凭二手资料轻易作断语。《东观汉记》与《后汉书》的《沛献王辅传》中,均有辅“善京氏《易》”一语,《四库提要》作者凭此判断该传中引《易林》一条繇辞“书出焦氏,足为明证”(因为《焦氏易林》属京氏《易》系统)。可是,适之先生转引的《文选》李善注文(注:任昉《齐竟陵宣王行状》李善注引,见《文选》卷60。)未见此句,因而断定“丝毫不能证明‘书出焦氏’”,进而说:“今本《易林》确是一千八百多年前汉明帝、沛王辅用来占卜的《周易卦林》。这是最难得的铁证。”“用的是崔篆的《周易卦林》,即是今本《易林》。”因未核对原文,误断的不是《四库提要》,恰恰是胡适自己。
第三,“孤证不立”,这几乎是凡作考证之人必遵的法则。胡适先生断定历史上只有一部《易林》,自《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本“经籍志”皆载的《焦氏易林》与《崔氏周易林》,“内容相同,而题名有两种:那题作焦赣的,或焦氏的,实是误题;那题作崔氏的,或崔篆的,是古写本的原题名,是不错的”。但他“最可证明”的证据只有一个,那就是唐代开成年间赵璘《因话录》中提及《崔氏易林》中的一首繇辞与今本《焦氏易林》中的一首(仅一首!)相同。凭此孤证贸然断定,三代史官及开元《群书四部录》撰者,均未校读过两部《易林》,辨别同异。谁能相信呢?
第四,信“孤证”而撇开有文字著述、有史实可依的主证或旁证,是《判决书》造成错判的主观原因。如:对崔篆生平及作《周易林》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动机,不以《东观汉记》、《后汉书》中有关传记为据,而以主观推测的成书时间写入“判决书主文”;判断《焦氏易林》是否与《崔氏周易林》并存,不以《隋书》、《旧唐书》均言之甚详的《经籍志·总论》为基础论据,曲解或不用《后汉书》唐代李贤注与宋代李石《续博物志》等确证焦、崔两《易林》内容不同、并存于世的资料,避开可确证《焦氏易林》在唐、宋存在并流传的晚唐会昌年间王俞《易林原序》、北宋政和年间秘书省校书郎黄伯思《较定〈易林〉原序》(此二文皆载于《四库全书·焦氏易林》卷首),等等。以主观臆测凌驾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之上,怎能谈得上是“做学问的良好习惯”!
第五,更为严重的是以伪证派生的伪证作为主干支撑。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者牟庭相动用已被历代学者共识是东汉以后人伪造的《易林序》,据其“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之所撰也”一句中前七字错误表述,竟无端妄测“天水”为“大尹”之误,“焦”为“崔”之误,“赣”为“篆”之误,乃至毫无根据地说“崔篆盖字延寿”等等。对于牟氏信口胡说,胡适首先说“粗看去很像是根据薄弱”。又说:“这种推理方法,本是很危险的,只有很精密的考据学者,十分严格的使用,才可以避免错误。”但因牟氏妄说对他的判决有利,故转而说:“照我们的分析,可算是大致不错的。”还称牟氏自诩之言“古人遗迹,信不可忽,虽伪谬犹足宝贵若此”,是“深知历史考据的老手说的话。……这句话真是考据学的名言。牟庭相的大功劳正在他能够从这一篇伪序的几个残字里寻出破绽,来替崔篆做第一篇伸冤状子。”如此肯定“伪序”派生出的伪证,最后又在八条结论中列为压轴之条:“现在完全证明为最大胆而不错误的结论。”此时,胡适先生大概将他“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一法则,忘却了!
胡适先生《判决书》之错判,我以为既有负于被无端剥夺著作权的焦延寿,也有负于“惭愧汉朝”的崔篆。自他以学术权威之首席于1948年发表此文后,只有钱钟书先生未予理睬,在《管锥编》立有《焦氏易林》专题,其他学子皆未敢再涉及此课题。现在,应该平反这桩错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