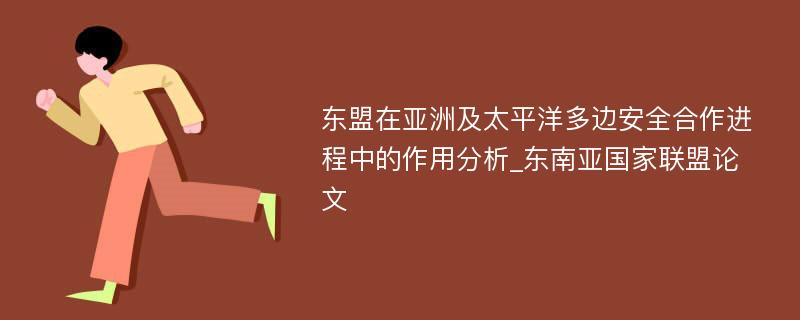
东盟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角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亚太论文,进程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4-0059-08
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是以东盟为主轴而展开的。东盟组织发起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涉及整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特色的制度文化和行为规范—“东盟方式”已经扩大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重要参照指标。目前,学术界对东盟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作用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东盟的大国战略。一般认为,冷战结束后,东盟在亚太地区大国之间推行均势战略(或称大国平衡战略),力求通过聚集所有大国的势力,使之相互制衡、平等对话,共同参与建构和维护亚太安全新秩序,而东盟在其中周旋和协商,扮演平衡者角色,发挥主控中心作用;① 第二,东盟地区论坛的创立及其作用。大部分学者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给以积极的评价,他们认为,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安全对话机制,它的建立和成功运作,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又为亚太地区持久的和平指明了方向。② 有的学者甚至从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出发,推断东盟地区论坛通过规范的社会化和认同的培养,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利于建构一个地区多元安全共同体。③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站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分析,认为东盟地区论坛仍然是为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实力均势政策服务的,或者只是力量均势的补充和润滑剂;④ 第三,“东盟方式”的内涵和价值。目前,学术界对“东盟方式”研究的重点放在其起源和内涵上面。关于“东盟方式”的价值方面,对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肯定它的价值,又要认识到它的不足甚至消极作用。⑤ 但是,学术界对于东盟在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领导角色的成因,缺乏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尤其缺少相关的理论解释框架支撑。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引入国际制度中的政治领导权理论分析冷战后亚太地区力量结构的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东盟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作用,最后探讨“东盟方式”在亚太地区的适用性和价值。
一、国际制度的政治领导权理论与亚太政治现状
从历史上国际合作的经验来看,一项国际制度要获得成功,政治领导权不可缺少。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首先无疑是国际制度的一项创新。在此,为了说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领导权问题,我们不妨引入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相关学说。根据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奥兰.R.扬(Oran R.Young)的观点,在(国际)制度(或机制)形成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政治领导模式,即结构型的领导(structural leadership)、倡导型的领导(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和智慧型的领导(intellectual leadership)。结构型领导一般指霸权国家,他依靠结构性的权力,将物质资源转化为谈判的筹码和条件。智慧型的领导不一定是国际独立行为体,他的作用是帮助观念力量的建构,从而影响参与方对他们有关选择的定义并有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而倡导型的领导,是指利用谈判技巧来影响在制度谈判背景下问题被提出的方式,从而达成彼此能接受的协议。倡导型的领导者们:(1)作为日程制定者,为提交的问题设计在国际层面上进行讨论的形式;(2)作为宣传者,使利益攸关问题的重要性得到重视;(3)作为发明家,设计出有创意的政策选择以克服谈判中的障碍;(4)作为掮客,制定交易协议、征集对重要方案的支持,⑥ 这种倡导型的领导角色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一般来说,霸权国家是国际制度的首选领导力量,但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即使在霸权缺失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国际合作,因为,根据上述理论,倡导型的领导(在智慧型的领导配合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发挥制度合作的先行者和组织者角色。
由于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呈现出混合型的特征,难以形成霸权管治下的制度合作,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政治多元性和安全结构多层次性。亚太这一以太平洋为中心而组成广袤区域,地理上又大致可以分三个次区域—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北美以及大洋洲(南太平洋)。其中,东亚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利益纵横交错的地缘战略中心区。冷战以后,亚太地区的力量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三重结构: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作为四个全球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拥有最大的利益和实力;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作为中等强国,是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东南亚国家作为连接大国和中等强国的桥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
其次,亚太地区的大国之间政治上相互信任程度较低,安全关系总体比较脆弱,呈现出一种“亚稳定”状态。这种“亚稳定是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灵活性的状况。在这方面更像铁而不像钢。这种状况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⑦ 在中、美、日、俄四大国当中,既有传统军事同盟关系,又有战略伙伴关系,也有非敌非友的竞争关系。美国与日本之间缔结了安全同盟条约,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双边安全关系。中国与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以上海合作组织(SCO)为框架形成了进行安全合作。而中国与美、日,俄国与美、日之间尚没有建立稳固的政治信任和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仍然处于调整之中,定位不明确,敌友状态不明,竞争与合作同在。由于亚太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地区安全结构出现明显的断裂和结构性的制度领导权缺位,使得亚太地区既难以形成像欧盟和北约那样完整的多边安全结构,也无法实现在霸权模式下的地区合作。
第三,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不稳定,一方面使中小国家感到无所适从,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机会。特别是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次区域的东南亚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南亚国家古代历史上受到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这一地区各国又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国家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政权。但是,由于受殖民统治遗留问题和冷战的影响,建国后的东南亚地区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矛盾十分尖利。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东南亚部分国家加入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美国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构成防止社会主义扩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的战略链条的重要环节。1967年8月,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五个实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的东南亚国家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东盟成立之初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合作,努力塑造和增进民族国家的抗御力(Resilience)与团结,进而培养地区认同意识。70年代初,东盟提出了地区中立化(ZOPFAN)的安全战略构想,试图通过由大国做出不干预东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承诺来实现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地区化解决。⑧ 80年代,东盟积极参与了以联合国为首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平进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冷战结束后,东盟积极参与地区新秩序的建构并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以大国平衡战略取代地区中立化传统理念。大国平衡战略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东盟作为中小国家集团的影响力,在本地区设法平衡各大国的利益,并使之相互牵制。“为实现这一平衡,东盟采取两种策略,一方面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牵制;另一方面把东盟自身当作砝码,在天平的两端进行调节。”⑨ 东盟的这种小国平衡大国的战略,十分类似于19世纪初奥地利国际思想大师梅特涅的手法。梅特涅高超的纵横捭阖术,成就了百年维也纳体系的辉煌。而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实施,使东盟由过去惧怕大国干预,对大国敬而远之,转变为积极介入并巧妙利用大国竞争,从而为东盟参与地区事务并发挥重要影响奠定了基础。
总之,由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多元混合性和大国之间的政治上互不信任,导致地区合作缺乏结构性的领导权,为中小国家组织—东盟可能发挥着倡导型领导角色提供了机会。
二、东盟—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传统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主要有三种模式: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其中,多边同盟是指三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对付共同的外部威胁而建立的军事同盟。这种同盟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对抗性,历史上的联盟战争就是例子,冷战时期北约与华约的对抗也是如此。大国协调机制是指地区所有大国按照多边主义原则合作管理地区事务,通过调节主要大国之间关系来防止大冲突。19世纪20-30年代,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建立了所谓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开辟了大国主宰地区事务的先例。而集体安全从本意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安全合作境界,它指国际社会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制止任何潜在侵略行为的安全保障机制。集体安全完全实施的条件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大国利益的一致性和人人为公的国际道德准则。⑩ 除了上述三种模式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曾经建立起以欧洲安全合作理事会(CSCE,后改为欧安组织OSCE)为框架的安全对话协商机制,并签署了《赫尔辛基文件》,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大环境下打开了一条相互沟通的管道,对维护欧洲甚至全球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多边主义对亚太地区来说是一个陌生名词和舶来品。冷战时期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形式,主要是以美国为轴心、以双边军事同盟为支撑的“辐辏型”安全结构。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出于其南下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需要曾经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遭到美国的坚决抵制。同时,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也强烈反对苏联的倡议,因为,他们不希望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成为大国的棋子和牺牲品。冷战结束初期,关于在亚太地区适用何种多边合作模式问题,政界和学界曾经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相对较为缓和,不存在明显的共同安全威胁,因而建立传统的多边安全同盟显然不合时宜。亚太主要大国存在政治上的严重不信任,价值观差异很大,也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机制。同时,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操控者是地区大国,中小国家处于边缘地位,或者跟随大国节拍而动。然而,如前所述,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结构中,中小国家是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的政治平衡力量,如果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任何大国合作都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欧洲安全合作的经验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亚太地区的差异性太大,各方顾虑很深。90年代初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政要先后提出过仿效欧安会(CSCE)的模式开展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响应,更没有合适的国家牵头。顾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亚太地区历史上缺乏多边合作的传统,各国对相关安全合作的游戏规则更是不甚了解,因而不敢贸然加入;二是美国担心多边安全合作一旦走上正规化有可能会冲淡它的双边安全结构安排,因而反应冷淡;三是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带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怀疑他们的意图,不愿意看到由他们提出甚至带头组织多边安全合作,更不愿意跟随其后。总之,亚太地区的特殊性使得在该地区不可能形成由大国主导,忽视中小国家利益的大国协调机制或者集体安全,也无法完全移植冷战时期欧洲安全合作的经验和做法。
在这种情形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到了东盟这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次区域国际组织的身上。1991年,东盟的智囊机构“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向东盟首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创新的时代》(A Tine for Initiative)的报告,建议应该由东盟担当起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任务。报告主张,“为了增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保障地区和平,目前已经有了、而且还将继续出现各种各样的有关建立多边进程和机制的倡议。无论建立什么样的进程和机制,东盟都必须扮演主导角色。东盟不但要积极参加,而且还要成为创造性的倡议者。总之,它必须做得更多。”(11) 该报告明确提出,利用一年一度的东盟与对话国会议(又称为部长后续会议ASEAN—PMC)空隙,召开涉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对话会议。东盟智囊机构提出的这种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构想,是一种超越传统的安全合作模式—合作安全。关于什么是“合作安全”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它的主要特点是:(1)合作安全没有明确的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2)合作安全以预防冲突为主,而不是威慑或者干预;(3)合作安全强调政治对话,建立信任措施和预防性外交为主要手段;(4)用协商一致的方式来进行合作,无须缔结条约。(12) 这种合作安全的理念符合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形势和多样性的现实。东盟组织领导人采纳了该报告的基本精神。根据该报告的提议,两年以后,1993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6届东盟外长会议特别安排了东盟6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泰国)与7个对话伙伴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3个观察员国(越南、老挝、欧共体)和2个来宾国(中国、俄罗斯)共18方外长参加的“非正式晚宴”。会上代表们对各自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并同意于1994年在曼谷召开首届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简称ARF)会议,就整个亚太地区政治安全问题展开非正式磋商,从此开启了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框架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
东盟发起和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之所以能够得到各方面积极响应,并顺利发展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难以建立以霸权国家为主导的安全合作模式。在亚太地区没有其他更好形式的多边安全安排的时候,“东盟地区论坛提供了一个地区主要国家之间很好的外交接触与对话的场所,从而有助于维护地区的稳定和秩序。”(13) 另一方面它是东盟长期推行大国平衡战略的一项积极成果。东盟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和制度创新,在大国间充当了“宣传者”和“掮客”,不仅增强了自己在多边合作中的地位,而且不失时机地填补了大国在亚太合作领导权上的“真空”。“东盟地区论坛的存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些结构性的条件,这些结构性的条件制约着大国在传统平衡意义上的选择,限制了他们确保稳定和预见性的能力,从而也为较小的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机会。”(14) 同时,东盟地区论坛奉行合作安全模式,适合亚太地区力量结构特点和政治多元化的现实,它没有假想敌,也不涉及强制措施,对国家主权和安全不构成威胁,因此,能够为各方广泛接受。这样,东盟由于成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力量结构对比的最佳平衡点而顺理成章地充当起了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发明家”,发挥着倡导型的领导者角色。
东盟地区论坛在东盟的主导下取得了较为迅速及平稳的发展。从1994年到2006年,东盟地区论坛共召开了十三届年会,成员扩展到23个,后来先后加入论坛的国家包括柬埔寨(1995)、印度、缅甸(1996)、蒙古(1998)、朝鲜(2000)。为了体现东盟组织的主导地位,东盟地区论坛没有另外创设一套独立的建制,只是作为东盟组织框架下的一个附属机制。目前,东盟地区论坛的各项运作程序主要依照1995年公布的《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规定执行。论坛的发展采取三阶段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建立信任措施;第二阶段,开展预防性外交;第三阶段,探索解决纠纷的办法。东盟地区论坛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加强对话和磋商,逐步建立和培养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因为,由于历史上的积怨,加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亚太地区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猜疑和不信任,成为可能引发冲突的重要根源。所以,只有通过不断的建设性接触和对话,增加各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透明度,才能消除因误会或战略利益分歧带来的不信任感和不稳定因素。在信任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基础上,通过制订国际和地区行为准则,依靠集体舆论的压力,约束各国行动,预防并及早制止冲突的发生。东盟地区论坛的运行模式表现出双轨道和多层次特点。除了一年一度的成员国外长会议在东盟各国轮流举行外,东盟地区论坛还设有高官会议、会间工作小组会议以及各种第二轨道(Track Two)的专题研讨会。目前,已经形成了部长会议——高官会议——会间会——专家小组会议——学术研讨会五个层次运行机制。(15) 论坛会议形式的灵活性和层次的多样性,使之成为一个主题包罗广泛,可以讨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多层次的亚太地区的安全对话系列活动。
除了发起并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外,东盟还是其他涉及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甚至全球性重大制度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东盟发起组织了系列南海工作小组会议(Workshop on Managing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in South China Sea),并在东盟的努力斡旋下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缓和了围绕南海领土主权问题的争端。东盟是亚太地区大量第二轨道外交活动的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亚太地区最大的第二轨道外交平台—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就是在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的促成和主导下成立的,其中东盟国家占了理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多。东盟国家发起和主办了三分之一的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安全对话会议,其中,太平洋圆桌会议(Pacific Roundtable)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二轨道会议,会议的主办方是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承办者是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东盟发起并于1996年主持了首届亚欧会议(ASEM),从而开辟了亚欧制度化联系与洲际合作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东盟通过发起和主导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要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充当了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
三、“东盟方式”在亚太的适用性
东盟对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东盟地区论坛为主要平台的制度创设和“日程的制定”上面,而且还突出表现在该组织所倡导的区域整合模式——“东盟方式”(ASEAN W ay)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推广效应方面。
尽管关于“东盟方式”的内涵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16) 但是,总的来说它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东盟组织的制度文化;二是指导成员国的行为规范。前者主要包括:(1)慎重对待制度化建设。即奉行所谓的“软制度主义”(Soft Institutiona liza tion)。东盟不主张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权威,决策权分散在各国的中央政府。它不提倡主权让渡,相反,而是奉行一种“强化主权的地区主义”;(2)成员加入标准依照“包容性”(Inclusive)原则。东盟在进行扩大化过程中,不对新成员制定严格的政治标准和准入门槛,尽量广泛吸收各种类型的国家参与到地区合作进程中来;(3)以“协商一致”(Consensus)的精神进行决策。东盟组织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不采取投票和否决制度,也不设立解决纠纷和强制执行的机制,在对待不同意见时,东盟采取一种完全民主的耐心说服和平等协商方式处理。后者包括(1)“和平解决争端”(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原则。东盟自创建以来,一直信守不使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原则。这一原则被写入1967年的《曼谷宣言》、1971年的《吉隆坡宣言》(《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和1976年的《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由于东盟宣示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家争端的手段这一原则的执行,使得它走上了一条类似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发展道路;(17)(2)“不干涉成员国内政”(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mal affaires of members states)原则。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原则是东盟地区主义的最为重要的原则。尽管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具体政策执行中往往难以落实。然而东盟的不干涉原则却明确规定成员信守以下义务:禁止对成员国政府对待其人民的行动进行批评,禁止把国家的国内政治体系和政府风格作为东盟成员国资格的条件;批评被认为是侵犯了不干涉原则的行为;禁止认可、庇护或以其他形式支持任何试图破坏或推翻邻国政府的反政府组织;禁止针对成员国开展的反对颠覆性和破坏性的行动提供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18) 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遭受了西方列强入侵,大多经历过漫长的殖民地统治时期,因而获得独立以后对国家主权倍感珍惜。体现了东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高度关切和敏感,这种做法可能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组织少有的。上述“东盟方式”包含的各项原则充分体现了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普遍原则与东南亚地区特殊性的高度结合与统一,是从多样性中寻求合作的典范,是40年来东盟组织倡导下的东南亚一体化进程的经验总结和根本保证,也是合作安全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对整个亚太地区而言,东南亚可能只是一个不大的次区域。在东南亚次区域成功的经验是否能推广到整个亚太区域运用,这对“东盟方式”无疑是一个考验。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盟地区论坛创建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发展历程来看,上述“东盟方式”所体现的主要原则和做法得到了有力的推广和普遍认可。
首先,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亚太地区安全合作采取了“东盟方式”中的谨慎机制化发展模式。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没有照搬欧安会模式,也没有创建一个亚太版的北约,而是依照“东盟方式”,走弱制度化的道路。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对西方制度文化中的“条文主义”(Institutionalism)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和不适应感,宁愿选择松散的组织方式。东盟地区论坛选择了最小的制度结构,至今没有建立独立的秘书处,只是作为东盟组织的附属机构而存在,其活动主要由东盟成员国轮流主持。在安全合作的议程方面,东盟地区论坛设想按照不快不慢的原则分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三阶段之间不设立明确的时间表和严格的路线图。所有安全合作活动均本着自主自愿原则进行,东盟地区论坛的各项决定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约束力。
其次,在成员准入标准方面,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延续了“东盟方式”的包容性原则。东盟地区论坛吸收新成员的最低标准有两条:一是成员国必须是主权国家;二是成员国必须是亚太地区国家(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同时,规定有关新成员的加入问题应该由现有所有论坛成员磋商,由部长会议批准。(19) 事实上,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已经超越了亚太地区范围,例如,它包括了印度、蒙古、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由于奉行包容性原则,尽量接受对亚太安全事务关切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使东盟地区论坛成为第一个真正覆盖广大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论坛,它也是今天世界上唯一的“地区”安全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国际体系中的所有重要参与者(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欧盟)都出现在东盟地区论坛上。
第三,在讨论所涉及的议题方面,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按照“东盟方式”原则,讨论不涉及各国内政事务,奉行不干预原则。根据不干预原则,东盟地区论坛第一轨道会议一般不讨论诸如人权、国内局势等敏感话题。这样做既照顾了各方对国家主权的关注,又可以避免因讨论涉及内政问题而危及的本就较为脆弱的信任关系。同时,为了弥补不干涉内政原则可能造成的敏感性缺失,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进程广泛引入了“第二轨道”外交作为一种辅助机制。对合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敏感问题,如南海问题、预防性外交、人的安全、反恐怖主义原则等问题都是首先在第二轨道对话会议上通过学术界探讨,初步取得一致意见后,才拿到官方(东盟地区论坛第一轨道会议)场合讨论并获得一致认可的。(20) 这种“第二轨道”外交恰好发挥了奥兰.R.扬所指称的“智慧型”的领导作用,它弥补了东盟组织作为倡导型领导角色本身的权威性的不足,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化引领力量。
显然,“东盟方式”采取的是一种有意回避矛盾、预防冲突的方式来小心翼翼地培养各方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寻求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冲突或争端的机制。“‘东盟方式’(的作用在于它)能够抑制武力的使用,并促成一种避免战争的习惯……在短期内,东盟地区论坛通过在主要大国中提供约束性的规范和建立信任措施,可能有助于形成均势(势力均衡)。在长期时间内,东盟地区论坛甚至可能使各个国家超越势力均衡方式。”(21) 所谓“超越势力均衡方式”意指这样做有利于推进论坛朝着地区多元安全共同体合作模式方向迈进。尽管学术界对“东盟方式”的有效性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在东盟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清谈馆”(22) 或者“沙粒中的建筑”。(23) “东盟方式”的特点是权威不足而灵活有余,无法触及根本的安全困境问题等等。(24) 这些批评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顾及其余。而且,从“东盟方式”发展到“亚太方式”,情况必然发生一些变化,毕竟亚太的地理范围和多样性大大超越了东南亚地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和将来一段时期内,这种灵活柔软的方式仍然是适合亚太地区现实的多边安全合作的最佳模式。
四、启示
通过本文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建设中由于缺少能够为各方接受的结构性的领导力量,东盟国家充当了集体倡导型的政治领导角色。
正如奥兰.R.扬所定义的,东盟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制度建设所发挥的倡导型政治领导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制度的发明者。东盟组织创建东盟地区论坛使之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政府间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开辟了地区安全合作的新局面;第二,规则的制订者。通过“东盟方式”的扩大化,使之与先进的合作安全观念相结合,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有了可借鉴的组织原则和行为规范,这些原则规范成为地区社会化的观念力量并有可能推动着合作进程朝着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方向的发展;第三,忠实的掮客和“协调人”(Middleman)。由于东盟的广泛宣传动员,使安全合作的利益攸关问题的重要性得到各方重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亚太地区的政治差异性及主要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使多边安全合作成为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共同事业。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东盟组织成员国经济和政治稳定受到冲击,并同时引发内部对一些原则性问题意见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集体影响力的发挥。与此同时,一些外部成员也对东盟组织在未来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甚至希望它让出“驾驶员”(Drive seat)的位置。但是,通过上述我们对亚太地区的特殊性分析,在较长时期内,亚太地区这种小国领导大国的安全合作模式似乎难以改变,东盟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政治领导作用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注释:
①张锡镇:《东盟的大国均势战略》,《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0-127页。
②梁云祥、赵天:《东盟地区论坛的功能与作用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期,第41-45页。
③阿米塔·阿查亚:《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240-241页。
④Michael Leifer,the ASEAN Regional Forum: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ADELPHI Paper,302 (London:The Intem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32.
⑤张振江:《“东盟方式”:神话与现实》,《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第22-27页。
⑥Oran R.Young"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n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 ( Summer,1991) ,pp.287-288.
⑦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⑧喻常森、方倩华:《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战略构想探讨》,《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
⑨张锡镇:《东盟的大国均势战略》,《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0页。
⑩陈寒溪:《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第33-38页。
(11)ASEAN-ISIS,A Time for Initiative,Proposal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Fourth ASEAN Summit ( Kuala Lumpur,ASE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1) ,p.8-9
(12)阎学通:《中国与亚太安全:冷战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走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13)Michael Leifer,The ASEAN Regional Forum: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ADELPHI Paper.302 London: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9.
(14)阿米塔·阿查亚:《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267页。
(15)喻常森:《亚太地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3页。
(16)张振江:《“东盟方式”:现实与神话》,《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
(17)David Capie and Paul Evans,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 theast A sian Studies,2002) ,p.15.
(18)阿米塔·阿查亚:《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81-82页。
(19)Chairman's Statement the 3rd ASEAN Regional Forum ( ARF) ,Jakarta,July23,1996.http://www.aseansec.org/1836.htm.
(20)喻常森:《“第二轨道”外交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5期。
(21)阿米塔·阿查亚:《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267页。
(22)Hiro Katsumata,"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Constructing A' Talking shop' or A' Norm Brewery' ? " Pacific Review,Vol.19,Issue.2( Jun,2006) .
(23)Robyn Lim,"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Building on San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 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Vol.19,Issue.2 ( Aug,1998) .
(24)沈逸:《合作安全的问题与前景-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例》,任晓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