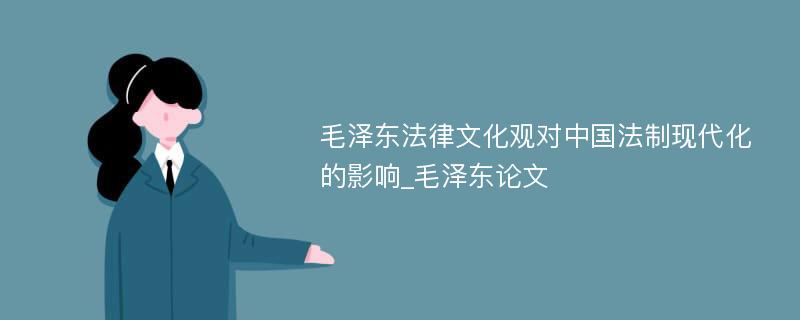
毛泽东的法制文化观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制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1-0062-03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回顾历史,我国法制现代化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利弊得失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展望未来,要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法制现代化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历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法律思想主要是主张废除旧法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法律思想集中于创建、执行新法律。总结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法律观念如下:第一,关于法律的作用,毛泽东强调法律保护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他说:“我们的法律,……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1]第二,法制要坚持民主原则,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订的,执法要通过群众。第三,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为了制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在1954年宪法起草时,毛泽东不仅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北京中央委员阅读1936年苏联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及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宪法,还要求他们读我国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和法国1946年宪法。其目的是为了提出全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第四,对敌我矛盾主要采取专政的办法解决,对人民内部矛盾主要采取民主的方法解决。第五,尽量减少死刑,杀人要少,对犯罪分子应该给以教育。在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也多次做过类似的论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七年内,法制建设主要由下面几个文件定下了基调,一是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二是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平津司法机关的建议》,三是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2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毛泽东指出“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2]。《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的基本精神也是如此,强调了法律的阶级性,批判了六法全书的反人民性,并且揭露了其欺骗性。概括这几个文件,可以看到当时的法制建设是在如下精神指导下进行的:第一,彻底废除旧法律;第二,法律的阶级斗争、对敌专政的政治功能受到了高度重视;第三,在新法律没有建立之前,政策是治理国家的依据,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第四,强调司法干部的政治素质,比较忽视其法律素质。可见,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以这些精神来指导法制建设是实事求是的,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在这些精神原则指导下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特点中已经隐含着偏离法制的倾向,有些提法作为权宜之计提出是适宜的,但必须根据变化的情况加以调整,否则,势必造成法律功能狭窄,公众忽视法律的局面。
二、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发展
纵观从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曲折发展轨迹:第一阶段从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法制建设顺利发展;1957年到1966年法制建设速度放慢,有些方面甚至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建设遭到彻底破坏,形成法律虚无的严重局面。
20世纪50年代初,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宪法和各部门法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毛泽东评价到:“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3]这部宪法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规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体和政体,这种国体和政体与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相吻合。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宪法是纲,纲举目张。在宪法原则的指导下,各个部门法也相继被制定出来,并调整规范着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在行政法律制度方面,首先是根据宪法制定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法,规定了各级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式和责任。其次,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法规,规定了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限和管理方法。再次,国家还建立了行政监察制度和公民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制度。行政组织法为依法行政提供了组织保障,行政管理法为行政行为设定了权限,行政监督法使管理相对人可以监督行政机关,补救行政权力滥用而导致的不良后果。
在民事法律制度方面,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过程。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在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围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这个中心任务,颁布了大量的民事法律法规。这些法律制度主要是有关土地问题的,加强对国有财产管理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成果和恢复国民经济。从1952年底到1956年底为保证“一化三改造”以及“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国家进行了频繁的民事立法,使民事行为、经济行为有法可依。
在中国的法律文化中,刑事法律制度一直比较发达。共和国成立之初,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种危害新政权的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为了稳定社会治安,巩固新生的政权,打击刑事犯罪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国家先后颁布了几个重要的刑事法规,安定了人心,巩固了新政权,对过渡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了保障。
在中国传统的法制观念中,一直是重视实体法,轻程序法的,所以诉讼法制建设一直是薄弱环节。共和国成立后,虽然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受到了批判,但已经内化于人们文化观念中的积淀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外力的作用下荡然无存的。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所以在1956年以前,诉讼法制建设发展较为缓慢。
当共和国的法制建设步入正轨,正要扬帆之际,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受到了来自政治运动的压力。在以后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共和国的法制建设一直是进三退二,徘徊前进,最后在“文革”的十年中几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三、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共和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法律必定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集团成员,特别是统治集团领导成员的法律文化观念肯定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毛泽东的法律文化观念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对共和国蓝图的构思,为“五四宪法”提供了指导,奠定了基础
国体、政体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内容,它制约并规定了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都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科学分析,并据此勾画出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建设蓝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4]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5]。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更明确指出,即将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毛泽东设想并已在解放区部分实行的国家制度法定化了。“五四宪法”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此外,关于共和国的经济制度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也作了阐述,“五四宪法”的规定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
2.坚定地治理腐败,整顿吏治,促进了行政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用群众监督的方法来防止腐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警告共产党人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这些思想势必反映在法制建立中。吏治腐败最令毛泽东痛心疾首,他多次严厉批评腐败现象,论及腐败对党和国家的危害。1951年他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给予人民权力,必须把这一权力用法律加以肯定强化。“五四宪法”第97条规定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虽然那时公民这项权利由于缺少诉讼制度而无法行使,但在中国历史上毕竟首先给了公民这种权利。这不能不说是行政监察法制建设的重要起步,也是毛泽东群众监督思想的立法实践。
3.毛泽东关于审慎判处死刑并给出路的观点有利于法制建设中改造教育相结合原则的确立
毛泽东对于判处死刑一直持慎重态度。在镇反中,关于处理社会上的反革命,毛泽东的要求是“少捉少杀”,关于处理机关、学校、部队里的反革命,毛泽东指示“大部不捉,一个不杀”。“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7]虽然共和国第一部刑法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的1979年出台的,但在毛泽东生前出台的几部刑事法律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等,便贯彻了毛泽东的少抓少杀的精神。由于对判死刑采取谨慎态度,并且给予活路,给我们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使他们重新做人提供了机会,大批的罪犯、战犯接受了改造,重新回到社会,社会得以稳定。
当然,毛泽东晚年的法制文化观对共和国法制建设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治国方略上“依法治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时有错位;过分地注重法律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作用,较为忽略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保护人民权益的作用;把“大民主”作为治国良方,混淆了“人治”、“法治”的界限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邓小平的巨大努力,我国的法制建设才又重新走上正轨。
收稿日期:2002-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