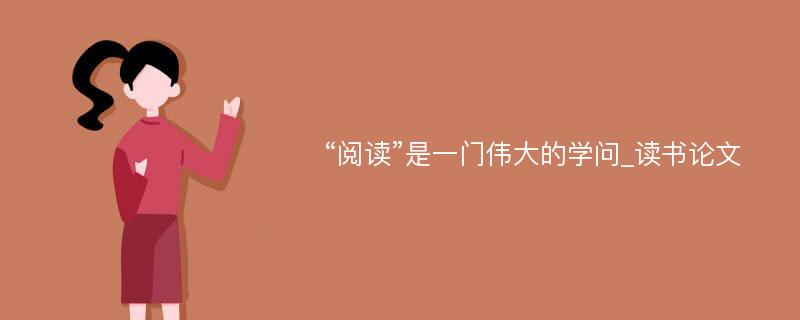
“读”是大学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让我们首先把书本知识比做海洋。
这里说的“书本”,包括学生的课本,也包括一切有益的课外读物。
在这样的海洋面前,常见的两种偏颇行为是:一,搭船过海;二,深入不出。
前者指的是读书上的以“看”代“读”。
不必讳言,眼下“看书”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少了。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难道看书与读书不是一个意思吗?
粗说,是一个意思
细说,不是一个意思。
例如眼下,可“看”的变相“书籍”与日俱增,如电影、电视、电子游艺设施、卡通读物等。有人看过了许多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片子,就自认为已经看过了这些文学名著本身。
还有的人,捧过一本读物,或是报纸、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一篇作品,用很短的时间来一番走马观花,略知其故事梗概、大略意思就认为是“读”了一番。
其实,上面的这些都属于“看”的范畴,没有上升到“读”的层次。
“读”和“看”有时候同义,有时候区别很大。“读”是一种主动的、有为的、目的性很强的求知行为,“看”则可以是被动的、无为的、随意性的精神活动。
“读书”比一般性的“看书”,收获也会大很多,比如说,“看书”看得认真些,可以掌握篇意、段意,句意、词意,但高水平的“读”却可以感受到或理解到作者比他人高明的意采、情采、词采。“采”恰恰是作者、作品的高明之处。
同是写几千年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只有鲁迅把它上升到了“吃人”的高度。这就是“意采”出色。
同是写“秋声”,大多数人只是写了有形的“声”,如风声、雨声、落叶声、虫吟声,只有欧阳修写出了“秋本身”的无形之声。这就是“情采”不凡。
同是写云的动态,大多数人都用“云飘”“云集”“云游”“云飞”,只有韩愈首用了“云横”词,别有气势。这就是“词采”的高明。
不认真地“读”,只是草草地“看”,是很难有上乘收获的。
“读书量”是判定一个人知识面大小的重要参考系数,但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量”?
一个人读过一千本书,一个人只读过一百本书,但前者所读的书都属于一类,例如都是文学作品(乃至文学作品中的一种),而后者所读的书却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谁更接近于“读书量大”的正确含义?当然后者。
一个善于读书的人,往往不吃“偏食”,善于博读各类的书,例如:
一、既读“顺情书”,又读“逆情书”。
一个人由于年龄、性别、职业、趣味上的原因,总有喜欢读的书和不习惯读的书。某些读起来兴趣盎然、手不释卷,在感情上能产生强烈共鸣的书,叫做“顺情书”;读起来就打瞌睡,拧着头皮也读不下去,觉得和自己很难产生共鸣的书,叫做“逆情书”。
一个人不能总读顺情书,应当努力地读一点有益的逆情书。比如,一个喜欢读诗(或者只喜欢读现代诗)的女中学生,应该分出些精力来读一点历史著作,或描写宏观世界、涉及广阔社会生活画面的文学著作。一个男性武侠小说迷,也不妨分出些精力去读一点涉及现代生活的各类文学作品。这样,才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不致成为知识结构残缺的人。
二、既读“近缘书”,又读“远缘书”。
立志学文的,除了侧重于多读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之外,也应适当地读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同样,立志学理的,在多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之外,也应读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
比如,一个准备搞文学的人,不能天天只读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不妨适当地读些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书。一个准备搞物理学或准备搞化学、生物学的人,也应在阅读本专业的书之外,不妨读一点文学、史学方面的书。这样,可以帮助一个人形成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能力。
三、既读“横向书”,又读“纵向书”。
眼下,随着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的活跃,我们从外国“横向移植”来的书籍越来越多。于是,就使很多青年的阅读兴趣产生了相应的位移——热衷于读外国的书,淡于读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这样的读者虽然会有较大知识面,但这知识仍不是立体的,即不完整的。应该同步读一些民族的、传统的、历史的书,而且应当精读、深读,使自己的知识趋于“纵向深化”。同样,阅读兴趣偏重于后者的人,也应读些“横向书”。
四、既能博读,又能精读。
读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书泛读即可,对内容做到大体了解即可,意在获取广泛的知识;有的书必须精读,逐字逐句地读,意在获取专深知识。一个人必须做到既“广知”又“专知”,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立体化起来。否则,单有知识“面”或单有知识“线”,都不能叫做具有了完整知识。
读书的“量”不够,是一种缺憾,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强调“量”的同时也应强调“质”。
有人将近几十年称为“知识爆炸”时代,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由于高科技的广泛应用和在应用中的惯性分蘖,牵动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学科和越来越多的知识门类。在占代,一个人发誓说要读尽天下书,掌握前人和当代人发现和创造的所有知识,是有一定可能的。而今天,这只能成为一种奢望。即使一个人的一生什么都不做,专门致力于读书,从生读到死,他所能读到的、读懂的书也很可能是世界上全部书籍的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而占更小的比例。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由于人们思想、情感的日益活跃,对社会、对人本身的研究和探索,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天天有所拓展,天天有所发现。于是,每天问世的新图书,新文章都是个天文数字。因此,一个人在读书上若是只追求“量”,即使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到头来读到的,“量”也仍然是可怜的。
知识像山,越来越高大;知识像海,越来越深广。人怎么办?
如果产生畏惧心理,畏其高,畏其深,甘于在山下仰望,在海边痴望,这当然是没有出息的,最终要被社会淘汰。
如果一味追着知识量气喘吁吁地奔跑,被动地让知识牵着鼻子走,做知识的仆从和奴隶,即使掌握了再多的知识,也只能把它背在肩上负重行走,活得很苦。
在“知识爆炸”形势下,人若是仍想做知识的主人,就必须改变自己登知识之山、涉知识之海的途径,提高“登”和“涉”的能力。
有了知识,还要善于培养自己的“知识形象”。
什么是知识形象?就是知识在人的手里的使用模样。
同是知识分子,乃至同是大知识分子,使用知识、演示知识的模样是很不相同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诸葛亮、周瑜,《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红楼梦》中的贾宝五,林黛玉,都是古代文化人,都有知识(至少都有书本知识),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模样、形象是何等不同!第一类人有了知识可以指挥战争,治理国家;第二类人有了知识只能应付考试,谋取功名利禄;至于第三类人则热衷于对社会风云人间斗争的逃避(他们当时这样做是有社会原因的,而且他们这种表现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抗)。
有知识的人,在知识形象上的第一大区别是思想意识的区别,精神品质的区别。
一般地说,有知识的人运用知识、使用知识,都是有“功利目的”的。这很正常。若是有了知识只想把知识当成观赏品、玩味品,或时时借用表演“我有知识”来装点自己的“雅人”形象,只此而已,是没有出息的。
但“功利”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功利”,一种是“个人功利”。一个人有了知识,运用知识、使用知识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就可以被称为“社会功利主义者”:一个人有了知识,使用知识或出售知识的目的只在于谋求个人的地位、利益,就属于“个人功利主义者”。
两种人的心思不同,对待知识的态度,使用知识的方式(总称知识形象)也不同。
前者永远是知识的主人,他们对未被人们实际使用的知识教条本身,或对根本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玄虚知识,从来不匍匐膜拜。他们占有知识的方式,也不是单一地囤积“知识量”,而立足于将知识弄“通”,更注重使知识理念和社会现实沟通起来,一切对知识的占有都服务于对知识的使用。
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和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都是这种大通家。他们很有学问,有大学问,在知识的占有量上绝对是他们所属的时代中最出色的,但他们本人却没有摆出什么学者架子,也没有使人产生单一的大学问家印象。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是知识的占有者,更是知识的通家。包括他们向别人讲知识、讲学问时,也能化解掉大量的条文、术语、概念,使之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
而后者,即个人功利主义者,对待知识的态度却往往是盲目膜拜知识符号、知识标签(如职称、名位等等)。他们使用知识的方式也常常是卖弄知识本身,演示知识本身,有时还要故意强化教条、术语、概念的神秘性,以讲得谁也不懂来营造自己的深奥形象,拒绝对知识和社会做出沟通。这样的知识奴隶,且又用知识来压迫别人的人,不能欣赏,更不能去学样。
我认为世界上有大作为、大学问的人,无疑是读过很多书的。如果将“读书量”仅仅以册数来计算,有没有比他们读的“量”更大但最终一事无成也没获得什么真学问的人呢?我想,肯定是有的。
此外,有没有因为读了书,读了很多的书,反倒成了无所作为,连常识性的知识也不具备的人呢?我想,也肯定是有的。至于说,因为读了书而变得坏起来或蠢起来的人,也一定是存在的。举此例子似乎并不困难。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假如不读书,做些务农或经商的事,总归还能练出一点谋生本领。只因为读了书,穿起了长衫,除了懂得一些诸如“茴”字的几种写法之类的无用“学问”之外,别的本事也实在没有一星半点儿。
古代有一则笑话,说是某秀才来到一条二三尺宽的水渠边,问老农怎样越过此渠,老农信口回答:“跳过去。”这秀才便想起书本上的“单腿为跳,双腿为跃”之类的“知识”来。结果,照此“知识”办理,便掉进渠水里。这则笑话讽刺的就是有人读了书,不仅没学到真知识,反倒连基本常识都丢了。
至于有人读了坏书,诸如赞美个人主义的书,赞美凶杀,暴力的书,兜售黄色淫秽的书,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坏人,这样的事更是不乏其例。有的“书呆子型”读书人,读了过时的书,骗人的书之后天天想着去做书中所虚构的那种“英雄”,一辈子都在四下碰壁中度过,这样的“越读越蠢”的人也是有的,荒唐人物唐·吉诃德便是一例。
因此,在“书海”面前不能盲读。只顾一下子跳进“海”里去,或弄一只小船投进海里去,盲游盲划,是有落水或被淹死的危险的。
因此,读书贵在选择。所谓读书会选择,主要是指会确定下列几种书:必读的书;慎读的书;少读的书;拒读的书。
必读的书是指必须读的,尽可能多读一点的书;慎读的书是指可以读也应当读,但必须靠自己去识辨、去判定的书;少读的书不是一点不能读的书,但要限定其量,此种书适当地读一点有益,过量地读便是时间上和精力上的浪费;拒读的书则是指不能去读的坏书,不读不是一种遗憾,而是一种幸运。
读书的“最佳选择”、有时得力于自己,有时得力于别人。后者指的是遇到了好父母、好长辈、好老师,这些人有意无意的正确引导能起很大作用。有时,能影响人的一生——尽管有人是无意的。
当然,一个人总会有独自到“书海”中去航行的时候,这时就不能依赖于别人代他“导航”,走哪一条航线要由自己定。
例如,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读文学书籍,所以将文学书籍作为阅读重点。但仅仅文学书籍也是个海洋,从哪里作起点去游这个海?此时,科学地选择入海码头,科学地确立航线是头等重要的事。少年时代我的决定是:
一、专读世界文学名著,不涉其他;
二、每个名作家的名著,先读一本,暂不贪多;
三、对文学昌盛的欧洲、亚洲、美洲、尽可能将著名作家的代表作都先读一部。
这样,我便大体上了解了世界级的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和艺术风格。现在回忆起来,我对世界上许多名作家的认识,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这样一段读书史,值得庆幸的只有三条:
一、读的书大部分是必读书,没有浪费精力去关注可读可不读或根本无需去读的书;
二、我对书的选择是选取和舍弃并重的:首先选取的是有定评的名家之作,舍弃的是平庸之作;在名家之作中,也首选其一部分,舍弃为时间、精力所不允许都去读尽的部分;
三、这些书大都思想健康、催人向上。
人这一辈子所读的书,除了必读书之外,还有“慎读的书”“少读的书”“拒读的书”。什么是慎读的书?什么是少读的书?什么是拒读的书?简单地说就是:一,有益也有害的书;二,害多益少的书;三,有害无益的书。上述的书怎样确定?要靠自己辨别,当然也要靠教师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