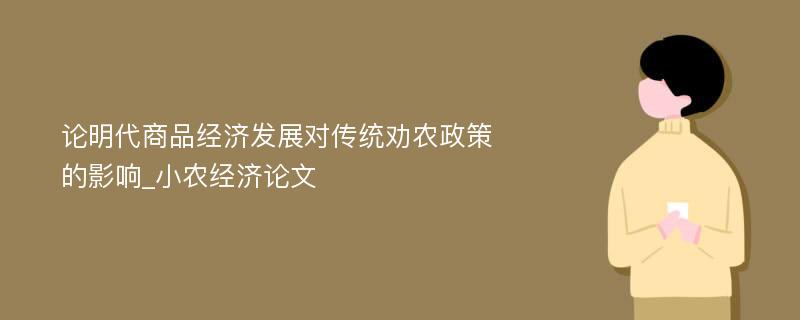
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对传统劝农政策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传统论文,政策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农经济、封建地租与宗法关系的相互结合,构成了典型的中世纪经济制度。为维护此种经济制度,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要殚精竭虑地实行劝农政策,抑制作为该社会“革命的要素”的商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力图减弱其对封建经济“起着解体的作用”,以阻止其成为“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①然而,小农经济发展的极限是很小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必然会越来越深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入明以降,已是封建社会的末叶与近代社会的前夜,已处于山雨欲来之前的“风满楼”时期。明人私乘、地方俗志备载,一股起自青萍之末、沾染着铜腥的“侈风”,正在日渐威猛地席卷着明代整个社会,引起明人生活方式的嬗变。我们透过明人生活上的变异现象,可以考察到该时期商品经济的脉搏在旺盛地跳动。不少迹象表明,当时确有一个异化力量正在刺激、摇撼着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宗法关系,使统治“法网渐疏”,礼制失控,人心浮动,使某些智识者颇有一种“天崩地解”的危机感。
这是封建社会后期小农经济行将崩溃前的一种征兆。
(一)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为国以足食为本。”朱元璋深知这个道理,故说:“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南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②的确,稳定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③的基础,是建设封建政典制度的物质前提。明继元后,朱元璋即收拾疮痍残局,一方面强化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统治。另一方面他继承传统政策着意强本抑末,倾注全力把黎民百姓驱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轨道,重新构建农耕社会编户齐民的传统秩序。
洪武移民诏曾称,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因而朱元璋采取移民就宽乡措施。明初归田,基本上有这几种:一是由政府出面强令组织迁徙;二是通过地方官给牛具、种子,“诏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定居,及时耕播;三是鼓励垦荒“不限顷亩”,并承认一部分农民已经垦荒耕作的事实,“听为己业”。凡是新附土地者,一律蠲免三年税粮徭役。在这优惠政策下,农民纷纷安居,土地逐年扩大垦植,人口与耕地比重失衡状态获得缓解,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也相对有所缓和。朱元璋也很注意与民休息,对入朝地方官们训谕: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宋免前往开封府就任,朱元璋指示他:“汝往治郡,务民安楫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④
实行强本抑末的根本目的,是把小农束缚于固定的土地上,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社会稍待安定,朱元璋就开始编户齐民计丁授田举措。一是清丈全国土地,按纳粮区划制鱼鳞图册;二是普查全国户口,先行户帖后建黄册,备载人户籍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室、资产等项;三是编制里甲。这样,政府不但把豪强隐瞒的土地和劳动力挖了出来,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基本上按平均主义原则做到耕者有其田,而且又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在户籍和土地基础上,以宗族血缘关系为胶凝剂,以乡里组织为纽带,编织成一个能够贯彻落实皇权政令的松散集合体。要求每一集合体能发挥其自给自足自保作用,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以确保完成向国家贡纳租税徭役的能力。为保证小农生产的列车在铺就的轨道中稳定地运行,明王朝赐钞备农具,购耕牛、种粮,贷给需要的农夫,使不违农时;从国子监选人才“分诣天下郡县修治水利”。据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共治理塘堰40987处,河首4162处,坡渠堤岸5048处,使少受自然灾害。
朱元璋以身作则,躬耕籍田,皇后亲蚕。其指导思想是: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他说,盛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妇作织,而百夫待衣,欲民无贫人得乎?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立场度衡农工商利弊,他认为“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要求臣民在生活上克勤克俭,保持朴素的“丰衣足食”水平。他将缴获陈友谅的镂金床砸碎,以示倡廉,并令庶民之家不衣锦绣。为体现重农政策,十四年,明政府又公布一个象征性规定,只准农民之家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准穿布。如农家有一人为商贾,亦不准穿绸纱,号召贸易在农隙,养兵于屯田,反复申明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
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凋敝的小农经济,经过明初的整治,又恢复了生机。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垦田猛增至8507000余顷,有户16052860,计60545812口,征得租税32789800石,致使仓储“蓄积既多,岁久红腐。”建文帝嗣极,亦欲于劝农振贫恢复王道有所举措,苦时短暂,建树不著。靖难兵燹过后,永乐承袭乃父劝农政策,本“爱民以实惠为先”精神,移民屯垦,治理运河、吴淞江,征耕牛、铸农器,恤民饥寒,故农村经济继续有所发展。洪、宣时期,政治已由严急趋向平稳,统治阶级内部相对稳定,政出三杨。当局对前代不恤农事,以徭役妨农作,召乱亡之鉴有所警惕,继续与民休息,实行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所以“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安心农亩无有他志。《宣宗实录》称:福建汀州仓储“可支官军百余年俸粮”,其他府县仓禀蓄积亦丰,“至红腐不可食”。⑤然而,很明显看出农政已今非昔比。永不起科的“皆核入赋额”,农民负担趋向繁重;土地兼并、逃户流民现象亦逐渐形成。于是,宣德间增设浙江钱塘、仁和、海宁、新城、昌化、嘉兴、海盐、崇德诸县县丞,⑥开专官治农之例。从明初不专设农官到置专官管理农事,既说明统治者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的重视,又可见农村中的事情复杂了,农业上不安定因素增加了。以后,增设各府州县劝农佐贰,置屯田水利臬臣,间或特遣重臣巡察,遂为成例。地方官员亦以有专司而弛肩担,唯把勾摄词讼作常务,不以农业政事为意。成化年间,先后设置了河南、山东等处布政司参政各一员,所属各府同知一员,职专提督农民耕耘,增设苏、松、常、镇、湖五府通判,并所属长洲等县县丞各一员,专司劝农,又增设山东、山西布政司参政一员、增设直隶、江西、湖广、湖南、应天诸州县判官主簿为劝农官。⑦嘉靖六年,当局反复通令所属府州县原设治农官处,不许营干别差,专一循行劝课;原无专官处,也要委派佐贰一员带管。⑧二十三年又增设凤阳府通判一员治农,并责令淮安、徐州督农官于各州县乡社,分设农耆等役。这些措施都说明明代农业上的问题日趋严重,范围日益扩大,并越来越病入膏肓了。
(二)
入明以后,随着封建结构的调整,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国封建社会内起伏曲折的商品经济也同时得到复苏并有所发展。朱元璋所谓“得万物自然之理”,⑨即继重本抑末传统,压制弃农从商势头,限制商贾生活上过高享受,缩小商佚农辛差别。然而,为维持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之平衡,即使在洪武年间,也不得不对商业采取相对宽容政策,如改革前朝苛重商税,裁撤364处税课司局;对商贾在人格上亦以平等看待,承认他们与农民一样都属人民范围,还让儒士编书教之,希望他们遵纪守法,好好做生意。这些措施对商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明代社会经济至宣德年间跃上一个台阶后,由于征伐、边患、中官擅权、土地兼并,赋役加重,农村社会不安定诸多因素,随即出现危机。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阶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在物质享受欲望刺激下,为购买那些日益精巧的民间手工业产品和外贸珍奇,及其他奢侈品,渴求攫取更多货币所造成的后果。朱元璋似乎早有决心,打击豪强,防治官僚阶层的腐败。可是实践证明,皇权的绝对化并未能阻遏住官吏们的腐化,相反倒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全方位的、深层次的重重矛盾,深刻地影响着朱明一代的政治,动摇其经济。《明史·食货志》称:商税的“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须纳税款的物品,皆榜于官署,按而征之。免税范围日益缩小,对偷漏税的处罚越来越严,均表明农业上的赋税剥削已远远满足不了明王朝国家机器日益增长的开支需求。正统时,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弛用银之禁,等于宣告当局回笼宝钞稳定币值努力的失败。于是“钞壅不行”,朝野率皆用银,势若众流之赴壑,至成、弘间再也无法阻挡。此种趋势,当与明中叶商业的再度发展,市场进一步扩大相适应,二则也同当局在财政上重视对白银的聚敛有密切关系。从田赋征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中间可见朱明王朝一些政策措施的改弦更张与商品经济发展的联系。这样,农民们和工匠们,还有那些欲求更多金钱的大人们,都被进一步推入市场经济的波涛。
就理论上而言,“班匠银”的施行,结束了中世纪官工徭役制度,使手工业者有更多时间从事本专业生产,或自由地改业农商。手工业技术和产品也可自由地以前所未有的高效投放市场,从而使一些民营手工业作坊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官营手工业作坊则以银从劳务市场招募技术熟练的雇工人生产。封建剥削的货币化,使农民不得不服从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地从事一些能多卖银子的作物生产。一些富农、地主索性把土地当机器,雇佣管理人员和劳力,专事生产市场所需的各类粮食和经济作物,转为经营地主。
社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使明代商业发展走向一个辉煌时期。是时,全国之道路通达,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品种不断增加,商人队伍日益壮大,销售范围愈来愈广泛。商贾拥资十万百万者比比皆是,藏镪数十万者屡见不鲜。名著全国的大商人集团数量增多且相当活跃。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对万历年间徽州商人集团资本总额的估计,在3000万两左右,年利在900万,比国库税入还多出一倍。商业的兴盛,不仅表现在原有城市商业网络的拓展、座商数量的增多,商品种类的繁杂以及街坊延伸、城区扩张,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市镇勃兴与城市点的繁荣。平地张幕、画界成巷的贸易点遍布于产地、城乡结合部、以及水陆交通枢纽地段。有的地方的集市渐渐发育成固定摊位、店铺,引导百业开发。明人笔记颇多载述,称其五方辐辏,居民日多,“成都成邑”,“无异城市”。
大大小小的城市是封建统治的官僚机构扎根,各级统治者及其爪牙、附庸们生活的地方。苏联大百科全书在写到有关城市章节时这样赞美道:中世纪东方所有的城市中,要数中国的城市人口最多,最繁华,最富庶、最美丽。丰富的物质资料,创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满足了统治阶级物质的、精神的消费需求,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百物皆仰给于贸居”。⑩地主乡宦富商大贾家族,艳羡城居生活的,亦纷纷向城市移民,便是当时城市经济繁华的明证。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明人的视野,也给明人的传统心理带来了不小冲击,精神上的裂变,引发观念的更新。那些皇亲国戚,公卿列侯、豪右势家自不待言,即如一些积资十万百万不稀奇的商贾们,亦因不甘寂寞而躁动不已。他们役财骄佚,食则饫甘厌肥,衣则锦绣丽服,居则绣户雕栋,行则舆马张盖,动辄数十万金;斋头清玩,案几床榻,备极精妙,咸不论钱,几成物妖。尤其是那些执商界牛耳者,在经济活动中与官僚集团或合为一体,或互相结托,掌专卖之权,得专卖之利,而又以鹾商为巨擘。其经济势力渗进地方透入庙堂之上,勾联结网,人情、财运通达,社会地位也相应上升。有财有势,他们就藐视“礼制”约束,敢向势要特权阶层挑战,以“僭侔公室”、“拟于王侯”的奢侈享乐来宣泄暴富后的失衡心态。《金瓶梅》里描绘的西门庆,起屋造园,花天酒地,穿太监送的“五彩飞鱼蟒袍”,吃变味清蒸红糟鲥鱼等举动,即是此种经商暴发户心态的反映。另外,皇家与官僚集团直接参与经商,商人可藉捐纳制度“衡金之多寡而畀”文武官员品级,(11)以及士商地位之互变,更使明代社会风尚大变: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12)群相蹈之,一发而不可收了。
(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专制主义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体制之间,自然环境与物质生产之间,社会发展与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导致了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起有伏的曲线状发展。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劝农政策的影响极大。它的发展决非在加固小农经济基础,而是步步进逼,摇动这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诚如明季思想家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在“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大潮冲击下,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赤裸裸的货币关系渐渐替代着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原来维系着封建统治基层组织的绑带正在发生断裂,过去那种闾阎安堵,比邻敦睦,家给人足,盗贼不生的淳朴民风和安居乐业的田园景象已经遭到破坏。因此,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总要运用其政权力量实行调控,形成强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以帮助节节败退的小农经济夺回其固有阵地。然尽管如此,社会发展进程显示,其势已越来越不可逆转。
明代商品经济齿轮的启动,把社会多层次的人士都卷入经商从贾的潮流之中。特别是那些封建官僚的追逐拜金主义,不仅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大大降低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结果是架床叠屋的官僚机构,臃肿的官吏队伍应运产生。在这唯耕惟读方是正道的社会里,科举进士的围城依然是人们苦恋与必闯之妙境,哪怕其时政坛波谲云诡,入围城者仍有“缙绅例有优免”的莫大利益可图。正德、嘉靖时人聂豹指出,士大夫一登仕籍,“乃听所亲厚推收诡寄”,“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削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以图全户优免”。(13)万历时的何良俊也谈及:松郡士大夫中进士,对过去那些谈文论道的朋友已不感兴趣,“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数百两,而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14)一些不能从正途进身者,靠捐资也要买顶纱帽来戴,故至万历时,行政机构已扩张原来12倍,官僚队伍增加原额20倍。皇家豢养的一支宦官队伍同样不断膨胀,与官僚队伍相犄并存,如再加上为官宦们当差的吏员杂役,其数量实在是相当的惊人。且以《虞谐志》中常熟县衙役举例:计有“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余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当局为稳定这支办事效率低,生活水准高的庞大统治阶级队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强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编民的超经济榨取。此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用开支。正是从这一利益角度出发,明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使国藏日益充”的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实行,在客观上却又把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向继战国、秦汉和唐宋以来的第三个高峰。
空前发达的商品经济,当然会对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的生活领域发生深刻的影响。在嘉靖前期就有人指出“扬俗尚侈,蠹自商始。”(15)后又有人说,扬商之“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致富者群慕效之”。(16)而扬之侈俗又随走南闯北的商贾行踪,“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俗”。(17)明代的江南,社会经济要比江北还发达。因此,张翰也说:明人生活“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18)民间的生活习俗是认识人们生活的一把锁钥。一切民俗形态,无一不与生活密切相连,与现实生活糅合一体,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范廉深有感慨地说:“习俗移人,贤者不免。”(19)这就是说,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形成一种赶时髦的社会消费心理,谁也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一般平民也用“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即便是“家无担石之储”的工人、店员,亦“耻穿布素”。服饰在社会生活中是可视性最强,最能影响和转移社会风气的因素。封建礼制对各类等级所用质料、色彩、款式的规格极严,“度爵而制服”,见其服饰而知贵贱。如今坚冰渐被打破,市井之妇、娼优贱婢、隶役长年、布衣蔬食者,都把五颜六色的罗绮绸缎作日常衣裳穿。人们又在款式上求新求异:“衣则忽长忽短,袖则忽大忽小,冠则或低或昂,履则忽锐忽广”。(20)这种反映明人对人生乐趣的追求,一旦成为民俗心理定势,漫延冲击着守旧秩序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看到明代社会在商品经济浪潮中挣扎的情状。
商品经济把一切复杂的东西都简单化了。“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本繁锁的征收,统统归并为征收货币。这对明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又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毕竟暴露出明政府向私家地主争夺小农,瓜分其剩余劳动的急切心态,目的依然在于企图使农村继续维持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状态,使其直接向国家贡纳赋税徭役,达到巩固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明初精心编制实行的里甲制度的衰败与社会经济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分解。新法初行,确曾使国家经济状况带来好转,说明其一定程度上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可是,封建制度上层建筑自然不可能没有限度的支持商品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以自毁其基础,即使在时人称便声中,就有人持批评意见,说这是“宽富累贫,徒滋吏弊”,“商宽农困”,“村疃为墟”。(21)既是事实,亦无法避免,恰好反映出封建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小农经济与发展中的商品经济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与耕地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户籍已紊乱不堪,加上封建吏治败坏之症结,条鞭之法后来执行中是鞭外加鞭,手续费倒要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因此,在农村中又出现一个振荡,“人心惊慌,欲变地产以避之”。(22)或因无法承受而作“投献”,或干脆弃农走避他乡。当局对此情况虽说十分清楚,但为保“国用”仍然严饬”各有司挨究种地人户分收子粒草束输纳。毋得私擅停减”,给在籍者无疑增添一条“陪纳”的锁练。顾炎武总结说:“愚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也。”这样,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风潮的侵袭之下,一旦遭受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其“稳定的”堤防一下子就被摧垮了。“民命不堪,遂皆迁业”。(23)富有缩资弃田,“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乃躲避赋役而趋末。有的地方—甲中止存四五,有些地方“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应付差徭,不复有种田之人。照何良俊的估计非农业人口已达到60-70%,某些地区“民逐末于外者八九”。经商队伍中,“缙绅仕夫多以货殖为急”,总的来看,“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由上情况可见,正德以后,嘉靖隆庆间的明代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了。
(四)
封建时代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反映在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方面。封建政府的职能便是最大限度地把一个个小农稳定地维持在一块块小耕地的占有上,“安居乐业”。明初统治者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丘浚后来说,“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几于倍蓰”,(24)当属人口增殖的正常现象。可是,在官方掌握的人户,却出现下降趋势,“版籍不可问矣”,而致“有绝不可信者”。(25)究其原因错综复杂,然而所谓承平日久之后,中国封建制度的痼疾在明代又很快暴露出来,产生危机是根本原因。痼疾的复发发明政治失控。当政府不再能强有力地有效压抑必然的、对它产生威胁的,但又具有十分诱惑力的商品经济,特别是商业发展的势头时,明初理想的田园牧歌诗般的农村社会就被搅乱了。
诚如前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队伍的膨胀,确已使明代社会的小农经济、封建地租、宗法关系的基础受着日益严重的威胁和腐蚀。明代商业的繁荣,又明显的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相协调,更与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的农业的发展比例失调,且以自耕农的大量破产、弃田为基础,使明代的农村问题和农业生产问题显得更其严重。这从明代中后期米价的升值得到反映。明统治者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它所能掌握的剥削对象,财政收入与统治的稳定。它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想力挽农民与土地急速分离的狂澜:一方面试图以赦免拖欠钱粮、免除杂泛差役,债务还本不加利,承认在外产业已成者原地附籍等让步措施,动员流民归田;另一方面接连颁布禁止“奏讨”和“投献”土地的法令,限制勋贵豪强无止境的占田;并在意识形态上加强封建思想的教育与宣传,强调“天下犹一家”的伦理纲常,反对人欲功利,号召民众“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希高慕外之心。”(26)可是收效甚微。王邦直奏称,明中叶以后,“自—州—县言之,大约流移之民恒居其半”,(27)几成全国之普遍现象,且呈恶性循环,日益严重。据李洵研究指出,在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沦为流民的至少有10%,即六百万。(28)与此同时,农民们也不断聚结起来,打杀官吏地主豪强,为反对土地兼并,捍卫自身不与土地分离,进行过不少此起彼伏的斗争,当然也遭到了失败。
至此,明代所继承的重农抑商,着意扶殖小农经济的传统劝农政策,无疑受到沉重的打击。它所赖以支柱的小农经济社会也被日益破坏。明代封建王朝的前途面临着重要的抉择,不是在它实行自我调整中保护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并促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胎儿的茁壮成长,便是待汇聚到由农民发动的,足以摧枯拉朽的伟大战争到来,在战争中得到调节,重复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故事。
注释:
① 马克思语,见《资本论》卷三,第1019页,人民出版社。
② 《明太祖实录》卷16。
③ 徐干《中论·民数篇》。
④ 《明太祖实录》卷34。
⑤ 《明史·食货志》。
⑥ 宋希庠《中国历代劝农考》,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69页。
⑦⑧ 《中国历代劝农考》第69、70页。
⑨ 《明史·太祖本纪》,朱元璋临终遗言。
⑩ 顾起元《客座赘语》。
(11) 《明史·杨继盛传》。
(12) 张瀚《松窗梦语》,卷十七。
(13) 《明经世文编》卷222,聂豹“应诏陈言以缉灾异疏”。
(1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正俗”。
(15) 邹守益:《扬州府学记》,见《民国续修江都县志》卷八上,“学校考”。
(16) 《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17)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下,第442页。
(18) 张翰:《淞窗梦语》卷七。
(19) 范廉:《云间据目抄》卷二。
(20) 见张翰:《松窗梦语》、龚炜:《巢林笔谈》、叶梦珠:《阅世编》、袁栋:《书隐丛说》等。
(21) 见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九,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下。
(22)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2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
(24)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14,《总论威武之道》。
(25) 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5《户部》;王世贞:《弁州史料后集》卷60。
(26) 《传习录》中。
(27) 《明经世文编》卷251,王邦直:《陈恤民十事——减赋役以招流移》。
(28) 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