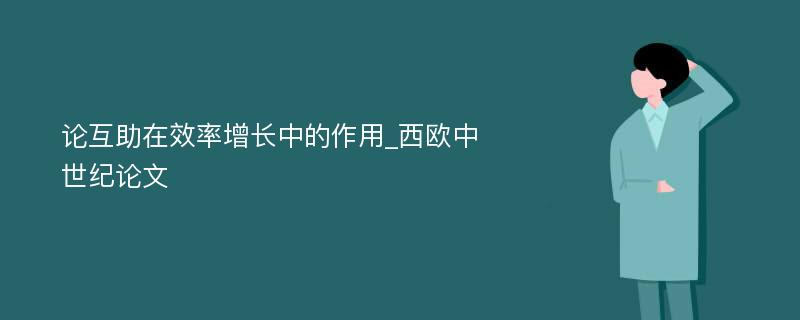
论互助共济在效率增长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作用论文,共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中国历史上的治水谈起
效率有两个基础,一是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是道德基础。仅有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1]。现在,专就效率的道德基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史料表明,中国古代屡遭严重的水灾,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把治水当做一件大事。由于中国古代就着重治水,于是国外有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由此断言,出于治理洪水的需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很自然地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怎能组织如此宏大的治水工程?似乎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渊源于经常性的洪水泛滥和庞大的治水工程。于是治水、集权、专制制度三者就不可分割地被拴在一起了。这种观点曾经在国外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中被宣传过,以致于有人把治理洪水所需要的高度集权与专制制度称作东方的传统。
为什么中国古代会形成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庞大的治水工程同专制政府作为治水的组织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看来也不能完全予以否认。但就从洪水泛滥与治水事业来考察,历史所给予我们民族的影响,决不是用以高度集权与专制制度为特色的所谓东方传统所能概括的。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传统同治水事业有关的话,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这样的:是疏导而不是堵截,是化解而不是淤结,是多方协调而不是独断独行,是互助共济而不是见利忘义,这就是几千年治水经验所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重在疏导而不在堵截,这是中国人历代治水宝贵经验的汇集。从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到各级政府官员,只要办过水利,处理过水灾水患,全都明白这个道理。堵截,至多成功于一时,但最终没有不失败的。疏导,才是有效的治水途径。疏导就是顺应自然。重在疏导,这个由治水得到的经验后来被广泛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从而在中国历史上与现实中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即使在民间,人们也往往用疏导二字来处理家族矛盾、邻里纠纷。化解的含义同疏导是相似的。人际关系中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或冲突,甚至逐渐留下了积怨。怎样对待它们?离不开疏导,离不开化解。如果说历年治水对中国民族传统的重大影响之一在于对疏导的重视和对化解的重视。可能并不过分。和为贵之所以成为中国民间待人处世的原则,不是偶然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因素在效率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生产经营和管理同治水一样,都要尽可能地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同治理水灾水患一样,重在疏导而不在堵截,重在矛盾的化解而不在问题的淤积,这是效率增长的源泉,也是效率增长的保证。
正因为重在疏导,重在化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年份出现了盛世。盛世,是疏导精神占据主流的年代,是社会上不少矛盾得以化解的年代。至于中国历史上某些年份之所以发生大的动荡、混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恰恰是由于政府背离了疏导原则与以化解为主的处理矛盾的方式。
疏导,既有疏,又有导。疏是疏通、疏散之意,导是指引导、分流之意。化解,即有化,又有解。化是指化开、稀释,解是指剖析、松绑、消散。疏导与化解,包含着宽容。矛盾宜疏不宜堵,宜解不宜结。以宽容的精神来处理人际关系中的摩擦、冲撞,即使是多年累积而成的疙瘩,也会逐渐消散。如果用堵截的方法来处理社会上的矛盾与纠葛,更有可能使矛盾越积越多,使日后的处理更加困难。治水给中国人的宝贵经验正在于此。
治理一条大江大河,需要多方协调,需要互助共济。上游与中下游,左岸与右岸,城市与乡村,这一州县与另一州县,这一村庄与另一村庄,无不处于同一个大协作网之内。对洪水的防治,对水灾水患的治理,既要靠疏导,也要靠协作。无论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之下还是在诸侯割据的政治格局之下,没有各个地区的协作,洪水及其造成的灾害依然是难以消除或减轻的。与治水有关的地区协作,尤其是民间的协作,历史久远,它们同样形成了中国的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协作意味着齐心,团体的凝聚力、社会的凝聚力,是在协作的基础上产生并巩固的。正由于有这种凝聚力,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尽管曾遭到多少次内忧、外患、战乱与灾难,但社会没有解体,民族没有衰亡,经济照常运转,人民照常生息、繁衍。什么是效率?这就是最大的效率,是经济学家一般不考察或不注意的效率。效率的背后是社会的协作精神,是社会的巨大凝聚力。
二、互助共济的启示
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治水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存在着以疏导、化解、宽容、协作精神为特征的民族传统,这是一种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凝聚力由此而来,效率也由此而生。
几千年来,中国这块土地是多灾多难的。水灾,只是若干种灾难中的一种。洪水、地震、兵灾、匪乱,都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治水过后要重修堤岸,再建家园;地震过后要在废墟之上新盖民居,新建村镇。兵灾匪乱之后,人们重返故土,恢复平常的生活。在避难中,离不开人们的互助共济;在重建家园时,同样离不开人们的互助共济。正是依赖这种互助共济,中国人在历尽磨难之后,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继续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和文化。互助共济,使中国人增添了同各种灾难抗争的毅力。
互助共济是来自民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捐资解囊,是互助共济;投亲靠友,也体现了互助共济。来自民间的这种互助共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因为它是非组织性质的、自发的,而这种非组织性质和自发性质的互助共济,依旧带来一种浓厚的自觉成分,假定人们缺乏自觉性,对受灾受难的人的帮助能持续存在么?互助共济的精神能发扬么?能被一代一代继承么?互助共济的精神是习惯与道德力量的体现,而习惯与道德力量在建立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是市场与政府都无法替代的。
当然,在政府形成以后,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了社会救济的责任。在政府的支出中,不管数额的多少,用于社会救济的支出总是支出项目之一。政府用财政支出来救济灾民或给鳏寡孤独者以补助,是从维持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考虑的。以对灾民的救济来说,政府的救灾支出通常是满足不了需要,所以来自民间的互助共济性质的社会救济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大灾之年,这种社会救济的作用更为突出。此外,与政府救济灾民主要着眼于维持社会安定这一出发点不同,来自民间的社会救济尽管也含有维持社会安定的意志,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出自人们对受灾受难的人的同情心,出自人们对其他人的命运与遭遇的一种关怀。捐资解囊的人并不打算从自己的捐助中得到什么回报,他们这样做,只是表明自己在尽到一份责任。如果说习惯与道德调节同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相比有种种区别的话,那么,在习惯与道德力量影响下人们出于同情心与责任感而对灾民或其他受难者的救济,就是区别之一,因为这种救济行为纯粹发自人们的内心。
互助共济与效率之间是什么关系?在防御洪水侵袭的过程中,在洪水成灾迫使居民逃难的过程中,以及在水灾过后人们重建家园、重建村镇的过程中,互助共济促使效率增长。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互助共济,受灾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不知会增加多少!水灾过后,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怎会取得这么大的成效?这不是效率的增长又是什么?有了互助共济,灾民不但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且抗灾、自救、恢复重建的信心会增大。有了充沛的信心,效率将会提高,这已被无数史实所证明。因此,治水和战胜水灾的历史所留给我们民族的,不仅是对疏导和化解的重视,也不仅是对协作精神与宽容精神的强调,而且还包括这种互助共济的传统。效率是在人际关系协调中涌现的,疏导、化解、协作、互助共济,在促进人际关系协调的同时,也带来了效率的不断增长。
三、对历史上互助共济行为的进一步分析
让我们再以西欧中世纪城市刚刚兴起时的互助共济行为作为例子,对互助共济与效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效率增长的源泉。
在中世纪的西欧,在城市刚刚兴起之际,自然灾害频繁,战争时常发生,城市居民所需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要靠外界供应。但这种供应并不是有保证的,一旦供应中断,不仅城市的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活动无法维持,连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维持不下去,效率增长问题就无从谈起。简言之,连人都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效率或效率增长?
为此,一些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采取了组织城市经济生活的措施,城市居民拥护这些措施,遵守城市定下的规章制度。城市组织经济生活的措施以及城市居民对城市有关规定的遵守,都体现了互助共济精神。例如,有的城市规定不许囤购粮食,不许面包作坊购买超过实际需要的小麦,不许城市里的作坊或居民到农村去预购粮食。有的城市还规定每个居民家庭一定时间内或一次购买粮食的最高限额。诸如此类的规定为的是不要让任何一个居民家庭因断粮而饿死[2]。
又如,有的城市公开宣布禁止“优先购买”,这就是说,由外地运入本城市的商品,必须先运送到城市指定的公开市场去出卖,供市民们自由选购,在一定的时间内,只零售,不批发。例如,在德国的符茨堡,当外地一条运煤的船到达该城市后,前八天只准零售,每户居民都可以来购买,但至多不超过50筐煤。八天以后,剩下的煤才准许批发出售[3]。在英国的利物浦等城市,规定到达港口的全部生活必需品, 都先由城市当局以城市的名义买下,再由城市配售给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城市居民,人人得到规定的一份。在法国的亚眠等城市,盐作为生活必需品,是由城市配售的;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一切粮食的买卖都由城市经营,以保障每个城市居民的需要。在中世纪的西欧,有些城市还实行过这样一种制度:外来的商船靠码头时,船上的商人要立誓,说明货物的成本和运费,然后由城市派遣的价格评议员根据商人的申报,定出价格,这才准许商船卸货,在本城发售。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尽管都属于中世纪西欧城市为保证城市供应正常的政府行为,但政府的行为仍同当时城市中流行的互助共济精神有关,而市民们之所以接受这些政府调节经济生活的措施,也同当时城市中的互助共济精神的影响有关[4]。
中世纪西欧城市在刚刚兴起时所采取的互助共济性质的措施有较广的范围,不限于组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例如,为了更好地组织城市经济生活,有些城市设立了“公灶”,让家里有困难的人到那里去烘烤面包;有些城市在郊外保留了公共林地和公共牧场,容许市民到那里去砍伐树枝,作为燃料,或在牧场自由放牧;有些城市中还设立了公营的当铺,在建立之初时往往不收利息,或者只收很低的利息,其目的是使城市中的穷人免受高利贷的盘剥[5]。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刚兴起时, 街道狭窄,住房拥挤,许多房屋是用木料建造的。为了防止火灾,不少城市很早就成立了义务消防队,把防火作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城市为了保证本城市的居民能正常生活,还规定义务的巡街值夜制度,成年男子都有巡街值夜的义务。
以上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中,在互助共济精神的影响下,公益性的、公共服务性的设施被城市当局和城市居民们看得何等重要。从经济上看,这显然是与当时社会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城市在兴起时的艰难处境有关的。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而城市与乡村又处于彼此对立、彼此隔绝的状态中,不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城市怎能继续存在下去?怎能进一步发展?可以认为,是一种互助共济的精神,使城市在艰难的年代里经受了考验,使城市以后逐渐成为吸引商人前来和吸引农奴前来的中心。如果要联系到效率问题来进行分析的话,十分明显的是:城市能够持续存在,能够不断发展,这本身就体现了效率,而且这种效率是同城市中的互助共济精神分不开的。互助共济,既保护了城市的弱者,也保护了无论是弱者还是强者的共同庇护所——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互助共济是对每一个城市居民的保护,不管他在何处,从事什么职业,身边有多少财富,只要他来到这座城市中,他就受到城市的保护,包括城市中的互助共济精神的保护。
四、互助共济的精神不会消失
从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时的情况可以看出,互助共济精神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促进效率增长与保证效率增长的重要作用。但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城市当局所实行的组织城市经济生活等措施后来又变成了阻碍技术进步和不利于效率增长的措施,那么这是不是说,互助共济也有其消极的、反面的作用呢?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有必要仍以中世纪西欧城市的措施谈起。在城市刚刚兴起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城市手工业者为了维持行业稳定,对于市场竞争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其出发点也是想使本行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并想使本行业的从业者有安定的生活。例如,在不少城市中,由手工业者所组成的行会对会员的生产经营有下述规定,如规定开店的手工业者不准从事贩运活动,即不准兼做行商,还规定手工作坊不许招贴广告以招徕顾客,不准拉顾客上门,不准削价出售商品。在某些城市,行会还禁止手工业者游街串巷,上门服务。例如,14世纪初,德国赫尔姆城禁止裁缝师傅上门干活;14世纪中期德国法兰克福城禁止鞋匠上门补鞋做鞋。上门干活被认为会加剧竞争,扩大同行业人员之间的摩擦,并使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又如,在当时的手工作坊中,按照行业的规定,劳动时间的多少也是有限制的。一般只容许从日出到日落之间进行生产和营业,只准利用自然照明,不许在灯光下干活,夜班被严格禁止。关于工资制度,行会也有规定。学徒只供食宿,没有工资。帮工的工资水平和发放工资的日期都有规定,禁止超过标准支付额外的工资或奖金。工资一般实行日工资制或周工资制。由于计件工资会增加产品数量,加剧竞争,所以许多城市禁止采取计件工资制,只是后来由于瘟疫流行,城市一度缺乏劳动力,计件工资制度才被某些部门采用,即使如此,计件工资的支付标准仍然统一规定。此外,行会还禁止行东们采取任何形式的联营或合并,以防止大型作坊的出现。
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限制竞争措施的作用,要有历史的分析。在城市兴起的初期,这些限制竞争的措施对城市的稳定与发展,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定,以及对效率的增长,都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互助共济精神在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行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后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这种限制竞争的措施束缚了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它们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抵触的,从而这些限制市场竞争的措施便逐渐被摒弃。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互助共济精神?如果说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之初,带有互助共济性质的城市组织经济生活的措施、行会限制竞争的措施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对互助共济精神应当予以肯定,那么到了中世纪西欧发展的后期,当这些措施已经阻碍技术进步,阻碍效率增长,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抵触时,是不是认为互助共济精神过时了呢?不能得出这样的论断。限制竞争的行政措施过时了,但这不等于互助共济精神的过时。
前面已经谈到,人们的互助共济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它出于对他人的同情心和对社会的责任心,因此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而不要求有什么回报。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政府或团体会实行一些措施,目的在于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免于饥饿,尤其是使贫困的家庭不致于无法生活下去。对中世纪西欧城市采取的有关措施,应当结合这些措施的目标来进行评价。
然而,对任何政府措施或团体措施的评价,包括对中世纪西欧城市当局的措施和行会这样的团体的措施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孤立地进行。当中世纪西欧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当局和行会的措施已成为生产力发展与效率增长的障碍时,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措施丧失了那种积极作用而变成了过时的东西,摒弃它们是必然的。但这只是表明具体的政策措施的过时,互助共济精神作为道德力量的一种体现,是不会过时,也不应消失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的互助共济精神可以而且应该体现于另一些与现代相符的形式。如果认定只有以往那种政策措施才能体现互助共济精神,从而不准备改变过时的政策措施,那是一种误解,其结果必定是互助共济精神的扭曲。历史条件变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可变,互助共济精神则会长存。
克鲁泡特金在其名著《互助论》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写道:国家吞没了一切社会职能,这就必然促使个人主义得到发展。对国家所负义务愈多,公民间相互的义务愈来愈少。在中世纪,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行会和兄弟会,两个“弟兄”有轮流照顾一个生病的弟兄的义务;而现在呢,只要把附近的贫民医院的地址告诉自己的邻居就够了。在野蛮人的社会里,当两个人由于争吵而斗殴的时候,第三个人如果在场而没有劝阻,致使它发展成命案,这样的行为意味着他本人也将被当作一个凶手看待。但是,按照现在的一切由国家保护的理论来说,旁观者是用不着去干涉的;干涉或不干涉,那是警察的事情。在蒙昧人的土地上,在霍屯督人中,如果在吃东西之前不大叫三声,问问有没有人来分享,就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而现在,一个可敬的公民,只要缴纳济贫税就够了,他可以坐视饥饿的人在挨饿[6]。
应当指出,克鲁泡特金的这段论述虽然相当精彩,但却犯了感情胜过理性分析的通病。国家行为是一回事,民间的互助共济行为又是一回事,二者是不可混淆的。互助共济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而且这种精神会一直存在下去,只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强烈些,在另一些情况下较弱而已。国家的政策措施则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调整,不能不顾客观情况而照搬以往曾经采用过的办法。
克鲁泡特金在这里一共举了三个例子:中世纪的,野蛮人的,蒙昧人的。
关于中世纪的例子,可以这么说,这里所提到的是团体(行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行会让成员们轮流照顾患病的成员,这属于互助共济的行为,而且同成员们出于互助共济精神而愿意承担这一义务有关。在行会解体以后,这种精神是应当保存下来的,关于人们采用什么方式来照顾患病的邻居或同事,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能认为必须沿用行会实行过的那种办法。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行会的解体与时代的变迁,互助共济的精神淡薄了。这才是应当注意的。
关于野蛮人的例子,可以这么说,克鲁泡特金把法律与习惯,或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弄模糊了。在野蛮人那里,法律尚未出现,只能按习惯或道德原则来处理,所以当两个人发生斗殴时,如果在场的第三人不出来劝阻,就要受到习惯或道德的制裁。这体现了互助共济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野蛮人中间是被人们遵守的。然而,在政府形成并有了法律之后,情况便不同了。命案照例应当由警察部门去处理,不能再像原始社会那样按照部落的习惯来处理,否则社会反而会变得无秩序。在场的第三个人的劝阻与否,不能视为是否把他定为凶手之一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个人可以袖手旁观或见死不救,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第三个人应当前去劝阻,因为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关于蒙昧人的例子,可以这么说,在蒙昧阶段,众人分享食物是正常的,当时的习惯或道德规范正是如此。假定在现代社会仍要照搬霍屯督人的做法,不仅是行不通的,而且也有可能给社会的分配秩序与消费生活增添麻烦。难道现在能做到在吃东西之前大叫三声要周围的人来分享么?一个人应当关心饥饿的人的生活,但现代有现代的做法,怎能沿袭原始社会的习惯?
由此可见,互助共济的精神要保持,要发扬,而互助共济的形式则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
收稿日期 1999—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