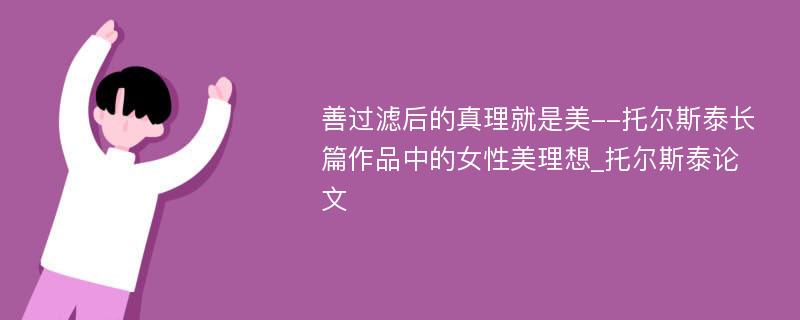
真经过善的过滤就是美——托尔斯泰长篇创作中的女性美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长篇论文,理想论文,女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分别代表了托尔斯泰三个时期创作的最高峰,体现了其世界观转变前后的精神历程。从女性审美的角度考察这几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注入了托尔斯泰对于女性美的一种比较恒稳的理想。本文拟对此作一粗浅探讨,以窥其丰富而具个性的精神世界之一斑。
一、“美——就是我们感到可爱的东西”
翻开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那么多可爱动人的女性形象活跃于眼前,使人难以忘怀:娜塔莎、玛丽、桑妮亚(《战争与和平》)、安娜、吉提、杜丽、瓦伦加(《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玛丝洛娃(《复活》)……她们以其欢笑、哭泣、爱情和痛苦,奏响一首女性交响曲,展示出女性世界的全部奥秘、风韵和光彩。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对他所钟爱的女性的肖像多作简约、朴素的神态描写,而绝少渲染其感官肉体之艳丽。他笔下那些可爱的人物单就长像来说甚至不够完美。玛丽王爵小姐就不用说了,托尔斯泰在很多地方直接描写道:这位可敬可爱的王爵小姐的脸和全身都十分“难看”。多方改变那张脸的配置和装饰,既使给她穿上最时髦的衣服,也不过使她“在这种打扮下非常难看,比往常更难看”。既就是最可爱迷人的娜塔莎、安娜,也并非毫无缺陷的“美人儿”:娜塔莎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是一个“黑眼睛,大嘴巴,不漂亮,但是富有生命力”的小姑娘;在作品的结尾处,她“长胖了,也长宽了”,不过是“一个强壮的、俊秀的、多产的女人罢了”。托尔斯泰这样描写渥伦斯基和安娜的初遇:渥伦斯基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漂亮,也不是因为她全部姿态上的端丽和温雅……”。比较起来,托尔斯泰贬低的爱伦倒是一位地道的艳妇。托尔斯泰多次写道:她有“同一不变的笑容——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的笑容”,经常裸露的“雪白的”肩、背、胸、“光泽的头发”、“古希腊式的异常美的身材”,是一个“既聪明又可爱的艳妇人”。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前者比后者给人的感觉更美好,更可爱,甚至前者使人回味无穷,后者令人厌恶。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先后同爱伦和娜莎塔结合。当他看出爱伦“用衣服遮起来的身体的全部诱惑力”的同时,当他对她说“我爱你”的时候,他却感到羞愧,感到“她在我内心引起的感情中,有一种恶心的东西,有一种不对的东西”。而当他向娜塔莎求婚时,尽管娜塔莎的那张脸在一系列挫折后已变成“冷冷的、瘦弱的、苍白的,看起来老了那么多”,然而“彼埃尔灵魂中一点也没有他对爱伦求婚时苦恼他的灵魂的那种东西了”。“他的心这时充满了爱,由于他无缘无故地爱那些人,他发现了爱他们的不可争辩的缘故”。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尼古拉为玛丽小组那种“特殊的精神美”所吸引,忘记了她那“难看的脸”;而当绝色佳人爱伦坐在莫特马尔子爵面前听他讲故事时,“子爵耸起一双肩头,垂下了眼睛,仿佛被一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吓住了”。
这种审美感觉中的“错位”现象,恰好应证了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美,就是我们感到满意可爱的东西。说它和悦可爱不是因为它秀美漂亮,而说它漂亮秀美,却是因为它和悦可爱。”〔1〕尼古拉对他太太概括得更为简明:“可爱的不是美”。对“美”和“可爱”的这种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表明,托尔斯泰的女性美理想绝不是停留在庸俗低级的感官满足上,而是属于一个更崇高、更内在、更诗意的层次。
二、“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
人,特别是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那么,这份可爱从何而来呢?托尔斯泰通过安德列1809春天的心理变化,深刻形象地揭示了这个女性之谜。在战争中虚荣心幻灭,丧失进取精神和生活信心的安德列,在视察田庄的路上看见一棵枝杈断裂,斑痕累累的老橡树,它又一次勾起了安德列的绝望:“我们的生命已经完了。”但是,随后邂逅“活泼而欢笑”的娜塔莎,听见了娜塔莎在月明似昼的春夜想飞出窗外的心曲,再看那棵老橡树,“那些结节的手指,多年的疤痕,旧时的疑虑和忧愁,一切都不见了。”它“展开一个暗绿嫩叶的华盖”,使得安德列陡然起了“一种欢喜和更新的不可理解的春天感”,唤起了他再度在人生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愿望:“不,生命在三十一岁上并未过完!”可见,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女性之可爱是“生命”、“春天”、“希望”和“更新”的同义语,女性的魅力来自一种能够唤起人对生命、生活的信念和热爱的力量。仔细考察他笔下那些可爱的女性,不难发现他正是把“可爱——美”和生命力的有无、生命力之充沛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托尔斯泰对于安娜那种“被压抑的生气”的描写是脍炙人口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地隐藏住她眼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在托尔斯泰对那些可爱的女性的肖像描写中,他所着力的那些特征无不流露出这种生命力。如娜塔莎的“黑眼睛、大嘴巴”、“容光焕发的脸”和“响亮的大笑”;安娜那变化多端的“颤粟的”、“起了大火”的眼睛、坚定敏捷的步伐、富于精力的紧握;卡秋莎那“青春的红晕”、“乌黑的眼睛”、“雪白的连衣裙、浅蓝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的鲜红的蝴蝶结”……这种蓬勃的活力洋溢在那些可爱动人的女性的全身,成了其女性魅力的一个显著标志,使得那些颇具眼力的男人们觉得“非再看她一眼不可”。
“爱醒了,生命也就醒了”。在托尔斯泰笔下,生命力就是“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意愿,就是个性、情感的坦露。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天性的最大限度的表露和满足。生命力的开放和凋谢尤其与爱情的到来和消失紧密相伴。娜塔莎最有生气因而也最动人的时候,是她煞有其事地和包里斯“接吻”的时候,是她第一次参加舞会和舞场上的每一个人“恋爱”的时候,是安德列寄宿她家的那个春夜,是她为阿那托尔的漂亮多情而晕眩的时候。在她已与安德列订婚却不得不忍受离别的孤独时,“她的神情有了变化,正如一个久病的孩子痊愈时改变了面部的表情”。当安德列死去,爱情消失在天国时,她“变瘦了,变苍白了,身体方面软弱得她们都谈论她的健康。”然而当她最后一次邂逅彼埃尔时,“一种隐藏的、她不知道的,但是压不下去的东西在她的灵魂中觉醒了。”这就是爱情。这种新的爱情使“她的脸、走路的样子、神情、声音都突然改变了……一种生命力和幸福的希望升到表面上来……一种熄灭了很久的光又在她的眼中照耀。”仿佛一种重复似的。和渥伦斯在一起,安娜的眼睛里闪烁着“颤粟的”、“黑夜中大火般”的光辉,而一旦回到她厌恶的卡列宁身边,“火好似已在她的心中熄灭,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即使是玛丽这样外貌奇丑的人,“从劳斯托夫进来的时候起,她的脸突然起了变化。好像在一只雕刻的彩绘的灯笼里点上了一盏灯,灯笼里边先前似乎黑暗、粗糙、没有意义的那复杂而精巧的艺术工作,突然以出乎意外的惊人的美出现了。”
托尔斯泰写了许多可爱的女性,其优美迷人的程度却不一样,给人的印象深浅和震撼大小也各不相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她们生命力之充沛程度有别,具体表现为爱的激情、力度、勇气有所不同。托尔斯泰塑造的可爱的女性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精神生活出类拔萃,为了爱情不惜代价地进行追求斗争的女性,如安娜、娜塔莎;第二类是恪守妇道,富于自我牺牲的女性,她们不同程度地渴望爱情,但又不同程度地受性格或传统观念的束缚,这样或那样地抑制甚至扼杀自己的热情和生活权利,如玛丽、桑妮亚、吉提、杜丽、司塔尔夫人、瓦伦加小姐等等。对第二类女性,托尔斯泰在肯定其对于家庭、社会稳定的意义的同时,又不无遗憾地借娜塔莎对桑妮亚的评价来概括她们是“一朵不结果的花”。而这类女性显然不及安娜和娜塔莎光彩夺人。娜塔莎和安娜是托尔斯泰笔下最富有生命力因而也最有魅力的人物。她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己生活的欲望十分迫切,爱与恨的体验和表达也异常强烈。娜塔莎一旦陷入爱情就“觉得那么温柔,那么多情,单是爱人和知道被人爱在她是不够的,她要立时、立刻,搂抱她所爱的人,说出并从他口中听到她满心的情话。”同样,安娜一旦发现了自己家庭生活的虚伪和屈辱,她就要摆脱它,争取新的生活,即使为此失去拥有的一切也在所不惜。当渥伦斯基对她开始厌倦、冷淡的时候,当她感觉到阅读、写作、英国式的家庭都不过是一种吗啡,自己不过是在拖延着一种结局的时候,她就不能再自欺欺人地活下去,毅然投身车轮下,亲手熄灭了自己的生命之火。作为一个孤立无助的女人,安娜在对整个敌对社会争取爱的权利、生活的权利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勇气、坚定和清醒达到了顶点。因此,她成了托尔斯泰笔下最激动人心的一个人物。“比他人更炽热地燃烧自己!”西蒙·德·波娃的这句铭言,再好不过地概括了娜塔莎、安娜这一类女性独特隽永的气质、风格。正是在这种更炽热的燃烧中,生命显示出异常的绚丽、壮美。
热爱生活,追求爱情是人类的天性。托尔斯泰把生命力作为女性美的标志,恰好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本质”。于是,美和真联系起来了。在这里,托尔斯泰的审美观已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美是生活。”〔2〕
三、“那是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的更崇高的境界。”
“比别人更炽烈地燃烧自己!”这是不是说,女人只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满足自己的热情、欲望,就可以使生命之树长青,因而可爱动人呢?
爱伦恐怕是托尔斯泰笔下最放纵的一个女人了。但是,正如彼埃尔所想:“爱伦除了关心她自己的身体以外,从来不关心别的。”在国难当头,全民参战的时候,爱伦却为不能同时嫁两个男人而痛苦不堪,饮鸩自杀。而且,对于自己的淫荡堕落,爱伦从未露出“些微迟疑、害羞或掩盖的形迹,”相反,却总是带着“习以为常的镇静和满足。”对这个女人,彼埃尔的看法是:“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中的一个。”托尔斯泰又借拿破仑之口对她下了一个准确的评价:“一个超等动物。”相反,难看而羞涩的玛丽却以她“特殊的精神的美”令古怪拉感动,她那“全部精神世界的深度”,对古尼拉成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可见,构成女性魅力的生命力绝不是一种原始的、野性的欲望的横流,而是和“精神世界的深度”相联系的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正如吉提对安娜的感觉:她的内心有“另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的更崇高的世界,那是吉提所望尘莫及的。”
这个“更崇高的境界”是什么?努力探讨人生价值的彼埃尔的一段思索也许可以作一个注解:“现在,被自己的感觉所支配的人应该在美德中找到感觉上的快乐。热情是不能根除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使热情朝着高尚的目标去发展,同时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在美德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热情”。在托尔斯泰心目中,这个使女人变得“惊人地美丽”的“更崇高的世界”正是真(热情)和善(美德)的浑然一体,是人的自然天性和社会伦理观念的完美结合。一句话,美是真和善的统一。这一审美观充分体现在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中,他也正是根据这一标准对其进行审美评价的。
在彼埃尔向娜塔莎求婚的前夕,娜塔莎发现他“变得非常清洁、光滑和新鲜”,好象他刚从一间“道德的浴室”里出来。同样,在和安娜的爱情达到高峰时,渥伦斯基也变得认真、严肃了,甚至能够为爱情付出一些牺牲(虽然有限)。在长篇创作中,那些可爱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使她们的爱慕者道德更新的力量。由此看来,在托尔斯泰的理想中,“美是真和善的统一”首先是指情感热烈和道德纯洁的完美结合。他笔下那些可爱的女性正是由于这个契合点上显出其可爱动人的。
少女卡秋莎和青年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里面没有一点“在肉体上占有的欲望。”那个时候的卡秋莎象她送给聂赫留朵夫的香皂和手巾一样“洁净、新鲜、惹人喜爱,”因此,那个初恋的夏天在聂赫留朵夫和读者心中是“一种美丽、珍贵、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可是,当她为了十个卢布向第一个摧残她的男人“妖媚又可怜地微微一笑”时,聂赫留朵夫痛心疾首地感到“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这时那张原来亲切可爱的脸变成了“饱经风霜的脸”,“仿佛储存在地窑里的土豆的新芽。”最后,当她在和革命者的结合中“复活”,恢复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活时,作家写道:她的“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原先那种卖弄风情的味道了。”这个时候的玛丝洛娃又重新给聂赫留朵夫,也给读者一种美好的感觉。托尔斯泰对于玛丝洛娃不同时期面貌的褒贬正是依据其道德的纯洁与否这一标准进行的。
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笔下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女性。平心而论,娜塔莎的举止行为并不是那么合乎规范和逻辑的。伴随她的常常是“一片碰椅子和倒椅子声”、旁若无人的大笑和号啕、和这个人那个人不断的“恋爱”。她甚至被阿那托尔这个漂亮的混蛋所迷惑,要毁去和安德列的婚约与其私奔,以致酿成一生的大错。然而,既使如此,娜塔莎也绝不给人淫荡的感觉。这是因为托尔斯泰准确而精妙地揭示了这个半是孩子半是姑娘的少女那种纯洁、稚朴、率直的心理性格特征,描绘了她特有的那种“处女的新鲜味”、那种“尚未熟练的天鹅绒般的柔滑感。”人们从她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过多的温情、对自己和他人过多的爱,而毫无矫揉造做和心计打算。更重要的,在娜塔莎的爱情寻追和迷惘中,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把感情和道德、热烈和纯洁协调一致的动机。娜塔莎真正爱过三个男人:安德列、阿那托尔和彼埃尔。安德列高尚、博学,却过于理智、严肃,所以对这桩婚事,娜塔莎及其一家虽然满意,却同时有一种拘束的、不自然的甚至是畏惧的感觉。正是这种热情上的距离埋下了娜塔莎变心的根子。当热情逼人的阿那托尔出现在面前,娜塔莎被诱惑就在所难免了。然而,尽管阿那托尔的热情令娜塔莎满足,但“没有她时常感到的横在她和别的男人们之间的那种礼法的遮栏”这个情况又使她发慌。于是,她陷入了是爱安德列还是爱阿那托尔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对前者精神品质的爱和对后者肉体的爱“为什么不能两全呢?”“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才是幸福的。”彼埃尔恰好弥补了安德列和阿那托尔的偏颇:纯洁而热情,富于思想而性情温和。因此,和彼埃尔的结合是最符合娜塔莎理想的生活。也只有在这种完美无缺的结合中,她才能不再苦恼,不再三心二意,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家庭的贤妻良母。正是由于引起情变的这种内因的合理性,才使得娜塔莎的闪失不但不减其魅力,反而更衬托出她青春的蓬勃和爱情追求的深度。
安娜是托尔斯泰笔下最有力度的一位女性。是什么使得这位“抛夫弃子”的“堕落女人”显出一种鹤立鸡群般的高雅、优美,使得跟她有不同关系、对她抱不同态度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出色、可爱、逗人怜喜的女人,”甚至她的情敌吉提也不得不承认,安娜的美的境界是她所望尘莫及的?正是因为安娜那深刻而纯洁的精神、道德力量。安娜的全部追求与反抗都指向一个目标:弃绝在虚伪里游泳,争取一种把爱情与婚姻、母爱、责任统一起来的真正清洁而道德的生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听厌了人家称赞她贞洁的话,”意识到安娜这种“维持式的不顾死活的热情”和上流社会藏奸养汉、偷鸡摸狗的二重生活格格不入,彼得堡上流社会三个集团才沆瀣一气,忙不迭地将一把把脏土掷向安娜,对她关闭大门,并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同样,安娜全部思想行动中的严肃性、合理性、人道性由此而来;她所特有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光辉、那种令人眩目的悲剧审美色彩由此生发。
在托尔斯泰的理想中,“美是真和善的统一”还指爱自己和爱别人的完善结合。他也正是从这个契合点上展示女性可爱动人,并根据这一结合的完美程度对人物进行褒贬的。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塑造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最美丽的爱伦“除了关心她自己的身体以外,从来不关心别的。”因此,在托尔斯泰眼中,她毫无美感可言,玛丽和桑妮亚是一种理性过重的人。尽管托尔斯泰对她们(尤其是桑妮亚)压抑感情,不敢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生活及其“不结果的花”的结局不无惋惜、遗憾,但由于她们的自我压抑和牺牲是建立在对别人的爱的基础上的(桑妮亚是为了罗斯托夫家族的幸福和重振;玛丽早期的自我压抑则是因为她觉得“基督徒的爱、对邻人的爱、对仇敌的爱”比起“一个青年人好看的眼睛在一个风流少女心中所能引起的感情”来,似乎更有价值、更美好),因此,在托尔斯泰笔下,她们虽有缺陷,却不无可爱之处。
娜塔莎的完美在于她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了。如前所述,在展示和满足自己作为女人的天性方面,在追求个人幸福方面,在珍爱自己方面,她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她从不压抑自己的个性,乐于在一切富于刺激和情调的场合释放激情和才华,在爱情追求上也异常热烈和投入。她爱自己甚至爱到忍不住以第三者的身份从镜子里欣赏自己、赞美自己。她的生命之花的确开放得蓬勃、绚丽,然而,娜塔莎绝不给人一种轻佻放荡之感,绝不让人讨厌。相反,这一切(包括她在爱情上的闪失)无不呈现出一种青春的光华和浪漫诗意。除了上述道德纯洁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她自然而然地、化为本能地把对自己的爱同对别人的爱结合起来,把人人都幸福作为自己幸福的一个条件。她的热情、她的胸怀是对所有的人、整个的世界敞开的。在出场中,她本是旁若无人地附在母亲怀里大笑,但一发现索妮亚不在就立刻出去寻找,当她看见索妮亚在哭泣时,便也大哭起来;安德列死了,她觉得自己也死了,可是,当听到母亲因为幼子丧生而发出的疯狂叫喊,“她立刻忘记了她自己和她自己的悲哀,”用那“不屈不挠的爱心”,“让母亲苏醒过来”;对仆人,她和蔼可亲,主仆同乐的游猎、歌舞晚会使她流连忘返;她亲近热爱大自然,那个月明似昼的春夜,她几乎融进了月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特别感人的是,在拿破仑入侵,举国抗敌的日子里,娜塔莎这种要求个人幸福同他人幸福相结合的理想扩展了、升华了。那个著名的“蛋教鸡”的故事——说服母亲腾出马车运送伤病员表明,娜塔莎实际上是把个人幸福同整个俄罗斯民族利益联系起来了,把自己充沛的活力、热情汇入了祖国解放的洪流中。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一如月光融进了夜色。正是这种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每个俄罗斯人息息相通的气质,使娜塔莎成了托尔斯泰笔下最惹人喜爱的、最诗意的女性。“家中没有人象娜塔莎那样支使人或给他们那么多麻烦……但是家奴们执行任何人的命令也没有象执行她的命令那么心甘情愿。”托尔斯泰是把她作为一个完美的标本来塑造的。
以这同一标准,托尔斯泰对于安娜的评价就矛盾得多。一方面,从肯定人的天性和生活权利出发,她让安娜喊出了“罪不在我,我是个活人,我要爱情。”他同情安娜没有爱情的遭遇,肯定了她为爱和生活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的合理性、纯洁性,并把这一斗争提高到和整个社会对立的高度,从这种力量的悬殊对比中,表现出安娜那使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崇高、优美。就追求个人生活权利、追求人个幸福的力度和深度来说,安娜超过了托尔斯泰笔下所有的女性,甚至超过了娜塔莎。另一方面,安娜对个人幸福和生活权利的追求,却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客观上造成了“抛夫弃子”的局面,造成了周围人的“不幸”(尽管她更不幸),这就违反了托尔斯泰的审美标准。从这一点出发,托尔斯泰在极力描绘、揭示出其优美、端丽和高贵的同时,又赋与其某种“残酷”、“象黑夜中的大火”一样可怕的眼神——“灵魂的表情”;在同情她、肯定她的同时,又让她背负着“抛夫弃子”的十字架,经受着一个“坏女人”、“堕落的女人”的心理折磨,在车轮下受到惩罚;另外,托尔斯泰还专门安排了杜丽、吉提这样一些为了家庭的安定而忍辱负重的贤妻良母形象及其幸福、美满的结局,来和安娜对照。
这里,托尔斯泰的女性美理想不只限于真,而且和“善”联系起来了。“任何事物,凡是我们 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3〕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论断又不谋而合了。
托尔斯泰的女性美理想是一种全面的和谐:外表和内心、热情和道德、个人和家庭、社会的完全统一协调,其核心是真和善的统一。
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托尔斯泰的女性美理想中明显地存在着积极与消极、进步与保守的矛盾,这种矛盾尤其体现在他对“善”的理解上。
一方面,重视个人幸福,为了满足人的天性和捍卫生活权利而斗争,纵情展示生命之力与美,追求精神生活的崇高,珍爱自己并关注他人,这些都属于托尔斯泰的“善”的范畴,是他极力肯定和赞赏的。这表现出托尔斯泰深厚的人道主义、纯洁的道德面貌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把对待卫国战争的态度、接近自然和人民的程度,作为“善”的一个具体内涵和准则,将娜塔莎全部魅力展示在她的纯真和这种“善”的融合中;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把安娜的爱情追求提高到向专制制度及其上流社会争取生活权利的高度,揭示出这个“坏女人”的“堕落”中合乎人性的真善,让她无穷的诗意和神韵由此生发,从而反证出专制制度及其上流社会扼杀人性的“伪善”;在《复活》中,让玛丝洛娃在与革命者的结合中精神“复活”——重归于善。在这里,托尔斯泰对“善”的理解及其女性美理想已经和他的俄罗斯气质即深刻的民族性和民主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了。而这一切,在专制农奴制解体,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安排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无疑是顺应了历史趋势,体现了时代精神的。
另一方面,和他的全部观点、学说一样,托尔斯泰“善”的观念中,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法式农民世界观的烙印。从宗法式农民立场出发,他反对妇女解放,反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在赋予“善”以某些确切的伦理内容的同时,他又将其夸大、抽象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永恒的道德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并据此不分清红皂白地认为一切胆敢破坏家庭的举动都是不道德的,有罪的,必将得到来自“天国”的报应。从上述对女性(尤其是对安娜)的审美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善”的观念及其女性美理想中违背历史方向的这一面。
然而,正如列宁所言:“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 ”〔4〕不断前进变化的生活真理最终超越了托尔斯泰“永恒的道德原则和宗教真理”,他的“善”的观念及其女性美理想中积极进步的一面最终压过了消极落后的一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他的笔下,安娜这个本要受到“上天”惩罚的负罪者,终于成了作者热情讴歌的超乎罪恶之上的美丽女神。由此,显示出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伟大,也使其以真善为核心的女性美理想瑕不掩瑜,获得了永久的生命。
注释:
〔1〕转引自雷成德等《托尔斯泰作品研究》第290页。
〔2〕〔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第575页。
〔4〕《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3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