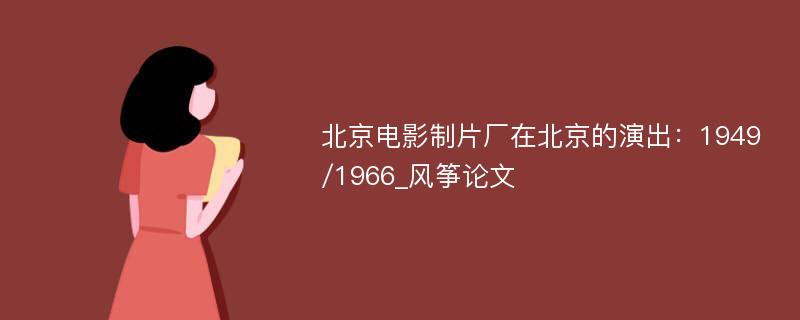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北京呈现:1949-196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电影制片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3)02-0083-07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电影和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互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不厌其烦的表现着这座城市,弄堂、南京路、咖啡馆、舞厅、剧院、爵士乐等成为重要符号,穿洋装的老板、穿旗袍的交际花、衣衫褴褛的贫苦大众粉墨登场,人物和环境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标识。老上海电影中的上海,已经不仅仅是电影发生的空间背景,更直接参与到了电影的叙事,老上海电影成为上海这一马赛克型现代都市的映像。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成为新政府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为“工农兵”服务的不二法则使战场、农村成为新中国电影的豪迈背景,城市沦为一小配角。老上海成为资产阶级的近义词,新上海以社会主义的全新面貌出现,割断了和昔日的脐带。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取代上海成为中国最核心城市。新中国电影必然要对北京进行书写,对于身处首都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来说,这份书写便显得更为重要。在“十七年”期间,北影厂的确对北京进行了超越其它制片厂的书写。
一、北平的革命历史书写
1950年,在北影厂出品的第一批故事片中,《民主青年进行曲》是一个发生在北平的故事,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北大物理系学生方哲仁在“五·二〇”事件前挣扎彷徨,最后转变走向抗争的故事。主角方哲仁由曾经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的著名演员孙道临饰演。由于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北平,影片拍摄得到了北京诸多高校的支持。“为了拍摄青年学生在‘五·二〇’的反内战及反饥饿运动等巨大场面以及学生们当时的生活,学习的真实镜头,曾得到‘北大’师生们的极大帮助,并且由他们直接参加了演出。”[1]影片开始便是北大学生在广场上举办纪念“五四”的营火晚会,由谢添饰演的宋教授发表演说,他控诉国民党发起内战,号召同学们继续斗争。在演讲中插入的纪录片画面展现的是一个残酷政府统治下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晚会之后,方哲仁和女友宋蓓华(姚向黎饰)送宋教授回家,胡同里有一家人,在听到巡警的声音后,母亲赶紧哄孩子,不让他哭出声,这是全片少有的对北平市民生活的展现。影片最后插入了北平解放的纪录片画面,百姓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北平,五星红旗升起。方哲仁和同学们穿着革命装幸福地走在街道上,前面打着建设新中国的标语。影片通过方哲仁的改造和转变之路将1947年席卷全中国的“五·二〇”学生运动浓缩于北平,开始建构北平的革命历史。
1959年摄制的《青春之歌》是国庆献礼片,是北影厂的大制作。在北平的革命史上,1935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无疑是浓重的一笔。《青春之歌》便将林道静个人的故事缝合到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1959年3月初,恰逢北京降雪,摄制组就在北京前门外地区抢拍下了雪景的戏。“3月15日,这部影片正式开拍,已经拍摄了许多内景场面。摄制组还在北京的鼓楼大街拍摄了特务逮捕戴瑜的外景;在北京的故宫一带拍摄林道静与余永泽在河边会面的外景;在北京的崇文门外一带拍摄了‘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的大场面”。[2]全片第一次对北平的大规模表现是林道静在北平火车站遇到了南下示威请愿的学生,这场戏的外景场地是在西直门外火车站,拍得气势恢宏,在这部北影厂斥资三十万打造的大片中,不乏这样的大场面,其中气势最宏大的一场戏是影片最后的“一·二九”示威游行,但是参加拍摄的群众就有一万余人。“拍摄那天,电车到崇文门就停住了,原来为了拍电影,从崇文门到花市大街南口这一段的交通都已断绝……出了城门,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世界,整条大街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崇外百货商店的门前换上了‘华祥绸缎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还有许多富有时代特征的招牌和广告也都挂出来,有‘裕大钱庄’、‘典’、‘当’,还有‘仁丹’、‘老刀牌’的广告。红、白布的幌子迎风招展,‘王麻子’大剪刀模型在铺子门前叮当作响,接头还摆了几辆破旧的人力车……这杂乱破旧的市容,立即在我眼前展现出一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图景”[3]。这场戏的拍摄得到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等各部门的支持,断绝了前门外的交通达一天之久,街道组织动员了两三千市民群众穿着自己的长袍大褂来当群众演员,还有两千名部队的战士和学校的学生参与拍摄。拍摄时候除了汪洋等北影的领导之外,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市委文化部副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交通处长、区委书记等组成一个现场总指挥部,这样的拍片气势可谓空前。
《青春之歌》的外景戏,仅是北京就是60多处。影片在革命叙事中不时呈现出北平的风貌,如林道静与余永泽会面时的故宫一带河边,林道静走在城墙下以及林道静和王晓燕及江华谈心时候的颐和园和北海,观众也随着林道静看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北平。全片定格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也让北平这一革命青年的战场变得更加宏大壮阔。
拍摄于1962年的《停战以后》进一步凸现了北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位置。1946年春,共产党与国民党签署了停战协定,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一面进行和谈,一面在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直接参与下,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停战以后》即是表现这一事件的政论性极强的故事片,而且极力打造了那一特殊年代的北平。
影片采用的是倒叙结构,一开始就是一个现代的北京城的展示:伴随着昂扬的音乐,汽车在宽阔的北京街道上行驶,空间广阔,影调明亮,最后汽车到达了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偶遇于此的昔日中方谈判代表顾青(张平饰)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李国卿(项堃饰),故事由此开始。顾青下火车后看到了抗战结束不久的古城北平,此时的北平在古老城楼的遮挡下形成了逼仄的镜头空间,国民党军队的卡车飞机制造出强大的噪音,大街上满是乞丐劳工,老北平城街道窄小而压抑。影片拍摄时,群众演员在北京铁路工人俱乐部剧场扮演走出“北平车站”的旅客,“根据戏的要求,他们都进行了不同的化妆造型。有的化装成脑满肠肥、服饰华丽的国民党的党棍要员,有的化装成油头粉面、西装笔挺的豪绅市侩,有的装扮成耀眼的‘小姐’、‘太太’,还有那身着军服面目可憎的反动官兵、警宪;也有的扮成褴褛不堪、衣不蔽体的贫苦市民,还有旧时代车站上特有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这里形形色色,反映出了当年北平车站景象。”[4]由于故事设计了燕京大学教授谢宏(梅熹饰)这样一个角色,影片中有不少镜头是在北京大学校园拍摄,博雅塔、未名湖的风光亮相于银幕,传承这一高等学府的民主传统。
在《停战之后》拍摄之时,北京的旧城改造已经开始,许多老建筑已被拆除。“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创作者也力求做到真实可信、生动感人,所有外景都是在昔年历史事件发生地拍摄。为了恢复已拆去的就旧安街、三座门这些背景,特技摄影师张尔瓒、陈晨与特技美工师刘鸿文合作,利用照片与模型接景恢复了旧北京古老建筑的风貌:加置的牌楼、有轨电车、人行道……使40年代的旧京华得以再现。”[5]《停战之后》为“十七年”电影中的老北京完美定格。
《民主青年进行曲》、《青春之歌》以及《停战之后》都是选择了对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拐点处的北平来进行书写,如“一二·九”学生运动、国共谈判等,突出了北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三部影片涉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也让“五四”以来的民主、革命传统在这个古都承继。北平不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资产阶级都市,而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和历史底蕴的古都。
二、从北平到北京的意识形态更迭
新中国电影对北平的书写是以文华影业公司的石挥导演并主演的《我这一辈子》拉开的大幕。影片是由石挥的哥哥杨柳青根据老舍写于1937年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描写了一位在旧北京过了五十年苦难生涯的老巡警对自己辛酸一生的回忆。由于老舍是北京人,石挥有过北平生活的经历,所以影片带有浓浓的京味。影片主要表现了老巡警解放前的故事,结束于北京解放,老巡警在街头冻饿而死,这种旧北平有余而新北京不足的处理也为影片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重返北京,有感于这个城市和人民的变化,于1951年写出了话剧剧本《龙须沟》。新中国成立前的龙须沟是北京天桥东边、金鱼池西的一条有名的臭沟,1951年,在党与人民政府领导下,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决定要彻底挖修龙须沟。剧本通过一个小杂院4户人家的苦辣酸甜,写出了北京龙须沟一带劳动人民生活、命运的巨大变化,成功塑造了程疯子、王大妈、娘子、丁四嫂等人物形象,通过他们心态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激变和新旧社会对“人”的不同态度,表现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剧本成为一曲热情洋溢的新社会赞歌。1951年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龙须沟》搬上舞台,由焦菊隐导演,主要演员有于是之、郑榕、叶子、黎频等。话剧《龙须沟》的演出引起了轰动,首都各大报刊一片赞誉之声,周恩来亲自到剧院观看,并热情向毛泽东推荐,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
1952年,刚开始故事片创作不久的北影厂决定将话剧《龙须沟》改编成电影,由冼群改编并导演。在电影拍摄时,剧本中的那条臭水沟已经在旧城改造中填平,剧组不得不重新挖了一条沟,搭出了建国前那条臭沟的景。在演员选择上,以北影厂的演员为主进行拍摄,谢添饰演程疯子,“记得只外请了北京人艺的叶子担任丁四嫂,我(于蓝)担任程娘子这一角色。我们深入生活,积极准备,并已投入拍摄。谁知经过一段拍摄,厂里领导发现,由于演员语言缺少地道的北京味,难以达到原剧效果,决定暂停拍摄”。[6]在经过两个月的暂停调整,影片又重新拍摄,换上了以话剧版演员为主的主演阵容,于是之饰程疯子、郑榕饰赵老头、黎频饰王大妈、叶子饰丁四嫂,他们都在话剧中饰演过同一角色。有过北平生活经历的于蓝依旧饰演程娘子,丁四由张伐饰演,此外,牛犇(饰二嘎子),黄素影(饰孟大妈),封顺(饰冯狗子),田烈(饰黑旋风)等参与演出。
影片中的人物是一群在北平土生土长的下层百姓,北平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因此影片对北平进行了带有日常生活色彩的书写。电影开场便明确交代了三层空间:最外围的是龙须沟沿岸,两岸贫苦低贱的百姓辛苦地劳作,他们把生活垃圾全倒在龙须沟里,使得沟里的水粘稠浑浊;接着下起了大雨,雨水灌进了主人公们生活的小院,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地方,是第二层空间;镜头进入室内,屋顶漏水、墙壁四面通风,雨水一直漫到炕沿上,房子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镜头由龙须沟层层进入了人物的生活空间,电影由此展开叙事。
大杂院里的人有曾经是说唱艺人的程疯子,早年因他不给恶霸黑旋风唱戏被黑旋风手下冯狗子带人殴打,从此不敢再上台表演,整日闲在家里成了废人,一家生活全靠老婆程娘子摆摊卖香烟支撑。由程疯子的说唱表演,影片展现了天桥戏院的景况,借由程娘子摆摊,影片呈现了就北平街头的风貌。拉车的丁四老实忠厚,女儿小妞子是全院人的开心果。另外还有疾恶如仇的赵老头,逆来顺受的王大妈以及年轻的二春和嘎子。这是一群生活在北平最底层的人,他们受恶霸欺压不堪忍受却又无可奈何,被苛捐杂税层层盘剥生活拮据,但邻里之间关系和睦互相帮衬。由于原著作者老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对剧中人的生活极为熟悉了,这些人物被塑造得非常生动。影片的前半部分展现出了旧社会老北平人生活的常态,这一部分的结局小妞子风雨之夜淹死在龙须沟,旧社会的生活以悲剧收场。
大杂院的人们瞬间经历了天地玄黄的时代变迁,五星红旗的升起昭示了一个新时代代的到来。影片中的新时代开始于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此时的大杂院整洁干净,程疯子站在门口看见新社会的一点点变化:当铺改成了合作社,安上了自来水站,赵老头成为了区人民代表,二嘎子找到了工作,二春进了工厂,恶霸黑旋风和冯狗子遭到了惩治。程疯子做起了卖自来水的工作,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程宝庆。影片最后,政府填平了龙须沟,程宝庆在胜利大会上兴奋地歌颂新政府,全片在热烈的庆祝场面中结束。
为了直奔歌颂新政府的主题,影片的新中国成立后部分显得直露而仓促,极力彰显新北京较之旧北平的意识形态优越性。当时的评论也指出了影片在表现新旧北京方面的失衡:“电影《龙须沟》在艺术描写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生活写得很逼真,很动人。我们合上眼,便可以看见那漂浮着垃圾与死猫的黑水臭沟,下雨天臭水从门槛下向院子里倒灌,小妞子为了一条小金鱼的哭泣以及小妞子的死……可是后半部,解放了,艺术描写突然从生活的深处,浮到了现象的表面。这样,电影后半部的动人力量就大大的减弱了……用一些辉煌却是无力的词句,如‘人民政府真是救命恩人’、‘毛主席叫咱们抬了头’来代替了艺术的具体描写。后者用丁四嫂正包着饺子,丁四又提回了猪头大葱这样的镜头,来肤浅地歌颂新的生活”。[7]
《龙须沟》在表现旧日北平时是在细腻地描绘着一个城市,仅从影片的声音处理就可以感受到,如胡同里的吆喝声,车行里的收音机,铁匠铺的叮叮当当,满大街的叫卖声,这样的音响建构出一个城市和市民的日常生活。而在影片后半部很少能听到环境音响,主人公们似乎生活在了真空中,取代了音响的是欢庆热闹的音乐。焦菊隐指出:“剧本的后半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些镜头,失之于概念化,因而显得空洞无力”。[8]影片的旧北平部分是在书写一个城市的记忆,而新北京部分却是在唱一个国家的赞歌,影片前后的错位正在于此。《龙须沟》成为表现意识形态更迭的一个典型文本,其新旧北京的书写所折射出的问题也正是新中国电影在进行城市书写与国家书写时难以弥合的一个缝隙。
1952年,北影厂还完成了一部配合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一贯害人道》,影片讲述了徐凤生(姚向黎饰)及其父亲、姑妈在新中国成立前被一贯道头子王继善(李景波饰)蒙骗迫害,父亲、姑妈被杀害,而徐凤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新政府所拯救,改邪归正得到新生。影片的主题即控诉旧社会,歌颂新社会。较之《龙须沟》,《一贯害人道》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宣传文本,影片故事是发生在北京,但在表现旧北平时并没有细腻勾勒这个城市的生活和风貌。影片是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叙事,开始就展示了天坛、北海公园等北京符号,渲染新北京的新风貌,控诉一贯道的“一贯道罪证展览会”也是在中山公园进行。在《一贯害人道》中,新北京是新国家的意识形态表征,影片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无意进行城市书写,形成新旧对比的是社会,而非城市,这种对比彰显的是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优越性。
三、首都的亮丽明信片
“1955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了巴黎寄来的一封信,并附来一个影片故事梗概,寄信的人是罗吉·比果先生,他的信充满着热情,愿意为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贡献,影片故事是梗概,是用中国的‘风筝’巧妙地连接起北京和巴黎,连接起中、法两国儿童的友谊。虽然,我和比果先生不相识,但,这封信和影片故事梗概确实吸引了我,特别是他们的纯真的友谊和良好的愿望,自然并迅速地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于是,我们很快就回信同意他的请求,这部影片的合作就开始了。”[9]在文化部的统筹安排下,北影厂接受了和法国加郎斯艺术制片公司联合摄制《风筝》的任务,由长影借调的王家乙和法国的罗吉·比果联合导演。影片在巴黎拍摄时,北影的副厂长何文今以及导演王家乙和洗印技师王雄等都到了巴黎。1957年9月,法国导演以及几个小演员等都到北京参加拍摄。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合拍故事片,《风筝》不仅是中法友谊的一个反映,也要担负起宣传新中国的重任。《风筝》要宣传中国的形象、中国电影的水平。《风筝》以中法两国的首都北京和巴黎作为背景,故事讲述的是几个法国小朋友捡到了一只孙悟空形象的风筝,风筝里藏着的信告诉他们风筝是由中国的小朋友宋小青放飞的,他希望和捡到风筝的人成为朋友。宋小青的地址写在了风筝穗上,却被主人公比埃罗的好友培培尔撕下抢走了。当晚,比埃罗梦见孙悟空把他和妹妹尼高尔送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开始了寻找宋小青之旅。他们游览了美丽的北京,认识了一群乐于帮助他们中国小朋友,最后他们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宋小青,兴奋地醒来。第二天比埃罗向朋友们描述了梦中的北京:“那个国家可美了,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在那儿,街上的人可多了”!“比咱们这儿还多吗?”“当然,要多得多。“那里的人呀,都是有说有笑的,可好了,真是个美丽的国家”“人家走在我们前头了!”小朋友们都沉浸在对北京的憧憬中,最后培培尔主动归还了宋小青的地址,他们一起写了回信并再次把风筝放飞,向全世界的小朋友传达宋小青的信息。
《风筝》是一部明信片式的电影,着力展示新中国首都的美好形象。影片中的北京是一个社会和谐、风景如画的地方。比埃罗先到的是古代的北京,他看到了故宫里的王侯将相,并险些被皇帝杀头。在从紫禁城逃脱之后,比埃罗和妹妹到了现代的北京,这是一座空间感迥异于巴黎的地方:影片开始展现的巴黎是几个小孩奔跑在空旷的街道上,而在北京,大街上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处处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兄妹两人游遍了北京最美丽的地方:故宫、景山、北海、颐和园、天坛等,在景山的一个环摇镜头将北京城全景尽收眼底。相比之下电影对法国巴黎的风光并没有着重展示,只有几个航拍巴黎的镜头,但法国儿童的戏却被拍得很有趣味。相比之下北京的儿童则规规矩矩,无论比埃罗兄妹走到哪里,迎接他们的都是北京儿童的一张张笑脸,皮埃罗感叹:“今天,在故宫,在公园,在所有的地方,全北京的儿童都在帮我找朋友”。北京的小朋友们被塑造成了乐于助人的一群人,他们富于组织性纪律性——集合的时候会排着队走过来,找宋小青要通过广播站发动全北京的小学生参与行动,虽然友好但却不免呆板,没有哪个人物因为性格鲜明而被人记住,他们听话懂事,却丧失了可爱。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部展示新中国首都的风光片。
1958年完成的《探亲记》讲述了一位老农民田老耕(魏鹤龄饰)进北京城探望十多年未见的已在北京当副局长的儿子故事。影片最初是想走讽刺喜剧之路,但拍摄过程中“反右”运动开始,于是改弦易辙,将其“易容”为歌颂式故事片,影片中的北京也和腐败、堕落无关,呈现出社会主义首都风貌。影片是以进京的田老耕的外地人视角来表现美丽的北京:宏伟的天安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有故宫、北海、颐和园那些风景名胜。事实上,影片中对北京的展示并非从田老耕到北京的时候才开始,他在乡下和乡亲父老告别,大家都在托他给北京的熟人捎东西时,大家就已经建构了一个想象中的北京,那是一个军民鱼水情、群众干部一家亲的北京。田老耕踏上大路,《社会主义放光芒》的歌声响起,这一抒情段落给人无限憧憬,展示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这也是北京城的前奏,一乡一城两种风光各有千秋,都是新中国建设的成就。
“象征着北京,象征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红色的天安门,庄严而亲切地屹立着;上空,一朵充满阶级友爱和共产主义风格的银华——系着急救药‘二巯基丙醇’的降落伞,正张着伞朵,迎着六十年代的第一度春风,神速飞降;下面,无数无数双手,伸向天空,在迎接从北京送来的‘神药’。这是画家董希文给影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画的一幅电影宣传画。”[10]在1960年的热门影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决定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生命的药物就在首都北京,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心脏位置得以充分展示。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位于王府井大街上的“八面槽”是戏份颇重的拍摄点,挽回中毒民工生命的药品就出自设于此处的特种药品商店,解决夜间空投发光设备器材与焊接的五洲电料行、五金电器修理行都与之紧靠在一起。在影片中,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得到充分展现,北京的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城市,而是升华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
1964年,谢添、陈方千导演儿童片《小铃铛》延续了《风筝》的儿童梦幻旅程,调皮的小满在梦中和报幕木偶小铃铛在北京的上空飞行,看到了新北京的风貌,一派宏伟壮丽的如画风景,影片依旧打造着北京的明信片。同年拍摄的《青年鲁班》也是发生在北京,不过呈现的是北京的建筑工地。同年的《千万不要忘记》虽没有强调故事的发生地,但熟悉北京的观众还是能辨别出小楼外景是西便门的铁道部宿舍,不过影片旨在“阶级斗争”,而无意书写城市。
不管影片内容如何,《风筝》、《探亲记》、《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影片还是非常难得的在“十七年”银幕上留下了那个年代的北京,成为可以长久保存的生动的北京明信片。
标签:风筝论文;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北京电影制片厂论文; 一贯害人道论文; 龙须沟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文艺电影论文;
